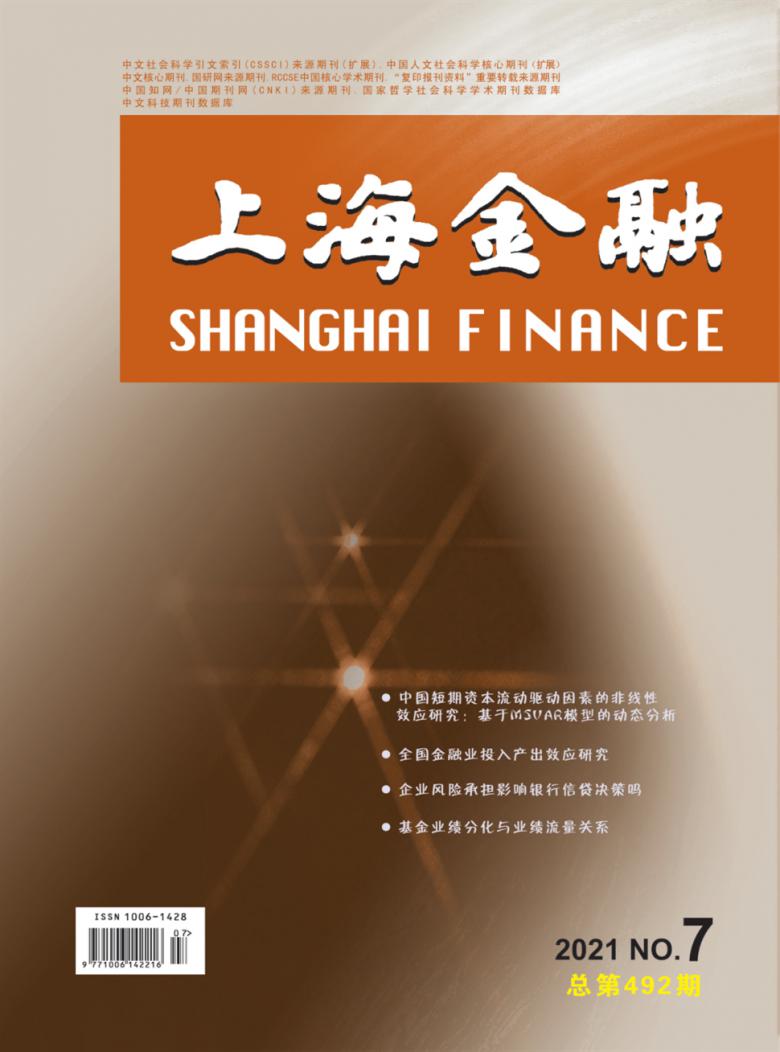現代性與近代以來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危機與重構
佚名
注釋;
[1] 現代性是一個十分復雜的概念,我們在本文中強調制度變遷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主要是接受了吉登斯的概念,即:“它首先指在后封建的歐洲所建立而在20世紀日益成為具有世界歷史性影響的行為制度與模式。‘現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業化世界’;現代性的第二個維度是資本主義,它意指包含競爭性的產品市場和勞動力的商品化過程中的商品生產體系。”(《現代性與自我認同》,16頁,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有人批評吉登斯的現代性描述忽視了文化問題,“吉登斯不認真對待文化問題,…認為不探討從目前有關文化的政治、文化資本、文化差異、文化同質性和異質性,族群性,民族主義、種族、性別等等爭論中產生的問題,人們也可以合理地說明當代的世界,這整個想法就令人難以置信。”(羅蘭,羅伯森:《全球化社會理論和全球文化》,18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本文的展開或許是參考了這種批評,但始終認為制度的變遷是中國文化認同危機出現的根本的和首要的因素。 [2]我們有足夠多的證據來證明傳統中國人對于自我形象的認識是“文化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這一方面是基于這樣一種信念,即認為中國文化是“天下”唯一真正的文明,其文化的優越性不容置疑,雖然周邊一些民族始終對它構成某種程度的軍事威脅,但是,他們并不能真正統治中國,除非他們接受中國的文化。其次,中國古代秩序的合法性依據來自于儒家,進而權力是向接受儒家規范并以之為行為規范的人開放,因此“文化主義拒絕承認一個由形式上互相平等的諸多國家構成的世界,并且堅持合法的統治需建立在遵循儒家規范的基礎上。” 復旦大學歷史系編:《近代中國的國家形象與國家認同》,176頁。關于近代中國人對于自我形象的認識是由“文化主義”向“民族主義”轉變的詳細討論可參閱金光耀:《中國的民族主義》,載《近代中國的國家形象與國家認同》,173-21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3] 趙汀陽:《認同與文化自身認同》,載氏著:《沒有世界觀的世界》,71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4] 對于國民性問題的詳細討論可參閱劉禾:《國民性理論質疑》,75-103頁。載氏著《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 [5] 對于由現代性問題而帶來的時間觀念的突顯,比如少年/新/現代等等,可參看汪暉:《現代性問題答問》,載《死火重溫》,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 [6] 同上書,75頁。但也有人認為中國人并不存在“認同危機”。白魯恂(Lucian Pye)并不承認由于制度變革對中國人所造成的認同危機“其他大部分的轉型制度都通常有過那種認同危機,中國人大體上沒有經歷過”,“他們幾乎對他們中國人的身份沒有產生過懷疑”,“他們對外部世界越開放,就越來越自覺地認識到自己中國人的身份”。The Sprite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e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 Development,PP5,6, M.I.T 1968. [7] 《新學偽經考序》,見《康有為政論集》上卷,9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8] 更詳細的分析可參看湯志均:《經學與近代政治》,18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9]其實康有為并非不知道,把《春秋》和現代西方的制度比附在一起的牽強之處,但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他甚至在給光緒帝的奏文中直接地道出了他之所以托古之原因:“誠以守舊者不欲變法,實為便其私途,而往往陳義甚高,動引孔孟程朱,以箝人口。……臣故博征往籍,發明孔子變法大義,使守舊者無所借口,庶于變法自強,能正其本,區區之意,竊在于是。” 《恭謝天恩并陳編纂群書以助變法請速籌全局折》,《杰士上書匯錄》,故宮藏本 [10] 陸寶千:《民國初年康有為之孔教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八輯,臺北,1983年6月。 [11] 《答朱蓉生書》,蔣貴麟編:《萬木草堂遺稿外編》(下),815頁。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 [12] 《上清帝第二書》,載謝遐齡編選《變法以致太平:康有為文選》,283頁。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 [13] 湯志均:《康有為政論集》,890—891頁,中華書局,1981。 [14]羅志田認為近代知識階層對儒家的批評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儒學再造”過程,也就是借批孔教會這樣的名義,將儒家描述成一種“迷信”,進而成為當時所盛行的“進步”和“科學”的對立面。說:“然而,盡管正宗的儒學或時人所說的‘國學’恰不欣賞‘子不語’,許多反孔反儒的新學家總是將兩者并聯起來視為一體,等于是傳統的‘再造’,則其批判打擊的‘傳統’實已具有一定的虛懸意味。新文化人其實是有意識地對中國社會某些特定面相進行‘主動’觀察,故多見所謂的‘烏煙瘴氣’,并將‘怪力亂神’的猖獗看作以‘孔家店’為代表的傳統之余威不絕,具有詭論意味的是,這些反孔教的趨新人物力圖打擊此種舊文化‘妖焰’的復熾,卻不啻繼承了儒家的正統精神。”《異端的正統化:庚子義和團事件表現出的歷史轉折》,《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30頁,中華書局2003。 [15]陳獨秀,《獨秀文存》,73-78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16] 《復辟與尊孔》,載龐樸等編:《先秦儒家研究》,114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17] 胡適和魯迅都曾經為他們的激進立場作出說明。魯迅認為中國人有其惰性,他打了一個著名的比喻就是,如果你想開窗透一下空氣,必會招致反對,但如果你說要把屋頂掀掉,人們自然會同意開窗。 [18] 《陳獨秀文章選編》,186頁,北京,三聯書店,1984。 [19] 《本志罪案之答辯書》,《陳獨秀文章選編》,317頁,北京,三聯書店,1984。 [20] 《答常乃惪》,《陳獨秀文章選編》,162-163頁,三聯書店,1984。黃進興認為其實康有為和陳獨秀同樣是以基督教為范型來評判宗教的作用。“以康氏為例,他認為歐美所以強盛,不徒在政治物質方面,更根本的是基督教的教化。相反地,梁啟超、陳獨秀諸人卻認為基督教在近代文明乃屬落后勢力,亟需加以革除。”載《圣賢和圣徒》,56頁,允晨出版實業有限公司,2002年。 [21] 《箴洋八股化之理學》,轉引自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346頁,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 [22] 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92頁,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23] 列文森:《儒教中國的現代命運》162,163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24] 汪暉:《死火重溫》,14頁、5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 [25]魯迅說過:“孔子這人,其實是自從死了以后,也總是當著‘敲門磚’的差使的。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自20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袁世凱時代,卻又被重新記得,不但恢復了祭典,還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們穿起來。跟著這事而出現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門終于沒有敲開,袁氏在門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軍閥,當覺得漸近末路時,也用它來敲過另外的幸福之門。盤踞著江蘇和浙江,在路上隨便砍殺百姓的孫傳芳將軍,一面復興了投壺之禮;鉆進山東,連自己也數不清金錢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數目的張宗昌將軍,則重刻了《十三經》,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體關系來傳染的花柳病一樣的東西,拿一個孔子后裔的誰來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門,卻仍然對誰也沒有開。這三個人,都把孔夫子當作磚頭用,但是時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敗了。” 《魯迅全集》第6卷,252-25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26] 孫中山:《三民主義》,39頁。岳麓書店,2000年。 [27] 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編:《戴季陶主義資料選編》,22頁,14頁。1981年。 [28] 蔣介石:《中國教育的思想問題》,轉引自《儒學在現代中國》,143頁,中洲古籍出版社,1991年。 [29]根據舒衡哲的研究,知識分子在反思“五四運動”的成果時,也開始有了一定的轉變,因為“在愛國動員的壓力下,對傳統的任何抨擊都很容易被看作是攻擊民族的集體精神。從這種極端條件下的觀點來判斷,反傳統和民眾忠于祖國的感情存在著明顯的對立。反傳統被看作是反對可以用來動員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感情。”載氏著《中國的啟蒙運動》,288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30]陳立夫:《文化與中國文化之建設—三民主義即文化建設之綱領》,載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47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31]根據舒衡哲的研究,知識分子在反思“五四運動”的成果時,也開始有了一定的轉變,因為“在愛國動員的壓力下,對傳統的任何抨擊都很容易被看作是攻擊民族的集體精神。從這種極端條件下的觀點來判斷,反傳統和民眾忠于祖國的感情存在著明顯的對立。反傳統被看作是反對可以用來動員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感情。”載氏著《中國的啟蒙運動》,288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32] 關于張氏兄弟在20世紀30年代的文化觀可參看拙作《張岱年30年代的文化觀》,《清華大學學報》2004年第四期 [33] 《關于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全集》第1卷,231頁。 [34] 1933年至1934年馮友蘭先生的文化觀也經歷了從“東西”向“古今”的轉變。“我第一次來到美國正直我國五四運動末期,這個運動是當時的不同的文化矛盾沖突的高潮。我是帶著這個問題而來的,我開始認真地研究它們。為了解答這些問題,我的思想發展有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我用地理區域來解釋文化的差別,就是說,文化差別是東方、西方的差別。在第二階段,我用歷史時代來解釋文化差別,就是說,文化差別是古代、近代的差別。在第三階段,我用社會發展來結實文化差別,就是說,文化差別是社會類型的差別。”按陳來先生的排列,1922年發表《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代表第一階段的看法。1933年至1934年的歐洲訪問才使他明確轉向新的解釋。1940年出版《新事論》提出中古和近代的差別實即社會類型的差別,這是第三階段。見《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73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 [35] 《西化與創造》,《全集》第1卷,260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36]艾思奇:《什么是新啟蒙運動》,載丁守和主編:《中國近代啟蒙思潮》,下卷,17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37] 陳伯達:《思想無罪》,載丁守和主編:《中國近代啟蒙思潮》,下卷,185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38] 張申府:《論中國化》,載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58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39] 艾思奇:《論中國的特殊性》,載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60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40]《新民主主義論》 [41] “誰來確定民族的本質內涵?由誰提出民族文化的語言?這個問題對于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在三十年代的民族危機中已經很迫切;他們對‘古老的’精英文化和20年代的西方主義都抱懷疑態度。他們帶著現代性在中國的歷史經驗中尋求一種新的文化源泉;這種文化將會是中國的,因為它植根于中國的經驗;但同時又是當代的,因為這一經驗不可避免地是現代的。不少人認為‘人民’的文化,特別是鄉村人民的文化,為創造一種本土的現代文化提供了最佳希望。”1718,王袞吾:(澳大利亞):《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人的毛澤東》,見《歷史的天平上》,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139頁。 [42]薩伊德《無知的沖突》的文章,嚴厲批判了“文明的沖突”,認為這種觀點“將‘文明’與‘認同’扭曲成已然定型、封閉的體系,剝奪了賦予人類歷史生機的無數潮流與逆流;也無視于數百年來的人類歷史不僅有宗教戰爭與帝國征戰,更有互相交流、增益與分享。‘文明沖突’之說全然忽略了歷史隱而不顯的這一部分,只急于以荒謬可笑、狹隘簡化的方式來凸顯文明的爭斗。”Edward W. Said: The Clash of Ignorance. The Nation. October 22,2002 issue. [43]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之下,各民族之間的經濟競爭更加激烈,而西方國家運用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強勢保持他們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時候,往往采取的是對于經濟和經濟弱小民族的一種壓制,作為對這種力量的反對,民族主義便增強了。那些處于邊緣的國家和地區開始采用爭取文化自主的運動,民族主義運動、族群運動,而且還呈現出采用各種形式的地方自治和社區自我控制的總趨勢。裂變在民族國家之下的最高層次是民族主義——族群性的、族群的和文化上的自主運動。 [44] “文化認同是我們面臨的這種失序現象的核心方面。這個術語指的是以有意識的具體特定文化構型為基礎的社會認同。歷史、語言和種族對文化認同來說,都是可能的基礎,并且它們都是被社會性地建構的現實。即便是認識到所有認同的建構程度,這也并不會使它們成為虛假的或意識形態的。” (喬納森,弗里德曼,郭建如譯,高丙中校:《文化認同和全球性過程》,356頁,商務印書館,2003年)這種判斷對于中國當下的經驗而言是有問題的。中國當代文化認同問題包含有作為沖擊傳統意識形態的合法性的因素是確定的。 [45] 羅蘭,羅伯森著,梁光嚴譯:《全球化社會理論和全球文化》,18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46] 1997年11月2日《人民日報》 [47] 2003年12月10日《人民日報》 [48]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的新道路》,《文匯報》2004年3月21日 [49] 羅蘭,羅伯森:《全球化社會理論和全球文化》,14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