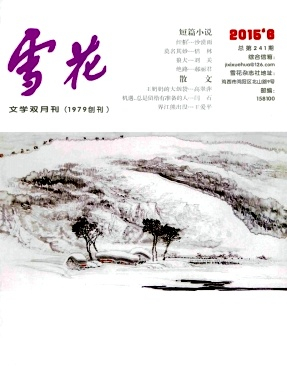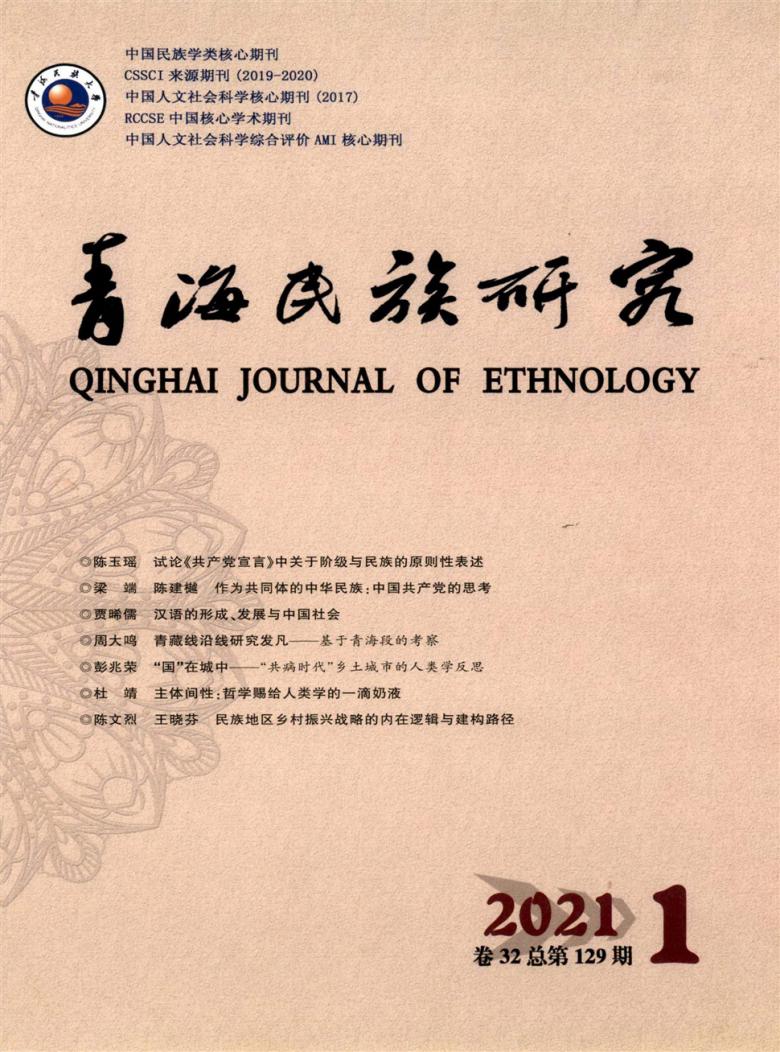民國教育史上一次“曇花一現”的改革——大學院與大學區制的試行
王倩
摘 要: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戰禍不斷,殃及教育。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以蔡元培為首的一些教育界有識之士提倡教育改革,開始推行大學院與大學區制。但兩年后,這一制度被取消。大學區制雖然失敗了,但它所提倡的“行政學術化”,仍有現實的意義,值得人們加以探討研究。
關鍵詞:大學院;大學區;蔡元培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教育行政腐敗,教育事業備受摧殘。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建立,開始推行教育改革。大學院與大學區制在試行兩年后,最終失敗取消。國民政府又恢復了教育部與教育廳制度,此后一直未變。由此可見,大學院與大學區制度在教育行政史上有承前啟后的作用,是教育行政發展上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雖然它來去匆匆,有如曇花一現,但“中國的教育經此變動之后,卻從此少有變革,進入了安定成長的時期,放大學院制便成為一個自變革入安定的明顯的分水嶺”。
大學院制作為教育史上一次改革嘗試,已經引起了學界的關注。特別是它僅有兩年的歷程,更是引發了人們諸多的思考。
一、背景與制度的確立
任何一新事物的出現都是一個新陳代謝的過程。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教育行政十分腐敗,教育部不過是各派軍閥勢力爭奪地盤和權勢的官僚機構。在軍閥混戰的情況下,得勢者上臺安插本系人員,失勢時便連帶下野。自1912年至1926年,14年中先后更換了38個總長,24個次長。1923年教育總長彭允彝干涉司法獨立,非法逮捕了北大兼課教師、財政總長羅文干。蔡元培對此十分氣憤,當即辭去北大校長的職務。他在辭呈中指出:“元培目擊時艱,痛心于政治清明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茍安,尤不忍于此種教育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
北洋軍閥對教育的摧殘,還明顯反映在克扣、挪用甚至侵吞教育經費上。從中央到地方,軍閥為支付龐大的軍費,經常以教育經費去頂補。“風雨飄搖,幾瀕破產”正是對當時教育事業困難局面的真實寫照。各地索薪罷教的斗爭不斷發生:1923年9月,廣州市中等以上教職員,因欠薪5個月,無法維持生活議決罷課。11月,安徽省教職員向省長索薪被毆傷,發生風潮,多人被捕。甚至教育部都發不出工資。1926年1月5日,發生部員開會索薪之事,決定查封《四庫全書》作為欠薪抵押品。11月17日,北京國立大學及專門學校八校因“政府積欠經費9個月,學校難以維持”,召開聯席會議宣告學校關閉。
可見,在北洋時期,政教已經處于敵對地位。教育受政治變動的影響,既不能安定地進行,也談不到整個教育政策的實施。有識之士認為教育要獲得發展,必須獨立。1922年3月,蔡元培發表了《教育獨立議》一文,認為教育必須獲得獨立,并且對于實行超然的教育,擬定了具體的辦法。他主張“分全國為若干大學區,每區設立一大學;凡中等以上各種專門學校,都可以設在大學里面。一區以內的中小學校教育,于學校以外的社會教育,都由大學校長辦理。大學的事務,由大學教授所組織的教育委員會主持。大學校長,也由委員會舉出。由各大學校長,組織高等教育會議,辦理各大學區互相關系的事務。教育部,專辦理高等教育會議所議決事務之有關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國教育統計與報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學區事務。教育總長必須經過高等教育會議承認,不受政黨內閣更迭的影響”。蔡元培在這里提出了大學區的藍圖,認為這樣教育就可以不受政潮的影響,達到學術化,獨立化的理想。
192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4月25日,國府召開第二次常委會議,議決任命蔡元培、李石曾等為中央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5月,蔡元培、李石曾、褚民誼三人被推為教育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蔡元培成為掌握全國教育的實權人物,于是他開始將“教育獨立”的理想付諸實踐。6月6日,蔡元培在中政會第102次會議上,呈請變更教育行政制度。他闡述了近年來教育的紛亂與種種弊端,并進一步提出“亦仿法國制度,以大學區為教育行政之單位”。6月12日,國民政府訓令在粵、浙、蘇三省試行大學區,廣東省暫緩試行。這樣,大學區完成了它的立法程序。
除了安排大學區來指導教育外,蔡元培還計劃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組織——大學院。蔡元培在6月13日的中政會第105次會議上提議組織大學院,作為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并附呈組織大綱。6月27日,中央政治會議第109次會議通過了大學院組織法草案,國民政府于7月4日公布。至此,大學院宣告成立。對于設立大學院的原因,蔡元培在《大學院公報》發刊詞中,已經說明“顧十余年來,教育部處北京腐敗空氣之中,受其他各部之熏染;長部者又時有不知教育為何物也,而專鶩營私植黨之人;聲應氣求,積漸腐化,遂使教育部名詞與腐敗官僚亦為密切之聯想。此國民政府所以舍教育部之名,而以大學院命管理學術教育之機關也”。可見,大學院是代替了教育部作為中央教育機關的。而大學區的實施則是替代地方的教育廳制度。蔡元培認為大學區制度優于省教育廳與市教育局,就是因為“大學有多數學者,多數設備,絕非廳局所能及”。
大學院與大學區在立法程序上的完成,標志著這一新制度最終確立了下來,并開始進入實際運行階段。
二、組織特點及試行經過
1927年7月4日,國民政府公布了《中華民國大學院組織法》。10月,大學院正式在南京成立,蔡元培被推為大學院院長。《組織法》就大學院的性質、組織、機構、職能等作了具體的規定。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機關,總攬全國學術與教育行政事宜;大學院設院長一人,總理全院事務。下設秘書處、教育行政處、國立學術機關及各種專門委員會等。大學院有三個特點:一、學術與教育并重,以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機關;二、院長制與委員制并用,以院長負行政全責,以大學委員會負議事及計劃之責;三、計劃與實行并進,設中央研究院,實行科學研究。設勞動大學,提倡勞動教育。設音樂院、藝術院,實行美化教育。”可見,大學院內部組織機構的設置,體現了改造原有中央教育行政的思想。大學院將教育行政與教育機關合而為一,“一切設施,務本學術研究之精神以進行,不獨要以科學方法舉行研究,并欲以科學方法處理公事”。
大學院在它存在的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作了一些有益于社會并對社會有較大影響的工作。
1.改革舊制。首先是廢止了春秋祀孔典禮。盡管五四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但各地春秋祀孔典禮依然在進行。因此1928年2月2日,大學院通令全國將春秋祀孔典禮一律廢除。此舉廢除了自漢代以來的祀孔制度,在改革社會積習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其次是提倡語體文。1928年7月26日,大學院通令小學一律用語體文教學,不準采用文言教科書。各級教育行政機關也應向社會宣傳提倡語體文。
2.延攬優秀人才。“專家辦教育”是大學院實行的一個重要教育思想。大學院在人事任用上,十分注意優秀人才的選拔。大學院所任副院長、各處處長、各大學區的大學校長等,均為國內著名學者和社會上德高望重之人。
大學院及其所屬機構的確是網羅了學界、科技界的知名人士,可謂是名家薈萃,體現了“學者主政”的思想。
3.設立研究機構。大學院設中央研究院作為全國最高科學研究機關;大學區也設研究院,作為地方研究機構。1927年11月20日,中央研究院召集籌備會議,通過了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中央研究院最初設立了理化實業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地質研究所、觀象臺四個研究機關,后逐漸擴充為氣象臺研究所、天文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化學研究所、工程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等。研究院以蔡元培為院長,楊杏佛為秘書長。各研究所還聘請了當時著名的研究人才。大學區中,只有北平大學區籌設了研究院,1929年9月9日正式成立,名為“國立北平研究院”。在大學院與大學區后來相繼結束后,作為大學院與大學區的產物,中央研究院與北平研究院仍然保存了下來。這兩個研究院一直以科學研究為基礎,將研究成果用于社會實業的發展,為國家的學術及科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吳相湘曾評價這兩個機構說:“北伐成功以后至對日抗戰以前十年間,成民國以來學術研究的黃金時代,且為盡三十年之學術奠定基礎。”這不能不說是實施大學院、大學區制的一項重大收獲。
4.召集全國教育會議,厲行義務教育。1928年5月15日,大學院在南京召集全國教育會議。此次會議規模宏大,與會代表及所聘專家達“一百數十人”。大會共收到會員議案82件,非會員提案164件。這些議案涉及教育的各個方面,包括教育行政、教育宗旨、高等教育、普通教育、社會教育、教育經費等等。大會將議案整理后,分為11個組討論審查。大會認為,普及義務教育,保障學齡兒童適時入學,對于提高國民文化整體素質,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這次會議有關普及教育的一項議案“建議在中央各省區、各市縣均設義務教育委員會,襄助教育行政機關,計劃及促進義務教育。并規定各地方失學兒童數應減少百分之二十,至遲到十八年五月底止,各省區、各特別市應將推行義務教育計劃呈報于大學院”。會議結束后,大學院即根據此案,通令付諸實行。1928年8月28日,厲行義務教育籌設委員會計劃進行;9月29日,大學院又發布中央義務教育委員會組織大綱。由于大學院存在的時間較短,義務教育的推行在此期間并未取得實績。但大學院已經設置了推行義務教育的機關單位,這為國民政府以后的實施奠定了基礎,也反映出大學院在普及教育方面所做的諸多努力。
有關大學區的提議是在中央政治會議第102次會議上提出的。蔡元培在當時提請變更教育行政時,首先提出的就是采取大學區制,并在附呈中擬定了九條組織條例。1927年7月8日,國府令江蘇省教育廳裁撤。7月9日江蘇省大學區正式開始辦公。省內的東南大學、河海工科大學、上海商科大學、江蘇法政大學等九所學校合并,改稱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張乃燕為校長。浙江大學區在1927年8月1日成立。它是將浙江公立工業專門學校、農業專門學校等改組為“國立第三中山大學”。到1928年底,又在北平試行大學區制,所以前后共有浙江、江蘇、北平三個大學區。
大學區的組織法歷經三次修改,其主要內容有:(1)全國依各地之教育經濟及交通狀況,定為若干大學區。每大學區設大學一所,大學設校長一人,總理大學區內一切學術與教育行政事項。(2)設評議會為本區立法機關。(3)設秘書處,輔助校長辦理本區行政上一切事務。(4)設研究院,為本大學研究的最高機關。大學區還設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擴充教育部,分別管理區內的大學、中小學及社會教育事業。因此,大學區與一般的行政區域不同。大學校長兼管全區的教育行政,加強了大中小學的聯系,便于整合統一教育計劃;大學區內設研究院,使教育行政與研究可以聯合進行;設地方評議機關,保證了政策相對的獨立性。所以,蔡元培認為大學區制比教育廳與市教育局的制度更為優越。
三、變更及取消
大學院與大學區作為一新制度,雖然創制宏遠,設想完美,但實行不久,即遭到一些黨政要員,甚至教育界人士的責問與反對。
最先對大學院提出質疑的是國民黨四中全會上的提案。1928年2月,在國民黨四中全會上,經亨頤、朱霽青、白云梯等人提出“設立教育部”案,反對大學院制。但是這個議案并沒有在大會上通過。1928年8月,在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上,經亨頤等人舊案重提,仍堅持設立教育部。郭春濤、劉受中等也提出了“撤銷大學院改設教育部”案。他們反對大學院的理由主要有官制不統一、將學術與教育混為一談、小學遷就大學等等。
在此期間,大學院組織法已經過了四次修改,在修正的過程中,大學院的權力不斷縮小。在4月11日的第二次修正中,大學院已由“承國民政府之命”變成“直隸于國民政府”,地位與其他各部無異。4月14日公布的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規定中央研究院不再附屬于大學院,其組織“設院長一人,由國民政府特任之”,也不再是由大學院長兼任。1928年10月國民政府令,大學院改為教育部,所有前大學院一切事宜,均由教育部辦理。
大學區的反對之聲主要來自基層,而最先反對大學區的則是中央大學區所轄的中等學校。1928年6月,中央大學區中等學校聯合會因大學區忽略中等教育,請設法變更。呈文中還列舉了大學區易受政潮牽涉、經費分配不公、行政效率減低、影響學風、釀成學閥把持勢力的五點弊端。
在北平大學區也受到抵制與排斥。1928年8月,《北平大學區組織大綱》通過后,河北省政府、黨部及北平各校學生均群起反對。1928年12月27日,河北省政府致電國民政府,認為大學區制是根據大學院制而產生,現在大學院已取消,大學區也沒有存在的理由;而且大學區有違黨化教育。12月28日,河北省黨務指導會也致電蔣介石,認為實行大學區制,“無異故意破壞河北教育”,主張“將大學區制根本取消,以永斷糾紛,而絕未來無窮之患”。
北平各校學生對于大學區制也強烈反對。1928年9月,北洋大學發起護校運動,抵制大學區制。11月14日,又擬組織“反大學區特別委員會”及“武力護校團”。1928年11月29日,北京大學學生示威游行至到北平大學校長辦,搗毀了辦事處,砸碎了“北平大學辦事處”和“北平大學委員會”兩塊牌匾。12月1日清晨,接收北大文理學院的人員,在武警的保護下進入校園,但學生聚集了三百多人,“分赴各院把守,拒絕接收”。此后,北平學潮此起彼伏,不斷擴大,北平終日處于擾攘與混亂之中。因此,1929年7月1日,國民政府決議“由教育部定期停止試行大學區制”。
至此,大學區制完全被取消,地方上又恢復了教育廳制度。歷時兩年的大學院與大學區教育制度的改革,員后以失敗告終。
四、原因及結論
大學院和大學區制作為對舊的教育行政制度改革的一種嘗試和探索,貫徹了教育機構學術化和學者管理教育行政的精神。特別是它擁有相對獨立于各級政府的立法權和決策權,這是對近代官僚體制的沖擊。然而此“良法美意”施行不久,即遭到眾多指責,短短兩年后就成為了歷史名詞。我們追尋大學院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教育無法完全獨立于社會政治之外。大學院與大學區制實行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使教育獨立化,教育獨立的核心在于獲得獨立的地位,不受政黨與宗教的把持。這一思想的提出旨在擺脫政治干預教育行政管理的狀況,在理論上也是完美無缺的。然而事實上執行起來,與理想卻是大相徑庭。南京國民政府在北伐勝利以后,提出“以黨治國”的口號,強調“軍政統一”、“思想統一”。而此時“要求經費獨立,立法獨立,人事獨立”的大學院就顯得不合時宜,與訓政黨治精神格格不入。因而“中央黨部和各級黨部均不予支持”。其實就是一般群眾與學生也不能理解。當時就有一名北洋學生發表文章說:“現在是統一的政府,一切權力都應當集中中央,誰都承認的,而此時忽有大學區之劃分,偏要把教育權分成零碎的,割據的,這就是系統嗎?”北洋學生在發表反對大學區宣言時,認為大學區“不但有背世界的潮流,亦且違黨化教育的原則”。可見“教育獨立化”在當時社會得不到各方的支持,這是大學院制度失敗的根本原因。
第二,改革的步驟過快,沒有考慮到體制過渡期的情形,在實施上也沒有充分準備,缺乏群眾基礎。蔡元培、李石曾等著名教育家,雖然在1922年即提出了大學區的藍圖,但能有此遠大目光者,畢竟為少數。就是到了1927年6月,大學院組織法獲得通過,大學院與大學區相繼試行,大部分人仍是對此了解甚少。當時社評說大學院實行時“標語口號,日新月異,每令局外人惶恐不解”。而且“大學區制之實行,既不聞當局者在理論上多所闡揚,又不聞在實施上充分準備,突然宣布,忽而執行”。顯然,人們對此沒有充分地了解,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又如何能理解與接受呢?而且這一改革理念,在實踐中難題頗多,問題與矛盾的繁雜是難以想像的。這就更需要體制的慢慢過渡,然而事實上,改變過于倉促,導致群起反對。1928年8月,政府在江蘇與浙江大學區沒有取得成績的情況下,又決定成立北平大學區,當即遭到北洋大學與北京大學學生的強烈反對。1928年9月5日,北洋大學臨時學生會發表宣言稱:“據大學院的最近決議,已把我們并入北平大學區管轄之下,并且命名我們為工科第二院,以副院長管理我們,這顯然我們是旁人的附屬品。我們過去歷史,卓著的成績,既是昭昭在人耳。對于這最高的工科學府,就應該保存他原來的地位,使他盡量發展他那固有的精神。不然,地位因以愈變愈低,豈不可惜么。”同時,北大學生也激烈反對合并,認為“獨有北大,一合并就糟!若內部之整個嚴密組織,及其校內特有校風與精神,亦因改組或合并而分崩離析,不是活活把北大槍斃!把一個在本國與國際間文化與學術上有相當位置的大學消滅了,我從人類進化上看這犧牲足近于自殺!”像北京與北洋兩所大學,本身有著輝煌的校史,在教育界有著較高的地位,對其進行內部重組,必然引發極大的爭議與反對。而大學院一開始就宣布將幾校合并,并且更改校名,試圖一步改組到位,這于情于理都是難以接受的,也難怪學生們會激烈反對了。大學院與大學區制不僅在實行上欠缺準備,而且改革只注重制度層面的革新,忽略了思想層面的改變,突如其來的變化令長期已習慣了原有思維與運作模式的人們難以接受,而且沒有過渡的時期,失敗也就在所難免。
第三,革去官僚氣息與人事糾紛的想法不現實。大學院制的改革本來是要以教育家管理教育,使行政學術化,革除官僚習氣,排除人事糾葛。然而,當時的中國官僚和黨爭嚴重,教育要排除官僚與黨爭又談何容易。圍繞中央大學校長人選所產生的糾紛即是典型一例。這一風波的興起源于1928年6月10日,“國民政府任命吳敬恒為中大校長”一事。中央大學校長原是張乃燕,而現在被調為大學院多事。大學院任命吳敬恒為中大的校長。但事實上,吳敬恒并沒有就職。后來大學院又下令,任命了自然科學院長和高等教育處長的人選。由于學校校長免職,“中央大學學生于十一日上午十一時,舉行紀念周,提議正式校長人選問題,決定汪精衛、胡漢民、于右任三人。學生全體對于校長問題任何人代理,均所反對。一致主張有正式校長長校”。中大教員也于6月12日召集教授會議,選舉臨時校務維持委員。后又發表校務臨時委員會宣言,提出校長人選三標準,對于學生所提名的人選均不滿意。可見大學院、學生、教員三方對于校長人選問題,意見分歧很大。
風波還不止于人選的分歧,張乃燕本人在解職一事上,對大學院組織的嚴密性提出了質疑。他在呈國府文中寫道:“竊查大學院委員會組織條例,大學校長人選為委員會會議職權之一。乃燕為大學委員,關于此次校長之更調,事前絕未奉召集委員會之通知,或事涉乃燕,理當延避出席。然詢其他委員,未聞經委員會會議之手續,突然調任,緊急處分,最可疑者,大學院在發表前項命令之日,同時即有正式函件致校普通教育處長,調某某繼任高等教育處長,一一指定姓名。此等內部職司,依法應由校長選聘。今新校長絕無表示,而大學院已事先預謀,越權指派,更代若此張皇,分配又如是詳密。”從張乃燕的呈文中,我們不難看出,大學院在兩個方面的做法有違規定。一是大學校長的任免,照例是要經大學委員會討論通過的。而此次更調,并未召集委員會。二是大學高等教育處及自然科學院長的任職,本為大學校長的職權,而大學院卻代為指定,顯然不合大學區組織條例。6月12日在國府會議上,“蔡院長以此事卻有未合法律手續,自請處分”的做法,也證明了張乃燕的質疑確實存在。更加令人費解的是,在這樣的各方爭吵中,中大易長風潮又忽然暫告段落,“大學院令中大在新校長未定前,由張校長繼續維持”。
此次中大更調校長,引起重大糾紛。我們且不必去分析其中各環節的原委,以及牽涉的各方利益,單就其忽而興起,又戛然而止,即可知情形十分復雜,派別紛紜,各持己見,“其內容實非外人所窺測”。這一事件本身的復雜性即說明在學界高層的內部存在著諸多矛盾與分歧,甚至有學閥把持的現象。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專制傳統的國家,階級觀念甚深,這種人事傳統上的觀念很難一掃而空。大學院試圖革除官僚氣息,排除人事糾葛的理想,在現實中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次易長風潮雖然過去了,但形成了“民眾早已痛心,社會妄多揣測,尤疑竇增生”的局面。
第四、實踐證明大學區實行以來,只見其弊,卻未收其利。這在北平大學區表現得尤為明顯。自1928年8月北平設立大學區開始,即遭到北京各學校的反對。北平“各校當局,左支右絀,日惟應付學潮是務。而所謂學潮者,甲起乙繼,此往彼來,題目無窮,有動無靜。當局無一月半月之安寧,社會群眾亦極感惶恐與厭惡。”以致“北平教育,有退無進”。而且“近年北平學界風氣之惡化,可謂已達極點。終年均有風潮,口實層出不窮。學生不讀書,教員不授課,在北平實為習見。各校學生中,終年包辦各項社會運動,政治運動,挾少數勢力以壓迫多數同學,且復受師長之敬畏者,視十年前情形,又復變本而加厲”。這些言論決非危言聳聽,而是當時北平教育狀況的真實寫照。北平本來有著雄厚的教育基礎,此時卻學業停頓,各種不良風氣充斥其中,一片混亂與衰敗的跡象,實在令人失望與惋惜。因此,“大學區試行一年,毫無成績,黨部群眾主廢止,學界亦不同情,而亦證明大學區制試驗之無益”。
綜上所述,大學院與大學區盡管在理論上杜絕了現行教育體制的諸多弊端,但是實際操作起來,卻是事與愿違。事實證明了它的不可行性和太過理想化。它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因而沒有得到政府和民眾的支持,最終失敗也是在所難免了。在中國,教育與政治一直是糾纏不清的,將教育與國家的正統意識分開是十分不易的。大學院與大學區制之所以能夠在1927年推行,并且較少受到政府的干預,并不是社會政治進步的結果,只是當時在軍閥混戰的年代里,缺乏一個中央政府而已,這只是一種暫時的平衡局面。一旦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出現,教育便又回到它的管制之下。所以說“與政治分離的,較獨立的教育發展總是斷斷續續,步履蹣跚”。
大學院制雖然不幸失敗了,但它在歷史上并不是了無痕跡的,它畢竟為我們的教育行政模式提供了另一種選擇。它所提倡的“行政學術化”、“學術研究化”的意圖,即使在今天看來,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和借鑒價值,值得探討和研究。
[1]陳哲三。中華民國大學院之研究[M].(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2]陳學恂。中國教育史研究(現代分卷)[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1994.
[3]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中國現代教育大事記[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8.
[4]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論著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27年1—6月)[M].1977.
[6]中國策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7]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譜(下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8]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27年7—12月)[M].1977.
[9]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革命文獻(第53輯)[M].中央文物供應社,1971.
[10]蔡元培。孑民自述[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11]劉國銘。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政職官人物志[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12]南京教育會議(三)[N].大公報,1928—05—13(6).
[13]吳家瑩。中華民國教育政策發展史[M].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0.
[14]北洋大學學生會擁護獨立運動[N].大公報,1928—09—16(5).
[15]北洋大學學生反對大學區制[N].大公報,1928—11—16(5).
[16]張樂天,檀傳寶。蔡元培傳[M].北京:團結出版社,1998.
[17]北大又演風潮一幕[N].大公報,1928—12—02.
[18]江哲岑。對于孫汝為的<對于北京北洋兩大學校運動之我見>之我見[N].大公報,1928—11—10(10).
[19]北洋大學學生反對大學區[N].大公報,1928—09—22(5).
[20]北京學潮之將來如何[N].大公報,1929—08—08.
[21]喚起教育大家之責任心[N].大公報,1929—07—22.
[22]北洋大學學生會擁護獨立運動[N].大公報,1928—09—06(5).
[23]李增濃。為什么我要求北京大學存在[N].1928—09—29(10).
[24]中央大學易長糾紛未已[N].申報,1928—06—13.
[25]中大校長人選難定[N].申報,1928—06—15.
[26]張乃燕呈國府文[N].申報,1928—06—12.
[27]蔡院長在國府會議上自請處分[N].申報,1928—06—15.
[28]中大風潮暫告段落[N].申報,1928—06—12.
[29]中大風潮內容復雜[N].申報,1928—06—17.
[30]衰落之北平[N].大公報,1929—07—04.
[31]中全會議決案一瞥[N].大公報,1929—06—20.
[32]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二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