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教育語文教學的五個注意點
江平
摘要:義務教育中的語文教學有五個注意點:1.語文學習與現(xiàn)實生活密切聯(lián)系;2.學習語文也是學習文化;3.語言教學與思維訓練同步;4.語言的積累有助于語感的培養(yǎng);5.語言的學習離不開言語的實踐。
關鍵詞:義務教育;語文教學;注意點
義務教育語文教學的注意點,指的是《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以下簡稱《語文課程標準》)中稱之為第一、二、三、四學段的語文教學過程中需要關注與重視的幾個方面:語文與生活、語文與文化、語言與思維、語言與語感、語言與實踐。這五個方面在新課程實施前的語文教學中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新課程的理念與實踐,使這五個方面在繼承我國語文教育傳統(tǒng)、吸收國外語文教育思想的基礎上,都有所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有了新的內(nèi)涵,且為語文教育與研究者注意。這使筆者有了論述的必要。
一、語文學習與現(xiàn)實生活密切聯(lián)系
語文學習與現(xiàn)實生活有著天然的聯(lián)系。“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生活是語言文字的源泉,語言文字記述了人物的生活事件,反映了生活中人們的情感波瀾。美國教育家華特說過的“語文的外延與生活的外延相等”,這句話上個世紀末一度被一份語文雜志引為封面題詞,因為它一語中的。自古以來的語文學習內(nèi)容從“三百千千”到最近媒體報道的清代道光年間的李家私塾課本,從民國初期的《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小學語文課本一、二兩冊,較多地反映的是當時社會現(xiàn)實生活與人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喜怒哀樂及其經(jīng)驗積累,亦即白居易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之所謂也。我們在學習這些課文(即言語材料)時,往往基于個人對當時社會背景與生活現(xiàn)實的了解與認識來想象作者描述的生活場景、理解課文的內(nèi)容、體會人物和作者的思想情感的。國外的語文學習也關注與現(xiàn)實社會生活的聯(lián)系。例如,課文生活化,是英美小學和初中的教科書特色。他們以現(xiàn)實生活為主題組織教學單元,把學習母語與認識現(xiàn)實生活結合起來。[1](610)可以這樣說,我們在學習語文的同時,了解并認識過去與現(xiàn)在的社會現(xiàn)實和人們生活,并在這個過程中獲得有益的生活經(jīng)驗和價值觀念。
生活又是語文學習的源泉,尤其是現(xiàn)實生活,是學生語文學習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是語文學習時的參照物、體察揣摩的情景場。例如,江蘇的一位教師在執(zhí)教蘇教版一年級上冊口語交際《自我介紹》一課時,直接將口語交際的能力訓練生活化。她先是引導學生在創(chuàng)設的生活情景中面向全班、面向小組介紹自己,再是制作名片,分發(fā)全班介紹自己。學生在生活化的交際情景中,口語交際以及與人共處的態(tài)度、能力得到了有效的練習。再如,一位教師在指導學生學習唐代詩人韓愈《早春》“草色遙看近卻無”一句時,擔心學生不好理解,于是就引導學生回憶生活中類似的情景。學生分別談了幾件事:一是遠遠望去,集市上人山人海,沒有一點兒空隙;可是走近時,人與人之間的空隙還有很多。二是插秧后發(fā)現(xiàn)田里的秧苗稀疏、零星,遠離秧田回頭看時,秧田里一片綠色,等等。教師的引導成功,顯然是喚起了學生的生活積累及其感受,并使之遷移到新學而難懂的詩句中,于是對句中描寫的意境就有了具體、真切的感受。可見,及時指點學生創(chuàng)設并回憶相關的生活情景,或引導學生聯(lián)系自己的生活經(jīng)歷,或調(diào)動學生已有的生活體驗,往往能幫助他們進入特定的情境之中,獲得感同身受的語文學習效果。
此外,自古以來,文人學子都關注社會生活、人生百態(tài)這本大“書”,古訓有“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到了現(xiàn)代,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又影響著教師們引領學生走近社會、走進生活學習與運用語文。例如,北京市曾組織小學生查找大街上的不規(guī)范用字。又如,重慶市一位老師組織學生學習人教版七年級上冊《漫游語文世界》時,發(fā)動學生上街勸改廠家、商鋪的錯別字,指導他們記錄廣播、電視中漢語、漢字使用方面的錯音別形字,布置他們尋找日常生活、校園網(wǎng)站、報紙雜志中不規(guī)范的遣詞造句現(xiàn)象。國外的語文學習也注意到用各種方法引導學生在生活中運用母語,使學習母語與現(xiàn)實生活聯(lián)系起來。可以說,類似這些指導學生在生活中正確運用語言文字的做法,有利于培養(yǎng)學生熱愛祖國語言文字的責任心,形成維護祖國語言文字規(guī)范運用的使命感,有利于培養(yǎng)學生在生活實踐中學用語文的敏度與美感。
眼下回歸生活的新課程理念、努力建設開放而有活力的語文課程基本理念,又在不時地提醒我們:語文學習植根現(xiàn)實、面向生活就有廣闊的天地。誠然,要引領學生進入這一廣闊的天地,教師首先要做個有心人,要在語文課程與教學中有意識地引導學生主動而有機地聯(lián)系校園生活、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并及時調(diào)動自己的生活閱歷及其生活體驗,使之成為語文學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后使他們耳濡目染、潛移默化,進而“習慣成自然”;學生在語文學習時才會無意識地自動化地聯(lián)系現(xiàn)實世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來感受語文,理解語文,提高語文的素養(yǎng)與實踐能力。久而久之,他們才能逐漸認識學習語文與聯(lián)系生活的必要與重要,逐漸體會聯(lián)系生活來學習語文時的自如與愜意。至此,他們在學習語文的過程中就會一如既往主動而自然地聯(lián)系生活,關注社會,體驗情感,品味人生,這對語文的學習與運用幫助很大。
二、學習語文也是學習文化
我國語言學家羅常培1947年在其論文集《中國人與中國文》中指出:“語言文字是一個民族文化的結晶,這個民族過去的文化靠著它來流傳,未來的文化也仗著它來推進”。[2]可見,語言文字與民族文化關系非同尋常,故申小龍先生稱之“互為觀照”。語言文字不僅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還是民族文化的載體。我們正是通過語言文字這個載體來學習文化、傳承文明的。從這個角度說,學習語文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學習民族先進文化與民族優(yōu)秀品質的過程。例如,人教版課標實驗教材一年級上冊中《識字(一)》“口耳目”的編排就充分體現(xiàn)了漢字中象形字的特點;《識字(二)》“日月明”的編排體現(xiàn)了漢字中會意字的特點;而在一年級下冊語文園地的“我的發(fā)現(xiàn)”中又讓學生去自主發(fā)現(xiàn)形聲字的特點。這無形之中使學生在了解神奇的漢字的同時,激起喜歡漢字的情感,進而接受漢字文化的熏陶。再如,教師組織學生在課堂上一邊識字組詞,一邊對對子,感受漢字漢語的巧妙與靈動,又加深了學生對漢字漢語的喜歡與熱愛之情。等到學會一定數(shù)量的漢字后,學習語文就離不開諸如課文一類的言語材料了。而這些言語材料往往積淀著豐厚而多彩的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又如,《懷素寫字》(人教版語文教材)和《燦爛的星空》(北師大版語文教材)一類的課文,其意在于將學生引領到勤奮學習、想象探究的精神世界。可見,語文學習的文化內(nèi)涵及其教育意義,在教材、在課程中無處不有、無時不在。而這一切,是用不著教師去特別提醒、刻意灌輸?shù)摹_@些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本身就寄寓在一則則語言文字材料之中;這每一則語言文字材料都連著東方道德和中華文化的根,每一則都充盈著人類先進文化和優(yōu)秀品質的魂。教師在引導學生學習這一則則語言文字材料時,也會自然而然地受到先進文化的熏陶與民族精神的感染。這種熏陶是耳濡目染的,這種感染是潛移默化的。學生在學習一則則言語材料的不知不覺中,為自己的精神世界打上了一層淺淺的,卻是難以磨滅的“底色”。例如,蘇教版一年級上冊教材有篇詞串識字的課文,內(nèi)容為:
沙灘 貝殼 腳丫 海風 海鷗 浪花
珍珠 海帶 魚蝦 港灣 漁船 晚霞
這種表述形式是對我國古代詩詞曲中幾個相關名詞并列意象組合的語言現(xiàn)象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一邊誦讀詞串,一邊想象畫面,默默記下這一個一個的詞串。然而當他們有一天吟誦到元代馬致遠《天凈沙·秋思》一類詩詞曲時,其思緒也許會在剎那間鏈接時空,想到以前的語文教師已經(jīng)給他們打下語言、閱讀和文學欣賞的“底色”了。更濃重的“底色”是一邊吟誦這些如詩句那么美妙的詞串,一邊想象并感受家鄉(xiāng)港灣的美麗的自然風光和感人的人文景觀,心中萌動、涌起并積淀著熱愛、保護、建設美好家鄉(xiāng)的情感、責任與使命。語文教學就是這樣不知不覺地滲透著文化及精神的熏陶與感染的。正可謂:“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
學習語文的確是在學習文化。既要學習民族的先進文化,“認識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吸收民族文化智慧”,還要學習人類先進的物質文明和高尚的精神文明,“尊重多樣文化,吸取人類優(yōu)秀文化的營養(yǎng)”。這就涉及古人提到的“文道結合”了。南朝梁代的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中寫道:“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如同欣賞音樂一樣,我們閱讀文章時,也自然而然地受其熏陶,被它感染。新中國成立后也強調(diào)“文道結合”,即語言文字的教育要與情感品德、思想認識的教育統(tǒng)一在語文教學過程中。事實上,學生接觸言語材料,接受言語教育的同時,無不受到字里行間的人物、事件、景色、數(shù)據(jù)中表露的思想、情感、道德、事理的耳濡目染,或真善美、或假惡丑的熏陶感染等。故日本的教育界人士認為:言語的獲得,就是認識的獲得、思想的獲得。[1](530)在這樣的“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過程中,我們要注意教學內(nèi)容價值取向的引導。孔子就認為,教學不但要“博學于文”,還要“約之以禮”。因此,作為語文教師,要使語文課程在義務教育階段圓滿完成它應“獨當”之“任”──組織學生“博學于文”,進行語言教育與言語訓練之外,還要負“分內(nèi)的責任”(葉圣陶語)──“約之以禮”,引導學生求真、向善、趨美。這就涉及注意語文課程與教學、言語材料與內(nèi)容的價值取向了。如果說,熏陶感染是潛移默化的話,那么價值取向就得引導與指點了。語文教師在語文課程與教學中應清楚地意識到教學內(nèi)容價值取向引導的職責,把社會主義的主流價值觀貫穿于語文課程與教學的整個過程之中。
三、語言教學與思維訓練同步
20世紀初,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曾把語言比做一張紙:“思想是正面,聲音是反面……我們不能使聲音離開思想,也不能使思想離開聲音。”[3]當代有關研究表明:人類認知能力(即思維能力)的發(fā)展先于言語能力的發(fā)展。思維能力的發(fā)展影響言語能力的學習與發(fā)展,而語言又會在很大程度上從多方面影響并制約思維。[4]嬰兒來到這個世界時,其大腦和發(fā)音器官就有父母遺傳下來的語言和邏輯的心理密碼。之后在社會環(huán)境的熏陶下,在觀察、模仿大人的說話過程中,基于上述心理密碼,逐漸掌握了語言和邏輯。特別是上學之后,學生活動及感知范圍不斷擴大,形象思維日漸發(fā)達,言語活動不斷增多,語言和邏輯在大腦皮層上也得到不斷的強化和鞏固,開始逐步掌握了本族語言的日常生活交際的最基本部分,這也就意味著掌握了抽象思維的基本部分。[5]語言研究與教學實踐也表明:思維的邏輯形式概念、判斷和推理,與語言單位詞、單句和復句基本對應。可以說現(xiàn)代兒童的言語、語言與思維、邏輯是同時產(chǎn)生,同步發(fā)展的,相輔相成,已逐漸成為語言學界和語文教育界的共識。小學與初中學生的思維主要是指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湖北的一位教師在《撈鐵牛》教學札記片斷四里記載道:課文快學完時,班上有位“百事通”認為“懷丙的方法還需要改進”。因為撈一只大鐵牛,就要鏟掉兩大船沙,使黃河的泥沙更多,水變得更渾濁。教師因勢利導,全班討論得熱火朝天。各小組發(fā)言中,有用水取代泥沙的,有用人取代泥沙的,更有再加兩船,用四艘船輪流鏟沙與拖拉,八次來回就把八只鐵牛打撈上來的設計……這個教學過程的的確確是一邊進行著語言學習,一邊進行著思維訓練。無論是語言的學習(此片斷主要為言語材料學習內(nèi)容的深化與擴展,表現(xiàn)形式為聽話、說話、討論、匯報),還是思維的訓練(此片斷有隨著言語材料學習內(nèi)容與學生認知的深化與擴展,與之同步進行的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都非常到位,且有顯效。
學與教的心理學研究表明,學生的學習心理發(fā)展存在兩類相互作用的活動,一方面是感覺、思維、知覺和智慧的活動,另一方面是感受、情緒、意志和性格的活動。換句話說,在教學情境中,教師要引導學生在這兩類心理活動過程中轉來換去。這位教師的教學札記也表明,片斷四“我認為懷丙的方法還需要改進”的活動過程是基于此前的活動過程(片斷一:“鐵牛怎么會被洪水沖走呢”,片斷二:“起作用的不光是水的浮力”,片斷三:“我還有別的辦法”)上的,它給我們的啟示是:首先是學生學習言語材料過程中的自主質疑,激起解惑的興致與情緒,引發(fā)學生思維的“野馬”在言語材料的“草原”中東奔西突。其次,教師的及時點撥,促使學生的積極思維,并與言語材料的“對話”中,與同學的思維碰撞出新的智慧火花。這時學生的思維往往是多角度、多層次的,富有成效的。這又進一步激發(fā)學生主動而強烈的學習與思考言語材料的情意與心志。最后,教師還要適時引導學生收攏思維的“野馬”,依據(jù)言語材料得出最佳結論。這樣的語言學習與思維訓練同步進行,效果往往很好。又如,湖南的一位教師教人教版七年級上冊《水調(diào)歌頭·明月幾時有》時,學生對“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兩句提出疑問。這位教師順水推舟組織討論:“是在月下起舞還是在月宮起舞?”“是天上美好還是人間美好?”此課置疑、釋疑與存疑的過程,使學生和老師的言語感受與思維砥礪都大有收獲。真可謂學貴有疑,疑則有進矣。這位教師這樣引領的語言學習與思維訓練有機結合,同步發(fā)展,值得提倡。它的確不同于應試教育下“零思考”──不給學生思考的機會,或“淺思考”──給思考機會卻淺嘗輒止,也不同于時下一些“另類思考”的做法──小學教《狼和小羊》時,教師指導學生發(fā)散思維、“獨特體驗”,結果小羊戰(zhàn)勝了狼(或獵人救了小羊)。這樣的求異、創(chuàng)新有違于原作者和選編者的初衷。求異思維、發(fā)散思維、創(chuàng)新思維是必要的,但求異后可否求佳,發(fā)散后可否相對認同,創(chuàng)新也要符合這篇課文的學習在當今時代體現(xiàn)出來的主流價值啊!如果把語言比做人類文化最美的花朵,那么人的思維應該是人類“最美麗的花朵”(馬克思語)。作為義務教育階段的語文教師,應該使這兩朵花開得更加自然而美麗。
要使這兩朵花開得更美,就要組織得當、引導得法,還得關注語言與思維的
四、語言的積累有助于語感的培養(yǎng)
20世紀20年代夏丏尊在《我在國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信念──傳染語感于學生》一文中指出:“一般作教師的,特別是國文科教師對于普通文字應該比學生有正確豐富了解力。對于文學應該有靈敏的感覺。姑且名這感覺為‘語感’。”[6]40年代葉圣陶與夏丏尊合著的《閱讀與寫作》又提出“語感說”。60年代郭沫若在《郭沫若論創(chuàng)作》一書中也提到語感。80年代葉圣陶、呂叔湘也論及語感。到了90年代,語感又成為語文教育界共同的話題。1995年王尚文先生在專著《語感論》中將語感界定為:社會的人對言語的感受與反應。[7](26)具體地說,“語感就是在視聽當下不假思索地從感知語音、字形而立刻理解語音、字形所表示的意義的能力。”[8]至此,我們對“語感”才有了較為科學而合理的解釋。語感之于人,猶如數(shù)感、美感、樂感、節(jié)奏感、球感等,它既有先天的因素,又有后天的原因。就語感之于人來說,既有“語言習得”的因素,又有“語言學習”的原因,而更多的是后者。2000年的義務教育小學與初中《語文教學大綱》和2001年《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多次提到培養(yǎng)語感。這給人以“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感覺,也昭示著語文的教學與研究從此進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時代。國外的母語教育對語感也較為重視。英國小學低段閱讀材料要求之一為“語言富有韻律感、節(jié)奏感,句子對稱”。美國和加拿大的中學則強調(diào)“語言美感”。日本在初中、高中的語文學習指導綱要中分別多次提到培養(yǎng)學生“豐富的語言感受能力”,“訓練語言感覺”。[9](247)
語感培養(yǎng)的確是提高學生語文素養(yǎng)的核心,是語文教學的牛鼻子。抓住了這個牛鼻子,語文教學才能破解“少慢差費”、事倍功半這一令人尷尬的難題,語文素養(yǎng)和教學效果的提高才會事半功倍。葉圣陶早就指出:“文字語言的訓練,我以為最要緊的是訓練語感,就是對于語文的敏銳的感覺。”[10]呂叔湘也指出:“語文教學的首要任務是培養(yǎng)學生各方面的語感能力。”[11]兩位大家言明了語感培養(yǎng)對于學生語文素養(yǎng),對于中小學語文教學的必要和重要。呂叔湘還指明語感培養(yǎng)的內(nèi)容,包括語義感、語法感和語音感。王尚文先生將語感分為:聽讀型語感和說寫型語感兩大類型,前者指聽覺語感與視覺語感,后者指口頭語感與筆頭語感。[12]韋志成先生將語感分為最基本的三類:規(guī)范感、得體感和情味感。[13]大家和專家分別從語言學、語文教育學與修辭學角度出發(fā),談了語感培養(yǎng)的內(nèi)容、類型和要求。筆者認為義務教育階段語文教學中的語感培養(yǎng),首先要從豐富語言的積累入手,來培養(yǎng)學生的字詞句段等基礎語感,具體地說,指的是字詞語感、句子語感、節(jié)段語感和篇章語感等。在此基礎上,再來培養(yǎng)學生的文章語感,具體地說,指的是敘事性語感、描寫性語感、說明性語感和議論性語感等。例如,有位教師在《雨中》一課的教學實錄節(jié)選里,引導學生閱讀理解“淅瀝淅瀝”等形象生動的詞語,“雨中的馬路像一條閃閃發(fā)光的飄帶”等比喻貼切、富有美感的句子以及寫雨景的兩節(jié)詩情畫意般的內(nèi)容時,也非常重視語感培養(yǎng)的過程。其間,教師先是引導學生默讀、劃讀、細讀、想象;接著是談想象中的雨景、自己的感受,以及練寫美麗雨景的片段;然后是聽讀分享雨景片斷以及填空比較,體會自己與作者描述的區(qū)別;最后解讀敘事中“為什么要寫雨景中的景色”。這一教學過程表明這位老師的確是從豐富學生的語言積累來培養(yǎng)字詞句段語感和描寫性語感與敘事性語感的。當然在積累與培養(yǎng)中借助了閱讀、寫作等方式,還借助于想象、感受、比較、體會等方法。尤其是在閱讀、理解、寫作、聽述時,學生調(diào)動了自身的生活與情感積累,容易與作者或讀者心意相契,非常有助于語感的培養(yǎng)。葉圣陶曾說過,“要求語感的敏銳,不能單從語言文字上揣摩,而要把生活經(jīng)驗聯(lián)系到語言文字上去……有了這種準備,才可以通過文字的橋梁,和作者的心情契合。”[14]美國語言學家薩丕爾也指出,語言感覺使語言不但是一種客體的東西,而且也是一種主體的東西。[15]可見,我們在豐富學生的語言積累時,除了豐富他們的語言形式的積累、言語內(nèi)容的積累外,還須豐富學生的生活閱歷的積累、情感體驗的積累和思想認識的積累等等。如此,才能培養(yǎng)學生良好的語感。自古提倡的“厚積薄發(fā)”與葉圣陶的“積累豐富而為文始饒”說的都是這個道理。
需要指出的是義務教育階段中語文教學的語感培養(yǎng)應有階段、有側重地進行。小學階段的基礎語感的培養(yǎng):第一學段可側重于字詞語感和句子語感的培養(yǎng);第二學段可側重于節(jié)段語感,即自然節(jié)與意義段的語感培養(yǎng);第三學段側重于篇章語感的培養(yǎng),如開頭與結尾、過渡與照應等有關篇章語感等內(nèi)容。初中階段(即第四學段)的文章語感的培養(yǎng):七年級可側重敘事性語感與描寫性語感的培養(yǎng),如敘事記人,寫景狀物之類語感的培養(yǎng);八年級可側重說明性語感與議論性語感的培養(yǎng),如解說事物、講清事理之類語感的培養(yǎng),提出觀點、發(fā)表意見之類語感的培養(yǎng);九年級可側重抒情性語感與敘事性語感、議論性語感等綜合運用。如寫景抒情、狀物寓意以及夾敘夾議等等,往往是幾種語感的交叉使用。誠然,以上各階段、各學段的語感培養(yǎng),并非起訖分明,序列井然,其間均有鋪墊與過渡。這里只是強調(diào)各階段、各學段的語感培養(yǎng)有所側重而已。
五、語言的學習離不開言語的實踐
恰似語感的培養(yǎng)離不開積累,需要語言、生活和情感等積累那樣;語言的學習,是口耳之學,它更離不開言語的實踐,即離不開聽說讀寫的實踐。1956年頒布的新中國第一部《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就明確指出:“小學語文科的目的在于提高兒童語言能力,培養(yǎng)兒童正確地聽、說、讀、寫的技能”。可見聽說讀寫這四項言語實踐,一直為人所重,為語言學習所重,并且向來作為語文基本技能,或者說學生的言語實踐能力來看待的。《語文課程標準》也將“適應實際需要的識字寫字能力、閱讀能力、寫作能力、口語交際能力”作為學生的語文素養(yǎng)之一,并要求在語文課程中“著重培養(yǎng)學生的語文實踐能力”,又在“教學建議”里提醒要“注重基本技能的訓練”。
建國以來的語文教學實踐也證明:聽說讀寫是言語實踐有效的基本方式。在聽說讀寫的言語實踐中,學生的言語實踐能力,即聽說讀寫的技能才能逐漸得到培養(yǎng)與提高。明代詩人周立有“一語不能踐,萬卷徒空虛”的詩句,巴金老人說“只有寫,你才會寫”,毛澤東同志也告誡大家要在游戲中學會游戲。教師一味地引導“言說”──傳授聽說讀寫的知識而不“踐行”,學生的語文實踐能力是無法形成的,語言的學習、語感的培養(yǎng)只是一句空話。只有重視在一定情境下的“踐行”,喚起并調(diào)動學生方方面面的積累,注重聽說讀寫的言語實踐,學生的口語交際能力、閱讀能力、寫話、習作和寫作等言語實踐能力才能逐漸形成、提高和發(fā)展。而“言說”的內(nèi)容,聽說讀寫的知識、規(guī)則等,也自會在言語實踐中逐漸得到理解與掌握,語言學習的目的、語感的培養(yǎng)才能達成。這正如張世祿說的那樣,“語文教學的本質特點是注重于言語活動的教育;它的每一環(huán)節(jié)都是富有實踐性的……”[16]國外的語文教育也非常重視言語的實踐性。德國主張給低年級學生創(chuàng)造豐富的學習語言的情境,讓學生在自由的言語的實踐中主動地發(fā)展語言水平。美國《英國教學綱要》的“交際能力”項目中明確提出:“通過讀、寫、說、聽和使用電化中介手段來參加社會事務”。[1](550)而法國的六年級(相當于我們的初一)語文教學大綱中則有“閱讀實踐”“寫作實踐”和“口語實踐”等條目及其具體要求。[9](472-477)可見各國都強調(diào)言語的實踐,并關注實踐的方式與手段。
尚需指出的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入學前已具備一定的聽話、說話能力,具有一定的口頭語言的能力。入學后進行語言學習與言語實踐時,原先擁有的聽話和說話的能力,即口頭語言的能力就可作為他們接受語言學習,進行言語實踐的基礎。有了這個基礎,他們閱讀、寫作的言語實踐能力的提高,就有了一定的前提與條件。如果說入學前具備的聽話與說話能力,即口頭語言的實踐及其口頭語語感的初步形成,是緣于“語言習得”的話;那么入學后小學與初中的“語言學習”,則側重于閱讀與寫作的書面語言的實踐及書面語語感的培養(yǎng)。當然入學后進行的“語言學習”也包含了口頭語言的實踐及口頭語語感的培養(yǎng)。這既有側重又有兼顧的特點在以上幾個教例中都得到體現(xiàn)。因為經(jīng)歷了“語言學習”,閱讀、寫作的言語實踐能力的提高,使學生的書面語語感得到美化和敏化,從而言語規(guī)范、優(yōu)美而得體,這自然有助于口語交際中口頭語語感的提升以及聽話、說話能力的提高。“腹有詩書氣自華”,腹有詩書,自然談吐得體,應對自如。這可謂聽說幫助讀寫,讀寫促進聽說。但是相對于“語言習得”階段來說,在“語言學習”階段,即中小學階段進行語言的教育與學習中,閱讀與寫作的書面言語實踐顯然要重于和多于聽話與說話的口頭言語實踐。這正如葉圣陶說的那樣:“國文教學自有它獨當其任的任,那就是閱讀與寫作的訓練。”[17]也正如韋志成先生指出的那樣:聽說讀寫都要抓,但以讀寫為重點。好似駿馬飛奔四條腿都要動作,但前面兩條腿要長些罷了。
就我們當前的語文學習來說,除了重視聽說讀寫的實踐及其方式或手段的與時俱進之外,書寫漢字的實踐不能忽視。一般來說,聽說讀寫中的“寫”專指寫作,不含寫字。而識字中的寫字往往又是為識而寫。現(xiàn)在的《語文課程標準》繼承與發(fā)揚以往的中小學語文教學大綱的傳統(tǒng),在各個年段的“識字與寫字”領域中,都規(guī)定了寫字的達標要求。每一學段除了書寫識字的數(shù)量要求之外,還有正確、工整、速度、美觀、字體、行款、書寫或輸錄工具的具體要求。這一切,學生需在教師的指導下,經(jīng)過日積月累的書寫等實踐才能達標的。然而應試教育的慣性下,中小學生練寫漢字的實踐機會更少了;再加上處于信息時代,有些孩子還患上提筆忘字的電腦“失寫癥”。這不能不叫人擔憂啊!書寫或寫字能力與口語交際等能力一樣,同為語文基本技能之一,均為學生的語文素養(yǎng)。規(guī)范、端正和整潔地書寫漢字,更是學生成長與發(fā)展的基礎、終身學習能力的基礎。而這些能力的形成、素養(yǎng)的積蓄和基礎的夯實是離不開實踐與培養(yǎng)的。因此,我們常說的語文基本技能“聽說讀寫”中“寫”的內(nèi)涵應包含寫作與寫字。
[1]朱紹禹,莊文中.國際中小學課程教材比較研究叢書·本國語文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陳建民.語言文化社會新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2—3.
[3]〔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158.
[4]何克抗.論語文教育中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培養(yǎng)[DB/OL].http://www.edu.cn/20021010/3069713.shtml.
[5]范曉.關于語言與思維的關系及其相關問題[J].語言科學,2003,(11):82—83.
[6]杜草甬,等.夏丏尊論語文教育[M].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7.
[7]王尚文.語感論(修訂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26.
[8]王尚文.語文教育學導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67.
[9]中外母語教材比較研究課題組.中外母語課程標準譯編[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
[10]葉圣陶.葉圣陶論創(chuàng)作·寫作漫談[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11]呂叔湘.學習語法與訓練語感[J].語文學習,1985,(1):54—55.
[12]王尚文.語感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41.
[13]韋志成.語文學科教育學[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151.
[14]夏丏尊,葉圣陶.閱讀與寫作[M].上海:開明出版社,1940.
[15]申小龍.文化語言學[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329.
[16]張世祿.一定要把語言與言語分開來[N].文匯報,19610225.
[17]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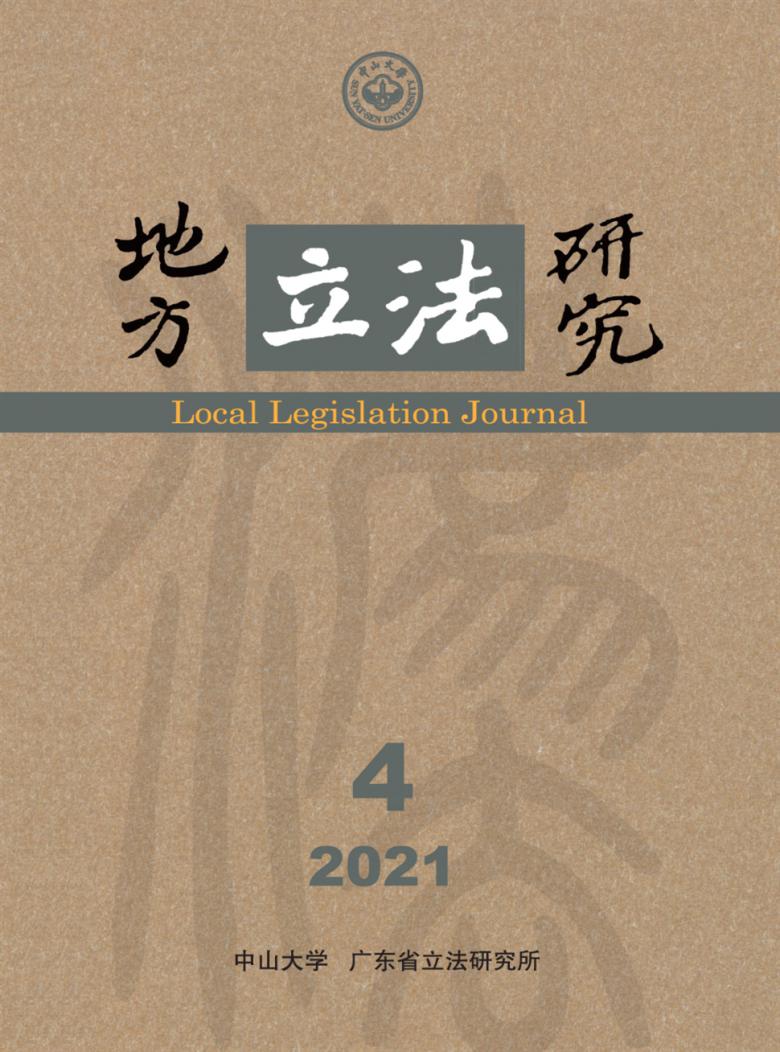


展和改革.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