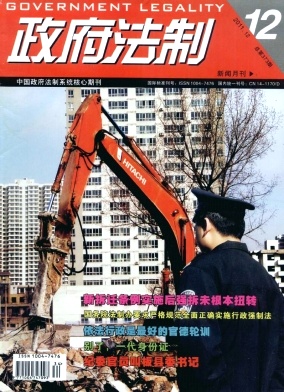法律發現的三種進路
摘要:從功能定位上看,法律發現屬于法律方法的"元問題"。然而,現有的理論研究較少涉獵這一主題,原因與法律發現的屬性和傳統形式邏輯的權威性有關。即便如此,考夫曼、齊佩利烏斯和菲韋格等德國學者對法律發現的技術還是頗有見地。考夫曼在批判傳統的"包攝模式"的基礎上提出了由演繹、歸納、設證和類比架構而成的"等置模式"。這一模式以類推的二層構造作為理論基礎,以事物的本質和法律目的作為中介要素,以比較點的尋找(構成要件的具體化)作為操作規程,并以法官的先前判斷和先前理解作為前置環節。與考夫曼不同的是,齊佩利烏斯將法律發現的規范前提落實于法律規范的結構,將類型化的案件比較作為法律發現的經驗前提,將"拉入視野"的技術、事實與規范之間的往返流轉作為尋找法律規范的基本方法。菲韋格則借鑒了由亞里士多德等先賢所闡釋的論題學,并主張論題學就是為問題尋找前提的技術。通過系統梳理論題學的基本觀點、思維特征,菲韋格從論題學角度對法學的結構提出了三點要求,從而為法律發現確定了前提獲取的范圍和原則。
注: 保護知識產權,如需閱讀全文請聯系法律方法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