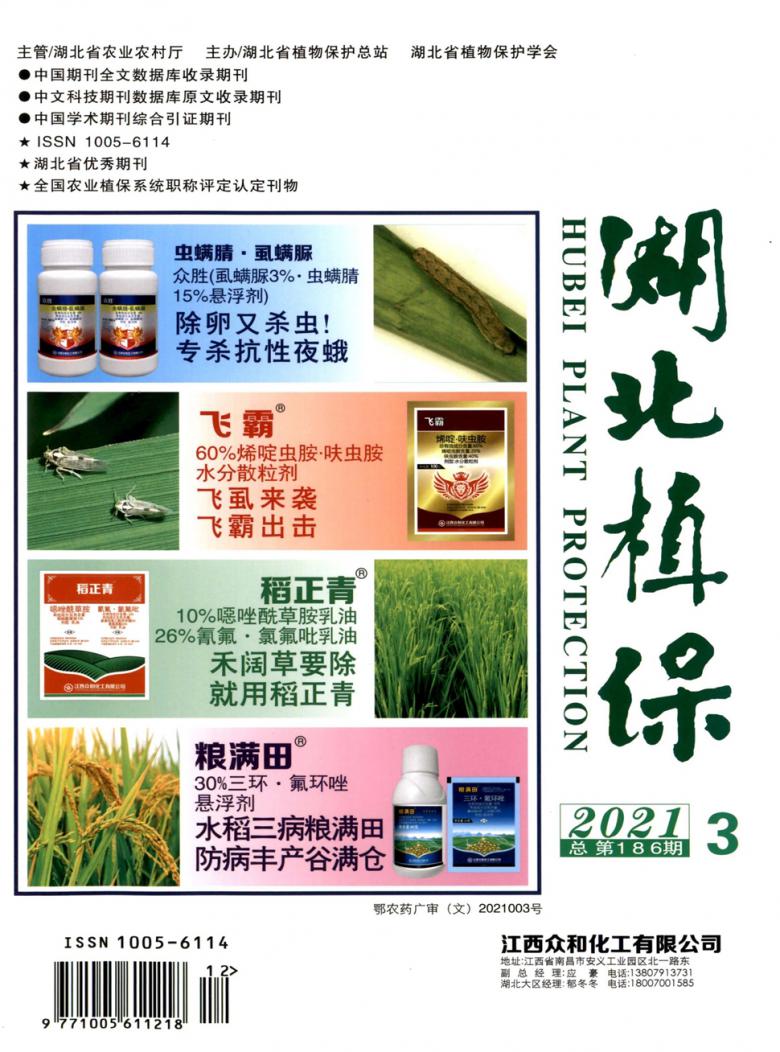中國歷史上肉刑的存廢之爭
趙曉耕 史永麗
1980年代,面臨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我國出現了“法治”與“人治”問題的大討論,此后,人們對法律文化的關注呈現出不斷升溫的趨勢。其重要結果就是:黨的十五大報告強調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并進而在1999年憲法修正案中增加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內容。這標志著我國法治建設的重點將從對法律文化定性的關注轉入對具體法律規范的不斷完善。刑法作為具有中國獨特傳統的一大部門法,其修改完善也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而其中的酷刑問題,則成為刑法學界討論的焦點。我國作為中華法系的代表,是一個刑法傳統發達的國家,以致很多人將我國的傳統法律文化用“重刑輕民,民刑不分”來概括。所以,酷刑問題不僅是一個現實問題,更是我國傳統法律文化歷史發展的延續。而當我們把視角投向中國古代刑罰制度的變遷時,肉刑存廢問題作為我國古代刑制改革的關鍵需要我們認真研究,這將有助于今人更為科學深入地認識現實社會環境下的酷刑問題。
一、肉刑存廢之爭的源起
肉刑是中國奴隸社會刑罰體系的主體。它不僅使人遭受肉體痛苦而且因受刑后特征明顯又有恥辱刑性質。隨著社會進步,肉刑因其殘酷性受到人們的質疑,在西漢文景之時被廢除。
東漢末年至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戰亂不斷、政權更替頻仍,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犯罪數量急劇上升。因此,統治者紛紛乞靈于重刑,妄圖以此來挽救政治危機,要求恢復肉刑的思潮逐漸形成。但由于廢除肉刑順應歷史潮流,所以,恢復肉刑的倡議不可避免地遭到駁斥。兩種觀點當時在朝野上下引起了激烈論戰,進而引發了中國歷史上長達三百多年關于刑罰作用、目的、原則等理論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推動了封建正統刑罰思想的發展,為封建刑罰制度的確立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礎,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反思。
二、肉刑存廢之爭
(一)要求恢復肉刑的主要觀點:
1. 中國遠古就開始適用肉刑并把社會治理得很好,今人也應繼續使用,并且他們在報應刑思想的指導下,認為“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天經地義,只有這樣,才能使罪刑相適應,所以應當恢復肉刑。
中國傳統社會文明是一種崇尚祖先的文明,“奉天法古”思想一直占據重要地位,在刑罰制度的設立方面也是這樣。班固是這種思想的典型代表,他認為只有效法遠古,恢復肉刑,才能罰當其罪,并克服當時社會上因廢肉刑而引起的種種弊端,班固以下持此論者代代有之。如東漢的酒泉太守梁統、名士荀悅;三國魏國的大鴻臚陳紀和御史中丞陳群父子;兩晉的廷尉劉頌等,都反對廢除肉刑,力主恢復古制。
2. 廢除肉刑以仁政為目的,其結果卻是以輕刑之名行殺人之實。
文帝出于恤刑慎殺的目的廢肉刑,但卻被后人認為是“以輕刑之名而內行殺人之實”,原因有兩點:一是漢文帝除肉刑改革將“斬止”并入死刑是加重了處罰,從而與輕刑的目的相左;二是以笞刑代肉刑是為了“全民”,但具體實施中卻因笞數太高而出現“或至死而笞未畢”的局面。例如,三國時魏相國鐘繇認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而御史中丞陳群更是直接抨擊漢文改制為沽名偽飾,實屬“重人肢體,輕人軀命”。
3. 恢復肉刑既可去除犯人的為惡之具,又可警示世人。
這種認識已經接近于近代刑罰理論中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的含義。由于當時社會動蕩不安,要求恢復肉刑以增加刑罰預防作用的主張自然就出現于當時的國家政治生活中。曹魏的袁宏認為:“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鄰里且猶恥之,而況于鄉黨乎?而況朝廷乎?”從而肯定了肉刑的一般預防作用。而御史中丞陳群則是主張增強刑罰特殊預防作用觀點的代表:“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奸矣。”此后各代都有相似的議論。
4. 恢復肉刑可以減少死刑的適用,有利于人口繁衍增長。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長期頻繁的割據爭戰,使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片凋敝景象,需要大量的輕壯勞力為其提供兵源和稅賦來源。漢改刑制把一些肉刑并入死刑,擴大了死刑的適用范圍,而恢復肉刑就可以減少死刑,確為“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于將來”的仁政之舉。魏相國鐘繇認為:“能有奸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晉代持這種觀點的有廷尉衛展、輔政桓玄和大臣蔡廓等。
(二) 反對恢復肉刑的主要觀點
1. 肉刑起源于蠻族,其野蠻殘酷性與華夏文明背道而馳。
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不少大臣從肉刑的歷史源頭來駁斥恢復肉刑的主張。魏朝尚書丁謐認為,肉刑的創制是緣于苗民的暴虐,行于蚩尤的殘暴之世,而為堯舜盛世拋棄使用,以鞭撲流放代之。考其始溯其源,肉刑并非如主復派所言始自三皇,因之三代。以此來作為恢復肉刑的理由缺乏說服力。
2. 肉刑過于殘酷,恢復容易失去民心。
自文帝除肉刑至三國鼎立,正律無肉刑已有三百多年,社會民眾對沒有肉刑也習以為常了。在天下紛爭之時,民心向背是爭霸勝利的有力保障。“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魏司徒王朗在反對恢復肉刑討論中所講的一段話頗有代表性,他說:“前世仁者不忍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以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于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于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
3. 為解決罪刑輕重失調的矛盾,可以用延長居作等方法,而不需要恢復肉刑。
“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一直是恢復肉刑論者的主要理由之一。東漢的后期,已經有不少有識之士認識到這一弊端,并想要進一步完善新刑罰體系。雖然要求恢復肉刑的呼聲很高,但是作為人類文明進步不可逆轉的潮流,一些具有遠見的官員強烈反對恢復肉刑,主張通過延長犯罪人勞役期限的方法,來填補因廢除肉刑而造成的生、死刑制之間差別懸殊,彌補新建刑罰體系中的缺陷。
4. 從刑罰的功效來看,與其恢復肉刑還不如擴大死刑適用范圍來以殺止殺。
肉刑和死刑相比是輕刑,按照“亂世用重典”的原則,死刑尚無法禁惡止奸,肉刑更無法獨懲時弊。這種認識與以往反對恢復肉刑的觀點相反,它把恢復肉刑看作是由重入輕,而非由輕變重,這種認識是當時不斷惡化的社會狀況的現實反映。為了改變當時社會動蕩,民變頻發、盜賊多有的狀況,重刑思想又占據了統治地位,所以,死刑也就自然被看作鎮壓暴民,懲治兇頑的利器。而肉刑不能從根本上消滅個體的反抗,無怪乎尚書周顗、郎曹彥、中書郎桓彝等重臣都反對恢復肉刑來縮小死刑的適用。
5. 維護社會穩定,必須從根本上消除犯罪原因,而僅靠恢復肉刑是不可能消滅犯罪的。
肉刑“損肢體,刻肌膚”,會斷絕罪犯改惡向善的道路,不利于教育廣大民眾。漢末之后的朝廷大臣和學者都認為刑罰的目的主要是預防,但主張恢復和反對肉刑的兩派在如何實現刑罰目的方面存在著很大分歧。與復肉刑一派“去其為惡之具”的報應刑思想不同,反對肉刑恢復一派主張以“教育”作為根本途徑。如孔融認為:他強調適用肉刑并不能使人改惡從善,反而愈發促使受刑之人變本加厲,從而得出了肉刑不應恢復的結論。魏末正始年間,征西將軍夏侯玄認為,要想有效預防犯罪,單靠刑罰是遠遠不夠的,只有盡量使民眾生活富足,在安居樂業基礎上以德導民,依靠道德力量才可能防止犯罪行為的發生。
三、肉刑存廢之爭的結果
隋唐之后,隨著新刑罰體系的確立穩定,肉刑存廢問題也漸漸平復,但此后每當中國社會動蕩紊亂之時,便時有恢復肉刑的論調出現,不過這只是肉刑存廢問題的余波而已,不再能引起社會較大的反響了。而且,作為一種刑罰制度的肉刑體系自從西漢廢肉刑之后便再也沒有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