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xué)者對(duì)中國近代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研究
陳意新
美國學(xué)者對(duì)中國近代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研究的興趣在于界定中國近代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問題并由此而展示解決問題的方案。由于受到原始資料的限制,學(xué)者們得出的結(jié)論很不一樣,甚至對(duì)同一地區(qū)使用同一套資料得出的結(jié)論也不同。正如馬若孟(Ramon Myers)指出:他和黃宗智(Philip Huang)及杜贊奇(Prasenjit Duara)都利用滿鐵(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huì)社)1930-1940年代在中國農(nóng)村所做的調(diào)查資料對(duì)近代華北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做了研究。在他1970年出版了《中國農(nóng)民經(jīng)濟(jì)》一書后,美國學(xué)術(shù)界對(duì)其做了否定的批評(píng),認(rèn)為他的結(jié)論是錯(cuò)誤的,過多地使用了日本人的資料;而黃宗智和杜贊奇在1980年的《華北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變遷》與《華北農(nóng)村的文化、權(quán)力和國家》中得出與馬若孟南轅北轍的結(jié)論后,學(xué)術(shù)界卻稱贊他們的見解新穎獨(dú)到。到了1990年代,絕大多數(shù)歷史學(xué)家又認(rèn)為馬若孟對(duì)史料的運(yùn)用是準(zhǔn)確的。(注:馬若孟著、史建云譯:《中國農(nóng)民經(jīng)濟(j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這些研究結(jié)論的不同和學(xué)術(shù)界的反復(fù)恰恰表達(dá)了美國學(xué)者對(duì)歷史資料的重新認(rèn)識(shí),對(duì)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和中國革命的重新理解,以及他們意識(shí)形態(tài)的取向。
一、卜凱和研究近代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起源
完整理解美國學(xué)者對(duì)近代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研究必須從卜凱(John Lossing Buck)開始,因?yàn)椴穭P不僅劃時(shí)代地建立起了中國近代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一套最完善的調(diào)查資料,并且他對(duì)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看法一直影響著后來的學(xué)者。而卜凱太太賽珍珠(PearlBuck)在1931年出版的寫中國農(nóng)村的小說《大地》不僅當(dāng)時(shí)獲得了普利策和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并且至今仍是許多美國高中的指定讀物,常成為普通美國人認(rèn)識(shí)近代中國農(nóng)村的第一本書。(注:New Hanover County Library,"High school summer reading list",North Carolina,summer,1999.)《大地》講述中國貧農(nóng)王朗(Wang Lung)由苦干而變?yōu)榈刂鞯墓适拢渲姓宫F(xiàn)了卜凱對(duì)中國農(nóng)村的認(rèn)識(shí):中國農(nóng)村存在著平等的機(jī)會(huì),只要肯干,就有可能上升。
卜凱1914年畢業(yè)于美國康乃爾大學(xué)農(nóng)學(xué)院,1916年到達(dá)安徽淮北傳教,1920年受康乃爾大學(xué)的校友、金陵大學(xué)農(nóng)學(xué)院院長芮斯納(John Reisner)的邀請(qǐng)擔(dān)任了金大農(nóng)學(xué)院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教授。1924年卜凱回到康乃爾,于1925年完成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學(xué)碩士學(xué)位后又回到中國。19世紀(jì)30年代,卜凱在出版了《中國農(nóng)場經(jīng)濟(jì)》和《中國土地利用》兩書后,廣泛被尊為世界上關(guān)于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最優(yōu)秀、最權(quán)威的學(xué)者。
卜凱是從農(nóng)場經(jīng)營的角度來認(rèn)識(shí)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在他看來,從經(jīng)營的角度,或者說從農(nóng)業(yè)投資、管理、產(chǎn)出、收入這些范疇來分析,中國近代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主要問題是廣義技術(shù)上的“落后”,除此以外沒有其它特別嚴(yán)重的問題。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直到15世紀(jì)以前還是世界上最先進(jìn)的,到了19世紀(jì)和20世紀(jì)初,歐洲和北美前進(jìn)了,經(jīng)歷了農(nóng)業(yè)革命和商業(yè)革命,而中國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卻沒有進(jìn)步。因此,對(duì)卜凱來說,解決近代中國農(nóng)業(yè)問題的辦法實(shí)際上很簡單:改善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的方式,提高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水平。卜凱為此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一整套、共108條改進(jìn)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建議,其中包括建立農(nóng)村金融設(shè)施、使用良種與化肥、改善交通運(yùn)輸條件等等。(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62-165,181-183.)
卜凱對(duì)中國近代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看法在30年代初發(fā)表后就受到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學(xué)者的批判。1930年代陳翰笙、錢俊瑞等曾在《中國農(nóng)村》雜志上撰文批評(píng)卜凱對(duì)中國農(nóng)業(yè)的調(diào)查方法和結(jié)論。他們認(rèn)為卜凱沒有使用地主、富農(nóng)、貧農(nóng)等這樣一些概念去調(diào)查,因此無視中國土地的分配不均,沒有看到中國的租佃剝削關(guān)系。(注:雷頤:《中國農(nóng)村派對(duì)中國革命的理論貢獻(xiàn)》,《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07-126頁。)卜凱當(dāng)時(shí)沒有對(duì)中國馬克思主義學(xué)者的批評(píng)作出直接的反應(yīng),但他顯然認(rèn)為自己對(duì)中國農(nóng)業(yè)的看法是正確的。卜凱于1922年第一次在安徽蕪湖對(duì)102個(gè)農(nóng)戶經(jīng)濟(jì)做了調(diào)查;然后在1922-1924年對(duì)中國7省17個(gè)地區(qū)2866家農(nóng)戶經(jīng)濟(jì)做了調(diào)查,最后1929-1933年研究中國土地利用時(shí)調(diào)查了22省168個(gè)地區(qū)近16786家農(nóng)戶。這些調(diào)查使卜凱對(duì)中國的農(nóng)戶結(jié)構(gòu)與土地得出的結(jié)論為:華北80%以上是自耕農(nóng),長江流域自耕農(nóng)為60%左右,在四川和廣東自耕農(nóng)為50%左右,并且中國自耕農(nóng)平均擁有3.1畝(1英畝=6.07畝)地。(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175-178,184;Joseph Esherick,"Number games",in Modern China,1981,vol.7,no.4,pp.387-411.)即在卜凱眼里,中國農(nóng)村是一個(gè)以小自耕農(nóng)為主的社會(huì),土地分配并沒有特別不均。此外,在租佃關(guān)系上,西方的佃農(nóng)比例比中國要高得多:中國農(nóng)民中有23%為完全佃農(nóng)(不包括半佃農(nóng)),美國的完全佃農(nóng)占農(nóng)民總數(shù)的38%,英國的完全佃農(nóng)占農(nóng)民總數(shù)的89%,但英美都實(shí)現(xiàn)了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因此,認(rèn)為佃農(nóng)率高了便會(huì)導(dǎo)致剝削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停滯并沒有其必然性的依據(jù)。(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
陳翰笙等中國馬克思主義學(xué)者對(duì)卜凱批評(píng)的要點(diǎn)是認(rèn)為卜凱沒有把中國農(nóng)村的問題看成是一個(gè)社會(huì)問題。美國學(xué)者史特羅斯(Randall Stross)在1980年代也指出:卜凱從美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教科書的觀點(diǎn)來認(rèn)識(shí)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對(duì)中國農(nóng)村的社會(huì)問題視而不見,因此沒能正確認(rèn)識(shí)中國農(nóng)業(yè)的經(jīng)濟(jì)問題。史特羅斯舉例說,卜凱在1920年剛?cè)ソ鸫筠r(nóng)學(xué)院要教4門課: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農(nóng)村社會(huì)學(xué)、農(nóng)場經(jīng)營、農(nóng)場工程,而他手頭主要參考書只有康乃爾大學(xué)農(nóng)學(xué)院教授華倫(George Warren)1913年所出版的《農(nóng)場經(jīng)營》一本教科書。不僅他的4門課全從這本教科書發(fā)展起來,并且他對(duì)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認(rèn)識(shí)也以這本書為基礎(chǔ)。而這本教科書是從經(jīng)濟(jì)學(xué)角度談如何經(jīng)營300英畝理想規(guī)模的美國標(biāo)準(zhǔn)家庭農(nóng)場,不能真正用來詮釋中國農(nóng)村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問題。(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p.162-164,216.)但卜凱畢竟對(duì)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做過大規(guī)模的調(diào)查,并且對(duì)中國農(nóng)村的社會(huì)問題也有認(rèn)識(shí)。例如,卜凱向國民黨政府進(jìn)言108條建議中曾提出要把租佃率做公平的調(diào)整。但卜凱顯然不認(rèn)為租佃率等這樣一些社會(huì)問題是建設(shè)中國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的主要障礙。此外,正如卜凱在《中國土地利用》一書的第一頁所表白:他不準(zhǔn)備“從農(nóng)民和其他社會(huì)階級(jí)之間的政治、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關(guān)系來考慮所謂的土地情況”。(注:John Lossing Buck,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Nanking:Univeristy of Nanking,1937,vol.1,p.1.)換句話說,卜凱認(rèn)為他只是一個(gè)美國人的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學(xué)家,他的責(zé)任是認(rèn)識(shí)中國農(nóng)業(yè)的經(jīng)濟(jì)問題并提出解決的方案,而不是中國農(nóng)村的社會(huì)問題;社會(huì)問題需要通過政治和社會(huì)政策來解決,這不是一個(gè)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的責(zé)任,而是中國政府的責(zé)任。
因此,從卜凱開始,不僅對(duì)中國近代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實(shí)證研究發(fā)展了起來,并且對(duì)中國近代農(nóng)業(yè)問題的認(rèn)識(shí)也分成了兩種觀點(diǎn)。卜凱認(rèn)為中國近代農(nóng)業(yè)問題主要是經(jīng)濟(jì)問題,解決的方案是廣義的技術(shù)進(jìn)步。這一思路形成了后來瑞斯金(Carl Riskin)所稱之為的“技術(shù)學(xué)派”。陳翰笙等中國馬克思主義學(xué)者1930年代也對(duì)中國農(nóng)村的局部地區(qū)做了一些調(diào)查,使用了階級(jí)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結(jié)論是中國農(nóng)村最主要的問題是土地分配不均,因此解決的方案是重新分配土地和財(cái)產(chǎn)。這一思路形成了瑞斯金所稱之為的“分配學(xué)派”。技術(shù)學(xué)派的觀點(diǎn)曾成為國民黨政府制定農(nóng)業(yè)政策的基礎(chǔ),而分配學(xué)派的觀點(diǎn)則成為共產(chǎn)黨社會(huì)革命的理論基石。(注:Carl Riskin,"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in Dwight 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49-84.)
二、中國革命的沖擊和1970年代關(guān)于中國近代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辯論
卜凱的技術(shù)學(xué)派觀點(diǎn)很快受到了中國革命強(qiáng)有力的挑戰(zhàn),使得分配學(xué)派的觀點(diǎn)在1949年之后一度為許多美國學(xué)者所接受。如果中國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問題不是社會(huì)問題,那么中國社會(huì)主義革命為什么會(huì)展現(xiàn)為一場農(nóng)民的社會(huì)革命?或者說如果卜凱的觀點(diǎn)正確,那么中國革命便不會(huì)有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的動(dòng)源。然而,當(dāng)人民公社與大躍進(jìn)災(zāi)難性后果逐漸展露出來后,美國學(xué)者又禁不住要問:中國社會(huì)主義革命對(duì)農(nóng)業(yè)問題的正確性又在哪里?
正是在這種對(duì)中國農(nóng)業(yè)問題的不確定認(rèn)識(shí)之中,馬若孟在1970年出版了他的經(jīng)典性著作《中國農(nóng)民經(jīng)濟(jì)》。馬的這本書寫的是河北和山東,或中國的華北。馬在60年代為這本書做了充分的研究準(zhǔn)備,利用了大量的滿鐵資料,并與當(dāng)年滿鐵在中國的調(diào)查人員做了許多訪談。
馬若孟認(rèn)為:理解近代中國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不能只依賴于1930年代前半期的調(diào)查資料,因?yàn)檫@正是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受到1929年以來世界性經(jīng)濟(jì)大蕭條沖擊的時(shí)刻;陳翰笙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學(xué)者們?cè)?933-1936年所做的調(diào)查只回顧了10年左右的時(shí)間,因此必然會(huì)得出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惡化和農(nóng)村社會(huì)破產(chǎn)的結(jié)論。馬若孟把他的研究范圍確定在1890-1949年之間,即考察從19世紀(jì)末期中國向西方敞開大門開始到20世紀(jì)中期社會(huì)主義革命勝利一段相對(duì)長的時(shí)段。馬對(duì)滿鐵所調(diào)查的沙井村等河北與山東的村莊資料進(jìn)行了詳細(xì)的研究,得出了與卜凱一樣的結(jié)論:近代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問題是廣義上的技術(shù)落后,它沒有其它大毛病。(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292.)
馬若孟認(rèn)為:首先,在1890-1937年間中國的農(nóng)業(yè)產(chǎn)量的年平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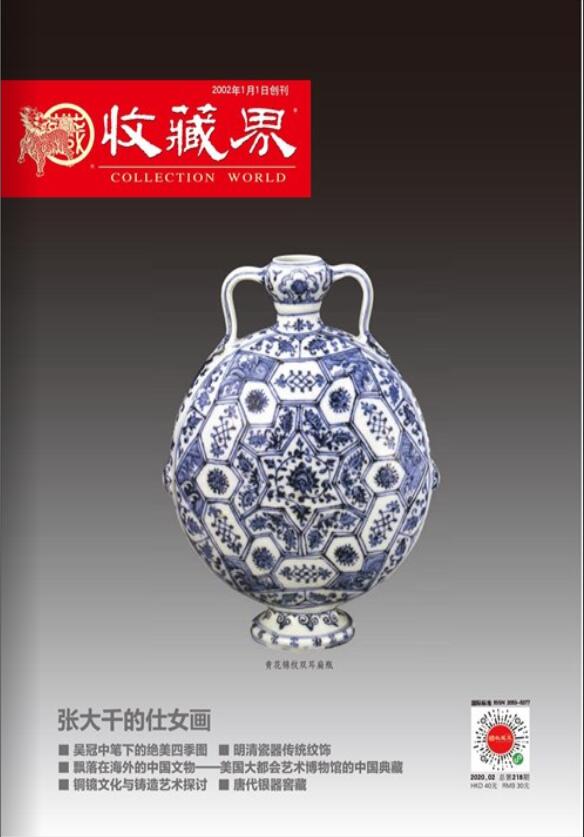
境通報(bào).jpg)
代出版.jpg)
院學(xué)報(bào).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