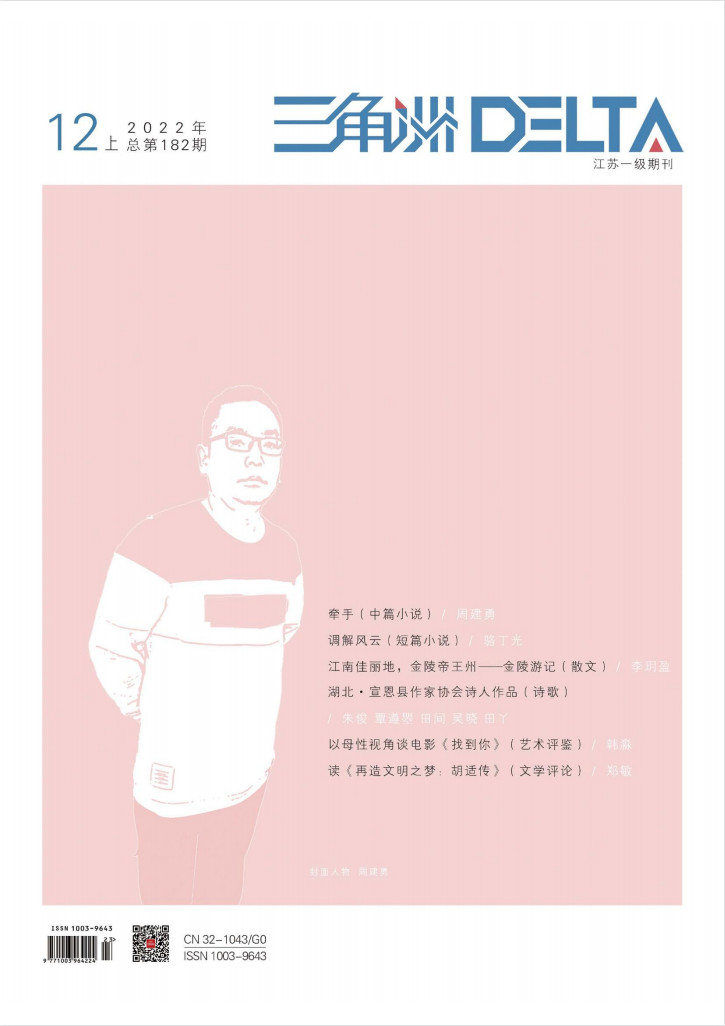從國際法角度看美國測量船闖入中國專屬經濟區事件
佚名
[提要]專屬區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新設立的一個區域,專屬經濟區的地位以及他國在其內所享有的權利一直是國際法學界所關注的之一。美國“鮑迪奇”號海洋測量船闖入專屬經濟區事件,引起人們對他國在該區域所享有的“航行自由權”、“海洋科研自由權”等進行再一次審視。在《公約》下,這種所謂的“自由權”絕對不是什么“不受任何約束”的權利。因此,各國在享有并行使這類“自由權”時,應不忘尊重沿海國的有關權益并遵守國際法準則。
[關鍵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專屬經濟區航行自由權海洋科研自由權
最近,據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報道,美國海洋測量船“鮑迪奇”號多次闖入中國黃海水域進行“勘探工作”,遭遇中國軍機和海軍艦艇的“攔截”和“尾隨”,中國艦船數次向美國測量船發出信號,要求其停止作業并離開這一水域。事后中國政府向美國國務院提出外交照會,抗議美國海洋測量船“鮑迪奇”號侵入中國黃海“專屬經濟區海域”,從事監聽、偵查等“活動”。而美國國防部的某些官員則指責中國的抗議“很無理”,因為“鮑迪奇”號沒有武裝,其水文測量行為并不對中國構成威脅;而且它是在中國海岸以外大約100公里的“公海”上作業,它應享有航行自由權。筆者認為,“鮑迪奇”號是一艘裝滿偵察設備的測量船,它在中國黃海所進行的不是一般的探測活動,而是進行“拖拽式聲納探測”及其他水下監聽活動,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它闖入中國專屬經濟區也絕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而是與去年美國軍機進入中國專屬經濟區上空進行偵察飛行性質類似的事件,是一起值得中美兩國政府認真對待的事件。本文試就該案中所涉及的主要國際法問題作一全面的。
一、“鮑迪奇”號闖入的海域屬于什么性質的海域?
美國政府就這一事件提出的抗辯理由之一,是“鮑迪奇”號是在中國北方海岸以外100公里的“公海”上作業。換言之,“鮑迪奇”號并未侵入中國的管轄水域。但美國政府的抗辯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有關規定嚴重不符,屬于無理狡辯。
盡管傳統國際法奉行“領海以外即公海”,但1982年所簽訂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86條明確規定,公海指“不包括在國家的專屬經濟區、領海或內水或群島國的群島水域內的全部海域”。該公約第57條則規定,所謂的“專屬經濟區”是指“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不應超過200海里”的沿海國海域。根據這兩項規定我們可以得出下列結論:(1)海洋法已將公海限制在各國所主張的“專屬經濟區”之外,而非領海以外;(2)“專屬經濟區”是沿海國可以通過國內立法自行確定其寬度的,但最寬從領海基線量起不超過200海里的海域。
1998年中國政府所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已明確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專屬經濟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以外并鄰接領海的區域,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延至二百海里”。換言之,中國政府已通過該法確立了從領海基線量起寬度達200海里的“中國專屬經濟區”。在本案中,“鮑迪奇”號所處的位子是距中國海岸以外僅100公里的水域,毫無疑問,它正是處于中國的專屬經濟區水域內,而非美國政府所稱的“公海”海域。很明顯,本案實際上是美國政府漠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及中國法律有關規定所產生的結果。
美國一向對他國宣布設立的某種管轄區域采取“漠視”態度,并在行為上予以“否定”或“挑戰”。比如,在上美國軍艦曾闖入被利比亞政府宣布為“歷史性海灣”的錫德拉灣。據稱,“鮑迪奇”號闖入中國專屬經濟區的使命之一,是宣揚美國海軍在此水域的自由航行權。但問題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將設立“專屬經濟區”的權利確定為沿海國自行斟酌是否行使的一項權利,并不要求這一設立行為必須獲得他國的承認,這與設立“歷史性海灣”的條件是根本不同的。在實踐中,各國對專屬經濟區的看法是不同的,有的通過國內立法確立了自己的專屬經濟區,而有的國家則根本沒有設立專屬經濟區。但無論如何,一國不設立專屬經濟區,并不等于它有權以此來否認或對抗別國所設立的專屬經濟區。因此,從國際法上講,即便美國沒有設立專屬經濟區,它也應該尊重中國所設立的專屬經濟區,它根本無權對此予以“漠視”甚至進行“挑戰”。
二、美國測量船在該海域應享有什么樣的“航行自由權”?
美國媒體在就這一事件的報道中提到,美國的船舶、飛機應享有“在12海里領海外包括國際海峽在內的所有海域進行自由航行和飛越”的權利。換言之,美國測量船是有權在中國黃海有關海域進行“自由航行”的。雖然國際法并不否認外國船舶在沿海國的專屬經濟區內享有這種“航行自由權”,但我們必須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有關規定進行全面的分析,才能對“航行自由權”有個正確的認識。
在國際法上,海域中的航行方式主要有“許可通過制”、“無害通過制”、“過境通過制”及“自由通過制”等幾種形式。“許可通過制”主要適用于國家控制的內水范圍內(包括“內陸水”及“海洋內水”兩部分),因此,外國船舶要通過沿海國內水均須事先請求并得到批準才行。“無害通過制”主要適用于沿海國領海、群島水域及部分不適用過境通過制的“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其特點是:外國船舶在不損害沿海國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繼續不停地迅速通過沿海國的領海,而無須事先請求并得到批準。但無害通過制有某些嚴格的限制的因素,比如,外國潛水器通過時必須“上浮水面、展示國旗”,外國的飛機不得作“無害飛越”。“過境通過制”主要適用于“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及群島水域中指定的航道中。其特點是:外國的船舶、飛機在不損害沿海國的主權及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在有關水域“毫不遲延地”迅速通過或飛越,而無須事先請求并得到批準。它與“無害通過制”所不同的是,它不限制飛機的飛越,也不要求外國潛水器必須“上浮水面、展示國旗”。“自由通過制”主要適用于公海及沿海國所控制的“專屬經濟區”及“毗連區”等水域內。其特點是,它不存在那些必須“事先請求并得到批準”、必須“繼續不停地迅速通過”或“毫不遲延地迅速通過”、潛水器必須“上浮水面、展示國旗”等限制性因素。無庸諱言,外國船舶可以在沿海國的“專屬經濟區”內享有航行自由權的這一點是得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充分肯定的。公約第58條規定:“在專屬經濟區內,所有國家,不論為沿海國或內陸國,在本公約有關規定的限制下,享有第87條所指的航行和飛越的自由,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的自由,以及與這些自由有關的海洋其他國際合法用途”。顯然不是我國一些記者所說的,外國船舶在沿海國專屬經濟區內只能享有“無害通過權”。
但是,航行自由權從來就不是什么毫不受任何限制的權利。從上講,“自由”本身應是一種法律狀態,它是受到某種法律因素制約的。各國在公海上航行自由權尚且如此,更何況是他國在沿海國的專屬區內的航行自由權呢!《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58條第三項對此有明確規定,即:“各國在專屬經濟區內根據本公約行使其權利和履行其義務時,應適當顧及沿海國的權利和義務,并應遵守沿海國按照本公約的規定和其他國際法規則所制定的與本部分不相抵觸的法律和法規”。根據公約的此條規定,外國船舶在沿海國專屬經濟區內航行必須尊重沿海國的權利,至少是不損害沿海國的權利。盡管公約本身對“沿海國的權利”沒有作出詳細的解釋,筆者認為這里所稱的“權利”無非有兩類:其一,是指沿海國依據國際習慣法而享有的一般權利,比如沿海國主權、安全及國家利益不受侵犯的權利等;其二,是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賦予沿海國的特定權利。《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56條規定,沿海國在其專屬經濟區內就人工島嶼、設施結構的建造使用,以及就區域內海洋科研及環保享有專屬管轄權。在本案中,“鮑迪奇”號并非一般穿越或經過的專屬經濟區,而是在該專屬經濟區作“軍事性探測”式航行,這種航行行為明顯地侵害了中國的主權和安全利益等一般權利。從另一角度看,其“探測”性的航行行為也侵害了中國在該水域中享有的“海洋科研專屬管轄權”。因此,“鮑迪奇”號的航行行為是不符合國際法中關于專屬經濟區內航行自由權要求的。
三、美國測量船在該海域是否可以進行所謂的“海洋探測”?
美國有關媒體稱,“鮑迪奇”號進入中國黃海的主要使命是進行“水文測量”。但事實是,“鮑迪奇”號在中國專屬經濟區不是進行一般的水文測量,而是進行具有軍事目的的水下監聽和探測,對于它的這種行為也值得從國際法角度一番。
所謂“水文測量”應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說的“海洋”的范疇。該公約雖不禁止他國在沿海國的專屬經濟區內進行海洋科學研究,但對此也規定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公約第240條規定:“海洋科學研究應專為和平目的而進行”。公約第246條規定:“在專屬經濟區內和大陸架上進行海洋科學研究,應經沿海國同意”:“本條所指的海洋科學研究活動,不應對沿海國行使本公約所規定的主權權利和管轄權所進行的活動有不當的干擾”。綜合這幾項規定的我們不難發現,他國在沿海國專屬經濟區內進行海洋科學研究必須具備兩個最基本的條件:
其一,應“為和平目的”而進行。對于什么是“為和平目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沒有具體的規定,但我們大致可以從1958年簽訂的《南極條約》看出這一用語的基本涵義。《南極條約》第1條規定:“南極應只用于和平目的。一切具有軍事性質的措施,例如建立軍事基地、建筑要塞、進行軍事演習以及任何類型武器的試驗等等,均于禁止”。根據這條規定,“用于和平目的”行為應基本上被界定為“非軍事性質的措施”。如依此作合理推論,為“和平目的”所進行的海洋科學研究也應是指“非軍事性質的”海洋科學考察。象“鮑迪奇”號所進行的旨在刺探中國軍事情報并侵害了中國國家安全的海洋探測活動,我們是很難將之歸入為公約所稱之“為和平目的”的海洋科學研究的范疇。
其二,應獲得沿海國的同意,并不應侵害沿海國的主權權利和管轄權。這條規定與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就海洋科學研究享有專屬管轄權的規定是完全一致的。沿海國就此事項享有專屬管轄權,也就意味著沿海國有權許可或拒絕同意進行這種海洋科研活動,有權通過國內立法來約束或規范這種海洋科研活動,也有權對違法的海洋科研考察活動采取任何必要措施。而且,公約在平衡沿海國管轄權與他國在沿海國專屬經濟區內的海洋科學研究權的關系時,基本上將沿海國的管轄權置于他國海洋科研權之上的。基于這一點,他國船舶能否在沿海國專屬經濟區內進行海洋科研以及在什么條件下進行此類海洋科研,應完全按沿海國的法律、法規的要求來辦。我國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第9條明確規定:“任何國際組織、外國的組織或者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進行海洋科學研究,必須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管機關批準,并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法規”。在本案中,“鮑迪奇”號在中國專屬經濟區內進行的所謂“水文測量”根本就沒有得到中國政府主管機關的批準,已嚴重地侵害了中國政府在該區域的專屬管轄權。
由此可見,“鮑迪奇”號在中國專屬經濟區內的所謂“水文探測”活動在國際法上屬于不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要求的海洋科研活動,按中國國內法也應屬于非法的海洋科研活動。
四、中國政府對“鮑迪奇”號采取的行動是否得當?
在“鮑迪奇”號闖入中國專屬經濟區后,中國的海軍艦艇及軍機對之進行了“攔截”和“尾隨”,這是符合國際法規定的正當行為。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賦予沿海國對其專屬經濟區以專屬管轄權的同時,為了有效地實現這種管轄權,也賦予了沿海國對區域內違法行為采取必要措施的權力。《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73條規定:“沿海國行使其勘探、開發、養護和管理在專屬經濟區的生物資源的主權權利時,可采取為確保其依照公約制定法律和規章得到遵守所必要的措施,包括登臨、檢查、逮捕和進行司法程序”。公約第111條則規定:“沿海國主管當局有充分理由認為外國船舶違反該國法律和規章時,可以對該外國船舶進行緊追”:“對于在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上,包括大陸架上設施周圍安全地帶內,違反沿海國按照本公約適用于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包括這種安全地帶的法律和規章的行為,應比照適用緊追權”。換言之,沿海國為實施其法律、法規,完全可以對在其專屬經濟區內的外國違法或違章船舶采取登臨、檢查、逮捕或緊追等必要的強制措施。對于公約的這些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也有相應的規定。該法第1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行使勘查、開發、養護和管理在專屬經濟區的生物資源的主權權利時,為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法規得到遵守,可以采取登臨、檢查、逮捕、扣留和進行司法程序等必要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在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法規的行為,有權采取必要措施、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并可以行使緊追權”。很明顯,中國軍艦和軍機對“鮑迪奇”號采取的強制措施,無論是在方式上還是在程度上都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有關規定,屬于按中國國內法所進行的正當執法行為。筆者甚至認為,如以后外國船舶在中國專屬經濟區內再從事類似的違法行為,我們完全可以將之扣留、逮捕并依法予以懲處。
以上只是從國際法的角度對“鮑迪奇”號事件中的一些基本法律作了些粗略的分析,事實上還有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比如,美國作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之一,它為什么會公然無視該公約的有關規定,肆意地侵害別國的利益?美國憑什么將自己權利和要求凌駕于別國的合法權利之上,認為它的“自由權”(如“航行自由權”、“飛越自由權”、“科學調查自由權”等)應優先于別國基本權利,甚至可以優于別國的主權?為什么在發生了“中美撞機案”后的不久,美國又故態復萌再一次侵入中國管轄水域?它的意圖究竟是什么?這些問題均有待于我們國際法學者以及國際關系學者作進一步的、更深層次的分析了。“鮑迪奇”號事件已經成為過去,雖然它算不上中美關系上重大磨擦和分歧,但對于這類小問題我們絕不能等閑視之,我們應當從國際法的角度予以合理地主張和抗辯,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效地抑制某些國家公然“漠視”或侵害我們合法權益的行為,有效地維護我國的國際地位以及維護國際的正常法律秩序,為世界和平與安全作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