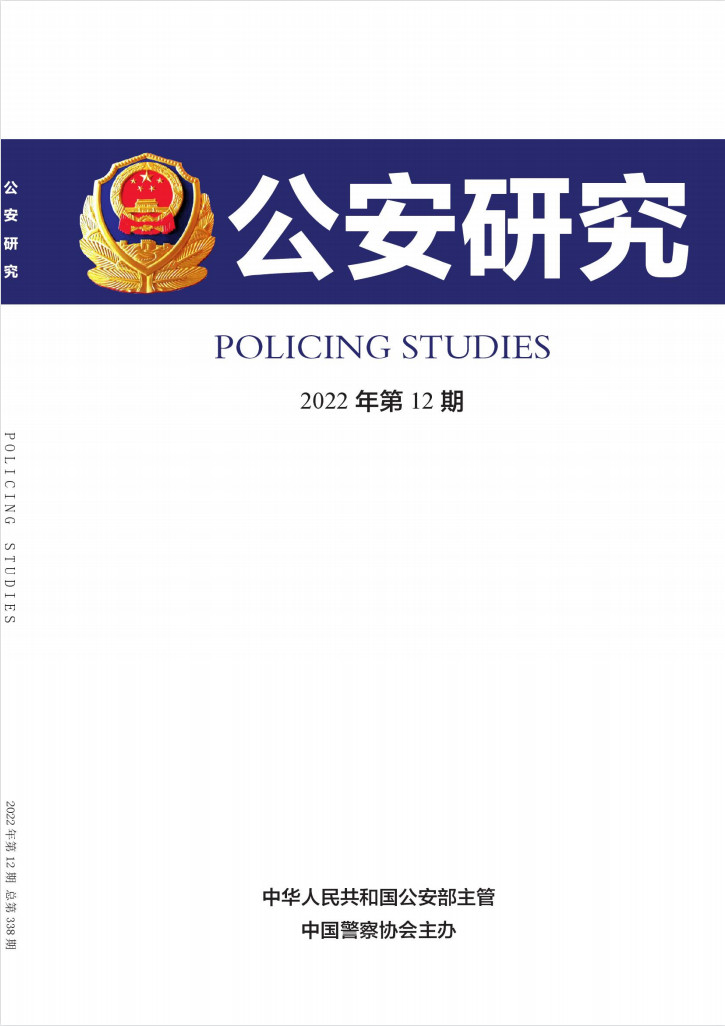邊際優勢戰略下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來自日本對東亞投資
楊宏恩
基于對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在世界經濟發展和本國經濟發展中重要性的認識,當前對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的關系的研究越來越多。除了一些研究明確地以政策制定為目的,另外一些純粹的研究同樣為政策制定提供了借鑒。作為政策制定者,將一種研究的結果上升為國家戰略,則更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邊際優勢戰略即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例子。日本通過它很好地協調了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的關系,獲得了經濟的巨大成功。日本邊際優勢戰略的主要對象是東亞,而中國同樣在東亞,與日本有著相近的文化;與此同時,中國是世界上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對外投資日益增加,貿易總量也排在世界前列,相應地也在越來越多的方面具有了和日本相似的經濟特征。因此,充分認識邊際優勢戰略下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將對我國外資和外貿政策的制定有所借鑒,同時也為我國制定長遠的對外經濟戰略有所幫助。
談到邊際優勢戰略以及日本經濟的成功,我們不免想起“東亞模式”和“雁行模式”。本文的研究也將反映出“東亞模式”和“雁行模式”之間的本質聯系,這同樣有益于我國在發展同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經濟關系方面政策的制定。
一、文獻回顧
按照主體的不同,對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的關系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以東道國為主體,研究東道國外來投資和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這種研究除了母國和東道國之外涉及到第三國,投資和貿易之間的關系也相對疏松。另一類以母國為主體,研究母國對東道國投資與兩國貿易之間的關系。在此只涉及母國和東道國,投資與貿易之間的關系相對密切。本文的研究即屬于后者,本文中的國際投資指對外直接投資,即FDI。
首先對國際投資與貿易關系進行研究的是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undell(1957)。Mundell的研究以標準的古典國際貿易模型為基礎,通過嚴格的假定,得出了國際投資替代國際貿易的結論。在隨后的60年代,又有學者的研究支持了投資替代貿易的結論,其中較著名的是Vernon(1966)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按照該理論,一般情況下,投資和貿易只是一種轉化關系,只有在投資提早發生的情況下,才發生投資對貿易的替代,而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條件下,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因此國際投資對國際貿易的替代越來越明顯。另一個研究來自于Johnson(1967)。Johnson認為,關稅導致的對外投資使不具有比較優勢的進口替代部門獲得了發展,因此減少了對外貿易量。
70年代開始出現投資和貿易具有互補性的研究成果。Helmberger和Schmitz(1970)的研究證明生產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可能既有替代關系也有互補關系。這一時期最著名的論著來自于。日本小島清教授(1977)。小島清特別強調國際分工的重要性,將對外投資和貿易統一在國際分工的基礎上,指出國際投資不是簡單的資本流動而是包括資本、技術、管理方式和人力資本的總體轉移。因此,對外投資應從本國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依次進行,這就是本文所談邊際優勢戰略的理論基礎。按照小島清的理論,國際投資一方面可以通過相近水平的技術轉移把東道國的比較優勢發掘出來,另一方面使母國集中資源開發新的技術并形成新的產業,因此將會擴大兩國的貿易。
無論是Mundell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還是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梁志成,2001)。這既有統計數據殘缺不全的限制,也有計量方法與工具上的局限。20世紀80年代以來,貿易和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同時更多的研究成果證明投資與貿易之間具有互補關系。Lipsey和Weiss(1981)依據美國70年代的統計數據,對美國跨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所設立的子公司的生產和母公司的出口行為進行了研究,發現同類產品的子公司的年產量與母公司對這些國家的出口總量呈正相關關系。Lipsey等人(1984)還進一步研究發現這種正相關或至少非負相關廣泛存在于美國近80%的產業部門中。Helpman和Krugman(1985)的研究表明,在要素稟賦不對稱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情況下,由于跨國公司的專有資產很難通過外部市場達成交易,就會存在大量的公司內貿易和對中間產品的需求,對外投資將會帶動母國的出口貿易。Ethier(1986)的研究給出了同樣的結論。Grossman和Helpman(1989)把產品的成長內生化,證明了在一個動態的模型中國際化生產和貿易可以是同時擴大的。然而,Markuson和Svensson(1985)則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貿易和要素流動(FDI)的相互苯系,指出兩者之間究竟表現為替代還是互補,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還是“非合作”的問題。
90年代的研究延續了80年代的趨勢。Hufbauer、Lakdawalla和Malani(1994)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上述Lipsey和Weiss(1981)的結論,他們重點研究了美國80年代以來的情況,發現在整個時間跨度中出口與FDI一直保持著正相關關系。隨后Gramham(1996)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Pattie(1994)根據對外投資的動機不同將FDI分為市場導向型、生產導向型和貿易促進型3類,認為只有市場導向型FDI容易替代對外貿易,而后兩種類型投資則增加貿易。Gray(1998)的研究得出了近似的結論。Pfaffermayr(1994)就奧地利FDI和出口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了分析,發現它們之間具有雙向的因果關系。Jun和Singh(1992)研究了1969—1993年間11個世界上最大引資國的出口和FDI的關系,其中有4個國家顯示出口是FDI的格蘭杰原因,只有一個國家顯示FDI是出口的格蘭杰原因,其余6國顯示出口和FDI之間不存在顯著的因果關系。與此同時,Porter(1990)、Hein(1992)、Lucas(1993)、Crosse和Trevino(1996)、Crosse(1997)等都證明了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存在高度的相關性。但不可忽視的是,Beldelbos和Sleuwaege。(1998)的研究支持了Mundell的結論,即在東道國存在貿易保護的情況下,FDI會替代母國的出口貿易。
2000年以后的研究以大量具體的實證研究為特征,且研究結果以FD!與貿易之間具有互補關系為主。張如慶(2005)的研究顯示我國對外投資不是進出口變化的原因,對外投資對貿易總額的影響不明顯,而項本武(2005)得出的“中國對外投資是出口創造性和進口替代型”的結論對此給予了解釋。王洪亮和徐霞(2003)證明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和中日貿易之間的確存在著長期的互補關系,FDI和制成品的出口具有雙向的因果關系,但FDI和進口僅有單向的因果關系。王洪慶、張浩和朱榮林(2004)的研究表明,美國在華投資與對中國總進口、工業品進口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與工業品出口之間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投資與出口以及中美的初級產品進出口之間均不存在因果關系。同時,王洪慶和朱榮林(2004)的研究表明,東盟對華直接投資積極地推動了中國與東盟貿易的發展,且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貢獻率較高。李保明和劉震濤(2004)的實證結果顯示,兩岸貿易總額、大陸進口和出口均表現出關于臺商投資的顯著正相關性,這說明臺商投資對兩岸貿易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此外,Stone和Jeon(2000)研究認為貿易與海外直接投資之間為互補關系,且兩者之間貿易更傾向于為主導因素;韓國學者Lim和Moon(2001)證明,當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投資,而投資是新設立的或者投資產業在母國是夕陽產業時,FDI和貿易之間是正相關關系;Blonigen(2001)深入到產品層次進行了分析,發現貿易和FDI之間既有替代也有互補的關系,而且替代效應的發生不是逐步的,而是短時間急劇變化的。
基于本文研究的側重,在此再對邊際優勢戰略和小島清的邊際優勢理論進行進一步的說明。邊際優勢戰略的概念來源于小島清的邊際優勢理論,但應該注意的是,邊際優勢戰略所代表的經濟行為早已存在,只是由小島清概括出來。邊際優勢理論更多地是一種國際投資理論,但因為它把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在同一基礎上進行分析,所以對投資和貿易的關系也給予了研究。同時也正因為它側重于國際投資的研究,對兩者關系的研究也并不全面。按照邊際優勢理論,對外投資應該從國內處于邊際優勢即相對劣勢的產業開始,而處于相對優勢的產業則進行對外貿易。按照小島清的分析,對邊際產業的產品需求應通過向海外投資的企業進口來實現。所以,小島清論述的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更多地是母國投資與進口之間的關系,這是一種單向的正相關關系。但與此同時,小島清也論述了兩國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張和貿易總量的增加,間接地論述了投資和出口的關系,這同樣是單向的正相關關系。但是,基于邊際優勢戰略,對投資和貿易之間的關系作這樣的理解還遠遠不夠,況且如上所說,小島清的理論是基于對現象的描述與分析,沒有通過計量方法得到實證檢驗,而本文將在上述方面給予補充和進一步的研究。
二、日本對東亞投資和貿易的歷史進程及兩者關系的描述
二戰以后至20世紀60年代,通過美國的幫助和自身的經濟改革,日本經濟得以恢復并實現了高速增長。而正是在60年代以后,很多東亞國家和地區(主要是亞洲“四小”、東盟四國和中國)紛紛實現了經濟起飛和長期快速發展,使東亞地區成為了世界經濟發展的熱點,以至于使人將這種發展狀態稱為“東亞奇跡”。很久以來,對“東亞奇跡”的研究存在著大量的各種形式的成果。在這些成果中,我們不難發現兩個最受人關注的詞匯:東亞模式和雁行模式。通過這兩種模式的論述,可以發現,先期發展起來的日本對上述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東亞模式揭示了上述東亞國家和地區對日本經濟發展經驗的借鑒和模仿,因而東亞模式被認為源于“日本模式”(孔凡靜,1999),同時東亞模式更多地強調了貿易尤其是出口的重要性。雁行模式揭示了日本與這些東亞國家或地區的國際分工關系,強調了日本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尤指直接投資)的重要性。所以,東亞模式和雁行模式的研究都說明了日本與這些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聯系在“東亞奇跡”中的關鍵作用。在此也可以理解,本文研究的日本對東亞國家或地區的投資和貿易之間的關系反映了東亞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