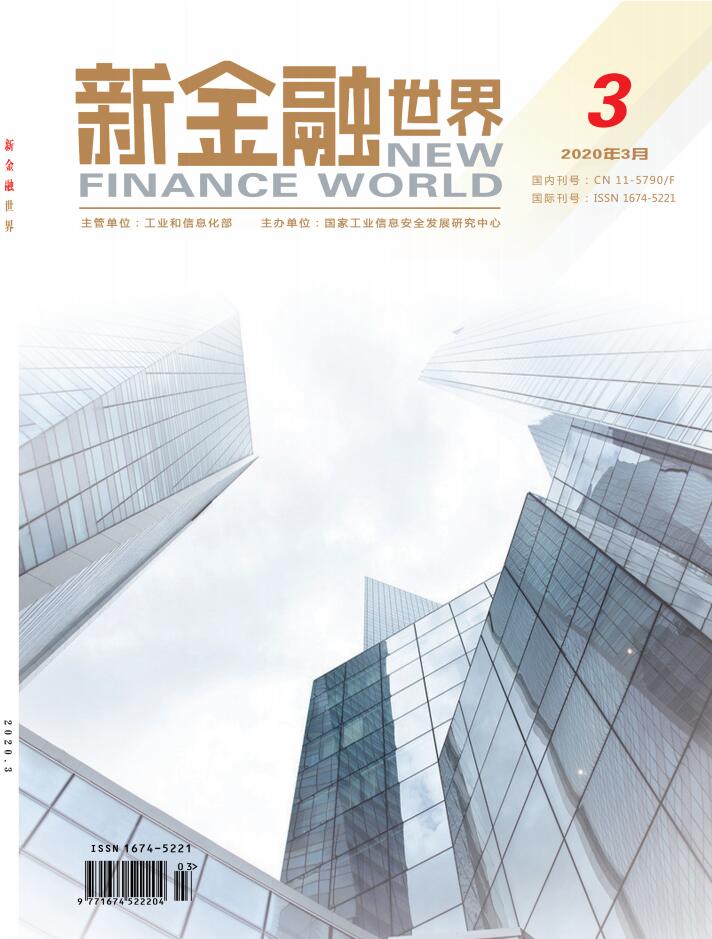從中國傳統哲學文化看周恩來外交思想
王湛森
摘要:周恩來是舉世公認的杰出外交家,他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周恩來深邃的外交思想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外交學說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而且還折射出中國傳統哲學文化的火花。從中國傳統哲學文化的角度進一步探究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可以給我們更多的啟示。
關鍵詞:中國傳統周恩來哲學文化外交思想 周恩來從小受到了良好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他的思想中處處可以找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打下的烙印。外交思想是周恩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周恩來的外交思想當中可以看出中國傳統哲學文化的影子。周恩來曾提出:外交行動要“見機行動”,要抓住時機,“守如處子、動如脫兔”;對待外交矛盾時要“恪守后發制人的原則”,“決不開第一槍”,“退避三舍,“有來不往非禮也”,“要禮尚往來”;要善于根據不同的外交問題,分別采取“針鋒相對”,“外松內緊,引而不發”,“有備無患”,“細水長流”,“見縫插針”等方法區別對待處理。周恩來在外交場合曾公開承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對其外交風格的影響。他在1963年會見埃及客人時就闡發過中國辦外交的思想:“我們中國人辦外事有這樣一些哲學思想。要等待,不要強加于人………這些優秀的哲學思想來自我們優秀的民族,不完全是馬列主義的教育”。因此,我們可以從中國優秀傳統哲學文化的角度去進一步研讀周恩來外交思想。 一、和平共處與中國傳統“和為貴”的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和為貴”、“尚和合”的哲學思想。這種和合不是異質事物簡單相加堆砌,而是各種不同性質的事物相互對立、沖突繼而融合趨同的一個辯證過程。《國語》中就有“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肢以衛體,和六律以充耳”、“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之論;《莊子》中也提到“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中庸》的作者寫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里體現了中為本,和為道的思想。《易傳》則強調“天人合一”,靠“和”來協調融合。《易傳》中有“夫大人者,與天地和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之說。以上這些都反映出中國傳統哲學文化中“天人合一”、“和為貴”的思想內核。這些論述著重強調了異質事物對立斗爭,再而融合再生的過程。這更是一種和諧共生共存之道。周恩來在外交實踐中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 周恩來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處。在周恩來經歷的眾多外交事件中都體現著他追求和平共處,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恩來被任命為總理兼共和國的首任外交部長。新中國成立伊始,外交政策、方針和外交任務究竟是怎樣?中國的外交往何處去?這不僅是外界所關心的,更是新中國外交事業不容回避的問題。新中國的外交政策一開始就堅決執行和平外交政策,將“和平共處”“革命不能輸出”的思想貫徹始終。 1949年11月8日,周恩來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做過這樣的論述“我們現在的外交任務是分成兩個方面的。一方面,是要同蘇聯人民和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兄弟情誼。我們在斗爭營壘上是屬于一個體系,目標是一致的,都為持久和平”。和平成為我國外交的一大目標。1950年,正當美國企圖將朝鮮戰爭擴大化時,周恩來就約見了印度大使潘尼迦,他指出“我們要和平,我們要在和平中建設。過去一年中我們在這方面已經作出了極大的努力。美國政府是靠不住的”。1953年6月,周恩來在闡述國際問題的主要矛盾是戰爭與和平問題這一重要思想時就指出“我們主張通過和平協商解決一切國際糾紛。”“帝國主義既怕和平,又怕戰爭,我們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戰爭。我們主張和平,反對戰爭”。 1954年,周恩來正式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不僅是中國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事件,而且對世界外交事業深刻的影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經作為普遍適用的國際關系準則。爭取和平,在和平中共處事是周恩來在外交事業中孜孜以求的。 二、求同存異與中國哲學的異同觀 “同”與“異”是一對哲學命題。中國哲學文化中對這對哲學命題有十分精辟的論述。在中國哲學史上“和”與“同”是相互區別的兩個哲學范疇。古人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古代的哲人一方面強調事物之間的差異性,明確地指出承認差異性的必要性。《荀子》中寫道“同則同之,異則異之,知異名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荀況從名實相副的角度論述了承認事物差異性的意義。宋朝哲學家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指出“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這段話說明了“太極”是基于“異”存在。另外一方面,古代哲人又辯證的看到事物的差異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矛盾對立雙方可以實現轉化。有“求同”的可能性。在這方面有比較深刻論述的是道家創始人老子。他在《道德經》中指出“反者道之動”,“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細”。老子通過闡述大小、難易、高下、禍福、有無等一系列矛盾在特殊情況下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關系。以上的這些論述都是關于“同”與“異”關系的思辨。這里兩者的內涵應該是“和合”而不是“去異”。承認差異并不是一定要消滅差異。“和諧統一”是一種新的境界。 “求同存異”的外交思想是周恩來對中國哲學辯證思維在外交領域的創造性發揮。周恩來的一生經歷了無數的外交風云,他總是冷靜沉著,細心觀察,善于在對立中積極尋找一致性,以更好地減少對立沖突,盡量擴大共識。這一點也是周恩來高超的外交藝術的生動體現。對于“求同存異”,他在會見埃及客人時談到“處理涉外分歧的時候要等待,不要將己見強加于人。事情總是勉強不得的”。1955年,周恩來率團參加亞非會議,當會議遇到逆流陷入僵局時,周恩來發言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亞非國家的共同之處是“是要解除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與支持,而不是相互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與對立”。縱覽周恩來的一生,他總是誠摯而又耐心地實踐著“求同存異”的原則。時至今日,這一點依然是指導著中國辦外交的重要哲學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