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對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增長的影響
黃少安 孫圣民
本文運(yùn)用計(jì)量和統(tǒng)計(jì)分析的方法,對1949—1978年中國大陸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進(jìn)行實(shí)證分析。分析結(jié)果表明,在不同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下,所激勵(lì)的生產(chǎn)要素投入量不同,從而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出有較大不同;在投入相同的生產(chǎn)要素和政策要素下,農(nóng)業(yè)的產(chǎn)出也有不同。綜合比較后認(rèn)為:“所有權(quán)農(nóng)民私有、合作或適度統(tǒng)一經(jīng)營”是相對較好的制度。因?yàn)樵谶@種制度下,能較大程度地激勵(lì)各生產(chǎn)要素的投入,土地和勞動(dòng)等要素的利用率也較高,從而使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高速而穩(wěn)定增長.
關(guān)鍵詞 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 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 面板數(shù)據(jù)分析
作者黃少安,1962年生, 山東大學(xué)經(jīng)濟(jì)研究中心教授(濟(jì)南 250100);孫圣民,1975年生,山東大學(xué)經(jīng)濟(jì)研究中心博士生(濟(jì)南 250100); 宮明波,1980年生, 山東大學(xué)經(jīng)濟(jì)研究中心博士。
————————
一、引言
自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的農(nóng)業(yè)取得了巨大發(fā)展,但也走過了一條曲折的路。據(jù)統(tǒng)計(jì),1950—1978年的29年間,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年增長在10%以上的有5年,負(fù)增長的也有5年,增長速度低于2%,基本上處于停滯的有3年。①這種起伏,可能與勞動(dòng)力、土地、化肥、役畜和農(nóng)業(yè)機(jī)械等生產(chǎn)性投入有關(guān),也可能與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事業(yè)的財(cái)政投入、工農(nóng)業(yè)產(chǎn)品價(jià)格差等政策因素有關(guān),更重要的是,受到其間以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為主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制度變遷的影響.本文就是試圖揭示這種影響。我們力圖盡量準(zhǔn)確地定量分析,但是需要克服兩個(gè)困難:一是1949一1978年間有關(guān)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的缺失,有關(guān)該期限內(nèi)中國大陸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的研究資料也比較少;二是土地制度對農(nóng)業(yè)產(chǎn)出的影響雖然客觀存在,但是不能直接度量,從而不能對土地制度的效率做出評價(jià)。本文對1949一1978年影響農(nóng)業(yè)產(chǎn)出的各種投入和政策因素進(jìn)行了分析,進(jìn)而分析出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對農(nóng)業(yè)產(chǎn)出的作用。
————————
① 參見李德彬、林順寶等編《新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紀(jì)事》(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9年)第l頁。
從理論上說,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會(huì)從兩個(gè)方面影響土地產(chǎn)出。一是直接影響,即土地產(chǎn)權(quán)安排對人們的激勵(lì)不同,從而影響人們投入生產(chǎn)的人力、物力和財(cái)力;二是間接影響,是指在不同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下,即使投入相同數(shù)量的勞動(dòng)力、生產(chǎn)資料等,也會(huì)有不同的產(chǎn)出。這是因?yàn)樵诓煌漠a(chǎn)權(quán)制度下,人們勞動(dòng)的積極性以及使用生產(chǎn)資料的效率是不同的.本文嘗試對兩種影響進(jìn)行定量分析.我們把以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為主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制度變遷作為主線,可以根據(jù)普遍現(xiàn)象或總體特征,大體上將1949—1978年分為以下幾個(gè)典型階段(每一個(gè)階段都可能有更小的階段,或者有上一個(gè)或下一個(gè)階段的少量現(xiàn)象或特征存在,對此,本文不再做具體劃分和分析):1949—1952年實(shí)施以“耕者有其田”為目標(biāo)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后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是土地分散私有、分散經(jīng)營.它不同于“土地改革”前的“地主集中私有、農(nóng)民在地主一定的統(tǒng)一規(guī)劃和支配下分散租佃經(jīng)營”;1953—1958年實(shí)行對農(nóng)業(yè)的社會(huì)主義改造階段,開始是政府引導(dǎo)、農(nóng)民自愿參加的互助合作階段,產(chǎn)權(quán)制度還是“所有權(quán)農(nóng)民私有、合作或適度統(tǒng)一經(jīng)營”,后來在政府的強(qiáng)制下,基本上實(shí)行了“土地集體所有、集體統(tǒng)一經(jīng)營”;1959—1962年實(shí)施強(qiáng)制性人民公社化階段,即土地變成了更大范圍內(nèi)的公有——人民公社統(tǒng)一所有,公社統(tǒng)一經(jīng)營;1963—1978年實(shí)行所謂的“三級所有、隊(duì)為基礎(chǔ)”,也就是劃小了公有的單位——由公社所有變?yōu)榇蠖鄶?shù)耕地為生產(chǎn)小隊(duì)所有,同時(shí)劃小了經(jīng)營單位——生產(chǎn)小隊(duì)統(tǒng)一經(jīng)營。
我們嘗試運(yùn)用計(jì)量分析的方法,對1949—1978年中國大陸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進(jìn)行實(shí)證分析,分析影響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的各因素,如勞動(dòng)力、土地、化肥、役畜和農(nóng)業(yè)機(jī)械等投入變量,以及支持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事業(yè)的財(cái)政數(shù)量、農(nóng)產(chǎn)品收購價(jià)格指數(shù)、農(nóng)村工業(yè)品零售價(jià)格指數(shù)等政策變量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的影響。從而也能一定程度上分析不同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對農(nóng)業(yè)的影響。
本文先對此時(shí)間跨度內(nèi)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分四個(gè)階段進(jìn)行計(jì)量回歸,并對結(jié)果進(jìn)行說明。在定量分析的基礎(chǔ)上得出結(jié)論,并且說明受到的啟示.
二、l949一1978年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的計(jì)量分析
在下面的分析中使用的數(shù)據(jù),包括中國大陸31個(gè)省、市、自治區(qū)中的28個(gè)在1949—1978年間的常規(guī)投入,如勞動(dòng)力、土地、化肥、役畜和農(nóng)業(yè)機(jī)械,以及農(nóng)業(yè)產(chǎn)出數(shù)據(jù)。①此外,還包括產(chǎn)業(yè)政策導(dǎo)向因素,如支持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事業(yè)的財(cái)政支出數(shù)量、農(nóng)產(chǎn)品收購價(jià)格指數(shù)、農(nóng)村工業(yè)品零售價(jià)格指數(shù)等政策變量。由于無法得到各省、市、自治區(qū)各時(shí)期能夠代表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變遷的數(shù)據(jù),本文在計(jì)量中沒有將其作為一個(gè)自變量進(jìn)行處理.關(guān)于資料具體出處和調(diào)整、換算的詳細(xì)情況在文章附錄中給出,這里僅列出數(shù)據(jù)處理的主要過程和結(jié)果。根據(jù)上文描述的中國大陸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階段性,下面的分析也按如下四個(gè)時(shí)間段進(jìn)行,即1949—1952年、1953—1958年、1959—1962年、1963—1978年。
本文中,農(nóng)業(yè)產(chǎn)出使用的是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y),主要是糧食和經(jīng)濟(jì)作物的產(chǎn)值,與之相近的一個(gè)概念本文也將用到,即農(nóng)林牧漁業(yè)總產(chǎn)值(y1),是指包括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y)在內(nèi)的農(nóng)業(yè)、林業(yè)、牧業(yè)和漁業(yè)的合并值。
————————
① 數(shù)據(jù)主要來自國家統(tǒng)計(jì)局國民經(jīng)濟(jì)綜合統(tǒng)計(jì)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tǒng)計(jì)資料匯編》 (中國統(tǒng)計(jì)出版社,1999年),其中包括中國大陸最新區(qū)劃的31個(gè)省、市、自治區(qū)的數(shù)據(jù),港、澳、臺除外。由于重慶市劃為直轄市時(shí)間較晚,并不在本文考察的時(shí)間跨度內(nèi),另外海南省和四川省由于個(gè)別重要數(shù)據(jù)不全(如缺失農(nóng)業(yè)產(chǎn)值的連續(xù)時(shí)間序列,也沒有可以用來換算的相應(yīng)的指數(shù)等指標(biāo),即使予以估計(jì)也將帶來較大誤差),所以本文所用數(shù)據(jù)不包括這3個(gè)省份的數(shù)據(jù)。
投入數(shù)據(jù)中包括四種:土地、勞動(dòng)、化肥、役畜和農(nóng)業(yè)機(jī)械。土地(1)使用的是農(nóng)作物總播種面積,而非糧食面積,因?yàn)檗r(nóng)業(yè)產(chǎn)出中使用的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主要是糧食和經(jīng)濟(jì)作物的產(chǎn)值,而并非僅是糧食作物的產(chǎn)值,這樣可使土地投入和產(chǎn)出的衡量對象一致。
勞動(dòng)(1ab.)指的是在糧食和經(jīng)濟(jì)作物等種植業(yè)中的勞動(dòng)者人數(shù),而這個(gè)數(shù)據(jù)無法直接得到,本文根據(jù)鄉(xiāng)村從業(yè)人員(1ab)的數(shù)量進(jìn)行了換算.鄉(xiāng)村從業(yè)人員中包括在種植業(yè)、動(dòng)物飼養(yǎng)、漁業(yè)、林業(yè)等生產(chǎn)中的勞動(dòng)者人數(shù),為了得到種植業(yè)部門中的勞動(dòng)力估計(jì),鄉(xiāng)村從業(yè)人員按農(nóng)作物產(chǎn)出占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出的價(jià)值份額,即按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y)占農(nóng)林牧漁業(yè)總產(chǎn)值(y1)的份額,進(jìn)行了加權(quán)。這樣可使勞動(dòng)投入和產(chǎn)出衡量的對象一致.
化肥(fer)指的是化肥施用量(折純量),由于各個(gè)時(shí)期化肥使用量數(shù)據(jù)的缺失,本文結(jié)合各省市自治區(qū)化肥產(chǎn)量和本地區(qū)化肥施用的變化規(guī)律,運(yùn)用相應(yīng)的方法對化肥施用量進(jìn)行了換算。
役畜(m1)和農(nóng)業(yè)機(jī)械(m2)中,本文將兩者換算為一個(gè)變量。役畜數(shù)是參照每年底大牲畜頭數(shù)來取得的,這是由于在1978年以前,中國大陸主要省份用于直接消費(fèi)的大牲畜頭數(shù),與用于耕作的役畜數(shù)相比比較小,可以忽略不計(jì)。當(dāng)然個(gè)別省份情況比較特殊,所以做了特別處理。農(nóng)業(yè)機(jī)械投入是以農(nóng)業(yè)機(jī)械總動(dòng)力來衡量的,這個(gè)數(shù)據(jù)可以直接獲得,部分缺失的數(shù)據(jù),根據(jù)中國大陸在1970年以后才真正推進(jìn)農(nóng)業(yè)機(jī)械化的實(shí)際,并結(jié)合各省份已有的數(shù)據(jù)進(jìn)行了換算。役畜的單位是頭,根據(jù)每頭役畜為o.7馬力的標(biāo)準(zhǔn),將其換算為馬力數(shù),一馬力相當(dāng)于0.735千瓦,這樣一頭大牲畜相當(dāng)于O.5145千瓦的農(nóng)業(yè)機(jī)械動(dòng)力數(shù)。①將役畜和農(nóng)業(yè)機(jī)械的單位統(tǒng)一起來,并作為一個(gè)變量引入分析中去。
————————
① 這種換算比例由國家統(tǒng)計(jì)局建議采用,參見林毅夫《制度、技術(shù)與中國農(nóng)業(yè)發(fā)展》 (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4年)第100頁.
產(chǎn)業(yè)政策導(dǎo)向因素,如支持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事業(yè)的財(cái)政數(shù)量(f)、農(nóng)產(chǎn)品收購價(jià)格指數(shù)(p1)、農(nóng)村工業(yè)品零售價(jià)格指數(shù)(Pi)等政策變量,均可以從資料中獲得.其中,支持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事業(yè)的財(cái)政數(shù)量,是指地方財(cái)政支出中支持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事業(yè)的數(shù)量,它是一個(gè)年度中用于本省份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事業(yè)發(fā)展的各種支付的歸并值,包括中央對地方農(nóng)業(yè)的支付.農(nóng)產(chǎn)品收購價(jià)格指數(shù)、農(nóng)村工業(yè)品零售價(jià)格指數(shù)被引入,主要用來反映國家制定的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政策,體現(xiàn)在農(nóng)民出售農(nóng)產(chǎn)品和購人用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工業(yè)品的價(jià)格上,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的影響。
關(guān)于表1的說明:
(一)本文類似于生產(chǎn)函數(shù)法設(shè)定方程,用面板數(shù)據(jù)法(panel data)進(jìn)行回歸。具體回歸方程為:
(五)在所有的回歸中,變量log(m’)均未通過90%的顯著性檢驗(yàn),表明該變量對產(chǎn)出影響很小。這可能是因?yàn)樵跀?shù)據(jù)換算中,用年底大牲畜頭數(shù)代表役畜數(shù)存在誤差,在將其與農(nóng)業(yè)機(jī)械總動(dòng)力加總后,由于農(nóng)業(yè)機(jī)械總動(dòng)力部分?jǐn)?shù)據(jù)的不準(zhǔn)確,將這種誤差放大了。另一種可能是,在1953—1978年經(jīng)歷的三種農(nóng)作制度,即對農(nóng)業(yè)的社會(huì)主義改造、人民公社化、生產(chǎn)小隊(duì)體制,雖然從統(tǒng)一經(jīng)營的意義上看,更有利于相對大型機(jī)械的使用,集體也可能更有能力購置機(jī)械,但是可能不利于農(nóng)業(yè)中農(nóng)業(yè)機(jī)械積極作用的發(fā)揮,機(jī)械的利用率低或者說對提高產(chǎn)出的作用有限.而1949—1952年實(shí)施土地改革階段,雖然是明確的土地等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但由于役畜和農(nóng)業(yè)機(jī)械的使用均相對較少,對產(chǎn)出影響不大,造成了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yàn)。
(六)在1949—1952年的回歸中,作為變量的土地投入量,其影響的顯著性不高,表明在這個(gè)時(shí)間段中土地投入對產(chǎn)出影響很小,但在其他年份的回歸中,這個(gè)變量對產(chǎn)出的影響卻很大,這有兩個(gè)可能:(工)真實(shí)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2)1949—1952年數(shù)據(jù)不足,回歸不準(zhǔn)確。后者可能性更大。
(七)可以看出,影響產(chǎn)出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土地、勞動(dòng)、化肥使用量。另外,財(cái)政支持農(nóng)業(yè)數(shù)也是影響產(chǎn)出的一個(gè)因素。
(八)四個(gè)時(shí)間段比較來看。若不考慮1949—1952年,在1963—1978年化肥使用量的產(chǎn)出彈性最大;1953—1958年次之,1959—1962年最小。在1959—1962年,土地投入的產(chǎn)出彈性最大;1953—1958年次之;1963—1978年土地投入的產(chǎn)出彈性最小。在1953—1978年,勞動(dòng)投入的產(chǎn)出彈性基本上保持穩(wěn)定,但在1953—1958年產(chǎn)出彈性最大。在1953—1962年,財(cái)政支持農(nóng)業(yè)數(shù)對產(chǎn)出的影響不顯著,但在1963—1978年,這一變量的影響增加很大。
(九)若不考慮1949—1952年中數(shù)據(jù)不足帶來的問題,在這個(gè)時(shí)間段中,勞動(dòng)投入的產(chǎn)出彈性在四個(gè)時(shí)間段中最大.
(十)另外,經(jīng)過計(jì)算,結(jié)果說明人力資本引發(fā)的勞動(dòng)力投入變動(dòng)對產(chǎn)出的影響極小,在回歸分析中可以不考慮人力資本因素對結(jié)果影響.
對表2的說明:除了1949—1952年的常數(shù)項(xiàng)不能通過90%的t檢驗(yàn)以外,其余可以通過檢驗(yàn)。
下面的表3是相應(yīng)年份和變量的全國數(shù)據(jù),由于資料中給出的數(shù)據(jù)不全,其中的斜體字為估計(jì)數(shù)值(估計(jì)方法與附錄中相同),加粗字體為1949—1952、1953—1958、1959—1962和1963—1978四個(gè)時(shí)間段中,數(shù)據(jù)較全的典型點(diǎn)數(shù)據(jù),本文將在下面的分析中使用這些數(shù)據(jù),配合前面的計(jì)量結(jié)果進(jìn)行進(jìn)一步討論。
為了便于觀察和分析,可以依據(jù)表3計(jì)算出不同時(shí)間段、也就是不同產(chǎn)權(quán)狀態(tài)下的要素投入增長率和農(nóng)業(yè)產(chǎn)出增長率,列為表4。
對表3和表4的分析:
1949—1952年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出現(xiàn)迅猛增長,年平均增長率達(dá)到13.81%.土地投入、化肥施用量和農(nóng)業(yè)動(dòng)力投入有較大幅度提高,年平均增長率分別達(dá)到工4.94%、183.33%和27.46%.但勞動(dòng)投入下降了2173萬人,年均下降4.06%.投入農(nóng)業(yè)的勞動(dòng)力減少可能與當(dāng)時(shí)的戰(zhàn)爭和支援戰(zhàn)爭占用大量人力有關(guān)。化肥和農(nóng)業(yè)機(jī)械(1952年僅為18萬千瓦,只相當(dāng)于當(dāng)年動(dòng)力總數(shù)的O.04%)等投入絕對數(shù)量十分小.還有一點(diǎn)需要重視:此期間國民經(jīng)濟(jì)、包括農(nóng)業(yè),具有明顯的恢復(fù)性質(zhì),從長期戰(zhàn)爭和動(dòng)亂時(shí)期轉(zhuǎn)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因此,無論是要素投入的增加還是產(chǎn)值的增長,都是恢復(fù)性的,與相應(yīng)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相關(guān)度不可高估。
1953—1958年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和各生產(chǎn)要素投入均穩(wěn)定增長,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年平均增長率達(dá)1.36%.勞動(dòng)、土地、化肥年均增長2.03%、1.11%、89.20%,土地和農(nóng)業(yè)動(dòng)力投入僅在1958年稍有下降(因?yàn)榇笠?guī)模“工業(yè)化”)。化肥和農(nóng)業(yè)機(jī)械(1957年僅為121萬千瓦,只相當(dāng)于當(dāng)年動(dòng)力數(shù)的2.73%)等技術(shù)因素投入絕對數(shù)量上相對落后。這一階段,雖然要素投入增長速度和產(chǎn)值增長速度都不是很快,但是增長平穩(wěn)。而且,經(jīng)過幾年恢復(fù)性增長后,可用于增加的要素已經(jīng)很有限,帶有技術(shù)性的要素又很缺乏,再加上國家的工業(yè)化開始明顯占用更多資源。所以,從要素增加速度和產(chǎn)出增加速度看,這一階段都不是很快,但是不等于投入和產(chǎn)出的比率不高。
1959—1962年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出現(xiàn)大幅波動(dòng),可以看出1959年和1960年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銳減,分別比上年下降12.19%和5.80%,1961年雖有好轉(zhuǎn),但只是比1958年稍有提高(另外一種說法是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在1959、1960年和1961年分別下降了14%、12%和2.5%)。1959—1962年4年勞動(dòng)力平均比1958年減少2%,土地年平均投入比1958年減少5%,化肥年均增加4.3%,農(nóng)業(yè)動(dòng)力年均增加3。5%。農(nóng)業(yè)產(chǎn)出年均下降5.6%.
顯而易見,伴隨著人民公社化運(yùn)動(dòng)(產(chǎn)權(quán)的“一大二公”)的是嚴(yán)重的農(nóng)業(yè)危機(jī)。勞動(dòng)力和投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勞動(dòng)力都減少(大量非正常死亡、因饑餓不能勞動(dòng)或外出盲目流動(dòng)),土地大量拋荒.作為當(dāng)時(shí)農(nóng)業(yè)動(dòng)力投入主要內(nèi)容的役畜數(shù)量下降(1959一1962年分別為7912、7336、6949、7020萬頭)。化肥施用量也出現(xiàn)大幅度波動(dòng),往年迅速增長的態(tài)勢已經(jīng)趨緩.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可以說與自然災(zāi)害有關(guān),但是更多的是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人為變化——人為提高公有化程度的影響.
與之相應(yīng),1959、1960年和1961年支持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事業(yè)的財(cái)政數(shù)量(f)出現(xiàn)大幅上揚(yáng),農(nóng)產(chǎn)品收購價(jià)格指數(shù)(P1)上升,并拉大了與農(nóng)村工業(yè)品零售價(jià)格指數(shù)(Pi)的差距。這是在國民經(jīng)濟(jì)困難時(shí)期財(cái)政對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民救災(zāi)性的政策。從前面的計(jì)量分析結(jié)果可知,前者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回升有效,后者可能無效。
1963—1978年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和要素投入增長相對平穩(wěn)。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年均增長7.03%,化肥、農(nóng)業(yè)動(dòng)力和財(cái)政支持的年增長率分別為49.84%、17.1%和16。45%,要遠(yuǎn)大于勞動(dòng)和土地的年均增長率2.09%和0。47%,其中農(nóng)業(yè)動(dòng)力投入的增加主要源于農(nóng)業(yè)機(jī)械化的推廣。和前面三個(gè)階段相比,在勞動(dòng)和土地增長較小的情況下(在一倍的增幅以下),化肥、農(nóng)業(yè)動(dòng)力和財(cái)政支持的數(shù)量卻增長了數(shù)倍。這一階段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是在經(jīng)歷了經(jīng)濟(jì)嚴(yán)重挫折后調(diào)整過的“三級所有、隊(duì)為基礎(chǔ)”。在該制度下,可以看出,土地和勞動(dòng)力投入雖然仍在增長,但是遠(yuǎn)遠(yuǎn)趕不上化肥和農(nóng)業(yè)動(dòng)力的增長速度.我們可以認(rèn)定:在這種制度下,有利于農(nóng)業(yè)機(jī)械的推廣和運(yùn)用——因?yàn)槭谴蠹w,既有能力(相對于分散私有)購置農(nóng)業(yè)機(jī)械,也便于使用機(jī)械(相對分散經(jīng)營)。但是,有一點(diǎn)很明確:農(nóng)業(yè)機(jī)械和化肥投入數(shù)倍的增長,遠(yuǎn)遠(yuǎn)沒有換取農(nóng)業(yè)產(chǎn)值應(yīng)有的增長,至少可以說,這些投入在當(dāng)時(shí)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下利用率很低.
為了比較相同或可比較的生產(chǎn)要素投入情況下,各時(shí)間段相應(yīng)土地制度下的產(chǎn)出情況,可利用已經(jīng)求得的4個(gè)回歸方程(每時(shí)間段一個(gè),包括各自的常數(shù)項(xiàng)),分別將表3中4個(gè)典型點(diǎn)(分別采自4個(gè)時(shí)間段中):1952、1957、1962年和1965年的各投入要素和政策變量數(shù)值,分別代人4個(gè)回歸方程中,得出16個(gè)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數(shù)量。也就是假定分別把1952、1957、1962年和1965年度的投入要素分別投入4個(gè)階段不同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下,觀察產(chǎn)值,然后對不同制度做比較和評價(jià)。這種方法類似于反歷史事實(shí)計(jì)量法(新經(jīng)濟(jì)史學(xué)的方法)。下面的表5是檢驗(yàn)和比較的結(jié)果。
關(guān)于表5的說明:
(一)應(yīng)該對所有年度的數(shù)據(jù)加以檢驗(yàn),之所以只選擇表5中4個(gè)年度的數(shù)據(jù),是因?yàn)槠溆嗄甓葦?shù)據(jù)缺乏,有一些是估計(jì)的,如果全部使用,會(huì)增加不準(zhǔn)確性。
(二)作為回歸結(jié)果的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和表3中相應(yīng)時(shí)間段內(nèi)實(shí)際產(chǎn)值有差異是正常的,因?yàn)榍蠼饣貧w方程時(shí)使用的數(shù)據(jù)是省際數(shù)據(jù),表3中的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是全國的數(shù)據(jù)。
(三)表中括號內(nèi)的數(shù)值,是根據(jù)波德(Borda)計(jì)算法①,按各行數(shù)據(jù)大小,分別賦予一個(gè)權(quán)數(shù),如產(chǎn)值最大賦予4,較大賦予3,較小賦予2,最小賦予l。最后一行是各時(shí)間段縱向的權(quán)數(shù)之和。
(四)由于1949—1952年的回歸中存在部分未能通過檢驗(yàn)的誤差,所以其排序和權(quán)數(shù)也會(huì)有一定誤差。其余時(shí)間段的估計(jì)和賦值相對比較準(zhǔn)確。
從表5中可以看出,在投入相同的生產(chǎn)要素和政策要素下,不同階段上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不同,從而農(nóng)業(yè)產(chǎn)出不同。按綜合得分來看,在投入相同的生產(chǎn)要素和政策要素下,1953—1958年的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最大,1963—1978年最小,1959—1962年和1949—1952年居中。這里體現(xiàn)了不同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對農(nóng)業(yè)增長的影響.
需要說明,借用這種方法,只能大體說明問題,大體顯示了制度優(yōu)劣,不具有準(zhǔn)確性。
通過以上的大致比較,發(fā)現(xiàn)1963—1978年間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比1958—1962年間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還要差(相對于農(nóng)業(yè)增長而言),人們可能覺得不可信或不好理解。其實(shí)也是可以解釋和理解的。因?yàn)椤肮缃y(tǒng)一所有、統(tǒng)一經(jīng)營”真正存在和發(fā)揮作用的時(shí)間極短,1958—1962年間,特別是1959—1962年間,已經(jīng)是特殊的時(shí)期了,既不是“公社統(tǒng)一所有、統(tǒng)一經(jīng)營”的制度(因?yàn)閷?shí)際上已經(jīng)不起作用),也不是“三級所有、隊(duì)為基礎(chǔ)”,反映的要素投入和產(chǎn)值變化情況不完全是“公社統(tǒng)一所有、統(tǒng)一經(jīng)營”下的情況。但是,1959—1962年的狀況又確實(shí)是1958年制度的結(jié)果,因而在上面分段時(shí),把這幾年歸為一段,即“公社統(tǒng)一所有、統(tǒng)一經(jīng)營”。
三、結(jié)論和啟示
以中國大陸1949一1978年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要素投入和農(nóng)業(yè)產(chǎn)出的相關(guān)性為研究對象,通過計(jì)量和統(tǒng)計(jì)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jié)論:
————————
① 這是讓一夏爾·波德(Jean-Charles de Borda)于1781年提出的一種表達(dá)偏好強(qiáng)度的方法。參見喬.B.史蒂文斯《集體選擇經(jīng)濟(jì)學(xué)》(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9頁。
(一)不同階段的不同產(chǎn)權(quán)制度,對人們投入土地、勞動(dòng)、化肥等生產(chǎn)要素的激勵(lì)程度確實(shí)不同(剔出了一些該剔除的因素以后得到的結(jié)論)。這是直接影響。
(二)如果投入相同的或者可比的生產(chǎn)要素,在不同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下,要素的利用率不同。這是間接影響。
(三)綜合考察和分析各時(shí)間段不同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對農(nóng)業(yè)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可以認(rèn)為:“所有權(quán)農(nóng)民私有、合作或適度統(tǒng)一經(jīng)營”是相對較好的制度。因?yàn)樵谶@種制度下,能較大程度地激勵(lì)各生產(chǎn)要素的投入,單位土地和勞動(dòng)等要素對產(chǎn)出的貢獻(xiàn)率也較高,從而使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高速而穩(wěn)定增長。
通過以上對歷史的分析,引發(fā)了我們多方面的思考.對我們思考中國農(nóng)村土地制度現(xiàn)狀和演變方向的啟示如下:
中國土地制度與經(jīng)濟(jì)增長和發(fā)展的相關(guān)性,是非常值得研究的。1949年或者更早一些至今的中國大陸土地制度的變化,就非常具有研究的理論和實(shí)際意義。這種研究現(xiàn)在不是多了、透了,而是不夠。本文只是在數(shù)據(jù)不太全面的情況下對1949—1978年間不同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對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增長的影響進(jìn)行了計(jì)量分析.但這種有限的研究對認(rèn)識我國土地產(chǎn)權(quán)的歷史、現(xiàn)狀和思考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進(jìn)一步變革還是有重要啟示的。歷史上的“農(nóng)民分散私有、分散經(jīng)營”制度曾經(jīng)短期內(nèi)使要素投入及其利用率都有大幅提高。以保留農(nóng)民土地私有權(quán)、自愿合作開始的合作化運(yùn)動(dòng),卻以土地公有(確切地說是公社所有)、公社統(tǒng)一經(jīng)營結(jié)束,從非常有利于要素投入和農(nóng)業(yè)增長開始,到使農(nóng)業(yè)陷于危機(jī)結(jié)束。人們可能會(huì)作如下假設(shè):如果合作化運(yùn)動(dòng)一直在保留農(nóng)民所有權(quán)和自愿前提下進(jìn)行,可能是一個(gè)理想的制度演進(jìn)路徑。但是歷史不能假設(shè),“三級所有、隊(duì)為基礎(chǔ)”的產(chǎn)權(quán)安排已經(jīng)是危機(jī)后不得不做出的“退讓”了,這個(gè)時(shí)期平均的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增長率并不低,可是,要素投入后的利用率卻很低,中國人民在較高的年增長率背景下一直未能解決溫飽問題。
家庭承包制的“集體統(tǒng)一所有、農(nóng)民家庭分散經(jīng)營”是中國大陸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重大創(chuàng)新,其短期的重大作用已經(jīng)被事實(shí)證明。但是其局限性在上個(gè)世紀(jì)80年代中后期已經(jīng)顯現(xiàn)。它與1949—1952年的制度有類似:都是分散經(jīng)營,農(nóng)民都有了屬于自己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但是不同的是:那時(shí)農(nóng)民有所有權(quán),而家庭承包制下農(nóng)民沒有(盡管農(nóng)民可能一定程度上有所有權(quán)幻覺,也確實(shí)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所有權(quán)的權(quán)能和收益)。對這種產(chǎn)權(quán)矛盾或模糊的狀況,黃少安曾經(jīng)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有所揭示和解釋——農(nóng)民沒有所有權(quán),卻能拿承包的土地人股、獲得土地股權(quán)、分享股權(quán)收益,當(dāng)時(shí)把這種情況稱為“準(zhǔn)土地股權(quán)”①。值得重視的是,上個(gè)世紀(jì)8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農(nóng)業(yè)中的股份合作制確實(shí)類似上個(gè)世紀(jì)50年代的股份合作制(1953—1958年間的前期).只是80年代的農(nóng)民沒有法律和實(shí)際上的完全的土地所有權(quán)。
2003年實(shí)施的《中國農(nóng)村土地承包法》賦予承包地以物權(quán)保護(hù)、允許轉(zhuǎn)讓,是否還是介于有無所有權(quán)之間?給農(nóng)民一個(gè)不完整的土地所有權(quán)或有一定的所有權(quán)幻覺和現(xiàn)實(shí),是否是現(xiàn)階段可行的產(chǎn)權(quán)安排(中國特色的農(nóng)業(yè)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如果農(nóng)民擁有現(xiàn)有土地的全部所有權(quán),是否可行、有何利弊?對于這些問題,是需要認(rèn)真研究后才能給與答案的.這可能需要重大的理論創(chuàng)新。就政策操作層面提出建議時(shí),我們需要更加慎重.不過我們有理由認(rèn)為(歷史也可以告訴我們):保留所有權(quán)(哪怕是不完整的所有權(quán)或非真正意義上的所有權(quán)),實(shí)行自愿前提下的適度統(tǒng)一經(jīng)營,走上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農(nóng)場式經(jīng)營,可能是中國農(nóng)業(yè)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和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組織形式的理想而可行的變革方向。
————————
① 黃少安:《從家庭承包制的土地經(jīng)營權(quán)到股份合作制的“準(zhǔn)土地股權(quán)”——理論矛盾、形成機(jī)理和解決思路》,《經(jīng)濟(jì)研究》1995年第7期。
附錄:
A. 關(guān)于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y)的換算。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是本文計(jì)量中的一個(gè)重要變量,在國家統(tǒng)計(jì)局國民經(jīng)濟(jì)綜合統(tǒng)計(jì)司編么新中國五十年統(tǒng)計(jì)資料匯編》中,河北省、 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廣東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等4個(gè)省份中缺失了1949—1978年的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的數(shù)據(jù),北京市缺失了1949—1956年、遼寧省和上海市缺失了1949—1951年、福建省缺失了1949年、湖北缺失了1966—1969年和1974—1978年、海南省缺失了1949—1969年、西藏自治區(qū)缺失了1949—1958年的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的數(shù)據(jù).個(gè)別省份也缺失了農(nóng)林牧漁業(yè)總產(chǎn)值(y1)的部分?jǐn)?shù)據(jù). 由于資料中已經(jīng)給出了缺失數(shù)據(jù)年份的相應(yīng)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的指數(shù)值,所以本文在分析中對部分重要的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數(shù)據(jù),根據(jù)相應(yīng)指數(shù)進(jìn)行了換算。但是由于資料中所給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和指數(shù)指標(biāo)間,進(jìn)行換算也會(huì)存在誤差(據(jù)有關(guān)統(tǒng)計(jì)部門的解釋,是國家對各省份數(shù)據(jù)宏觀調(diào)整的結(jié)果),所以本文對部分缺失的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進(jìn)行了盡可能少的換算。對估算后誤差較大的樣本點(diǎn),在盡量不影響計(jì)量分析的情況下予以舍棄.
B. 關(guān)于化肥施用量的換算.對于各省份某個(gè)時(shí)期缺失的化肥使用量數(shù)據(jù),本文結(jié)合相應(yīng)年份全國化肥施用量、全國化肥產(chǎn)量, 以及各省市自治區(qū)化肥產(chǎn)量和本地區(qū)化肥施用的變化規(guī)律,運(yùn)用相應(yīng)的方法對化肥施用量進(jìn)行了換算.全國化肥施用量、全國化肥產(chǎn)量的有關(guān)數(shù)據(jù)和分析如下:
表中所列數(shù)據(jù)中全國化肥產(chǎn)量和用量均來自國家統(tǒng)計(jì)局國民經(jīng)濟(jì)綜合統(tǒng)計(jì)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tǒng)計(jì)資料匯編》,個(gè)別化肥施用量數(shù)據(jù)缺失,使部分“用量/產(chǎn)量”和“今年用量/去年用量的比值”數(shù)值需要估算.對各省份化肥施用量進(jìn)行的估算,主要依據(jù)其當(dāng)年的化肥產(chǎn)量,盡量保持各個(gè)省份數(shù)據(jù)的有效性.在這個(gè)前提下,同時(shí)對有部分化肥施用量點(diǎn)數(shù)據(jù)的情況,根據(jù)其省份化肥施用量已有數(shù)據(jù)的規(guī)律進(jìn)行了折算;對化肥施用量無典型點(diǎn)數(shù)據(jù)、且數(shù)據(jù)序列缺失較多的情況,主要依據(jù)全國化肥施用量的部分規(guī)律進(jìn)行了折算。
C. 關(guān)于農(nóng)業(yè)機(jī)械總動(dòng)力的估算。下面表中,對國家統(tǒng)計(jì)局國民經(jīng)濟(jì)綜合統(tǒng)計(jì)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tǒng)計(jì)資料匯編》中,給出的全國農(nóng)業(yè)機(jī)械總動(dòng)力 (單位:萬千瓦)、年底大牲畜頭數(shù)(單位:萬頭)數(shù)據(jù)進(jìn)行了計(jì)算(僅有典型點(diǎn)數(shù)據(jù),并沒有完整的時(shí)間序列數(shù)據(jù))。其中農(nóng)業(yè)機(jī)械總動(dòng)力/年底大牲畜頭數(shù)的比值,是根據(jù)一頭大牲畜相當(dāng)于0.7馬力 (一馬力相當(dāng)于o.735千瓦)來換算的,這樣一頭大牲畜相當(dāng)于0.5145千瓦的農(nóng)業(yè)機(jī)械動(dòng)力數(shù)。這種換算比例由國家統(tǒng)計(jì)局建議采用,見于林救夫著《制度、技術(shù)與中國農(nóng)業(yè)發(fā)展》,第100頁,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4年11月第l版。
本文在計(jì)量分析中,將年底大牲畜頭數(shù)近似估計(jì)為當(dāng)年的役畜數(shù),并將農(nóng)業(yè)機(jī)械總動(dòng)力與之歸并在一起,作為生產(chǎn)性投入進(jìn)行計(jì)算。從上表中,可以看出1952年的農(nóng)業(yè)機(jī)械總動(dòng)力數(shù)相對于年底大牲畜頭數(shù),是可以忽略不計(jì)的, 中國大陸農(nóng)業(yè)機(jī)械化的推廣主要是在1970年以后展開的。 因此,對部分省份缺失的1952年農(nóng)業(yè)機(jī)械總動(dòng)力數(shù),本文將其數(shù)值估算為o(實(shí)際情況也確實(shí)如此,個(gè)別省份擁有的1949—1952年農(nóng)業(yè)機(jī)械總動(dòng)力的數(shù)據(jù),數(shù)量級十分小).考慮到農(nóng)業(yè)機(jī)械是一種耐耗品,不會(huì)因一次性投入而消失,所以參照全國增長的趨勢,各省份的農(nóng)業(yè)機(jī)械總動(dòng)力也會(huì)出現(xiàn)持續(xù)增長的趨勢。因此,對于擁有較多典型點(diǎn)數(shù)據(jù)的省份,本文對其缺失的農(nóng)業(yè)機(jī)械總動(dòng)力數(shù)值直接進(jìn)行了估算。對于缺失農(nóng)業(yè)機(jī)械總動(dòng)力數(shù)據(jù)較多的省份,考慮到資料中給出的全國相關(guān)數(shù)據(jù)也是點(diǎn)數(shù)據(jù)的情況,所以又根據(jù)下表進(jìn)行了換算:
說明:個(gè)別省份數(shù)據(jù)的換算用如下方法,先用省際農(nóng)作物播種面積除以全國農(nóng)作物總播種面積,得到一個(gè)百分比,再用全國農(nóng)業(yè)機(jī)械總動(dòng)力乘以這個(gè)百分比。在得到各省市自治區(qū)上述相應(yīng)年份的農(nóng)業(yè)機(jī)械總動(dòng)力點(diǎn)數(shù)據(jù)后,根據(jù)原來已有的部分?jǐn)?shù)據(jù),換算得到其它數(shù)值。
D. 關(guān)于鄉(xiāng)村從業(yè)人員數(shù)據(jù)的換算。國家統(tǒng)計(jì)局國民經(jīng)濟(jì)綜合統(tǒng)計(jì)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tǒng)計(jì)資料匯編》中,有部分省份的鄉(xiāng)村從業(yè)人員數(shù)據(jù)缺失, 由于在1949—1978年間中國大陸鄉(xiāng)村中的第二產(chǎn)業(yè)和第三產(chǎn)業(yè)并不發(fā)達(dá)(中國大陸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和農(nóng)村服務(wù)產(chǎn)業(yè)主要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才發(fā)展起來的), 鄉(xiāng)村從業(yè)人員主要指的是鄉(xiāng)村在第一產(chǎn)業(yè)中從業(yè)的人員,所以從業(yè)人員按照產(chǎn)業(yè)劃分,第一產(chǎn)業(yè)中從業(yè)人員數(shù)量十分接近鄉(xiāng)村從業(yè)人員數(shù)。對于部分省份缺失的鄉(xiāng)村從業(yè)人員數(shù)據(jù),本文用第一產(chǎn)業(yè)從業(yè)人員進(jìn)行了近似替代。個(gè)別省份還出現(xiàn)了上述兩個(gè)連續(xù)數(shù)據(jù)均缺失、只有鄉(xiāng)村從業(yè)人員或第一產(chǎn)業(yè)從業(yè)人員點(diǎn)數(shù)據(jù)的情況,本文用各省份農(nóng)業(yè)年底總?cè)丝诘脑鲩L比率作為依據(jù),推算出了相應(yīng)年份的鄉(xiāng)村從業(yè)人員的數(shù)值.
E. 關(guān)于農(nóng)作物總播種面積的換算。湖北省、河北省和浙江省等3個(gè)省份缺失了部分農(nóng)作物總播種面積的數(shù)據(jù),本文根據(jù)各省同年的糧食面積的變化率為依據(jù),對部分農(nóng)作物總播種面積進(jìn)行了換算。
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中央檔案館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經(jīng)濟(jì)檔案資料選編》農(nóng)業(yè)卷,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1991年;王琢、許浜:《中國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論》,經(jīng)濟(jì)管理出版社,1996年。
進(jìn)展.jpg)
雜油氣藏.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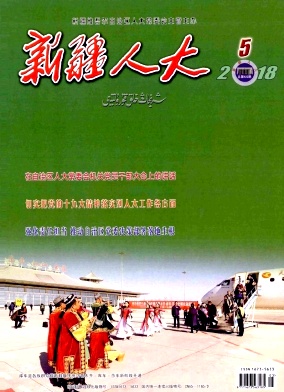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