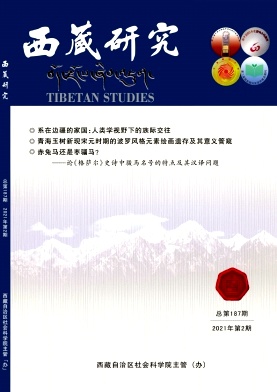金沙江邊農村人口流動類型分析——以車軸村為個案
佚名
編按:本文為蕭亮中先生一篇未完成的作品,蕭亮中先生逝世后由其生前好友在整理他的電腦資料時發現。現征得蕭亮中先生家屬的同意,首次公開發表,作為對蕭亮中先生逝世半年的紀念。
金沙江水蜿蜒流下,兩岸分布著許多呈扇形的緩坡壩子,這是由云嶺嶺脊發育的一條條季節河形成的沖積扇。江水呈S形往下,臂彎里便抱出了一塊塊大水不等的壩子,上面的村落像珠子般串起來鋪在兩岸。在中甸和麗江,這一帶叫江邊,這里的居民也稱作江邊人。
車軸村就是這一帶的一個典型的自然村落,隸屬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中甸縣金江鎮,離長江第一灣50公里,距縣城188公里,行政上剛好是一個村治。截至2000年11月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車軸村有467戶,2030人1。實際調查時,我發現該資料尚包括集體戶和外來無戶者,這與傳統認可的實際戶數略有出入。如減去這類戶口,則車軸村在籍戶數為460戶,而1970年僅為350戶,1666人2。
下面,筆者擬就以車軸村為個案,從江邊農村人口流出及外地人口流入兩個角度描述分析。
一江邊農村人口流出類型
(一)「國家人」
整個江邊素有濃厚的讀書傳統。1937年,車軸士紳盧維韓與吾竹爭奪設點創辦縣立小學名額勝出,該年春季即在車軸設「縣立第三兩級小學」,改舊式私塾學堂為新式教育。這段史實在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中甸縣志》上有兩段記錄:「設于車軸舊觀音廟,新建平房三所于廟后」;「由縣教費內發新幣十四元,余均由地方自籌。本校附設民眾識字班共成年男女二十九人。」 3可見當時民眾接受正式學校教育之殷切。
建立正規學校教育后,車軸不斷涌現優秀學生。解放后,新政權需要大批本地干部,當地年輕人只要家庭成分好,受過一些教育都被安排工作,這也部分得益于解放前盧維韓等人開創的新式教育。上世紀80年代初,迪慶州很多單位及教育部門都缺少工作人員,──而江邊家長供孩子讀書的勁頭都很大,江邊子弟在中甸各類學校里成績也最好4,──這樣,陸續有很多車軸農家子弟通過大中專畢業、考工考干等方式在鄉鎮、縣城、州府甚至省內外工作,變成農民眼里的「國家人」。據筆者統計,這個數位達到五百多人。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的統計包括在鄉鎮工作家屬在農村,或夫妻都參加工作但家安在農村的「城鄉結合型家庭」。這一類國家干部、職工名義上在上班,是「工資人」,但幾乎都在農村社區活動,并經常性地參與農事,可以說是拿著工資的準農民(筆者稱為「工資農民」)。另外,筆者也將離退休回家度晚年的老干部(曾經的國家人)計算在內。一句話,只要是不在村政府戶口名簿上,但在車軸村「活動」的人士,都悉數予以統計。
純樸的農人本意是讓后代能走出鄉土過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并沒有更多的報恩期冀,但這批走出車軸的農家子弟還是多多少少能為家庭和鄉土做一些事。大多數在外工作者(尤其是在縣內的)都經常回家,尤其是過年,村里一下子就增加很多人。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甸縣城都遠沒有今天的繁華和旅游熱,一到過年,江邊人都跑回家,白雪覆蓋的縣城一下子寂靜空寥,幾乎就是一座空城。平時,各戶頭都是小家,但仍然保持著以父母甚至是兄弟之間「遠距離」、有獨立發展又有合作關系的「聯邦式家族(庭)」5。出現這一類家庭的主要原因是工商業化、都市化發展影響到傳統家族房、戶居住地域格局。中國大陸工商業起步晚,又有著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戶籍限制,所以這類家庭模式的出現晚于臺灣地區。
吉同樂一帶農戶,幾乎家家都有人在外面工作,有些家庭還有兩三個。在外面的車軸子弟和他們的子家庭對母家庭有多大的幫助呢?很多人會回答你「幫助不大」,──但細心調查卻發現真實情況大相徑庭。農人如此做答也可能由于確實意識不到,但大多數則是出于「要面子」的習慣性保護。這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式「人倫相對性直覺」6:一般來說,外來者來到一個被事先安排的會見場合,因事先暗示與安排,人們不約而同地掩飾或放大某些資訊。有時當調查者進入一個未被事先安排的場合,還可以發現文化直覺主義的兩種反應:人們理會如何應付場面,即時直覺地放大或刪除某些資訊;或是人群中敏銳的直覺者壓抑遲鈍的直覺者的意見7。
雖然在上世紀80年代初,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江邊發展很快,有幾年似乎與縣城的差距都不是很大。但經濟發展很快就沒有了后勁,尤其是最近幾年,江邊和縣城的差距更是不斷拉大。一些農村家庭一年的收入還沒有城市職工一個月的薪水多。這種時候,外出工作者的作用更加體現出來:他們向母家庭提供借貸、資訊輸送、務工中介等實實在在的幫助;與此同時,他們也部分地成為農村家庭到城里的「招待所」、「銀行」及「中介處」!
筆者還注意到各個村莊貧富變遷和現在的貧富分化與外出工作者對車軸社區的幫助息息相關。總體上,解放前迪古人生活較好。迪古幾乎都是納西族,作為本地人,他們擁有大量田產。另外,其他村子的地主收入自然也會好一些。過去交通差,住在壩區和山區實際上沒有多少差別。像巴迪的吉才和學智家,原從斯勒下村遷來,至今已七代,是解放前車軸田產最多的地主,并沒有因為住在山區而影響家業發展。相反,今天生活相對不錯的滿庫一、二社在過去卻是最窮的村子之一。滿庫大多數是客籍居民,無田或少田,很多是迪古、吉同樂地主的佃戶。加上村子位于江邊沙壩,新開田地收成非常低,不像迪古一帶老田肥力充足,收成相對要高。今天,還有迪古人會嘲諷過去滿庫人糧不夠吃,經常前身衣襟揣兩團冷飯在田頭簡單就餐。看來,地域區別在過去并不是導致貧富差別的因素。解放后,迪古人的很多土地劃到滿庫,加上1958年后,滿庫又在江邊大量開墾田地,以至于后來居上,人均占有畝積在車軸名列第一。上世紀70年代后期,化肥使用逐漸鋪開,沙壩田開始增收,加上當時滿庫隊長李濤很得力,生產隊還購置農機,甚至修了一座電影院。總的來說,大集體到80年代是滿庫的黃金時期。而其他生產隊,像吉皆樂人口增殖過多田地少,巴迪、嘎子樂位于山區,不產水稻,雖畝積大但收成極低。到90年代,包產到戶釋放的生產力已經耗光,沒有了多少后勁,加上糧食不再作為農村經濟發展的單一衡量指標,滿庫的輝煌翻過了歷史一頁。相反,吉同樂的經濟則相對要好得多。由于村民重視教育,外出工作者比例遠遠高于其他村子(可以從下表人口、戶數上比照觀察),有些家庭甚至幾個子女都參加工作,一如上文描述,這批人對母家庭的幫助確實是很大的。
表 1: 變遷表(單位:戶)
年份 村莊 車軸村戶數 滿庫一社 滿庫二社 迪古一社 迪古二社 吉同樂一社 吉同樂二社 吉同樂三社 吉同樂四社 吉皆樂一社 吉皆樂二社 吉皆樂三社 巴迪一社 巴迪二社 嘎子樂一社 嘎子樂二社 八家社 1974 354 18 45 63 39 40 31 26 30 31 23 8 1982 370 19 42 34 32 19 19 22 19 32 25 35 16 16 16 8 8 1999 457 28 48 35 35 25 21 22 21 44 38 51 24 18 19 17 8 2000 460 29 43 76 25 23 22 21 44 38 52 42 45
表 1 資料來源及說明: 1. 1974年車軸戶數資料來源于車軸村公所《1974年農業生產統計年報表》。解放后村名及劃分經常變動:迪古一、二社時稱「光榮生產隊」;吉同樂稱「光明」,時設兩個隊,現一、二社為當時一隊,三、四社為當時二隊,故表上戶數分兩欄;今巴迪一、二社及嘎子樂一、二社、八家社稱「紅光」,巴迪一、二社為紅光一隊,嘎子樂一、二社為紅光二隊,八家社為紅光三隊,故分為三欄;吉皆樂當時稱「文化」,吉皆樂一、二、三社分別為文化一、二、三隊。 2. 1982年戶數為當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車軸村戶數,資料摘自迪慶州政府編:《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中甸縣第三次人口普查手工匯兌資料匯編》(內部資料,1983年3月)一書。 3. 1999年資料來源于車軸村公所藏《車軸村基本情況及農業生產條件表》。 4. 2000年資料為筆者親自找當地各社干部和農民核實錄入。時恰逢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后于金江鄉政府獲《車軸村戶主姓名底冊》。此次普查不實行「戶口歧視」,無戶者照錄,另還包括村公所、小學校等集體戶,但調查統計無需括入,故最后核實得出了上面的戶數。以上的資料核實過程也說明搜集資料不應過分相信文牘材料,任何事情都要身體力行實地調查。
上表中戶數裂分最多的是吉皆樂三個社、滿庫一社、嘎子樂二社;而吉同樂四個社及迪古兩個社的裂分相對不多。尤其是吉同樂三、四社,1972年到2000年僅增加了三戶。依江邊傳統,幾個兒子分家即裂開戶頭,那么應不止此數,經調查,這仍是因為有子弟參加工作,裂分戶頭不在車軸村統計之故。吉同樂田地少,經商者不多,也沒有鄉鎮企業,甚至連村道等公共設施都比較差,滿庫在這些方面的指標均比吉同樂強,但經濟和生活水平卻遠遠比不上。車軸所有村子吉同樂收入最高,這與參加工作者回饋母家庭有很大關系。這樣的回饋是多種多樣的,不能光以傳統的錢款支援衡量。吉同樂四個社91戶,在外工作者超過150人,其中回鄉的離退休干部二十余人。可以說,這在經濟上是一個比較大的支撐群體。就連筆者調查車軸村惟一的市場──每十五天趕一次的街子時,也發現消費者主要還是離退休老干部、城鄉結合家庭和有人在外工作「吃皇糧」的人家。簡單說,也就是家庭有固定經濟來源(農人謂之「有閑錢」)的人在消費。
所以,車軸村歷史上的貧富變遷和現在的貧富分化除了傳統原因制約外,還存在著一個「工資經濟」的解釋。在一個基本依靠農業,工商業與市場都極不發達的較貧困的農村社區,存在著一定數量依靠國家工資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城鎮戶口職工。他們或參與農村社區生活和農業生產(相當大一部分是「工資農民」),與整個社區有著天然的、無法剝離的關系,工資收入在社區經濟中占有較大比重,成為支撐(或部分支援)某些家庭的經濟力量;或與農村居民結成聯邦制家庭,對農村母家庭有錢款支援、資訊輸達、代管子女教育等多種回饋行為。
(二)「跑北方」的女性
解放后,江邊一帶的自由移民完全中斷,群體和個人的自由流動隨之消失,僅有不多的人物出去參加工作。──當然,這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移民了。然而,惟一的這個脫離農村戶籍的途徑也完全是在政府的支配安排下。直到「文革」結束,國家控制才逐漸松弛,村民獲得了很大的人身自主,僅僅只是幾年的變化和調整,又開始有了往外流動的人口。應該說,這類正在發生的人口流動,仍然可以納入到廣泛意義上的「移民」范疇。
最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政策變松后,偶有一些做生意的江浙人來到江邊。在當地人看來,這些外地人見多識廣,穿著又光鮮華麗,于是很快吸引了一些年輕女性的目光;而在這些外地人眼里,江邊姑娘老實厚道,肯吃苦,也較為中意。于是,兩廂情愿,陸續有姑娘嫁給他們。村民告訴我,最早來的幾位江浙人先是與吉皆樂二社常康全家攀上了親戚,(常康全父親是國民黨兵,解放前跑到車軸落籍。)靠上這層關系,他們陸續在車軸找到媳婦。最早嫁出去的姑娘是吉皆樂二社苗族鄭國繁的女兒阿石頭,這是一位很有主見、膽子大的姑娘,她第一個吃了螃蟹。阿石頭第二年回來時穿著講究,還帶來了讓村子里女性振奮的消息:「北方好,生活遠遠比這邊好。」于是,隨阿石頭來的兩個浙江人也順利地找到了媳婦。到1985年左右,吉皆樂一、二社甚至讓人感覺天天都有姑娘遠嫁外省,于是被人譏諷為「跑北方」。(江邊一般把較遠的外省籠統稱為「北方」)
表2:車軸村遠嫁外省婦女各社統計表(單位:戶、人)
統計 村莊 整個車軸 滿庫 迪古 吉同樂 吉皆樂一社 吉皆樂二社 吉同樂二社 吉同樂三社 吉同樂四社 1982年戶數 370 61 66 79 32 25 35 32 32 外嫁人數 73 2 1 9 25 20 5 0 11
表 2 幾點說明: 1. 本表僅嚴格統計嫁到外省去生活者,嫁給到中甸務工的外省人但仍在中甸生活(最近兩年增多)及嫁到外地州者概不列入。 2. 由于外嫁行為高潮是在1985年左右,現戶數早已增加,故筆者選取了1982年人口普查的權威戶數及人口來統計,這樣能盡量構擬當時的實際狀態。
上表中清楚看出外嫁行為主要發生在吉皆樂,其中尤以一、二社為最。這與兩個社相對貧窮,年輕女性想通過婚姻改變命運有直接關系。另外,這七十三位外嫁婦女中,苗族占三十六位,達到一半,剩下的三十七位里,四外籍又占了十多個,故當地人戲稱的「苗族四外跑北方」也有一些道理。
剛開始,這些外省男性確是為找妻子而來,早期一般是由已嫁出去的婦女和已在這邊找到妻子的外地男性領來。有意思的是,莊孔韶在福建黃村也發現,當地因重男輕女導致性比失衡,另外也因彩禮苛重及婚禮費用太大而外尋妻室,亦有從西南一帶遠娶者8。來江邊找妻子的很多外地人也有著同樣的囿因。但到上世紀80年代末,由于有利可圖,漸有拐賣婦女行為發生。筆者調查,車軸村現已確認失蹤的有七人,另還有個別外嫁女性沒有回過娘家也沒有來過信,基本上可以與失蹤畫等號。90年代,拐賣婦女現象在全國各地均有蔓延。1994年、1995年國家嚴厲打拐,公安系統相應增加防范,加上社區已有多起拐賣案,民眾警惕性非常高。這樣,拐賣人口現象才基本得到制止,「跑北方」的風氣也隨之逐漸淡下去。
當然,1990年以后也陸續有婦女外嫁,但一般是本地外嫁婦女回鄉領出去。當事者很審慎,父母一般還會阻攔,如果外面的誘惑對女兒實在大,也一定要求男方先過來相一面。另外,民眾觀念也開始轉變。他們甚至告訴筆者:這么遠來找媳婦,還不是因為在當地家境貧困、個人條件差,我們的姑娘怎么能隨便嫁出去呢?!確實,這一時期的外嫁女性有很多是智障者,當地人又這樣說:「我們這里不要的才被外地人撿了去!」
當地民眾都看不起外嫁女兒的家長,譏諷說是為了幾百塊錢賣女兒。由于外嫁婦女中苗族占多數,事實上這又成了其他族群加重對苗族歧視的例證。1985年左右,車軸村苗民約為五十戶,外嫁婦女就有三十六位,比例確實相當高。在吉皆樂一、二社,幾乎每戶苗民都有女兒嫁到外省,有些家庭甚至達到三四個,二社鄭國繁甚至五個女兒都嫁到外省。這樣的事實對苗族的認同會造成影響嗎?畢竟苗胞給外人的印象是族內通婚。不過,在苗族看來,外省人雖然也是漢人,但外嫁女兒和與本地其他民族通婚不同,因為前者不會直接對當地苗族族群的血統和認同構成影響。這一種現象姑且可稱為族群認同中的「遠親近防」原則:一族群與遙遠的它族群之間界線往往模糊,并且可以想象兩者之間的親近關系并付諸聯姻等行為;但在與自己混雜居住關系密切的外族群之間,卻因經常發生各種影響,感受到壓力,恰恰需要加固彼此的界線。不過,這也從反面表明苗族并不是嚴格地不與外族通婚,互不聯姻的主要原因還是外界歧視加固了族群界線所致。迪古和萬舉就得意地告訴筆者,只有苗民才往外嫁女兒,我們納西就沒有。但調查卻證實,納西族外嫁婦女也有十四位,不過從人口比例來說相對要小得多,并不像苗民那樣,大量女性外嫁甚至對性比都造成了一定影響。
(三)討生活的外遷戶
解放后,國務院分別于1956年、1958年頒布《建立戶口制度的指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從此,版籍森嚴的戶籍制度建立并逐漸完善9。這從根本上限制了人口流動。除了因畢業分配、招工招干、軍人轉業等不多的途徑,農村戶口的居民幾乎不可能遷徙到城市。即使農村之間,除了一些特殊原因由政府指令搬遷,似乎就只有男女婚娶才能成為一個合法的遷徙理由。由于居民流動少,人員交際圈小,婚姻圈也就不斷縮小,傳統的一些婚娶路線消失,人口流動性也隨著大幅度下降。村民告訴我,集體時出一趟門都要在生產隊交假條,并且還要開證明帶糧票,這樣,要找個媳婦還不就在江邊。以前民家人都跑到大理、劍川去找媳婦,解放后哪有這種可能?!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由于政策松動,農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整個社會層面才重新有了人口流動的可能。到90年代,農民離開鄉土往外遷移更變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問題。從廣義上看,這也是一種移民行為。在車軸村,除到外地參加工作和女性外嫁,這也算是新近出現的外流移民。
傳統中國社會把農民遷徙看成是當地生活貧困的結果,也就是說農民是迫于無奈而遷移的。以此觀點為基準,歷代政府總是把移民和人口流動當作不穩定的因素10。上世紀90年代今天也有學者提出「警世恒言」,認為外出打工現象值得警惕,因為從歷史上看,流民潮的出現往往是不祥之兆11。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農村人口遷徙問題,李普頓(Michael Lipton)提出的「農村沙漠化」理論頗能說明問題。該理論歸結為以下幾點:一、人口外出必然造成農村中最有活力、最有技術、最有革新思想的人才流失,農業變得更為落后、松散,農村社區的自我維持能力也會減弱。二、外出者雖然會向農村寄回錢物,但數目少,作用不大,并會使居民產生依賴感,還有可能把所匯回資金用于儀式性的、炫耀性的消費,而不是進行生產性投入。如這樣,則對農村發展沒有任何貢獻,相反還增加了對外部世界的依賴。另外,如果匯款用于投資而非消費,那多半也是被已經富裕起來的村民利用,他們會變得更富有,這樣相反會更加劇農村內部的不平等。以上事實也會促使外出村民回來投資家鄉的行為逐漸減少。三、人口流動導致城市因素向農村滲入,這種力量對農村是解構性的,會導致農村這個具有內聚力的、同質性的社會分化,甚至加劇不平等。四、農村輸出人口都是年輕一代,這使得農村居民生育能力下降,從而造成人口隨之自然下降,甚至出現「荒漠化村莊」12。事實上,內地很多地方已有這種兆頭。2000年發生在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身上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的個案。李昌平于2000年2月10日含淚以一封題為〈一個鄉黨委書記的心里話〉并被稱為「建國以來監利縣影響最大」的信上書國務院。里面赫然提到棋盤鄉「全鄉4萬人,其中勞力18000人。現在外出25000人,其中勞力15000人」13,資料讓人咋舌。
江邊的情況當然沒有這樣典型,但至2000年人口普查,車軸村全家外出戶竟有了九戶14,而這樣的情況以往是絕對沒有的。包產到戶政策放松后,江邊人每到農閑都愛出去務工,當地沿用集體時的叫法稱為「找副業」。這些人物多是在鄉間頭腦靈活,在縣城及外地有親戚朋友可以照應、依靠的年輕男性。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這類行為增多,但仍然幾乎是男性,而且只是家庭個別成員利用農閑外出務工,一般鮮有超過半年者,──而現在竟一下子有九戶全戶外出。這里的外出戶概念是徹底地出門:把家里的牲畜賣掉,把承包地租出去或干脆撂荒,房屋請鄰居親戚代為看護,總之幾乎就是一走了之。這樣典型的外出戶在1999年才開始出現,變化確實是非常之大。
這是甚么原因呢,一位叫盧佳嶺的農民對我說:「前幾年這種事很少很少,出去打工的幾乎都是男人,父母和老婆孩子留在家中。現在是把全家人一個不落全帶走,好像是迫不及待要把農村的一切都扔掉,一點都不回頭。我想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種田賺不了錢甚至倒貼。前兩個月我去中甸,聽說湖北省有一個叫李昌平的鄉黨委書記寫信給朱熔基總理,那些地方是真沒有辦法才往外跑啊15。都是農民,我看了很難受。江邊倒沒有這么差,但再這樣下去也很危險。李昌平那里種田剛能保本,我們這邊今年種一畝小麥有五十到一百元的收入,這都不計算辛苦費,也就是說把農民的播種收割、田間管理全白搭進去。像我們吉皆樂一社,本來就田少,有些家庭兒女沒有出去工作的,幾弟兄都窩在家中。前幾年國家政策就有規定,不用再依據每家的人口數重新調整責任田畝積,這樣一來,像隔壁的王程東,四個兒子一分田,每家就一畝多一點,你就是在田上繡花也沒有用。讀過農高(指中甸二中的農業高中班)、腦子活的三兒子阿桑就帶著老婆孩子到縣城賣豆腐去了,我到中甸發現他至少比在村里日子好過。像這樣的事也是今年(2000年)才普遍起來,應該說是逼得沒辦法了。吾竹那邊出去的農民比車軸更多。像堆滿四社,很多家都跑到中甸守收費公廁,現在大家稱呼他們『廁所隊』。──守廁所還比種田好!另外還有『建筑隊』、『垃圾隊』,都是一個村一個村跑到中甸,靠在工地賣苦力、撿垃圾維生。不過,話說回來,車軸再怎么也走不到李昌平那里的地步。總體上江邊田地并不少,吃飯不會有問題,但家里如果有小孩讀書、生個病甚么的就真沒有辦法了。前幾個月斯勒一家傈僳族為了供孩子讀書,把房子都賣了一所,但賣了房子后你還能賣甚么?!如果再這樣下去,農村還怎么發展?!話說到頭,有一點可以肯定:只要糧價繼續低,農民還會不斷往外走!」
二流入江邊的外來人口類型
(一)新四外人
上世紀70年代末,許多川籍人來到江邊一帶務工,80年代初曾達到高峰。那時每個社都有三至五人,整個車軸村大概有五十多人在進進出出流動著。村民們會這么說:又來了一些新的四外人。這與當時四川人口眾多,田地緊張有密切關系;另外,四川省也早在80年代初就正式下文,把勞動力外出務工作為一項政策來推行。當時「文革」剛結束,老實巴交的村民都還不敢到處亂跑,見到這么多四川人,總會有些奇怪。問及他們,詼諧的四川人會笑著說:鄧小平是四川人嘛,四川老鄉多,活不下去了,他老人家就準我們跑出來混口飯吃。這個詼諧的口傳版本至少說明,當時大量川籍人就近來到毗鄰省區務工至少得到了上層的默許和支援,另外,中甸毗鄰川省,歷史上就有川人前來謀生,這里顯然有一個就近原則。這些川籍務工者確實也不奢望賺多少錢,有些甚至就為了吃飽肚子。那時,這個群體是清一色的男性,一般在江邊從事制瓦、燒窯等活計,也有一部分完全靠賣工度日。他們或承包一項工作,或要求東家包吃包住,每天干活,月結工錢。一到農忙,來找活做的四川人更多,村子里天天能聽到他們大聲、樂觀地講四川話。到江邊時間長了后,一些人就在當地談戀愛,找媳婦,入贅女方家庭,這一類人共有十一個。最早村民告訴我是四人──他們是早期入贅者,連戶口也轉過來的;調查后馬上發現另外還有五人,由于轉戶口困難或無所謂,他們的戶口都沒有過來,從調查客觀性來看,這五人應計入;另還有二人遺漏。村民無意識地把他們分開,這與其心理上把轉戶口與否當成一個「入籍」車軸的門檻有關。──轉了戶口者才是車軸人,未轉者自然就是外地人。這種思維定勢與今天一些大城市的定位不謀而合,可見解放后長期實行的戶籍制度對民間思維的影響之深,它甚至已影響到民眾對事物標準的畛別、判定。
最早到車軸定居的一位四川人叫老福,他于上世紀80年代初到江邊修路,后入贅吉皆樂一社王阿奶(馬桂英)家,接著就把戶口也轉了過來。當時,老福很希望把四川那邊家人的戶口都轉過來,但村民和政府沒有答應,因為轉戶口就意味著要分地,而吉皆樂一社的土地已經很緊張。這以后,凡是在車軸入贅的四川人想轉戶口都非常難。看來,即使是在偏遠的鄉村,戶口也像是一道閘,它的后面仍然多多少少跟著一系列的資源待遇,這恐怕也是新四外們沒有更多落籍江邊的主要原因。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來車軸務工的四川人逐漸減少,到90年代,常年在村里的不到十人。這與80年代中后期城市改革興起,川籍務工者大多數改行去城市有關;另外,那時江邊經濟已初露頹勢,客觀上也雇不起長期務工者,這也是川籍人離去的另一個原因。1996年,筆者訪問車軸,村子里已經見不到往日活躍的川籍務工者身影,只剩下了最后三四人。一位李姓四川人長期在迪古一戶人家做活;另一位老胡從90年代初就在吉皆樂私營酒廠做工至今。2000年筆者調查時這兩人都在,不過客觀地說,他們的身份已類似舊時的長工了。兩個人年紀都大了,也沒有文化,現在也沒有去外地務工的能力,村民們都想當然地認為,他們回四川可能連生活也對付不了。另外,嘎子樂磚瓦廠的師傅也是四川人,他還帶著個云南昭通的徒弟。就目前來看,也不知道兩人今后的打算。
我就這一批務工群體的來去消失問起村民,他們笑著說:「我們車軸人都要到外面打工了,哪里還請得起工啊!」至此,曾經活躍在江邊的一撥撥「新四外」已走得無影無蹤;而同時,江邊人也面臨著與他們同構的命運。
(二)「藏族姑娘下壩」
從整個中甸縣來看,解放前不同族群之間的通婚例子不是很多,即使有聯姻行為,也主要是在同一區域毗鄰各族群之間,像中甸北部藏區和民族雜居的江邊之間通婚例子就很少,在車軸幾乎就只有幾例。
然而這個狀態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有了根本改變,很多中甸藏區甚至四川鄉城等地的藏族婦女陸續嫁到江邊一帶。前文說過,車軸村一部分婦女遠嫁外省,對性別比例有一定影響,現在,這些藏族姑娘事實上起到了補缺作用。在車軸,最早來的是陳學忠媳婦卓瑪拉初。1987年,陳到中甸做生意,認識了卓瑪拉初。兩人中甸、江邊跑了幾次,感情逐漸上升,遂于1988年結婚。婚后夫妻關系非常好,在卓瑪拉初介紹下,又有幾個藏族姑娘來到車軸。到90年代中期,不斷有藏族姑娘嫁下來,江邊人戲稱為「藏族姑娘下壩」。訪談人告訴我,前兩年甚至還有東風牌卡車載著滿滿一車藏族婦女到江邊一路問著找丈夫的事情。現在,嫁到車軸村的藏族婦女共十六人,其中吉皆樂七人、滿庫四人、巴迪一人、嘎子樂四人。目前,這樣的趨勢仍在上升。
11月18日,筆者到金江鄉政府查閱人口普查資料,路上見到吾竹堆滿三社有戶人家在辦喜事。按江邊風俗,辦喜事是在春節,這戶人家卻在夏季?進去一問,原來是一位鄉城藏族婦女嫁過來。村民們還告訴我,原先村子里就已經有了嫁過來的鄉城姑娘,這位新娘子是跟著過來主動先找丈夫的。兩人從認識到結婚沒用多少時間,連等到過年都來不及了。隨后的調查得知,嫁到這些靠近集鎮、條件遠比車軸好的村子的藏族婦女更多。
村民們都認為,是江邊條件比藏區好吸引了這些女性,嫁到當地的藏族婦女也執這個看法。另外,由于一些藏族姑娘嫁的家庭家境不是很好,甚至還屬于在當地受歧視的族群,故筆者也聽到個別村民對這類事的主觀評說多少帶著族群中心意識。于是,筆者決定親自探訪車軸村藏族媳婦的娘家。在吉皆樂一社王峻龍妻子拉姆和她的弟弟還俗喇嘛七林頓珠的幫助下,我追蹤來到建塘鎮尼史辦事處比桑谷村,在拉姆的娘家「古張」(意為橋頭)家住下,進行了短期的主題調查,最后大致找到了藏族姑娘嫁到江邊的一些原因。
首先,最重要的一點是,藏族傳統上沒有重男輕女思想,男女性比合適。但由于有一部分男性出家當了喇嘛,加上外出工作的也大多為男性,所以女性相對「過剩」。這是大量藏族姑娘嫁到江邊最根本的原因。
其次,迪慶州一帶傳統的藏族并不像漢人,或受到漢文化影響有家族觀念,藏人傳統是「家戶」,并不贊成隨意分家。具體辦法是幾弟兄共同找一個妻子,同屋共爨。如果留長女居家,那么就嫁出其他女兒,男性則去入贅或送去當喇嘛。這些措施都切實地保證了該家戶盡量不予裂分。盧佳嶺甚至告訴筆者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2000年上半年他在德欽霞若鄉白術村修建希望工程學校校舍,了解到白術村解放前是十一戶,現在加上80年代從另一個村搬來的二戶共十三戶,實際上那十一戶一直就沒有變化。白術村所有的家庭都是招婿或弟兄共妻,村民們根深蒂固的理念就是家戶不能拆分,大家永遠住在古堡似的碉房里。中甸藏區雖然沒有這么嚴格,但基本理念也一脈相承。所以說,這些婦女在娘家的社區環境里遲早要游離出家戶之外,嫁往不同文化特質的地方也可以說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再次,雖然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甸藏區經濟逐漸強于江邊,但主要靠木材、松茸16,這兩年還有一些旅游業的支援,但受益面主要是靠近城鎮、交通線和設旅游點的農村,很難惠及比桑谷這樣偏遠的村落。藏人的傳統觀念仍然把種田放牧當做居家的根基,江邊畢竟有著很強的農業優勢,氣候溫和、舒適,適于居家生活,所以家長們一般也不予干涉。
還有,藏區廣種薄收,人均耕地多,勞動強度遠遠超過江邊。筆者1997年到「夏那藏家」田野調查時就驚嘆于藏族婦女的勞動強度,即使是農閑,夏那家的主婦拉茸卓瑪從早到晚也沒有停歇過17。王峻龍妻子拉姆也告訴筆者:中甸藏區田地面積很大,每家都有四五十畝土地,而江邊就小得多,但由于江邊畝產高,也能抵上藏區的廣種薄收。所以說,雖然在江邊種地要比在娘家精細,但總的來說,農活要輕松得多。這樣兩相比較,大家自然覺得還是在江邊生活、勞動舒適一些。
最后還有一個特殊原因。相比在草原上過著游牧生活的其他地區藏民,康巴藏族大都生活在橫斷山區,住所流動性較小,故人們很重視房屋的設計與構造。他們甚至認為一個人一生的成就主要就體現在住宅上,許多人都傾其畢生精力建造住宅。這里的藏房建筑風格獨特,高大寬敞;由于寒冷,又很講究墻體厚實、料質緊密,以達到防寒功效。以中甸藏族房居來說,樣式上分為河谷土墻碉房和高原土掌房兩種類型,用材均十分驚人。前者僅用木材一項就達到71.15立方米,還不包括大量的土石方18。至于后者,據筆者在「夏那藏家」的調查,建筑面積在三百平方米以上,耗用木料雖少于河谷型,但也十分可觀19。在中甸藏區,另立家戶就必須另外擇址新建住房,而一所藏房的木材用料至少是江邊一所房子的三倍以上。1998年以后,中甸森林一定程度上禁伐,民用木材漸少,建蓋傳統藏房難度越來越大。但由于對住房居所的高度重視,不管建房多么辛苦,分家戶也得咬著牙上。如果不造一幢象樣的房屋,就會被旁人看不起,在社區也不好立足。所以,事實上的建房困難也是導致藏族姑娘往江邊嫁的一個側面原因。筆者還從反面發現了有意思的一個佐證:如果你家里連新房也沒有,藏族姑娘確實也不愿意嫁。
我向七林頓珠父親問起這邊家長對女兒嫁到外地,尤其是江邊的態度。老人笑一笑說:「國家規定婚姻自由,我怎么能管他們呢。我女兒嫁江邊人,兒子頓珠找的是江邊姑娘,這也不虧嘛!」聽了老人的話,我不禁啞然失笑,我們愛從文化上找原因,但有時卻會犯泛文化的錯誤。七林頓珠的女朋友和江梅是麗江江邊龍蟠的納西族姑娘,我到比桑谷時她已經在古張家呆了一個多月了。老實的小和告訴我,她在這里最大的不適就是聽不懂藏語,但我亦發現古張家會說漢語的和她對話都會盡量用上拗口的漢語,而小和也在努力地適應著。現在,頓珠也有很多苦惱。「古張」這個家戶是大姐的,更何況他從小就被送到松贊林寺為僧,家里也不會有他的份了。按藏族習俗,頓珠注定是一個分家戶,總要出去成家立業,而這首先就要建蓋一幢象樣的藏房。由于比桑谷周圍山上已砍不到多少木料,建房備料就得跑到很遠的山區,費很大的人力物力,確實不容易做到。作為男人,頓珠當然愁上眉頭。這位浪漫的還俗喇嘛從小就在寺廟里,實在是連農活都不熟悉,也不像傳統的農村人那樣能吃苦。好在他在寺廟學了一手彩繪技術,現在是一位中甸藏區頗有影響的民間畫家。藏民家庭喜愛彩繪房屋,只要頓珠出去接一些活,錢還是比較寬裕。頓珠也向我坦率承認,自己實在吃不了苦,以后干脆建一幢當地叫「漢房」的新式住宅算了。這樣避重就輕,也輕松許多。不過,比桑谷可全是傳統的藏式房屋,如果他真這么做,那毫無疑問會帶來一定的文化震蕩。至于和江梅,她一直就坦率地表態不喜歡傳統的藏房。「一點也不好,竈也沒有,就一個火塘,做飯吃飯都不方便,今后我的房子可不要這樣的。」想到她終歸要和頓珠出去組建小家庭,這位姑娘悄悄地臉紅了。
這樣的文化沖突在江邊也會遇到。吉皆樂陶生的媳婦央宗嫁到他家時,家里已有三所大瓦房,兩兄弟尚未分家,生活很好,央宗也很高興。后來弟兄分家,按江邊幼子繼承家產的慣例,大哥陶生就要讓出去。這時,央宗不干了,中甸藏族是長子(女)繼承制,其他弟妹都要出嫁或分家另外建房。央宗認為要弟弟讓,退一步至少也得平分。但沒有用,后來陶生還是只能和她去重新建房蓋屋,分家另過。就為這事,央宗還和自己的丈夫、婆婆家一直有些不愉快。
注釋 1 金江鄉政府藏:2000年11月1日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甸縣金沙江車軸普查區《車軸村戶主姓名底冊》(內部資料)。 2 車軸村公所藏:《1970年農業生產統計年報》(內部資料)。 3 〔民國〕段綬滋篡修:《中甸縣志》,現收錄于和泰華、段志誠校注:《中甸縣志資料匯編》(3)(內部資料),1991年,頁98-99。 4 另可據馬茜:《多民族地區教育的地域性闡釋--以云南省中甸縣第一中學為個案》,北京:中央民族大學2001年碩士學位論文,頁12-13。 5 莊英章:〈臺灣農村家族對現代化的適應──一個田野調查實例的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1972年第34期,頁88。 6 莊孔韶:《銀翅--中國的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北京:三聯書店,2000),頁498-503。 7 同注6,頁501-502。 8 同注6,頁295-296。 9 許欣欣:《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與流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108-111。 10 Will Pierre- Etienne, Bureaucracy and Fam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 秦暉:〈「離土不離鄉」:中國現代化的獨特模式〉,《東方》雜志,1994年第1期。 12 Michael Lipton,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3 黃廣明、李思德:〈鄉黨委書記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動情批覆〉,《南方周末》,2000年8月24日頭版頭條。 14 金江鄉鄉政府藏:2000年11月1日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甸縣金江鄉車軸普查區」《車軸村戶主姓名底冊》(內部材料)。 15 此事可參見黃廣明、李思德:〈鄉黨委書記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動情批覆〉,《南方周末》,2000年8月24日頭版頭條。 16 屬口蘑科,學名櫟松茸,藏名「鼻沙」,為橫斷山脈特有種,經濟價值非常高,中甸為主產地,其售賣一直在中甸經濟收入中占很大比重。參見段志誠主編:《中甸縣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頁101。 17 蕭亮中:《夏那藏家》(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頁56-63。 18 參見馬建忠:《霞若鄉的民俗、宗教與自然生態》(云南省林業科學研究院內部調查報告),1999年。 19 同注17,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