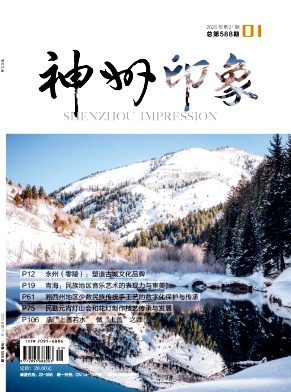“氣”文化與中國古典美學
張榮翼
中國古典美學是指19世紀中葉以前的中國美學。這一時段中國美學的意義在于,它是在中國本土文化和傳統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而在此后的近代美學則是上承古代,又旁納歐美的多重文化范型和思想取向的雜糅體。在今天的文學發展狀況和視野下來重新發掘古典文學的美學蘊含,對于尋求我們文學的文化根基,從而參與與整個世界文學的對話有著積極的實現意義。
下面,我們以“氣”作為切入點來展開論析。
一、 “氣”概念包含的哲學美學意義
“氣”的概念無論在其內涵還是外延上都是非常豐富的,它同道、仁道等概念構成了中國思想史上最為基本的范疇,在中國道家學說、宋代程朱理學、清代戴震等人的學說中都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并且內化為一種美學思想。
“氣”的概念由先秦思想家提出后直到清代的2000余年間綿延不衰,這本身就是一個十分特殊的現象。我們有必要探討“氣”長久保持理論魅力的原因,而這正是由其具有的哲學蘊含所賦予 。
首先,“氣”的概念作為天地萬物生成的基本元素這一認識體現了古人“萬物歸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在這一認識下,天地不過是氣分離后的生成物,而人也不過是氣的特殊的聚散方式,這樣,天地之氣與人之氣可以互相轉化。孟子在回答別人提問時曾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為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1]即那種合乎孟子所理解的正氣可以與天地之氣融通,以至于可“塞于天地之間”。在這一“氣”的溝通下,人與自然萬物、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對象的兩極對立的思維法則被消解了,人對世界的認識不是以人的實踐來探究世界的方方面面,而是人以內省的方式來追詢自我的意識,因為在“氣”的觀點看來人與世界是同質同性的,不直接問諸內心而去探求外界就顯得舍近求遠,舍本逐末了。同時“氣”作為萬物的根本來說,尋成物的根源不過是回到氣的存在狀態,所以,以“氣作為哲學思想核心概念的中國古代思維是重視整體的綜合而輕視具體的分析的。這種對分析方法的忽視也導致了哲學概念與命題上證偽的難以施行,因而“氣”的概念提出后很難發生某種根本的變化。
其次,“氣”的概念還表明了一種抽象與具象之間的中立狀態,它是形而上與形而下的交接點,而這個點的設定對于處理一些具體的認識問題是有著諸多方便的。對“氣”的描述可以將一些模糊的現象加以充分的說明。按照“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區分標準,將抽象出的形而上者稱為“道”或“理”,存在于具象中的形而下者稱為“器”,而“氣”則可兼含兩方面的因素,因為“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在“形”尚未形成因而“器”的性質,但同時“氣”又并不是完全不可言說、不可湊泊的道。如漢代王符所說,“是故道德之用,莫大于氣。道者,氣之根也;氣者,道之使也。”[2]道與“氣”畢竟又非同一的事物。由此,“氣”處在道和器之間的位置。對“氣” 這一特征的認識在日本學者大田晴軒對《老子》第42章“道生一”這一段的詮釋中也可見出。大田晴軒說:“道,理也;一,一氣也;莊周所謂‘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是也。二,陰陽也;三,形氣質之始也。第十四章曰‘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蓋此三者也。意謂道生一氣,一氣分為陰陽,氣化流行于天地之間,形氣質具,而后萬物生焉,故曰‘三生萬物’也。”[3]如果我們將對“氣”的認識與西方柏拉圖哲學作一比較,則柏拉圖學說中的理念作為事物的根本與“道”有相通之處,柏拉圖理念論中所說的具體事物則相當于“器”,而作為中立項的“氣”卻是中國哲學思想中獨有的。它在某些方面看具有“道”的性質,《易·系辭上》云:“一陰一陽謂之道”,氣是化生萬物之源,這使其具有道的抽象性;另一方面“氣”又是“道”的具體化,人們正是通過對“氣”的體察來領悟道的存在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它是載道之“器”。日本學者戶部芳郎從訓詁學角度提出:“在小學上,‘氣’和‘器’有意義上的關系。比如氣息和息器、氣量和器量等等。”[4]南宋朱熹更是明確提出:“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5]綜上所述,“氣”應被視為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一步器之間的一個概念,它可分享二者的一些性質,但又同二者保持著一段距離。
其三,“氣”的概念還表明了運動的觀點。原始混沌的氣因清濁不同而出現陰陽二氣,兩者相互對立斗爭,造成萬物的生衍化育。《淮南子·天文訓》曰:“道者,規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而萬物生。”這一認識體現了古人辯證的思維,更進一步,氣作為萬物化生之本源,氣的運動使人們也持發展的觀點來看等事物,如宋人張載認為“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6]這就把由氣衍生的萬物歸結為氣,即氣不僅化生萬物,而且萬物也因此體現出氣的運動變化的屬性。再進一步說,人也是由氣的聚散所致,人的生死、善惡、榮辱等都可用“氣”來說明終級原因,因此在氣的運動中,人一方面必須順其自然,另一方面也可適度調養,孟子的“養氣”說,黃老思想中的調氣等學說除了具有我們現在所說的調整精神、身體的意思外,還包括將已之一身與天地萬物溝通,以天地四時調順來養育已之一身的意思。這樣,人生活在運動著的世界,并且可以通過得“道”來參與運動著的世界。“氣”的運動這一觀點使中國古代思想對于事物的相對性有所認識,由于運動,事物會發生由此向彼的轉化,彼和此并不是不能逾越的鴻溝,同時在評判事物時,由于人這一評判相位變化運動之中的,萬物以人為尺度的評判前提因人的評判相位變化而發生變化,因此,“氣”的運動這一觀點還有著認識論上的哲學意義。
由以上對“氣”的哲學意義的闡釋我們又可順理推及其美學意義,因為一定的哲學思想必然要對美學有所影響。
由“氣”所闡明的“天地一氣耳”、“天人合一”的思想表達了一種認識上、實踐上主體客體交融的思想,孟子曾說,“萬物皆備于我”, [7]這種物和我二者的交接狀態很自然地為審美活動中物我交融乃至物我兩記忘的境界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中國美學中所追求的并不是藝術品客體的如何精致,而是作品客體能夠激發人的感應的強度,因此它追求的是傳神而非象形,傳神在本質上講就是作品所表達的精神與感受作品者的精神達到契合的強度,它是作品與人、人與作品間的一種對話溝通。
“氣”所表明的形而與形而下的中間狀態使中國文論始終保持著對于文學自身的興趣。在西方,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反文藝觀晃要驅逐詩歌,認為詩足以惑人,即使要有少量詩作,也要限定在頌神的范圍內,這樣,文學作為祭祀活動的犧牲才有部分價值。亞理斯多德反拔了柏拉圖的觀點,認為詩歌通過典型化的描寫可以超越具體事物真實性的束縛,達到比一般歷史敘述更為深刻的真實,在這里文學又是被作為具有哲學洞見之物來獲得認可的。總之,無論反對或贊同文學存在的理由都將文學自身作為一個工具、手段來理解,文學的本體價值是不存在的,而在中國,與正道的研討四書五經之類學問的工作或經邦濟世的政治活動相比,文章只是小道,所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為”(揚雄),但它與具體的生活瑣事及一般人們的職業活動相比,它又可以達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文章千古事”(杜甫)的高度。文學活動本身并不等于“道”,因此要求“文以載道”、“文以明道”,但并不是要求文學達到道的高度和地位,只是說文學中要闡明“道”,文學本體的存在仍是被承認的。歐洲中世紀的文學則不是“載道”的問題,它是整個被納入一教會的精神統治中,文學只劃從屬于“道”。歐洲的文學觀念認為文學本身是形而下的,它必須以形而上的追求來獲得價值,中國文學的觀念則是說文學相對于具體事物已有形而上的部分性質,因此它已有了自身價值,只是相對于道則又有形而下特征,需以“道”來燭照。歐洲文學史上對形而上理想的追尋導致了各種激進的文學運動,它或者以嚴格的文學律條來作規范,如古典主義的“三一律”之類,或者是以反對既有的文藝觀念來標舉新的美學理想,如浪漫主義的現代派藝術。而在中國一般而言相對平和一些,各個作家可以有自己的不同愛好的和情趣,并不一定采取排他的方式來對待其他人的美學主張,原因就在于中國文學均視為“氣”的表現,不同的文學在“氣”這個角度都是可以溝通的。
二、 一“氣”貫通的中國古典美學
由于“氣”所概念所具有的哲學思想涵義使得中國的古典文藝美學理想具有特殊的美學品格,這種品格不僅是作為一個“點”或理論的發生起點來影響中國的文藝思想的,而且它也作為一條“線”貫穿中國的整個文藝美學思想體系,使之成為“一‘氣’呵成”的文藝美不學。當然,由于東方思維并不十分注重理論的體系化,而不象西方往往某一思想家就可獨自構建出一個邏輯上統一的理論系統,所以這種以“氣”貫通的中國古典文藝美學體系是經過了許多代人的努力才得以完成的,并且對它的清晰認識還得經由一定的勾勒、梳理。它主要由以下線索構成。
1.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文學本質論厘定
中國古典文藝美學在文藝的反映說和表現說二者上偏重(不是偏執)于表現說的一方。在文學本質論上,那種“言為心聲,書為心畫”的表現說的主張是世所公認的,不過也得承認表現的根源還在于人對世界的“感應”。南朝鐘嶸在《詩品·序》中開章明義地提出:“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由這一論述來看,藝術的表現在根本上是藝術家的物感。而物感之所以發生,又在于人與物都是“氣”的運行所造成的,這就使得中國古典文藝美學中的文學本南論兼含了反映與表現說兩重因素而又不發生內在沖突。
將“氣”的概念用于文學以說明文學反映性質的較為典型的例子是清代廖燕,他指出,“故吾以為山水者,天地之憤氣所結撰而成者也。天地未辟,此氣嘗蘊于中,迨蘊蓄既久,一旦奮迅而發,似非尋常小器可以當之,必極天下之岳峙潮回海涵地負之觀,而后得以盡其怪奇焉。其氣見于山水者如是,雖歷經千百萬年,充塞宇宙,猶未知其所底止。故知憤氣者,又天地之才也。無才無以泄其憤,非憤無以成其才;則山水者,豈非吾人所當收羅于胸中而為怪奇之文章者哉?”[8]在這一段文字中,廖燕的將山水收羅于胸中之說即與我們今天講的搜集生活素材,觀察生活細節的意思有相通或相近之處,同時它又將山水形貌視為先山水而有的天地之氣所成,這就是超越個人甚至超越人類的主觀性的”擬人化“,山水不復只是山水,更是一種天地之氣的表現,這樣,對山水世界的感受就只在其形貌上追尋,更有一種對其“人化”境界的揣摸、求索,它涉及到調動創作主體想象、聯想、移情等主理功能,因此,它比起一般的文學反映說來說更具有美學上的意義,而不只是在認識論上指明文學的產生源泉。
2、文以氣為主——文學創作論的描摹
將“氣”視為天地萬物及人的內在構成要素或內在依據,文學表現人的情志就不能不同“氣”發生關系,在孟子提出“養吾浩然之氣”的主張之后,率先將“氣”概念應用于文論上的當推魏文帝曹丕,他在《典論·論文》中,以“氣”來品評了同時代的詩人王粲、徐干等人,爾后又提出一個重要命題“文以氣為主”,這個“主”,不是一般分清主、次的“主”,而是指“氣”主導著作文呤詩,作者要根據自己的才性、氣質來創作,“不可力強而致”。有論者認為,曹丕這里的“氣”是指作者的氣質、才氣,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作此理解的,天地與人都自稟其氣,在人來說是才氣、血氣,在于地來說則是陰陽、明晦,其實南上是相通通。但也是盡然,原因在于,中國古代思想中人的主體特質與對象,環境的客體特質并不是截然分開來理解的,上述廖燕談及山川得天地憤氣,而這一“憤氣”也即“天地之才也”,所以,身為人主的曹丕并不以作文為雕蟲小質,而提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將作文提到與事功并立的地位。為文有如此大用,是因它依持著人的才氣和天地之氣的緣故。
宋代蘇轍則在孟子養氣說基礎上進一步加以發揮,他說,“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越間豪俟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上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9]在蘇轍看來,為文不過是“氣”的表現,因此作文應貴乎自然,竟至于不自知的程度,而“學”反而難以成功。他舉出孟子和司馬遷二人的為文之道,都是“以氣為主”,只是孟子主要靠內省的方式提高品性修養,司馬遷主是靠外游的方式充實人生閱歷,途有殊而歸所同。雖然文者都是氣之所形,但并不是說創作就是千篇一律,沒有作者個性的,實質上不同的人都稟同樣的天地之氣,卻因養氣不一而呈現為千差萬變的狀貌。曹丕在《典論》中品評“建安七子”就指出了他們的“氣”有不同的調養。唐代白居易則指出,“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美蓋是氣,凝為性,發為志,散為文。粹勝靈者,其文沖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者,其文蔚溫雅淵,疏朗麗則,檢不扼,達不放,古淡而不鄙,新奇而不怪。[10]從這里一理論表述看來,作家的氣性之異先在于內,然后有作文的格調差異現于外,如此不同作家方可以找到最適合于自己的創作表達方式,作文的立足點首先是作者的養氣問題。
3.氣韻生動——文學批評論的標準
從文學的本質即“氣”的理論出發,再結合文學創作是“氣”之所形的認識,自然地在文學批評領域也會把“氣”作為批評的重要衡量標準。在這方面,謝赫所提的“氣韻生動”堪稱其中代表。
南朝時謝赭提出的批評標準共有六條,即“畫有六法”,它本是畫論的一部分,便在“詩畫同源”的藝術氛圍下,其對于文學也有相當大的適用性。謝赫的六法是“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11]對此六法的關系問題,有論者提出“‘六法’是一個互相聯系的整體。‘氣韻生動’是對作品總的要求,是繪畫中的最高境界。它要求以生動的形象充分表現人物的內在精神。‘六法’的其它幾個方面則是達到‘氣韻生動’的必要條件。”[12]如果此說可以成立的話,那么也就可以說“氣韻生動”是對藝術的總的美學要求,而后幾個方面則是在繪畫上完成它的特殊手段。對于文學來說,“氣韻生動”在后世成了批評上的一條評價標準。
對“氣韻生動”一語由于謝赫本人未多加說明,因此后人在理解上存有歧見,有將氣韻折為二字來解的,也有將氣韻作為一個整體來認識的,至于將之分為二詞的則還有“氣之韻”、“氣和韻”等不同解法,不一而足。[13]其中元代書法家楊維楨所釋的“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大體能成為諸家論者的共識,即氣韻生動主要指在圖畫景物人物形貌之余更應有對其精神狀態的揭示,謝赫自己也曾將“氣韻”說為“神韻”,大抵表達了這樣的意思。從理論淵源來說,謝赫的“氣韻生動”是對前人尤其是對顧愷之“以形寫神”論進一步拓展,而從理論創意來說,它從之于形神論更推衍到充溢天地萬物的氣的節奏韻律,即天地萬物的氣是比具體的物之形更為根本的,寫形關鍵是要寫出氣的流動、變化。這樣,它就比形神之辯邁進到一個更具有實證性、操作性的地步。宗白華先生指出,“氣韻,就是宇宙中鼓動萬物的‘氣’的節奏、和諧。繪畫有氣韻,就能給欣賞者一種音樂感。”[14]在具體談論中國畫的特征時他將繪畫的這種氣韻作了一段描摹:
……中國畫的光是動蕩著全幅畫面的一種形而上的、非寫實的宇宙靈氣的流行,貫徹中邊,往復上下,古絹的暗然而光尤能傳達這種神秘的意味。西洋傳統的油畫填沒畫底,不留空白,畫面上動蕩的光和氣氛仍是物理的目睹的實質,而中國畫上畫家用心所在,正是無筆墨處,無筆墨處卻是飄渺天倪、化工的境界。(即其筆墨所未到,亦有靈氣空中行)這種畫面的構造是植根于中國心靈里蔥籠纟因 缊蓬勃生發的宇宙意識。[15]
同樣中國園林建筑等藝術形式中也有類似的情形,如建筑物上挑的“飛檐“,仿佛屋宇振翅欲飛,一窗一牖也是將有限推及無限的畫框,所謂“川俯繡戶,日月近雕梁”、“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杜甫)。上述中國畫的空白也好,建筑上的“飛檐”、窗牖設置也好,它都表現了一種“氣”的運動感,如屋檐本給人一種壓抑感,但上挑后的“飛檐”又有一種向上的動感,仿佛是一種“氣”將屋檐向托舉。
氣韻體現在文學中也有相當奧妙,在其實質上來說,文學與給畫、建筑中的氣韻實際上都是體現了一種整體的綜合的審美意識,即努力使藝術形象具有超越形象之外的含義,但由于文學形象由語言媒介來塑造,因此安的體現就更依賴于創作與接受作品的人的想象活動,更具有氣韻的魅力源于對形象的深層意義的直覺感受,鄧形象背后的含義不是通過分析來理解,而是通過直覺式的感受來品味的,它可以達到對深層意義的某種程度的體驗,體驗后的美感賦予作品魅力。從葉燮對杜詩下列詩句的剖析就可見出中國古典詩歌“氣韻”的體現,他說:
又《夔州雨濕不得上岸作》“晨鐘云外濕”句:以濕鐘為物而濕乎?云外之物,何啻以萬萬千計!且鐘必于寺觀,即寺觀中,鐘之外,物亦無算,何獨濕鐘乎?然為此語者,因聞鐘聲有觸而云然也。聲無形,安能濕?鐘聲入耳而有聞,聞在耳,只能辨其聲,安能辨其濕?曰云外,是又以目始見云,不見鐘,故云云外。然此詩為雨濕而作,有云然后有雨,鐘為雨濕,則鐘在云內,不應云外也。斯語也,吾不知其為耳聞耶?為目見耶?為意揣也……聲中聞濕,妙悟天開,從至理實事中領悟,乃得此境界也。[16]
鐘聲作用于聽覺,而“濕”作用于觸覺,言鐘聲“濕”,于字面似有不妥但它將晨鐘初發時其聲透過霧靄而來的清越,冷寂之感表現得淋漓盡致,這其實就是“氣韻生動”的佳句。
4、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文學發展的勾勒
“氣”的概念本身就包含了運動,變化的意思,大則天地由陰陽二氣驅動生出四時五行,小則人的呼吸吐納,氣血盛衰,都莫不是“氣”的運動作用使然,由“氣”的觀點來論文,理所當然地在文學史觀上體現為文學的發展論,但另一方面,氣又是萬物本原,是形而下事物在經驗層次上的最高抽象,事物的變化是由于“氣”所作用,并且它也是“氣”的體現,因此這種文學發展觀認為變化推移的終究只是文學的具體形貌,而統攝古今文學的“氣”的本體則是不變如一的。
葉燮指出,“蓋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禪……今就《三百篇》言之,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風雅已不能不由此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在而刪變也。”[17]基這里變化是以“遞變”來表述的,而不變如一的方面是以“相禪”來表述的,《三百篇》中雖有正變之分,但“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的概括則是周全的,反過來說,編收《詩經》的孔子也不能存在刪變,也得正視創作時間上的差異可能達數百年之久的詩篇中的不同狀況。
從明代舉人胡應麟對唐詩幾個佳句的例析中也可見出古人的這種與“氣”相關的文學發展觀,他說:“盛唐句,如‘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中唐句,如‘風兼殘雪起,河帶斷水流。’晚唐句,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皆形容易物,妙絕千古,而盛、中、晚唐界限斬然。故知文章關氣運,非人力。”[18]在詩例中,幾個句子都有一種凄清、惆悵的氣氛,但盛唐句的“海日”、“江春”表達出一種博大宏曠的胸襟,一種向外進取、開拓的精神,它的惆悵是一種青年人對未來感到迷惘的惆悵;中唐的“殘雪”、“斷冰”則境界已變,它是對人生坎坷,世事艱難的切身痛悟而生發的類于中年人飽經摧折的惆悵;晚唐句的“雞聲”、“人跡”、“茅店”、“權橋”貼近于生活中的細微未節,是一種老年人式的世事不堪回首的落寞惆悵。用我們今天的觀點來講,文學是一定社會情緒的寫照,唐代詩風的轉變體現了國熱變化對唐人心理模式的鑄冶,這在古人言之為“氣運”。在此變化中,幾個詩句在形容景物上都堪稱“妙絕千古”,又體現了文學在變化中的同一性,以古代文學審美標準來衡量,它們都是“氣韻生動”的佳句。
以“氣”來貫通的文學發展既講文之變,又講文之通,認為變是外在的、不變是本質的。劉勰在《文心雕龍·通變》中講“文辭氣力,通變則久”,通指古今之通、之同,講的是繼承,變是古今之變、之別,講的是革新,而這兩方面并非等價的,“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體是本體,是根本性的,文即“紋”,是外在表現,屬相對次要的層次。而不管文的外在表現如何,其“序志述時,其揆一也。”其根本性的方面是不可變更的,實際上,今人的發展觀是在進化論影響下形成的,其發展被理解為一個線性的過程,如果它仍會回到與以前同一的性質特征上,那也被理解為螺旋式的上升和回復。古人的發展觀則是建立在陰陽互反的理論背景下,發展更象是拉鋸式的回復或推磨式的回旋。現在有些論者在引述古人對文學發展問題上的“通變”觀時,動輒貫之以辯證的繼承革新發展觀來評之,好象幾百年、上千年前的古人就比今人認識得更為合理,其實,古人之“文學”與今人的理解有著根本性不同,而其發展也是在不同的理論背景下進行的,今天對它們的整理、學習,也只能持以“通變”的態度。
三、以“氣”為核心的中國古典美學的兩種品格
魯迅曾說:“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界的自覺時代。”[19]這種自覺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在認識上的,此前多是談文學的“用”,即文學有何功有,而文學的“體”即文學的本體位置,它所應別于一般文章的特性則未曾談得充分;二是在實踐上的,此前的文學是一個兼括文史的龐大體系,文學的自覺的藝術追求未被重視,僅僅是“辭達而已”,以表達思想作為核心,曹丕的時代就是在這兩方面較之前人有了進步,表現出了文學的自覺意識。
曹丕在理論上提出的“文以氣為主”可以說是認識上對文學的自覺,即文學并非只是受制于寫作題旨的“達意”和寫作對象上的“稱物”,更是作家主動脈體氣質的投射,而魏晉以后的文學創作追求“滋味”、“神韻”、“傳神”、“意境”等則是從實踐上對文學產生自覺的表現。
我們在前面論述“氣”的哲學意義時曾指明了該詞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雙重含義,而魏晉六朝時它基本上以形而上的意義出現在文論中。宋人王柏曾說:“夫道者,形而上者也;氣者,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不可見了,必有形而下者炎之體焉,故氣亦道也。”[20]這一解釋基本體現了魏晉之際以氣論文者的傾向。這種強調以形而上的“氣”來論文、作文的狀況與當時莊禪的興盛密切關聯,此岸世界形、體被彼岸世界的神、道逐到一個不重要且基本處于被否定的地位上,士大夫追求放浪形骸、不拘禮俗的風貌,以一言取人,以氣韻評人的風氣相當普遍,在《世說新語》中對此有相當細膩的寫照。以“氣”論文在當時的核心意義在于,它把文學的形、言作為我在的表象,認為沒有本體的意義,文學在語言的外表下是以文學形象的“氣”為主,形象又是以作者的“氣”為主,作者又是以天地陰陽之氣為主,再極而言之,中央電視臺天地又是以太極一氣為主,這就把文學推以了一個形而上的永恒性的彼岸世界,或者說給文學賦予了超越具體經驗之外的形而上的意義。
魏晉以降的中國古代文藝美學認為,文學創作應“超以象外,得其環中”,“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生氣遠出,不著死灰”,“離形得似,庶幾斯人”(司空圖語),詩的藝術特色應是“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嚴羽語),這些認識都是在以“氣論文氛圍下產生的。唐詩的意境,宋詞的韻味,元曲的雋永,都與此前尤其是魏晉之前的詩賦那種難以句摘的整體之美有著判然之別,唐詩宋詞元曲之美往往是整個作品中以一二句體現出全詩精華,進一步說在一二佳句中又可能是以某一字來作為詩眼盡傳精神的”王國維在評詞時曾說:“‘紅杏枝頭春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21]這種以局部來代表整體,以個別來統率一般的做法在作文與評文中都成為一種相當普遍的風習,推究起來,它實則是標舉“氣”的形而上的一面,是以文之“氣”來觀文的必然結果。
與之相反,“氣”畢竟屬于形而下的事物,在形而上的“道”面前,它是對“道”的一種施行、運用,因此,在莊禪之學興盛的魏晉六朝,由于重神輕形,重彼岸輕此岸,重一世輕今生的文化氛圍,“氣”的形而上一面被充分強調,隨著后來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中的正宗地位不斷鞏固,儒家的現實理性又必然地會將“氣”作為與“言”相對概念已具有一般的作者主觀意圖的意思,說“氣”相當于水,“言”相當于水之浮物,在這一比喻中“氣”的形而下的一面得到了體現,進一步看,隨著中國古典文學的發展,元代的戲曲,明清的小說、散文,已經各自在當時成為比詩歌更基本的文學體裁。它們在篇幅上遠大于一般詩詞,在創作角度上它們也由以抒情寫景為主轉為敘事寫人為主,在這種氛圍下,那種由一二詩眼、一二佳句就可提挈全文篇的“氣”就是易發揮作用了,而且敘事的魅力只能在敘事的“過程”中來體現,只由某一句子作為敘事作品的提示或敘事的結果的作法都與敘事之價值毫不相干,這與抒情之作適成鮮明對照,這樣,以“氣”論文中的“氣”就演變為對作品氣勢——作品篇章結構和語言運用方式——的評說,在這里體現了一種雙向思維的流變,即以“氣”來論文時,由于將“氣”視為比文更為根本的存在,因此,層層推衍,最終將“氣”推到了不可湊泊、難以言傳的形而上的境地;另一方面,由于文在根本表現形態上是相當具體的,所以在論文時僅以飄渺虛空的“氣”來評說又確乎顯得大而無當,過于空泛,于是又作逆向推衍,將“氣”落實到可以眼見口誦的形而下的方面,有清一代的桐城派文論可以說就是這樣一個代表。
桐城文論如只作純粹的文論來看,由于論者的思想保守,乃至反動,一般地說它的負面價值是大于正面價值的,但每種理論都有其產生的時代背景,都在某一些回答了時代的要求,那么以此來認識,桐城派文論也是有積極作用的。
桐城派的劉大魁在以“氣”論文時一反將“氣”推到形而上境界的思路,認為“氣”應在形而正氣詞句音節中尋求,所謂“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精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然論文而至于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者,神氣之跡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于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近人論文,不知有所謂音節者;至語以字句,則必笑以為末事。此論似高實謬。[22]桐城派另一干將姚鼐也說“文字者,猶人之言語也。有氣則充之,則觀其文也,雖百世而后,如立其人而與言如此,無氣則積字焉而已。[23]在這里“氣”被視為是使文學作品字句、音節體現出魅力的實體,“氣”不是一種作品之外的神韻,而就是作品,就是作品字里行間的生氣所在。我們說,桐城派文論回答了時代的要求,應從它將“氣”的形而下的一面加以強調的時代背景來看,明清兩朝以“八股”取土后,文人們以“義理、考據、文章”并重,光憑一時的才氣作文就可象唐宋之時那樣中舉及第已不太可能,在這一趨勢下有影響的文人要求除了有生花妙筆之能以外,不要成為經綸滿腹的飽學之士,因而以“氣”的形而上的一面來論文對他們來說就有些空泛,“義理”要求作文中須體現學識、邏輯,考據“則要求作文中用詞要知曉其出處、音韻,這樣,形而下一面的“氣”就派上了用場。盡管清代時也有其它反對桐城派的文論,但基影響都無出其右,并不能動搖桐城派的地位,其原因就在于這一背景因素在起作用。再從文學發展的自身邏輯來看,清代以來小說文體已不光是創作上成就突出,而且它也開始登上大雅之堂,尤其后來西主文化影響滲入后,小說更成為文學中最重要的文體。對這一新的文全光憑“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氣韻生動”的標準來衡量就顯得不太合適,小說文體的特性在于它的不可濃縮性,詩可用某一詩眼、佳句來代表,小說則是以全文來展示整體的魅力,它的價值主要是描寫之中,“氣”的形而上的一面有些不著邊際。區別小說文體與一般非文學作品的差異就在于小說語言的審美性,這樣,字句、音節的重要性就突出了。姚鼐曾把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字視為作文的要求,而神、理、氣味需在格、律、聲、以上具體體現,他雖是就一般散文創作角度來提的要求,但也反映了小說登上文壇盟主地位的過渡時期的理論需要,由此也可見出由“氣”評文的側重點的轉移。
如果說魏晉以降對文學的自覺體現在文藝理論上是以“氣”論文,揭示出文學的超越具體字句的形而上的意義的話,那么清代以來對“氣”的形而下的一面的強調,突出文學詞語審美的功能則可說是對文學的第二次自覺,這樣來認識可以使我們對問題有一種總攬全局的整體的眼光。
注:
《孟子·公孫丑上》。
王符:《潛夫論·本篇訓》。
轉引自沙少海、徐子宏譯注《老子全譯》第42章校注[1]釋文,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85頁。
參見[日]小野譯精一等編《氣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19頁。
《朱文公文集·答黃道夫書》。
張載:《正蒙·太和》。
《孟子·盡心上》。
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四《劉五原詩集序》。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白居易:《白香山文集》卷五十九《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謝赫:《古畫品錄序》。
北京大學哲學系編《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上卷,編者附言,中華書局1980年版,1990頁。
可見見高楠《道教與美學》第三章中《道教思維與“氣韻生動” 》一節,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44頁,71-72頁。
同上
葉燮:《原詩·內篇》。
同上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
魯迅:《而已集·魏晉風度及藥與酒的關系》。
引自郭紹虞等主編《中國歷史文論選》第二冊,287頁。
王國維:《人間詞話》。
劉大魁:《論文偶寄》。
姚鼐:《惜包軒文集·答翁學士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