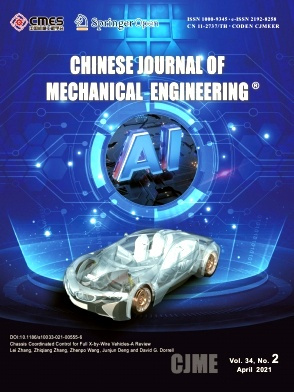“倫理化”的漢語基督教與基督教的倫理意義—基督教倫理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的可能性及其難題
楊慧林
“倫理”或“道德”之謂(Ethics or Morality),在中文與西文中均可作兩個層面上的解釋,即:內在的價值理想或者外在的行為規范。而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實際碰撞中,由于“至簡、至圓”、“陰助教化”的本土傳統之引導,這兩個層面的發展是極不平衡的。就其總體情況而言,行為規范意義上的“倫理化”或者“道德化”始終是漢語基督教的主要路向。這種“單向度”的闡釋框架,使“倫理化”的漢語基督教與基督教所應當包含的倫理資源之間,常常存有一定程度的錯位。不解決這一問題,基督教倫理便無法在中國文化語境中實現其潛在的可能性。
一 漢語基督教的“倫理化”過程
基督教初入中土之時,景教文典首先是日益見出“撮原典大部之要,引中土佛道之俗”的傾向,即所謂“以佛老釋耶”。 立于公元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和譯述于初唐的《一神論》,已開始借用佛老的“妙有”、“無為”、“法界”等,并有“神識”、“五蔭”、“四色”之謂,被研究者對應于佛家的“識蘊”、“五蘊”、“四大”。中唐以后的《宣元至本經》更有“無元”、“無言”、“無道”、“無緣”、“非有”等道家語。其中“妙道能包含萬物之奧道者,虛通之妙理,群生之正性;奧,深秘也”等等,被認為是老子《道德經》“道者萬物之奧”的注釋;“善人之寶”以及“美言可以市人,尊行可以加人”基本上是引用老子的原句。《志玄安樂經》則是以“無欲”、“無為”、“無德”、“無證”貫穿其解說,甚至借耶穌之口作佛老之言:“凡修勝道,先除動欲,無動無欲,則不求不為;無求無為,則能清能凈;能清能凈,則能悟能證;能悟能證,則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樂緣。”
過于附會佛老的釋經方式,使景教難以獲得獨立的文化身份,乃至其大部分經文竟是夾雜在佛教典籍中得以保存。這樣,它在唐武宗以后一禁而絕,并不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對于后世基督教的再度傳入中國,景教至少留下了三方面的結構性影響。第一,異質文化的移植,似乎必須經由一種本土的闡釋方式加以引導;明清之際的“以儒釋耶”或可說是此種邏輯的又一次推演。第二,“以佛老釋耶”在義理上的結果,是通過“玄無至樂”趨向形而上之思;這正是中國知識分子所津津樂道的。第三,“以佛老釋耶”的結果落實到世間,則是遣欲澄心、遺形忘體的“養性”之德;漢語基督教的“倫理化”過程,在此埋下了第一顆種子。
明清之際“以儒釋耶”的典型,可見于明弘治二年(1498)、正德七年(1512)和清康熙二年(1663)分別豎立于開封以色列教寺的三塊石碑。其碑文不再附庸佛道,卻反復強調基督教“與儒書字異而義同”,所同之處則是“孝悌忠信、仁義禮智”、“不外乎五倫矣”。其中許多措辭,反復涉及君臣父子、天命王法,與《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公孫丑上》如出一轍。 附會儒理的漢語基督教,更多地執著于倫常日用、世俗綱紀的“修身”之德,這成為漢語基督教之“倫理化”過程中的關鍵一步。雖然“禮儀之爭”使這一過程暫時停止,然而根據儒學傳統和世俗道德來褒揚或者批判基督教,已成中國受眾的基本格局。
鴉片戰爭強行打開“教禁”,為基督教在中國的第三次更大規模的傳播提供了便利。不過在很多中國人眼中,這恰恰使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侵略”難脫干系。如同林語堂所說:“中國基督徒不近鴉片”,外國的傳教士也當然譴責鴉片;但是其中的“戲劇性和悲劇性成分,是傳教士的同胞們把它帶進來而用槍逼我們接受。” 因此就連林語堂這樣一個與基督教淵源深厚、并且最終皈依了基督教信仰的人,也相當刻薄地描述了基督教在中國的尷尬:“傳教士進入中國……正是在中國人被鴉片惡臭熏醒的時候。……傳教士及鴉片都在戰艦的蔭庇之下得益,使這情形變得不但可嘆,而且十分滑稽可笑。……傳教士曾關心拯救我們的靈魂,所以當戰艦把我們的身體轟成碎片的時候,我們當然是篤定可上天堂,這樣便互相抵消、兩不相欠。” 在這樣的背景下,本世紀以來“本色化”運動的實質性任務,其實就是“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號”。 惟其如此,基督教才有可能融于現代社會以及中國文化的語境。而要完成這一任務的直接進路,仍然被認為是“倫常日用之間”——基督教倫理的世俗功能再次得到重申。就此,許多神學主張并不相同的漢語基督教學者均有相似的論說。 中國大陸的基督教領袖丁光訓先生,近年來也多次強調福音中的倫理內容,以及基督教之“救贖”與“服務”相統一的道德作用。
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基督教發展迅速,有些地區基督教信徒的增長已經遠遠超過其人口增長的比例。 教外研究者的一些善意的調查報告常常會著重說明:基督教信仰的傳播對于改善當地的社會秩序、提高大眾的道德水準等,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教會內部也與佛教的“利樂有情”、道教的“兩世吉慶”相應,提出“榮神益人”,并大力表彰修橋鋪路、植樹造林中的基督徒積極分子和“五好家庭”等等。 這些進展當然可以標志著基督教已經更多地為中國社會所接納;但是另一方面,當“倫理化”的闡釋方式進深到體制性層面時,我們或可發現漢語基督教在神學理念上似乎始終沒有發生過多少變化。
時至90年代,天主教神學家漢斯·昆所倡導的“世界倫理”構想有可能成為漢語基督教之“倫理化”的新的生長點,同時它也迫使我們更直接地面對其中的問題。比如:第一,世俗的倫理準則并非絕對的道德命令,如果抽去其背后的信念依據,它是否可以為自身提供合法性說明?第二,事實上,任何一種不道德的行為都可以從不同角度獲得道德的辯護,那么世俗的倫理準則能否解決這種內在的悖論?第三,無論是“底線”的還是“高線”的倫理準則,在各種文化傳統和信仰資源中都并不缺乏,然而這些準則何以不能產生實際的約束力?
二 “倫理化”的漢語基督教所受到的挑戰
儒學傳統在現世道德和人生境界方面的優勢,使漢語基督教的“倫理化”傳播從一開始就處于不利的地位。其中的悖謬在于:一方面似乎是“倫理化”的路向才使基督教在漢語語境中得到成功的發展,另一方面則是執著于世俗倫理的漢語基督教在義理上并不優于其施教對象,從而無以確認基督教在漢語語境中的立身依據。在明清文人依據儒家道德對基督教進行“格義”、“判教”及其相互攻訐中,這一點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
另一方面,在基督教進入中國之前,儒釋道三家便已在皇權的涵攝下形成“三教論衡、同歸于善”的傳統。所謂“善”者,乃是“陰助教化”之謂。由此論之,“倫理化”并不為漢語基督教所獨具,而是中國文化語境中的一種強大的慣性。基督教要在這一語境中進行涵化,“同歸于善”當然最為簡便,但是“陰助教化”的“善”必然要求放棄異質的價值理想,在“用”的意義上融入世俗綱常。因此“同歸”的選擇只能再次印證中國傳統的包容性和化解力,并不能解決漢語基督教的文化身份問題。其實這種包容性和化解力更注重的只是“同”,而不是所“歸”的對象。乃至有伶人戲噱“三教論衡”時,甚至可以將“善”轉換為“婦人”,“同歸”的邏輯卻仍然不能動搖。
再者,中國與西方均可以在傳統中找到“道德形而上學”的思想資源。但是如前文所述:“引導”過景教的佛老思想最終是落實于“養性”;作為明清以后漢語基督教之主要闡釋依據的儒家學說,則以“修身”為根。隱含其間的,正是漢語本義上的“道德”。“道德”在中國的古文字中,與人類的行為密不可分。“道”字從“走”從“首”;“走”是人的行止,“首”則像“人頭有發形”。“德”字從“彳”;“彳”也是“小步而行”,所以“德”即是“用力徙前”。直到《禮記·中庸》的“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和《易經·乾卦》的“君子進德修業”,倫理道德之學大體是以行為規范的意義傳世的。 西方從柏拉圖的“理念論”到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對“至善”的追索始終潛在其間; 這與基督教的神學倫理含有相似的指向,卻完全不同于漢語基督教所屬意的世俗秩序。
中國更具形而上意味的道德學說或許是由天及人的老莊之道,然而它在“及人”之處落實于“為無為、事無事”、“欲不欲”、“學不學”等一系列否定式的原則。老子《道德經》甚至提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這樣,明清以后被肯定現世秩序、強調“收拾人心”的儒家思想所闡釋的漢語基督教,似難以取道老莊。
儒家之道則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從這“以人為本”的出發點關聯到基督教,在辜鴻銘1901年所著的《總督衙門來書》中引出了一段有趣的解說:“無論你是猶太人、中國人、德國人,是商人、傳教士、兵士、外交家、苦力,若你能仁慈不私,你就是一個基督徒,一個文化人。但如果自私、不仁,即使你是世界的大皇帝你仍是一個偽善者、一個下流人、一個非利士人、一個邪教徒、一個亞瑪力人、一個野蠻人、一只野獸。” 辜鴻銘的措辭盡管極端,對“人能弘道”的把握并沒有錯,即:所謂“道”并不能通過其他途徑而被確認,它只是在道德主體的行為中得以顯現的。關于這一點,孔子本人也有“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之說。 恰如識者所斷:“儒道‘道德觀’的分野,全在于是否‘依于仁’。”
按照儒家理想,世間道德所憑依的“仁”是與“圣”相通的; 同時,與“圣”相通的“仁”又完全是人力所能及,正所謂“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既然“仁”能通“圣”、且可以“至”(獲得),而“至善”之“道”只能存于“志”,那么祈向絕對價值的“究元”當然要取道于相對性的現世德行。由此似可為儒家的“極高明而道中庸” 作一別解。盡管“中庸”被孔子釋為“至德” ,此處的“至德”卻顯然有別于作為“圣”本身的“至善”,其關鍵的落腳處不在于“至”而在于“德”。“德”所指涉的很難說是“形而上之境”,恐怕更多的還是現世中的“修養踐履”。基督教的理想一旦被這樣的道德學說加以闡發,在適應中國文化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