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國的可能性——兼論對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解讀和反思(二)
佚名
在法治秩序的建構(gòu)屢試不成、改革的目標(biāo)遲遲不能達(dá)到的今天,的確有必要檢討一下對傳統(tǒng)文化和現(xiàn)實的把握是否正確、新制度的設(shè)計是否適當(dāng)、能否采取某種與西歐法治模式在功能上等價的替代性方案等。無論如何,首先需要換一個角度對中國傳統(tǒng)秩序原理進(jìn)行考察、理解以及再解釋,否則關(guān)于中國法治的討論就無法深入下去。
前面引粱啟超的見解,指出中國思想往往視法律和命令同為一物。但是也要看到,法律體系的設(shè)計以及運作的實踐還存在另外一個側(cè)面,這就是“禮法雙行”、“刑政相參”、“情法兼到”、“德刑并用”的多元性契機。制度層面的這種多元構(gòu)成在漢代儒士主持所謂“以禮人法”的解釋運動之后表現(xiàn)得十分鮮明。雖然中國學(xué)者對這一特征不可謂不重視,但是,對“以禮入法”所引起的中國秩序原理的變化及其深遠(yuǎn)的意義似乎沒有充分展開討論。我認(rèn)為,有可能解決問題的關(guān)鍵恰恰就在這里。
關(guān)于“禮”的論述已經(jīng)不勝枚舉,但從法社會學(xué)的觀點來考察,禮的本質(zhì)無非是特殊的持續(xù)型人際關(guān)系的制度化形態(tài),是在互惠原則和禮樂教化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關(guān)系秩序”,用昂格爾(Roberto M.Unger)的話來說,是“相互作用的法”。在日常生活當(dāng)中,通過拉關(guān)系的相互作用、討價還價的試錯過程以及“建構(gòu)關(guān)系的社會工程”(金耀基),人與人之間的結(jié)構(gòu)勢必會按幾何級數(shù)不斷增長,因而關(guān)系秩序勢必會迅速擴張或者稠密化,演變得非常復(fù)雜。與歐美社會不同,在中國“關(guān)系秩序”不僅僅是在國家制度之外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其核心。為此,中國被認(rèn)為是“關(guān)系本位”的,是一種“關(guān)系”社會的典
型。另外,“關(guān)系秩序”也不僅僅是區(qū)別于“法律秩序”的非正式民間秩序,它還被編織到“法律秩序”當(dāng)中并成為正式的國家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樣的格局里,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無所不在,個人甚至可以借助“關(guān)系學(xué)”的技術(shù)來為自己或者為他人作出角色定義,改變自己與社會的邊際,從而部分地塑造和修改社會的結(jié)構(gòu)。那么,與上述特殊狀態(tài)相對應(yīng),國家制度究竟是如何運作的?社會秩序的特征應(yīng)該如何闡述?法治的理念是否可行?現(xiàn)在來對這些問題進(jìn)行初步的探討。
1.作為復(fù)雜系的法律秩序
不妨這么來看中國傳統(tǒng)的秩序原理,即通過漢代“以禮入法”的解釋性轉(zhuǎn)變,形成了把強調(diào)整齊劃一的“法律秩序”(律令)與強調(diào)臨機應(yīng)變的“關(guān)系秩序”(禮教)結(jié)合在一起的社會結(jié)構(gòu),其中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是呈幾何級數(shù)不斷增長的。為了在這兩種性質(zhì)迥異、相反相成的秩序之間保持均衡,作為秩序載體的司法官僚等必須基于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則,參照復(fù)數(shù)性的規(guī)范、當(dāng)事人的意愿和滿足度以及社會關(guān)系恢復(fù)協(xié)調(diào)的要求再三進(jìn)行調(diào)整和說服。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任何一項具體的法律決定都是以全體承認(rèn)、沒有異議為目標(biāo),都可能表現(xiàn)為試錯、反饋以及通過無限反復(fù)達(dá)成的“合理的合意”。在這個過程中,根據(jù)特定當(dāng)事人之間的主觀性進(jìn)行的社會交換必然頻繁出現(xiàn),引起法律適用方面的隨機漲落甚至導(dǎo)致一種復(fù)雜的混沌狀態(tài)。中國秩序的上述機制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分形(fractals)”式的“復(fù)雜化(complexification)”:類似復(fù)函數(shù)z2+C那樣的由倍增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變動系)與機械的法律體制(定常系)所組成的統(tǒng)治公式,通過極其簡單的非線性過程(交涉、議論以及合意)的反復(fù)以及向各組成部分的反饋而呈現(xiàn)出無限豐富的變形。我認(rèn)為,中國傳統(tǒng)的法律秩序完全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復(fù)雜系(a complex system)。
迄今還沒有人從這樣的角度來理解中國的秩序原理。但是,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一些洞察力很強的學(xué)者已經(jīng)隱約感覺到某些相關(guān)的跡像。例如,韋伯把中國法文化理解為一種官僚根據(jù)實踐理性進(jìn)行的試驗,即權(quán)力的試行;指出中國早期就存在資本主義萌芽及其他與西歐類似的現(xiàn)象少強調(diào)中國人精神結(jié)構(gòu)中的多元性組合;注意到在“天人合一”觀念下出現(xiàn)的類似分形原理或者全息原理的“小宇宙(microcosm)”。龐樸揭示了中國傳統(tǒng)的辨證法是“一分為三”、“循環(huán)滋生”、“脫胎于混油的雜多”。劉長林特別強調(diào)《呂氏春秋》中提出的社會控制方面的圜道觀,認(rèn)為這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最根本的觀念之一,即通過循環(huán)“從有限中引出無限”。
顯而易見,我稱為“復(fù)雜系的秩序”這樣的制度設(shè)計,從整體上看,完全不同于凱爾森(Hans Kelsen)所設(shè)想的金字塔型的井然有序的規(guī)則體系,它不采納把所有事實都九九歸一于法律條文之下的包攝技術(shù),因而不可能按照還原主義的“法律八股”的思路進(jìn)行復(fù)雜性縮減,也很難通過透明而精確的概念來充分保障行為結(jié)果的可預(yù)測性。這種秩序是在各種差異因素互相干涉中形成并不斷改變的有序化的一種過程和一定狀態(tài),可以想像為從律令制的主干不斷分枝、生長的一棵活的“決定之樹”。在如此豐富多樣而又變易不居的各種不同因素之間,當(dāng)然需要維持盡可能多的反饋和溝通的渠道,或者建立某種能使法律與互相聯(lián)系貫穿的“通道性制度”(圖依布納Gunther Teubner的表述),這就是“圜道”、即中國所說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上通下達(dá);需要在各種相生相克的訴求中達(dá)成均衡的睿知,這就是通過試錯進(jìn)行適當(dāng)調(diào)整的實踐理性;需要秩序擔(dān)綱者勵精圖治的勤勉,因此必須規(guī)定嚴(yán)格的責(zé)任以及加強監(jiān)督機制。如果不具備上述條件,那樣一種包含許多偶然性、建立在安定與變化的微妙均衡之上的動態(tài)秩序就會立即而然地分崩離析。
2.制度設(shè)計的擬態(tài)性
根據(jù)現(xiàn)代原理建立起來的單純系(這里的所謂“單純”,僅指即使再精致復(fù)雜的抽象建構(gòu)都可以通過線性過程進(jìn)行要素還原和實驗再現(xiàn)),只有預(yù)設(shè)了前提條件才能成立。但是,復(fù)雜系卻充滿了整個世界。從傍晚山村的裊裊炊煙,到陽春京城的絲絲柳絮,從掠過晨空的鳥群,到尋覓過冬儲備食物的蟻陣,那隨機的軌跡、那偶然的隊形,雖然一過即逝、了無舊痕、只可追憶不可重演,但都能夠用復(fù)雜系來描述和說明其基本原理。因此,作為復(fù)雜系的法律秩序顯然更接近天然狀態(tài),或者說是有意模仿天然狀態(tài)。中國法制的設(shè)計思路正是如此,所以說“道法天然”,“道生法”。例如,在時間維度上,為適應(yīng)季節(jié)的性質(zhì)而編制“時政綱領(lǐng)”,司法審判活動也必須因時制宜;在空間維度上為適應(yīng)方位的性質(zhì)而講究“風(fēng)水堪輿”,甚至連兵刑施政場所的決定也必須因地制宜。
在這樣互相關(guān)聯(lián)的有機性宇宙秩序當(dāng)中,自然的災(zāi)異祥瑞與社會的動蕩安寧是互相關(guān)聯(lián)的,反常變異的現(xiàn)象往往被理解為對冤獄多有、民意郁結(jié)的一種“天譴”或“示威”。根據(jù)的記載,例如雄雞下蛋、肥豬啃人等奇事發(fā)生時,在西歐是法官按照審判人犯的程序一本正經(jīng)地向行為不軌的動物卻問罪科罰,而在中國,皇帝將按照整頓綱紀(jì)的程序反過來對本來八桿子打不著的法官們追究責(zé)任。韋伯認(rèn)為諸如此類的巫術(shù)信仰正是中國統(tǒng)治權(quán)力分配的憲法性基礎(chǔ)的一部分。讓我更感興趣的并不是中國式秩序的終極根據(jù)的性質(zhì),恰恰是法律規(guī)范對具體事實的“變己適應(yīng)(autoplastic adaptation)”,即法的擬態(tài)性或者仿生學(xué)。法律有時君臨社會之上,但更多的場合卻隱蔽甚至融化在社會之中。這種擬態(tài)性使得表面上看來十分簡單機械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可以具有相當(dāng)程度的彈力和生命力,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國家的合法化契機就隱藏在這種迷彩變色、流轉(zhuǎn)不居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之中。因此,中國的社會秩序并沒有設(shè)定作為“憲法性基礎(chǔ)”的終極根據(jù),而只需要對在“求民情”和“教化”基礎(chǔ)之上作出的“明斷”表示心悅誠服的承認(rèn)規(guī)則。
另外,法律還要與民間的自發(fā)秩序保持一致,就像“變色龍”或者木葉蝶的色彩、斑紋甚至形狀與周圍的物質(zhì)環(huán)境相似并隨之變化,借以自我保護(hù)。所謂“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網(wǎng)“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藏于官則為法,施于國則成俗”、則“律意雖遠(yuǎn),人性可推”,則表明國家為了與地方風(fēng)土民情相協(xié)調(diào),并不強求統(tǒng)一,反而特意為差異性留下了回旋余地。因此,法律系統(tǒng)與外部環(huán)境之間的分際是流動的、連續(xù)的。在這樣的條件下,國家秩序比較容易借助社會的內(nèi)在化支持而長治久安,也比較容易進(jìn)行“奇正相生”、“反復(fù)其道”的自我復(fù)制以及多樣化的創(chuàng)造和選擇,甚至像種牛痘那樣通過導(dǎo)入異物來刺激抗體增殖的方式或者小范圍內(nèi)摹擬異物、在調(diào)整適應(yīng)的經(jīng)驗中進(jìn)行的方式來獲得對違法行為、外部干擾等的免疫能力以及從混沌中有序化的自組織能力。
在這樣的擬態(tài)性制度設(shè)計里,國家對于手段的運用很難精密化。恰恰相反,必須采取整體生態(tài)的觀點、辨證法的觀點來把握法律與關(guān)系的互動,將諸如歪打正著、輕重微調(diào)、連鎖反應(yīng)之類的實施效果也都納入令行禁止的視野或者校準(zhǔn)目標(biāo)誤差的范圍之內(nèi)。
有人或許要問,如果法的本質(zhì)真的是結(jié)合了決定論和概率論,有一套“變己適應(yīng)”的工夫,那么粱啟超所提出的“視法律與命令同為一物”命題還能成立嗎?豈不是有些自相矛盾?
在回答這個之前,首先應(yīng)該對觀念的不同層次進(jìn)行區(qū)分。討論法律與命令的關(guān)系,著眼點其實是落在權(quán)力狀態(tài)上。從命令的角度來理解法律,是指國家意志以上下級縱向關(guān)系的方式傳達(dá),具有直接的物理性強制力,在命令者與被命令者之間缺乏公正程序、嚴(yán)格的概念解釋以及獨立的第三者裁判等中間環(huán)節(jié)或者客觀化機制作為媒介。雖然天理和民情也可以對權(quán)力的行使進(jìn)行限制,但限制也好、不限制也好都具有很強的主觀性和偶然性,缺乏制度條件的擔(dān)保。特別是在權(quán)力與民意發(fā)生沖突的場合,是權(quán)力而不是民意占據(jù)絕對的優(yōu)勢,這時法律的命令特征就會表現(xiàn)得很露骨。因此,本文開首援引的粱啟超命題仍然成立,只是不應(yīng)片面理解其內(nèi)涵,從而忽視中國法還存在著強制與合意短路聯(lián)接的那一面。
還需要指出的是這樣一個特殊的悖論:正由于中國的關(guān)系秩序無所不在、極其堅韌,國家才特別有理由維持法律作為命令的強制力,以便對不斷伸張的社會性權(quán)力予以制衡,讓主權(quán)者的意志穿透重重疊疊的中間層滲透到末端。一般而言,當(dāng)民間自發(fā)秩序出現(xiàn)以下兩種情形時,國家性權(quán)力的長驅(qū)直入就會發(fā)生;是現(xiàn)實的交涉和人際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使社會的力量對比失去均衡(例如貧富懸殊過大、地區(qū)差距過大),頻繁出現(xiàn)以強凌弱的局面,國家必須站出來“為民申冤”;二是社會的次級文化過分發(fā)達(dá),達(dá)到“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程度,出現(xiàn)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國家不得不把權(quán)力集中起來以維持“大一統(tǒng)”。“這當(dāng)然不等于說國家的集權(quán)性決斷和強制命令都可以正當(dāng)化。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只要社會的功能關(guān)聯(lián)和涵義關(guān)聯(lián)沒有整體性改觀,變革的各項措施沒有配套,那么權(quán)力就必然會繼續(xù)按照現(xiàn)有的邏輯行事。
另外,關(guān)于法律的概念理解可以有廣義、狹義之分。筆者在前面對中國法秩序的闡述,基本上是把“以禮入法”之后的法律體系作為前提的,而粱啟超在談法律時顯然側(cè)重于“禮法雙行”、“禮先法后”那個射程更加有限的“法”。由于這樣的區(qū)別,在表述上當(dāng)然會出現(xiàn)不同。但是,即使對中國法采取廣義的界定,即使承認(rèn)基于他人意志的強制與基于環(huán)境甚至本人同意的強制之間的分際在中國的“父母官”式的文化氛圍里有些暖昧不清,我們不得不承認(rèn)在這里個人的精神自主性和潛在能力還是備受壓抑的,也非常缺乏民權(quán)的觀念,所以有些敏銳而激進(jìn)的文士(例如戴震、魯迅)會發(fā)出國家“以理殺人”、“禮制吃人”之類的感嘆或抨擊,所以傳統(tǒng)的法律還是不能說它已經(jīng)真正脫離了強制性命令的窠臼。
3. 劇場國家以及共鳴效果的產(chǎn)生
但儒家的理想畢竟是要否定強制和命令,實現(xiàn)禮樂教化的德治。這與公器私化的“家天下”以及絕對君權(quán)的實際政治往往產(chǎn)生尖銳的矛盾(順便指出,這種事實性矛盾的存在也使中國法律秩序的描述很容易給人有邏輯性矛盾的印象)。正因為理想與現(xiàn)實的反差如此之大,才特別需要“以刑去刑”的修辭來自我解嘲,所謂“內(nèi)圣外王”、“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統(tǒng)治模式只好多半停留在禮儀表演的層面。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認(rèn)為傳統(tǒng)的秩序原理造就了一種劇場國家。
“劇場國家”的概念是人類學(xué)家吉爾茲(Clifford Geedz)提出來的。他認(rèn)為如果按照政治與儀禮的關(guān)系進(jìn)行分類,可以發(fā)現(xiàn)三種不同的國家制度安排,即一是把以強制力為背景的立法權(quán)、征稅權(quán)等硬件作為政治的本質(zhì),否定或者無視儀禮等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二是雖然也承認(rèn)儀禮的重要性,但把這種軟件部分看成只是硬件的附屬物;三是把儀禮等看作政治的本質(zhì),例如印度尼西亞的巴里政治文化,表現(xiàn)出劇場國家的特征。日本的法家長尾龍一認(rèn)為強調(diào)“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中國傳統(tǒng)秩序也是如此。鑒于中國“漢承秦制”、“外儒內(nèi)法”以及在搖役和租稅方面具有很強的資源汲取能力的事實,我對把中國完全歸入上述第三類型倒是持保留態(tài)度的。但我也認(rèn)為中國的確很接近劇場國家、只是除了通過祭把典禮進(jìn)行禮樂教化這一幕劇情,還應(yīng)看到“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振木鋒以徇之,使萬民觀”以及公開行刑示眾的森然場面。前者是皇權(quán)威儀和萬眾歸順的表演,后者是皇權(quán)報復(fù)和逆賊痛苦乃至伏罪悔過的表演。在劇場國家之中,人民既是演員又是觀眾,還起著見證或說服的作用。
關(guān)于劇場國家使制裁可視化的側(cè)面,福柯在《監(jiān)獄的誕生》一書中以法國的事實為素材作了非常精彩的。他在指出肉刑以及公開處決作為性典禮儀式的性質(zhì)之后,進(jìn)一步對其涵義和功能作了以下解釋:
“肉刑之所以被深深嵌入司法實踐當(dāng)中,是由于它可以在明示事實同時運用權(quán)力。肉刑可以保征書征與口供、秘密與公開、勘驗程序與動員坦白的結(jié)合。此外,它還可以在罪犯袒露的身體之上再現(xiàn)犯罪事實并使之自受。它甚至還能通過給予同樣恐怖的方式在揭露犯罪之余消滅犯罪。它使被處刑者的身體變成了統(tǒng)治者適用制裁的場所、權(quán)力現(xiàn)形的錨地以及夸示統(tǒng)治者與罪犯之間的力量懸殊的機會”。
“……在肉刑儀式里,民眾扮演主角,只有經(jīng)過他們在現(xiàn)場的親身見證之后,惟幕才會落下”。
“在本應(yīng)只宣示國王權(quán)力并讓人感到顫栗的處刑中,也存在著類似節(jié)日狂歡的非禮的一面,使各自的角色被顛倒,權(quán)力者受到愚弄,罪犯儼然成為英雄”。
后面提到的正邪逆轉(zhuǎn)、騷動造反情節(jié),在(例如《水濟(jì)傳》里描述那樣)也比比皆是。為了避免上述以肉刑為支點的政治互動的風(fēng)險,于是乎出現(xiàn)了對刑罰乃至司法制度的化改革,基本方向是把肉刑儀式變成通過勞動和說服對罪犯實施精神改造的學(xué)校。其結(jié)果,表演性的肉刑淡出視野,更加隱蔽、更加個別化的懲罰方式取而代之。但是在中國,傳統(tǒng)的制裁可視化儀式至今還仍然殘存在某些地方、某些時期的公審或公判大會當(dāng)中。
另外,在解決民事糾紛以及形成村落自治秩序方面,雖然不像肉刑或處決那么富于“戲劇性”,但也存在著說理者、心服者以及被說服者之間的角色分擔(dān)和演出,存在著“刑牲誓神”、“化民成俗”、“耆老一唱眾人和”的祭祀典禮和締約儀式。日本東洋法制史教授寺田浩明用“主唱·唱和”的公式來表述這種齊心合意的社群機制,很能傳神。在這里,與國家祭典和行刑儀式有所不同,民間儀禮是與人與人之間交互行為的自發(fā)規(guī)則聯(lián)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存在著特殊的關(guān)系和共鳴結(jié)構(gòu),中國的實施更容易傾向于采取樹立模范、開創(chuàng)風(fēng)氣這樣一種似乎比較間接的方式,從而劇場國家的屬性也得以維持甚至強化。
4.尋找均衡點的博弈
在強調(diào)觀眾視角和共鳴效果的制度條件下,個人對服從法律往往比較容易提出討價還價的要求,交涉成為秩序原理非常重要的因素。交涉是以互惠為基礎(chǔ)的,伴隨著各種形式的性交換和性交換;而交涉的結(jié)果如何則取決于社會力量對比以及正當(dāng)化處理;因此可以說交涉過程中既存在市場化的契機,也存在政治化的契機。當(dāng)市場化到了連原則和規(guī)范都可以成為交易對象的程度,當(dāng)政治化到了廣大民眾都被卷進(jìn)來的程度,這時某種特殊的當(dāng)事人主義和過分的交換性就會滲透到法制之中,進(jìn)而引起解構(gòu)現(xiàn)象。無怪乎人們可以在中國法律秩序的深層結(jié)構(gòu)中發(fā)現(xiàn)一些“超現(xiàn)代(hypermodem)”或類似“后現(xiàn)代”的因素。
一般認(rèn)為中國社會的傳統(tǒng)是“上下有序”,在上與下之間只存在縱向關(guān)系,這種觀念是片面的。正如津梅爾(Georg Simmel)指出的那樣,上下關(guān)系里面其實也存在著橫向的交互性以及選擇的機會,即使在絕對專制主義統(tǒng)治之下,被統(tǒng)治者還是可以提出諸如對庇護(hù)承諾之類的要求,還是有一定選擇空間的。如果法律作為強制命令試圖抹殺法律限制對象的一切自發(fā)性和反作用,那么法律本身就很難內(nèi)在化、社會化,執(zhí)行的實效也會成。換言之,在關(guān)系秩序發(fā)揮功能的一切地方,個人都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因此法律秩序不可能還原為某個單純的要素,規(guī)范也不可能是單義的,對具體案件的處理更不可能徹底排除偶然的因素。于是,司法以及其他有關(guān)的社會現(xiàn)象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理解為尋找互動關(guān)系均衡點的試錯過程(類似經(jīng)濟(jì)學(xué)蛛網(wǎng)模型所描述的市場動態(tài)),在其中起驅(qū)動作用的主要機制就是津梅爾說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性博弈(Gesellschaftsspiel)”。
在關(guān)系秩序和博弈現(xiàn)象很突出甚至于普遍化的,權(quán)力的行使不得不面對由交涉引起的層出不窮的偶然性、復(fù)雜性以及動態(tài)性,有時懷柔優(yōu)撫,有時凌厲無赦。因此,對同一種秩序,韋伯可以看到“中國式的博愛”、“儒教合理主義”、狄百瑞(Wm.odore de Bary)可以看到“自由的傳統(tǒng)”,而魏特夫(Karl A.Wittfogel)則看到國家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東洋專制主義”。但當(dāng)我們采取多元化的視角來重新審視中國的經(jīng)驗素材時就會發(fā)現(xiàn),“以禮入法”之后的秩序原理已經(jīng)不能再進(jìn)行還原主義的處理,為了避免繼續(xù)犯“盲人摸象”那樣的錯誤,有必要提出新的工具框架乃至范式來進(jìn)行整合性的和說明。本文把中國秩序理解為復(fù)雜系,就是這樣一種嘗試。顯而易見,這樣的秩序原理對西歐法治的模式是一大挑戰(zhàn)——似乎存在一種難以還原為個別主體意志的統(tǒng)治戰(zhàn)略,然而究竟是誰設(shè)計了整體格局卻又說不清楚;權(quán)力本身是彈性可變的,但同時也的確能夠排除社會于對規(guī)范本身的討價還價,即決定過程中存在過度的交換性或市場性,導(dǎo)致超越于當(dāng)事人主觀滿足度之上的客觀性標(biāo)準(zhǔn)無從確立甚至公器私用。如果上述趨勢一旦普及、泛濫,那么任何個人或集團(tuán)都難以挽狂瀾于既倒。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超現(xiàn)代的泛化交換性或市場性是一種強有力的社會結(jié)構(gòu)溶解劑。因此,法制變革的基本任務(wù)就是通過政治體制的現(xiàn)代化來盡早為市場奠定非市場性的基礎(chǔ),以防止出現(xiàn)如下情形:健全的大規(guī)模市場機制所需要的普遍信用也被特殊化的市場性本身反噬殆盡。這種奠定非市場性基礎(chǔ)的作業(yè)還表現(xiàn)為:在通過有決斷力的國家來打破地域性秩序、中間共同體以及人際關(guān)系的割據(jù)、形成統(tǒng)一的國內(nèi)市場的同時,也通過分權(quán)制衡的制度設(shè)計、透明而確定的法律規(guī)則以及公平合理的程序來限制這種強大的主權(quán)國家,并且采取制度化的方式把個人選擇轉(zhuǎn)寫到公共選擇的框架里,再用公共選擇的框架反過來限制個人選擇。對于中國而言,這個基本任務(wù)在相當(dāng)程度上意味著要使已經(jīng)生效的法律規(guī)范和判決不再廣泛容許討價還價的事后交涉,使權(quán)利體系與互惠關(guān)系有所區(qū)隔。用更加簡潔的公式來表述,就是從“以禮入法”的狀態(tài)回到真正意義上的“禮法雙行”——既保留更大的選擇空間,又避免本質(zhì)互異的規(guī)范和程序糾纏不清。
以上說的都是中國法制現(xiàn)代化的必要性。我們還應(yīng)進(jìn)一步探討現(xiàn)代法治的現(xiàn)實可行的途徑。對傳統(tǒng)秩序原理進(jìn)行重新審視的結(jié)果表明,要原封不動地推行“法律至上”、“審判神圣”的西歐式法治主義理念的確是極其困難的,但是,認(rèn)真而嚴(yán)格的依法行政和守法奉公卻并非奢望。在“以禮入法”運動之后,中國法律秩序中產(chǎn)生了強制與合意的短路聯(lián)接,結(jié)果導(dǎo)致了強制不行、合意不純的尷尬局面。因此,所謂回到“禮法雙行”就是首先要實現(xiàn)“合理的合意”與“正當(dāng)?shù)膹娭啤钡姆蛛x,使合意成為真正的個人意思自治,使強制能真正貫徹落實。眾所周知,在今天中國的民間糾紛解決以及民事訴訟制度下,“合理的合意”已經(jīng)進(jìn)一步演化成為“合法的合意”,而在更大的范圍內(nèi),“正當(dāng)?shù)膹娭啤币踩找姹焕斫鉃楹虾醭绦蛘x的強制,顯然,社會的現(xiàn)代法治化趨勢正在逐步成為主流。
有人曾經(jīng)對特別強調(diào)法律程序的意義表示懷疑,也有人曾經(jīng)對中國社會居然能夠迅速接受新程序主義觀念表示吃驚。其實只要對中國傳統(tǒng)的秩序原理進(jìn)行一番觀察和思考就可以認(rèn)識到,在那樣一種圍繞情、理、法、權(quán)、術(shù)、勢的交涉動態(tài)和偶然結(jié)局中,推行法治必須從交涉的有序化、偶然的非隨機化開始,否則一切都無從談起。可以說,在傳統(tǒng)的互動過程與現(xiàn)代的公正程序之間其實是一紙之隔兩重天,現(xiàn)在我們應(yīng)該做而且能夠做到的不外乎捅破天窗紙來說亮話、減少黑箱操作而已。通俗地闡述程序的意義,就是在抓牌和打牌之前先把規(guī)矩說清楚、定下來,只有這樣做無論結(jié)果是贏是輸所有玩家都能認(rèn)可和接受。這層道理顯然是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都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社會價值激烈沖突和轉(zhuǎn)換的過程中,更容易達(dá)成共識或妥協(xié)的究竟是“公有理、婆無理”這樣的實體性判斷還是“公說半晌,婆也說半晌”的程序性安排,究竟是證明的客觀性判斷還是舉證責(zé)任的分配方式,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只有在程序得到解決之后,實體問題的解決可能性才會顯著增大。
特別是在規(guī)范多元化或者價值多元化的狀況下,如果非要在涉及信仰或真理等實體上爭出個高下是非來,那種場面決不會比因端午節(jié)賽龍舟而發(fā)生的械斗更溫和。而法治的程序論就是要以承認(rèn)多元性為前提,劃出一塊理性討論和決定整體利益的公共空間,而把難以進(jìn)行理性討論的價值問題都?xì)w類于私人領(lǐng)域,不作出武斷的裁判。既然認(rèn)識到文化本來就具有多元化契機,而當(dāng)前的社會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正在進(jìn)一步加劇多元化的進(jìn)程,那就完全沒有理由拒絕承認(rèn)程序在多元調(diào)整方面的決定性意義。試問:在多元化的背景下,如果離開了程序正義,還可以到哪里去尋求公認(rèn)的正義?!這么說決不是在提倡一種還原主義。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主張各種并存的價值相互之間不能還原,正是由于正視復(fù)數(shù)主體的判斷因人而異且變化不居,才特別需要程序來作為建構(gòu)法治秩序的基石或者錨地。僅就這一點而言,程序論既有現(xiàn)代性,也有后現(xiàn)代性。
在社會的多元構(gòu)成比較明顯的背景下,中國傳統(tǒng)的設(shè)計是通過“圜道”這樣的通道性制度來媒介不同部分、不同因素。在當(dāng)代,形成了更先進(jìn)的“群眾路線”、“試行”、“判后回訪”等反饋機制。我認(rèn)為,這種上通下達(dá)的各種途徑和方式其實都可以按照程序正義的原理進(jìn)行改編重組,在這么做了之后,議論和審議的合理性就會大大增強,法律決定過程的民主化水準(zhǔn)就會大大提高。特別是如今信息技術(shù)和互聯(lián)網(wǎng)日益普及,在虛擬空間的公告欄(BBS)、電子論壇、政府上網(wǎng)工程、電郵線路、電腦資料庫以及“案件審理流程管理”的追蹤系統(tǒng)里,可以發(fā)現(xiàn)“圜道”的最新版本以及反思性調(diào)整的無限可能性。這種狀況一方面為民主的法治秩序提供了前提條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合理主義層面法制現(xiàn)代化的效率。特別是通過司法行政電腦化(virtualising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中國有可能跨越現(xiàn)代司法制度基礎(chǔ)建設(shè)的某些階段,減少事務(wù)性中間環(huán)節(jié),以更迅速、更廉價的方式把信息傳遞到更廣的范圍。審判空間的可視化既有利于下級法院的合議庭或獨任法官抵制來自上級法院以及外部社會的干涉,也有利于司法行政當(dāng)局督促辦案人員提高審判的效率,還有利于加強社會監(jiān)督或輿論監(jiān)督以達(dá)到“審者也受審”的民主化司法目標(biāo)。當(dāng)然,在此基礎(chǔ)上,像福柯借助“全視性監(jiān)督裝置”的隱喻所提示的那種現(xiàn)代性國家權(quán)力的基本屬性也有可能完全實現(xiàn),甚至不妨設(shè)想某種有中國特色的現(xiàn)代法治秩序正是在既分散、又集中、互相監(jiān)督、互相制約的電子、技術(shù)編碼以及合理化程序中得以形成和。
如果說中國傳統(tǒng)秩序的特色是在“情理兼到”的原則之下最大限度容許在法律過程中進(jìn)行交涉、交換、說服、屈服的相互作用,現(xiàn)代法治建構(gòu)的上述思路并沒有完全抹殺這一特色。只不過要對原有的設(shè)定進(jìn)行如下修改:把非正式的討價還價變成合乎公正程序的辯論協(xié)商,把用儒家倫理語言展開的議論變成用法言法語展開的嚴(yán)密論證,把作為善意和自警裝置的“圜道”變成以權(quán)利和外部監(jiān)督為基礎(chǔ)的公共論壇,把主體之間純屬偶然的訴訟博弈變成在法律職業(yè)協(xié)助下操作的技術(shù)性博弈,把對司法機關(guān)采取“權(quán)限不清、責(zé)任嚴(yán)究”的管理方式變成“權(quán)限分明、責(zé)任自負(fù)”的管理方式,如此等等。在這樣的變革當(dāng)中,雖然立法者很重要,但解釋者的角色作用也很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因為法律秩序?qū)﹃P(guān)系秩序的滲透不可能表現(xiàn)為直接的令行禁止,需要通過解釋者的記敘、闡述、說理以及宣傳來爭取更廣泛的理解并形成共鳴效果。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與培養(yǎng)合理的解釋者有關(guān)的一切制度化作業(yè),特別是包括審判方式的合理化、全國法律家資格統(tǒng)一制度的設(shè)立等在內(nèi)的司法改革的將是非常深遠(yuǎn)的。
總而言之,現(xiàn)代的民主法治在中國不僅是必要的,而且還是現(xiàn)實可行的。鑒于傳統(tǒng)秩序原理的特征,法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在交涉、議論等相互作用的固有動態(tài)中,通過程序和論證來形成合理的定向化公共選擇機制。在今后推動改革深入的過程中,有必要逐步把社會的關(guān)注點從立法者轉(zhuǎn)到解釋者。我們將迎來一個依照程序性規(guī)則重新解釋中國社會、重新解釋現(xiàn)代法治的!
.jpg)

與環(huán)境科學(xué).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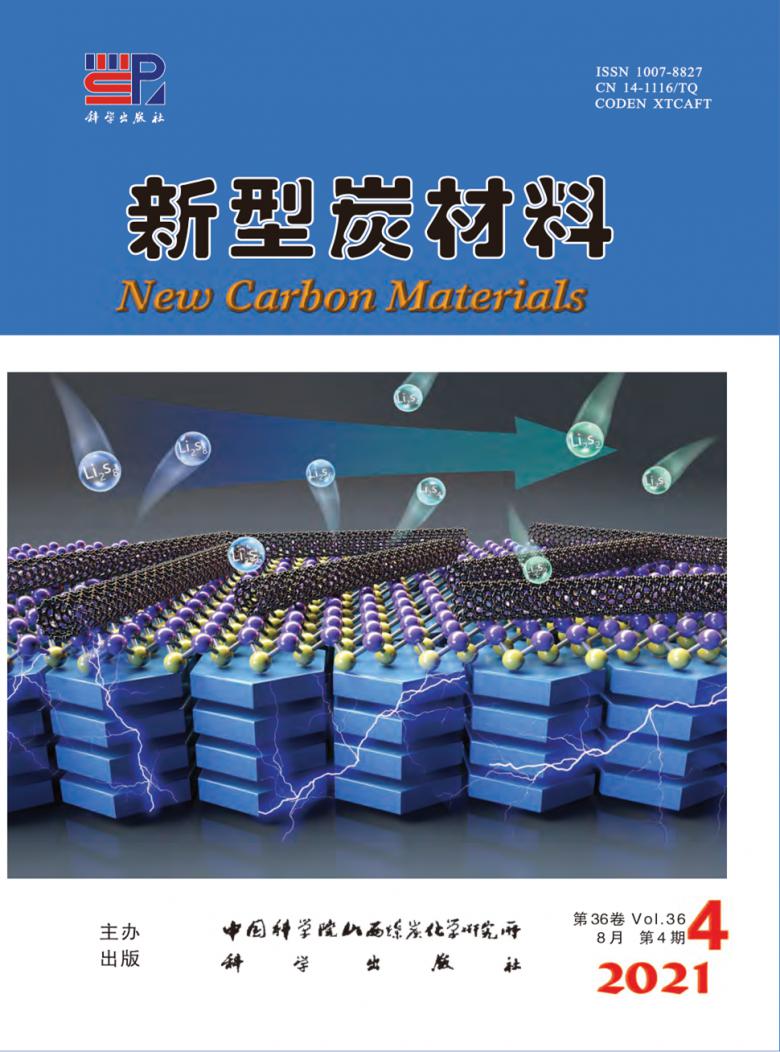
學(xué)報.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