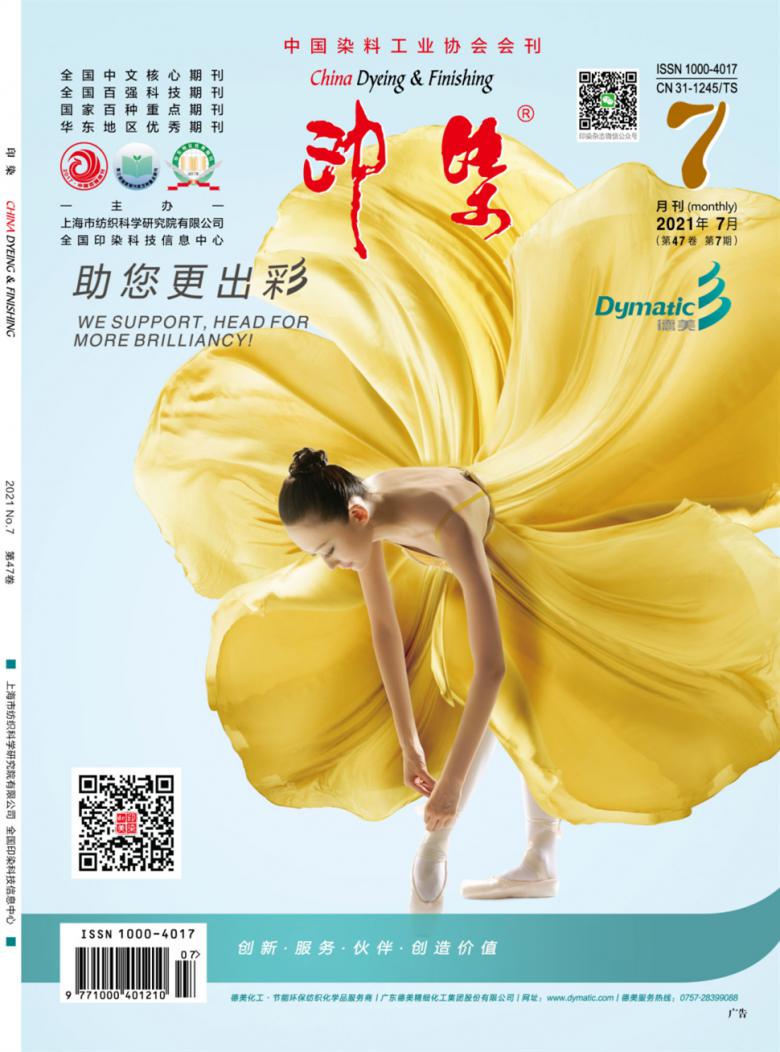朱熹的農業科技思想
樂愛國
在朱熹的思想體系中,理學占據主導地位,而“理一分殊”是其基礎;換言之,他的“理”,既是作為萬事萬物最高抽象的“理一”,又是作為具體事物特殊規律的“分殊”。尤其是,他較多地論及“分殊”,因而在認識論上較為強調“格物”,包括格自然之物。正因為如此,他的思想體系中包含有不少自然科學的東西,也包括農業科技思想。朱熹的農業科技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任地方官期間所頒發的若干《勸農文》及有關的榜文之中,其中宋淳熙六年(1179年)十二月在南康軍(今江西星子)頒發的《勸農文》(見《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九,四部叢刊初編)和宋紹熙三年(1192年)二月在漳州(今福建漳州)頒發的《勸農文》(見《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一百) 較為重要。
朱熹的《勸農文》往往是在農事的關鍵時候為勸導農民不誤農時盡力務農而頒發的官方文告;其中既有農民必須遵照執行的條令,也包含了應當如何操作的具體方法,因而也多少反映出一定的農業科技思想。分析朱熹的《勸農文》可以看出,他的農業科技思想基本上繼承了中國古代農業科技的精耕細作的優良傳統,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深耕細耙,改良土壤。朱熹非常重視土壤的深厚對農作物生長的重要性。他分析南康軍土壤貧瘠的原因時說:“本軍田地蹺埆,土肉厚處不及三、五寸,設使人戶及時用力以治農事,猶恐所收不及他處。”[1]他還認為,正是由于“土脈疏淺”,因此土壤的保水性能差,“雨澤稍愆,便見荒歉”。所以,他主張要深耕。朱熹還認為,土壤既要深耕還要反復耙犁,使生土變為熟土。他說:“大凡秋間收成之后,須趁冬月以前,便將戶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凍令酥脆,至正月以后更多著遍數,節次犁杷,然后布種,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種禾易長,盛水難干。”[2]他認為,經過秋天的深耕和初春的犁耙,土壤深熟肥厚,有利于農作物的生長。
在當時,耕牛是犁耙的重要工具,因此,朱熹提出要保護耕牛,他說:“耘犁之功,全藉牛力。切須照管,及時喂飼,不得輒行宰殺,致妨農務。”[3]他還具體規定了宰殺耕牛的處罰辦法。
第二,適時播種,不務農時。朱熹非常重視農時。在他知南康軍和知漳州期間,每逢春播時節,他都要事先頒發《勸農文》,要求農民及時播種。淳熙七年(1180年)二月,他在南康軍先是頒發《勸農文》,后又頒《申諭耕桑榜》(見《晦菴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九),可見他對農時之重視。他于二月頒發的一份《勸農文》中寫道:“今來春氣已中土膏脈起,正是耕農時節,不可遲緩。仰諸父老,教訓子弟,遞相勸率,浸種下秧,深耕淺種。趨時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無致因循,自取饑餓。”[4]他認為,是否及時播種直接關系到收成的好壞。至于秧苗長成時,也必須及時栽插,他說:“秧苗既長,便須及時趁早栽插,莫令遲緩過卻時節。”[5]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獲得好收成。
第三,多施基肥,適時追肥。南康軍土地瘦瘠,且農民施肥又不盡力。針對這種情況,朱熹提出要多用糞肥。為此,他還提出了用糞肥伴和種子的施肥方法,他說:“耕田之后,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段,多用糞壤拌和種子,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秋冬無事之時,預先刬取土面草根,曬曝燒灰,旋用大糞拌和入種子在內,然后撒種。”[6]此外,朱熹還十分重視農作物生長時的追肥,他還曾專門頒發過《勸農民耘草糞田榜》(見《晦菴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九),督促農民及時除草追肥。
第四,加強田間管理。田間管理是農業生產的重要一環,而除草是其中的一項。對此,他說:“禾苗既長,稈草亦生,須是放干田水,子(仔)細辨認,逐一拔出,踏在泥里,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屬,亦須節次芟削取令凈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將來谷實必須繁盛堅好。”[7]主張除草以肥田。在論及桑樹的種植時,他說:“其桑木每遇秋冬,即將旁生拳曲小枝盡行斬削,務令大枝氣脈全盛自然,生葉厚大,喂蠶有力。”[8]主張秋冬時節要給桑樹剪枝。
第五,注重興修水利。農作物的生長離不開水,南方的水稻更是如此。因此,朱熹極力主張興修水利。他在南康軍的《勸農文》中說:“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如有怠惰,不趁時工作之人,仰眾列狀申縣,乞行懲戒;如有工力浩瀚去處,私下難以糾集,即仰經縣自陳官為修筑。”[9]他在漳州的《勸農文》中說:“陂塘水利,農事之本。今仰同用水人,葉力興修,取令多蓄水泉,準備將來灌溉,如是干眾即時聞官,糾率人功借貸錢本,日下修筑,不管誤事。”[10]此外,他還專門就修筑陂塘多次頒發榜文(見《晦菴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九)。
顯然,朱熹重視農業科技并有所研究,形成了一定的農業科技思想。盡管他的研究主要是直接針對各所在地的具體情況,尤其是他的農業科技思想只是反映在《勸農文》之類的官方榜文之中,因而顯得零亂,但是,他畢竟作了研究,而且對農業生產的各主要環節均有論述。
朱熹一生致力于理學;在他到南康軍任官之前,其理學思想體系已經形成。此前,他已編寫了大量著作,其中主要有:《程氏遺書》(1168年)、《資治通鑒綱目》(1172年)、《西銘解義》(1172年)、《太極圖說解》(1173年)、《通書解》(1173年)、《程氏外書》(1173年)、《伊洛淵源錄》(1173年)、《近思錄》(與呂祖謙合編于1175年)、《論孟集注》(1177年)、《論孟或問》(1177年)、《詩集傳》(1177年)、《周易本義》(1177年)等;著名的鵝湖之會也已成過去。至他在漳州頒發《勸農文》之前,他已為其《大學章句》和《中庸章句》二書作了序,二書也已修改定稿;此外,他還刊行了《易》、《詩》、《書》、《春秋》“四經”和《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換言之,他那兩篇重要的《勸農文》以及其中的農業科技思想與他的理學思想的完成是同步的。當然,朱熹始終是把理學思想體系的建構放在首位。為此,他多次提出辭官,希望專心于理學研究;其農業科技思想至多只能處于次要的位置。但在他那里,理學與農業科技思想并行不悖,農業科技并沒有受到輕視,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朱熹的理學較多地論及“分殊”,他甚至把農業科技也納入到他的理學體系之中。他說:“雖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豈不可以格。如麻、麥、稻、粱,甚時種,甚時收,地之肥,地之蹺,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11]他認為,農作物的生長及種植有其自然規律,這就是理;所以要“格”,要研究農業科學技術,盡管他認為,這只是“小道”,“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12]在朱熹看來,在農業科學技術之上,還有“大道”,也就是說,農業科學技術只是“理一”之下一“分殊”,但是他又說:“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卻有道理在。”[13] 可見,農業科學技術也包含在他的理學之中,也是需要研究的。此外,他還說:“若夫農之為務,用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14]這里的“自然之理”雖不是指自然科學規律,而是指從事農業生產的客觀規律,但也是“理”。
朱熹之所以研究農業科學技術,除了有其理學的基礎外,還由于他的為官實踐。宋淳熙五年(1178年),由于朝廷重臣史浩的推薦,朱熹被派知南康軍,次年三月到任。南康地方地瘠民貧,當時又發生旱災。朱熹一方面通過各種方式積極賑災救荒,另一方面深入田間地頭研究農事,分析情況。他說:“當職久處田間,習知檣事,茲忝郡寄職在勸農,竊見本軍已是地瘠稅重,民間又不勤力耕種,耘耨鹵莽滅裂,……所以土脈疏淺,草盛苗稀,雨澤稍愆,便見荒歉,皆緣長吏勸課不勤,使之至此。”[15]所以他要用科學的方法有效地組織農業生產。朱熹在知南康軍以及后來為地方官期間,深知農業之重要。他說:“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16]又說:“契勘生民之本,足食為先,是以國家務農重谷,使凡州縣守倅皆以勸農為職。……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17]農業是治國生民之本,勸農是為官之職,這也就是他為什么要積極研究農業科技之緣故。
朱熹研究農業科學技術,不僅說明他本人并不鄙視(而是重視)農業科學技術,更表明他的理學具有很廣泛的開放性、包容性。他的理學雖然強調“理一”,但并不排斥甚至較多地言及“分殊”,把包括農業科技在內的所有科學技術都融入他的理學結構之中。朱熹所處的宋代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高峰時期,農業科技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而且他自己在科學技術的諸多領域也有所研究,因此,他在建構他的理學體系時不是排斥而是以吸收的方式接納各種思想,其中科學技術思想是重要的一個方面。他說:“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個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18]所以,研究科學技術也是“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的重要途徑。正是在這樣的結構中,朱熹研究農業科技,形成了農業科技思想。
注釋:
[1][2][5][6][7][8][9][14][15][16]《勸農文》,《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九。
[3][4][10][17]《勸農文》,《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一百。
[11]〔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第十八,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20頁。
[12][13]《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九,第1200頁。
[18]《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二,第14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