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zhuǎn)軌前中東歐與中國經(jīng)濟(jì)體制的“可放棄性”問題
佚名
「內(nèi)容提要」對(duì)經(jīng)濟(jì)轉(zhuǎn)軌后出現(xiàn)的“中國奇跡”與“東歐困境”的解釋,已成為國際上轉(zhuǎn)軌經(jīng)濟(jì)學(xué)界最大的論題之一,論者在概念上似乎都認(rèn)為中國與中東歐在改革前都是“計(jì)劃經(jīng)濟(jì)”,兩者的差異只在于對(duì)“計(jì)劃經(jīng)濟(jì)”采取了不同的改造方式。其實(shí),中國與中東歐在改革前的經(jīng)濟(jì)體制差異更大,中國具有更多的“命令經(jīng)濟(jì)”的成分,而中東歐則較多的“理性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成分,后者的績(jī)效顯然優(yōu)于前者。但在邁向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道路上,后者注定要付出更大的代價(jià)。
「英文標(biāo)題」“Abandonability”of the Central &East European and Chinese EconomicSt ructures Before the Transformation
「英文摘要」Interpretations of the“Chinese wonder”and “East European predicament ”after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themes of theinternational transformational economic community.Conceptually ,sc holars seemto believe that pre-reform China and Central East Europe lived under planned economy,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being the diff erent modes of reform over plannedeconomy.As a matter of fact,great dif ferences existed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East Europe in their economic s tructures before the reforms.The Chinese economyhad more elements of“o rder economy”,while the Central &East European economyhad more elemen ts of “rational planned economy”with obviously better achievementsthan the former.However,the latter had to pay a greater cost on the way to market economy.
「關(guān)鍵詞」中國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理性計(jì)劃經(jīng)濟(jì)/“命令經(jīng)濟(jì)”
reform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structure/rational planned economy/“order economy”
“走出……”之別,還是“走向……”之別?
國際上轉(zhuǎn)軌經(jīng)濟(jì)學(xué)界對(duì)所謂“中國奇跡”與“東歐困境”即所謂“中國之謎”的解釋已成為最大的論題之一,而且似乎形成了“漸進(jìn)—激進(jìn)”的討論模式。古典自由主義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往往認(rèn)為東歐的“激進(jìn)轉(zhuǎn)軌”雖付出很大代價(jià),但一舉解決了實(shí)質(zhì)性問題,將來會(huì)顯示出大效果;中國的“漸進(jìn)轉(zhuǎn)軌”雖然獲得了持續(xù)的經(jīng)濟(jì)增長,但實(shí)質(zhì)性問題繞不過去,將來會(huì)遇到大困難。相反,凱恩斯主義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則認(rèn)為東歐轉(zhuǎn)軌恰恰陷入了“市場(chǎng)原教旨主義”的“激進(jìn)”誤區(qū),而中國的漸進(jìn)轉(zhuǎn)軌具有更多的凱恩斯式或福利國家式的政府干預(yù)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當(dāng)然,將來雙方的對(duì)比也不會(huì)逆轉(zhuǎn)。顯然,這種爭(zhēng)論的背后包含某種共同前提,即中國“漸進(jìn)”——更多凱恩斯或福利國家或社會(huì)主義——因而經(jīng)濟(jì)(根本性的或暫時(shí)的)增長,東歐“激進(jìn)”——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因而經(jīng)濟(jì)(根本性的蛟菔鋇模┧ネ恕?br>但是筆者認(rèn)為,這個(gè)前提是大可質(zhì)疑的。首先就轉(zhuǎn)軌目標(biāo)模式而言,中國明確地自認(rèn)為是“摸著石頭過河”,而多數(shù)東歐國家倒是明確地以加入歐盟為目標(biāo),歐盟多數(shù)國家是當(dāng)今世界上福利國家的典型,東歐各國入盟談判中的“福利門檻”、“勞工保護(hù)門檻”往往比“市場(chǎng)化門檻”還高。而現(xiàn)實(shí)就更不必說:恐怕沒有人能證明如今的中國比東歐更像“福利國家”。“劇變”后的東歐——前經(jīng)互會(huì)國家轉(zhuǎn)軌戰(zhàn)略各有特點(diǎn),其中像白俄羅斯與愛沙尼亞這兩個(gè)空間與歷史都相近的“前蘇聯(lián)”國家,其轉(zhuǎn)軌經(jīng)濟(jì)政策相差懸殊之大實(shí)難以用“東歐轉(zhuǎn)軌”這個(gè)概念來包容:盧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羅斯基本上拒絕市場(chǎng)化,而愛沙尼亞以“面向外資全賣光”方式實(shí)行的私有化堪稱東歐最激進(jìn)之一。如果僅從經(jīng)濟(jì)上講,所謂中國與“東歐”轉(zhuǎn)軌政策的差異恐怕遠(yuǎn)不及東歐內(nèi)部之差異來得大。
國際上的轉(zhuǎn)軌經(jīng)濟(jì)學(xué)爭(zhēng)論基本上是西方經(jīng)濟(jì)學(xué)兩大傳統(tǒng)即古典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爭(zhēng)論在轉(zhuǎn)軌問題上的延伸。在中東歐轉(zhuǎn)軌10年間它們分別形成了所謂“華盛頓共識(shí)”與“后華盛頓共識(shí)”,并各自對(duì)中國與中東歐轉(zhuǎn)軌戰(zhàn)略的異同作出了解釋。但他們?cè)诟拍钌纤坪醵颊J(rèn)為中國與中東歐在改革前都是與“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相對(duì)立的“計(jì)劃經(jīng)濟(jì)”,兩者的差異只在于對(duì)這同一個(gè)“計(jì)劃經(jīng)濟(jì)”采取了不同的改造方式。人們很少反過來想:也許中國與中東歐的“改造方式”差異不是那么大(就經(jīng)濟(jì)改革的方向而言),而改造前的經(jīng)濟(jì)體制倒是差異更大些,由此可以更有效地解釋后來的改造績(jī)效?換句話說,中國與中東歐如今的轉(zhuǎn)軌績(jī)效之別也許更多地屬于“走出……”之別,而不是“走向……”之別?
以往的轉(zhuǎn)軌經(jīng)濟(jì)討論中已談到過“走出……”之別,尤其出自古典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華盛頓共識(shí)”派學(xué)者如薩克斯等,都側(cè)重于以“初始條件”來解釋“東歐困境與中國奇跡”。但他們通常強(qiáng)調(diào)的是發(fā)展水平不同(中國更不發(fā)達(dá)),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不同(中國是農(nóng)業(yè)國),乃至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慣性不同(中國只搞了30年而蘇聯(lián)搞了70年)。這些不同當(dāng)然有影響,但僅此而已說服力是不大的。因?yàn)檫@樣說來,最能擺脫困境創(chuàng)造奇跡的應(yīng)當(dāng)是更窮、更農(nóng)業(yè)化、“計(jì)劃”歷史也更短的非洲國家了。
我現(xiàn)在強(qiáng)調(diào)的是,在“走出……”方面更重要的是經(jīng)濟(jì)機(jī)制的不同。在這方面,古典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之外的一些被稱為“新左派”的學(xué)者倒是談到過。崔之元先生大講“鞍鋼憲法”就是一例。他把這個(gè)“憲法”說成是“后福特主義”的種種褒評(píng)我是完全不同意的,并就此提出過批評(píng)。但“鞍鋼憲法”之與“馬鋼憲法”(當(dāng)年中國人對(duì)以蘇聯(lián)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聯(lián)合企業(yè)經(jīng)營管理模式為代表的工業(yè)體制的稱呼)大異其趣,的確不可忽視。作為轉(zhuǎn)軌過程的起點(diǎn),這種差異對(duì)后來進(jìn)程所起的路徑依賴作用(盡管這種作用恰恰與崔之元講的相反)十分重要。而西方左右兩派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把轉(zhuǎn)軌前體制大而化之都視為“計(jì)劃經(jīng)濟(jì)”、只重視走出這種體制后在民主福利國家與公民自由交易兩者間進(jìn)行選擇與搭配(中國與中東歐恰恰不是這種區(qū)別),這就很難真正理解所謂“東歐困境”與“中國奇跡”的產(chǎn)生機(jī)制。
事實(shí)上,無論古典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shí)”強(qiáng)調(diào)的市場(chǎng)機(jī)制優(yōu)越性,還是凱恩斯—羅斯福主義的“后華盛頓共識(shí)”強(qiáng)調(diào)的國家調(diào)控必要性,都不足以解釋這種“奇跡”。在筆者看來,這個(gè)“奇跡”的形成機(jī)制可分為兩個(gè)階段:20世紀(jì)80年代,主要是由于中國式的命令經(jīng)濟(jì)與中東歐理性計(jì)劃經(jīng)濟(jì)相比的極端無效率導(dǎo)致它可以“無代價(jià)放棄”和“放棄即受益”(無論是改行理性計(jì)劃,還是改行市場(chǎng)機(jī)制都能得到純?cè)鲆妫约鞍ń^大多數(shù)國民(農(nóng)民)處在有束縛而無保障的“負(fù)帕累托過程”(不同于中東歐的束縛—保障協(xié)調(diào)型體制)而導(dǎo)致的條件:“走出負(fù)帕累托過程即帕累托過程(即人人受益過程)”。相比之下,絕大多數(shù)中東歐國家只能從一種非帕累托過程走向另一種非帕累托過程。
命令經(jīng)濟(jì)與計(jì)劃經(jīng)濟(jì):非現(xiàn)代性與異化的現(xiàn)代性
過去人們認(rèn)為,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jīng)濟(jì)”,而資本主義以廣泛的交換打破了自給自足,于是有了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同時(shí)啟蒙運(yùn)動(dòng)造成的“理性的自負(fù)”和工業(yè)文明的科學(xué)主義又使人追求人為設(shè)計(jì)的經(jīng)濟(jì)資源最優(yōu)化配置,于是有了計(jì)劃經(jīng)濟(jì)。但歷史并非如此簡(jiǎn)單。馬克思當(dāng)年就談到過“人的依附性”時(shí)代以“統(tǒng)治—服從關(guān)系為基礎(chǔ)的”、作為“共同體之現(xiàn)成基礎(chǔ)”的“強(qiáng)制勞動(dòng)”可能包含的協(xié)作。[1](p.197,496,517)諾貝爾經(jīng)濟(jì)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J ·希克斯更認(rèn)為真正無交往無分工的“自給自足”并不存在,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中可能有相當(dāng)規(guī)模的分工與要素流動(dòng),只是它并非因市場(chǎng)而起,而是“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層指導(dǎo)的專門化”。[2](p.23)他把這稱之為“指令經(jīng)濟(jì)”。而經(jīng)濟(jì)現(xiàn)代化在他看來,就是傳統(tǒng)“指令經(jīng)濟(jì)”向現(xiàn)代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演變。這種“指令經(jīng)濟(jì)”與工業(yè)文明無關(guān),它與其說是“理性的自負(fù)”不如說是“權(quán)力的自負(fù)”,與其說是“科學(xué)主義”不如說是浪漫主義。正是這種“指令經(jīng)濟(jì)”或“排除交換的權(quán)力—分配經(jīng)濟(jì)”,而不是“自然經(jīng)濟(jì)”,構(gòu)成所謂“農(nóng)民社會(huì)”的基本特征(當(dāng)然這并不意味著它有利于種田人或?yàn)榉N田人所喜)。
而所謂計(jì)劃經(jīng)濟(jì),無論它的倡導(dǎo)者還是反對(duì)者都公認(rèn)它是一種近代現(xiàn)象或工業(yè)文明時(shí)代的現(xiàn)象。倡導(dǎo)者如馬克思,是把它當(dāng)作“資本主義容納不下的高度生產(chǎn)力”的產(chǎn)物,反對(duì)者如哈耶克,也再三指出它淵源于啟蒙運(yùn)動(dòng)導(dǎo)致的“理性的僭妄”與科學(xué)主義擴(kuò)張,而強(qiáng)調(diào)它與中世紀(jì)強(qiáng)制制度的區(qū)別。眾所周知,盡管純粹作為經(jīng)濟(jì)行為的國家強(qiáng)制與自由放任可以分別追溯到重商主義與重農(nóng)主義、德國歷史學(xué)派與亞當(dāng)·斯密學(xué)派,但馬克思的經(jīng)濟(jì)思想與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中最主張自由市場(chǎng)的重農(nóng)學(xué)派到亞當(dāng)·斯密一系關(guān)系密切,與強(qiáng)調(diào)國家統(tǒng)制的重商學(xué)派到德國歷史學(xué)派一系關(guān)系疏遠(yuǎn)而敵對(duì)。這當(dāng)然不意味著馬克思“親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只意味著作為計(jì)劃經(jīng)濟(jì)倡導(dǎo)者的他,與斯密式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論者同樣是敵視命令經(jīng)濟(jì)的。總之,贊成者與反對(duì)者都肯定計(jì)劃經(jīng)濟(jì)與傳統(tǒng)命令經(jīng)濟(jì)是不同的——盡管這兩者都與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對(duì)立,因而也有許多共性。走向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過程,既可以意味著走出計(jì)劃經(jīng)濟(jì),也可以意味著走出命令經(jīng)濟(jì),而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因素并存的強(qiáng)制體系中這兩者的成分往往并存,但畢竟也還有哪種成分為主的問題。
被希克斯稱作“命令經(jīng)濟(jì)”的類型,是農(nóng)業(yè)文明(但不一定是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產(chǎn)物,這種經(jīng)濟(jì)可以不需要“工業(yè)文明”,不需要“理性主義”、“科學(xué)主義”。它不考慮投入產(chǎn)出系數(shù)、沒有數(shù)理邏輯基礎(chǔ)上的“計(jì)劃均衡”概念、不考慮經(jīng)濟(jì)過程的最優(yōu)化原則,而僅以人們對(duì)共同體的依附性為基礎(chǔ),以掌權(quán)者的長官意志、浪漫心理、個(gè)人需要或某種社會(huì)激情來支配經(jīng)濟(jì)。
一般地說,如果把市場(chǎng)機(jī)制下通過供求與價(jià)格信息反饋調(diào)整經(jīng)濟(jì)決策的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看作“即時(shí)糾錯(cuò)”的經(jīng)濟(jì),那么上述這種指令制度相對(duì)于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來說,就是一種“無法糾錯(cuò)”的經(jīng)濟(jì)。除非因不可抗拒的自然規(guī)律使舊的“命令”者退出,新一代的“命令”者有可能與民更始,它就很少有其他糾錯(cuò)機(jī)制。
另一種體制則是建立在工業(yè)文明、理性主義、科學(xué)主義基礎(chǔ)上的現(xiàn)代計(jì)劃經(jīng)濟(jì)。據(jù)認(rèn)為,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最大弊病在于市場(chǎng)“無政府狀態(tài)”,使其糾錯(cuò)過程滯后并造成效率損失。在這種狀態(tài)下,生產(chǎn)是盲目的,產(chǎn)品要上市后才能發(fā)現(xiàn)決策偏差(過剩或不足),然后根據(jù)市場(chǎng)信息進(jìn)行調(diào)整,在一次次調(diào)整、一次次試錯(cuò)中達(dá)到市場(chǎng)均衡,實(shí)現(xiàn)資源配置的最優(yōu)化。自從理性主義興起后,相信數(shù)理邏輯的人們認(rèn)為,完全可以把一切事先計(jì)劃好,把均衡關(guān)系預(yù)先計(jì)算出來,以免除接觸市場(chǎng)以后才發(fā)現(xiàn)的種種錯(cuò)誤,即把“市場(chǎng)試錯(cuò)”要解決的問題以模擬經(jīng)濟(jì)參數(shù)的計(jì)算而“預(yù)先”得知,也就是說,一開始就根據(jù)資源配置最優(yōu)化原則設(shè)定。
這種經(jīng)濟(jì)也可以叫“預(yù)先糾錯(cuò)”的經(jīng)濟(jì)。它依賴于通過精密的科學(xué)計(jì)算“預(yù)先”建立的“計(jì)劃均衡”。如果僅僅就實(shí)現(xiàn)均衡(即實(shí)現(xiàn)最優(yōu)配置)而言,它在理論上完全可以勝于或至少不亞于通過“即時(shí)糾錯(cuò)”建立的“市場(chǎng)均衡”。事實(shí)上純從數(shù)理邏輯角度看,市場(chǎng)均衡與計(jì)劃均衡都是合乎“經(jīng)濟(jì)理性化”的。因此作為現(xiàn)代數(shù)理經(jīng)濟(jì)學(xué)奠基者的帕累托的如下態(tài)度便毫不足怪:他一方面反對(duì)貿(mào)易保護(hù)、支持極端的市場(chǎng)自由,另一方面似乎同樣肯定“計(jì)劃最優(yōu)化”。這個(gè)以效率理論大師著稱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認(rèn)為:如果計(jì)劃足夠“科學(xué)”,那么“社會(huì)主義國家比基于私有財(cái)產(chǎn)經(jīng)濟(jì)的國家能更好地把經(jīng)濟(jì)引向均衡”。即使不說“更好”,至少也可以設(shè)想“計(jì)劃經(jīng)濟(jì)和市場(chǎng)經(jīng)常產(chǎn)生相同的結(jié)果,因而社會(huì)主義制度和完全自由的制度可能同樣的有效率”[3](p.863)。數(shù)理經(jīng)濟(jì)學(xué)“在理論上可以達(dá)到恰好與理想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的均衡力量所致的相同的經(jīng)濟(jì)‘計(jì)劃’”。[4]在帕累托看來惟一的問題似乎在于:人們的計(jì)算技術(shù)是否已經(jīng)能夠產(chǎn)生這樣的“計(jì)劃”:“如果我們考慮四千萬人口和幾千種商品產(chǎn)生的巨額數(shù)量的方程,這將不是數(shù)學(xué)幫助了經(jīng)濟(jì)學(xué),而是經(jīng)濟(jì)學(xué)幫助了數(shù)學(xué)。”[3](p.863)
這種“預(yù)先糾錯(cuò)”的經(jīng)濟(jì)在理論上似乎很理想,而從物質(zhì)生產(chǎn)(不是效用生產(chǎn))的效率看它也許比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好,當(dāng)然比瞎指揮的“命令經(jīng)濟(jì)”更好。這洋一種設(shè)想最大的問題,與其說在于它沒有效率,不如說在于它不人道。它的設(shè)計(jì)無論如何“科學(xué)”,也是完全排除了消費(fèi)者主權(quán)或更廣義的個(gè)人效用主權(quán),把人當(dāng)作完全劃一、沒有生命的物體,當(dāng)作生產(chǎn)—消費(fèi)機(jī)器上的一個(gè)零件看待。例如,這種經(jīng)濟(jì)完全可以給一千個(gè)人配置出一千雙鞋,不多一雙,也不少一雙。既沒有過剩也沒有不足。它還可以通過精確計(jì)算做到所有的材料部物盡其用。根據(jù)這一千雙鞋所需要的材料安排皮革、橡膠等的供給,所有經(jīng)濟(jì)環(huán)節(jié)環(huán)環(huán)緊扣、精確銜接。它完全可以做到每個(gè)人都有鞋穿——但惟獨(dú)不考慮個(gè)人的喜好和特點(diǎn),它把消費(fèi)者主權(quán)與個(gè)人效用原則排除在外,給你什么你就得接受什么。
從理論上、從物質(zhì)生產(chǎn)的效率來說,它可以做到最優(yōu)化。但我們現(xiàn)在所講的效率不只是物質(zhì)生產(chǎn)效率,更主要是講效用增益效率,就是要滿足人們主觀福利偏好的效率。從這個(gè)角度看,這種經(jīng)濟(jì)就沒有效率,至少遠(yuǎn)不如以個(gè)人效用主權(quán)為基礎(chǔ)的公平競(jìng)爭(zhēng)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那么有效率。還用上面的例子說,為一千個(gè)人生產(chǎn)的這一千雙鞋,也許有大半是人們所不喜歡的。如果硬性配給,效用效率談不上,物質(zhì)生產(chǎn)效率(以實(shí)物即所謂“產(chǎn)品”計(jì)量的效率)在理論上還是有保證的。但這種保證必須以“最優(yōu)化計(jì)劃”的一元化控制為前提。也就是說它不可能“與市場(chǎng)機(jī)制相結(jié)合”。按“科學(xué)計(jì)劃”的確可以做到以最高的效率為一千個(gè)人提供一千雙鞋,但如果還要加一點(diǎn)市場(chǎng),允許這些人有權(quán)選擇,那么這一千雙鞋就很可能大半賣不出去,這些人就要從另外的途徑、在充分市場(chǎng)化以前往往是成本很高的途徑(自制或走私等等)來得到鞋子。于是效用生產(chǎn)效率的損失便轉(zhuǎn)化為物質(zhì)生產(chǎn)效率的損失,反而不如一點(diǎn)市場(chǎng)都沒有,通過越來越精密的“科學(xué)計(jì)劃”還可以保證物質(zhì)生產(chǎn)效率的提高。但計(jì)劃越科學(xué)“。加入市場(chǎng)因素后由效用效率損失轉(zhuǎn)化為物質(zhì)效率損失的現(xiàn)象就越嚴(yán)重。
兩種轉(zhuǎn)軌前體制的邏輯基礎(chǔ):“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還是“計(jì)劃科學(xué)”
這種按“經(jīng)濟(jì)方程的最優(yōu)解”運(yùn)行的“科學(xué)經(jīng)濟(jì)”到底能否實(shí)現(xiàn)?帕累托提出的這個(gè)問題在20世紀(jì)20—30年代引起了奧地利學(xué)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和社會(huì)主義學(xué)者蘭格、泰勒等人的長期爭(zhēng)議。前者認(rèn)為由于經(jīng)濟(jì)變量的無限性,按預(yù)先糾錯(cuò)的理論,把經(jīng)濟(jì)過程的所有變量都作為參數(shù)代入一個(gè)超多元的方程,求出一系列的生產(chǎn)函數(shù),這是“理性不及”,亦即人的能力所不能達(dá)到的。而以蘭格為首的一派、直到后來的數(shù)理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坎托洛維奇等認(rèn)為是可能的。現(xiàn)在東歐的左派理論家亞當(dāng)·沙夫仍然認(rèn)為,以前受科學(xué)水平所限,信息處理能力不足造成了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失敗,當(dāng)今電腦時(shí)代這些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他的結(jié)論是“新技術(shù)革命”是通過“真正計(jì)劃經(jīng)濟(jì)”來達(dá)到“新型社會(huì)主義”的必要手段。但在米塞斯一派的后學(xué)看來,人們需求信息的變化永遠(yuǎn)比人們處理信息的速度更快,所以坎托洛維奇等人的最優(yōu)化計(jì)劃只是“電腦烏托邦”,永遠(yuǎn)不可能實(shí)現(xiàn)。對(duì)這種爭(zhēng)論至少可以說:建立在最優(yōu)化數(shù)理經(jīng)濟(jì)模型基礎(chǔ)上的經(jīng)濟(jì)是不是比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更有效率可以另當(dāng)別論,但它比既沒有計(jì)劃也沒有市場(chǎng)的“命令經(jīng)濟(jì)”效率高是毫無疑問的。
東歐、俄羅斯與中國在建立社會(huì)主義時(shí)都處在不發(fā)達(dá)狀態(tài),都有“命令經(jīng)濟(jì)”傳統(tǒng)。但相對(duì)而言,蘇東的近代化程度較高,受工業(yè)文明影響較早,科學(xué)主義、理性計(jì)劃的成分因而比中國改革前大得多。與蘇聯(lián)東歐相比,改革前大多時(shí)間內(nèi)我們搞的實(shí)際上更近似于“無計(jì)劃的命令經(jīng)濟(jì)”。這兩種經(jīng)濟(jì)類型的理論模式最典型的表述就是過去人們經(jīng)常談到的“馬鋼憲法”和“鞍鋼憲法”。當(dāng)年援華蘇聯(lián)專家引入斯大林時(shí)代樣板企業(yè)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聯(lián)合企業(yè)運(yùn)營管理體制,企業(yè)中雖有黨組織但基本不設(shè)專職黨干,強(qiáng)調(diào)一長制、科層化管理、專家治廠,嚴(yán)格經(jīng)濟(jì)核算與計(jì)劃平衡。而中國的鞍鋼憲法則強(qiáng)調(diào)企業(yè)中設(shè)立強(qiáng)大的專職黨政機(jī)構(gòu),實(shí)行群眾運(yùn)動(dòng)、政治掛帥、黨委領(lǐng)導(dǎo)、政工治廠、階級(jí)斗爭(zhēng)等。前者主要體現(xiàn)理性計(jì)劃原則,后者主要體現(xiàn)浪漫命令原則。應(yīng)該說這兩種經(jīng)濟(jì)類型在蘇東和中國都有,但相比較而言,中國“命令經(jīng)濟(jì)”的成分要多得多,蘇東“科學(xué)計(jì)劃”的成分要多得多,而且隨著其工業(yè)化的發(fā)展而加深。從列寧欣賞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時(shí)期的“馬鋼憲法”諸原則,直到勃列日涅夫時(shí)代大興數(shù)理經(jīng)濟(jì)學(xué),實(shí)行“最優(yōu)化模型主義”,“科學(xué)計(jì)劃”體制越來越“理性”了。
一般而言,理性計(jì)劃經(jīng)濟(jì)、命令經(jīng)濟(jì)與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區(qū)別可表列如下:
表1理性計(jì)劃經(jīng)濟(jì)、命令經(jīng)濟(jì)與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區(qū)別(一)
表2理性計(jì)劃經(jīng)濟(jì)、命令經(jīng)濟(jì)與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區(qū)別(二)
有趣的是在“創(chuàng)新效率”方面,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均衡永遠(yuǎn)是動(dòng)態(tài)的,由于競(jìng)爭(zhēng)與需求的激勵(lì)、過剩與不足的交替,均衡不斷被打破和重建,兩者都能推動(dòng)創(chuàng)新,而市場(chǎng)本身又具有鑒別有效創(chuàng)新、淘汰無效創(chuàng)新和“偽創(chuàng)新”的功能,因而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實(shí)物生產(chǎn)效率,甚至最重要的也不在于效用增益效率,而在于它那無可比擬的創(chuàng)新效率,這是它能淘汰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直接原因。理性計(jì)劃經(jīng)濟(jì)與命令經(jīng)濟(jì)在創(chuàng)新問題上似乎顯得“兩極化”:理性計(jì)劃經(jīng)濟(jì)由于它那靜態(tài)均衡和“預(yù)先糾錯(cuò)”性質(zhì),是最難產(chǎn)生創(chuàng)新激勵(lì)的。在一個(gè)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最優(yōu)化計(jì)劃”中如果一個(gè)環(huán)節(jié)出現(xiàn)創(chuàng)新,反而會(huì)打破靜態(tài)均衡,導(dǎo)致來自其他環(huán)節(jié)的壓力。因此理性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理性”從另一面看,實(shí)為泯滅創(chuàng)新激情的惰性。蘇聯(lián)經(jīng)濟(jì)墨守成規(guī)、產(chǎn)品幾十年一貫制,傻大黑粗而“經(jīng)久耐用”是出了名的。而命令經(jīng)濟(jì)由于既無均衡觀念,又不講究環(huán)環(huán)相扣,還沒有科層化的約束,就顯得很不“墨守成規(guī)”,它常常能夠激勵(lì)浪漫的“創(chuàng)新”狂想:沒有哪個(gè)體制能像改革前的中國那樣成天號(hào)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保守”,拔“白旗”,創(chuàng)“奇跡”,“放衛(wèi)星”,“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砸爛規(guī)章制度”,“打破條條框框”……然而,這種體制致命的問題在于沒有鑒別有效創(chuàng)新、淘汰無效創(chuàng)新和“偽創(chuàng)新”的機(jī)制,因而往往是“偽創(chuàng)新”、“奉旨創(chuàng)新”的效率特別“高”。而這種“偽創(chuàng)新”只會(huì)浪費(fèi)資源、敗壞風(fēng)氣,對(duì)國民經(jīng)濟(jì)的效用增益起負(fù)面作用。因此在效率方面,命令經(jīng)濟(jì)的“偽創(chuàng)新”通常還不如理性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不創(chuàng)新。不過,如果就打破體制本身束縛的“創(chuàng)新”而論,命令經(jīng)濟(jì)的這種特性倒使它比理性計(jì)劃經(jīng)濟(jì)更容易被“創(chuàng)新”掉。
理性計(jì)劃經(jīng)濟(jì)與命令經(jīng)濟(jì)的績(jī)效比較不僅可以在理論上分優(yōu)劣,而且經(jīng)驗(yàn)上也十分清楚。工業(yè)戰(zhàn)線的老同志都知道:如今向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轉(zhuǎn)軌中成為老大難問題的許多大型國企,尤其是以東北等地為中心的“156個(gè)大型項(xiàng)目”在改革前曾長期作為我國工業(yè)中的精華,其經(jīng)濟(jì)效益與業(yè)績(jī)指標(biāo)大都遙遙領(lǐng)先于我國工業(yè)的其余部分。這些企業(yè)當(dāng)年均由蘇聯(lián)、捷克等國一手援建并奠定了其經(jīng)營管理模式,后來雖然這種計(jì)劃經(jīng)濟(jì)模式受到“反修”的沖擊,畢竟還有相當(dāng)影響。而在“反修”中我們“自力更生”搞的那些運(yùn)動(dòng)型企業(yè),包括“躍進(jìn)牌”企業(yè)、五小工業(yè)、三線工業(yè)等等,除了少數(shù)像大慶這樣的資源型企業(yè)與煙草工業(yè)這類特殊專營企業(yè)外,絕大多數(shù)績(jī)效都很差。
但也有人認(rèn)為,從整體經(jīng)濟(jì)指標(biāo)看,改革前我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速度總的來說并不亞于蘇聯(lián)。其中最極端者(如韓德強(qiáng)先生)甚至認(rèn)為改革前經(jīng)濟(jì)績(jī)效高于改革后:雖然那時(shí)生活較差,但是高積累高速度奠定了工業(yè)化基礎(chǔ),改革后只是在吃老本。如果就發(fā)展績(jī)效而言,這個(gè)說法是完全錯(cuò)誤的。盡管經(jīng)過長期戰(zhàn)爭(zhēng)與革命后,改革前我國經(jīng)歷了近代以來從未有過的30年和平時(shí)代,在這個(gè)背景下舊體制與“計(jì)劃經(jīng)濟(jì)”類似的高積累機(jī)制也的確對(duì)工業(yè)化原始積累發(fā)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在“原始積累”以外的意義上,這個(gè)體制的績(jī)效確實(shí)很差。不僅與改革后相比,就是與現(xiàn)在被公認(rèn)為弊端百出的蘇聯(lián)模式計(jì)劃經(jīng)濟(jì)相比也是如此。韓德強(qiáng)等先生喜歡用改革前官方統(tǒng)計(jì)數(shù)字,從這些數(shù)字看,即使現(xiàn)在被稱為“十年浩劫”、“國民經(jīng)濟(jì)瀕臨崩潰”的“文革”時(shí)期,發(fā)展速度似乎也不比改革后低。國外早就有學(xué)者以此為據(jù),說了不少“文革”的好話。本文在這里不打算全面評(píng)價(jià)這種統(tǒng)計(jì)方式存在的問題,只是想以同樣口徑因而也存在類似問題、但因此反而有相當(dāng)可比性的蘇聯(lián)時(shí)代數(shù)字作為對(duì)比,看看蘇聯(lián)計(jì)劃經(jīng)濟(jì)與我國改革前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績(jī)效。
這里必須指出,盡管中蘇等國因政治因素決定的統(tǒng)計(jì)模式相似,但有一點(diǎn)明顯不同:在傳統(tǒng)上中國歷來以與1949年的比較來統(tǒng)計(jì)發(fā)展成就,而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都是按國際通常的口徑與戰(zhàn)前和平年代最高水平作比較來統(tǒng)計(jì)發(fā)展成就的。1949年是個(gè)10余年毀滅性戰(zhàn)爭(zhēng)后的廢墟狀態(tài),嚴(yán)格地講不適于用作比較基期,尤其不適于用作評(píng)價(jià)制度性因素對(duì)發(fā)展之影響的比較,更不適于與上述蘇聯(lián)式的發(fā)展統(tǒng)計(jì)相比。近來我國的統(tǒng)計(jì)界已經(jīng)意識(shí)到這個(gè)問題,因此統(tǒng)計(jì)發(fā)展成就多改以“國民經(jīng)濟(jì)恢復(fù)時(shí)期”結(jié)束的當(dāng)年即1952年為比較基期。“國民經(jīng)濟(jì)恢復(fù)”后的數(shù)字盡管并不完全等于戰(zhàn)前最高水平,但由于我國情況特殊,很難確定一個(gè)年份代表“戰(zhàn)前最高水平”(注:我國農(nóng)業(yè)以1936年為戰(zhàn)前最高水平,但抗戰(zhàn)時(shí)期雖然內(nèi)地工業(yè)破壞慘重,日本在其占領(lǐng)相對(duì)穩(wěn)定的東北等地則靠野蠻手段達(dá)致戰(zhàn)時(shí)經(jīng)濟(jì)的一定程度發(fā)展,使全國統(tǒng)計(jì)的若干工業(yè)品產(chǎn)量高峰出現(xiàn)在1942-1943年前后。),因此用1952年數(shù)字代表“戰(zhàn)前最高水平”還是最為近似的。
在此基礎(chǔ)上,我們可以把改革前中蘇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中長期業(yè)績(jī)作出如下幾項(xiàng)分段比較:蘇聯(lián)經(jīng)歷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與三年大規(guī)模內(nèi)戰(zhàn)后,1921年基本恢復(fù)和平(當(dāng)年仍有收復(fù)遠(yuǎn)東、平定伏爾加流域農(nóng)民起義、烏克蘭—中亞地區(qū)民族主義抵抗與喀瑯施塔得“叛亂”等局部戰(zhàn)爭(zhēng)),由此至1940年共20年和平建設(shè),到1940年與戰(zhàn)前經(jīng)濟(jì)最高水平的1913年相比,國民收入達(dá)到611%,工業(yè)產(chǎn)值達(dá)到852%,農(nóng)業(yè)產(chǎn)值達(dá)到141%,[5](p.58)農(nóng)業(yè)人口比重由1913年的82.1%降至1939年的67%。[6](p.12)中國1950年基本恢復(fù)和平(海南、舟山、西康仍有局部戰(zhàn)事,至于抗美援朝則是境外作戰(zhàn),人力損失雖大而物力主要靠蘇援,對(duì)國內(nèi)建設(shè)影響不大),由此至1969年也是20年和平建設(shè),而1969年與“恢復(fù)到戰(zhàn)前經(jīng)濟(jì)最高水平”的1952年相比,工業(yè)產(chǎn)值僅達(dá)到477%,“社會(huì)總產(chǎn)值”在1952-1971的20年里只增加到339.8%,農(nóng)業(yè)產(chǎn)值則增加到162.9%(注:據(jù)汪海波:《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yè)經(jīng)濟(jì)史》,山西經(jīng)濟(jì)出版社,1998年,第902、888-889頁有關(guān)數(shù)據(jù)推算。)。實(shí)際上蘇聯(lián)的農(nóng)業(yè)雖然糟糕,主要表現(xiàn)為產(chǎn)量增長慢以及為實(shí)現(xiàn)集體化付出的慘重代價(jià),但蘇聯(lián)農(nóng)民因工業(yè)化而明顯減少,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率還是頗有提高,而中國農(nóng)民在此期間仍不斷增加,其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率明顯下降,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者年人均凈產(chǎn)值從“一五”時(shí)期的215.6元降至“三五”時(shí)期的182.4元。[7](p.358)
1941-1945年蘇聯(lián)陷入空前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1946年恢復(fù)和平建設(shè),歷14年至1959年與戰(zhàn)前經(jīng)濟(jì)最高水平的1940年相比,國民收入達(dá)到405%,工業(yè)產(chǎn)值達(dá)到480%,農(nóng)業(yè)產(chǎn)值達(dá)到156%,[5](p.59)農(nóng)業(yè)人口比重由1940年的67%降至1961年的50%。[6](p.12)如果同樣以14年的時(shí)間看中國,則1950-1963的14年發(fā)展使中國在1963年達(dá)到相當(dāng)于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52年工業(yè)產(chǎn)值的284.5%,1952-1965年間社會(huì)總產(chǎn)值只增加到212.1%,農(nóng)業(yè)產(chǎn)值只增加到137%(注:據(jù)汪海波:《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yè)經(jīng)濟(jì)史》,山西經(jīng)濟(jì)出版社,1998年,第902、888-889頁有關(guān)數(shù)據(jù)推算。),而農(nóng)業(yè)人口比重在這14年前后幾乎完全沒有變化。(注:中國城鎮(zhèn)人口在“大躍進(jìn)”中一度猛增,災(zāi)難發(fā)生后又大力清退,使1966年底城鎮(zhèn)人口總數(shù)降至1957年水平。但由于總?cè)丝谠黾樱擎?zhèn)人口比重這時(shí)已降至1953年水平,即13.4%。參見胡煥庸、張善余主編:《中國人口地理》上冊(cè),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84年,第273頁。)
經(jīng)過以上兩個(gè)階段共32年的和平建設(shè),1959年蘇聯(lián)工人平均“實(shí)際收入”達(dá)到革命前最高年份(1913年)的390%。[5](p.76)應(yīng)當(dāng)說這個(gè)增長速度并不高,可是與中國相比還是很驚人了:同樣是32年和平建設(shè),中國經(jīng)濟(jì)到1984年工業(yè)職工平均“實(shí)際工資”僅為1952年(相當(dāng)于革命前最高年份)的129.4%。而且這點(diǎn)可憐的增長也都是1956年以前“完全學(xué)蘇聯(lián)”時(shí)期與1977年以后很大程度上是恢復(fù)“蘇聯(lián)模式”的那幾年的成果。如果以開始大批“一長制”的1957年與結(jié)束“文革”的1977年相比,則在這“中國特色”最濃的20年間中國工人的平均實(shí)際工資指數(shù)(以1952年為100)竟然從116.3降至92.7,即凈減少20.3%
即使在工資有所增長的蘇聯(lián),國民總體生活水準(zhǔn)的提高主要也不是靠這種增長,而是靠大量農(nóng)民轉(zhuǎn)為城市人口帶來的生活水平變化。中國雖然工人農(nóng)民各自收入水平部很低,兩者間的差距卻很大,“農(nóng)轉(zhuǎn)非”更是這一時(shí)期中國人生活提高的主要希望。遺憾的是:這一希望在中國比在蘇聯(lián)渺茫得多。在上述同一時(shí)期,蘇聯(lián)農(nóng)業(yè)人口比重已由革命前經(jīng)濟(jì)最好時(shí)的82%降至50%左右,基本達(dá)到了進(jìn)入工業(yè)社會(huì)時(shí)的都市化水平。中國同樣是32年和平建設(shè),城鎮(zhèn)人口比重僅由1949年的10.6%升至1981年的19.8%,其中非農(nóng)業(yè)人口僅為13.9%。“農(nóng)民國家”的面貌基本未變。而且同樣,這點(diǎn)增加也是1957年以前、1977年以后“蘇聯(lián)模式”還算管點(diǎn)用時(shí)的情況,而在1960-1976年間城鎮(zhèn)人口從13073萬降至11342萬,[9](p.272)純減幅達(dá)13.2%。這樣的“逆城市化過程”無論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國家還是在蘇聯(lián)東歐的所有計(jì)劃經(jīng)濟(jì)國家部沒有出現(xiàn)。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按20年、14年、32年和平發(fā)展的績(jī)效分別進(jìn)行中蘇改革前舊模式的比較,得出以下三表:
表320年績(jī)效比較(20年和平發(fā)展后與戰(zhàn)前最高年份之比)單位:%
表414年績(jī)效比較(14年和平發(fā)展后與戰(zhàn)前最高年份之比)單位:%
表532年發(fā)展績(jī)效(32年和平發(fā)展后與革命前最高年份之比)單位:%
這里當(dāng)然還有一些不可比因素,如蘇聯(lián)在二戰(zhàn)前處于“一國社會(huì)主義”狀態(tài),經(jīng)濟(jì)發(fā)展基本無法指望外援。而中國在50年代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得益于蘇聯(lián)援助的成分是不能否認(rèn)的,但是即使排除這些因素我們也不難看到:中國改革前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績(jī)效的確與蘇聯(lián)式計(jì)劃經(jīng)濟(jì)有明顯的差異。當(dāng)然蘇聯(lián)式發(fā)展的代價(jià)也是駭人聽聞的,從今天改革的眼光看,蘇聯(lián)式的體制并不可取,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區(qū)分兩種體制的差別。
因此,這兩種經(jīng)濟(jì)在改革過程中面臨的問題有很大的不同。命令經(jīng)濟(jì)與“科學(xué)計(jì)劃經(jīng)濟(jì)”一樣不人道,一樣缺少效用生產(chǎn)效率,但它因“不能糾錯(cuò)”而比“預(yù)先糾錯(cuò)”的經(jīng)濟(jì)更糟,因?yàn)樗€嚴(yán)重地?fù)p害實(shí)物生產(chǎn)效率。而“科學(xué)計(jì)劃”在這方面卻有長處,起碼它是一種“次優(yōu)”的選擇。但也正因?yàn)榇耍懊罱?jīng)濟(jì)”的可逆性較強(qiáng),它會(huì)把經(jīng)濟(jì)搞得一團(tuán)糟(像“文革”、“大躍進(jìn)”時(shí)期)。但從這種“無序的命令”中走出來卻相對(duì)容易,而“科學(xué)計(jì)劃經(jīng)濟(jì)”卻是一種嚴(yán)格有序的經(jīng)濟(jì),對(duì)它的改革容易產(chǎn)生無序。一般地講,改掉“命令經(jīng)濟(jì)”可以通過兩種方式進(jìn)行:一是放棄命令走向市場(chǎng),遵循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規(guī)則就能較易實(shí)現(xiàn)過渡。二是放棄浪漫命令,約束長官意志,“按科學(xué)規(guī)律辦事”,運(yùn)用最優(yōu)化數(shù)理方法來實(shí)現(xiàn)計(jì)劃科學(xué)化、理性化。對(duì)命令經(jīng)濟(jì)成分較多的國家來說,無論走哪條路付出的代價(jià)都比較小。因?yàn)樵瓉淼摹跋怪笓]”本來就不能建立均衡,當(dāng)然就不存在改革破壞均衡的問題。這時(shí)無論通過“最優(yōu)化”改革來建立“計(jì)劃均衡”,還是通過市場(chǎng)化改革來建立市場(chǎng)均衡,都會(huì)帶來經(jīng)濟(jì)上的純?cè)鲆妗6鴮?duì)于計(jì)劃經(jīng)濟(jì)成分較多的國家來說,問題就復(fù)雜得多。它可以通過“科學(xué)”手段使計(jì)劃更加精確、周密、完善,越來越吻合于最優(yōu)化數(shù)理模型。但這種改善有一個(gè)悖論,它在科學(xué)計(jì)劃上越走得遠(yuǎn),要轉(zhuǎn)到市場(chǎng)就越困難。因如此精確的計(jì)劃均衡極易被破壞,而市場(chǎng)均衡機(jī)制卻不那么好建立。如此環(huán)環(huán)相扣、分工細(xì)密、有機(jī)聯(lián)系的經(jīng)濟(jì),只要計(jì)劃一中斷,整個(gè)系統(tǒng)就會(huì)崩潰,生產(chǎn)就會(huì)完全紊亂。
現(xiàn)在有人說:民主造成了混亂,過于激進(jìn)的經(jīng)濟(jì)變革造成了混亂。然而蘇聯(lián)東歐在舊體制時(shí)代不是沒有試過非民主狀態(tài)下的漸進(jìn)改革,但往往就是“一改就亂”。人們就是從中認(rèn)定政治不改革,經(jīng)濟(jì)改不動(dòng),或者漸進(jìn)無效果,必須徹底市場(chǎng)化的。早在60年代,人們就發(fā)現(xiàn)了這種兩難處境。60年代蘇聯(lián)的利別爾曼建議就是要在體制內(nèi)局部引進(jìn)市場(chǎng)激勵(lì)的。這個(gè)潮流傳到東歐,東德,捷克、波蘭等國都搞過“利潤掛帥,市場(chǎng)導(dǎo)向”。然而不久就發(fā)現(xiàn),這么一搞,原有的計(jì)劃就紊亂,原有的分工協(xié)作體系就受干擾以至中斷,生產(chǎn)出現(xiàn)下滑。后來中國那種市場(chǎng)因素“引進(jìn)一點(diǎn)改善一點(diǎn)”的好處,他們沒有嘗到。于是只好又回頭搞計(jì)劃科學(xué)化的模式。最典型的例子是東德。東德在60年代學(xué)利別爾曼建議也搞過放權(quán)讓利、加強(qiáng)經(jīng)濟(jì)核算的新經(jīng)濟(jì)體制,遵循一些市場(chǎng)選擇,結(jié)果馬上產(chǎn)生混亂,只好更換方向,到70年代走上“計(jì)算中心”指揮下的全國“托拉斯”化道路,不斷集中不斷地搞全行業(yè)一體化。捷克在60年代也企圖搞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改革,“布拉格之春”是政治先行,在《兩千字宣言》和《捷共行動(dòng)綱領(lǐng)》中都有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內(nèi)容。捷克“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理論家奧塔·希克就是代表。但經(jīng)濟(jì)改革還沒來得及實(shí)行就被明火執(zhí)仗的武力卡斷了,到了胡薩克時(shí)代,捷克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又努力使計(jì)劃“更加符合最優(yōu)化方向”,居然還真使經(jīng)濟(jì)一度又有起色。
利別爾曼建議的產(chǎn)生地蘇聯(lián)也是如此,赫魯曉夫后期的改革未能取得效果,這成為他被趕下臺(tái)的原因之一。在“河”里沒有摸到“石頭”的蘇聯(lián)人認(rèn)為退回原處沒有出路,因此改而強(qiáng)調(diào)優(yōu)化計(jì)劃。于是抽調(diào)專家到計(jì)委,給計(jì)劃統(tǒng)計(jì)部門配置高級(jí)計(jì)算機(jī),進(jìn)一步發(fā)展數(shù)理經(jīng)濟(jì)學(xué)。但“科學(xué)計(jì)劃”越是“理性”就越不食人間煙火的反人道之弊卻不是“最優(yōu)化”所能消解的,到一定程度人們又會(huì)有效用追求、亦即向往市場(chǎng)的追求。7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晚期又一次循環(huán)到放權(quán)讓利、擴(kuò)大企業(yè)自主權(quán)的階段,這新的輪回再次重復(fù)了60年代的情況:一放就亂,而且越是“科學(xué)”的計(jì)劃,一旦放棄,那“亂”的代價(jià)也越大,只好又強(qiáng)化“聯(lián)合體”制和“經(jīng)濟(jì)區(qū)”制,把一個(gè)行業(yè)的生產(chǎn)全部歸到一起,實(shí)行全國“托拉斯”化,在一個(gè)“預(yù)先糾錯(cuò)”的體系下按“最優(yōu)化參數(shù)”進(jìn)行生產(chǎn)。
在這一過程中,數(shù)理經(jīng)濟(jì)學(xué)越來越取代“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成為東歐計(jì)劃經(jīng)濟(jì)學(xué)的主流。數(shù)理經(jīng)濟(jì)學(xué)是從理性主義的角度以最優(yōu)化模型來配置資源的一門學(xué)問。而傳統(tǒng)的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要解決的是道德判斷問題,即證明資本主義是惡而社會(huì)主義是善,但它對(duì)怎么搞“計(jì)劃”(這是道義原則無法解決的運(yùn)算問題)是不加考慮的。所以可以說,與計(jì)劃經(jīng)濟(jì)相應(yīng)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就是數(shù)理經(jīng)濟(jì)學(xué)。而“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盛行、數(shù)理經(jīng)濟(jì)學(xué)空白則是“命令經(jīng)濟(jì)”在學(xué)術(shù)上的體現(xiàn)。
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在馬克思那里是用于批判資本主義的,但計(jì)劃經(jīng)濟(jì)本身是否有自己的經(jīng)濟(jì)學(xué)?馬克思并沒有涉及這個(gè)問題。后來斯大林署名搞了一本“蘇聯(lián)經(jīng)濟(jì)學(xué)圣經(jīng)”即《蘇聯(lián)社會(huì)主義經(jīng)濟(jì)問題》,該書傳入中國后成為直到改革之初一直壟斷經(jīng)濟(jì)學(xué)界的“社會(huì)主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體系”的祖本。盡管與蘇聯(lián)相比,中國版的社會(huì)主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政治性更濃邏輯性更差,總體學(xué)術(shù)水平未必能及蘇聯(lián),但“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一統(tǒng)天下之地位卻是東歐萬不能及的。
然而在蘇聯(lián)本國,即使在斯大林神化最甚時(shí),計(jì)劃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數(shù)理化方向已經(jīng)大成氣候。20年代涅姆欽諾夫的統(tǒng)計(jì)分析理論與30年代坎托羅維奇的最優(yōu)化模型建構(gòu),分別為計(jì)劃經(jīng)濟(jì)中的經(jīng)濟(jì)信息處理與系統(tǒng)最優(yōu)化控制奠定了“科學(xué)”基礎(chǔ)。而“社會(huì)主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卻長期受冷遇。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與布哈林雖被鎮(zhèn)壓,計(jì)劃經(jīng)濟(jì)下無“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而只有“計(jì)劃科學(xué)”的看法在30年代仍然影響大多數(shù)蘇聯(lián)經(jīng)濟(jì)學(xué)家。1936年聯(lián)共(布)中央《關(guān)于改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教學(xué)》的決議和后來的斯大林“圣經(jīng)”雖然都指令要搞社會(huì)主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但直到1951年聯(lián)共(布)中央召開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教科書未定稿討論會(huì)時(shí),仍然有許多學(xué)者盡管承認(rèn)要搞“社會(huì)主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卻堅(jiān)持認(rèn)為它不研究“生產(chǎn)關(guān)系”(即不像“資本主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那樣承擔(dān)制度褒貶功能),而只應(yīng)研究“生產(chǎn)力的合理組織和國民經(jīng)濟(jì)的計(jì)劃化”問題,實(shí)際上還是把它看作非“政治”的“計(jì)劃科學(xué)”。
直到1954年,蘇聯(lián)才出版了包含“社會(huì)主義”內(nèi)容的《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教科書》。而這時(shí)斯大林已死,蘇聯(lián)也已在沒有“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情況下靠“計(jì)劃科學(xué)”完成了工業(yè)化。隨著理性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與早期命令經(jīng)濟(jì)成分的消失,“社會(huì)主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地位從赫魯曉夫時(shí)代逐漸式微,數(shù)理經(jīng)濟(jì)學(xué)、尤其是坎托羅維奇所開創(chuàng)的“最優(yōu)化計(jì)劃”成為蘇聯(lián)理論經(jīng)濟(jì)學(xué)的主流。早期的維恩斯坦、諾沃日洛夫,晚期的阿甘別吉楊、沙塔林直到后來改宗西方經(jīng)濟(jì)學(xué)而成為劇變后經(jīng)濟(jì)轉(zhuǎn)軌理論家的蓋達(dá)爾、亞夫休斯基等等,這些掛帥人物無不是數(shù)理經(jīng)濟(jì)學(xué)出身的。60年代后對(duì)蘇聯(lián)經(jīng)濟(jì)決策具有現(xiàn)實(shí)影響力的經(jīng)濟(jì)學(xué)研究機(jī)構(gòu)也是中央經(jīng)濟(jì)數(shù)學(xué)研究所、科學(xué)城工業(yè)經(jīng)濟(jì)研究所等數(shù)理經(jīng)濟(jì)學(xué)重鎮(zhèn),而傳統(tǒng)上主要承擔(dān)“批資”、“衛(wèi)道”意識(shí)形態(tài)職能的機(jī)構(gòu)如蘇聯(lián)科學(xué)院經(jīng)濟(jì)研究所等,這時(shí)也已突出了數(shù)理化色彩。
有趣的是,作為現(xiàn)代性異化的典型體現(xiàn),科學(xué)主義的過分?jǐn)U張一方面以“理性的僭妄”壓抑了人性,另一方面也會(huì)沖擊中世紀(jì)式的“神性”,而不同于僅僅以人身依附為基礎(chǔ)的傳統(tǒng)“命令經(jīng)濟(jì)”思想。一些數(shù)理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由于其強(qiáng)烈的科學(xué)主義現(xiàn)代性取向,對(duì)掌權(quán)政客“反科學(xué)”的恣意妄為與瞎指揮深惡痛絕,往往容易發(fā)展出離經(jīng)叛道的異端傾向。早在20世紀(jì)60年代,老一代數(shù)理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涅姆欽諾夫、維恩斯坦等人就激烈批評(píng)“僵化的經(jīng)濟(jì)體制”,認(rèn)為“一個(gè)從頭到腳被束縛得如此厲害的經(jīng)濟(jì)體制,將阻礙社會(huì)與技術(shù)的進(jìn)步,并遲早將在經(jīng)濟(jì)生活實(shí)際進(jìn)程的壓力下走向崩潰”。(注:B ·C ·涅姆欽諾夫:《論進(jìn)一步完善計(jì)劃與經(jīng)濟(jì)問題》,轉(zhuǎn)引自金雁:《蘇俄現(xiàn)代化與改革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6-57頁。)當(dāng)時(shí)要求改革的新派經(jīng)濟(jì)學(xué)家都由他們構(gòu)成,轉(zhuǎn)軌后最狂熱地主張自由市場(chǎng)的也是前數(shù)理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然而,又恰恰是被數(shù)理經(jīng)濟(jì)學(xué)高度“最優(yōu)化”了的俄國計(jì)劃經(jīng)濟(jì),成為最難搞市場(chǎng)化轉(zhuǎn)軌的經(jīng)濟(jì)體。所謂東歐擁有“最好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與最差的經(jīng)濟(jì)”這樣一種奇怪的景觀,說穿了也并不奇怪。
而在中國,“社會(huì)主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一直到改革前夕還是舊體制經(jīng)濟(jì)的惟一理論形態(tài)。可以說,1978年以前在中國經(jīng)濟(jì)學(xué)界,既沒有人吃西方經(jīng)濟(jì)學(xué)這碗飯,也沒有人搞坎托洛維奇那套東西。這不能以那時(shí)政治上“反修”、與蘇聯(lián)學(xué)術(shù)隔絕來解釋。因?yàn)樘K聯(lián)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數(shù)理化早在斯大林時(shí)代已經(jīng)很明顯,那時(shí)中國根本沒有反修之說,而是事事學(xué)蘇聯(lián)的,可是中國并沒有引進(jìn)涅姆欽諾夫、坎托羅維奇之學(xué)。這只能理解為當(dāng)時(shí)中國的命令經(jīng)濟(jì)還只需要“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來為“命令”作道德論證,并不需要什么最優(yōu)化機(jī)制。
我們現(xiàn)在常說,蘇聯(lián)忽視了信息技術(shù)革命,這話要看怎么說。蘇聯(lián)人的確壓根兒想不到去開發(fā)作為市場(chǎng)信息載體的互聯(lián)網(wǎng),更不會(huì)發(fā)展作為新一代市場(chǎng)消費(fèi)熱點(diǎn)的個(gè)人電腦及其大批相關(guān)商品——正是這些東西導(dǎo)致西方發(fā)達(dá)國家經(jīng)濟(jì)出現(xiàn)質(zhì)的飛躍。但若論計(jì)算機(jī)在要素配置中的應(yīng)用,從宏觀的計(jì)劃制定到微觀的企業(yè)管理,蘇聯(lián)在世界上都是最早注意的。早在電腦時(shí)代之前,以解復(fù)雜數(shù)理方程來求得經(jīng)濟(jì)參數(shù)最優(yōu)化就成為蘇聯(lián)式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核心思想之一。無怪乎東歐人都寄厚望于電腦,數(shù)理經(jīng)濟(jì)學(xué)因而被稱為“電腦烏托邦”。早在第二代計(jì)算機(jī)時(shí)代,蘇聯(lián)對(duì)電腦的運(yùn)用已經(jīng)從一般數(shù)據(jù)處理與統(tǒng)計(jì)分析發(fā)展為使用經(jīng)濟(jì)數(shù)學(xué)模型制定最優(yōu)化計(jì)劃。以后蘇聯(lián)的生產(chǎn)越來越朝理性計(jì)劃發(fā)展,越來越強(qiáng)調(diào)生產(chǎn)函數(shù)最優(yōu)化設(shè)定。早在70年代末,蘇聯(lián)已普遍設(shè)立了各專業(yè)部計(jì)算中心,并在互相聯(lián)通的基礎(chǔ)上建立了全蘇計(jì)算機(jī)中心(ВЦВЦИО)。80年代前期,蘇聯(lián)當(dāng)局又提出“當(dāng)今時(shí)代的特點(diǎn)之一,是廣泛采用計(jì)算技術(shù)設(shè)備來解決復(fù)雜的計(jì)劃—經(jīng)濟(jì)、組織和管理課題”。
與宏觀經(jīng)濟(jì)中的計(jì)劃最優(yōu)化相應(yīng),蘇聯(lián)企業(yè)的微觀管理也向“最優(yōu)化”發(fā)展。當(dāng)時(shí)推廣的“謝基諾實(shí)驗(yàn)”通過優(yōu)化勞動(dòng)組織、運(yùn)用運(yùn)籌學(xué)等科學(xué)計(jì)劃手段,分解經(jīng)濟(jì)指標(biāo),實(shí)行物質(zhì)刺激而實(shí)現(xiàn)減員增效。通過實(shí)驗(yàn),謝基諾化工聯(lián)合企業(yè)產(chǎn)值增加兩倍,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提高三倍,人員減少1570人,平均工資增加46.5%。當(dāng)時(shí)還有所謂茲洛賓方法、列寧格勒經(jīng)驗(yàn)、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是計(jì)劃最優(yōu)化在微觀經(jīng)濟(jì)中的實(shí)踐。
走出“命令”與走出“計(jì)劃”:改革的“效率代價(jià)”問題
然而,計(jì)劃經(jīng)濟(jì)固有的創(chuàng)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設(shè)計(jì)”人的行為這種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鉆“最優(yōu)化”的牛角尖也無法解決的根本弊病。進(jìn)入80年代后,“計(jì)劃最優(yōu)化”已出現(xiàn)明顯的邊際效益遞減。而西方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卻在這時(shí)出現(xiàn)了信息技術(shù)革命、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jí)和“里根—撒切爾繁榮”。形勢(shì)迫使蘇聯(lián)人不得不改弦更張。但是,放棄這樣嚴(yán)密的“科學(xué)計(jì)劃”對(duì)經(jīng)濟(jì)的沖擊是很大的。東歐人在這一過程中無疑有這樣或那樣的失誤,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誤,一個(gè)時(shí)期的經(jīng)濟(jì)滑坡也在所難免——最明顯的是:甚至連并沒有面臨轉(zhuǎn)軌問題的芬蘭,僅僅由于其與經(jīng)互會(huì)國家貿(mào)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計(jì)劃的廢棄,在1989年后經(jīng)歷了連續(xù)數(shù)年的經(jīng)濟(jì)大滑坡。1991-1994年,芬蘭國民生產(chǎn)總值從1220億美元降至958億美元,降幅達(dá)21.5%。[11](p.607)
在蘇聯(lián)東歐一會(huì)兒?jiǎn)柦蛴谑袌?chǎng)、一會(huì)兒又轉(zhuǎn)向琢磨怎么使計(jì)劃更“理性”的曲蛇形探索的同時(shí),中國卻相反地走上一條一邊割斷市場(chǎng)“尾巴”、一邊搞亂計(jì)劃秩序,越來越走向命令經(jīng)濟(jì)之路,如所周知,中國在“大躍進(jìn)”時(shí)代曾搞過“吃飯不要錢”,在“文革”中把農(nóng)家養(yǎng)雞都當(dāng)作“資本主義尾巴”來禁止,許多地區(qū)一度取消傳統(tǒng)農(nóng)村集市,不但消滅私人經(jīng)濟(jì),把集體企業(yè)也當(dāng)作“集體資本主義”來打擊。在理論上不僅大批“等價(jià)交換”,甚至連命令經(jīng)濟(jì)中的工資制也被當(dāng)作“資產(chǎn)階級(jí)法權(quán)”痛加貶斥。除這些特殊時(shí)段外,一般而言中國在票證、戶口控制等“反市場(chǎng)制度”方面也比蘇聯(lián)更極端。但是盡管如此,改革后中國市場(chǎng)關(guān)系的恢復(fù)與發(fā)育卻比前經(jīng)互會(huì)國家相對(duì)容易,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國的命令經(jīng)濟(jì)至少以與消滅市場(chǎng)同樣的程度,消滅了理性計(jì)劃機(jī)制。
本來,正如蘇聯(lián)建國之初在落后農(nóng)業(yè)文明土壤上亦有命令經(jīng)濟(jì)成分一樣,中國建國之初受工業(yè)化蘇聯(lián)的影響也引進(jìn)了若干理性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因素。“馬鋼憲法”尤其是其中的“一長制”等內(nèi)容,曾在東北等地的一些蘇援工廠實(shí)行。據(jù)薄一波的回憶,1956年前實(shí)行蘇式廠長負(fù)責(zé)制的地方,尤其是156項(xiàng)目中較系統(tǒng)地引進(jìn)蘇式管理制度的那些企業(yè),績(jī)效還不錯(cuò):“東北就是完全學(xué)蘇聯(lián)的,成績(jī)顯著。”[12](p.963)
1956年中共召開“八大”,按薄一波的說法,就是在這次大會(huì)上,毛澤東發(fā)動(dòng)了大批“一長制”的潮頭。中國工業(yè)從此恢復(fù)戰(zhàn)爭(zhēng)年代“中國特色”的政工治廠(即“黨委領(lǐng)導(dǎo)下的廠長負(fù)責(zé)制”)模式。此后,企業(yè)管理就日趨混亂,“提倡算政治賬”,取消經(jīng)濟(jì)核算,“不計(jì)成本不計(jì)盈虧現(xiàn)象相當(dāng)普遍”,“無人負(fù)責(zé)和瞎指揮盛行”,甚至“有些單位把規(guī)章制度文件像土改中燒地契那樣燒毀”,“車間‘自由生產(chǎn)’;倉庫‘門戶開放’”,[12](pp.961-982)直到釀成三年“人禍”。以劉少奇、薄一波為代表的部分領(lǐng)導(dǎo)人后來力圖恢復(fù)一些“馬鋼憲法”的東西,1961年的《工業(yè)七十條》就是經(jīng)過力爭(zhēng)后的產(chǎn)物。薄一波認(rèn)為它雖然未能恢復(fù)“一長制”,但通過拒絕規(guī)定“車間、工段實(shí)行黨總支、黨支部領(lǐng)導(dǎo)下的車間主任、工段長負(fù)責(zé)制”,總算抵制了政工治廠的惡性發(fā)展。[12](p.964)從而為中國工業(yè)贏得幾年喘息時(shí)間。然而“四清”開始后,《工業(yè)七十條》就“被扔到一邊”,不用說恢復(fù)“一長制”,“就是黨委領(lǐng)導(dǎo)下的廠長負(fù)責(zé)制也受到‘左’的嚴(yán)重干擾”,被說成是“架空黨委”、“沒有跳出蘇聯(lián)‘一長制’的框框”。1965年“上海座談會(huì)”提出“割去廠長負(fù)責(zé)制這個(gè)尾巴”,學(xué)習(xí)軍隊(duì),實(shí)行政委制,“企業(yè)管理日益‘政治化’”,[12](p.981)終于導(dǎo)致“文革”中徹底的“運(yùn)動(dòng)經(jīng)濟(jì)”和“無計(jì)劃的命令經(jīng)濟(jì)”。
實(shí)際上,“文革”前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所謂路線分歧幾乎就是“鞍鋼憲法模式”還是“馬鋼憲法模式”、“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還是多少講點(diǎn)“計(jì)劃科學(xué)”的區(qū)別。眾所周知,在蘇聯(lián),改革前曾長期堅(jiān)持以計(jì)劃經(jīng)濟(jì)批判“市場(chǎng)社會(huì)主義”的教條傾向。而在中國,那時(shí)并沒有“市場(chǎng)社會(huì)主義”的問題,改革前20余年間不斷地“反對(duì)修正主義”,與其說是以計(jì)劃經(jīng)濟(jì)反對(duì)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毋寧說是以胡鬧的命令經(jīng)濟(jì)來反對(duì)理性計(jì)劃經(jīng)濟(jì)傾向。
當(dāng)時(shí)經(jīng)濟(jì)上的“反修”舉動(dòng),除了反對(duì)“三自一包”帶有“反市場(chǎng)”色彩外,其他如反對(duì)“消極平衡”,反對(duì)“條條專政”、反對(duì)“托拉斯化”、反對(duì)“一長制”與“管卡壓”,推行消滅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優(yōu)化配置的“五小工業(yè)”等等,都是反對(duì)理性計(jì)劃機(jī)制的。劉少奇、薄一波這些所謂“修正主義者”那時(shí)并沒有搞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念頭,他們只是想要多一點(diǎn)理性計(jì)劃經(jīng)濟(jì),少一點(diǎn)大轟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優(yōu)勢(shì)是主流,前者是劣勢(shì)是支流,在后者的進(jìn)逼下全無招架之功,何談“恢復(fù)”之力。根據(jù)薄一波的回憶,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東北)較多理性計(jì)劃的成分、1962-1964年間又有更弱的“恢復(fù)”嘗試外,連“八大”到“反右”之間、“四清”到“文革”之間這些一般認(rèn)為尚屬正常的年月,理性計(jì)劃亦無力推行。更何況反右、“大躍進(jìn)”與“文革”那些年月了。到了改革前的“文革”時(shí)代,薄一波式的“修正主義”實(shí)即計(jì)劃經(jīng)濟(jì)派徹底失勢(shì),中國經(jīng)濟(jì)完全陷入“命令破壞計(jì)劃”的非理性混亂之中。建設(shè)中盛行“邊勘測(cè)邊設(shè)計(jì)邊施工”,“首長工程”、“條子項(xiàng)目”大行其道。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規(guī)章制度”、“條條框框”都被砸爛,正如改革之初一篇著名社論所說:那時(shí)根本不把“計(jì)劃”當(dāng)回事,而是“用個(gè)人的喜惡來左右一切”,“于是,設(shè)計(jì)改來改去,壩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謬誤取代,科學(xué)為獻(xiàn)媚遮蔽。你要堅(jiān)持不同意見,那就是‘立場(chǎng)問題’、‘態(tài)度問題’,甚至是‘搞陰謀出難題’。不幸,這樣的事情,前些年在我們國家還是不少的”[13].因此不難理解:中國改革在相當(dāng)長的一個(gè)時(shí)期,不僅從引進(jìn)市場(chǎng)因素中獲益,而且實(shí)際上也從“恢復(fù)”蘇式計(jì)劃經(jīng)濟(jì)中獲益。在改革初期,后者甚至更為重要。這是東歐人不可能享有的獨(dú)特“優(yōu)勢(shì)”。鄧小平后來曾說:其實(shí),改革在1975年就開始了。“那時(shí)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qiáng)調(diào)把經(jīng)濟(jì)搞上去,首先是恢復(fù)生產(chǎn)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14]眾所周知,1975年的“整頓”并沒有任何“市場(chǎng)取向”的影子,而只是部分放棄了“運(yùn)動(dòng)經(jīng)濟(jì)”,部分恢復(fù)了被“文革”徹底“砸爛”的“修正主義”的即蘇式的經(jīng)濟(jì)管理,或者說減少一點(diǎn)“鞍鋼憲法”色彩,增加一點(diǎn)“馬鋼憲法”色彩,減少一點(diǎn)“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增加一點(diǎn)“計(jì)劃科學(xué)”。就這樣中國的經(jīng)濟(jì)頓時(shí)有了明顯的起色,“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而蘇聯(lián)東歐當(dāng)然完全不可能得到這種效果——他們?cè)缫咽前俜种俚摹榜R鋼憲法”了,還有什么可“整頓”的?他們已經(jīng)把理性計(jì)劃發(fā)展到“最優(yōu)化”的地步,繼續(xù)發(fā)展已無潛力。而要放棄“最優(yōu)化”,那代價(jià)是很大的。正如匈牙利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沙巴所說:東歐的前計(jì)劃經(jīng)濟(jì)運(yùn)行得相對(duì)成功,這使轉(zhuǎn)軌成為“一次痛苦的長征”。而“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則使得轉(zhuǎn)軌“成為一場(chǎng)愉快的郊游”![15]實(shí)際上,中國改革同時(shí)享有“引進(jìn)市場(chǎng)”和“優(yōu)化計(jì)劃”的雙重好處,雖然后者的比重漸小,但迄90年代仍未完全消失。那時(shí)中國一定程度上還在用“全國托拉斯化”的思路來解決重復(fù)建設(shè)、山頭經(jīng)濟(jì)的問題。例如近來的民航重組就是如此:90年代中期中國一度出現(xiàn)了多達(dá)44家獨(dú)立航空公司,比任何發(fā)達(dá)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國家都多,民航總局出面將其“重組”為實(shí)力大致均衡的國航、東航、南航三大集團(tuán)。對(duì)此,有人擔(dān)心行政性重組會(huì)開市場(chǎng)化的倒車,有人則譽(yù)為國家調(diào)節(jié)市場(chǎng)的凱恩斯主義杰作。實(shí)際上,此前的44家公司既非民營企業(yè),亦非按市場(chǎng)規(guī)則運(yùn)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承繼“文革”中“山頭經(jīng)濟(jì)”、“五小工業(yè)”、諸侯攀比的命令經(jīng)濟(jì)遺風(fēng)。民航總局的“重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與其說是“國家調(diào)控市場(chǎng)”的凱恩斯式成功,毋寧說是理性計(jì)劃糾正命令經(jīng)濟(jì)的成功。
如上所述,由于作為“現(xiàn)代性異化”的“計(jì)劃科學(xué)”與反現(xiàn)代性的命令經(jīng)濟(jì)有矛盾,前者因不滿后者而容易產(chǎn)生改革思想,蘇聯(lián)后期的這一邏輯在中國表現(xiàn)得同樣明顯。早期發(fā)動(dòng)改革的鄧小平、薄一波等人基本都屬于“文革”前的理性計(jì)劃派。只是他們遠(yuǎn)比蘇聯(lián)東歐的同道更不幸——改革前他們被整得無所作為,但因此他們也比蘇聯(lián)東歐的同道更幸運(yùn)——正因?yàn)檫^去理性計(jì)劃無所作為,改革后他們無論搞理性計(jì)劃還是搞市場(chǎng)化都能大有作為。而東歐同道們過去的成功恰恰成了他們?nèi)缃癖仨毟冻觥按鷥r(jià)”的原因。
「參考文獻(xiàn)」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c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J·希克斯。經(jīng)濟(jì)史理論[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7.
[3]A·P ·柯曼。作為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的帕累托[A].新帕爾格雷夫經(jīng)濟(jì)學(xué)大辭典:第三卷[M].北京:經(jīng)濟(jì)科學(xué)出版社,1992.
[4]E·羅爾。經(jīng)濟(jì)思想史[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1.
[5]蘇聯(lián)部長會(huì)議中央統(tǒng)計(jì)局。蘇聯(lián)國民經(jīng)濟(jì)統(tǒng)計(jì)年鑒:1959[M].北京:世界知識(shí)出版社,1962.
[6]李仁峰。蘇聯(lián)農(nóng)業(yè)統(tǒng)計(jì)資料匯編[M].北京:農(nóng)業(yè)出版社,1981.
[7]趙德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jīng)濟(jì)史:1967-1984[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8]汪海波。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yè)經(jīng)濟(jì)史[M].太原:山西經(jīng)濟(jì)出版社,1998.
[9]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cè)[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84.
[10]G ·I ·馬爾丘克。蘇聯(lián)1981-1985年及至1990年170項(xiàng)綜合目標(biāo)規(guī)劃概況[J].蘇聯(lián)科技參考資料,1983,(總13)。
[11]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94Book of the Year )[Z].Chicago :EncyclopaediaBritannica Inc.,1994.
[1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M].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13]再也不要干“西水東調(diào)”式的蠢事了[N].人民日?qǐng)?bào),1980-04-15.
[14]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為中華之崛起——紀(jì)念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80周年[OL].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019.htm.
[15]Laszlo Csab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China and EasternEurope Compared[J].Communist Economie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1996,8,(1)。
計(jì)師.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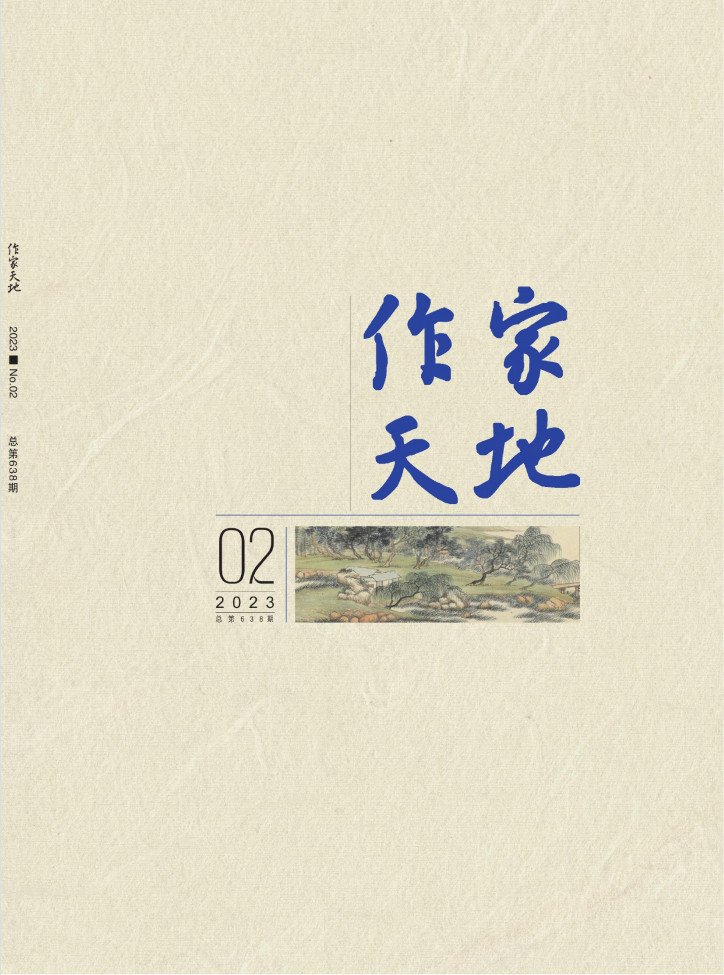
代英語.jpg)
.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