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格”農(nóng)村信用合作社,重構(gòu)農(nóng)村合作金融體系
佚名
摘要:本文認為,我國農(nóng)村金融改革應(yīng)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商業(yè)性、互助性金融組織并存的農(nóng)村金融服務(wù)體系為目標,實現(xiàn)這個目標的關(guān)鍵在于重構(gòu)農(nóng)村合作金融體系,“降格”現(xiàn)有的農(nóng)村信用社,把它改造為真正意義上的農(nóng)村合作金融組織,對于當前中國絕大多數(shù)農(nóng)村地區(qū)來說,這是一種最為現(xiàn)實的選擇!
關(guān)鍵詞:農(nóng)村,合作金融,信用社,重構(gòu)
\
2000年8月至2001年底,中國人民銀行在江蘇省進行了農(nóng)村信用合作社改革試點工作,這次改革的主要內(nèi)容是:把農(nóng)村信用社統(tǒng)一為縣級法人單位、成立省級聯(lián)社和組建農(nóng)村商業(yè)銀行。這種“上規(guī)模、上檔次”的改革即使在江蘇是成功的,但其在全國能夠推廣的范圍是極其有限的,因為這種改革只適用于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而我國目前如江蘇之發(fā)達的省份畢竟是少數(shù),所以這種改革不足以解決當前絕大多數(shù)農(nóng)村地區(qū)信貸方面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對于中國絕大多數(shù)農(nóng)村地區(qū)來說,農(nóng)村信用社不僅不能“上規(guī)模、上檔次”,而且應(yīng)該“降格”,使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農(nóng)村合作金融組織,以徹底解決農(nóng)村信用社在經(jīng)營管理、信貸業(yè)務(wù)等方面存在的“農(nóng)轉(zhuǎn)非”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實現(xiàn)國務(wù)院在《關(guān)于農(nóng)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提出的:“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為基礎(chǔ),商業(yè)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協(xié)作的農(nóng)村金融體系”的改革目標。
農(nóng)村合作金融的發(fā)展歷程昭示著農(nóng)民對合作金融的客觀需求
農(nóng)村分散的社區(qū)結(jié)構(gòu)和小農(nóng)經(jīng)濟格局客觀上要求農(nóng)民們在對抗大資本的艱苦歷程中要團結(jié)起來,事實上,無論在農(nóng)村還是在城市、在中國還是在外國,合作社都是弱勢群體對抗大資本的“自救性組織”,因此,為人民謀福利的政黨、政治家和理論家無不把合作社當作為人民謀幸福的重要工具。孫中山先生于1924年在宣講“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時指出:“合作社是由許多工人聯(lián)合起來組織的。工人所需要的衣服飲食,如果要向商人間接買來,商人便從中取利,賺很多的錢,工人所得的物品一定是要費很多的錢。工人因為想用賤價去買得好物品,所以他們便自行湊合,開一間店子,店子內(nèi)所賣的貨物都是工人所需要的。所以工人常年需要貨物,都是向自己所開的店子內(nèi)去買,供給便利,價格又便宜。到了每年年底,店中所得的盈利,便依顧主消費的多少分派利息。這種店子分利,因為是根據(jù)于顧主消費的比例,所以就叫做消費合作社。現(xiàn)在英國許多銀行和生產(chǎn)的工廠,都是由這種消費合作社去辦理。”晏陽初、梁漱冥等理論家則把孫先生的這種思想引向了農(nóng)村,他們分別在河北和山東創(chuàng)辦了中國最早的農(nóng)村合作社,雖然他們的試驗后來因戰(zhàn)爭原因而被迫終止,但是他們的行動為當時試驗地的農(nóng)民謀得了一定的福利,這是毫無疑問的。
中國共產(chǎn)黨使得農(nóng)民翻身解放的標志性制度建設(shè)之一是,繼承孫中山先生的“合作社思想”,于建國之初就在中國農(nóng)村普遍建立了信用社、供銷社和生產(chǎn)合作社等農(nóng)民“自己當家作主”的農(nóng)村合作經(jīng)濟組織。1950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在第一屆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確定了試辦農(nóng)村信用社的方針和任務(wù)。此后,農(nóng)村信用合作社在中國農(nóng)村紛紛建立,農(nóng)村信用合作社成立之初,大多采用“農(nóng)民入股、民主管理”的模式,農(nóng)民們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自己當家作主”的感覺。1954年2月人民銀行召開全國首次農(nóng)村信用合作社工作座談會,確定了發(fā)展信用合作社的方針、步驟和具體計劃。同年4月12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積極發(fā)展農(nóng)村信用合作》,為農(nóng)村合作金融推波助瀾。從此,農(nóng)村信用合作社走上了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正規(guī)化、法制化”的軌道。應(yīng)該承認,農(nóng)村信用合作社的建立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和農(nóng)村戰(zhàn)后經(jīng)濟恢復(fù)作出了極大的貢獻。但1955年3月中國農(nóng)業(yè)銀行成立后,農(nóng)村信用合作社“稀里糊涂”地接受了農(nóng)業(yè)銀行的領(lǐng)導(dǎo),農(nóng)民們開始感覺到自己的信用社已經(jīng)是“公家”的了。雖然直到1969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在天津召開的信用合作社工作座談會上仍然強調(diào)農(nóng)村信用合作社應(yīng)該是“貧下中農(nóng)管理;職工不脫產(chǎn),走亦工亦農(nóng)的道路。”但在此后的“一大二公”和“人民公社化”的滾滾潮流中,農(nóng)民們?yōu)榱恕案锩鼰o不勝”不得不自覺地“加強紀律性”,并慢慢理解了“民主管理”需要以“集中”為前提的深刻“革命”內(nèi)涵,而信用社也在農(nóng)民的“覺悟”中加快了“農(nóng)轉(zhuǎn)非”的步伐,先是信用社的信貸業(yè)務(wù)納入了銀行部門的“統(tǒng)一計劃”,信用社的“班子”接受黨的“一元化領(lǐng)導(dǎo)”,后是信用社的職工跳了“農(nóng)門”,領(lǐng)導(dǎo)有了“行政級別”,員工有了“商品糧戶口”,農(nóng)民們怎么看信用社也不象是自己的了。到1979年,黨為農(nóng)民們當初的“二元錢”股金“落實政策”時,農(nóng)民的感覺已不是驚喜,而是驚愕!
平心而論,從1969年農(nóng)村信用社全面“異化”到1979年我國全面改革開放的十年中,雖然農(nóng)村信用社和農(nóng)民有了一定的“感情隔膜”,但“取之于農(nóng)、用之于農(nóng)”的辦社方針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貫徹,為當時的“農(nóng)業(yè)學(xué)大寨”和“農(nóng)業(yè)機械化”作出了“貢獻”。而改革開放后,尤其是中央于1993年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戰(zhàn)略目標之后,農(nóng)村信用社也加快了“與市場接軌”的步伐,農(nóng)民和信用社的關(guān)系已不僅是“感情問題”了。
在“市場經(jīng)濟理論”指導(dǎo)下的農(nóng)村信用社一下子轉(zhuǎn)變成“經(jīng)濟人”,他們的業(yè)務(wù)操作變得越來越“理性”了,他們感到和分散的小農(nóng)們打交道的交易成本太高,于是“取之于農(nóng)、用之于農(nóng)”的辦社方針被“取之于農(nóng)、用之于城”的“發(fā)展戰(zhàn)略”所代替——信用社變成了農(nóng)村資金的“抽水機”了。以1993年為例,當年全國農(nóng)村信用社存貸款差額高達1153.4億元,其中農(nóng)戶存款3756.2億元,而農(nóng)戶得到的貸款僅有880.6億元。人民銀行合作司司長張功平同志于2002年初在介紹江蘇農(nóng)村信用社改革情況時表示:“截至2001年底,全國農(nóng)村信用社各項存款余額17263億元,占金融機構(gòu)存款總額的12%;各項貸款余額11971億元,占金融機構(gòu)貸 款總額的11%,其中農(nóng)業(yè)貸款余額4417億元,占金融機構(gòu)農(nóng)業(yè)貸款總額的77%。農(nóng)村信用社已成為我國農(nóng)村聯(lián)系農(nóng)民的重要金融紐帶和支持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經(jīng)濟發(fā)展的金融主力軍。”但仔細研究張司長這“鼓舞人心”的話語后我們發(fā)現(xiàn),農(nóng)村信用社這個“支農(nóng)”主力軍把他的63.1% (1-4417÷11971=63.1%)的貸款放在了“非農(nóng)部門”,而包括農(nóng)業(yè)銀行在內(nèi)的所有商業(yè)銀行對農(nóng)業(yè)部門的貸款僅有1319億元[(4417÷77%)×23%=1319]。溫鐵軍博士的最近研究則表明:“1985年以前農(nóng)戶貸款中絕大部分來自農(nóng)業(yè)銀行和信用社,1990年以后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占了40%左右。而1995-1999年下降為低于25%。”從各方面資料綜合來看,農(nóng)村無疑已成為資金的凈流出部門,而農(nóng)村信用社對此“功不可沒”。
農(nóng)民們不能不感到農(nóng)行和信用社是靠不住了。于是,1983年在黑龍江省的農(nóng)村誕生了第一個后來被稱為“農(nóng)村合作基金會”的農(nóng)村合作基金組織,在政府先默許后承認的政策下,此后這類農(nóng)民自發(fā)組織的“農(nóng)村合作基金會”雨后春筍般地在全國農(nóng)村建立、發(fā)展起來,到1992年全國已建立鄉(xiāng)(鎮(zhèn))級“農(nóng)村合作基金會”17400個,村級合作基金會112500個,分別占鄉(xiāng)(鎮(zhèn))總數(shù)和村總數(shù)的36.7%和15.4%;農(nóng)民們慶幸地想:自己的“銀行”總可以更直接、更方便地服務(wù)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了吧?事實也果真如此,自1990年至1996年,全國農(nóng)村合作基金會累計投放于種植、養(yǎng)殖業(yè)生產(chǎn)的資金達到1515億元;其中1996年投放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資金占其當年投放總額的比重高達43.3%,投放于農(nóng)村生活服務(wù)方面的資金占其當年投放總額的19.9%,這兩項支農(nóng)資金合計占其投放總額的63.2%,大大地高于農(nóng)業(yè)銀行和信用社支農(nóng)資金所占的比重。但好景不長,1999年1月,在“規(guī)范金融市場,整頓金融秩序”的旗幟下,國務(wù)院一個3號文件否定了農(nóng)民們在農(nóng)村合作金融領(lǐng)域的“二次創(chuàng)業(yè)”——“農(nóng)村合作基金會”關(guān)閉了。
然而,我們從農(nóng)民們的“二次創(chuàng)業(yè)”中至少得到兩方面的啟示,它一方面說明了農(nóng)村信用社已經(jīng)“異化”為不被農(nóng)民所信任的“虛假”合作金融組織,另一方面它又昭示著農(nóng)民對真正意義上的合作金融的客觀需求!
資金稀缺已成為農(nóng)村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重要制約
在農(nóng)村信用社和商業(yè)銀行的“離農(nóng)”傾向越來越嚴重、農(nóng)民的合作金融“二次創(chuàng)業(yè)”又被否定的情況下,農(nóng)民們的理性替代行為只能是“大力發(fā)展”民間借貸了,其結(jié)果是當今農(nóng)村高利貸盛行,農(nóng)村信貸環(huán)境進一步惡化。
當然,把農(nóng)村信貸環(huán)境惡化完全歸咎于農(nóng)村信用社也是不符合實際的,事實上,造成當前農(nóng)村資金稀缺的原因至少有四個方面。其一,四大國有商業(yè)銀行發(fā)展戰(zhàn)略向大中城市轉(zhuǎn)移,縣及縣以下的金融服務(wù)網(wǎng)點大幅度減少。據(jù)中國人民銀行統(tǒng)計,全國已經(jīng)削減1萬多個銀行分理處和其他營業(yè)網(wǎng)點,被削減的主要是各商業(yè)銀行縣及縣以下的營業(yè)機構(gòu)。其二,四大國有商業(yè)銀行實行了新的信貸授權(quán)制度,縣及縣以下金融機構(gòu)的信貸權(quán)限縮小,且各商業(yè)銀行都強調(diào)四個百:兩個百分之百(貸款手續(xù)的合規(guī)合法性和利息收回百分之百)兩個百分之九十八(本金收回和商業(yè)承兌匯票到期資金收回率百分之九十八),客觀上造成了農(nóng)村信貸投放力度減弱。有關(guān)研究表明,農(nóng)戶從正規(guī)金融機構(gòu)得到的貸款占其借款總額的比重從1985年以前的約40%下降到了1999年的24.4%。其三,郵政儲蓄部門只存不貸和國有商業(yè)銀行資金上存也是造成農(nóng)村資金向城市大量轉(zhuǎn)移的直接原因,據(jù)郵政儲匯局統(tǒng)計,全國郵政儲蓄額2000年增加761億元,2001年增加額超過1000億元,其中75%來源于縣及縣以下的郵政儲蓄機構(gòu)(直接來自農(nóng)村地區(qū)的占34%)。自1997年以來,僅廣西梧州地區(qū)的四大國有銀行即資金上存6.7億元(2001年11月末余額數(shù)),全國商業(yè)銀行的資金上存額可以想見。其四,隨著四大國有商業(yè)銀行退出農(nóng)村,農(nóng)村信用社成了農(nóng)村金融市場上孤軍奮戰(zhàn)的“支農(nóng)”力量,在現(xiàn)有體制下其“支農(nóng)”決心和能力都很有限。
面對商業(yè)銀行的日趨“商業(yè)化”和信用合作社的“不合作”,農(nóng)民們無可奈何地把他們的借貸希望寄托于民間借貸,圖一是根據(jù)溫鐵軍博士的研究結(jié)果繪制的趨勢曲線,該圖清楚
地表明,自1995年以來,農(nóng)戶的約七成借款來源于民間借貸,而且這個比重總體上呈上升趨勢,它從反面證明了農(nóng)村資金的稀缺和金融機構(gòu)“支農(nóng)”效率的低下。更為嚴重的是,伴隨著農(nóng)村資金供給的緊張,高利貸大量發(fā)生。以下是根據(jù)溫鐵軍領(lǐng)導(dǎo)的課題組對全國15個省份24個市縣的41個村落的調(diào)查資料整理所得的農(nóng)戶民間借貸利率分布表,表一表明月息1.5分以上的農(nóng)戶高利率民間借款占63.6%;容易計算,農(nóng)戶民間借款的平均利率為2.423分/月(平均利率=∑xf),即無論是從頻率分布還是從均值的角度來看,高利貸現(xiàn)象已經(jīng)在農(nóng)村普遍存在。而1999年有關(guān)部門對固定農(nóng)戶觀察點的跟蹤調(diào)查則表明,農(nóng)戶生活性借款的比重已經(jīng)達到了45.93%,高于生產(chǎn)性借款1.68個百分點,這說明許多農(nóng)民已經(jīng)借款度日了,這不能不使人聯(lián)想起解放前的“黃世仁”對“楊白勞”的高利盤剝。
我們可以根據(jù)科布——道格拉斯生產(chǎn)函數(shù)對當前農(nóng)村經(jīng)濟形勢作一個簡單分析,科布——道格拉斯生產(chǎn)函數(shù)的表達式為:
Y=A?Lα?Kβ
其中Y表示產(chǎn)出量,L表示勞動投入量,K表示資金投入量,α表示勞動力產(chǎn)出彈性,β表示資金產(chǎn)出彈性,A表示科學(xué)技術(shù)進步效果。對我國多數(shù)農(nóng)村地區(qū)來說,在小農(nóng)經(jīng)濟格局未改觀之前,科技進步對勞動力和資金投入的替代是緩慢的,我們可以假定A為不變因素;而我國農(nóng)村勞動力供給是過剩的,即L是不受制約的;對于一個國家來說,α、β在一定時期內(nèi)是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常數(shù),所以可以得出結(jié)論,我國農(nóng)村當前經(jīng)濟增長的關(guān)鍵因素取決于農(nóng)村資金供給的增長。遺憾的是,我們農(nóng)村經(jīng)濟發(fā)展的問題恰恰出在資金供給上,看到這一點,我們對農(nóng)村基層干部抱怨:“(農(nóng)業(yè)發(fā)展)思路是新的,口號是響的,任務(wù)是硬的,資金是‘軟’的。”就不難理解了!
農(nóng)戶民間借貸利率分布表(表一)
月利率(分/月) 組中值(分/月)x 比重(%)f xf
0——1.5 0.75 36.4 0.273
1.5——2.0 1.75 20.5 0.359
2.0——4.0 3.00 18.2 0.546
4.0以上 5.00 24.9 1.245
合計 —— 100 2.423
重構(gòu)農(nóng)村合作金融體系
國務(wù)院在《關(guān)于農(nóng)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指出:“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為基礎(chǔ),商業(yè)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協(xié)作的農(nóng)村金融體系”,很明顯,中央的意圖是要在農(nóng)村構(gòu)建政策性、商業(yè)性、互助性三種金融并存的金融服務(wù)體系,并用政策性金融帶動商業(yè)性和互助性金融。隨著糧、棉流通體制改革的深入,農(nóng)業(yè)發(fā)展銀行將逐步由糧、棉收購企業(yè)“跟班”的角色轉(zhuǎn)變?yōu)檗r(nóng)業(yè)開發(fā)性銀行,擔(dān)負起國家金融支農(nóng)的職責(zé);無論何時何地,包括農(nóng)業(yè)銀行在內(nèi)的商業(yè)銀行的逐利本性是不會改變的,也不能改變的,只要國家政策引導(dǎo)得當,使之“有利可圖”,他們自然會增添對農(nóng)村市場的興趣;難題在于如何“建立和完善” 互助性“合作金融”這個“基礎(chǔ)”,筆者認為,夯實這個基礎(chǔ)的辦法只能從“改造”現(xiàn)有的農(nóng)村信用社著手,“另起爐灶”或“消滅”、“升格”農(nóng)村信用社對中國絕大多數(shù)農(nóng)村地區(qū)是不可取的,“改造”的辦法就是“降格”農(nóng)村信用社——管理“降格”、規(guī)模“降格”、業(yè)務(wù)“降格”。
關(guān)于農(nóng)村信用社的管理問題,目前理論界普遍認為,問題的根源在于農(nóng)村信用社的產(chǎn)權(quán)歸屬不明確,應(yīng)該承認這是個問題,但筆者認為它并非問題的關(guān)鍵,問題的根源在于農(nóng)村信用社的管理模式背離了合作經(jīng)濟組織應(yīng)遵循的原則。況且,農(nóng)村信用社的產(chǎn)權(quán)一時難以到位,因此“理論家”們在這個問題上作過多的“理論”爭執(zhí)于事無補。合作經(jīng)濟組織自17世紀在歐洲興起以后,經(jīng)過300多年的發(fā)展,已經(jīng)形成了“自愿、互助、民主和非盈利性(或低盈利性)”等國際公認的組織原則。這些原則表現(xiàn)在合作經(jīng)濟組織內(nèi)部管理上就是“自治、自主、民主”,所以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落實中國人民銀行《農(nóng)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規(guī)定》中把農(nóng)村信用社建成“一種以鄉(xiāng)鎮(zhèn)為依托建立起來的社區(qū)性合作金融組織”的“社區(qū)性、合作性”精神,試想如果社員能夠自由翻看信用社的帳本、參與信用社的決策、決定信用社主任的任免和員工的待遇,那么信用社內(nèi)部管理混亂的發(fā)生率還會高嗎?在外部管理上,地方政府和金融監(jiān)管機構(gòu)應(yīng)充分尊重信用社的“自主性和民主性”,再不能把信用社辦成政府或銀行的附庸,人民銀行對信用社要加強金融監(jiān)管、弱化行業(yè)管理,不能象過去那樣以金融監(jiān)管為名行行業(yè)管理之實,而地方政府對信用社的日常活動則不要干預(yù)。若能如此,即使農(nóng)村信用社的產(chǎn)權(quán)虛置問題暫時得不到解決,農(nóng)村信用社的“社區(qū)性、合作性”也能得到很大程度的體現(xiàn),即只要把農(nóng)村信用社由“官辦”降格為“民辦”,信用社就一定會更象一個“合作社”!
在農(nóng)村合作金融組織規(guī)模大小這個問題上,目前有三種看法。一種意見是,農(nóng)村信用社統(tǒng)一升格為縣級法人單位,以增強信用社的實力、提高規(guī)模效益,以此作為信用社擺脫困境的突破口;這種意見即使是正確的,如前所言,它也只能適用于象江蘇、廣東這樣的農(nóng)村工業(yè)化程度很高的發(fā)達地區(qū)。另一種意見是,把現(xiàn)有的農(nóng)村信用社商業(yè)化,任其自生自滅,而以村為單位重建農(nóng)村合作金融組織,這種另起爐灶的想法理由是,“小規(guī)模”便于體現(xiàn)“社區(qū)性”、“參與性”和“合作性”;根據(jù)民政部和國家統(tǒng)計局的統(tǒng)計資料,全國現(xiàn)有村委會70萬個, 農(nóng)村住戶21455.74萬戶,平均每村306.5戶;全國農(nóng)村從業(yè)人員為56085.58萬人,平均每村801人,在山區(qū)和西部地區(qū)村均戶(人)數(shù)會遠低于全國平均數(shù)。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很清楚地告訴我們,這種規(guī)模已經(jīng)小到了合作金融組織難以發(fā)揮作用的程度了,況且,既然是“金融組織”就必須對其進行監(jiān)管,如此分散的小規(guī)模“金融組織”遍地開花,人民銀行豈不累死?因此這種想法也是不切實際的。還有一種意見是,維持現(xiàn)有的一鄉(xiāng)(鎮(zhèn))一社的格局不變;根據(jù)民政部的統(tǒng)計公報,全國農(nóng)村現(xiàn)有鎮(zhèn)政府(不包括城關(guān)鎮(zhèn)) 16124個,占全部鄉(xiāng)鎮(zhèn)個數(shù)的37.4%,每個鎮(zhèn)鎮(zhèn)區(qū)平均占地面積為2.42平方公里;即我國60%以上的基層政權(quán)是鄉(xiāng)政府,這些鄉(xiāng)政府的管轄面積遠大于鎮(zhèn)政府的管轄面積,一般來說,東部地區(qū)的鄉(xiāng)政府管轄面積有幾十平方公里,西部地區(qū)的鄉(xiāng)政府管轄面積則有上百平方公里、甚至幾百平方公里,即使農(nóng)村信用社在制度上已經(jīng)轉(zhuǎn)變?yōu)檎嬲摹昂献魃纭保r(nóng)民行程十幾公里甚至幾十公里去參與信用社民主管理恐怕很難激發(fā)農(nóng)民“當家作主”的熱情,民主管理難免流于形式。根據(jù)上面三種情況的分析結(jié)果,筆者建議將農(nóng)村信用社恢復(fù)到1992年以前的規(guī)模和布局。1992年農(nóng)村實行撤區(qū)并鄉(xiāng),每三個左右原來的“小鄉(xiāng)”(現(xiàn)在基層干部稱原來的“小鄉(xiāng)”為“工作片”,以下簡稱片)歸并為一個“大鄉(xiāng)”,相應(yīng)地幾個片的信用社歸并為一個鄉(xiāng)社,各片社則成為鄉(xiāng)社的分社或直屬營業(yè)點。顯然,采用一片一社的格局,規(guī)模比較適中,既能體現(xiàn)“社區(qū)性”,又便于“民主管理”;而且,各片社的機構(gòu)、人員、營業(yè)場地業(yè)已存在,有些地方至今仍采用“鄉(xiāng)社一級法人、分社分帳管理”的模式,在財務(wù)上也便于“分家”,所以,把“一鄉(xiāng)一社”“降格”為“一片一社”的難度不大。
在農(nóng)村信用社業(yè)務(wù)發(fā)展的問題上,一種比較流行的看法是,農(nóng)村信用社要拓寬業(yè)務(wù)范圍、發(fā)展中間業(yè)務(wù)和其他業(yè)務(wù),建立聯(lián)行清算,通過這種辦法來吸引客戶,提高效益,以便把農(nóng)村信用社“搞活”。筆者認為,持這種意見的人對“合作金融”的性質(zhì)還沒有正確的認識。合作金融是合作經(jīng)濟在金融領(lǐng)域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它是一種“會員制”,“會員”以金融資產(chǎn)的形式參與合作,目的是通過資金聯(lián)合使資金實力弱小者之間實現(xiàn)互助,其服務(wù)對象也主要集中在“會員”范圍之內(nèi)。合作金融的終極目標在于利用團體合作的方式,解決其單個“會員”不易解決的經(jīng)濟問題。簡單地說,合作金融組織是一種弱勢群體的互助、自救性組織。因此農(nóng)村信用社的任務(wù)不是要去和商業(yè)銀行競爭,它應(yīng)面對分散的“小農(nóng)”,最大限度地實現(xiàn)“小農(nóng)”群體內(nèi)部資金余缺的有效調(diào)劑,并和農(nóng)業(yè)發(fā)展銀行充分合作,充當農(nóng)業(yè)發(fā)展銀行在農(nóng)村服務(wù)農(nóng)民的的代理機構(gòu)。中國人民銀行規(guī)定農(nóng)村信用社“對本社社員的貸款不低于貸款總額的50%”,“貸款應(yīng)優(yōu)先滿足種養(yǎng)業(yè)和農(nóng)戶生產(chǎn)資金需要”,就是基于這種考慮。所以,“一存一貸”、代理農(nóng)發(fā)行的農(nóng)村業(yè)務(wù)就是農(nóng)村信用社的中心工作,也就是它的市場定位。為農(nóng)業(yè)、為農(nóng)村經(jīng)濟發(fā)展提供金融支持的任務(wù)應(yīng)由農(nóng)業(yè)發(fā)展銀行和農(nóng)業(yè)銀行去承擔(dān)。農(nóng)村信用社不必為自己不是“銀行”而感到難過,相反,它應(yīng)該盡可能地把它現(xiàn)有的“銀行業(yè)務(wù)”“降格”為“合作社”業(yè)務(wù)!
為了把農(nóng)村信用社“降格”為真正意義上的農(nóng)村合作金融組織,還應(yīng)該做好下面幾方面的工作。首先,在法律上把合作金融和商業(yè)銀行擺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我國商業(yè)銀行已經(jīng)有了《商業(yè)銀行法》的保護,合作金融也應(yīng)當像商業(yè)銀行一樣擁有獨立的法律保障,要盡快出臺《合作金融法》,通過立法,明確農(nóng)村信用社的制度、機制和運作方法。其次,農(nóng)村信用社現(xiàn)有不良資產(chǎn)的形成具有與四大國有商業(yè)銀行類似的歷史原因和體制性因素,現(xiàn)在國有商業(yè)銀行已經(jīng)由國家成立托管機構(gòu)、將其不良資產(chǎn)剝離,農(nóng)村信用社也應(yīng)享受同等待遇,這不僅是為了體現(xiàn)公平,而且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促使農(nóng)村信用社重組、改造、規(guī)范和輕裝前進,或者說這是農(nóng)村信用社改造為真正意義上的合作金融組織的一個重要前提。最后,還必須特別強調(diào)指出,“搞活”農(nóng)村信用社的辦法不是鞭策農(nóng)村信用社積極參與市場競爭,而是要在法律上把它界定為非盈利組織;信用社由于規(guī)模小,必然經(jīng)營成本高,現(xiàn)在信用社各項存款利息支出加上管理費用,每一百元就要支付2.95元,比商業(yè)銀行高出1.5至2.2個百分點。政府目前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允許農(nóng)村信用社貸款利率參照商業(yè)銀行貸款利率上浮40—50%,這顯然不是“支農(nóng)”,而是“坑農(nóng)”了。在美國這樣極端發(fā)達的國家,農(nóng)民已經(jīng)由過去的“小農(nóng)”變成今天的“地主”了,但《聯(lián)邦信用社法案》仍然把他們的農(nóng)村信用社定為非盈利組織,免繳營業(yè)稅。我們發(fā)展中國家就更沒有理由不“參照執(zhí)行”。而且,加入WTO后,對農(nóng)村合作金融組織財政政策傾斜——“間接”支農(nóng)比“直接”財政補貼更容易為貿(mào)易國所接受,更何況我們長期以來的“支農(nóng)補貼”大量沉淀于流通領(lǐng)域,農(nóng)民并未真正得到多少實惠!
筆者堅信,“降格”農(nóng)村信用社即使不是重構(gòu)農(nóng)村合作金融體系的最佳選擇,起碼也是一個不壞的選擇!
①溫鐵軍 《我國農(nóng)村普遍發(fā)生高利貸的問題、情況與政策建議》 中國鄉(xiāng)村網(wǎng) 2002年3月22日
②戴根有 《關(guān)于農(nóng)村金融體制的幾個問題》 金融時報 2001年11月17日
③徐諾金 《農(nóng)村金融服務(wù)體系的構(gòu)建及農(nóng)信社的改革方向》 金融時報 2002年1月21日
④民政部 《2001年民政事業(yè)統(tǒng)計公報》
⑤全國農(nóng)業(yè)普查辦公室 《關(guān)于第一次全國農(nóng)業(yè)普查快速匯總結(jié)果的公報》第3號
⑥全國農(nóng)業(yè)普查辦公室 《關(guān)于第一次全國農(nóng)業(yè)普查快速匯總結(jié)果的公報》第4號
機.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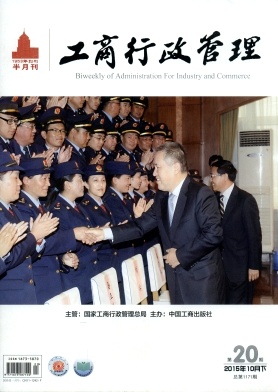
經(jīng)濟.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