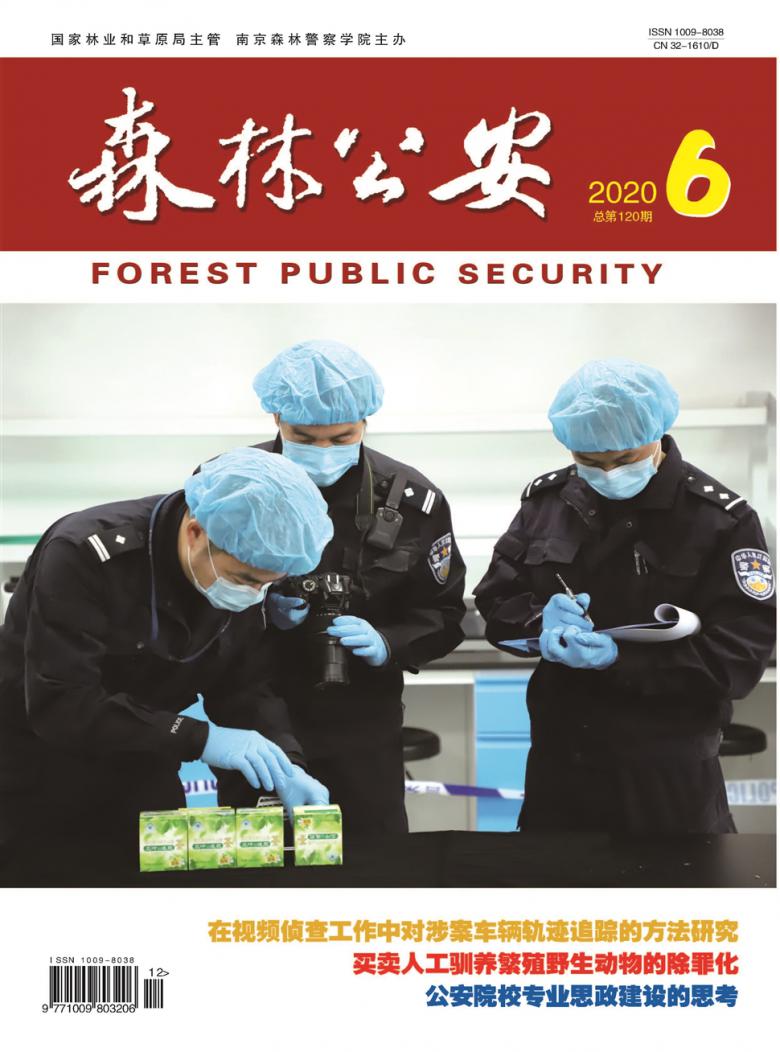近代交通運輸與晚清商業(yè)的演變
佚名
我們知道,商業(yè)作為專門從事商品流通活動的獨立部門,是商品交換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在再生產過程中是一個不可缺少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對生產和消費起著橋梁與紐帶的作用。這種性質,決定了商業(yè)與運輸業(yè)的聯系十分緊密,可以說“商業(yè)是交通的先導,交通是商業(yè)的基礎”。雖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環(huán)境下,作為近代交通運輸工具的鐵路和輪船,其出現并非是社會經濟發(fā)展的產物,輪船是資本主義列強強行引進的,在中國首先出現的也是外國輪船公司。鐵路絕大部分靠借外債修筑,有相當部分控制權不在中國人手中。但它們的出現,仍然是晚清中國社會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國交通運輸業(yè)在近代的巨大轉折和變化。雖然到清朝結束時的1911年,這種新式交通工具的數量還很有限, 相對于中國遼闊的土地及人口,遠遠不成比例,分布也不盡合理。在經營管理以及其它方面,還受到諸多方面因素的制約。但它們的出現,已經初步展示了這種新式生產力的威力,對晚清中國的商業(yè),也顯示出越來越明顯的沖擊作用并產生了深遠的。
鐵路輪船進入中國后引起的反響是多方面的。本文僅從進出口貿易、農產品商品化、新興市場的開拓和近代城市的興起等幾個方面,對鐵路輪船與晚清商業(yè)間的關系進行一下初步的考察。
1. 進出口貿易的變化
中國近代交通運輸工具鐵路和輪船對晚清商業(yè)的影響,主要表現在1895年后。這是因為1895年前,中國全國擁有的鐵路,僅僅只有微不足道的364公里,只是在甲午戰(zhàn)爭中敗于日本之后,興辦實業(yè)救國救亡的熱潮,才使中國興起了修建鐵路的第一次高潮。幾條較長的干線如東清、膠濟、滇越、京漢、粵漢、津浦、滬寧、京綏鐵路均在這一時期開始興建, 即使這樣,1911年清朝統(tǒng)治結束時中國的鐵路也只不過才有9618公里。 輪船也是如此,1895年前,清朝政府并沒有開放民間自由興辦輪船公司的禁令,除清政府批準的輪船招商局以外,很難舉出其它的華商輪船公司。1895年時,中國的輪船只數大小一共只有145只32708噸。此后,馬關條約的簽訂使帝國主義的輪船得以進入中國內河,清朝政府才被迫取消了華商開辦輪船公司的禁令。這樣,1911年時中國的輪船只數才上升到901只90169噸。 因此,近代鐵路輪船對商業(yè)方面的影響,從1895年以后比較明顯,我們的考察,也主要從這里開始。
下面,我們先看看這期間進出口貿易的統(tǒng)計情況:
表1 中國對外貿易數值及其指數(1895-1911年) 單位:1000海關兩
年份|出口凈值|進口凈值|總值|貿易總值指數
1895|143293|171697|314990|100
1896|131081|202590|333671|105
1897|163501|202829|366330|116
1898|159037|209579|368616|117
1899|195785|264748|460533|146
1900|158997|211070|370067|117
1901|169657|268303|437960|139
1902|214182|315364|529546|168
1903|214352|326739|541091|172
1904|239487|344061|583548|185
1906|236457|410270|646727|205
1907|264381|416401|680782|216
1908|276660|394505|671165|213
1909|338993|418158|757151|240
1910|380833|462965|843798|268
1911|377338|471504|848842|269
說明:貿易總值指數為筆者。
資料來源:鄭友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發(fā)展》,上海社會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335-336頁。
從這個統(tǒng)計表中可以看出,1895到1911年,中國不管進口還是出口的貿易數值,都呈直線上升的趨勢,進出口貿易總值16年中增加了二倍多。在貿易數值的迅速增長中,表1未能反映出來的是進出口商品的結構也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從下面的進出口貨物分類結構變化表中可以明顯的反映出來。
表2 1873-1910年中國進出口貨物分類變化表 單位:千元
年份|進口貨物|出口貨物
|生產資料| 消費資料| 農產品| 礦產品|半制成品制成品
|值| %| 值| %|值| %|值| %|值| %
1873|8383|8.1|95104|91.9|2866|2.6|—|—|105572|97.4
1893|19733|8.4|216090|91.6|28423|15.6|—|—|153290|84.4
1903|76582|15.0|432477|85.0|89496|26.8|1563|0.4|242902|72.8
1910|126948|17.6|594351|82.4|231957|39.1|4416|0.7|356964|60.2
說明:“半制成品和制成品”主要指絲、茶和一些手工業(yè)品。
資料來源:根據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tǒng)計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72頁表14、表15重新計算編排。
從這張表進行觀察,在進口各項貨物的變化中,生產資料的數值和比例在逐步增長,但增長的幅度均不大。消費資料的進口雖然所占比例數在逐漸減少,但絕對進口數卻呈明顯的增長。在出口貨物中,礦產品的出口數量微不足道,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出口數值有一定的增加,但在出口貨物總值中所占的比例卻呈減少的趨勢。只有農產品的出口,不管絕對數值還是所占指數,增長幅度都十分驚人。1873年時,農產品的出口數值只有286.6萬元,在出口貨物總值中僅占微不足道的2.6%,此后迅速增加,1893年增加到2842.3萬元,占出口總值的15.6%,1903年進一步增加到8949.6萬元,占出口總值的26.8%,1910年更猛增到23195.7萬元,占到出口總值的39.1%。1910年與1903年相比,7年之間農產品出口數值增長2.6倍。與1873年相比,增長更達80.1倍之多。在各項出口貨物中增長的幅度高踞第一位。農產品的出口之所以增長如此之快,與鐵路輪船即近代交通運輸工具在這期間的發(fā)展有著根本的關系。因為,這期間的農產品,還只能作為原料品出口,鐵路輪船的發(fā)展,大大縮短了內地到通商口岸的運輸距離和時間,降低了運輸費用,使一些量大價賤、容易腐敗破損的農產品的長途運輸成為可能。因而使得許多過去無法出口的農產品成為出口貨物。而且,農產品的出口結構也因運輸工具的變化而發(fā)生了重大變化。1895年即甲午戰(zhàn)爭前的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國最主要的出口農產品是茶葉、生絲和絲織品。七十年代,這三項土貨的出口數值占整個出口額的90%左右,1892年仍占62.5%。 其它農產品雖有出口,但數量有限,而且產地需在口岸附近才有可能。二十世紀開始后,隨著鐵路干線的修筑和輪船運輸的發(fā)展,這種狀況有了明顯的變化。表3選擇的8種主要農礦產品1871-1911年的出口統(tǒng)計數字,就反映了這四十年中出現的變化。
表3 1871-1911年8項主要農礦產品出口統(tǒng)計 單位:公擔
年代|茶|絲|大豆|豆餅|花生|棉花|豬鬃|錫
1871-73|1022159|37529|57506|—|—|8486|—|—
1881-83|1238145|39345|84760|—|—|17473|—|—
1891-93|1055064|59946|760522|—|—|290417|—|—
1901-03|877899|69292|1348622|2062384|—|367898|21056|—
1909-11|911629|80424|7338488|5614669|430199|556152|31588|56939
資料來源: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tǒng)計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74-75頁表17。
從表中看,進入二十世紀后,過去傳統(tǒng)的出口農產品中,絲的出口數量有所上升,但幅度并不大。茶葉的出口數量卻在此前大幅跌落的基礎上繼續(xù)跌落,1903年與1883年相比,20年中減少36萬多公擔。但是,此期棉花大豆等農副產品的出口卻代替了傳統(tǒng)的絲茶地位,出現了大幅的增長,尤其是大豆的出口增長幅度十分驚人,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的不滿6萬公擔增加到1911年的733萬多公擔,增長127倍多。棉花也從同期的8486萬公擔增加到55萬多公擔,增長65倍多。過去沒有出口記載的花生、豬鬃和錫等農礦產品,此期也開始對外輸出,而且在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扮演了重要的出口角色。
這種狀況,在通商口岸特別是有鐵路深入內地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寧波、漢口、廣州、天津、大連、安東、青島等城市,表現的尤為突出。上海1900年的出口貿易額為7800萬兩,后因滬寧、滬杭甬鐵路相繼修成通車,大大促進了棉花和蠶繭等的生產和輸出, 1910年上海的出口額已增至17800萬兩。1900年廣州的出口額僅1900萬兩,在廣三、廣九兩鐵路通車后,出口額即增至1910年的5400萬兩。鐵路的修建對漢口和華中地區(qū)的出口貿易影響更為明顯。1904年漢口的輸出額不過714萬兩,1905年京漢鐵路通車,再加上湖南等地開辟內河輪船航運,華中地區(qū)的農產品等土貨出口情況為之一變。過去出產不多或難以外運的棉花、芝麻、大豆、花生、桐油、禽蛋、牛羊皮、生漆等等內地土貨,在出口貿易中越來越占著重要的地位。過去,漢口以“茶港”聞名中外,出口土貨中茶葉一直占居首位。但到1909年,芝麻的出口值已經超過茶葉。1910年,漢口的出口總值已增加到1790萬兩。 華北地區(qū)的主要港口城市天津,由于京奉、津浦等鐵路的修筑,特別是京綏鐵路京張段的修建,出口土貨的來源顯著擴大。直隸、山東、山西的棉花和別的農產品,紛紛集中天津外運。京綏鐵路京張段完工后,山西北部的亞麻、小麥、內蒙地區(qū)的雜糧、羊毛等產品源源運往天津出口,天津的出口貿易額迅速擴大。據說京張線營運后,天津出口額“于一年之中驟增數百萬”。
鐵路輪船的發(fā)展,除了推動進出口貿易的增長外,也大大帶動了國內貿易的發(fā)展。使得商品的運銷范圍和市場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觀。劉克祥在“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鐵路沿線地區(qū)的農產品商品化”一文中對這種情況作了很多描繪。如河南安陽的棉花,在火車未通時,僅由小車或馬車運銷到鄰近的衛(wèi)輝、懷慶以及開封、許昌一帶。此后由于鐵路的修建和機器棉紡織業(yè)的發(fā)展,安陽棉花除部分供應該地廣益紗廠外,其余北銷天津、石家莊,東至青島、濟南,南運鄭州、漢口,轉銷上海。其流通范圍之廣,“已非往昔之局促于本省者可比”。價賤量大的糧食,流通范圍的擴大更是有賴于鐵路和輪船的運輸。過去只供生產者自用或就近銷售的鮮果、蔬菜、禽蛋、魚蝦等農副產品,流通范圍也明顯的得到擴大。如河北唐山、昌黎離天津并不遠,但直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這一帶捕撈的魚鮮,還難得運銷到天津出售。自京奉鐵路通車后,那里的魚鮮即迅速進入天津銷售。 河南新鄉(xiāng)的西瓜,自“火車通行,銷路益遠”。奉天北鎮(zhèn),“昔年多種菜蔬,僅銷境內,近年交通便利,運銷外縣者甚夥”。廣西桂平一帶,自從西江輪船通行,“土物出境倍易于前,山間物產外銷,獲利不少,而家畜雞豚亦各載之舟中,隨大江東去,售諸港粵,日月不休”。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甲午戰(zhàn)后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加深和帝國主義侵略方式的變化,在鐵路不斷修建和輪船不斷發(fā)展的同時,一方面,是農副產品的出口持續(xù)增長和國內農產品市場的擴大,另一方面,如上表所示,國外工業(yè)產品和各種消費品的進口數額,也在持續(xù)增長中,并隨著鐵路輪船而運銷到廣大內地,沖擊和改變著傳統(tǒng)的中國商業(yè)和經濟結構。而這種變化的體現之一,就是農產品的商品化趨勢明顯增強。
2. 農產品的商品化和產業(yè)的專門化
在以鐵路輪船為主干的近代交通網的作用下,通商口岸城市和廣大內陸腹地的聯系大大加強,農產品的長途運銷和進出口貿易的增長,使許多農副產品的國內國際市場得以擴大。這種商品交換和市場機制通過鐵路輪船的傳導,帶來的必然后果就是作物的商品化和產業(yè)的專門化。在作物的商品化方面,鐵路和輪船航道沿線地區(qū)的棉花、大豆、花生、芝麻、桐油、麻類、禽蛋、牛羊皮的出口大大增加就是明顯的表現之一。其中,經濟作物的產量快速增長表現的最為明顯。這里僅以棉花和大豆的情況為例,簡述如下:
1、棉花 棉花是鴉片戰(zhàn)爭前后已有相當發(fā)展的一項重要經濟作物,原來主要產于江浙閩粵等南方地區(qū),十九世紀初開始向黃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區(qū)推廣。甲午戰(zhàn)爭以后,南方和北方的種植面積都有了更快的發(fā)展。但無論南方還是北方,最重要的商品棉產區(qū),大都在通商口岸附近和鐵路沿線及輪船通行的河流兩岸。例如,這時期以漢口、沙市為中心的京漢、粵漢鐵路沿線和長江、漢水流域地區(qū),棉花種植的推廣和商品化的擴大就十分明顯。1898年,匯集到漢口的棉花只有702擔,還不夠本地之用,反要通過上海輸入通州棉花四萬擔。此后隨著京漢、粵漢鐵路的修筑和湖南輪船運輸的發(fā)展,棉花的產量迅猛增長,匯集到漢口的棉花,也以湖北、湖南和河南三省生產的為中心,其中又以湖北產的占其大半。1901年已可輸出24397擔,1902年增長到133361擔,1903年又增長到332102擔,京漢鐵路全線通車前夕的1904年,更增加到399720擔。而總生產額則估計“當為百萬擔內外”。 山東也是同樣,隨著膠濟、津浦鐵路的修建,鐵路沿線的棉花種植迅速增長。據日本人的調查,1914年山東植棉面積365萬余畝,棉花總產10724萬余斤,其中鐵路沿線州縣的植棉面積為269萬余畝,棉花產量8575萬余斤,分別占總數的74%和80%。
2、大豆 大豆是我國的特產,很早就作為城鄉(xiāng)居民的廉價高營養(yǎng)食品和照明用料而廣為種植。
制成品有豆面、豆腐、豆油、豆醬、豆餅等等,長期以來以自給性消費為主。二十世紀初,歐美和日本等先進工業(yè)國家發(fā)現了大豆在食品和化學工業(yè)方面存在著廣泛用途。它們利用豆油工省價廉的優(yōu)點,經過提煉精制,取代橄欖油和棉籽油,充當人造豬油、人造牛乳的原料,普通豆油則用來代替亞麻仁油,制作油漆、涂料,也用來制造肥皂。豆餅原來只用作肥料和牲畜飼料,二十世紀初,歐美和日本利用豆餅中豐富的蛋白質含量,用來制作豆粉,加在面粉中烘制面包。又用來制造醬油和味精。這樣,大豆的市場需求成倍增長,迅速成為世界性商品。1908年,日本三井會社把東北大豆輸往英國,大受歡迎。歐洲各國商人亦爭至東北搜購,因而其利益明顯,種植益多。原來主要種植小麥的東北,很快就發(fā)展成為中國和世界著名的大豆產地, 可以說,整個東北,幾乎到處都有大豆種植。在鐵路和輪船航道的沿線地區(qū),發(fā)展則尤其迅速。如奉天的沈陽,大豆為“出產大宗,占輸出品巨額”。遼陽農作物中,“首推大豆”。撫松大豆“出產最多”。通化大豆“居五谷之首”。安東、鐵嶺“無處不宜豆”,實為出產大宗。吉林雙城,“有地皆種,十歲九稔”。農安1914年的大豆播種面積,據說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 顯然,在這里,鐵路和輪船的發(fā)展對于大豆種植的迅速擴大和出口的增加,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以漢口為中心的漢水和長江平原,是豆類的又一集中產區(qū),“其產額頗大”,“每年僅輸出之豆類,不下三百萬擔”。據統(tǒng)計,1902年時,漢口輸出的豆類為49萬擔左右,僅僅過了四年,1905年就增長到288萬擔左右。 無疑,這與1905年京漢鐵路全線通車有著直接的關系。據日本當時駐漢口總領事水野幸吉觀察,京漢鐵路通車初期,湖北和河南之間的商品流向主要為,“由河南則專輸送麥、黃豆、芝麻、牛羊皮、藥材、煙葉等于漢口,由漢口則輸送海產物、石油、棉紗、支那紙、棉布類、其它雜貨于河南”。又由湖北沿路地方“送棉花于榷山堰城地方者甚多,一年可預測為五六萬包以上。”據他估計,由湖北、湖南、河南和四川陜西水陸兩路匯集漢口進而輸出的農產品價值,“每年實不下三千萬兩”,但將來若“川漢鐵道、粵漢鐵道開通”,“大約可至七八千萬兩”。 近代交通運輸業(yè)發(fā)展對農產品商品化產生重大推動作用的狀況,于此可見。
鐵路輪船對產業(yè)專業(yè)化的推動作用,這里可以舉定縣和高陽的土布業(yè)為例加作說明。
所謂土布,是指農村以舊式生產工具制成的棉織品。定縣的土布業(yè)在光緒初年即已起步,1892年銷往外地的土布數量已達60萬匹,主要的銷場為西北一帶。 此后,隨著京漢鐵路的修筑,定縣土布的出口量隨之增長,其增長的情況可見表4:
表4 1900-1911年定縣土布輸出西北各地的數量和價值
年代|匹數|價值(元)|年代|匹數|價值(元)
1900|850000|595000|1906|1250000|1000000
1901|890000|623000|1907|1350000|1080000
1902|950000|665000|1908|1450000|1160000
1903|980000|784000|1909|1800000|1350000
1904|1100000|880000|1910|2000000|1500000
1905|1200000|960000|1911|2600000|2028000
資料來源:張世文《定縣農村工業(yè)調查》頁113。轉引自彭澤益編《中國手工業(yè)史資料》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二卷,第424頁。
1899年,京漢鐵路修到定縣,此后定縣的土布輸出年年上升,1911年與1900年比,11年中增加175萬匹,價值增加143.3萬元。顯然,定縣土布輸出數量的迅速增長,與京漢鐵路通車后原料輸入和產品輸出更方便,市場更加擴大分不開。定縣土布輸出數量的迅速增長,反映出來的另一面事實是農村從事這一勞動的人數在增長。據調查,織土布是定縣最重要的經濟活動。該縣東不落岡村,1892年從事土布紡織業(yè)的有92戶,1912年達130戶。全縣從事織土布的村莊比例相當大,占全縣的83%。而且,定縣農家的土布制作,絕大部分是為市場進行的生產。以定縣的第三、第六兩區(qū)來說,自用的布匹只占全部生產總值的0.36%, 余皆推入市場。這種狀況,說明定縣的土布制造受京漢鐵路的影響,專業(yè)化的程度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了。
高陽的土布織造業(yè)比定縣興起稍晚,但發(fā)展很快。二十世紀初,因機紡洋紗的大量輸入和足踏鐵輪紡機的引入,地理位置與京漢鐵路和原料產地天津均靠近的高陽,土布織造業(yè)在原有基礎上得到迅速發(fā)展,不僅很快成為凌駕定縣地位之上的土布織造業(yè)中心,還出現了專業(yè)化分工的明顯趨勢。這種趨勢正如吳知在“鄉(xiāng)村織布工業(yè)的一個”一文中所敘述的,分別表現在以下幾方面:A、專業(yè)紗布商人的興起。在洋紗和鐵輪機輸入以后,因為布匹產量和原料消費量大有增長,進行紗布貿易又“獲利甚厚”的緣故,因而“以販賣紗布為業(yè)的一批布商,乃應運而生”。這些紗布商的業(yè)務包括從天津販入洋紗和織機;收買或以紗換取農民織造的布匹;將布匹運往外地銷售牟利等三方面。民國初年,這種布商在高陽已“不下二十家之多”。B、高陽附近各自分立的若干土布區(qū)域,逐漸形成以高陽為中心的一個大的體系。由于洋紗和鐵輪機取代土紗和木機,高陽商人乘機在過去各土布交易中心如青塔、莘橋、大莊等處設立分號推銷棉紗,收購布匹。并進而出現把棉紗賒給農民織布,再把布匹收回結帳的中間商號。高陽也逐漸成為“附近各織布區(qū)域的原料散出和出品集中的中心,于不知不覺中把各區(qū)域維系起來,成為以高陽為中心的一大體系”。C、織布農民和布商間的關系,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即出現了農民從商人處賒取棉紗,替商人織布而賺取工資的雇傭關系。這時候,農民雖仍在自己家內用自己的工具織布,但已發(fā)展成為受商人的監(jiān)督而受雇于商人的雇傭關系,在性質上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 總的來說,定縣和高陽成為織布業(yè)的中心,專業(yè)化發(fā)展越來越明顯的情況,是由多種內外因素相互影響促成的,但鐵路輪船等近代交通工具的發(fā)展在其中發(fā)揮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則是無可置疑的。
3. 近代交通工具鐵路輪船與市場開拓的關系
馬克思曾說:“資產階級社會的真實任務是建立市場,(至少是一個輪廓)和以這種市場為基礎的生產”。而“交通運輸業(yè)的變革,是奪取國外市場的武器”。 西方資本主義列強進入中國后,攫奪中國的內河航行權和鐵路修筑權,始終是其爭奪中國資源、傾銷本國商品、開辟新的市場的重要政策之一。他們通過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方式,把內河航行權一步步攫奪到手。長江航行權的被攫奪過程就十分有代表性。1842年的南京條約,列強攫取到沿海航行權和長江出海口上海的航行權。1858年的天津條約,規(guī)定開放長江沿岸的鎮(zhèn)江、南京、九江和漢口為通商口岸城市,列強攫取的航行權亦隨之從上海延伸到長江中游的漢口。1876年的煙臺條約,又規(guī)定增開蕪湖、宜昌為通商城市,外國在長江的航行權又進一步延伸到宜昌。1895年的馬關條約進一步規(guī)定開放沙市、重慶、蘇州、岳州為開埠通商城市。這樣,除長江干流的航行權被列強延長到四川的重慶外,還使外國輪船打破了過去不得駛入內河的禁令,使其得以沿吳凇江經運河駛入蘇州和杭州。與此同時,列強還取得了土貨航運權和內地通商權等一系列特權,打開和取得了通向中國廣大內地市場的通道。列強在步步獲取中國內河航行權的同時,攫取中國鐵路修筑權的活動也始終沒有停止過。例如,英國商界的“主要的野心是要使中國進入鐵路,一半是為有投資場所,一半是為深入內地市場”。 因此,英國除了在內地與列強激烈爭奪鐵路修筑權外,還“非常關心建筑一條由仰光到云南的直達鐵路,來打開進入中國的后門”,并為此“擬定了各種計劃”, 準備通過進入中國內地的這條大西南鐵路,一方面與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利益相結合,另一方面與法國在中國南部和越南的擴張勢力相對抗。
列強極力攫取中國的內河航行權和鐵路修筑權的事實,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近代交通運輸工具鐵路和輪船在開拓市場,攫取商業(yè)利潤和擴展列強勢力方面的巨大作用。這種作用,在作為落后農業(yè)大國,同時又國勢孱弱,缺乏先進生產力的中國,表現的尤其明顯。這一點,19世紀60年代在長江輪船航運中起過重要作用的美國旗昌輪船公司的主要人物金能亨,對長江航運客貨運業(yè)務利益所作的一個調查就很有代表性。他在經過一番調查后認為,長江的“營業(yè)額幾乎是難以估計的……,即以原棉一項而論,估計長江流域的產量便大大超過美國全國的產量。中國國內貿易的運輸量姑且置之不論,單以外國人經手的貨運而言,其數量便十分可觀。湖南、湖北的茶葉有500多種規(guī)格,在供應市場時,……肯定還得順長江而下,僅以兩湖茶葉而論,總量便估計有7萬噸。凡熟悉中國貿易的人都十分清楚,繼7萬噸貨物之后,還有更多的生意可做”。在回程販運貨物方面,金能亨估計,“回程貨運量同樣是巨大的。在漢口出售的外國棉織品,估計一開始就會達到2.5萬噸”,而“這些棉織品只占上海總進口量的一小部分”。 事情確實如此,當取得長江輪船航行權后,外國輪船商在所從事的輪船航運業(yè)中,都賺到了高額的利潤。就拿金能亨的美國旗昌輪船公司來說,1867年這一年,“純利潤就高達806011兩”,其中“單以往長江上游裝運棉花而論,便為該公司掙得毛利約24萬兩”。 美國公司如此,英國公司也如此,“大英輪船公司的董事們同中國的交易全是史無前例的最賺錢的買賣,單就上海的絲這一項來看,今年(1860年)完全有可能達到5萬件。絲的運費是每件白銀10兩,總數就是50萬兩,合英鎊十六萬二千五百鎊!!!”
除了攫取巨大的商業(yè)價值外,利用鐵路輪船開拓中國內地市場,同樣是列強注目和爭奪的焦點之一。攫取長江上游航行權進而打開四川省乃至更廣大的西南內地市場,就是典型的一例。例如,1871年在英國樸內茅斯召開的商會聯合會上,就有不少商人提議,“為了促進對華貿易,要說服(英國)政府在下次修訂條約時,為英國商人取得通過長江進入中國腹地(的權利)”。 1872年,商會聯合會又寫建議書“要求揚子江上游對外國輪船開放,以便中國最富足勤勉的一省(四川)…可以直接與歐洲交通”。 而1878年宜昌口的商務報告則認為,“如果不在最短期間出現足夠噸位的輪船供應本埠的全部貿易和通過本埠的對四川的貿易,英國商人便會大大改變這種狀況,增置輪船。”因為“輪船運輸的收益絕非該業(yè)的唯一利益,它還附帶給予湖北省西部的生產事業(yè)以新的刺激。” “漢口與宜昌之間輪船航運的最大優(yōu)點在于將英國貨物能比現在提早30天運到巨大的四川市場上。四川是一個極富饒的省份,幅員廣大,物產豐富,運輸工具的增加會使那里對于英國貨物的消費和當地剩余產品的輸出給予直接和明顯的刺激。”而“那里已經成為我們最好的中國市場之一,每年銷售九十萬匹以上的棉布和十一萬匹呢絨。”
1886年5月12日,英國人霍西在曼徹斯特商會的一次特別會議上宣讀文件時,又特別聲明:“我們曾經常要求同重慶建立定期的輪船交通,這將給商業(yè)帶來巨大的利益”。據他的調查,如果重慶得以成功通航,那么“到那時,我們的制造品在交納海關稅以后將存在重慶,而來自本省以及來自云南、貴州各大城市的買主,就能夠從這個據點(重慶)用子口稅單運走他們購買的貨物,只需交付轉口稅便能運到最后的目的地”。他興奮的預言:“四川,作為英國工業(yè)品的消費者,將很快在世界市場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交通運輸的改善將促進四川省各種產品和工業(yè)的巨大發(fā)展。我用不著拿川絲作例子,這項有價值的產品的可能的發(fā)展,的確是不可限量的。在四川省東部和中部,幾乎每家每戶的婦女和兒童都從事養(yǎng)蠶繅絲。川絲和其它出口貨的發(fā)展,將因長江上下游之間比較安全、比較迅速和比較廉價的交通運輸手段而興旺起來,這將大大地提高和平、勤勞而富裕的四川人的購買力。這里我還可以告訴大家,在中國西部,煤產豐富,煤礦就在河邊”。 英國《泰晤士報》1888年也說,假如重慶輪船航運成功,“則七千萬人口的貿易就送到門上來了;蘭開夏、米地蘭及約克郡的制造商就能從倫敦、利物浦用一次簡單轉口,繳付從價稅5%運入深入一千五百哩的亞洲心臟地帶或幾乎是中亞高原的腳下。他的成功意味著在廣大遙遠的人口與西方制造商之間以及住在揚子江下游地帶千百萬人民及海口之間的自由而廉價的交通。它還意味著在世界上最長的一千五百哩航線上安全、快速與價廉的交通”。
以后的發(fā)展,確實也證明了四川內地市場的開發(fā),與川江行駛輪船是緊密不可分的結合在一起的。可見,列強對中國內河航行權和鐵路修筑權的爭奪,一方面是因為內河航行權和鐵路修筑權的取得,是列強開拓和獲取新的商品市場的重要保證,同時還因為這是構成列強在華權益及勢力范圍的重要內容和表現之一。這一點,日本駐漢口總領事水野幸吉所說“輪船航路,表示商權伸張,一國利權之植立,而為開始”的說法,以及日本在開拓長江航路中發(fā)揮過重要作用的白巖龍平“蓋貿易和殖民必然有待于交通運輸線的擴展伸張”的說法,就是典型代表。在這里,鐵路輪船這種近代交通運輸工具的發(fā)展,扮演了擴張外國經濟侵略和政治勢力、擴大外國商品在中國市場和破壞中國自然經濟結構、擴大中國內地市場的雙重作用。而且,這段時期這種作用的主要表現方式,是以帝國主義列強對落后國家經濟掠奪的需要為依歸的。但同時我們也看到,鐵路輪船作為一種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作為中國過去未曾有過的先進運輸方式,其本身客觀存在的先進沖擊落后的內在性,在這里同樣得到了體現。關于這一點,本文第一第二節(jié)的描述也已有所證明了。
四、近代城市的興起
在鐵路和輪船等近代工具推動貿易和市場開辟的進程中,城市的發(fā)展也出現了與過去完全不同的變化。中國過去的城市,其功能大都是以或軍事為中心,隨著中國被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和對外貿易的迅速增長,一批因工商業(yè)而興的城市迅速出現壯大。這些城市,毫無例外的是具有優(yōu)越交通條件的沿海沿江和鐵路沿線的通商城市。 如上海、天津、廣州、漢口、青島、廈門、重慶等等。其中,長江流域的三大重鎮(zhèn)上海、漢口和重慶,就都是典型的因便利的交通而發(fā)展起來的新型城市。上海在開埠初期,僅是一個不大的城市,“縣城周圍約五英里……人口據說約有12萬……在建筑、外貌、富裕等方面,均次于寧波。” 但因為其具有相當便利的交通條件,“經由水路交通,它就能夠和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國聯系起來”,而且,“上海和中國大部分地區(qū)之間的內地交通幾乎和它的水路交通同樣便利,這里的貿易額相當大,大多數在中國有聲望的英國洋行和美國洋行在這里均設有分支機構。” 在中國的外國輪船公司,總部相當部分都設在上海或在上海設有分公司。中國最早的輪船公司也成立于此。因此,依靠長江流域廣闊的腹地市場和便利的交通條件,上海開埠以后很快就取代廣州而成為中國進出口貿易的中心。到1911年時,上海在中國對外貿易總值中始終占有44.2%以上的比例, 幾乎達到整個中國進出口額的一半。本世紀二十年代初時,已形成包括內河、長江、沿海和外洋等四大航線的港口樞紐城市,出入上海的商船數和噸位數都占全國總數的20%以上,成為我國最大的港口城市。再加上1908和1909年滬杭鐵路通車和1929年連接國內各大埠的航空線開通,上海進而成為全國最重要的交通運輸樞紐城市。這種因商而興的特點,又帶動了、城市建設、以及其它相關產業(yè)和行業(yè)的發(fā)展。到本世紀30年代,上海人口已從開埠初期的十余萬增長到200多萬,成為全國最大的城市。工業(yè)也有了飛速的增長,如上海30人以上的工廠數占全國12個大城市總數的36%,資本額占12個城市總數的60%,產值更達12個城市總數的66%。上海還始終是中國棉紡織業(yè)、面粉加工業(yè)等多種輕工行業(yè)的中心。由于工商、金融的集中,近代上海不僅成為萬商云集之地,城市化設施和市政建設在全國也是第一流的。 上海發(fā)展的這些特點,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于其它因交通條件便利而發(fā)展起來的城市中。如素因交通便利而有《九省通衢》的漢口,在近代以前即因水道縱橫、交通便捷的地理環(huán)境而成為以轉運貿易為主的商業(yè)港口城市。進入近代后,又是中國近代輪運最早出現的地區(qū)之一。19世紀60年代初,漢口與上海輪運通航,70年代末漢口與宜昌通航。到20世紀初,漢口除了與長江沿線各重要城市都有輪船通航外,內河小輪船航運業(yè)方面也有長足進展,形成了一個以長江航線為主干,連接通達湘江、漢水內河的近代輪運體系。19世紀70年代末,漢口與外洋直接通輪后,漢口還成為國內對外貿易的重要轉銷口岸。1905年,京漢鐵路通車,使?jié)h口在原有東西水運線貫通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南北鐵路溝通的現代條件,鐵路對漢口貿易和城市建設的直接推動作用,從下述記載中可見一斑:“近來貿易額之大增進,其盛況僅次于上海廣東”,而“外國租界,家屋之新造,已月異歲不同,如法國租界,俄化為殷盛之場者,非不全賴鐵路之河南內地前進之力乎?”而“粵漢鐵路將開通,則占水陸要沖之地,其繁盛當至隆隆沖天,則西人之擬漢口于米國芝加哥者,真非無故也。” 漢口在實現了真正現代意義上東西南北相交會的交通地理新格局后。便利的交通條件刺激了商業(yè)的進一步繁榮,商業(yè)的進一步繁榮又刺激引誘了更多的商人在此聚集,使得商業(yè)更加繁榮。出現了“中外商賈咸集于此,角逐競爭,商業(yè)貿易,極稱繁盛”的局面。漢口的城市地位也因此而直線上升:“與武昌漢陽鼎立之漢口者,貿易年額一億三千萬兩。夙超天津、近凌廣東,今也位于清國要港之第二,將進而摩上海之壘,使視察者艷稱為東洋之芝加哥。”
重慶的情況也如此。重慶是長江東西貿易主干道西線的起點,又是長江上游商品集散的中心。重慶-漢口-上海的長江航線,是西南與東部沿海商品貿易的主渠道。長江上游的商運以水路為主體。長途販運往往以河流為依托,與沿河城市串通,形成了以重慶為樞紐的商業(yè)貿易網絡。在1891年重慶開埠后,越來越多的洋貨通過輪船運到重慶,進而深入西南,在促使重慶商業(yè)貿易功能明顯擴大的同時,也使得重慶城市商品結構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在進口商品方面,洋紗、洋布、洋雜貨逐步取代了湖廣土布和手工業(yè)品。出口集中的絲、繭、白蠟等一部分貨物也開始通過輪船沿長江向國外出口,并增加了豬鬃、羽毛、羊毛、牛羊皮和桐油等新品種。這一切變化的綜合作用,終于使得19世紀末20世紀初時,重慶開始出現了近代工業(yè),重慶市的功能也從單純的商業(yè)貿易中心逐步向商業(yè)、工業(yè)、金融、交通等綜合性經濟中心以及近代技術和信息中心轉變。并因交通運輸業(yè)的發(fā)達日益擴大其輻射和作用,成為長江上游最重要的經濟中心和多功能城市。
在河流水道條件遠不如長江水系發(fā)達的北方,近代交通運輸工具特別是鐵路的出現,對商業(yè)中心和城鎮(zhèn)的盛衰更替有著更為明顯的影響。例如哈爾濱原是松花江右岸的幾個村。1898年俄國人開筑鐵路,據此地為辦理中東鐵路的總匯之所,使其急劇興起,1900年聚居者即達2萬人。再過五年,激增至10萬,成為“中外交通之樞紐”,與南部的沈陽一起,很快成為整個東北地區(qū)的又一中心。與營口相鄰的大連和旅順,本是一個不著名的土名叫作“青泥洼”的海灘。南滿鐵路支路通達此地后,沙皇政府發(fā)現其地理條件優(yōu)越,便在1899年6月明令經營,“作為無稅口岸”。該地筑港設埠后,又經過1905年后日本的繼續(xù)經營,迅速成為取代營口地位的東北的貿易中心。1909-1911年,它在全國對外貿易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上升到4.9%。華北的煙臺為渤海沿岸貿易集散中心,是山東南與江蘇、浙江、福建以至廣東,北與東北地區(qū)交往的通道。1862年被迫開為通商口岸。直到20世紀初山東建設鐵路前,仍然是華北對外的一個重要的貿易港。1903年經過煙臺的貿易值在山東的進出口貿易值中比重占到了72%,可見其興盛的程度。但是自從華北地區(qū)的鐵路漸成系統(tǒng)之后,它的地位便衰落下去,尤其是膠濟鐵路通到青島之后,它的地位便被青島所取代。青島原是膠州灣邊的一個荒僻漁村,因為德帝國主義者修筑膠濟鐵路而成為東邊的終點站和出海港。也正因此,青島得以迅速發(fā)展起來,1902年時,人口總計不過1.6萬人,1904年膠濟鐵路通車后,人口急劇增加,1910年已達到16.5萬人,增加了整整十倍。1900年青島開埠設關時直接進出口貿易總計不過19萬兩,1904年膠濟鐵路通車后達到429萬兩,1911年津浦鐵路通車后更增加到2355萬兩。青島港的進出口船只裝貨噸數,也同樣表明了這種變化趨勢。在開埠的頭五年間,年平均裝貨30.5萬噸,膠濟鐵路通車后五年間,增至年平均47.2萬噸。津浦鐵路通車后頭三年,年平均更增至86.1萬噸。
鐵路和輪船在中國大地上的出現,除了作為工業(yè)文明生產力的體現,作為一種大量機制產品進入中國內地和列強掠取大量中國資源的載體外,它還是外部世界信息進入的媒介,是震撼和沖擊中國古老生產生活方式的演變器。因而它的影響和作用絕非僅僅停留在商業(yè)的變化、城市的興衰更替和交通運輸功能的改善上,而是會擴散和影響到生活的各個層面和中國大地的各個方面。這種擴散和影響反過來則會對整個社會發(fā)生作用,只不過這種作用沒有政治變化那樣明顯和外在。因此,上述鐵路輪船出現后在晚清社會中激起的變化,預示著的,也僅僅是此后更大變化的一個開端而已。
生部公報.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