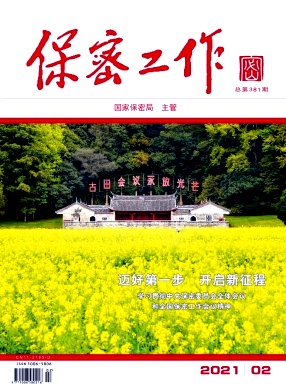構建經濟強國的科技創新體制——日本科技體制改革的政策解析
龔旭
摘 要:1995年以來日本的科技體制發生了重大變革,其深遠影響不僅限于科技界,而且波及日本的經濟、社會、教育等領域。本文試圖深入考察日本科技體制改革的動因、契機、政策措施與手段,為我國在新世紀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提供參考與借鑒。
關鍵詞:日本;體制改革;科技政策;科技評價
1995年11月日本國會一致通過了曾被稱為“幻影法案” [ ]的《科學技術基本法》,拉開了半個世紀以來再度重建日本科技體制的序幕。隨后,依此法進行了科技體制的根本性改革,制定和實施第一期(1996-2000財年)和第二期(2001-2005財年)科學技術基本計劃,以及政府在科技投入、科技政策和科研機構和體系結構等方面實行的一系列重大變革,不僅對日本的科技、教育等相關領域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而且震動了整個國際科技界,甚至有人將此次改革看作是日本科技史上“第三次最重要的變革”,與明治維新和“二戰”后日本現代科技體制的建立相提并論。[ ]日本一向被認為是以技術立國的典范,特別是在“二戰”結束以來,其以技術為基礎和導向的經濟建設與發展的成就令世人矚目。然而,為什么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要進行科技體制的重大改革?改革的動因和目標是什么?改革的條件與舉措有哪些?采取了什么配套政策和手段?本文試圖對上述問題進行解析,目的不單是為了得到答案,而是希望通過深入分析與我國有著相似文化傳統的日本進行科技體制改革的深層次因素,探討所謂“后發”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科技發展的道路,特別是經濟強國的科技競爭力的提升以及經濟發展同科技體制創新的關系等,為我國在新世紀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提供參考與借鑒。
1 重建經濟強國的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動因與要求
“二戰”后的日本經濟直到20世紀80年代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高速增長“奇跡”。經歷戰后20余年的艱苦努力,1968年日本國內生產總值首次超過了當時的西德,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到80年代末,其人均產值更是超過了美國,雄居世界各國榜首。在對日本“經濟奇跡”的諸多解釋中,提及最多的因素之一是所謂的“后發優勢”,即日本通過引進、吸收、消化、利用和發展其他發達國家已有的技術而不是自主開發,集中力量實現技術產業化,并以此推動了經濟增長。事實也確然如此,證明了日本戰后的科技體制與政策在很長一段時期里無疑是成功的。但是,為什么到了90年代中日本卻要開始實行科技體制的根本性改革呢?改革的動因是什么?要達到什么目的?以下將從兩個方面分析。
1.1 “技術引進”時代的終結與經濟強國的責任
根據日本科技政策史研究會的研究,日本的“外國技術引進”時期是在戰后的1945年至1959年。日本用于購買國外專利的投入在1951年為24億多日元,到1959年激增至近223億日元[ ]。由于日本的技術引進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以培育自主創新能力為目的,因此引進的過程并非單純性的技術引進,而是技術引進與吸收、消化和改進相結合。60年代隨著日本在引進過程中技術能力的成長和實行開放性經濟體制所帶來的自由化程度加大,日本逐漸過渡到以提高國際競爭力為目標的“確立自主技術”時期。這一時期雖然技術引進的數量繼續增長,但本國科研投入也大幅度增加,1969年比1960年增加了5倍,占國民收入總額的比例也達到了1.9%。反映在技術貿易方面的變化是,日本的技術引進額和研究與發展(R&D)經費的比例持續下降,到1971年已降至10%,而技術出口額則逐年攀升,1971年技術出口收入與引進支出之比上升為1:8。隨著日本技術自主創新能力不斷增強,到了70-80年代,日本已從50-60年代的技術引進依賴型轉向了轉移促進型和技術發展型,并在制造業、醫療衛生、能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等領域進一步發揮其技術優勢,不僅大大提高了本國人民的生活質量,而且其經濟強國的地位繼續加強,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日趨加大。1986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11.9%,國外資產總額為180億美元,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盡管科學技術在日本的經濟增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長期以來日本不重視基礎研究,只對商業目的的科技活動感興趣,對科技的投入是以產業界為主體而不是政府,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是日本戰后科技政策與體制同其他發達國家的主要區別,因此也是其受到國際社會廣為批評的原因之一。
伴隨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其經濟發展中蘊藏著的危機因素也日見彰顯。自80年代后期起,日本的經濟強國地位和世界科技的突飛猛進對其以技術引進為主的科技政策與體制愈來愈構成嚴峻的挑戰。隨著日本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貿易摩擦日益加深,發達國家紛紛要求日本在經濟領域向世界開放市場,改變國際貿易的不平衡狀況。同時,在對經濟發展具有最重要的基礎性意義的科學技術領域,國際社會也對日本有了更高的期望值。要求日本認識到發達國家對發展科學技術負有的重大責任,將科學研究、特別是基礎研究的成果視為國際社會的公共財富,并且要求作為經濟強國的日本必須改變在科技發展中“搭便車”的一貫做法,必須對包括知識進步在內的人類進步做出與其經濟和科技實力相稱的貢獻。
1.2 舊體制變革的必要性與“科技創新立國”時代的到來
在日本國內方面,經歷了40多年的經濟持續增長后,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經濟開始進入了持續低迷的“平成不況”時期,所謂“產業空洞化”等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凸顯出來,“僅僅通過傳統的宏觀政策來和經濟周期相抗衡,已經無法解決問題”[ ],科學技術成為人們期待中復興日本經濟的關鍵。但是,改革前的日本科技體制與政策已遠不能適應新的需要,必須進行重大改革。
如前所述,戰后日本科技政策和體制中最為人詬病的是對基礎科學重視不夠。盡管日本全國的R&D支出與GDP之比自80年代后期以來一直高于美、德、法、意等主要OECD國家,但政府對科技的投入一直處于較低的水平。讓我們來看日本科技同志改革前一年的1994年的一些數據。1994年的數據顯示,日本政府R&D支出占GDP的比例僅為0.62%(自然科學為0.53%),而美國是0.91%,德國0.95%,法國1.10%,英國0.67%;1994年日本平均每個研究人員的R&D支出為2120萬日元,而美國1993年就達3150萬日元、英國2810萬日元,德國在1991年已達3150萬日元、法國3710萬日元;1994年日本平均每個研究人員只有0.13個輔助人員,而德國和法國是1.1個,英國1.2個;日本國立大學49%的研究設施和科技廳與通產省所屬實驗室29%的R&D設備運行都已超過了20年,這些實驗室82%的活動設備都已超過了服役期。[ ]受到行政管理體制等因素的影響,日本科技體制中的另一大問題是,不同部門(大學、政府實驗室和私營公司等)間、不同研究領域間的研究人員難以合作,影響了科技創新以及科技對經濟推動作用的發揮。此外,由于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等日本特有制度以及缺乏競爭機制等原因,日本的科研缺乏活力,不利于青年科學家的成長,科學研究領域對許多年輕人的吸引力不夠,嚴重影響了科學事業的健康持續發展,如此等等都對日本科技創新形成障礙。市場導向的科研雖然對經濟發展有著直接作用,但基礎研究的缺失與不足勢必造成科技創新的巨大阻力,而基礎研究需要政府更多地投入,科技體制改革更需要政府來進行,日本必須大幅度增加政府對R&D的投入,同時建立靈活高效的科技管理體制,才有可能實現新的科學和技術突破。
曾任日本內閣科學技術政策擔當大臣的尾身幸次先生于1995年向眾議院陳述科學技術基本法提案的理由時指出,日本從發達國家引進先進技術的時代已經結束,今后,必須向新的科學技術領域拓進,最大限度地發揮創造性以開拓未來;與此同時,日本為了解決自然資源匱乏、人口急劇老齡化、產業空洞化、經濟自由化和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競爭加劇等問題,必須發展獨創性的、尖端的科學技術,開創新的產業。[ ]一位日本資深科學家也表述了同樣的觀點:“戰后日本的產業政策是要在技術上趕上西方,當時的科技戰略是為促進產業發展而從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引進科學和技術,通過技術轉移和工程技術進步,日本如今已躋身于世界經濟強國之列”。于是,“不能再從別人那里照搬什么了,因為你已經站在了前沿。你必須在科學上有獨創,有自己的技術突破。……否則,日本的產業將不會創造新的奇跡”。[ ]總之,無論是科技管理者還是科學家都明確認識到日本科技政策與體制改革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必須從戰后以引進為主轉向基礎科學推動為主,實現科學技術的全面進步。21世紀的日本已步入“科技創新立國”的新時代。
2 走出傳統體制與更新認識:體制改革的契機與條件
僅有改革的挑戰或要求還不夠,必須具備改革的契機與條件,才能深入到科技體制的全方位改革。實際上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日本已開始意識到對基礎研究的忽視可能會影響到國家經濟社會與科技的可持續發展。文部省、通產省、科技廳等政府機構和部門為推動科學技術、尤其是基礎研究的發展,也曾陸續制定和實施了一些帶有改革色彩的政策措施,1992年內閣辦公室的科學技術會議還提出了政府將R&D經費增加一倍的建議。但為什么到90年代中期《科學技術基本法》才得以通過和頒布,科技體制改革才正式啟動呢?最直接的原因是,90年代中期日本的政治體制改革發生了重大的變革,科技體制隨之而變化。隨著自民黨相繼在國會的參眾兩院失去多數席位,1993年自民黨結束了一黨執政的歷史,被迫與其他政黨一起組建新政府,自1955年由自民黨長期單獨執政以來所確立的所謂“55體制”走到了盡頭。
2.1 政治體制改革與《科學技術基本法》的頒布
關于“55體制”及其在戰后對日本社會、經濟和科技發展的積極作用與弊端,西方和日本學者都有不少研究。這一體制的主要特征是官僚政治,立法機構與行政機構高度一致,幾乎所有的立法動議都來自于官僚機構——政府各官僚機構及其官員是權力的核心,其影響力遠大于國會和內閣;官僚機構或部門條塊分割嚴重,而且,為了維護各自的既得利益,它們一般不愿冒險提出超出自身利益之外的政策動議。[ ]1995年通過并頒布的《科學技術基本法》就不是來自政府部門的動議,而是在社會黨黨魁村山富市擔任內閣總理大臣期間由國會提出審議的,這在日本戰后的立法史上是罕見的。當時失去國會多數席位的自民黨為了重新獲得公眾的信任,在國會積極致力于新的立法建議,而當時任國會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長的自民黨議員尾身幸次一向極力主張日本發展基礎研究,由他向國會提出《科學技術基本法》的提案也就不足為奇了。
《科學技術基本法》開宗明義說明該法旨在提高日本的科學技術水平,在各條款中,第九條關于科學技術基本計劃的規定至關重要[ ]。根據這一條款,政府應當每五年制定一次推動科學技術發展的基本計劃;基本計劃應包括政府促進R&D(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開發研究以及技術開發)發展的綜合性和系統性方針,涵括研究設施的裝備、R&D信息集成的促進、R&D環境建設等相關的政策。為了切實保障基本計劃的實施,政府應在每年度國家財政允許的范圍內,采取必要措施從經費預算上予以保證。日本政府的兩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1995-2000財年、2001-2005財年)以及政府科技投入的大幅度增長、科技政策形成機制和科技體制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都直接源于該基本法。
日本政治體制改革經歷了一個過程。中央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自1996年開始醞釀,1997年12月正式提出,到1999年才開始實施,改革的核心是削減中央政府各部門的權力,通過精簡機構達到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以及提高效率的目的。在國會的批準下啟動的一系列改革法案,其中包括改革內閣體制、合并政府機構與部門,還包括改革國立大學和國家實驗室等等,這些政策措施對日本科技體制產生了深遠影響。政治體制改革成為深化科技體制各個的契機,為日本戰后五十年科技體制的重構提供了條件。
2.2 對基礎研究性質與作用的再認識
除了政治體制改革對科技體制改革所產生的直接推動作用之外,科技界及相關各界對科技活動及其作用基本認識的變化,也影響到對改革的期望值以及改革目標的認同度。雖然基本法中所指的科學技術的范圍覆蓋了R&D的全部活動,但鑒于日本的應用研究與開發能力在80年代初就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也正因此造成對基礎研究的忽視引起日本國內外科學界的廣泛批評。所以,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基本法的核心是要提高日本的基礎研究能力,并以此提升國家競爭力。那么,人們真的相信基礎研究能提升日本的國家競爭力嗎?在80-90年代的日本,人們是如何看待基礎研究的?
在戰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在關于基礎科學及其與技術創新關系的認識上,包括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一直流行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再到試驗發展及至生產經營的所謂“線性模型”。基礎研究被認為是“為了科學知識的增加而進行的工作,不考慮實際的特殊應用”[ ],但隨著人們對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過程及其性質認識的加深,80年代以來,諸如“并行模型”、“鏈式連接模型”等越來越多的“動態模型”取代了原來的“線性模型”。其中,一些模型就是建立在對日本創新型公司研究的基礎之上的,如平澤冷提出的“并行模型”就是將研究、開發、生產及銷售各階段看作是相互重疊而非按時間順序排列的;竹內廣孝和野中郁次郎則進一步對這兩種模型進行了對比,將“線性模型”比作接力賽,將“并行模型”比作橄欖球比賽,以此說明技術創新的諸要素之間是一種整體配合的關系。[ ]這顯示了日本專家對基礎研究在技術創新乃至經濟增長中重要地位的確認。美國政策研究專家認為,1996年出臺的日本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所體現的新的科技政策,改變了日本科技政策重在技術開發的戰后模式,以一種新的眼光來看待基礎研究及其作用,并努力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之間達至平衡。[ ]
3從政策制定到機構改革:體制改革的主要舉措
科學技術基本法頒布之后的日本科技體制改革堪稱全方位的改革,在科技政策形成的機制、科技計劃的制定與實施、科技管理機構和科研機構的法律地位及其管理等諸多方面,都進行了實質性的改革,的確是戰后科技政策與組織管理的一次“根本性重建”。以下分三個方面分析其主要改革舉措。
3.1 重構科技政策體制與機制
一個國家的科技體制由科技活動的決策、執行和管理等機制及相關部門所構成,其中決策機制的中心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改革前日本政府制定科技政策的決策機制隨時代發展已呈現重大缺陷,相關部門雖有針對自身利益而提出政策變革的動議,但內閣和國會缺乏進行統一規劃與協調的獨立的政策機構。改革后的政治體制加大了內閣及總理大臣的權力,尤其是在政策制定方面,注重發揮其超越各部門之上的綜合協調作用。
2001年1月6日日本政府實行了內閣改革。新設立了內閣辦公室,直接對內閣總理大臣負責。從法律地位上講,其地位高于各政府部門,其成員不僅來自政府各相關部門,而且來自民間和非政府組織。內閣辦公室特設的擔當大臣中有一名為科學技術政策擔當大臣;內閣還設立了幾個相應的“智囊”機構(稱之為“會議”),負責科學技術政策的機構是“綜合科學技術會議”[ ],在法律上受內閣總理大臣領導,但實際上由科學技術政策擔當大臣具體負責,其規模、組織、權威和職責都遠遠超過了其前身——1959年設立的原“科學技術會議”。
與原科學技術會議相比,綜合科學技術會議的特點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戰略性與及時性。該機構負責起草綜合性科學技術戰略,討論與研究科技資源配置問題,并對國家重大的R&D活動及計劃開展評估。該機構每個月開一次會,而不是象過去的科學技術會議那樣每年開1-2次會。(2)綜合性。新體制下的科技政策討論與制定包括了人文社會科學,而不是如舊體制下只有自然科學;因此,涵括科學、技術與社會等重要而廣泛的問題都在綜合科學技術會議的科技政策考慮之列;(3)自主性。新機構更多地是向內閣總理大臣提出政策建議,而不是被動地回應總理大臣的咨詢要求。2001年3月,綜合科學技術會議結合審議第二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提出了國家的4個重要戰略科技領域,即生命科學、信息技術、環境科學和納米技術/材料,還向公眾宣布日本“在未來50年內產生30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奮斗目標,這一目標也寫進了基本計劃。另外,該機構還與內閣辦公室的另一個“智囊”機構“經濟財政咨詢會議”合作,在國家預算編制和實施過程中發揮重要影響。2001年6月經濟財政咨詢會議將“科技創新立國”的思想寫進了其基本方略中,保證了科學技術預算的地位,并且在2002財年的具體預算編制中,將科學技術列為國家財政的7大重要領域之一。可以看出,綜合科學技術會議力圖改變過去科技政策制定中的部門分立色彩,以及科技發展與國家財政預算關系不夠緊密的狀況,加強了科技政策的戰略性、全局性和綜合性,成為推進科技體制進一步改革的制度保障。
3.2 制定與實施科學技術基本計劃
根據日本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每五年制定一次科學技術基本計劃,通過基本計劃的實施,增加對R&D的投入,提高日本科研人員的創造力,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間建立更為協調的平衡關系。如前所述,自1996年起日本已連續制定了兩期基本計劃。
日本在第一期基本計劃中提出,到2000財年政府將R&D投入增加一倍,1996-2000財年累計R&D投入為17兆日元(約1500億美元)[ ],這在90年代中后期經濟尚處于低迷狀態的日本無疑是個驚人之舉!但是,與提出的科技體制的改革目標相比,這樣的投入還不是最令人吃驚的。基本計劃明確指出,要“構建新的R&D體系”,以使科技更有效地與經濟及更廣泛的日本社會相聯系。第一期基本計劃中最重要的政策措施還包括:在國立研究機構和國立大學引入人員任用任期制,到2000年創造10000名博士后研究人員位置,通過改變知識產權的有關條款和放寬國立大學研究人員的兼職限制等舉措促進產學合作,改變傳統的資助模式加大競爭性經費的比例,引入嚴格的、系統的評價程序,并將評價結果應用于研究經費的分配,大力改善大學的R&D設施與設備等等。顯然,在經費充足等前提條件下,上述政策措施中有一些實行起來相對簡單,但另一些的實施則較為困難,需要改變已經存在了半個多世紀的科技體制與機制、乃至人們的觀念。2000年前后一些針對第一期基本計劃實施的評估也表明,人們普遍對投入的增長和博士后位置的增加表示滿意,而對科技體制改革的效果有所不滿,希望繼續進行深層次的改革[ ]。
日本第二期基本計劃的制定和實施是在國家行政管理體制發生重大變革的過程中進行的,也直接受到這一變革的影響。因此,如果說第一期基本計劃的目標還只是對日本科技體制的基礎有所改進的話,第二期基本計劃則是針對科技體制本身的改革,尤其是科研體制的改革[ ]。第二期基本計劃提出,2001-2005財年日本政府的R&D投入繼續增長,五年間將共投入24兆日元。除了增加投入之外,基本計劃的主要目標有6個方面:確定政府R&D投入的戰略方向,營造R&D的競爭環境,提高人才的流動性,改進R&D評價體系,通過促進官、產、學結合加強對研究結果的應用,以及促進科技界與社會的交流。該基本計劃在科研體制改革方面最重要的舉措有兩項。一是大幅度提高競爭性科研經費,將2000財年的9%提高到2005財年的18%,進一步擴大研究人員對研究課題選擇和經費使用的自主性,為科研營造活躍的環境,同時改進評價活動,建立最大限度發揮科研人員創造力的評價制度;二是允許為競爭性研究課題匹配30%的間接經費,由獲得競爭性經費的研究人員所在機構統一管理,用于改善獲得競爭性經費人員的科研環境,提高所在機構的科研能力,同時促進科研機構之間的競爭,以提高研究質量。[ ]第二期基本計劃目前還在實施中,其效果雖一時尚難以評估,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由于綜合科學技術會議的設立和運行,基本計劃中涉及到跨部門或多機構的科技政策和R&D活動的實施將更為有效,而且在執行中出現的問題也將得到綜合科學技術會議更及時的討論,有利于問題的解決。
3.3 改革科技管理部門和科研機構
根據1999年日本國會通過的政府改革法,2001年1月在改革內閣的同時,政府一系列行政體制改革也正式啟動,其中包括:將中央政府原有的22個部門和機構壓縮為13個,將原各政府部門和機構下設的局由128個壓縮為96個,將這些部門和機構下屬的咨詢機構由211個壓縮為89個,將一些國立機構(國家實驗室、國立醫院、國立大學等)的性質改變為“獨立行政法人機構”,賦予其組織和管理上更大的自主權。此外,根據政府改革法,到2010年底公務員的總人數要削減25%。[ ]對日本科技體制影響最大的改革舉措當屬將原文部省與科技廳合并為文部科學省(英文名稱為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Culture,Sports,Science and Technology,縮寫為MEXT),以及將國立大學和部分國立研究機構“改制”為獨立行政法人機構。
在舊體制下,文部省和科技廳掌握了政府研究經費的近70%(1997年這兩個部門分別為43%為25%)。[ ]由于這兩個獨立的部門任務職能不同,在R&D預算和科技政策導向方面一直存在競爭關系,因此,即使同屬國立機構,但由文部省管轄的國立大學和科技廳所屬的國立研究所很難開展合作。此外,雖然文部省掌握的研究經費在各政府部門中份額最大,但由于其管轄機構之多與人數之眾,分散到每個研究人員的經費十分有限,研究人員不得不向其他部門和機構(如科技廳、通產省等)申請經費。可是,不同渠道的科研經費在使用方向上各自有嚴格的要求,不利于研究人員開展穩定方向的研究,而且,來自不同渠道的經費不能統一用于購買儀器設備,這也是造成改革前大學研究設備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自2001年4月1日起這兩個部門合而為一,新成立的文部科學省的科學政策旨在改善大學的科研環境與條件,促進國立大學和國立研究所之間更緊密的合作,推動官、產、學聯合。這一舉措受到了日本科技界的普遍歡迎。
日本科技體制改革的另一重要舉措就是前述的將國立大學和部分國立研究機構改變為獨立行政法人機構。首先改制的是國立研究機構,自2001年4月始,改制的研究機構成為獨立行政法人,采用靈活自主的管理模式,使研究機構從官僚控制中擺脫出來,獲得更多的管理靈活性和學術自由。[ ]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將于2004年4月開始實施,改革將涉及到大學的法律地位、組織、治理、人事、績效考評、財務管理、財產管理等重要而廣泛的問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為獨立法人后,大學的教職工將不再是國家公務員,因而大學靈活的人事與工資制度、任期制、教師兼職、聘請外國人擔任大學校長或系主任等都將成為可能。現任文部科學大臣遠山敦子將國立大學改制為獨立行政法人后的優勢總結如下:[ ](1)大學法人化可以確保大學的自主性及其自立;(2)可以運用富有民間特色的經營手法,引入機動、靈活、具有戰略性的組織和財務運營方式;(3)實現以校長為中心的高層管理方式;(4)通過設立大學外部理事等方式,邀請外部人員參與管理,實現開放式的大學運營。當然,這些優勢不會在大學改制后自動顯現,而是需要有一系列配套政策與措施的實施,而且,大學必須在轉變“身份”后逐步建立起一套自我管理的制度與方法,培育其自主發展與完善的能力,才能最終達到改革的目的。
4重視與規范科技評價:改革實施的重要手段
日本科技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提高科研的競爭性,營造更有利于創新的環境,以促進科技和經濟的發展。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建立嚴格的評價體系。事實上,在兩期基本計劃中都有專門條款針對評價體系的建立與評價活動的規范。為了配合基本計劃的實施, 1997年8月內閣批準實施了《國家R&D評價的大綱性指針》(以下簡稱為“評價指針”),到2001年11月,又批準了修改后的評價指針。政府各部門根據具有指導性的評價指針開展評價活動,一些部門還制定了自己的評價指針。評價活動的規范與改進以及評價結果的合理使用,在日本的科研資源配置、科技政策制定、科研機構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4.1綜合科學技術會議高度重視評價活動
綜合科學技術會議是日本科技政策的最高決策機構,在其每月例會中,關于評價議題的例會次數最多,差不多是其他議題的兩倍。[ ]該機構還將改進評價體系作為第二期基本計劃的主要目標之一,提出了改革與完善現有評價體系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為了突出評價的重要性,在其成立之初設立的5個“專門調查會”[ ](后擴展為7個)中就有“評價專門調查會”,職責是制定評價準則,對重要的R&D活動開展評價等,以對R&D資源實行有效配置。自成立以來,該專門調查會平均每1個多月就召開一次會議,研究與評價相關的問題。會議常常就評價中的具體問題進行研究,針對現狀分析問題,并提出改進的方向。例如,在討論競爭性經費支持的研究項目評價時,針對科研經費的補助金問題,首先分析現狀如相關部門主管評價活動的人員設置、評價人員的年齡構成、參與事前評價的評議專家的評議工作量等;然后整理出存在的問題,如主管評價活動人員的職責不清、評價人員年齡偏大、評價時間限制過緊以及評議專家負擔過重等,基于這些問題,最后提出改進評價工作的方向,包括:在相關部門增加熟悉評價工作的人員并明確其職責,擴大評價專家中年輕研究人員的數量,培養評價專家,充實評價經費等。
4.2制訂評價指針規范評價活動
由于評價具有很強的政策導向,評價活動本身又很復雜,涉及到科技活動的方方面面,因此,盡管在兩期基本計劃中對評價活動也有一些具體的要求,但政府出臺內容全面的評價指針來規范各類評價活動,仍然很有必要。新舊兩個“版本”的評價指針在基本框架和內容上是相似的,都說明了評價的意義與作用,規定了評價指針所涉及的評價對象,明確了評價各方的責任,針對不同類型的評價對象,回答了評什么、何時評、怎么評、誰來評等問題,提出了評價結果使用的原則與范圍,突出了評價活動中應當注意的問題。
在國家R&D評價指針的指導下,各相關部門還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制定了在本部門范圍內適用的評價指針。以文部科學省2002年6月頒布的評價指針為例[ ],其評價指針包括評價的基本思路、通用事項、評價分類、注意事項等內容。由于文部科學省的資助對象以大學為主,因此,在注意事項中特別指出了對大學開展的學術研究進行評價應當注意的問題,強調要充分考慮到大學里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不同學科領域研究的特性、內容、規模等的多樣性,要尊重學術研究的獨創性、長期積累性以及研究在其初期的不確定性等特點,要認識到這些特點給評價帶來的困難。評價需要有不同的視角,既要關注研究的前沿性、創新性,也要關注研究對技術開發及社會經濟的貢獻,還要考慮從長遠效果看研究對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促進作用。
4.3評價指針的動態改進
隨著2001年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啟動,同年6月日本通過了《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案》,要求將評價作為政府部門和機構的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必要程序。與此同時,國立研究機構和大學的改制工作也加大了對評價活動的需求,因此,2001年11月新出臺的評價指針根據上述形勢發展的要求,對原有的評價指針進行了修改。例如,新的評價指針增加了有關R&D政策評價的條款,指出在R&D政策制定與實施前,必須評價其是否符合國家政策,是否能夠在確保與相關政策協調的同時得到有效實施;對政策實施后結果的評價必須反饋給決策和實施部門,并將評價結果反映到對政策的改進或廢止中。新的評價指針還增加了評價改制后作為獨立行政法人的研究機構的內容,指出此類機構的評價要根據《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由獨立行政法人評價委員會對其進行績效評價,評價結果要反映在相關部門的資金分配中,同時反映在機構的運營之中。[ ]根據國家重大決策的出臺和政策調整,對評價指針進行適時的動態調整,才能使之更有針對性,在實施中也更具可行性。
以上,就日本科技體制改革及相關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梳理和分析。應當看到。我國與日本同屬東亞文化圈國家,雖然兩國的政治、經濟制度不同,但所選擇的現代化道路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如都經歷了一個從發展經濟到科技強國的歷程,將發展科技作為立國之本,注重發揮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日本科技體制改革的動因、條件、政策措施與手段,特別是通過上述對其在科技立法、政策制定、機構改革、評價體系等方面改革舉措的解析,總結其經驗教訓,對我國的科技體制改革和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的制定以至現代化建設應當具有借鑒意義。
[ ]“二戰”結束后的20世紀50年代日本政府就討論過通過立法保障科學技術發展的問題,在經濟和科技迅速發展的60年代,內閣和國會還曾試圖制定、審議、頒布一部《科學技術基本法》,但在草案形成后,因對其中的一些重要內容爭論頗多分歧太大,最終由于國會審議無結果而成廢案,故被稱作“幻影法案”。
[ ]日本原科學技術會議主席、日本腦科學研究所前所長伊藤正男先生在接受美國衣阿華州立大學教授Yong S. Lee等的訪談中曾對此作出較為詳細的說明,參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東京地區辦公室備忘報告00-08號:Yong S. Lee, Koichi Kitazawa, Shigru Nakayama: A Radical Restructuring of Japan’s Postwar S&T Policy and Institutions, May 15, 2000, http://www.nsftokyo.org/rm00-08.html
[ ] 日本科學技術政策史研究會編,邱華盛、李向東等譯,《日本科學技術政策史》[M],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p160。本段其他幾處數據分別出自該書的p112-114、p156-160和p93。關于日本在戰后為何實行“技術引進”政策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而沒有根據當時流行的經濟理論(即比較優勢理論)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西方對此有許多研究。參見日本國家科技政策研究所研究報告(Material_No.17): Peter Van der Sta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 Japan, 1992, http://www.nistep.go.jp/index-e.html。
[ ] 青木昌彥,超越官僚制多元主義,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專欄文章,http://www.rieti.go.jp/cn/columns/a01_0001_t.html,2001年5月15日
[ ]以上數據來源于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東京地區辦公室備忘報告96-11號:Japan’s Basic Law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pril 3[R], 1996, http://www.nsftokyo.org/rm96-11.html
[ ]日本內閣辦公室,科學技術基本法について:科學技術基本法提案理由説明,http://www8.cao.go.jp/cstp/cst/kihonhou/riyuu.htm
[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東京地區辦公室備忘報告00-08號:Yong S. Lee, Koichi Kitazawa, Shigru Nakayama: A Radical Restructuring of Japan’s Postwar S&T Policy and Institutions[R], May 15, 2000, http://www.nsftokyo.org/rm00-08.html
[ ]詳細分析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東京地區辦公室備忘報告01-02號(Central Government Reform in Japan:Rationale and Prospects[R],February 9,2001)和00-08號(注釋7)
[ ]日本內閣辦公室,科學技術基本法,http://www8.cao.go.jp/cstp/cst/kihonhou/houbun.htm
[ ] D.E.司托克斯著,周春彥、谷春立譯,基礎科學與技術創新[M],科學出版社,1999年,p55
[ ]同上,p72。但該譯本翻譯日本學者的姓名有誤,Roy Hirasawa應為平澤冷,而不是洛易?哈若沙瓦,Hirotaka Takeuchi和Ikujiro Nonaka(p145注釋中誤寫為Noaka)應為竹內廣孝和野中郁次郎,而不是西山田志和一吉那仁。特此更正。
[ ]同7
[ ]該機構的日文名稱是“総合科學技術會議”,但英文名稱為“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縮寫為CSTP),說明其職責主要在于科技政策。
[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東京地區辦公室備忘報告01-15號(Hayashi,A New System for Promo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Japan[R],December 4,2001)
[ ]科學技術基本計畫,http://www8.cao.go.jp/cstp/cst/kihonkeikaku/houbun.htm
[ ]參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東京地區辦公室備忘報告00-06號(Japan STA Policy Committee, Follow-up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ic Plan: An Interim Summary[R], March 7, 2000)和特別科學報告03-02號(William A. Blanpied, The Seco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ic Plan: a Blueprint for Japa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R], May 19, 2003)
[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東京地區辦公室特別科學報告03-02號
[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東京地區辦公室的備忘報告00-18號(Hiroo Imura, Preview of the Seco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ic Plan[R], December 4, 2000)
[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東京地區辦公室備忘報告99-11號(U.S. NSF Tokyo Regional Office, The Government of Japan’s Reorganization and Reform Plan[R], October 7,1999)
[ ]同7
[ ]轉引自藤本昌代,關于確立獨立行政法人組織特征的課題,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專欄文章,2002年4月9日,http://www.rieti.go.jp/cn/columns/a01_0038_t.html
[ ]參見澤昭裕,國立大學法人化過程中存在的大學改革死角,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論文選登,2003年7月,http://www.rieti.go.jp/cn/papers/contribution/ze01.html
[ ]同14
[ ]蔡虹、許曉雯,對日本科技政策形成機制改革的分析及其思考[J],中國軟科學,2002年第8期,pp82-85
[ ]日本文部科學省,文部科學省における研究及び開発に関する評価指針,http://www.mext.go.jp/a_menu/kagaku/hyouka/020701.htm
[ ]日本內閣辦公室,國の研究開発評価に関する大綱的指針,http://www8.cao.go.jp/cstp/hyoukasisi.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