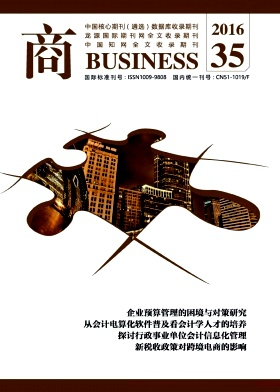西方經濟學的“烏托邦”
侯惪夫
這里所謂的西方經濟學,是指西方主流經濟學,是中國那些缺乏常識的經濟學家賴以揚名立萬的“圣經”。現在輿論一味指責他們成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卻不探究其理論本身,恐怕有失公道吧。
研究經濟學的三種方法
研究經濟學的方法有三種:實踐的、歷史的和理論的。
理解這三種方法,莫過于拿學習軍事學來作比。經濟學與軍事學的相似之處在于,它們都要應用于實際中才有意義,與實際相脫離,后者要打敗仗,前者則會付出甚至比戰場上的流血犧牲更大的代價,尤其如今經濟學已成為重要的政策指導工具,真的是“經世濟民”了。
很多人喜歡對軍事夸夸其談,儼然一幅軍事家的模樣。實際上,要獲得“軍事家”這個稱號比獲得“經濟學家”的頭銜可難多了,能否成為一名優秀的指戰員,與你所用的學習方法密切相關:
1、實踐的方法。這是第一方法,換句話說,其它兩種方法都要受它檢驗,也必須以之為土壤。如成吉思汗,“只識變弓射大雕”(當時蒙古人還沒有文字),然而他的軍事思想和指揮藝術與他率領蒙古騎兵創造的輝煌戰績,同樣在世界軍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我軍許多指戰員從不識字的娃娃成長起來,也是“從戰爭中學習戰爭”。
2、歷史的方法。比起實踐法來,這種方法成本低得多。如諸葛亮耕讀于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出山后無論治國治軍,果然出手不凡,蓋其盡已博取前人經驗得失。而太平天國楊秀清屢挫清軍,卻多是從三國演義中學得計謀。今日MBA教學的案例法,實際也就是歷史方法的一種變形。
3、理論的方法。這要求的抽象思維水平最高,但危險程度也最高。因為前兩種方法以歸納法為基礎,上升為理論后,則以演繹推理為主,從而使之普適化。理論的這種獨立的傾向,往往使其信奉者在現實中碰壁,如趙括紙上談兵,馬謖失守街亭,結局令人沉痛。
然而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卻以數理分析為主,幾乎已演變為一種理論游戲。蓋其已建立起一套宏偉精密的數學模型,排除了實際中很多因素,在邏輯上達到自洽,讓人欽佩其構思的精妙,不知不覺成為它的信徒。就像人們把星星分成各種星座,孰不知這種人為制造的彼此關系并不是它們的自然結構。
故而弗里德曼提出“實證經濟學”以糾時弊,然而他本人卻是新自由主義的貨幣學派的代表,認為“一幣就靈”,這就像阿基米德所說的:“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動地球。”其言壯也,可即使理論上能找出支點、現實中能有這樣的杠桿嗎?
觀其行比察其言更重要。實際上,資本主義國家真正施行的經濟政策,與西方經濟學的主張從來就不一致,典型如羅斯福的“新政”,當時曾被批評為“社會主義”。可以說,迄今并沒有哪種西方經濟學說能夠被完全落實。反過來說,凡是全照西方經濟學那一套來的,無不遭遇災難,如葉利欽聘請哈佛教授薩克斯為俄羅斯高級經濟顧問,以其“休克療法”為改革綱領,最終平民成為最大的犧牲者,奇怪的是,現在有不少人撇開經濟方面來為西方經濟學辯護,真是所謂“一葉障目”啊!
在“前經濟學時代”,先人們發展經濟主要是從務實、從解決問題出發,同樣也曾取得過巨大的成功,如商鞅變法,使秦一躍而為強國。從整體來看,中國古代在當時社會條件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直到康乾盛世仍位居世界第一,那時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也并不比西方平民低。正是出于“嫉妒”,西方在以販賣鴉片竊取財富受阻之后,以槍炮強逼中國打開了大門,從此開始了其赤裸裸的經濟掠奪,在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里,如一座大山沉重地壓在中國人民身上。
如今,這座大山被推翻了,但我們又對西方經濟學這座大山頂禮膜拜。由于當今經濟學家普遍對歷史缺乏常識,甚至習慣用西方視角來看問題,導致中國至今缺乏產生原創性經濟學的學術氛圍。當西方正在興起“行為經濟學”、“信息經濟學”等,對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假設進行反思、乃至顛覆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把西方經濟學看得太完美了呢?
西方經濟學的“強盜邏輯”
西方經濟學的確在某種邏輯上達到完美,這是一種什么邏輯呢?
這里有一個故事可以說明。有五個強盜,搶得100枚金幣,為如何分贓爭執不休,于是他們制定了如下規則:
① 抽簽決定各人的號碼(1、2、3、4、5);
② 由1號提出分配方案,然后5人表決,如果方案超過半數同意就被通過,否則他將被扔進大海喂鯊魚;
③ 1號死后,由2號提方案,4人表決,當且僅當超過半數同意時方案通過,否則2號同樣被扔進大海;
④ 依次類推,直到確定一個多數人接受的方案(當然如果只剩下5號,他就獨吞了)。
現在,假設你抽到1號,你要提出什么樣的分配方案,才能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
如果你認為你夠聰明,不妨把它當作一道考題來認真算計一下,因為據說凡在20分鐘內答出正確答案的,就有望加入微軟,獲得8萬美元以上的年薪。
也許公認的標準答案會把你嚇壞了:1號強盜應該給自己97枚金幣,而給3號1枚,4號或5號2枚。分配方案可寫成(97、0、1、2、0)或(97、0、1、0、2)。
推理的過程是從后往前的。顯然5號巴不得前面所有人都喂鯊魚。4號呢?很危險,如果只剩下他和5號,5號一定投反對票讓他喂鯊魚,以獨吞全部金幣,所以4號惟有支持3號才能活命。那么3號就會提(100、0、0)的方案,因為他知道4號一無所有還是會投贊成票,再加上他自己一票,方案即可通過。
不過,2號推知3號的方案,就會提(98、0、1、1)的方案,因為此時4號和5號比3號主持分配時畢竟有利,所以必將支持2號。
那么,1號針對2號的方案,給3號1枚金幣,而給4號或5號2枚金幣,就能獲得這兩人的支持,加上1號自己的票,即可以多數同意通過方案,獨得97枚金幣。
結果難以置信,推理無懈可擊。然而這個方案惟有在以下三個條件成立時才能真正實現,而這三個條件恰是西方經濟學的三大基礎:
1、理性人(經濟人)假設。在這場嚴酷的游戲中,每個參與者都必須是完全理性的,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這符合個人的某些經驗,卻忽略了另一些經驗,如情感因素的影響,天性中的利他(道德)傾向(源于任何物種都具有繁衍種族的本能)。
2、對數理分析的偏執。個個絕頂聰明,精于數學運算。似乎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辦法。西方經濟學因之而數學化,熱衷于運用各種數學模型,不論它們與實際有多大差異。同時,高深的數理邏輯也讓普通人對經濟學望而生畏,使經濟學成為被少數所謂精英壟斷的工具。
3、規則具有絕對權威。每個人惟有服從到底,每次判決都能順利執行。在西方經濟學中,這就是對私有制的美妙無限夸大,對自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盲目崇信,即使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也只是起著修補匠式的作用。其根源,則是認為資本主義是最好的人類制度,是永恒存在的真理。
現在,我們回頭再看故事本身,顯而易見的結論是,這樣的規則在現實中是永遠不可能產生的,因為既然每個人都能算出自己和他人的處境與方案,當初怎么可能同意制定出這樣的規則呢?除非他原本就甘愿接受貧富分化的結局,或認為自己能成為“幸運”的1號——這樣,他又變成了傻瓜。
哦,這只不過是個故事而已,存在些矛盾之處也沒什么要緊,不然推理的樂趣從哪里來呢?可是,如果這種“強盜邏輯”不再只是虛構,而是被西方經濟學用來經世濟民,那又將造成怎樣的后果呢?
于是,一個在教科書上描繪的巨大的“烏托邦”,在全世界流傳,也在每一個角落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