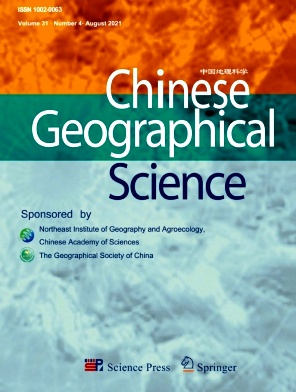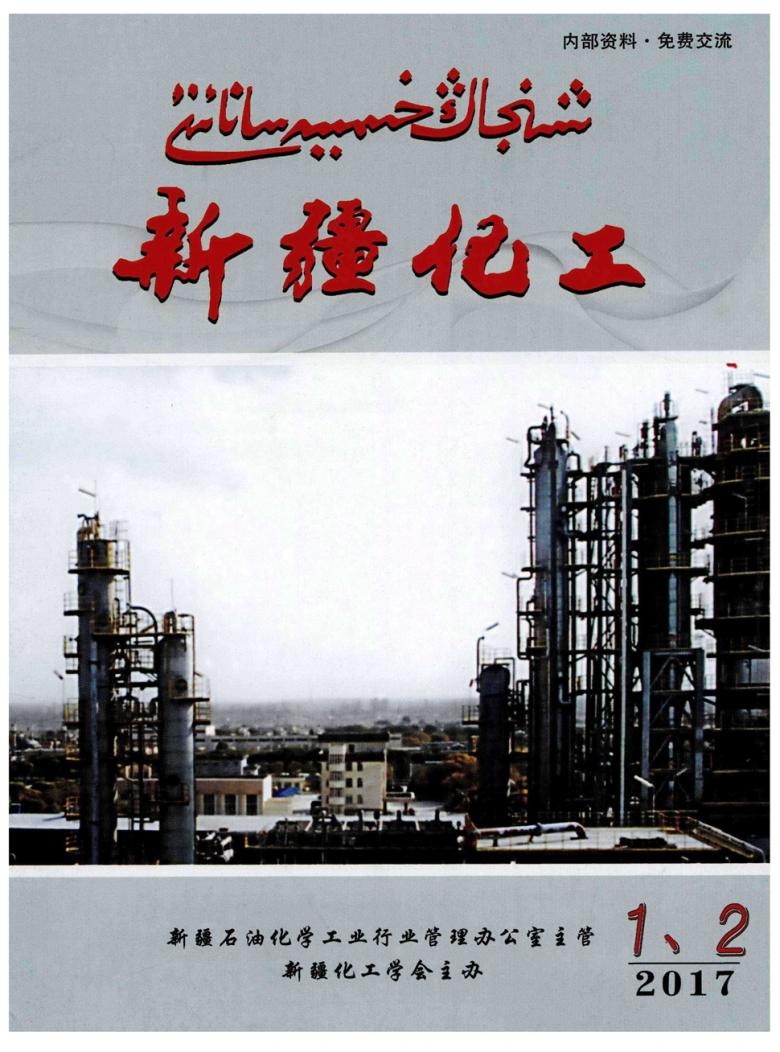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對發展經濟學的影響
魯政委/楊秀云
摘 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論沒有能夠成功地引導廣大發中國家從貧窮走向富裕,發展經濟學自20世紀70 年代末起,便受到嚴厲的批評,學科本身則面臨生存危機。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新制度經濟學向發展經濟學的滲透,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
以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作為思想淵源的制度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產生于19 世紀20 年代初。其產生之后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切爾等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時期;20世紀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爾布雷斯等為代表的從舊制度經濟學向新制度經濟學過渡的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今,以科斯、諾斯和威廉姆森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時期。[1](p.3)而對發展經濟學影響最大的是處于第三階段的新制度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將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介紹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的興起,第二層次闡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對發展經濟學的改進,第三層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處看發展經濟學今后的發展。
一、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方法的興起
隨著二戰以后一批殖民地國家的獨立,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從其誕生之日起,發展經濟學就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休戚相關,其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解釋力和其政策主張的切實效果將直接決定該學科的發展命運。20世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結構主義從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剛性”出發,提出“資本化、計劃化和工業化”“三位一體”的“國家控制教條”(拉爾語),政策推行的結果盡管使一些國家經歷了初期的短暫增長,但最終使廣大發展中國家使陷入了農業停滯、工業蕭條、尋租盛行、二元結構次級分化和經濟發展乏力的惡果。
不僅如此,結構主義在以發展中國家特殊國情為基礎,向理論宏觀化方向發展的同時,其理論基礎卻依然置身于傳統西方主流經濟學中,自覺不自覺地將發達國家的發展經歷作為參照來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張。一句話,沒有將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研究貫徹到微觀層面,結構主義最終造成了發展經濟學微觀與宏觀的不協調,影響了其整體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論建構和政策實踐上的雙重缺陷,最終使結構主義主導的發展經濟學逐漸失去了發展的動力。
在猛烈抨擊結構主義中興起的新古典主義,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為零和完全信息的嚴格假定下,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與發達國家的人們一樣會在理性的驅使下,對價格機制做出靈活的反應。發展中國家只要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經濟發展就會自動實現。既然“價格—市場”機制可以同時解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那么獨立的發展經濟學就無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義“單一經濟學”(哈伯勒語)主張的沖擊下,發展經濟學面臨著“走向死亡”的危險。
事實上,正如尼古拉斯·阿爾迪托-巴萊塔所指出的,“過去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夠充分解釋經濟增長,關鍵是第四個因素—制度—受到忽視。”[2](p.2)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新古典主義,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視了制度對于經濟發展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制度缺陷,這不僅損害了經濟效率,而且也使持續的經濟發展成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經濟學者意識到了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劉易斯在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術進步是表層原因,而由土地制度、產權制度和專利制度等所激發的技術創新熱情才是更為深層次的因素。他對二元結構的分析顯著的解釋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繆爾達爾討論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循環累計因果效應,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進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才能擺脫惡性循環,走向良性循環。庫茲涅茨對大量低收入國家的歷史統計和羅斯托對“傳統社會”的分析,也體現了政治結構、法律體系及社會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根源。但是,在這些學者看來,制度是很難進行嚴格分析的范疇。他們只是描述、羅列了大量的現象,并沒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體系。[3](p.362)激進主義學派的發展經濟學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但他們更多的是從階級的視角來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對發展經濟學產生巨大影響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以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利用科斯和諾斯等人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對以資源、技術和人的偏好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思想提出了挑戰,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新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家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4](p.41) 二、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1、在方法論上
新制度經濟學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對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在對新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論文的詳細考察中發現,“其研究方法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入手。” [5]諾斯也強調:“歷史至關重要。……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過去只有在被視為一個制度演進的歷程時才可以理解。”[6](p.2)這對后來運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產生了深遠地影響。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對“運用啟發式研究”的推崇即與科斯、諾斯一脈相承。他們期望“運用啟發式研究來詳細闡述選擇—行動的情況以及這些情況內在的約束和刺激”,傳統經濟發展理論特別是新古典理論“被過度概括模型的危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啟發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環境適時并安置可變物進行詳細說明而得到避免 。”在現實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制度分析可允許我們“穿透”社會事實而不是遠離事實的分析模式來對發展問題予以說明。同時,通過“跨文化的啟發式研究”得到大量的個案積累,也“應該產生對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內在的行動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實上,不同國別發展績效的差異,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釋,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許多情況下對發展績效會有更大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個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對不同時空中制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具有的較大異質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見。新古典主義的約束條件根本不足以表達這諸多的復雜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將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意識形態等制度因素給排除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過度簡單化傾向,而且還克服了其把經濟理論置于抽象時空的歷史虛無主義。
以赫希曼、繆爾達爾為代表的早期發展經濟學家也曾就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進行過個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從總體上來把握有關變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倡導方法論個人主義,認為“對社會單位的分析必須從具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開始”,“‘社會’、‘人民’、‘企業’或‘政黨’不是再被認為是‘一個像個人一樣行動的集體’”。[7](p.4)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學者也明確指出,“采取這樣的(啟發式研究)方法時,我們不必設想人類經驗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為諸如‘國家’和‘社會’、‘市場’和‘經濟集團’或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類籠統的東西。我們可以取而代之地設想交換關系存在于所有社會之中,市場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動情況中的角色既面臨約束也面臨機會,約束和機會的存在依靠各種結構的環境所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對特定環境下個體行為的重視有可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建立堅實的微觀基礎,克服結構主義微觀基礎建構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義過于抽象的不足。
雖然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引入制度作為分析對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義方法的“內核”,具有與新古典主義一樣的靜態和比較靜態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諾斯和福格爾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則通過對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歷史的考察,更具有動態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將靜態方法用于分析發展這一動態問題的窘境。
2、在發展的決定因素上
反貧困首先始于對制約發展因素的探討。所以對發展決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依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和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認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決定因素,形成了過分強調資本形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資本論”。根據這種理論,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源在于資本稀缺。納克斯提出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和納爾遜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則進一步展示了資本不足與發展停滯的惡性互動關系。
但“唯資本論”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在發展中國家資本不足的同時,廣泛地存在著資本低效配置和資本浪費現象。正如麥金農所指出的,“在所謂資本匱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門遭受供給瓶頸限制的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卻是過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廠和設備。”新制度經濟學指出,“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發揮作用。制度至關重要。”[2]( p.122)這充分說明,資本不足不是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發達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