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jì)劃生育跨入法治時(shí)代
鄧 科
經(jīng)過(guò)20多年的研究論證,《人口與計(jì)劃生育法》將于9月1日正式實(shí)施,這被很多人認(rèn)為是“我國(guó)人口事業(yè)發(fā)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
計(jì)劃生育的立法從1970年代末就開(kāi)始了,整個(gè)過(guò)程可以說(shuō)“一波三折”,經(jīng)歷了1978年、1982年、1988年、1993年四次論證、起草,但皆因“條件不成熟”沒(méi)有出臺(tái)。1998年,計(jì)劃生育立法被第五次“擺到了臺(tái)面上”,經(jīng)過(guò)三年多的努力,2001年12月29日終獲通過(guò)。
關(guān)于“一波三折”的原因,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法工委副主任張春生說(shuō),除去沒(méi)有國(guó)際上立法經(jīng)驗(yàn)可供參照外,制定這部法律本身還存在一個(gè)難點(diǎn),這就是,法律中規(guī)定的政策、措施、辦法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的過(guò)快增長(zhǎng),又要能為國(guó)際社會(huì)基本接受。多年來(lái),在這個(gè)問(wèn)題上進(jìn)行了艱苦的探索。
而《人口與計(jì)劃生育法》的出臺(tái),一方面表明這方面的探索已取得了相當(dāng)共識(shí),另一方面,也是因?yàn)橹袊?guó)計(jì)劃生育已經(jīng)實(shí)現(xiàn)了重大跨越,具備了法治化、規(guī)范化的基本條件。
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人口與發(fā)展研究中心副教授穆光宗博士則稱,這標(biāo)志著中國(guó)計(jì)劃生育已經(jīng)開(kāi)始從行政強(qiáng)制為主導(dǎo)向以群眾的滿意程度為第一標(biāo)準(zhǔn)的新階段轉(zhuǎn)變。
焦慮時(shí)代的計(jì)劃生育
中國(guó)大規(guī)模的計(jì)劃生育并非始于人們通常印象中的改革開(kāi)放之后,而是從1970年代就開(kāi)始了。
當(dāng)時(shí),關(guān)于計(jì)劃生育的提法是“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歲、女23周歲才結(jié)婚;“稀”指兩胎要間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兩個(gè)孩子。
1978年3月,計(jì)劃生育被寫(xiě)進(jìn)了憲法。就在這一年,中國(guó)進(jìn)入了一個(gè)新的歷史時(shí)期。
“當(dāng)時(shí)很多人都有很強(qiáng)的‘強(qiáng)國(guó)夢(mèng)’,都想用最快的速度把國(guó)家搞上去,在這種急切的心情下,對(duì)人口實(shí)行‘急剎車’成為了一種當(dāng)然的選擇。”穆光宗博士說(shuō)。
1980年,新華社公布了中國(guó)人口發(fā)展進(jìn)程百年預(yù)報(bào):如果按中國(guó)當(dāng)時(shí)的生育水平延續(xù)下去,2000年中國(guó)人口要過(guò)14億。
有媒體報(bào)道說(shuō),這一消息發(fā)布后,引起很大震動(dòng)。一度曾有人主張“我國(guó)人口近期宜取負(fù)數(shù)發(fā)展”,建議20年內(nèi)采取一切措施,使每年人口出生率低于人口死亡率,進(jìn)入人口的負(fù)增長(zhǎng)。
但這將意味著有一半左右的夫婦終生不能生孩子或至少20年內(nèi)不能生孩子。因此響應(yīng)者不多。
另一種觀點(diǎn)則影響很大。幾位科學(xué)工作者建議從1980年起大力提倡一對(duì)夫婦只生一個(gè)孩子,這樣到2000年人口自然增長(zhǎng)率可接近零,全國(guó)人口可控制在11億以下。
這個(gè)方案曾對(duì)我國(guó)的人口政策產(chǎn)生了直接影響。
1980年出現(xiàn)了計(jì)劃生育發(fā)展史上標(biāo)志性的事件,即中共中央發(fā)表了《關(guān)于控制我國(guó)人口增長(zhǎng)問(wèn)題致全體共產(chǎn)黨員、共青團(tuán)員的公開(kāi)信》,鄭重向全國(guó)發(fā)出了“一對(duì)夫婦只生一個(gè)孩子”的號(hào)召。
隨后,中國(guó)的計(jì)劃生育政策在數(shù)量上進(jìn)一步收緊。“晚婚、晚育、少生、優(yōu)生”取代了“晚、稀、少”的提法。中國(guó)人口學(xué)會(huì)副會(huì)長(zhǎng)、北京大學(xué)人口所教授張純?cè)f(shuō),兩種說(shuō)法相比較,晚婚、晚育沒(méi)有變化,少生從允許生二孩調(diào)整為基本只準(zhǔn)生一孩。稀是就生育間隔而言的,只生一孩,就不存在間隔了,稀被取消了。
“這一調(diào)整在城鎮(zhèn)采取一些必要措施還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在農(nóng)村卻困難重重。”張純?cè)淌谡f(shuō)。
一位研究者指出,拋開(kāi)農(nóng)耕文明形成的“多子多福”的觀念不談,僅就農(nóng)村的生產(chǎn)方式、社會(huì)福利狀況以及偏遠(yuǎn)地區(qū)的醫(yī)療條件而言,對(duì)家庭成員的依賴也使只生一個(gè)、尤其是只生一個(gè)女孩,成為一件難以接受的事。
在這種情況下,計(jì)劃生育的推行在農(nóng)村遇到了困難,矛盾一度變得十分突出。
對(duì)此,中央及時(shí)作出了調(diào)整。重新規(guī)定,在農(nóng)村仍要繼續(xù)提倡一對(duì)夫婦只生一個(gè)孩子,但也要適當(dāng)放寬生育第二個(gè)孩子的條件。
行政措施推行:“功不可沒(méi)”
很顯然,政策調(diào)整后群眾的生育愿望和政策要求之間仍然有差距,計(jì)劃生育僅靠公民的自覺(jué)行為還不可能實(shí)現(xiàn)。
從現(xiàn)實(shí)來(lái)看,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從高生育水平向低生育水平轉(zhuǎn)變用了100多年的時(shí)間。這種轉(zhuǎn)變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往往是同步進(jìn)行的,也就是說(shuō),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生育意愿下降,從而導(dǎo)致整個(gè)社會(huì)的生育率下降。
但是作為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中國(guó)卻不允許重復(fù)這條路。因?yàn)榻?jīng)濟(jì)發(fā)展在對(duì)生育率的下降發(fā)揮拉動(dòng)作用之前,已經(jīng)受到了人口問(wèn)題的制約。
在不能坐等依靠經(jīng)濟(jì)發(fā)展來(lái)降低生育水平的情況下,借助行政強(qiáng)制力解決人口問(wèn)題就成了合乎邏輯的必然選擇。況且中國(guó)要用30年的時(shí)間完成西方用了100年的人口轉(zhuǎn)變,這更加重了對(duì)這一力量的依賴。
穆光宗博士說(shuō),在改革開(kāi)放后的頭十年里,計(jì)劃生育的推行基本上是行政強(qiáng)制型,采用的是社會(huì)制約機(jī)制。
這個(gè)階段的工作重心在人口數(shù)量的控制上,可稱為“以數(shù)為本”的階段。
對(duì)于這個(gè)時(shí)期的工作成效,中國(guó)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于學(xué)軍稱其“功不可沒(méi)”。他認(rèn)為最大的成績(jī)就是使現(xiàn)行的人口與計(jì)劃生育政策得到了穩(wěn)定和完善,為1990年中國(guó)人口轉(zhuǎn)變歷史性的飛躍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
與此同時(shí),這個(gè)時(shí)期暴露出來(lái)的一些問(wèn)題也得到了人們的關(guān)注。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法工委副主任張春生說(shuō),長(zhǎng)期以來(lái),地方政府以及計(jì)劃生育部門(mén)主要是依靠強(qiáng)有力的行政措施推行計(jì)劃生育的,有的在執(zhí)法中還存在侵犯公民人身權(quán)、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違法行為,影響了黨群、干群關(guān)系,造成了一定負(fù)面影響。
為了規(guī)范計(jì)劃生育行為,國(guó)家計(jì)生委出臺(tái)了包括不準(zhǔn)非法關(guān)押、毆打、侮辱違反計(jì)劃生育規(guī)定的人員及其家屬,不準(zhǔn)毀壞違反計(jì)劃生育規(guī)定人員家庭的財(cái)產(chǎn)、莊稼、房屋等內(nèi)容在內(nèi)的一些規(guī)定。
這些規(guī)定使計(jì)劃生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規(guī)范,但專家指出,這些問(wèn)題往往與指標(biāo)、任務(wù)聯(lián)系在一起,要想徹底解決,還得依靠法制的建設(shè)和工作模式的轉(zhuǎn)變。
轉(zhuǎn)變的社會(huì)基礎(chǔ)
這種轉(zhuǎn)變的萌芽在進(jìn)入1990年代后出現(xiàn)了。一些地方除了行政強(qiáng)制力外,引入了利益導(dǎo)向機(jī)制。有的把計(jì)劃生育與扶貧結(jié)合起來(lái),同是貧困戶,生一個(gè)的就比生三個(gè)的享受更多的政策優(yōu)惠。
在此基礎(chǔ)上,“兩個(gè)轉(zhuǎn)變”被作為重點(diǎn)提了出來(lái):即由孤立地就計(jì)劃生育抓計(jì)劃生育向與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緊密結(jié)合,采取綜合措施解決人口問(wèn)題轉(zhuǎn)變;由以社會(huì)制約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導(dǎo)向和社會(huì)制約相結(jié)合的機(jī)制轉(zhuǎn)變。
這些轉(zhuǎn)變的實(shí)質(zhì)就是由“以數(shù)為本”轉(zhuǎn)為“以人為本”,計(jì)劃生育不僅僅是一項(xiàng)關(guān)于數(shù)量、指標(biāo)的工作,更要考慮人的利益、需求、發(fā)展。
這些轉(zhuǎn)變從目前來(lái)看還是初步的、局部的,大都集中在經(jīng)濟(jì)條件較好的地區(qū),但它所展示的方向令人肯定。
在經(jīng)歷了10多年舊有的工作模式后,計(jì)劃生育在1990年代悄然發(fā)生了重大變化。
研究者認(rèn)為,這與整個(gè)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生的重大變化密切相關(guān)。北京大學(xué)人口所教授陸杰華認(rèn)為,隨著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建立與完善,計(jì)生工作出現(xiàn)了許多新問(wèn)題、新情況與新現(xiàn)象,例如流動(dòng)人口計(jì)劃生育管理問(wèn)題、人戶分離的計(jì)劃生育管理問(wèn)題等等。這些新問(wèn)題對(duì)傳統(tǒng)的計(jì)生工作模式產(chǎn)生了巨大的沖擊。但必須承認(rèn),正是這種沖擊,促使政策決策者產(chǎn)生了管理理念的創(chuàng)新。
中國(guó)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于學(xué)軍認(rèn)為,隨著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啟動(dòng),整個(gè)社會(huì)和經(jīng)濟(jì)的運(yùn)轉(zhuǎn)機(jī)制、政府和個(gè)人之間的關(guān)系、人們的價(jià)值觀和理想追求、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包括婚姻和生育觀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在生育的問(wèn)題上,人們也有了更多的靈活性和選擇性。
可以說(shuō),在影響生育水平的兩大重要因素,即政策作用和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作用中,后者起著越來(lái)越大的決定性作用。
影響計(jì)劃生育工作模式的另一個(gè)因素就是我國(guó)的人口轉(zhuǎn)變?cè)?990年實(shí)現(xiàn)了歷史性飛躍,中國(guó)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下降,并持續(xù)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即一對(duì)夫婦生小孩在2個(gè)以下)。按照國(guó)家計(jì)生委主任張維慶的劃分,我們從降低生育水平階段過(guò)渡到了穩(wěn)定低生育水平階段。這兩個(gè)階段應(yīng)該有不同的管理模式和工作機(jī)制。
法制化軌道
國(guó)家計(jì)生委主任張維慶曾指出,50多年來(lái)中國(guó)人口與計(jì)劃生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史,是一部曲折、悲壯、輝煌的歷史。
一個(gè)10多億的人口列車,經(jīng)過(guò)幾十年的摸索、總結(jié),如今正式駛上了法制化的軌道。
這種探索在1990年代終于形成了一整套經(jīng)驗(yàn),其中包括成熟的生育政策,“三三三二一”工作模式以及“以人為本”原則的確立。可以說(shuō),這些構(gòu)成了《人口與計(jì)劃生育法》這部關(guān)乎中國(guó)“國(guó)際形象”的法律出臺(tái)的先決條件。
一位專家指出,如果退回到10年前,這些顯然都還不夠成熟。
《人口與計(jì)劃生育法》的核心是穩(wěn)定現(xiàn)行生育政策,既不收緊也不放松。與此同時(shí)它也明確了實(shí)現(xiàn)這一政策的途徑并不是過(guò)多地依賴行政強(qiáng)制力,而是建立利益導(dǎo)向和社會(huì)制約相結(jié)合的機(jī)制,依法行政、依法生育。
從現(xiàn)實(shí)來(lái)看,依法行政的一個(gè)重要前提就是把基層的工作人員從指標(biāo)和任務(wù)的重壓中解放出來(lái),這就涉及到考核體系和工作方式的改革。因此這部法的推行還必須在不斷的改革創(chuàng)新中完成。
與此相關(guān)的一個(gè)問(wèn)題是,依法行政、行為規(guī)范后會(huì)不會(huì)造成計(jì)劃生育工作力度減弱,引起生育率的反彈?國(guó)家計(jì)生委宣教司負(fù)責(zé)人認(rèn)為不會(huì)出現(xiàn)這種情況,因?yàn)椤肮ぷ髂繕?biāo)、工作力度并沒(méi)有因此改變”。
實(shí)際上從研究來(lái)看,以人為本、優(yōu)質(zhì)服務(wù)對(duì)低生育水平的穩(wěn)定會(huì)起到積極的效果。于學(xué)軍說(shuō),1980年以來(lái)的多次生育意愿調(diào)查結(jié)果表明,育齡婦女的意愿生育水平低于實(shí)際生育水平,這恰好從一個(gè)側(cè)面說(shuō)明了中國(guó)育齡婦女中非意愿生育的存在,意味著中國(guó)的育齡婦女并沒(méi)有完全掌握自主的生育權(quán)利。從這方面來(lái)說(shuō),優(yōu)質(zhì)服務(wù)可發(fā)揮作用的空間很大。
對(duì)于一個(gè)有著10多億人口的大國(guó)來(lái)說(shuō),人口問(wèn)題確實(shí)關(guān)乎著它的生死存亡。《人口與計(jì)劃生育法》的出臺(tái)標(biāo)志著這輛巨大的人口列車駛上了一條新世紀(jì)的軌道。
藥理學(xué)通報(bào).jpg)
.jpg)
土資源情報(bào).jpg)
.jpg)
教材教學(xué).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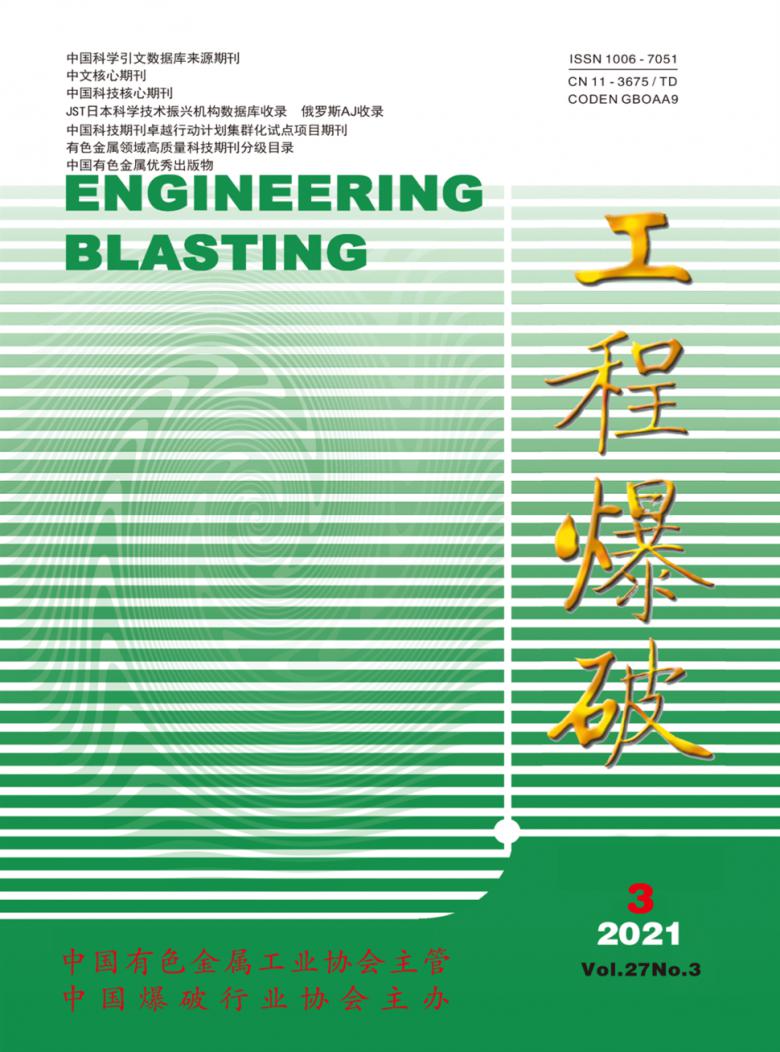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