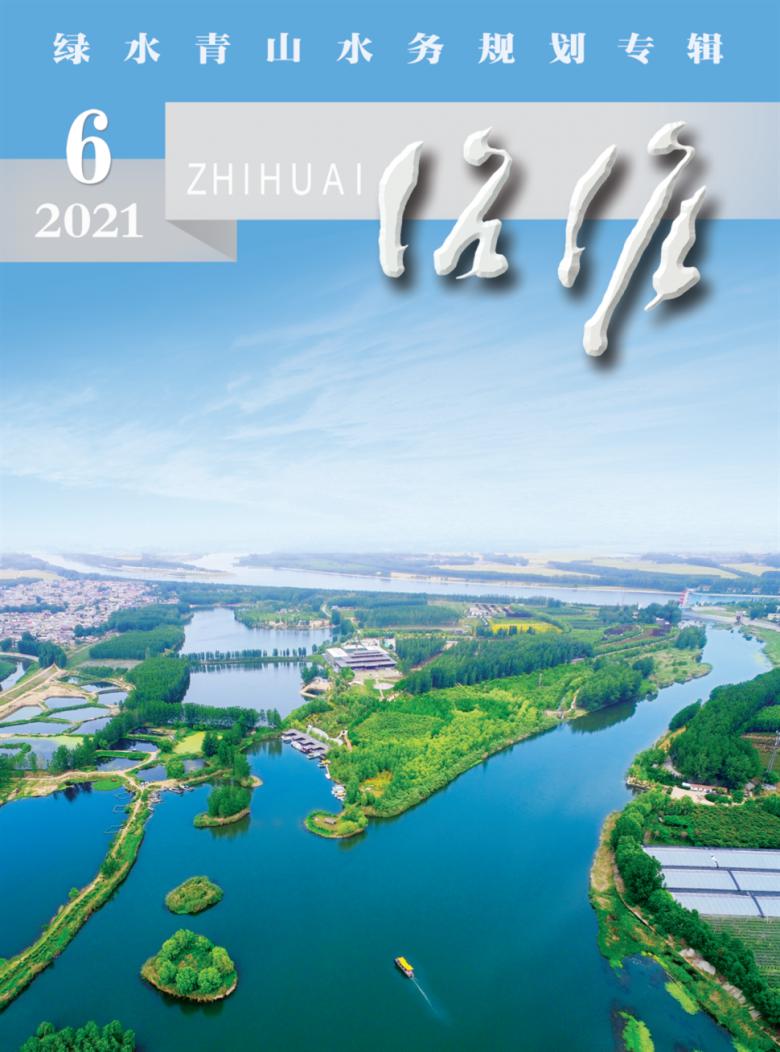農村生育取向和家庭贍養義務——從土地制度角度分析
佚名
在研究三農問題的諸多文獻中,絕大多數將農村的人口生育問題作為一個外生變量,著眼點大多放在了研究既定的人口因素對農地制度選擇的制約,同時卻沒有分析既定的農地制度對農民生育取向和家庭贍養義務履行的重大影響。事實上,這種影響要比基層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要大得多。
一、蓋爾.約翰遜的模型解釋
一些學者將中國農村人口過快增長的原因歸結為以下幾點:農村缺乏應有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家庭為主的田間勞動需要更多的男性勞動力,客觀上刺激和強化了農民“多子多福” 、“重男輕女”的思想;農村相對于城市人口的撫育成本低得多;農村人口素質較低,普遍存在著“多子多福” 、“重男輕女”等傳統觀念。而劉守英、蓋爾.約翰遜等則認為農村的財產制度特別是土地財產制度和其所決定的經營方式是影響農民家庭生育決策的主要因素。蓋爾.D.約翰遜的研究對此方面進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提出的一個簡單的模型表明,家庭在生育方面的決策,如同在組織資源方面一樣是具有理性,家庭生育率是由家庭想要得到的孩子數量和實現這一預期愿望的成本決定的。如果村子里的土地是根據人口變動來分配的話,那么,當一些制度建立后,多生育一個孩子帶來的重要好處是收入或資本的轉移。他們的案例研究表明,1987年停止了周期性土地調整的農村改革試驗區貴州省湄潭縣,1989年的人口出生率是全省的83%,而1992年就下降到了全省的62%。而在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中韓國和臺灣的農民大多得到了自己的土地,人口生育率從50年代初的高于中國大陸下降到80年代僅相當于大陸的一半;韓國和臺灣都制定了生育計劃,但都沒有對多生育制定處罰,這表明了適當的財產制度和政策激勵可能比行政手段更為有效。在農村地區,由于沒有其他的養老手段,養兒防老的客觀需要使農村地區的生育率難以迅速下降。在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之前,土地所有權可以作為一種替代的養老手段。如果既沒有社會保障體系,又沒有土地所有權,對大多數社會里的農村居民來說,為了應付年老時的疾病、傷殘而擁有一個兒子是很重要的。有些學者認為由于計劃生育的實施,在1970-1990年代的30年里中國少出生了3億人。但這一論斷的假設是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在1970年的高水平上。而這一假設是不成立的。中國在這30年里的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不會使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不變。教育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上升都會降低人口出生率。發展中國家的隨機抽樣表明,“在過去的四分之一個世紀里,中國并不是唯一大幅度降低生育率的國家”;“在未來的20年里,計劃生育政策對控制人口增長的作用可能不會很大”。
姑且不論蓋爾.約翰遜的解釋是否完全符合事實,但他確實指出了這樣一點,即,由于集體所有制中內含的福利分配制度安排,它本身就起著刺激人口生育意愿的內生作用(劉守英,1999)。從這一方面來看,“新增人口,不再分地”的新制度安排,將對抑制人口增長起到積極的作用。1989年對貴州湄潭開始試點“新增人口,不再分地”制度,1999年對該縣的調查得出結論:“新增人口,不再分地”的制度對農民的收入分配、土地占有、勞動力流動都有積極的作用,并對人口生育意愿有正的影響。
二、土地制度與人口生育取向
在中國,任何一種土地財產制度都必須接受人口生育的考驗,如果客觀上起到了刺激農民增加生育的作用,所帶來的制度收益不能抵消人口增加的影響,那么這種土地制度就不能稱之為合理的財產制度。我們在考慮農村計劃生育時,往往希望用行政手段,用層層落實指標的辦法來實現基本國策。強調農民生育觀念的落后,同時卻忽視了農民生育過多的根本原因。事實上,在既定的土地財產制度下,在不斷存在調整土地可能性的情況下,生育較多的子女特別是男孩,是農民最穩妥的投資(家庭的男性后代將有權利并在事實上能夠分得土地),也是對自己土地的保護(如果自己家的成年男性后代較少,那么在生育多的家庭的要求下,自己家的土地勢必要被分割出去一部分)。既然作為土地所有者的集體的成員不斷增多,每人所均攤的土地面積越來越小,那么人口增加較快的家庭將能獲得相對更多的土地,而人口增加較慢或者減少的家庭就只能保留越來越少的土地。集體里所有的家庭即使為了保護現有的耕地和宅基地,也必須參加這種生育的競賽。在計劃生育工作、自然生育極限和撫養能力的限制下,大多數村落逐漸會形成一種“生育競賽的均衡”。土地的調整也會實現一定的穩定期,但是一旦有家庭在生育競賽中落敗(例如沒有子女或者多為女孩),隨之而來的土地調整即使再小,對這個家庭來講卻往往是致命的打擊。不用太多,一年幾個這種生育競賽失敗家庭的事例就足以教育整個村莊的農民:一定要多生而且要生育男孩,才能保證家庭的基本經濟安全。在這種群體意識的長期影響下,多生育和生男孩的觀念就由一種個體的理性經濟選擇上升到了一種在某種程度上脫離開經濟因素的倫理選擇,這可以解釋為什么個別家庭寧愿流離失所也要生男孩,但絕大多數家庭還是會選擇經濟上最合算的生育方案。當生育過多的子女時(如四五個以上,不同地區有所不同),更沉重的撫養負擔和面臨的經濟懲罰都會使大多數的家庭在經濟上變得不再合算而放棄繼續生育。農村基層通過行政強制手段所達到的降低生育率的努力在福利化的土地制度對農民的生育刺激面前往往顯得無力,而且越是經濟不發達的農村,土地對農民家庭的重要性就越強,農民進行這種生育競賽的動力必然更強大,這也許就是“越窮越生”背后的經濟根源。
現行的計劃生育制度是和戶籍制度緊密結合的,離開了牢固的戶籍制度,生育計劃便無法貫徹實施。而大多數鄉村的土地調整又是和農民的戶籍所在密切相關,高度行政化的生育計劃和土地分配制度通過戶籍連成一體。維持這種生育計劃的成本就是維持戶籍制度,但是今天經濟發展要求勞動力自由流動和公民權利自覺性的提高,要求戶籍制度必須逐步的加以改革、取消,因此最終我們應當也必須建立一種以自愿的經濟手段調節人口而不是主要依靠行政力量的“計劃”手段的制度。1950年代末以后我們的生育強度達到了其他國家所沒有達到的程度。中國農村人地比例超過印度等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表明中國農村家庭即使在強大行政壓力下的生育沖動仍然強烈,在人地比例極端失衡的情況下,大多數的家庭所采取的生育方案對農民整體來講無異于自殺,這就是所謂個體的理性導致了集體的非理性。但是我們應當看到,在類似韓日臺等國兼顧農戶土地權利保障的地區,如果農村人地比例到了一定程度,農民并不會采取過度生育的策略,大多數人并不會因為所謂的習俗就愿意讓自己家庭破產。我國解放戰爭中后期在廣大解放區開展的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產生大量的自耕農,生產的積極性大大提高,生育趨向就和后來的農民不一樣。農業集體化運動以后,人口的超常增長與其說是人民對于政治口號的響應,不如說是農民家庭在鼓勵生育的土地財產制度下的理性選擇。當前一些從事三農問題研究的專家提出了鞏固、完善土地的福利功能的理論,這些帶有平均主義色彩的方案是否會進一步造成農民生育的增加?如果進一步刺激農民增加生育或者強化現有較高生育率,那么就應當重新考慮這些方案是否真的能夠促進農村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的持續發展。
三、不履行贍養義務:道德滑坡還是制度原因?
農村出現的以兒女不履行贍養義務為代表的道德滑坡,一定程度上就和農村集體組織調整土地的做法有關。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以前,農民的主要財產權耕地和房地產由自己支配,老年人就可以使用不分配或者不給予遺產的方式,對子女中不“孝順”的成員進行懲罰。這種懲罰可能發生的概率很小,但是一旦發生,對個人和村落的影響非常大,因為在鄉村經濟中,一個人的名聲不好還不是致命的問題,但如果沒有自己的房屋和土地就只能淪為佃農或流民,其進行經濟活動和建立家庭的能力都會顯著下降,再背負著不孝的罵名,生存甚至都會受影響(諾斯、青木昌彥都十分強調非正式規則對社會變遷的影響,實際上在這個問題上是諾思所說的意識形態起了作用)。村落中個別的不孝子孫受到的家庭的懲罰,對于整個村落的家庭成員來講都是個教訓,這就會進一步減少“不孝順”等不道德行為,也會減少這種剝奪子孫繼承權的極端做法的使用。在農業合作化運動和土地收歸集體所有以后,雖然農戶家庭對不道德成員的繼承權剝奪大大削弱了,但是鄉村政治生活和對個人道德約束的加強,使得家庭道德的水準不至有明顯的下降。而農村改革以后,鄉村政治生活對個人道德的約束基本消失后,農戶家庭對成員道德的物質約束作用的薄弱就凸顯出來,對于子女中不負擔贍養責任的成員,農戶家庭的年長成員無法采用剝奪期繼承權的辦法進行懲戒。因為在集體擁有宅基地和耕地所有權,并且有權進行分配和處置的情況下,農戶家庭的年長成員基本不能決定子女在集體中取得宅基地和耕地的權利,這就失去了家庭對成員基本的也是最極端的制裁手段。而當幾乎所有的農戶家庭都對不孝行為失去物質的制裁手段時,年老的家庭成員已經不再是家庭經濟的核心,而成了負擔;在日益嚴重的人地壓力下,年老的家庭成員受到物質匱乏的虐待幾乎成了廣泛的選擇,這樣的選擇對于受制于既定農地制度下的農戶家庭來講是維持簡單再生產的理性選擇,許多農村的老年人甚至已經心甘情愿得接受這種境遇。集體組織原本是試圖改造農民教育農民的,但客觀上卻起到了降低道德水平的作用。當我們譴責這種不道德行為時,不要忘記,少數人道德水平低那是個人的品德問題 ,如果普遍的出現道德危機 ,那就是制度出了問題。不改變制度上特別是經濟體制上的缺陷,無論多少道德文章的說教都不會達到目的。家庭是社會的基礎,而家庭道德水平的下滑最終將影響到農村社會倫理的方方面面,最終會造成農村商業活動的極端短期化行為和無效率。當農村家庭單個子女對老年父母的贍養意愿下降時,單個的子女既然對父母的效用降低了,如果要保持將來年老時的基本生活水準,生育盡可能多的子女就是必然的結果。子女贍養意愿的降低進一步強化家庭的生育意愿,但是因為土地調整因素的存在和不同地區的計劃生育執行強度不同,這種意愿并不一定表現為生育率的上升。
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是要確立廣大農民的私人決策權,有限的私人決策權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張曙光,2002),導致農民對未來預期的不穩定。農村人口的生育取向和所謂的道德滑坡皆與此有關。最為重要的是,隨著中國改革進程的推進和市場化程度的加深,正在形成新的“公地災難”:不僅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而且,一些握有調整土地權力的人正在通過各種方式變相的剝奪農民的土地,從中漁利。在我國加入WTO的背景之下,國外大資本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室,并與本土的新權貴們結合在一起,形成所謂“新權貴資本主義”,這足以令中國的民間資本望塵莫及。因權勢而有錢財,比因錢財而有權勢更為危險得多,無論何時,我們始終不能不警惕權貴資本家階層的悄然登臺。
主要
1、諾斯,1994,中譯本,《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店。
2、奧爾森,1993,中譯本,《國家興衰探源》,商務印書館。
3、溫鐵軍:《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讀書》1999(12)。
4、林毅夫、蔡日方、李周,1994,《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三聯書店。
5、遲福林主編,2000,《走入21世紀的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國經濟出版社。
6、葉劍平等,2000,《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研究》,中國農業出版社。
7、郭書田,1993,《變革中的農村與農業》,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8、蓋爾.約翰遜:《中國農村人口政策的缺陷與選擇》,《中國農村經濟》1994(6)。
9、管清友:《由財政壓力引發的農民超負擔:一個解釋》,《上海經濟研究》2002(7)。
10、鐘偉:《2002年企業家最關注之大事記》,香港文匯報、《中國改革報》雜志社2002年中國的經濟、改革、企業"專家論壇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