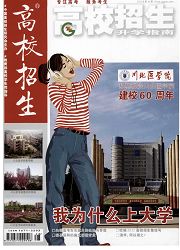國民政府十年(1939—1949)基層民意機關建設數量分析
未知
【內容提要】1939年,為擺脫內憂外患的困境,國民政府重拾地方自治,推行新縣制。在縣及縣級以下設立基層民意機關,然而,從1942、1944、1947年三個典型時間階段看,稍能體現民主性質、國民政府又三令五申、傾力打造的基層民意機關并沒有如期建立,這就使民主政治喪失了基本的組織基礎。因此,所謂地方自治只能是無法實現的虛幻夢想了。
【摘 要 題】民國史研究
【關 鍵 詞】國民政府/基層民意機關/民主政治
【正 文】 1939年,國民政府在內憂外患中改革舊的基層組織,頒布《縣各級組織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確立新的縣政體制,即新縣制。新縣制重拾地方自治,在縣及縣以下逐級建立基層民意機關,為此,國民政府大張旗鼓地宣揚:建立民主政治,從基層做起。 從1939年起,國民政府就著手在其控制的范圍內建立起從保甲到鄉鎮及縣市的各級民意機關,即保民大會、鄉鎮民代表會、縣參議會。同時,國民政府還大造輿論,大肆宣揚:民主政治從基層開始。國民政府為什么在抗戰最為艱苦——人力、物力、權力需要相對集中的時候,卻拋出“民主繡球”,讓蕓蕓眾生各表其意、各抒己見呢?
一新縣制下基層民意機關建立的背景
(一)面對困境的政治反彈 國民黨在抗戰時期加緊實施“地方自治”,建立基層民意機關,首先可以理解為它是一種自然性的政治反彈。任何政府在遭遇危急的時刻,都會采取一些應急措施來度過難關。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國民政府選擇此舉確實事出有因。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政府丟失了沿海地區和東南工業中心,退居以四川為中心的大后方,使政府一貫仰仗的海關和工商業稅收幾近斷絕,在飽經內戰破壞而又相對貧瘠的大后方,國民黨政府面臨重重困難,承受著來自國內外的巨大壓力。國際上,隨著世界大戰的爆發和演變,英美與中國關系日益密切,英美對國民政府的專制與腐敗則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中國內部的不協調,國民黨蔣介石政治的不民主,影響了軍事,英美對此也表示不滿”。[1] (P. 134) 從國內看,為了消除后方人民對政府專制的不滿和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資源與日軍作戰,蔣介石希望通過建立基層民意機關,向社會各界表現出一定的民主姿態,一方面能夠及時征兵征糧,補充軍需和兵員以應付危險形勢、穩定政局;另一方面又能達到強化基層政權、增強政府統治效能。 (二)國民黨加緊推行“地方自治”,建立縣各級民意機關,也是同共產黨爭奪民眾,鞏固其政權基礎的需要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各根據地相繼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尤其是農村各級基層政權普遍建立起來。中國共產黨在各級基層政權中進行的民主選舉嘗試,使得農村中幾千年來倍受剝削壓迫的勞苦大眾第一次翻身得解放、當家作主人,所以他們革命熱情高漲,踴躍參軍保衛新生政權,這也為中國共產黨力量的迅速增強和堅持敵后抗戰提供了可靠保證。與此相對比,國民黨在農村的基層政權則相對薄弱,而且聲名狼藉。為了同共產黨爭奪民眾,鞏固后方,達到“限共”、“防共”的目的,國民黨從抗戰爆發后也日益關注農村工作,建立基層各級民意機關這一具有民主精神的組織機關就是政府借以改變民眾對專制政府看法的一種手段。 (三)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實行地方自治,建立基層民意機關也并非一時興起,它有著深厚而長久的歷史淵源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許多先進知識分子都在洋人堅船利炮的轟炸下,開始審視自己的國力、制度和文化。康有為、梁啟超都曾對地方自治抱有幻想。康有為曾多次上書光緒帝,指出唯有變法,召開國會,“各省設民政局,舉行地方自治”,“凡善良之政體未有不從自治來也”[2] (P. 37),才可最終圖強,以救中華。梁啟超也說:“就天下萬國比較之,大抵其地方自治之力愈厚者,則其國基愈鞏固,而國民愈文明。”[3] (P. 47)一代偉人孫中山先生更對地方自治情有獨鐘,他希望通過建立牢固的基層民主,最終使中國走上富強民主之路。 從1928年起,國民政府就一直聲稱要完成孫中山先生的遺愿,實行地方自治,所以頒布《縣組織法》,制定了地方自治原則,準備建立縣各級民意機關。但隨著內戰的爆發和擴大后,國民政府很快便用保甲制度取代了地方自治,縣各級民意機關根本沒有建立,更無所謂的民選、民議等四權的行使。雖然如此,孫中山先生的先進思想卻并未受到人們的懷疑和拋棄,相反,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民主人士認識到孫中山地方自治思想在中國實踐的艱難和重要,更加信仰三民主義。所以,這時期孫中山先生的地方自治思想仍是凝聚社會力量、鼓舞民心和士氣的有力武器。 于是,在內憂外患中,國民政府開始大張旗鼓宣傳地方自治,并不遺余力地推廣各級民意機關。
二縣各級民意機關建設狀況
(一)1939年民意機關在理論上確立 從1939年起,國民政府開始推行新縣制,縣各級民意機關從理論上首先確立。 《綱要》規定:縣為自治單位;縣以下為鄉(鎮),鄉(鎮)內之編制為保甲;縣設縣參議會,由鄉(鎮)民代表會選舉縣參議員;鄉(鎮)設鄉鎮民代表會,由保民大會選舉之代表組織;保設保民大會,每戶出席一人;甲設戶長會議。這樣,基層各級民意機關實際是指縣參議會、鄉(鎮)民代表會、保民大會、戶長會議。 1939年《綱要》實施,然而,縣各級民意機關并沒有立即在全國推廣設置。首先在程序方面,國民政府設置了許多難以突破的障礙。國民政府規定了各級民意機關候選人必須經過一系列程序篩選,重要的如:公民宣誓登記;保甲編整與職業團體組訓;公職候選人考試等。然而,建立必要機構、完成這些事宜的配套法規還沒有及時制定、公布,或即使公布了也沒有宣布立即實施;《綱要》還規定,地方民意機關的建立,采取遞級設置及間接選舉的辦法,自下而上,即由保民大會而鄉鎮民代表會,而縣參議會,依次成立。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需要相當長的準備時間。因此,《綱要》實施后,縣各級政府遲遲沒有動作,連最簡單、最初級的公民登記都未能進行。 (二)1942年,廣西、四川出現民意機關 1942年抗戰形勢日益緊張,各民主黨派、各社會團體紛紛要求國民政府進行改革。迫于抗戰需要及人民要求民主和改革政府的壓力,許多省份開始自訂法規,越過保民大會和鄉鎮民代表會先期設置縣臨時參議會,如廣西省訂定《縣臨時參議會章程》、四川省訂定各《縣臨時參議會組織規程》(以下簡稱臨時法規),1942年,在廣西、四川最早出現了國民政府的民意機關,縣臨時參議會。 四川首先揭開創建基層民意機關序幕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政府抗戰開始后,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政府內遷,丟掉了東南工商業中心的國民黨稅收大減,只能把西南一隅作為財源的聚斂地,然而西南的云南、貴州、西康都比較貧窮,只有四川基礎稍好,所以抗戰需要的兵、糧、稅等任務大多由四川來承擔。但是,四川省區域大,縣份多,情形復雜,同時征兵、征糧、征工、征稅又急如星火、刻不容緩,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四川勢必陷入混亂,而若四川動蕩,國民政府則再也難找立足之處。 1942年春,四川省提議組織縣臨時參議會,其理由是:“在抗戰期間,許多重要的政令(如征兵、征糧)均須與人民代表協助進行,可以減少許多阻礙,推行較為利便。”[4] (P. 20)中央政府思量再三,又拿不出更好的辦法,于是批準試行。結果,四川省縣臨時參議會成立以后,“頗有成效”,“舉凡征兵、征糧、征工、征稅等等工作,有了縣臨時參議會的‘贊助’,就更得心應手,予取予求。”[5] (P. 213)縣臨時參議會的建立真如靈丹妙藥,于是各省紛紛效仿,先行成立縣臨時參議會。1942年,內政部對各省成立的縣臨時縣參議會數作了一番統計,如下表[4] (P. 22-23): 省別 已設立臨時參議會的 已舉行鄉鎮民代表會的 已舉行保民大會的 縣市局數 縣市局數 縣市局數 總計323 203 507 四川138 —— —— 云南 70 —— 130 貴州 籌設中 —— —— 湖南 籌設中 —— —— 湖北——22 廣東—— —— 37 廣西 9999 99 江西 14 —— 44 福建—— ——已舉行 河南—— 19 67 安徽 籌設中 —— 38 西康 籌設中 65 陜西 籌設中 —— 74 甘肅 籌設中 —— —— 青海—— —— 11 浙江—— 77 已舉行
1942年,全國共成立縣臨時參議會323個,其中,四川一省幾占半壁江山,共有138個;其次是廣西,建立99個,也近總數的30%,再次是云南和江西,分別是70和14個,占總數的20%和4%。 從數據來看,當時的縣臨時參議會數額雖有較大改觀,但相對于全國來說,不僅總數少,而且分配極不均勻,在國民黨統計的16個省份中,已經建有縣臨時參議會的只有4個,占總數的1/4。已舉行鄉鎮民代表會的縣市局數只有5個,占總數的1/3,如果用已成立民意機關的總數與各省實際的保、鄉鎮、縣的總數相比,各省民意機關的成立率更是微乎其微。依靠這樣的民意機關去行使民主權利,其結局可想而知。更何況,我們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全國各省建立民意機關的意圖已從“喚起民眾參政熱情”、“訓練人們行使四權”等方面轉移到了單純為了籌糧籌款等抗敵、鞏固政權方面了。 (三)1944年,民意機關建設在緩慢中進行 1942年的實踐使國民政府有了意外發現,民意機關不但不妨礙政府法令的推行,反而可協助政府催糧催款。這給國民政府以很大的啟發,于是他們開始加大推行力度。1943年5月5日,國民政府公布成立《縣各級民意機關步驟》五項。[4] (P. 23)規定縣參議會成立的條件,以及縣參議員候選人的檢核、縣參議會組織條例、縣參議員鄉鎮民代表選舉條例等等。1943年11月,行政院決議:限民國三十三年內(1944年)一律成立縣參議會,其不能依法成立之縣,得先成立臨時參議會,但仍應督飭各該縣依照步驟舉行保民大會及鄉鎮民代表會,務期正式民意機關得于一定期間一律依法成立。行政院還規定縣參議會正式成立的縣份,臨時參議會應即撤銷。 自這個《步驟》和《決議》公布后,各省依照規定,籌設各級正式民意機關。1944年9月內政部公布了1944年6月以前成立的縣各級民意機關數目,如下表[4] (P. 24-25): 省別 已成立縣臨時參議會的縣數 已舉行鄉鎮民代表會的鄉鎮數 已成立保民大會的保數 總計 784 15,703 322,689 四川 1424,462 74,947 云南 107 ——14,367 貴州39 ——14,193 湖南75 ——20,425 湖北35 86331,855 廣東66 83131,197 廣西 100 2,34323,992 江西691,884 21,806 福建641,183 13,034 河南 —— ——15,621 安徽 ————23,780 西康14 —— 4縣 陜西24 —— 7,182 甘肅30 —— —— 青海 ———— —— 浙江194,13740,290 寧夏 ———— ——
從上表看出,在國民政府管轄控制的17省范圍內,四川、廣西兩省縣各級民意機關建立的情況最好,到1944年,四川已成立縣臨時參議會142個,鄉鎮民代表會4,462個,保民大會74,947個。四川之所以情況最好,一方面因為這里僻處后方,較為安定,沒有戰事的侵擾;另一方面,這與蔣介石親自督政密切相關,蔣介石曾親任省政府主席,多次要求把四川建成全國各省效仿的對象。蔣介石網羅一批主張地方自治的學者、專家,像張群、李宗黃、胡次威等,他們極力推行新縣制,建立各級民意機關,這批學者的鼓動與實踐對四川民意機關的建立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自1944—1947年,縣市參議會由784個增至1387個,臨時參議會也成立了383個。鄉鎮區民代表大會由15,703個增至31,990個。保民大會由322,689個增至395,242個。各級民意機關的總數與全國同期的縣市、鄉鎮、保等的總數相比,均占3/5左右。也就是說,從“新縣制”開始實施到“新縣制”即將被“憲政”所代替,全國仍有2/5的縣市、鄉鎮、保沒有建立相應的民意機關。 從表中數據看,除四川、廣西兩省縣各級民意機關數目獨占鰲頭外,云南、貴州、廣東、江西、河南、甘肅、青海、浙江、寧夏、綏遠、山西、臺灣等12省基層民意機關建立率也高達90%以上,然而其中的湖南、湖北、廣東、青海等省竟出現了縣各級民意機關建立數超過實際存在的縣、鄉鎮、保數,這不免讓人懷疑其數字的可靠性和真實性。不過即便如此,我們仍能從表中看到許多省份,如江蘇、河北、山東等省民意機關建立的情況依舊少得可憐,有的地方建立率不及1/10,還有一些省份如遼寧、遼北、熱河等甚至就沒有任何國民政府民意機關的存在,各大城市雖然區、保兩級民意機關建立率高達90%多,但有些城市如上海、天津、北平都沒有建立正式或臨時的局、區級民意機關。顯然這樣的結果與國民政府最初設計和標榜的大相徑庭。 1947年內戰全面爆發,國民政府更無心建設基層民意機關,于是,這場當時學者大力鼓吹、許多民眾抱以巨大希望的所謂民主運動逐漸歸于沉寂,各地基層民意機關更是名存實亡。 綜上所述,從1939—1949的10年間,國民政府基層各級民意機關的建設情況可用“糟糕”二字來概括。《綱要》1939年公布實施,1942年才有縣臨時參議會在個別省份建立,而且,還缺少鄉鎮、保級的民意機關作為基礎。整個10年,1947年的情況最好,而那時,全國仍有2/5的縣市、鄉鎮、保沒有建立相應的民意機關。我們暫且不論國民政府民意機關職權是否完備,運作是否優良,性質是否民主,單就以民主政治的基層載體——民意機關的建設的數量情況來看,全國2/5民意機關的缺席,就足以使任何民主政治的實施成為泡影。
三民意機關數量缺失背后的原因
新縣制是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極力推行的政治改革,政府對建立各級民意機關投入的物力、人力不可謂不多矣,然而,這場聲勢浩大的系統工程最終卻以失敗告終,其根本原因不能不歸于其本質的專制。 為了掩人耳目,國民政府費盡心機對縣各級民意機關進行了精心包裝。國民黨首先為其規定了總的原則,即在“訓政時期原則指導下,使民眾在實際政治活動中訓練四權的行使,引發民眾參政興趣而遂其長”。[6] (P. 2022)從字意上來看,國民政府真是要為促進中國民主進程作點貢獻,然而,一句“訓政原則指導下”則包含了多少專制的寓意。在沈鵬主編的《縣政實際問題研究》中作者則明白表示了國民政府對縣各級民意機關設計宗旨,即“民意機關是地方自治開始時應有的組織,亦為人民行使四權之初步運用,一方面代表人民以監督政府,一方面協助政府以領導人民,其為用貴在以超然地位與政府通力合作推行政令,所謂一體兩面,為溝通人民與政府之橋梁者也。”[7] (P. 33)這里,國民政府首先為民意機關設定最高限制,它是“地方自治開始時應有的組織”,其為用貴在“與政府通力合作推行政令”。由此看出,無論民意機關如何設計,它總逃脫不了為國民黨政府服務的本質和特性。 關于基層民意機關,國民政府自1939年9月19日頒布《縣各級組織綱要》這部母法后,又陸續頒布十幾部法律文件,如,《地方自治實施方案》、《縣參議會暫行條例》、《參議會組織暫行條例》、《縣參議會議事規則》、《鄉鎮民代表選舉條例》、《成立縣各級民意機關步驟》、《公民宣誓登記暫行辦法》等[8],通過這些法律對基層民意機關進行重新規劃,不僅剝奪了普通民眾的選舉、被選舉權,而且剝奪了民意機關的人事權、監督權、質詢權、選舉權等種種權利,甚至民意機關的生存權都無保障。《縣參議會組織暫行條例》三十三條規定,“省政府對于縣參議會之議案認為有違反三民主義或國策情事者,得開明事實,咨由內政部轉呈行政院核準后,予以解散重選”。[9] 其它各級民意機關命運也大致如此。《鄉鎮組織暫行條例》第二章第二十六條、第五章第五十一條也分別規定上級行政部門對下級民意機關可以解散重選。即,國民政府先用種種法規限制民意機關權力的行使,如若民意機關俯首聽命那則聽之任之,而若有絲毫違令,則隨時用“解散”來對待之,保證萬無一失。由此看來,國民政府的宣揚的“基層民主”其實玩弄的是“舊瓶裝新酒”,以“變”來應“不變”,變化的是“民主”的形式,不變的仍是專制的本質。 也就是說,國民政府利用強權,玩弄“舊瓶裝新酒”的伎倆,牢牢控制了基層民意機關,使“孫悟空縱有萬般本領也翻不出如來佛的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