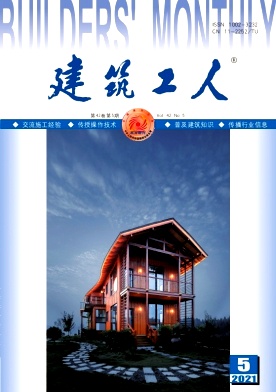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下檢察官客觀性義務的確立(190)——以北京城管被殺案為視角
陳宇清
[摘要]北京城管被殺案表明,部分檢察人員對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不夠全面準確,導致對案件的處理失之偏頗。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與檢察官客觀性義務的內在要求高度一致。各級檢察機關和檢察人員應當把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與落實檢察官客觀性義務結合起來,以保證客觀公正地履行檢察職責,不斷增強懲治犯罪、保護人民、化解矛盾、促進和諧的能力。
[關鍵詞]寬嚴相濟 客觀性義務 檢察
一、北京城管被殺案的簡要案情及審理結果
被告人:崔英杰,男,23歲,漢族,出生地河北省保定市,初中文化,名柜餐飲娛樂(北京)有限公司員工,暫住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51號樓南側出租房(戶籍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阜平縣各老村160號)。因涉嫌犯故意殺人罪于2006年8月12日被羈押,同年9月19日因涉嫌犯故意傷害罪被逮捕。
被告人:張雷,男,21歲,金渤瀚國際商務會館員工。
被告人:牛許明,男,20歲,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恒昌技術有限公司職員。
被告人:段玉利,男,24歲,北京雨辰視美科技有限公司職員。
被告人:張健華,男,20歲,金渤瀚國際商務會館員工。
被告人崔英杰于2006年8月11日17時許,在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一號橋東南側路邊無照擺攤經營烤腸食品時,被北京市海淀區城市管理監察大隊的執法人員查處,崔英杰對此不滿,以持刀威脅的手段抗拒執法,當執法人員將崔英杰經營烤腸用的三輪車扣押并裝上執法車時,崔英杰進行阻攔,后持刀猛刺該城市管理監察大隊海淀分隊的現場指揮人員李志強(男,歿年36歲)頸部一刀,致刀柄折斷,后逃離現場。李志強因被傷及右側頭臂靜脈及右肺上葉,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被告人張雷、牛許明、張健華、段玉利明知崔英杰實施了犯罪行為,張雷、張健華仍為崔英杰聯系藏匿地點,牛許明、段玉利分別向崔英杰提供人民幣500元幫助崔英杰逃匿。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人崔英杰犯故意殺人罪,被告人張雷、牛許明、張健華、段玉利犯窩藏罪一案,于2006年12月1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崔英杰以暴力方法阻礙城市管理監察人員依法執行職務,并持刀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犯罪性質惡劣,后果特別嚴重,應依法懲處。考慮崔英杰犯罪的具體情節及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對崔英杰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崔英杰犯故意殺人罪,被告人張雷、牛許明、張健華、段玉利犯窩藏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指控罪名成立。根據被告人崔英杰、張雷、牛許明、段玉利、張健華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三百一十條第一款、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七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七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第三十七條、第六十一條、第六十四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三條、第六條的規定,判決被告人崔英杰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牛許明犯窩藏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被告人段玉利犯窩藏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被告人張雷犯窩藏罪,免予刑事處罰;被告人張健華犯窩藏罪,免予刑事處罰。1
二、本案的法理分析
本案中控辯雙方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定罪問題,即被告人崔英杰的行為究竟構成故意殺人罪還是故意傷害(致死)罪;二是量刑問題,即被告人崔英杰的罪行是否達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第一個問題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之內,本文主要從量刑情節的角度對第二個問題加以分析。
所謂量刑情節,是指定罪情節之外的,人民法院據以在法定刑限度之內或者以下對犯罪分子從重、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主客觀事實情況。以情節的淵源不同為根據,可將量刑情節劃分為法定量刑情節、司法解釋規定的量刑情節、定罪剩余的構成事實轉化的從重情節和酌定量刑情節四類。以情節的性質不同為根據,可將量刑情節劃分為從重處罰情節和從寬從輕處罰情節兩類。2
在本案中,一審公訴人和辯護人提出的量刑情節均為酌定量刑情節,不涉及法定量刑情節、司法解釋規定的量刑情節、定罪剩余的構成事實轉化的從重情節。進一步分析,公訴人提出的全部是酌定從重處罰情節,而辯護人提出的全部是酌定從輕處罰情節。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起訴書》稱:“本院認為,被告人崔英杰無視國法,以暴力手段妨害城管執法人員依法執行公務,并持刀行兇,致人死亡。犯罪性質極其惡劣,情節、后果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公訴人在庭審中提出:“崔英杰實施了故意殺人行為,有以下兩點情節,應該成為對其從嚴懲處的理由:一、故意殺人的行為具有暴力妨害公務的性質,今天在法庭上崔英杰極力回避的就是這一點,但是從大量的證據來看,其行為都是妨害公務過程中,崔英杰與李志強沒有個人恩怨,只是因為他的個人無照經營被查處就產生了報復念頭,其報復念頭并不是單單指向李志強一個人,而是指向在場的城管隊員,其行為反映出無視國法的主觀惡性。 二、被告人崔英杰的犯罪手段特別兇殘,其犯罪行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實施的,不僅造成被害人的死亡,而且嚴重違反了社會治安秩序。”筆者將控方提出的酌定從重情節歸納為兩點:一是動機惡劣——為報復依法執行公務的城管執法人員對其無照經營的查處而殺人;二是手段兇殘——光天化日之下持刀行兇,致人死亡。
辯方提出的酌定從輕情節較為分散,筆者將其歸納為以下五點:
(一)被告人的犯罪動機不屬十分惡劣
首先,被告人妨害的并非公務。關于起訴書指控的妨害公務,被告人崔英杰的第一辯護人夏霖律師認為,妨害公務是指以暴力、威脅的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或履行職責的行為。行為人必須明知自己阻礙的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明知阻礙之人是在依法履行職務或職責;客觀上該人員也必須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事業編制人員,該機關必須是依法設立的、擁有合法授權的適格的國家機關。本案中崔英杰實施了妨害的行為,但其妨害的并非公務。理由如下:1.現行國家法律、行政法規沒有規定城管類組織具有行政處罰權。2.控方未能證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的設立已經法定程序報請國務院批準并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未能證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是適格的行政機關。3.控方未能證明參與當天現場執法的人員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者事業編制人員的身份。4.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執法人員缺乏執法依據并且嚴重違反執法程序。
其次,被告人不是為了報復城管而殺人。被告人崔英杰的第二辯護人李勁松律師提出,“根本不是像公訴人剛才所說的,他是因為自己的車被沒收,受到了損失,就報復所有的城管。而且,這個報復目標是不特定的,是到了見城管就殺這種程度。”“他第二次返回,根本不是為了殺死李志強,就是為了討回自己的謀生工具,他發現自己的車被查抄,他為了使自己不被帶走、不被罰款,臨時起意把劣質水果刀推向了李志強,這些事實能夠證明他根本不是為了蓄意謀殺李志強。”“從受害人以及其他城管工作人員向第二次跑出來的崔英杰圍上去,到崔英杰把水果刀推向受害人的時間僅僅3秒鐘,這3秒鐘能說崔英杰是要報復而實施殺人嗎?”再次,被告人的行為屬于典型的激情犯罪。夏霖律師指出:“從犯罪心理學來說,本案是典型的激情犯罪。崔英杰是在混亂之中,情急之下,奔逃途中,順手一刀。其實施犯罪,完全是在一種強烈的感情支配下導致的犯罪。”
(二)被告人的犯罪手段不屬兇殘
李勁松律師強調:“他(崔英杰)所用的,所謂匕首,其實并不是一個匕首。其實只是他隨手拿著的工作工具。所以,我認為公訴人也應該如實陳述這個事實。你在陳述他持刀殺人的時候,最好能把事實如實說清楚,他持的是他的工作工具,是一個不到20厘米的,一塊錢一把的劣質水果刀。而并不是大家印象里、想象中的匕首。它并不是故意殺人的蓄意殺人者作案時會選擇的,有殺傷力的一種致命武器。”
(三)被告人品行一貫良好,屬初犯、偶犯
辯方向法院提交了崔英杰家鄉的村委會、鎮政府、派出所出具的證明,崔曾就讀的小學、中學出具的證明,崔曾服役的部門頒發的優秀士兵證書,崔在名柜娛樂城的同事的調查筆錄,以及崔的戰友、村委會、村民給法官的求情信等證據。據此,夏霖律師提出:“以上證明證實崔英杰一貫表現良好,無打架斗毆,也無前科,確系良民。在部隊還是優秀士兵。在城市生活艱辛,為生存掙扎。另外調查還證明,崔英杰沒有暴力傾向,不是天生犯罪者。”
(四)被害人有一定過錯
在法庭調查階段,辯方對被告人崔英杰和證人趙某某的發問以及當庭播放的視聽資料均證實,包括現場指揮人員李志強(時任海淀城管隊副隊長)在內的城管執法人員查扣崔英杰的三輪車時,既沒有出示執法身份證件,又沒有填寫行政處罰決定書,更沒有出具扣押物品通知書,其執法行為明顯存在程序上的瑕疵。1
(五)證明被害人死因的證據不能排除合理懷疑
辯方在庭審中提出:“我們有一個合理的懷疑,尸檢報告上反映受害人左側靜脈,法醫常識告訴我們靜脈不會出現大量的出血死亡,當時刀折斷在被害人的脖子里面,這里面是否有救助不當的問題。” 控方對此未作回應。
此外,辯方還列舉了北大醫學院安然故意殺人案等12個被判處死緩的案例,對起訴書中認定被告人崔英杰“犯罪性質極其惡劣,情節、后果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提出質疑。認為被告人崔英杰的社會危害性、人身危險性遠遠低于上述案例中的犯罪分子,其罪行沒有達到極其嚴重程度,即使構成公訴人指控的故意殺人罪,應當判處死刑,也不是必須立即執行。
三、從本案看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下檢察官的客觀性義務
(一)檢察官應全面理解和把握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
從上文的分析可知,控方提出的酌定從重處罰情節與辯方提出的酌定從輕處罰情節相比,相關證據的證明力顯然較弱,而且起訴書中認定被告人崔英杰“犯罪性質極其惡劣,情節、后果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也過于嚴厲。一審判決書認定被告人崔英杰“犯罪性質惡劣,后果特別嚴重,應依法懲處”,但“考慮崔英杰犯罪的具體情節及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對崔英杰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表明法院在一定程度上采納了辯方的意見。
筆者認為,本案表明部分檢察人員對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不夠全面準確,導致對案件的處理失之偏頗。傳統的刑事訴訟理念在相當一部分檢察人員的頭腦中仍然根深蒂固,這必然造成對于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片面化、機械化理解。我們在行使檢察權時,往往偏重于對涉嫌犯罪行為的認定和對刑事處罰的預期,往往習慣于單純地站在追訴者的立場一味地追訴犯罪。也就是說,片面地追求打擊犯罪的效果,只強調打擊而忽視保護,只講嚴而忽視寬。同時,受傳統刑事訴訟理念以及現時社會公眾可接受程度的影響,對輕緩刑事政策的適用在案件類型上多限于未成年人犯罪及輕傷害案件,未能普及到全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指出,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中的寬與嚴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二者相輔相成,必須全面理解,全面把握,全面落實。既要防止只講嚴而忽視寬,又要防止只講寬而忽視嚴,防止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其實質就是要求檢察機關區別對待,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寬嚴互補,寬嚴有度,對嚴重犯罪依法從重打擊,對輕微犯罪依法從寬處理,對嚴重犯罪中的從寬情節和輕微犯罪中的從嚴情節也要依法給予寬嚴的體現。在以“和諧社會的刑事法治”為主題的中國法學會刑法學2006年年會上,有學者進一步提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既是基本的,也是具體的刑事政策;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既是結果也是過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應適用于每一案件,及于每一案件的全過程。1筆者對上述觀點持贊同態度。
(二)本案應運用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從寬處理
本案中,相對于控方提出的從嚴懲處意見,辯方明確呼吁運用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從寬處理。針對公訴人提到的必須嚴打暴力抗法的問題,辯護人表示:對暴力抗法行為,的確需要保持高壓嚴打態勢。對于嚴重刑事犯罪,還是應該從重的要堅決從重,該判死刑的決不手軟。但同時,對于具有法定或者酌情確定從輕的罪犯,無論他的罪輕罪重,無論他是否屬于嚴打對象,都要一視同仁,該兌現政策的都要依法予以從寬處理。如果因為嚴打,而不兌現政策,就會導致犯罪分子喪失對國家法律的基本信任,也會導致其他的人喪失對國家法律的信任。只有審時度勢,堅持寬嚴相濟,才能產生積極的、正面的社會效果。在強調堅持嚴打方針的同時,要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
對于崔英杰的行兇行為,從法學界到許多普通市民在表示譴責的同時,也表現出強烈的同情。著名刑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其林通過媒體公開表示,對犯罪的處罰,不僅要看結果,還要對整個案件進行綜合考察才能正確定罪量刑。在他看來,“崔英杰為了謀生受到處罰,在城管執法要沒收其生產工具,一時激動之下殺人,是激奮殺人,不同于有預謀的故意殺人,因此,對崔英杰適用死刑將不合適。”另一種民間輿論,更是將此案放到了城管執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方面來考察,認為正是城管由來已久的粗暴執法和違法扣押公民財物行為,導致了執法者和小販之間的嚴重對立情緒,崔英杰案件只不過是這種情緒的爆發性體現。北京大學人民代表大會與議會研究中心,亦曾就本案舉行專題討論。與會學者認為,崔英杰案不僅僅是一起簡單的刑事案件,在行政法角度來看,更是暴露了目前城市管理中行政執法的法律缺陷。1在李志強被殺之后,包括上海在內的許多城市,對于小商販的管理政策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一些城市劃出專門的區域供小販擺攤。北京對于小商販的經營管理也緩和了許多。2由此可見,在構建和諧社會、關注民生疾苦、倡導文明執法的形勢下,運用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對被告人崔英杰予以酌情從寬處理,有利于化解矛盾,減少對抗,促進和諧,是順應潮流、合乎民意的。
(三)實施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要求確立檢察官客觀性義務
檢察官的客觀性義務,是指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為了發現案件的真實情況,檢察官不站在當事人的立場而是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不偏不倚地全面收集證據、審查案件和進行訴訟的活動。3
公檢法都應當客觀公正,為什么惟獨強調檢察官的客觀性義務?這是因為,警察的任務是破案,所以警察關注的重點是找出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的證據;法官的任務是根據檢察官的指控作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判斷,前提是檢察官向其提出的指控是否客觀全面。而檢察官既要防止警察為了破案而片面地搜集證據,也要保證提供給法官的證據是真實的、全面的。因此,檢察官的客觀性義務在刑事訴訟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需要專門強調。故而將客觀性作為檢察官的義務。1
按照聯合國《關于檢察官作用的準則》的規定,檢察官的客觀性義務,主要包括以下內容:⒈ 不歧視任何人。檢察官在履行職責的時候,要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場,不得對任何人進行任何政治、社會、文化、性別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歧視。⒉ 按客觀標準行事。檢察官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要充分注意到案件的一切有關的情況,特別是對犯罪嫌疑人有利的和不利的各種因素,不得顧此失彼或厚此薄彼。⒊ 保證公眾利益。在適當考慮犯罪嫌疑人人權的同時,要充分考慮到社會的利益,特別是在有被害人的場合,要考慮到受害者的立場和權利。⒋ 必要時中止追訴。在訴訟過程中,如果調查表明起訴缺乏根據,檢察官就不應提出或繼續檢控,或應竭力阻止訴訟的繼續。⒌ 依法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如果得知或認為其掌握的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證據是通過嚴重侵犯其人權的非法手段取得的,檢察官就應拒絕使用此類證據,并應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確保將使用非法手段的責任者繩之以法。⒍ 酌處中的客觀公正性。在其他任何情況下,檢察官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權時,應當充分考慮各方面的利益和情況,確保作出決定的必要性、客觀性和連貫性。2
由此可見,檢察官客觀性義務的內涵與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要求是一脈相承的。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要求將寬與嚴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予以全面把握,而客觀性義務要求檢察官按客觀標準行事,在履行職責中秉承客觀的態度,既注意對被追訴者不利的方面,又注意對被追訴者有利的方面,既注意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又不簡單地站在被害人的立場從事訴訟活動。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要求從寬和從嚴都必須嚴格依法進行,做到寬嚴合法,于法有據。而客觀性義務要求檢察官依法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追訴犯罪要運用合法搜集的證據。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要求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對不同的罪行分別給予嚴厲或輕緩的處罰,以協調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反映各方的利益訴求,實現司法公正和社會公平與正義。而客觀性義務要求檢察官客觀公正地行使自由裁量權,充分考慮各方面的利益和情況,確保所作決定的必要性、客觀性和連貫性。
對于公訴工作而言,客觀性義務要求檢察機關在履行職責、參與訴訟的過程中,不是單純地處于追訴者的立場一味地追訴犯罪,而是必須通過一系列的訴訟活動著力于發現事實真相,盡可能地尋求客觀真實。必須依照法定程序,全面收集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特別是對無罪證據、罪輕證據都必須全面收集和全面出示,不得隱瞞。對于警察收集移送的證據材料和移送起訴的意見,檢察官應當客觀全面地進行審查,不能只注重有利于追訴的證據材料。對于在審查起訴中發現確系無罪的案件,檢察官應當決定不起訴,確保無罪的人不受追訴。在法庭審判中,檢察官應當向法庭客觀、全面提供有關定罪量刑方面的各種證據,向法院提交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的一切證據。對于在出庭、審判過程中發現無罪、出現無罪證據的情況,檢察官應當及時作出延期審理、撤回起訴的決定,使被告人免受無罪之羈押。對于辯護律師沒有收集或者忽略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檢察官也有義務向法庭提供,以確保審判的客觀公正。1
總之,各級檢察機關和檢察人員應當自覺按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全面準確地理解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把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與落實檢察官的客觀性義務結合起來,以保證客觀公正地履行檢察職責,不斷增強懲治犯罪、保護人民、化解矛盾、促進和諧的能力。
1 本案判決書、起訴書、辯護詞、庭審實錄的相關內容分別引自《北京崔英杰案一審判決書》、《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起訴書〉》、《崔英杰案一審辯護詞(夏霖律師)》、《崔英杰案一審辯護詞(李勁松律師)》、《北京崔英杰案庭審實錄》 2 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第3版,第279-280頁。 1《行政處罰法》第三十四條第一款規定:“執法人員當場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應當向當事人出示執法身份證件,填寫預定格式、編有號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行政處罰決定書應當當場交付當事人。”第三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行政機關在調查或者進行檢查時,執法人員不得少于兩人,并應當向當事人或者有關人員出示證件。當事人或者有關人員應當如實回答詢問,并協助調查或者檢查,不得阻撓。詢問或者檢查應當制作筆錄。”第三十七條第二款規定:“行政機關在收集證據時,可以采取抽樣取證的方法;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后難以取得的情況下,經行政機關負責人批準,可以先行登記保存,并應當在七日內及時作出處理決定,在此期間,當事人或者有關人員不得銷毀或者轉移證據。” 1《聚焦刑法理論與實踐中的五大熱點問題》,載《檢察日報》2006年10月20日。 1 陳杰人:《小販殺死城管案一審結果的里程碑價值》,載《中國青年報》2007年4月12日。 2《〈解密案卷〉系列之崔英杰和李志強的前塵往事 北京“小販殺城管”案背后的故事與反思》,載《法制日報》2007年6月6日。 3 劉佑生:《重視檢察官的客觀義務》,載《人民日報》 2007年7月13日。 1《如何理解檢察官的客觀性義務·2004檢察官論壇》 2 在我國,檢察官的客觀性義務是有法律根據的。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第四十四條規定:“公安機關提請批準逮捕書、人民檢察院起訴書、人民法院判決書,必須忠實于事實真象,故意隱瞞事實真象的,應當追究責任。”第一百三十九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聽取被害人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見。” 但是,我國立法并未將檢察官的客觀性義務作為一項基本原則予以明文規定。 1 陳國慶:《論構建客觀公正的公訴制度》,載《人民檢察》2007年4月(下半月)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