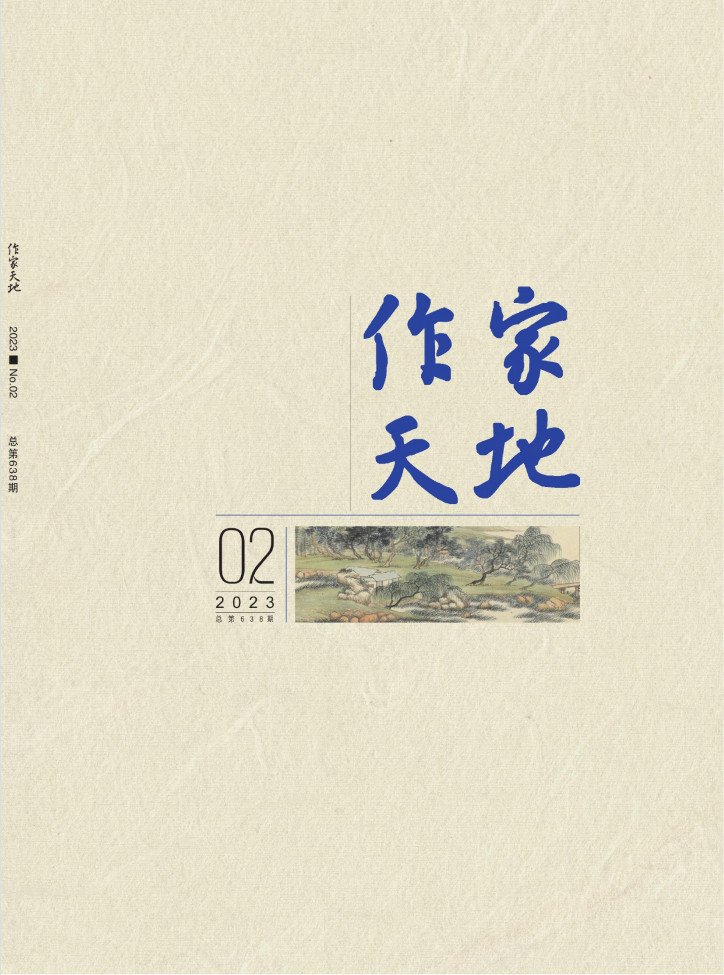美國私營監獄的復興——一個懲罰哲學的透視
陳頎
關鍵詞: 私營監獄/復興/懲罰哲學/福柯
內容提要: 美國私營監獄的復興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背景。當下英美學界對美國私營監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本—收益的實證分析和規范的懲罰哲學這兩條進路。這兩條進路面臨各自的解釋困境并且相互對立,其背后更深層的理論問題是懲罰哲學在20世紀晚期的迷失。福柯的作為規訓權力的懲罰之理論模型,能在溝通上述兩條進路的基礎上更好地解釋私營監獄的復興現象。這意味著未來的規范的懲罰哲學應當超越抽象的哲學討論,吸取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理論資源,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中尋求可能的答案。 懲罰馴服人,但并不能讓人“更好”。① 密納發的貓頭鷹要等黃昏到來,才會起飛。②
引言 現代監獄自誕生以來,便以國家機器的形象為世人所知。似乎國家天然地和合法地壟斷了監獄權,正如國家天然地和合法地壟斷刑罰和暴力一樣。然而從20世紀下半葉起,在世界范圍內興起的私營監獄(private prison)或者說監獄私營化(prison privatization)③現象似乎正在淡化和挑戰作為國家機器的監獄形象。 這一全球范圍特別是以英美兩國為代表的私營公司參與監獄以及其他監禁機構的建設、管理和為監獄提供服務的現象,也得到學術界的關注和研究。大致而言,西方學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本—收益的經濟分析和規范的懲罰哲學這兩條進路,前者持經濟學立場,為私營監獄的經濟、現實和社會合理性辯護,后者則站在道德哲學—倫理學立場,從規范的懲罰哲學角度批評私營監獄。具體而言,學者的研究領域集中于國際范圍特別是英美兩國的監獄私營化的歷史和緣由、發展趨勢、成就、利弊得失、責任及其與公有監獄的比較等問題,以及各國私營監獄的比較研究。④而國內學者對私營監獄的研究以簡單評介為主⑤,此外還討論美國監獄私營化的原因、目的和效果,以及美國監獄私營化的政府角色研究等。⑥ 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為美國私營監獄的復興。⑦這是因為美國的監獄私營化在西方各國監獄實踐中最具典型性和影響力。這表現在:私營監獄和私營拘禁機構和在押囚犯的數量眾多、增長迅速,私營監獄公司的市場化的運營管理和資本運作,以及聯邦、州和各級地方政府對私營監獄的支持或默許態度等。⑧ 私營監獄的復興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背景。一般而言,研究者大多承認,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監獄私營化的初始原因和解決目標,在于緩解美國聯邦和各州監獄過于擁擠、床位不足的現象。這一現象的直接原因是美國社會20世紀中期以來居高不下的犯罪率。然而監獄私有化作為一種趨勢,為何在20世紀80年代起得到美國各州政府、議會和監獄管理部門的青睞而得以壯大發展,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探討和爭論。根據一個綜述性的研究,學者們的不同見解可分為政治、經濟、實用和法律等四個因素:政治原因如里根政府保守主義的政府意識形態——要求政府加大打擊犯罪的力度、私營監獄公司的游說集團的壓力等;實用原因如公立監獄的床位不足、管理混亂,而且面臨不斷增長的囚犯壓力,以及由此而來的嚴峻財政壓力;經濟原因主要是在成本—收益分析視角上私營監獄足以比公立監獄提供更好的效率(efficiency);法律因素是法院特別是聯邦法院禁止不合乎標準的監獄投入使用,這導致各級政府和監獄管理部門對新監獄的迫切需要。⑨ 然而本文不準備投身于眾說紛紜的“根本原因”研究,顯而易見,美國監獄私有化的影響因素眾多,一味探尋哪個或者哪些因素是影響或推動監獄私營化的根源無異于解開“阿里阿德涅線團”的死結。而且,對于當下拘禁超過12000名成年和青少年囚犯的美國私營監獄和被數家上市公司壟斷的每年超過10億美元的私營監獄工業市場而言⑩,討論到底是什么根本因素導致私營監獄的復興已經不合時宜——實踐、政治、經濟、法律乃至更廣泛的歷史—社會因素都有影響。更重要的理論問題可能是,私營監獄為何能在美國刑罰—監獄體系中蓬勃發展并牢牢扎根,盡管自私營監獄的復興之始各類批評和反對之聲便不絕于耳。 監禁作為現代主要刑罰形式即自由刑的最重要方式,在懲罰哲學中通常被天經地義地視為由國家壟斷,并且主流的懲罰哲學——無論是報應論還是功利論——都將懲罰的正當性這一規范問題建筑在國家對懲罰權的壟斷之上。因此,晚近私營監獄的復興無疑是對國家的刑罰壟斷權的直接挑戰。所以,探討私營監獄與懲罰哲學的關系乃至潛在沖突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與實踐價值。本文傾向于把晚近美國監獄私營化的實踐當成一個事實狀況,探討對這一事實狀況的法哲學特別是懲罰哲學解釋,及其對現有法律理論的可能啟迪。 我將論證,成本—收益的經濟分析和規范的懲罰哲學這兩條進路都面臨各自的問題,前者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嚴謹性問題上遭到質疑,后者無法在規范層面證明當代監獄實踐的正當性,這背后更深層的理論問題是懲罰哲學在20世紀晚期的迷失。福柯的作為規訓權力的懲罰的理論模型,能在溝通上述兩條進路的基礎上更好地解釋私營監獄的復興現象。但是福柯的理論模型不是完美的,仍然有待進一步深化。這意味著未來的規范的懲罰哲學必須超越抽象的哲學討論,吸取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各學科的理論資源,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中尋求可能的答案。 在結構安排上,本文第一部分討論當下美國公立監獄的實踐和理論上的雙重困境,認為這導致作為解決監獄緊張和財政危機的應急手段的私營監獄得以復興。正如第二部分所展示的,私營監獄的復興引起從不同層面對私營監獄的三重批評,在學術上學者們主要采取了兩條主要研究進路:以成本—收益為中心的實證分析為方法論的辯護進路和以規范化的合法性分析為方法論的質疑或反對進路。正如該部分細致辨析的,成本—收益的實證分析面臨著社會科學方法研究本身的各種問題,而規范立場的懲罰哲學的問題在于不能在體系內自圓其說,且與現實的懲罰—監獄實踐脫節。因此,在第三部分回顧了美國監獄的實踐與規范化理論脫節的狀況后,在第四部分我將轉向一個福柯式的以規訓權力為中心的監獄的理論模型以解釋私營監獄的復興現象,并分析私營監獄的復興背后隱藏在現代監獄內部和深處的物質主義或者經濟學的懲罰理論。本文并未簡單地用福柯的理論模型否認懲罰的規范化理論的存在或可能性,而是通過該理論模型分析以往的懲罰哲學研究與監獄實踐的缺陷所在,強調未來的規范性的懲罰哲學需要哲學與社會學、經濟學和歷史學等多學科的共同努力,在實踐和理論的結合中尋找可能的答案。
一、美國私營監獄的復興 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這段并不漫長的時期里,公立監獄統治了美國的矯正和監禁領域。然而隨著1960年以來美國監禁人口的持續增長,公立監獄的壟斷局面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被私營監獄的再度出現所打破。 (一)矯正理論的失敗:公立監獄的內外困境 美國公立監獄在20世紀70年代后的困境有其復雜的內部和外部原因。內部因素是美國20世紀以來的主流刑罰理論——矯正理論——的失敗引發監獄理論和實踐的危機,這一因素往往被論者所忽略,但正如我們接下來要討論到的,矯正實踐的失敗導致的刑罰和監禁理論及實踐的一系列變化,是私營監獄復興的一個重要內部因素。而且,只有深刻理解這一內部因素,我們才能更好地規范化評價私營監獄的可能意義和問題。 自1870年全美監獄大會宣言通過矯正思想的實踐原則以來,監禁和刑罰矯正理論開始成為美國刑罰和監禁體系的主流理論,甚至以監獄和拘役所為代表的監禁體系都被稱為“矯正機構”。 在刑罰理論上,矯正思想強調通過對罪犯的改造或再教育,使之適應社會或者再社會化。矯正理論的實踐表現在刑罰體系和監獄內部兩方面上。在刑罰體系上,矯正實踐表現為緩刑、不定期刑和假釋制度;在獄內制度上,矯正實踐表現為各種矯正方案;而且,囚犯的獄內矯正計劃的表現與不定期刑和假釋制度的執行聯結在一起。(11)然而,數十年的矯正實踐不僅造成政府部門的巨大財政支出,更致命的是矯正的實踐完全失敗了。這一重磅炸彈是由羅伯特·馬丁森等人于1970年完成的研究報告向矯正理論的擁護者們投擲的。馬丁森等在1974年發表著名的研究成果《有什么效果?關于監獄改革的問題與答案》(12),而后出版了人稱為“馬丁森炸彈”的《矯正治療的實效》一書,宣稱犯罪人矯正并無效果。這篇論文是馬丁森與他的同事對1945年1月到1967年底之間完成的1000多項有關監獄矯正的研究重新加以檢驗的結果,他們認為其中只有231項符合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標準,然而這些彼此孤立的實例無法表明某種矯正效果的清晰模式。(13)馬丁森的批評導致一場關于矯正的命運的大辯論,雖然有支持者反駁馬丁森的批評,然而批評者一直無法拿出比馬丁森報告更實證嚴謹的矯正實效的分析,因而馬丁森的“矯正無實效”的結論成為刑罰和監獄領域的一個共識。因此,大眾、政府和學者和監獄部門的共識是:矯正的時代已經結束。 在實證研究外的刑罰理論界以及政治哲學界,對矯正的批評也益發嚴重。左翼的自由派批評矯正把罪犯當成“病人”來看待,其背后存在著嚴重的種族和階級偏見,故而呼吁一種更為“公正(justice)”的刑罰理論;而右翼的保守派認為過分“溺愛”罪犯的矯正模式如假釋、不確定刑制度是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罪魁禍首,故而支持更嚴厲的獄內控制和以剝奪犯罪人犯罪能力和更具威懾刑的確定刑。(14)兩派不約而同地重燃對曾經被視為“不人道”和“殘忍”的刑罰報應主義理論的興趣,反映在監獄實踐上便是里根政府時期確定刑的大量增加,和以監禁方式嚴懲毒品犯罪,以及視犯罪人的危險程度而對監獄分級的政策。“必須保護社會”為口號的報應主義似乎代替了以改造和治療囚犯為目的矯正理論和實踐。 加大犯罪處罰力度的結果,使美國出現了因為囚禁人數不斷增加所導致的監獄過度擁擠、與日俱增的營運開支、納稅人拒絕為建立新監獄買單等問題。美國的公立監獄體系正面臨著嚴峻的危機。 (二)私營監獄的興起 1985年,美國監禁人口超過74萬人,其中有22.6萬人是過去十年所增加的,到1990年,這一數字突破110萬,1995年接近160萬。(15)而2003年美國監禁人口超過210萬。(16)監禁人口的劇增,使政府部門、議會和監獄管理部門不得不面臨兩個讓人頭疼的政治—經濟問題:如何安置好龐大的監禁人口?如何應付安置監禁人口造成的財政壓力? 起初,政府部門試圖盡量利用現有監獄容量盡力安置新增長的監禁人口,這一權宜之計讓監獄在短時間內擁擠不堪,囚犯生存環境惡劣,最終引發法院系統的介入——法院要求相關部門必須建造更多合乎要求的新監獄以解決監獄擁擠的狀況。對于政府部門而言,這一解決之道也是問題眾多。首先,新監獄花費不菲;其次,建造周期長;再者,監獄的管理和服務人員的征募和培訓需要時間和資金;最后,建造新監獄的支出也引發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財政和預算危機。 與此同時,政府和監獄部門重新拾起被拋棄已久的監獄勞動方案,試圖開放監獄工業以解決犯人懶散、改善矯正措施、設施和經費不足等問題,在支付犯人工資的前提下試圖更好地“矯正”犯人,有助于犯人的就業前景和技能培訓。因此在1979年美國政府廢除了1940年限制州際監獄商品流通的法令,推出支持監獄工業的《珀西修正案》(Percy Amendment[1979])。然而受到官僚主義的惰性影響,且在許多州的監獄工業存在著巨大的法律障礙,公立監獄內部的監獄工業有其規模的局限;最大的問題是,政府主導的監獄工業并不能解決洶涌而來的監獄囚犯人數膨脹的浪潮。因此,作為解決矯正危機和監獄人口膨脹的方法,政府試圖將監獄工業甚至是整個監獄“私有化”。 公立監獄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面臨的危機,迫使政府尋求私營部門的幫助。美國第一個地方政府層面的監獄私營化合同簽訂于1984年,州層面的監獄私營化合同簽訂于1985年。參與監獄私營化的第一家美國公司是成立于1983年、擁有不少前聯邦監獄署官員和前州立監獄管理人員的美國矯正公司(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稍后成立的是從著名的沃克安保集團(Wackenhut Security,Inc.)中分立出來的同樣以營利為目的沃克矯正公司(Wackenhut Corrections Corporation)。在90年代中期,這兩家公司占據了超過75%的私營監獄的市場份額;到1999年底,美國私營機構監禁超過30000名青少年囚犯,約占青少年被矯正和監禁總人數的30%;而到2003年底,美國3/5的州都有私營監獄,大多數州都與私營監獄公司簽訂了關押囚犯的合同;私營機構監禁了超過94000名成年囚犯,占美國聯邦、州和地方矯正機構監禁總人數的8.5%。(17)私營監獄已經在美國矯正和監獄領域牢牢扎根。 私營監獄,如許多寧愿用“監獄私營化”作為替代用法的論者所言,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是個相當模糊的稱謂。具體而言,監獄私營化表現為兩種形式。第一種形式是私營部門幫助政府建造新的監獄,運營管理權仍在政府部門手中,因而被稱為是“名義上的私營化”。第二種形式是私營公司和政府部門簽訂合同,保證以比公立監獄更低的成本運作監獄,完全負責監獄事務的日常管理,因而被稱為“運營的私營化”。后者并非是美國20世紀晚期的新鮮事物,早在1970年代美國聯邦移民局(INS)就已經與私營企業簽訂合同,由后者負責建造拘留所和管理關押等待驅逐聆訟的非法移民者。(18)然而不同尋常的是,現在由私人公司建造的是監獄,管理的是刑事罪犯,而過去數十年里刑事罪犯都號稱屬于國家刑罰體系所管轄。盡管存在這一本質差別,然而在實際上私營監獄和聯邦移民局拘留的私營化程序大致相同:政府決定哪些監獄進行私營化和提出此類合同,私營企業進行投標,政府支付每個囚犯每天的費用,而企業承擔管理監獄和供給囚犯的需求的職責。監獄承租人的私營化范圍可以從不具備監獄設施所有權和部分監獄營運管理權,到完全的監獄設施所有權和完全的監獄內部的管理權力。盡管有這樣的差別,然而私營監獄的指導思想是很明確的:私營企業將監獄運營成本維持在(合同)談判金額以下,是政府支付囚犯日常費用和允許企業謀利的根本條件。 在現有的私營化圖景中,國家擁有決定刑罰和判決階段的全部權力,通過合同授權非政府機構執行監獄運營和管理的職能。在理論上,監獄私營化的承租人可以是私立的非營利組織,也可以是私營的營利組織,然而在實踐中,美國(以及其他監獄私營化國家)所有私營監獄或者矯正機構都是由以營利為目的私營公司所承租和運營。正如有論者所言,這一現象引發了關于私營監獄的大多數爭論,公眾和學者們關注或質疑營利機構是否應該和如何可能成功管理和控制一個監獄。(19)在支持者們看來,和其他私營化領域一樣,私營公司當然可以進入監獄市場,因為私營監獄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靈活高質的監獄服務,而反對者認為國家有責任承擔管理好監獄的職責,而私營監獄并不見得能降低多少監獄運營成本,而肯定會使監獄狀況更加糟糕。 因此,圍繞私營監獄的爭論可以分為如下三個互有重疊的層面:(1)私營監獄比公立監獄表現更好嗎?也就是說,私營監獄能用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監獄服務嗎?如果私營監獄的效率更低的話,那么試圖以私營監獄為解決監獄擁擠和財政危機的初衷顯然是失敗的。(2)私營監獄在合法性上是否存在著有問題的特性?(3)私營監獄是否在規范層面特別是道德或層面上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缺陷? 這三個層面的爭論引發了私營監獄研究的兩條主要進路和質疑/辯護策略:以成本—收益為中心的實證分析為方法論的辯護進路,和以規范化的合法性分析為方法論的質疑或反對進路。
二、收益—成本分析與合法化論辯:私營監獄的兩條研究進路 (一)“表現更好”的私營監獄?——成本—收益的實證分析 自創辦之日起,私營監獄就面臨嚴峻的競爭和挑戰:必須以比公立監獄更低的成本運營私營監獄。私營公司投標的目的就是從政府處贏利,所以比起同等狀況的公立監獄,私營監獄公司在運營上的成本需要相當大幅度的降低。與此同時,監獄合同禁止私營公司降低監禁條件、質量和囚犯安全狀況的任何行為;對于這點,即便私營監獄最堅定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認:“減低成本并不意味著可以降低監禁質量。”(20) 贏得和維持監獄合同意味著激烈的競爭,這正是私營公司降低成本的主要動力和原因。因為一旦成本提升或者質量下降,私營公司就很難在監獄市場上贏得更多的合同。私營監獄通過一系列與公立監獄迥異的措施節約成本,如降低勞動成本,緩和監獄管理人員和囚犯之間的緊張狀態,充分利用監獄容量,更有效率的采購等。(21) 到目前為止已有相當數量的對私營和公立的監獄運營成本的比較研究,這里將根據西格爾(Geoffrey F. Segal)在2002年底對有代表性的28項監獄成本研究所做的比較分析。西格爾把這些研究分成三類;第一類(表1A)是在方法論上自覺采用嚴格、中立、學術規范化研究方法的,有較高的可信程度的研究;第二類主要是政府部門或政府委托的關于私營監獄平均成本的研究;第三類研究一般因為在方法論上缺乏科學對比的嚴謹,故而一般被視為是不可靠的。見“表1”(22): 通過對“表1”特別是“表1A”所顯示的比較研究的數據的分析,我們可以斷定在一般情況下私營監獄可以比同等情況下的公立監獄節約10%—15%的運營成本。這一結論也得到了有私營監獄經驗的州政府部門以及官員的認同。正如西格爾所總結的,競爭壓力激勵著私營監獄提升效率、節約成本,通過創新規劃和管理實踐,私營監獄成功地降低了成本。 如果說私營監獄成功地降低運營成本,那么監獄質量和安全是不是因此成為犧牲品呢?現有研究似乎提供了明晰和重要的證據,說明比起公立監獄,私營監獄至少在運營質量上并未下降。來自莫爾(Adrian T. Moore)和西格爾的2002年的報告,對現有的18個對各種標準的監獄質量所做的比較研究進行了分類和總結,分為嚴格學術規范的A類,和方法論與分析存在缺欠的B類,見“表2”(23): 莫爾和西格爾的報告說明了在大多數情況下,私營監獄的質量和表現并不比公立監獄差。然而另一方面,研究者對私營監獄與公立監獄的比較研究在項目設計內容和范圍等方面一直存在爭議,不斷有新的研究成果號稱自己比過去的項目更完善和科學,而之前的項目則存在著方法論和比較項目設計上的嚴重缺陷。(24) 除了監獄內部的質量比較外,對私營監獄在改造/矯正囚犯和降低累犯率方面的低效工作的攻擊是反對者聚訟不絕的地方。雖然達拉斯縣司法治療中心的研究認為,參加私營矯正項目的囚犯比未參加該項目的同等囚犯在累犯率上降低50%,然而更多的研究認為私營監獄在矯正和威懾方面效果糟糕。(25)2005年耶魯大學的拜爾(Patrick Bayer)和波曾(David E. Pozen)在《法律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發表的對佛羅里達州矯正機構的囚犯重新犯罪(累犯)率的研究認為,雖然在運營成本上私營監獄要低于公立監獄,然而其代價是累犯率的增加。(26)因此,即便堅持用成本—收益進路分析,從長遠來看并不合算。因此,很難準確比較私營監獄和公立監獄的績效。 (二)合法性危機?——圍繞私營監獄的合法性爭辯 不僅是比較的實證研究沒有定論,反對者們還擔心以牟利為根本目的私營監獄無法阻止類似“揚斯敦(Youngstown)丑聞”的事件發生。 1997年落成之時,美國矯正公司(CCA)的俄亥俄州揚斯敦監獄接收了來自擁擠過度的華盛頓特區監獄體系的一批安全級別最高的“高風險”囚犯。然而該監獄的設計安全級別僅為中等,無法按規定的安全措施來安置這批最高安全級別的囚犯。因此在之后的18個月中,揚斯敦監獄發生了42起襲擊事件和2起致命的刺傷事件,其中1名犯人因缺乏監獄足夠的隔離設施而被刺死,此外2名管理人員被劫持后遭受生命危險。(27)不僅如此,唯利是圖的揚斯敦監獄還大量裁減管理人員,監獄老板還稱“一頓給囚犯兩片面包足矣”(28)。在揚斯敦,甚至連廁紙都定量供應,一旦有特殊情況發生,囚犯們只能用床單作為替代品。(29) 揚斯敦并不是唯一爆發丑聞的監獄,其他監獄也有類似的問題發生。(30)如果認真審視目前的監獄私營化狀況,我們會發現出現類似“揚斯敦丑聞”的事件并不出奇——這植根于政府部門和私營公司的合同中。批評者認為,目前已經發生的監獄丑聞是政府和私營公司合謀降低監獄成本所導致的。政府簽訂合同的目的是為了減少支出,而私營公司的目的是為了贏利,在缺乏更有效的監管和激勵機制的前提下,當然可能出現私營監獄為了削減成本而置監獄質量于不顧的狀況。 與此同時,監獄事務并不僅僅局限于以管理者為中心的監獄運營事務,而且涉及一個國家(社會)—監獄—囚犯三者及其之間互動的復雜網絡體系。私營化的反對者們據此認為允許私營公司控制監獄是把監獄從完整的司法系統割裂出來,因而是個不合法的政府授權。雖然支持者們區分了法院和監獄的不同功能——因而,私營監獄可以很好地執行對違反法律的犯罪人作出的正當判決。然而反對者堅持認為私營監獄容易混淆這兩項功能,誠如DiIulio教授所言,私營監獄的管理人員擁有施行從剝奪放風權到強迫禁閉的懲罰性手段的特權,而私營監獄行使這些懲罰性手段時常常不顧犯人的性質或承受能力。(31) 更為危險的前景是,私營公司嘗到利用私營監獄贏利的甜頭后,會以一個私營監獄共同體的形式游說乃至操縱監獄和刑事領域,以求實行更嚴格和更長期的刑罰,而根本不顧對犯罪人的刑罰是否合理或者正當。目前幾家獨大的私營監獄工業體系已經讓人隱約察覺到是出現某個私營監獄壟斷體或托拉斯的危險先兆。已有證據表明,私營監獄所屬的企業已經形成若干院外游說集團以影響聯邦、州和地方的各級政府和機構的決策和立法。只要“政黨存在著加大懲罰和監禁力度的經濟動機,它們就會對犯罪判決的性質和范圍施加影響”,因此必然危害“懲罰的合法性”,這是多洛維奇(Sharon Dolovich)在《杜克法學雜志》(Duke Law Journal)發表的論文所關切的中心議題。(32)在她看來,政府不應當鼓勵和扶持一個像私營監獄那樣出于其本身的營利目的而在未來可能危及懲罰的合法性的工業部門出現。 在反對者們看來,私營監獄因其獨特的性質而不能以與其他私營化部門類似的方式得到正當化論證。這是因為,監獄關涉的乃是國家刑罰與個人自由,私營監獄的存在不能保證懲罰的合法性,而公立監獄的合法性來源于國家主權和社會-個人自由的劃分。唯有堅持公立監獄的合法性,法治、人道等現代國家—社會的基本原則才能得到根本貫徹而不被侵蝕,個人自由才能得到真正落實和保障。 總之,反對者們懷疑,利益驅動下的私營監獄怎么可能公正地執行作為法院判決(潛在的)一部分的懲罰性措施,又怎么可能很好維護囚犯的基本權利——遑論囚犯改造和矯正實踐?而且,鑒于監獄連接的是囚犯和社會,反對者們擔心私營監獄最終會干涉整個司法和刑罰體系,乃至造成危害美國政治和社會秩序的惡果。 面對反對者們從實踐到理論的各方面嚴厲批評,在我看來,私營監獄支持者們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回應。 首先,迄今為止的私營監獄實踐和研究表明,私營監獄比起公立監獄節約了經濟成本,而且在監獄質量上至少并不遜色。私營監獄偶有丑聞,公立監獄也絕非清凈之地——事故和丑聞同樣不斷。因此,私營監獄固然有其缺陷,然而與公立監獄比較,迄今為止的私營監獄實踐仍值得稱道。 其次,私營監獄的確存在著只求利潤而忽視質量的隱患,然而在政府部門與私營公司的合同里已經明確規定,私營公司只有在保證監獄質量不下降的情況下才能贏得和維持合同,這本身已經極大地約束私營監獄的運營實踐。如果非要說這樣的合同缺乏改進監獄狀況和進行矯正實踐的動力,那么政府可以改進現有合同的內容以加大提高監獄質量的條款的激勵作用——把批評的中心指向私營公司未免過于偏頗。在政府、企業和學者的努力下,諸如政府官員失職、監獄獨立王國、相關法規不足和沖突等困難不是根本性的,完全可以克服。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作為20世紀80年代西方國家特別是英美私營化實踐的重要部分,私營監獄不僅帶來了更高的經濟效率和更富有創新精神的實踐,同時也間接促進公立監獄的改革。與其他市場化的私營化部門一樣,私營監獄當然可以組織和資助有關的研究智庫和游說集團,然而它們都是在法律所允許的范圍內設置和運作的。代表私營監獄利益的游說集團能更好地與政府部門和立法機構溝通和協商,改進私營監獄的未來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私營監獄帶來的競爭壓力和創新動力所引發的“鰻魚效應”,可能比私營監獄節約成本本身更有意義。 因此,私營監獄支持者們可以用一個“雙贏”的理論模型試圖證明私營監獄與其他私營化部門一樣,具備實踐和規范意義的合法性。這一理論模型既有業已存在的成功的私營化實踐作為直接論據,又有主流經濟學和公共管理學說的強力支撐(33),因此獲得不少支持者的肯定。 歸根到底,從方法論上而言,規范化的監獄質量比較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是,我們必須有一個規范化的監獄理論告訴我們什么是“表現優異”的監獄,而什么不是。然而正如前面我們提過的,在矯正理論和實踐遭到廣泛質疑,刑罰—監獄的規范化理論仍然晦暗不明的情況下,研究者似乎也只能把精力投入到充滿實踐感的監獄成本—收益的實證分析上。
三、迷失的監獄規范化理論——對監獄的懲罰哲學分析的批判 (一)曖昧的監獄規范化理論 正是因為成百上千的囚犯在監禁中被迫過著一種與正常的社會生活截然不同的與世隔絕的生活,我們得追問,監獄規范化的理論基礎到底是什么?現在我們有大量探討懲罰正當性的抽象理論,但沒多少懲罰理論關心監獄的正當性問題。似乎只要在懲罰哲學特別是抽象的道德哲學層面證明了懲罰的正當性,作為懲罰的主要形式和機構的監獄的正當性就順理成章地得到證明。 懲罰,通常意味著一定的政治組織(如國家)把痛苦加諸個人身上,它本身意味某種惡,正如邊沁所言:“我們必須牢記,懲罰本身就是一種代價:它本身就是一種惡。”(34)因此,懲罰本身的正當性需要人類的證明,這就是自古到今無數關于懲罰正當或不正當的著作和文章出現的原因。現在,我們擁有從“報應”“矯正”或“威懾”等抽象理念到“道德表達”、“恥辱標簽”等沒那么抽象的理念來論證刑罰的正當性。(35) 對比懲罰哲學的正當性論證,監獄的正當化論證則是另一番圖景。社會學家、法律人、政策制定者們關心的乃是具體的監獄實踐問題,比如什么人被關入監獄之中,他們因為何事被關進監獄,如何讓監獄醫務更有效率等。當然,這些具體的實踐問題也會引發規范性的問題,比如為什么如此眾多的大大超出人口比例的黑人和拉丁美裔人會被關押在監獄之中?然而另一方面,黑人監禁人口的例子反映了懲罰哲學的抽象話語和監禁實踐話語的二元區分:監獄里充斥著混亂和不“道德”的現象,諸如囚犯間的暴力和性虐待,不成比例的少數民族監禁人口,體罰和斑紋的囚衣,乃至利用以營利為目的私營公司來管理監獄等。然而這一切并沒有引發多少關于監獄合法化的爭論,或者說遠遠沒有引發像證明國家刑罰正當性那樣鄭重其事的思辨討論。在把監禁作為主要懲罰方式的當代,我們卻從懲罰的道德性中抽出監獄的道德性。懲罰哲學在監獄規范化理論中被邊緣化,反映了監獄規范化理論本身的含混和缺失。 懲罰的規范理論和具體實踐并非總是脫節的。懲罰哲學最著名的兩個代表人物康德和貝卡利亞各都有一套完整的懲罰哲學和相應的特定制度形式。康德的純粹報應論認為,所有人都具有內在的平等的價值,因此需要法院和立法者在制度上平等地保障和執行這些價值,因此死刑必須作為對惡意殺害他人的報復。(36)貝卡利亞同樣認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他推崇刑罰的威懾作用以反對他那個時代專橫殘暴的刑罰報應,因此他把合理的監禁判決作為刑罰的主要制度化形式。(37) 以美國歷史為例,更晚近的例子是1962年美國法學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修訂的具有規范指導作用和廣泛影響力的《模范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該法典在刑罰規范理論和具體刑罰實踐中都貫徹了以矯正為中心的刑罰哲學。(38)矯正被視為合乎道德和科學:前者因為矯正更人道主義和更具社會親和性,后者是因為矯正依賴于經驗的實證。(39)雖然20世紀50年代后失敗的矯正實踐宣告了矯正理念的幻滅,然而并沒有導致人們對監獄失去信心。或許正是這點導致了懲罰的規范化理論與具體監獄實踐的分離。如今在懲罰哲學上我們有報應、矯正、威懾、復原、混合、表達……乃至更多的規范化理論。于是在具體實踐中,監獄似乎成了執行各種各樣的懲罰的場所,犯罪人可能需要某種治療,可能需要善意的威嚇,可能需要重新回歸社會,以及首要的,我們可能僅僅需要將犯罪人與外界隔離。懲罰就是監禁,所以監獄的規范理論和具體實踐問題也將成為懲罰的問題。 (二)迷失的監獄:以監獄規范化理論為分析對象 20世紀70年代后,矯正作為美國刑罰體系的主流理念遭到了現實的嚴重挫敗:一方面是監獄的矯正實踐被宣布為失敗,一方面監獄的威懾作用也在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和累犯率面前遇到挫折。那么,是堅持矯正論,還是回到把監獄和刑罰當作是國家行使的對犯罪人之惡所做的報復的報應主義,抑或另外的模式?諷刺的是,試圖以懲罰哲學和各種主流理念或者理念之綜合為基礎的監獄合法化理論模型在實踐中遭遇了或大或小的失敗,正如下文分析的那樣。 倘若監獄的確缺乏一個規范化的理論基礎,那么實踐上的理由是否能成為監獄優于其他懲罰的原因呢?我們首先討論犯罪人的矯正治療,因為盡管不再是監獄的規范理論的主流,矯正仍然是監獄實踐的重要部分。治療實踐的動力之一就是它能在紀律化的狀態下消耗犯罪人的時間,這與矯正理想的初衷——必須采用互相隔離的大監獄以求最有益于犯人的改造——剛好顛倒,治療方案成為應付隔離化的龐大監獄的手段。龐大的監獄體系并不需要矯正作為懲罰哲學的基礎,它需要的是日常的安全、食品衛生、治療和娛樂事務。治療方案在如何控制數量眾多的監獄人口上發揮了“作用”,但并不意味著治療方案依賴于作為懲罰的監獄:治療方案似乎成了某種最小化不安定因素的技術。 那么,懲罰實踐成功地向違法者表達了某種代表否定的信息了嗎?這是刑法學家和道德哲學家孜孜以求地尋找答案的問題。聯邦、州和地方的監獄和拘留所關押了超過全美2%的勞動人口(40),這意味著什么?不用晦澀抽象的懲罰理論探求問題的答案,答案已經非常明顯。這意味監獄發揮了作用。什么作用?監獄使得美國減少了2%的失業人口,解決了立法者們通過的越來越多犯罪立法所帶來的麻煩。 另一個麻煩的問題是監獄似乎并不能解決犯罪問題。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監禁人口仍隨著犯罪率的上升而增加。刑罰的威懾論是監獄的一個重要的合法化理論,它認為對犯罪人施加足夠痛苦的威脅,會在不違反犯罪人和其他人的人權的情況下,使他們不犯罪。這一理論被自身的功利主義進路證偽了,大量嚴謹的實證研究認為監禁幾乎沒有威懾犯罪的作用。(41)我們甚至不能說監獄代表了某種刑罰上的報應主義。刑罰報應論把監禁當作是施加在犯罪人身上的報復性的痛苦,然而有研究表明,最頑固的罪犯同時也是最能抵御監禁的“痛苦”的犯罪人。 總之,監獄絲毫不按照刑罰目的所設計的那樣運作。因此,以一個規范化的理論模型來批評監獄的具體實踐的進路是無效和缺乏實際意義的。正因為如此,回顧私營監獄的種種爭論,我們才能發現雖然相關的以懲罰哲學為基礎的監獄規范化理論批判不斷,然而在蓬勃發展、大致有序的私營監獄市場實踐面前卻是多么得蒼白無力。
結論 現代國家,正如韋伯(Max Weber)影響巨大的經典定義所言,是某種能夠成功地借助于對暴力的合法行使之壟斷而在某—地域上維持統治的組織,其本質在于(合法的)暴力壟斷。(54)隨著國家壟斷機制的形成,暴力不再是國家統治的常態,它被授予給特定的組織(如軍隊、警察等)在特定時期或情況下(如戰爭、鎮壓犯罪等)使用。 而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認為韋伯的定義失之偏頗。埃氏認為國家不僅是對軍事或暴力的壟斷,同時也是對稅收和金融的壟斷,簡言之,是對暴力和稅收的孿生或雙重壟斷。埃利亞斯認為這兩種壟斷是互為條件、缺一不可的。稅收的壟斷維持了暴力的壟斷,后者反過來又維護了前者。二者不是誰先誰后的因果關系,而是同時產生的互動的雙方,是同一壟斷的兩個方面。一方消失了,另一方亦隨之消亡。(55) 重溫韋伯和埃利亞斯對現代國家及其合法性的經典研究,對我們當下的懲罰和監獄正當性問題研究大有裨益。 韋伯對暴力的論斷提醒我們,雖然國家背后隱藏的可能是壟斷性的鎮壓和暴力,然而在國家的合法化壟斷暴力成為現代世界的常態之后,其對暴力的壟斷權可能會產生某種形態的退縮或者弱化,就像暴力的某種合法授權,就像國家與私人的合作治理。回到監獄和懲罰議題上,私營監獄的出現也是在國家壟斷機制形成后,暴力不再是國家統治的常態,國家統治和個人自由往往被“權利”等似乎不直接涉及強制性暴力的字眼所遮蔽,而監獄往往也有意無意地被隔絕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之外。“隨著自由刑逐漸替代死刑而成為刑罰體系的支柱,監獄便成為國家刑罰體系的物化象征。社會日益開放,整體自由增強,信息渠道暢通,社會關系日趨復雜,國家對社會的控制逐漸弱化,自由刑(監禁刑)功能將趨于降低。監獄的未來命運也將與之相關”。(56)因此,私營監獄的出現并不稀奇,死抱著一種或者某種規范化的懲罰哲學,并不能對私營監獄的合法性造成致命的打擊,因為,懲罰及其所依靠的暴力本身已經潛遁在法律背后。 埃利亞斯對韋伯的國家定義的補充是極具洞察力和解釋力的,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懲罰機制與財政經濟的互動機制。對監獄理論和刑罰哲學研究而言,這意味著監獄理論和刑罰哲學的規范化理論不能脫離軍事/暴力與稅收/財政的互動結構,因為一旦忽視了暴力和刑罰的經濟機制,規范化理論就有可能成為無本之木。我們前面討論過的規范化刑罰哲學在具體監獄實踐上的失敗和無效,恰恰反映了埃利西斯的這一洞見。而私營監獄的復興和發展,一方面印證了韋伯的國家強制性暴力壟斷形成后,便不再是鐵板一塊不可分割,而是可以為其他主體所分化吸納;另一方面,在埃利亞斯的國家模型中,私營監獄的出現可以幫助國家解決和平時期難以承擔暴力—刑罰—監獄體系的巨大財政支出的難題。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而言,私營監獄反映的是國家懲罰體系20世紀晚期之后在暴力與財稅的互動機制下的“合理”變遷。 因此,以往的懲罰哲學研究與監獄實踐脫節乃至與更廣闊的經濟社會背景脫節的后果,往往導致懲罰哲學在解釋具體的現實問題上的無力乃至失敗。傳統的懲罰正當性的堅持者以論證暴力—刑罰正當性的國家/社會二元對立的契約論法哲學模式,來批評暴力—刑罰的分散化和授權化,忽視了國家壟斷機制形成后的暴力相對“弱化”的狀況;而且,傳統的懲罰正當性的堅持者更忽略了暴力—刑罰體系所依賴的財稅經濟基礎,往往把國家用于懲罰的經濟資源視為是無限的。在當代美國監獄出現極度擁擠和財政緊張之時,私營監獄的出現及其發展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這一實踐雄辯地說明,在國家暴力—財稅機制下,私營監獄并非如某些論者所認為的那樣侵蝕了國家的暴力—刑罰體系和機制,而是維護和增強了這一體系和機制。 以往的懲罰哲學及其所依賴的道德哲學討論的無效,根本原因是忽略了刑罰體系本身就是公立和私營的經濟部門的重要部分。(57)在很大程度上講,國際經濟狀況、國內政治—經濟體制、資源限制和增長潛能影響并決定了如何和怎樣去懲罰。因此,假如我們仍然是就事論事地用功利或者報應的概念,或者用懲罰哲學體系本身去論證需要更多或更少的刑罰,支持或反對某種刑罰或刑罰的方式,而忽略了實際的狀況和限制,那幾乎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 福柯對懲罰與監獄的解構,也讓我們的討論更加復雜和魅惑。福柯試圖揭露的是“現行的科學—法律綜合體之間的系譜。在這種綜合體中,懲罰權力獲得了自身的基礎、證明和規則,擴大了自己的效應,并且用這種綜合體掩飾自己超常的獨特性。”(58) 福柯從根本上質疑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和法律規范的正當性。在他看來,“監獄的出現標志著懲罰權力的制度化”,它蘊涵了一套新的權力技術,具有新的獨到功能。監獄是全面而嚴厲的“規訓機構”,監獄的各種矯正技術所試圖恢復的與其說是“法律主體”,不如說是“馴服的臣民”。私營監獄的出現并不意味著懲罰權力的減弱,而只是作為集規訓技術之大成的監獄形態的變化。一方面是在置身于越來越龐大復雜的全球化背景之中的美國政治—經濟體制下,越來越多無足輕重的過失犯被判決關押在監獄之中,另一方面則是在規訓權力替代主權權力和司法權力的狀況下,私營監獄能以更低的政治—經濟成本執行更好或者同等的規訓權力和技術。故而在福柯的懲罰理論框架中,懲罰理論或者監獄本身無所謂正當性,而只是一種新型國家權力以及一種新型身體處理技術的誕生過程而已,私營監獄的復興則只是這一機制的最新變化。 福柯并非簡單地反對國家、懲罰或者暴力的合理性,他對“懲罰合理性”的分析在于指明理性、人道與政治權力、法律權力之間的“名”、“實”關系,他說:人類的所有行為都通過合理性而被安排和規劃。在制度、行為和政治關系中都存在邏輯。甚至最殘暴的行為中也存在合理性。暴力中最危險的就是它的合理性。當然,暴力本身是很可怕的。但是,暴力最深刻的根源以及暴力的持續來自于我們所使用的合理性形式。如果我們生活在理性的世界,我們就能消除暴力,這種想法是極端錯誤的。暴力與合理性并非兩相對立。我的問題不是要審判理性,而是要搞清楚這種合理性與暴力竟然如此的相容。(59) 顯然,福柯的分析并沒有得到道德哲學家和法哲學家們的重視,雖然他的規訓權力概念似乎已經成為當代懲罰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我并不全部贊同福柯對懲罰或者暴力的合理性所做的解構、對國家和法律的合法性和規范性的批判以及對懲罰和權力關系的分析,也不認為在私營監獄這一案例中,福柯的規訓權力的懲罰理論能夠解釋和說明全部問題。然而福柯的分析的價值在于,他從根本上質疑現代以來的法律和懲罰體制的正當性,提醒懲罰哲學和監獄規范化理論的革新很可能依賴于社會體制的整體性前提。 懲罰哲學作為一種論證懲罰正當性的理論,當然并不意味著現實的懲罰實踐就一定如此。然而,私營監獄的出現及其成功實踐,以及眾多試圖給私營監獄以“規范”的批判或贊成的懲罰哲學討論的無效和失敗,深刻地反映了當下監獄實踐缺乏一個規范化的懲罰哲學基礎的事實,也說明傳統的懲罰哲學的思辨討論距離懲罰實踐過于遙遠。 如果規范性的哲學理論不與正在發生變化的懲罰實踐相結合,這種規范性理論將注定要失敗。哲學家和法哲學家們是否能夠更好地評價私營監獄等懲罰實踐,或者提出更好的刑罰改革建議,取決于他們對事實的把握。那么,福柯的批判式的分析進路就自有其意義,哲學家因此也需要對福柯的權力概念進行辨析和思考乃至回應。更廣泛地講,未來的規范性的懲罰哲學需要哲學與社會學、經濟學和歷史學乃至知識社會學等多學科的共同努力,在實踐和理論的結合中尋找可能的答案。(60)唯有如此,在解釋變動中的諸如私營監獄這樣的懲罰實踐的問題上,懲罰哲學才不會迷失答案。 最重要的可能是反思和尋找。至于答案本身,誠如福柯所言:“我知道我找不到答案,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不去問問題。”(61)
注釋: ①Friedrich W. 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in Walter Kaufmann, trans. & ed., Basic Writings of Nietzsche,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68, p. 83. ②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賀麟、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4頁。 ③本文把“private prison”譯為“私營監獄”而非“私有監獄”,因為現有的私營監獄在刑罰層面上必須依賴國家,私營公司擁有的是監獄設施的產權和監禁犯罪人等監獄運營的權利。 ④Chase Riveland, "Prison Management Trends, 1975-2025", Crime & Justice, Vol. 26: 163—204(1999). ⑤例見于世忠、鄭黎平:“評美國監獄的私營化趨勢”,載《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4年第4期;杜強:“美國監獄私營化現象”,載《社會》1999年第4期。 ⑥例見王廷惠:“美國監獄私有化實踐中的政府角色研究”,載廖進球、陳富良主編:《規制與競爭前沿問題》(第二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 ⑦本文用“復興”而不是“出現”來描述20世紀晚期美國私營監獄實踐,是因為(西方)監獄自誕生至近代之前都屬于私營而非公立。本文的“復興”為中性含義。 ⑧Chase Riveland, "Prison Management Trends, 1975-2025", supra note④, at 164. ⑨Yijia Jing, "State prison privatization in the US: A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magnitude", at http://www.ohiolink.edu/etd/send-pdf.cgi?osu112257130,最后訪問日期2008年10月2日。盡管這一概括忽略了許多重要因素,比如懲罰實踐的失敗,但仍然是目前為止的比較全面的一項綜述性研究。 ⑩Paige M. Harrison & Jennifer C. Karberg, "Prison and Jail Inmates at Midyear 2003",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Bulletiu, 2004, p. 1, at http://www.ojp.usdoj.gov/bjs/pub/pdf/pjim03.pdf,最后訪問日期2008年10月2日。 (11)David R. Werner, Correctional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California: Interstate Publishers, Inc. 1990, p. 121. (12)Robert Martinson, "What Works?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Prison Reform", Public Interest, Vol. 12: 22—55(1974). (13)理查德·霍金斯、杰弗里·阿爾珀特:《美國監獄制度——刑罰與正義》,孫曉靂、林遐譯,郭建安校,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58—59頁。 (14)Robert Martinson, "What Works?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Prison Reform", supra note②, at 47. (15)Hindelang Criminal Justice Research Ctr., U.S. Dep't Of Justice, Sourcebook Of Criminal Justice Statistics 2002, p. 478, at http://www.albany.edu/sourcebook/pdf/sb2002/sb2002-section6.Pdf,最后訪問日期2008年10月2日。 (16)Paige M. Harrison & Allen J. Beck, Prisoners In 2003,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U. S. Dep't Of Justice, Bulletin No. NCJ 205335, 2004, p. 2. (17)Paige M. Harrison & Jennifer C. Karberg, "Prison and Jail Inmates at Midyear 2003",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Bulletin, 2004, p. 1, at http://www.ojp.usdoj.gov/bjs/pub/pdf/pjim03.pdf,最后訪問日期2008年10月2日。 (18)James Austin & Garry Coventry, "Are We Better Off? Comparing Private and Public Pris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t Issues In Crim. Just. , Vol. 11: 179(1999). (19)Sharon Dolovich, "State Punishment and Private Prisons", Duke Law Journal, Vol. 55: 437—546(2005). (20)Charles H. Logan, Private Prisons: Cons And Pros, in Douglas C. McDonald, ed., Private Prison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 (21)Daniel W. Okada, "Maybe This Will Work", Infrastructure Finance, October 1996. (22)Geoffrey F. Segal, "The Extent, History, and Role Of Private Companies in The Delivery of Correctional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Study, Vol. 302: 1—22(2002). (23)Geoffrey F. Segal & Adrian T. Moore, "Weighing the Watchmen: Evaluating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utsourcing Correctional Services", Policy Study, Vol. 290: 3(2002). (24)這方面的研究很多,如Camp等人2002年在《刑事評論》發表的研究,參見Scott D. Camp, G. G. Gaes, J. Klein-Saffran, D. M. Daggett, and W. G. Saylor, "Using Inmate Survey Data in Assessing Prison Performance: A Case Study Comparing Private and Public Prisons", Criminal Justice Review, Vol. 27: 26—51(2002). (25)Geoffrey F. Segal & Adrian T. Moore, "Weighing the Watchmen: Evaluating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utsourcing Correctional Services", Policy Study, Vol. 290: 3(2002), at 9. (26)Patrick Bayer & David E. Pozen, "The Effectiveness Of Juvenile Correctional Facilities: Public Versus Private Managemen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48(2): 549—590(2005). (27)60 Minutes: Private Prisons Break Rules to Make a Profit(CBS television broadcast May 2, 1999). (28)Mark Tatge, "Employees Criticize Privately Run Facilities", Cleveland Plain Dealer, Aug. 30, 1998, at 18A. (29)Cheryl W. Thompson, "Ohio Issues Restraining Order for Prison Firm; Control of Facility Cannot Be Changed", Wash. Post, Nov. 19, 1998, at B4. (30)See Kim Bell, "Texas Jail Says Incident Was Over blown", St. Louis Post-Dispatch, Aug. 26, 1997, at 1A. (31)John DiIulio, The Duty To Govern: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Private Management of Prisons and Jails, in Douglas C. McDonald, ed., Private Prison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0. (32)Sharon Dolovich, "State Punishment and Private Prisons", Duke Law Journal, Vol. 55: 438. (33)D. C. McDonald & C. Patten, "Governments' Management of Private Prisons"(a research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t http://www.ncjrs.gov/pdffilesl/nij/grants/203968.Pdf,最后訪問日期2008年10月2日。 (34)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J. H. Burns and H. L. A. Hart, eds.,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70, p. 179. (35)Antony Duff, Punishment,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 (36)Immanuel Kant,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Mary J. Gregor & Roger J.Sullivan,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33. (37)Cesare Beccaria, 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and Other Writings, Richard Bellamy, ed., Richard Davies, tra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9. (38)雖然《模范刑法典》并不具備法律效力,然而至少有37個州以該法典為藍本制定本州刑法,而新澤西州、紐約州、賓夕法尼亞州和俄勒岡州幾乎完全采用該法典。見維基(wiki)百科“Model_Penal_Code”條,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del_Penal_Code,最后訪問日期2008年10月2日。 (39)Francis A. Allen, The Decline of the Rehabilitative Ideal: Penal Policy and Social Purpos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2. (40)Katherine Beckett & Bruce Western, "How Unregulated is the U.S. Labor Market? The Penal System as a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 Am. J. Soc., Vol. 104:1030(1999). (41)Franklin Zimring, "Imprisonment Rates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Criminal Punishment", Punishment & Society, Vol. 3: 161(2001). (42)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306頁。 (43)同上注,第312頁。 (44)安東尼·吉登斯:《社會學》(第4版),趙旭東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頁。 (45)米歇爾·福柯:《必須保衛社會》,錢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頁。在我看來,正是在經濟與規訓權力的關系問題上,福柯的懲罰理論并不能很好地解釋私營監獄的重生和蓬勃發展,福柯似乎忽視了經濟—政治結構的強大決定作用。 (46)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354頁。 (47)Davids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ociety in Soci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 129. (48)參見王立峰:“對法律懲罰的批判:馬克思主義的進路”,載《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6期。 (49)福柯原文出處不詳,轉引自誠之:“法律、權力與規訓社會”,at http://lawroad.net/bbs/archiver/tid-555.html,最后訪問日期2008年10月2日。 (50)福柯:《性經驗史》,余碧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增訂版,第66頁。 (51)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5頁。 (52)同上注,第351頁。 (53)盧瓦克·瓦關:“從福利國家到‘監獄國家’:美國將窮人關進監獄”,載《[法]外交世界》1998年第7期(Le Monde diplomatique, July 1998), at http://www.xsjjy.com/rqwx/mgqiongren.htm,最后訪問日期2008年10月2日。 (54)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5頁。 (55)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第二卷),袁志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18—120頁。 (56)轉引自佚名:“當代中國監獄結構與現代監獄制度建構論”,監獄信息網,at http://prison.com.cn/Theoretics/2004-9-23/A1BB8D01-38FF-4CC1-BBAD-1D68B65D21E6.Html,最后訪問日期2008年10月2日。 (57)Sarah Armstrong, "Model Penal Code: Sentencing: Bureaucracy, Private Prisons, and the Future of Penal Reform", Buff. Crim. L. R.., Vol. 7: 275(2003). (58)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351頁。 (59)Michel Foucault, Foucault Live(Interviews, 1961-1984), in Sylvère Lotringer, ed., Lysa Hochroth & John Johnston, trans. , 2nd edition, New York: Semiotext(e), 1996, p. 299. (60)需要指出的是,規范性(哲學)理論和社會理論之間存在著“應然”和“實然”之間的差別,因此,規范性理論必然不同于社會理論以及經驗研究。然而另一方面,又不存在完全脫離“實然”狀況的“應然”理論。一個規范性理論如果與實踐脫節很大,卻又支配人們的思維模式,勢必會造成理論和實踐的種種問題,比如傳統的懲罰哲學在解釋私營監獄問題上的迷失。 (61)Michel Foucault, Politics and Reason, in Lawrence Kritzman, Michel Foucault: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 New York: Routledge, p. 74.中文版見福柯:“政治與理性”,趙曉力、王宇潔譯,at http://fabiusblog.blog.hexun.com/15515172_d.html,最后訪問日期2008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