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我們究竟打造什么樣的監(jiān)獄?
佚名
黨的十六大的召開具有跨時(shí)代的偉大意義,在新修改的黨章中,“三個(gè)代表”被寫進(jìn)了黨章,這其中一個(gè)重要的內(nèi)容就是要求我們共產(chǎn)黨人必須與時(shí)俱進(jìn)。這些天,通過深入地學(xué)習(xí)黨的十六大文件,心潮起伏,不能平靜,聯(lián)想到我們所從事的監(jiān)獄工作,總感覺到有許多話要說,也就是說,我們應(yīng)當(dāng)打造什么樣的監(jiān)獄,才能夠與時(shí)俱進(jìn)。 綜觀近十余年的監(jiān)獄工作,變化之巨、發(fā)展之巨是過去任何時(shí)期都少有的,現(xiàn)在走到哪兒,都可以見到建筑典雅、環(huán)境衛(wèi)生的監(jiān)獄或者是監(jiān)區(qū)。雖…… 第一,關(guān)于監(jiān)獄體現(xiàn)國(guó)家意志還是體現(xiàn)最廣大人民意志的問題 高文同志說:“將國(guó)家與社會(huì)等同,或者用國(guó)家取代社會(huì)是非常有害的,應(yīng)當(dāng)逐漸將二者分開”。“我們的監(jiān)獄是不是應(yīng)該順應(yīng)時(shí)代的發(fā)展要求,逐漸地從國(guó)家意志的具體體現(xiàn)向最廣大人民意志的具體體現(xiàn)轉(zhuǎn)變”。我們?cè)谶@里暫且不去討論國(guó)家與社會(huì)的差別,但是在我們這個(gè)由人民當(dāng)家作主的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里,國(guó)家的意志和最廣大人民的意志是統(tǒng)一的,兩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監(jiān)獄所體現(xiàn)出來的國(guó)家意志就是全社會(huì)最廣大人民的意志,兩者并不矛盾。把這兩者割裂開來,對(duì)立起來,轉(zhuǎn)變過來是徒勞的。 第二,關(guān)于監(jiān)獄的本質(zhì)職能問題 高文同志說:“對(duì)于監(jiān)獄而言,其最終的意義也應(yīng)當(dāng)是社會(huì)管理的一種方式,而絕非國(guó)家意志的體現(xiàn)”。我們并不否認(rèn)監(jiān)獄是社會(huì)管理的一種方式,但是,監(jiān)獄是社會(huì)管理的一種特殊方式,這種方式是由代表國(guó)家意志的監(jiān)獄人民警察去實(shí)施對(duì)罪犯的管理職能,帶有強(qiáng)制性,這與社會(huì)上普通公民內(nèi)部的自我管理方式是有本質(zhì)區(qū)別的。正因?yàn)槿绱耍鳛閲?guó)家機(jī)器的典型工具之一,監(jiān)獄只能是國(guó)家意志的體現(xiàn)。只要監(jiān)獄存在一天,它的本質(zhì)職能是絕不會(huì)改變的。在我國(guó),監(jiān)獄的本質(zhì)職能就是《監(jiān)獄法》規(guī)定的“正確執(zhí)行刑罰,懲罰和改造罪犯,預(yù)防和減少犯罪”。 第三,關(guān)于對(duì)罪犯的評(píng)價(jià)和對(duì)監(jiān)獄警察作用的評(píng)價(jià)問題 高文同志說:“實(shí)際上,就絕大多數(shù)罪犯而言,除了法院為他貼上罪犯的標(biāo)簽這一點(diǎn)外,他的日常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應(yīng)當(dāng)說和普通公民沒有多大差別,否則的話,監(jiān)獄秩序不可能那樣穩(wěn)定。這里我絕沒有否定我們監(jiān)獄警察的作用”。這里我們姑且不論罪犯的日常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與普通公民的差別問題,但是有一個(gè)原則問題是必須搞清楚的,那就是被法院判刑入獄的絕大多數(shù)罪犯僅僅是被法院貼上了罪犯的標(biāo)簽?zāi)剡€是他們真是罪犯?如果絕大多數(shù)罪犯真是除了法院為他貼上罪犯的標(biāo)簽這一點(diǎn)外,而沒有社會(huì)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刑法當(dāng)罰性,監(jiān)獄還有什么存在的價(jià)值?如果因?yàn)樽锓傅娜粘P袨楹退季S方式與普通公民沒有多大差別,就能確保監(jiān)獄秩序的穩(wěn)定,那還要監(jiān)獄警察干什么呢?試問如果沒有監(jiān)獄警察的辛勤工作,監(jiān)獄秩序可能那樣穩(wěn)定嗎?這里顯然是否定了我們監(jiān)獄警察的作用。 第四,關(guān)于對(duì)我們監(jiān)獄改造作用的評(píng)價(jià)問題 高文同志在列舉了一個(gè)好人關(guān)進(jìn)監(jiān)獄變壞的例子后說:“一個(gè)并不是罪犯的人經(jīng)過我們監(jiān)獄的改造,變成了罪犯的樣子,那么,對(duì)于那些本身就是罪犯的人,結(jié)果會(huì)怎樣呢?所以說,對(duì)于罪犯的行為,更多意義上應(yīng)該是一種管理,而非改造。否則的話,不僅僅是對(duì)絕大多數(shù)罪犯的不公平,而且極有可能對(duì)罪犯的心理造成傷害,使其難以適應(yīng)社會(huì)”。言下之意,監(jiān)獄不是改造罪犯的地方,而是把一個(gè)并不是罪犯的人“改造”成了罪犯的樣子。罪犯是越改造越壞,所以對(duì)罪犯應(yīng)該管理而非改造。這里顯然否定了我們監(jiān)獄改造罪犯的積極作用,這是和“以改造人為宗旨”的監(jiān)獄工作方針相違背的。 第五,關(guān)于罪犯的改造是針對(duì)群體還是個(gè)體的問題 高文同志說,改造“所針對(duì)的應(yīng)該是罪犯群體,而不應(yīng)該面對(duì)著罪犯?jìng)€(gè)體。不然的話,就是將它與管理等同起來,與具體的管理措施都等同起來,其結(jié)果就是使改造庸俗化了”。我們知道,任何群體都是由個(gè)體組成的,沒有個(gè)體就沒有群體,在監(jiān)獄的工作實(shí)踐中,對(duì)罪犯群體的改造都是從對(duì)罪犯?jìng)€(gè)體改造中體現(xiàn)出來的,對(duì)罪犯群體的改造成果都是由無數(shù)罪犯?jìng)€(gè)體改造成果累積起來的。按照因人施教的原則,對(duì)罪犯的改造應(yīng)該從個(gè)體出發(fā),逐步擴(kuò)大個(gè)別教育的范圍,避免千篇一律、無的放矢,才能提高改造質(zhì)量。由此可見,改造所針對(duì)的應(yīng)該是罪犯?jìng)€(gè)體,而管理所面對(duì)的才是罪犯群體。試想,如果改造所針對(duì)的是罪犯群體,對(duì)于情況各不相同的罪犯群體的改造還有什么針對(duì)性呢?這是與分類改造的原則相抵觸的。問題的關(guān)鍵并不在于改造是針對(duì)群體還是個(gè)體、管理是針對(duì)群體還是個(gè)體,改造和管理對(duì)于罪犯群體和個(gè)體的適用效果有待探討。高文同志把對(duì)罪犯?jìng)€(gè)體的改造斥之為“使改造庸俗化”,實(shí)際上是對(duì)改造的否定。 第六,關(guān)于罪犯是“存在”還是“意識(shí)”的問題 高文同志說:“社會(huì)上還有犯罪人、犯罪人親屬以及那些對(duì)犯罪問題有自己獨(dú)到見解的團(tuán)體或者人群,千萬不能忽視他們,他們是一個(gè)非常龐大的群體,其中絕大多數(shù)都是我們社會(huì)主義事業(yè)的擁護(hù)者,在他們的心目中,那些犯了罪的人,不是什么罪犯,而是他們的父母、兒女、丈夫或者妻子……他們所期求的恐怕更多的是監(jiān)獄要善待罪犯,期求罪犯能夠早日平安地返回家鄉(xiāng)。如此說來,現(xiàn)行監(jiān)獄法為監(jiān)獄所設(shè)定的角色就不太妥當(dāng)了。我個(gè)人認(rèn)為,切不可以將懲罰罪犯作為監(jiān)獄的一項(xiàng)重要職能”。這個(gè)觀點(diǎn)如果能夠成立的話,那么世界上就無罪犯可言了。這是在罪犯問題上“存在”和“意識(shí)”誰是第一性的問題。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diǎn)看問題,罪犯是客觀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這里有一個(gè)大是大非問題,即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入獄的罪犯到底是不是罪犯?是不是因?yàn)榉缸锶擞H屬的情感因素就能改變罪犯的性質(zhì)?是不是因?yàn)闉榱苏疹櫡缸锶擞H屬等人群就要改變懲罰罪犯的職能呢?監(jiān)獄的工作方針是“懲罰與改造相結(jié)合,以改造人為宗旨”。對(duì)罪犯實(shí)施懲罰的職能既是監(jiān)獄人民警察行刑的法律依據(jù),又是行刑的必要手段。罪犯危害社會(huì),觸犯刑律,受到法律制裁是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正義的判決。懲罰罪犯正是體現(xiàn)了社會(huì)的公正性、正義性,同時(shí)懲罰是改造罪犯的強(qiáng)制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在司法部頒布的《罪犯改造行為規(guī)范》中明確規(guī)定了罪犯服刑期間必須做到“十不準(zhǔn)”。這是對(duì)罪犯行為的法紀(jì)約束。懲罰和改造的關(guān)系是對(duì)立統(tǒng)一關(guān)系,它們各以對(duì)方的存在為前提,離開了懲罰就不能穩(wěn)定監(jiān)獄的正常秩序,改造就無法進(jìn)行;離開了改造,單純的懲罰就失去了懲罰固有的意義。懲罰是改造的前提和保證。懲罰從打擊犯罪、伸張正義的角度來看它是目的;從保證改造任務(wù)實(shí)施來看,它又是手段。由此可見,懲罰的職能對(duì)于罪犯不僅是正義的,而且是必須的。沒有懲罰的改造工作是不可想象的。 第七,關(guān)于懲罰的內(nèi)容問題 高文同志說:“除了執(zhí)行刑罰,法律似乎并沒有賦予監(jiān)獄其他懲罰罪犯的權(quán)力,但是,由于監(jiān)獄法將懲罰作為了監(jiān)獄的一項(xiàng)重要任務(wù),這就為在具體的實(shí)踐工作中大量的懲罰罪犯的措施出臺(tái)大開了方便之門”。這里先分析一下懲罰的內(nèi)容:筆者以為懲罰是與罪犯所應(yīng)承擔(dān)的法律責(zé)任相適應(yīng)的,一是依法剝奪或限制罪犯的自由;二是對(duì)于附加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罪犯在法定的期限內(nèi)剝奪其政治權(quán)利;根據(jù)我國(guó)憲法、監(jiān)獄法等法律規(guī)定,“罪犯的政治權(quán)利,主要是指沒有附加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罪犯依法可行使選舉權(quán)。除此之外,罪犯的政治權(quán)利都處于被剝奪或停止行使?fàn)顟B(tài)”。三是對(duì)警告、記過或禁閉措施的使用。當(dāng)發(fā)生罪犯聚眾哄鬧監(jiān)獄,擾亂正常秩序的8種破壞監(jiān)管秩序的情形,監(jiān)獄可以給予警告、記過或者禁閉。對(duì)發(fā)生罪犯加戴戒具后,仍不能消除其犯罪危險(xiǎn)的4種情況,監(jiān)獄可采用禁閉這種強(qiáng)制防范措施,這也是對(duì)罪犯的一種行政處罰措施。對(duì)于罪犯聚眾哄鬧監(jiān)獄,擾亂正常秩序,構(gòu)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zé)任。四是對(duì)警棍、警繩、戒具和武器的使用。對(duì)發(fā)生罪犯結(jié)伙斗毆、毆打他人、尋釁滋事、哄鬧監(jiān)獄、行兇暴動(dòng)的4種情形時(shí),經(jīng)警告無效的,可以使用警棍。當(dāng)監(jiān)獄人民警察在追捕逃跑的罪犯和押解罪犯途中,可以使用警繩。當(dāng)發(fā)生罪犯有脫逃行為等4種情形時(shí),可以使用手銬等戒具。對(duì)發(fā)生罪犯聚眾騷亂、暴亂等5種情形時(shí),非使用武器不能制止的,按照國(guó)家有關(guān)規(guī)定,人民警察和武警部隊(duì)執(zhí)勤人員可以使用武器。五是履行某些罪犯特有的法定義務(wù)。六是使罪犯受到應(yīng)有的法律上的譴責(zé)。明確了上述懲罰的具體內(nèi)容,就不難看出那些體罰、變相體罰、刑訊逼供或者某些土政策等等都是法律所不允許的,都在嚴(yán)格禁止或糾正之列。所以,決不能把執(zhí)法執(zhí)紀(jì)中存在的問題歸咎于“由于監(jiān)獄法將懲罰作為了監(jiān)獄的一項(xiàng)重要任務(wù)”之過。

江叢刊.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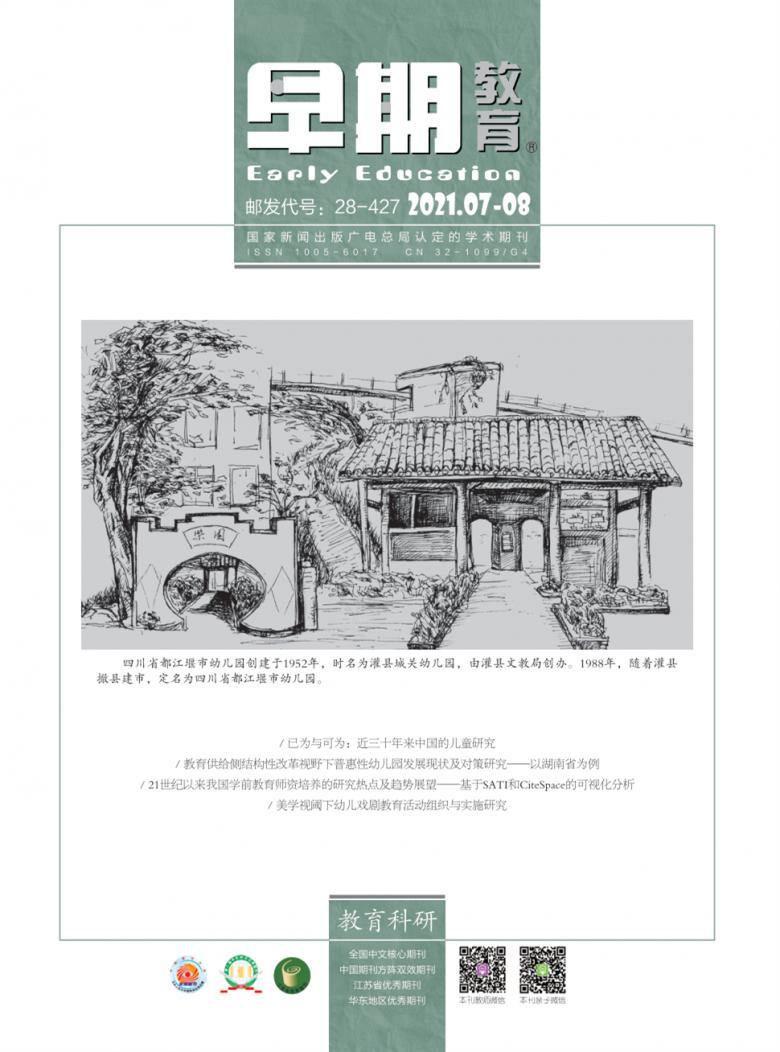
代園藝.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