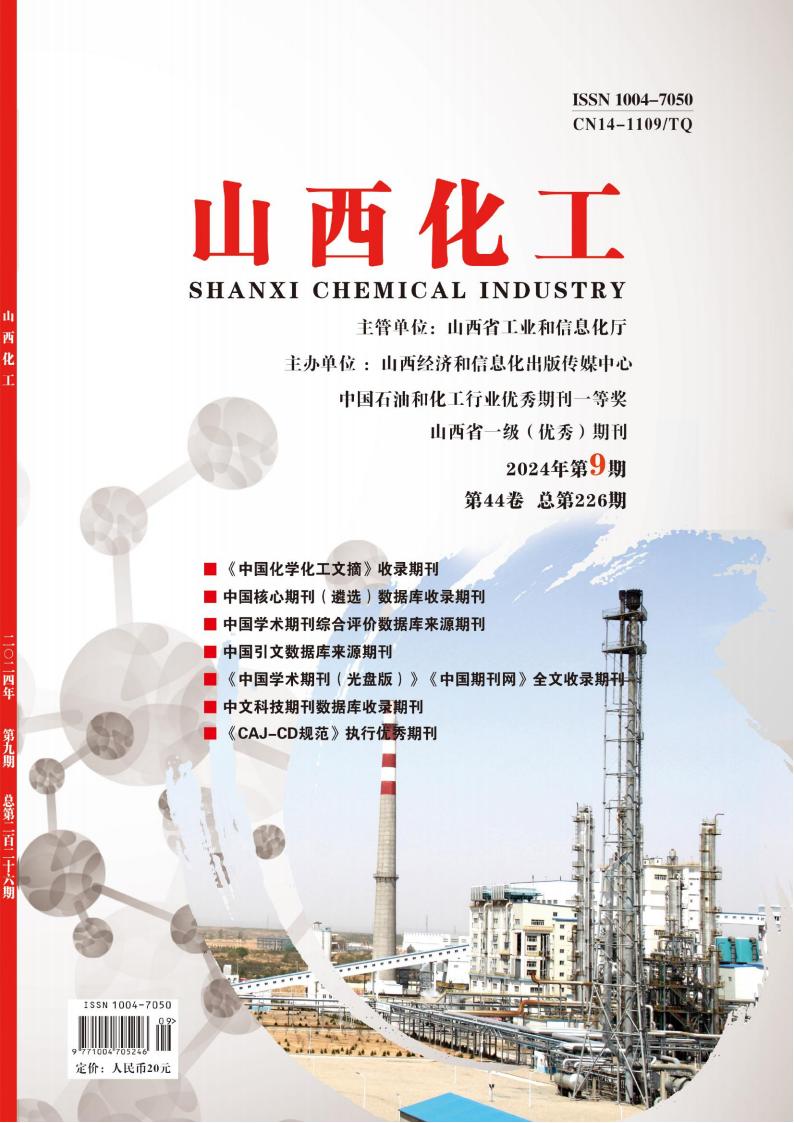商議性民主與公眾參與環(huán)境治理:以浙江農(nóng)民抗議環(huán)境污染事件為例
佚名
一、前言
在西方,公眾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受到廣泛的重視,但是,中國的公共政策的制定鮮有大眾的參與。近些年來,浙江發(fā)生農(nóng)民以暴力抗議當?shù)丨h(huán)境污染之事件時有發(fā)生。這些暴力事件不僅挑戰(zhàn)了以GDP為核心的發(fā)展觀,而且凸現(xiàn)出中國公共政策之缺失。本文以2005年發(fā)生于浙江省東陽市與新昌縣兩起農(nóng)民暴力抗議環(huán)境污染之事件為個案,探討商議性民主與公眾參與環(huán)境治理之關系。東陽市與新昌縣兩起農(nóng)民暴力抗議環(huán)境污染之事件不僅反映了地方政府、企業(yè)與農(nóng)民在價值和利益的沖突,而且表明在涉及到本地環(huán)境問題上公共決策制定與執(zhí)行的缺失,指向了中國環(huán)境不正義之現(xiàn)狀。本文從商議性民主理論與實踐角度來探究環(huán)境保護、治理與公眾參與的關系。一方面從兩起農(nóng)民暴力抗議環(huán)境污染事件導引出商議性民主機制對于公眾參與環(huán)境保護之意義,另一方面嘗試提出環(huán)境保護與治理過程中幾種公眾商議實踐,作為減少直接暴力的沖突、讓公眾有效地參與環(huán)境治理的未來可能發(fā)展的一個方向。文章的中心論點就是,環(huán)境治理應該強化民主的協(xié)商(democratic deliberation),倡導“商議合作型環(huán)境治理”模式,從而最終走向生態(tài)民主化之路(toward ecological democratization)。
文章的結(jié)構(gòu)如下。第二部分描述分別于2005年4月和7月發(fā)生于浙江省東陽市和新昌縣兩起因環(huán)境污染而造成當?shù)剞r(nóng)民與軍警發(fā)生沖突的事件。接著分析農(nóng)民集體杭議環(huán)境污染之性質(zhì)及發(fā)生暴力沖突之根源。第四部分分析將商議性民主機制引入到公眾參與環(huán)境保護與治理中的意義,討論了在環(huán)境保護與治理過程中幾種公眾商議(public deliberation):公民論壇、全民公決和調(diào)停。第五部分是結(jié)語,是全文的一個簡單的總結(jié)。
二、2005年浙江兩件農(nóng)民抗議環(huán)境污染事件[1]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經(jīng)濟成就,然而代價是環(huán)境污染問題嚴重。盡管在2002年6月,浙江省第十一次黨代會提出建設“綠色浙江”被省委確定為浙江省在新的歷史階段的戰(zhàn)略目標,但是,三年來浙江卻發(fā)生了多起因環(huán)境污染而造成當?shù)剞r(nóng)民與軍警沖突事件。而2005年對于浙江省的環(huán)保包括經(jīng)濟發(fā)展本身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因為民眾不滿的情緒瞬時被激蕩出來,匯集成勃興的社會力量,開始爭取被發(fā)展為本所剝奪的環(huán)境權利,發(fā)生了多起因環(huán)境污染而造成當?shù)剞r(nóng)民與軍警沖突事件。其中東陽市畫水鎮(zhèn)農(nóng)民集體抗議與新昌縣農(nóng)民集體抗議最引人注目。
(一)、“歌山畫水”變成“山不再青,水不再美”:東陽畫水鎮(zhèn)農(nóng)民環(huán)境的抗爭
“還我土地,我要生存;還我土地,我要健康;還我土地,我要子孫;還我土地,我要吃飯;還我土地,我要環(huán)境。”這是浙江省東陽市畫水鎮(zhèn)農(nóng)民面對當?shù)鼗て髽I(yè)所造成的極其嚴重的環(huán)境污染而不得已打出的標語。
畫水鎮(zhèn)有5.3萬人口。原來這里依山傍水,素有“歌山畫水”的美譽,現(xiàn)在卻“山不再青,水不再美,農(nóng)田不可以耕種,莊稼無法良好生長。”因為自2001年起,原畫溪鎮(zhèn)政府以租賃土地的形式,開始建設竹溪工業(yè)園區(qū),目前園區(qū)占地約千畝,共有13家化工、印染和塑料企業(yè),其中化工企業(yè)有8家。據(jù)當?shù)卮迕穹从常盎S、農(nóng)藥廠常常排出大量的廢氣、廢水,發(fā)出難聞的氣味,刺鼻又刺眼。特別在悶熱天氣,化學氣體驅(qū)之不散,在嚴重的時候刺得孩子們睜不開眼睛。”
2001年,東農(nóng)化工公司和當時的畫溪鎮(zhèn)政府及畫溪五村達成土地租用協(xié)議時,時任五村黨支部書記的王偉并沒有去簽字。當年9月,王偉來到金華市某藥業(yè)公司,咨詢了東農(nóng)的情況之后,寫了一份名為“給東農(nóng)公司畫像”的公開信。東農(nóng)公司的前身是東農(nóng)農(nóng)藥廠,原坐落于吳寧鎮(zhèn)盧宅村東面,其生產(chǎn)的氟樂靈,三環(huán)唑、代森猛鋅及中間體,在生產(chǎn)過程中都產(chǎn)生大量廢水廢渣,因此被當?shù)卮迕耱?qū)趕。“畫像”稱,后東農(nóng)欲搬至李宅蔡盧村,但被當?shù)卮迕褡柚梗缓笥职嶂廖荷芥?zhèn)白塔村,因遭當?shù)卮迕穹磳Γ瑢U水拉到舊廠址偷偷排放,后經(jīng)當?shù)孛襟w曝光,當時的浙江省長柴岳松批字,予以停產(chǎn)。王偉和其他村民復印了150份“畫像”,從金華寄到畫溪鎮(zhèn)五村和附近村莊。之后有600多名村民對此進行了簽名呼吁;而王永飛等村民又復印了1000份。當年10月,當?shù)嘏沙鏊终{(diào)查“畫像”來源,并通知知情人王某某前去談話;王同其他村民約定,若一小時內(nèi)不返回,大家就敲銅鑼去解救他。結(jié)果一小時后村民前去“解救”時,半路遭遇正返回的王,大家索性前去鎮(zhèn)政府陳情。后在一家飯店看到正在吃飯的鎮(zhèn)里領導許某,村民把許拉出去要求解釋。在將許拉往竹溪化工園區(qū)的路上,村民沖散前來為許解圍的民警,并和許發(fā)生肢體沖突,致使許受輕傷。到了園區(qū),村民強行將化工廠員工趕出宿舍,并毀壞了機器設備等設施,造成損失11萬多元。之后,王偉等12人被捕。據(jù)《鳳凰周刊》得到的一份東陽法院刑事判決書:2002年,王偉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判刑3年,王永飛等其他村民以同一罪名判1年或幾個月不等刑期,兩個緩刑。
村民稱,2005年3月15日是東陽市政府市長接待日,當?shù)卮迕袂叭シ从澄廴締栴}時,未被有關領導接待。3月20日起,村民開始在化工園區(qū)鄰近各村的出路口搭建了十多個毛竹棚,并由村中老人駐守,堵塞路口,強烈要求化工廠、農(nóng)藥廠搬遷。村民說:“3月28日,百多名執(zhí)法人員和鄉(xiāng)鎮(zhèn)干部放火燒掉了大棚。而鄰村村民募捐給我們的6000多元錢,也不知是給燒掉了還是給沒收了,沒有下落。”之后,村民再次搭起毛竹棚。期間,鄰市的一些義烏商人支持村民,免費供應面包、方便面。 4月1日,東陽市政府出臺“四條意見”,下發(fā)文件,決定對畫水鎮(zhèn)竹溪工業(yè)功能區(qū)內(nèi)的13家工業(yè)企業(yè),從2005年4月2日起實施停產(chǎn)整治。
4月5日,畫水鎮(zhèn)團委、婦聯(lián)、老齡委、殘聯(lián)發(fā)出一份倡議書,稱要“堅決與少數(shù)擾亂社會正常秩序的不法分子作斗爭,并積極勸說少數(shù)盲目跟風的人及時回頭。”4月6日,畫水鎮(zhèn)委和鎮(zhèn)政府“致全鎮(zhèn)人民公開信”:嚴正警告“那些極少數(shù)不法分子懸崖勒馬,積極主動地配合政府做好工作,否則,對策劃、參與、繼續(xù)制造事端、擾亂社會秩序者一律從重從快予以嚴懲。”4月6日,東陽市公安局發(fā)出通告:“限令滯留在畫水鎮(zhèn)竹溪工業(yè)功能區(qū)路口的群眾盡快撤離現(xiàn)場,所設置的路障(毛竹棚、石頭等)盡快拆除清理,立即停止一切違法行為。否則政府公安機關將采取措施予以強行帶離現(xiàn)場、強制拆除清理。妨礙執(zhí)行公務的,將承擔一切法律后果。” 4月9日晚間,當?shù)劓?zhèn)政府派出10多名執(zhí)法人員來到畫溪村出路口,說夜里要刮風下雨,勸村里老人離開毛竹棚,但老人們沒有聽從。之后,地方政府采取了清理行動:4點多時,包括警車和公交公司的大巴車共有100多輛運送執(zhí)法人員到達。據(jù)村民說,當時執(zhí)法人員封鎖了毛竹棚所在地,一排警察手持盾牌,組成方陣,阻止大量趕來的村民進入拆除現(xiàn)場,執(zhí)法者設立了現(xiàn)場指揮部,市主要領導在現(xiàn)場指揮。多名目擊村民稱:“執(zhí)法人員包括公安、城管及保安人員,另有花錢請的附近鄉(xiāng)鎮(zhèn)機關的人員,約計3500人。”
地方政府對事件已有相當?shù)男睦頊蕚洌潞髞砜矗麄儗π蝿莸墓烙嬋燥@不足。村民越聚越多,后來有兩三萬人,聲勢浩大。警方發(fā)現(xiàn)對峙下去可能會造成大規(guī)模沖突,開始主動撤離。但此時,外圍的村民坐在路上阻止官方撤離,造成混亂。情緒激動的村民開始追打身穿警服或政府配給雨衣的執(zhí)法人員,一些執(zhí)法人員紛紛扔下警棍、橡皮棍、盾牌、砍刀,并脫去鋼盔和制服,撤離現(xiàn)場。
這就是東陽市畫水鎮(zhèn)農(nóng)民集體抗議環(huán)境污染事件之梗概。
(二)、“寧愿被打死也不愿被熏死”:新昌逾萬名農(nóng)民抗議藥廠污染環(huán)境
浙江京新藥業(yè)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浙江省新昌縣青山工業(yè)區(qū),是一家國家藥品GMP認證、ISO14001環(huán)境認證企業(yè),擁有博士后工作站的國家重點高新技術企業(yè)。京新藥業(yè)前身為浙江京新制藥廠,始建于1990年。京新藥業(yè)的半成品生產(chǎn)廠,位于浙江中部新昌縣和嵊州市交界處,工廠后方即是受污染的新昌江。嵊州市境內(nèi)的黃泥橋村距該廠最近處僅有幾十米。
據(jù)一位村民反映,化工廠成立已10年,建廠生產(chǎn)3個月之后,當?shù)卮迕癜l(fā)現(xiàn)井中的地下水已經(jīng)不能飲用。后來的幾年里,村民們陸續(xù)發(fā)現(xiàn)河里的魚、蝦、田螺、甚至連青蛙都絕跡了,田里的莊稼開始大幅度減產(chǎn),化工廠所排放出的氣體讓村民有一種“寧愿被打死也不愿被熏死”的感覺。村里的小伙子已經(jīng)有好幾年不能應征入伍了,原因是肝功能不達標。據(jù)反應,該村35至40歲的村民患肝病的人超過50%,而40至45歲以上的患肝病者高達60%。 2005年6月22日,京新廠發(fā)生爆炸,1死4傷。事故觸動了村民心中由來已久的恐慌和不滿。7月4日,黃泥橋村大約50名村民到京新藥廠反映污染問題,并要求廠家為村民進行體檢并賠償“營養(yǎng)費”。由于廠方領導一再推遲見面時間,村民情緒開始激動,并將接待室的玻璃門砸壞,由此引發(fā)村民與廠家的第一次沖突。
事件引起新昌縣和嵊州市兩地官員的重視,7月5日,在政府勸說溝通之后,化工廠于當晚緊急停產(chǎn),村民們也返回家中。但是這一事件又引發(fā)新昌江下游同樣遭污染侵害的嵊州村民的關注。化學廠緊急停產(chǎn)后,400多個反應爐中還存有1000噸化學物品,有關專家認為這些原料如不經(jīng)及時處理,容易引發(fā)燃燒和爆炸。于是政府同意工廠在7月15日8點開始用7天時間處理該批危險化學品。誤會廠方復工四方農(nóng)民圍廠。政府公告發(fā)出之后,村民卻以為是化工廠借口開工。7月15上午,數(shù)百名黃泥橋村的村民聚集在化工廠門前要求工廠立即停止生產(chǎn),并與保安以及前來維護治安的警察發(fā)生沖突。據(jù)稱,當天加上從四面涌來的圍觀群眾,化工廠門前大約有數(shù)千人。當晚,在當?shù)毓賳T勸說下,黃泥橋村的村民返回家中等待消息。不料,新昌江下游的村民們在得知7月15日發(fā)生的事情之后,決定聲援黃泥橋村。「事情越大越好,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引起政府重視。」這是當時村民們普遍的心態(tài)。 16日晚,由于當?shù)卮蠓秶k姡笩o事可做」的村民開始從四面八方涌來,警察在104國道和新昌高速公路口設置關卡,仍然無法阻止村民的腳步。警方在化工廠門前安放巨型水泥管道充當隔離墻,防止村民沖進廠區(qū)造成意外。雙方處于對峙狀態(tài),村民投擲石塊,但警方為防事態(tài)擴大沒有還擊。后來臺風襲來,暴雨驅(qū)散了人群,緩解了危機。接下來的幾天里,化工廠附近村民有過幾次小規(guī)模聚集,沒有造成沖突。至21日上午7點,化工廠完成處理危險化學品之后,廠外已經(jīng)沒有村民聚集,警察也已撤離。據(jù)官方提供的材料稱,整個事件中,警方表現(xiàn)克制,沒有造成人員死亡。
這就是新昌逾萬名農(nóng)民抗議藥廠污染環(huán)境之梗概。
三、價值、利益與環(huán)境污染事件:一種社會自力救濟的集體抗議
如何解讀浙江新昌、東陽兩地上萬名農(nóng)民抗議環(huán)境污染事件?筆者以為這是兩起以“不得已的暴力”進行抗議的社會自力救濟,而釀成暴力抗議的根源在于價值、利益之沖突,而公眾又沒有參與事關自己生存權的環(huán)境決策之機會。
(一)、以“不得已的暴力”[2]進行抗議的一種社會自力救濟
臺灣學者蕭新煌教授曾經(jīng)將環(huán)保運動分為兩種類型:污染驅(qū)動型與世界觀模式,前者是與環(huán)境惡化及被害者生存有著密切的關系,為特定的事件所激發(fā),后者是由對地球的健康和平衡的考慮而觸發(fā)的。[3] 轉(zhuǎn)型社會中的環(huán)境保護運動大多屬于污染驅(qū)動型,因為快速的工業(yè)化尤其化工行業(yè)的發(fā)展經(jīng)常導致環(huán)境污染事件并且危害受害者的健康與生存。尤其在發(fā)展初期,生存與減少貧窮要比環(huán)境保護更為重要,而且認為造成環(huán)境污染與惡化被認為一種必然的代價。“老百姓對于財富的渴求比對清潔環(huán)境的要求要強得多。不過,當環(huán)境污染影響到個人生計的時候,受到影響的人們會采取行動來要求解決問題”。[4] 根據(jù)蕭新煌教授的分類,發(fā)生于浙江東陽與新昌兩地的農(nóng)村的集體抗議行動均屬于污染驅(qū)動型。之所以會發(fā)生新昌事件,實際上與當?shù)剞r(nóng)民的健康與生存面臨嚴重的威脅有著直接的關聯(lián)。黃泥橋村年年沒有合格兵員,該村35至40歲的村民患肝病的人超過50%,而40至45歲以上的患肝病者高達60%;空氣水源無一幸免;再加上2005年6月22日京新廠發(fā)生1死4傷的爆炸事件,觸動了村民心中由來已久的恐慌和不滿。而素有“歌山畫水”的美譽東陽畫水鎮(zhèn)“山不再青,水不再美,農(nóng)田不可以耕種,莊稼無法良好生長”,生存狀況極其惡化。
這種污染驅(qū)動型的暴力抗議是一種社會自力救濟。中國各地農(nóng)村的集體性暴力抗議時有發(fā)生,這些抗議大多是一種社會自力救濟的行動,并且多數(shù)的“暴力”是“作為善良民眾不得已的出路”。他們之所以采取激烈的方式抗爭,是因為“先透過反映、陳情、請愿等合法手段,無奈中央與地方環(huán)保公權力不彰,使受害居民必須靠‘私力’救濟的舉動來達到權利救濟的目的。”[5] 正是在健康與生存面臨嚴重威脅的情況下發(fā)生了暴力抗議環(huán)境污染事件。東陽畫水鎮(zhèn)村民反映:“化工廠搬來后,我們多次到東陽市、金華市、浙江省的環(huán)保部門上訪,省環(huán)保局曾明確回答我們,其中幾家化工廠是不符合有關規(guī)定的。因為化工廠一直沒有停止生產(chǎn),我們還幾次去北京,向國家環(huán)保總局投訴,找北京的記者,但問題仍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而 “由于環(huán)境保護保護問題已經(jīng)成為政治正確的標簽,老百姓也懂得運用環(huán)境作為保護自己利益的理由和藉口”。[6] 這恐怕是老百姓普遍的心態(tài),正如新昌事件中黃尼村的村民所說,“事情越大越好,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引起政府重視。”
東陽、新昌農(nóng)民暴力抗議環(huán)境污染事件都屬于社會自力救濟,但還不能算是社會運動。自力救濟是基于自己或自己的群體或社區(qū)的權利或利益受到侵害,個人或結(jié)合其它受害者進行示威、游行等抗議的活動。“環(huán)境糾紛的自力解決,是指環(huán)境污染和破壞的受害者,在不能或無法通過正常的公力手段解決與加害人的環(huán)境糾紛時,為了保護其合法的環(huán)境權益,而自行對加害人及其設施造成適當損害的行為”[7],該行為通常稱為“環(huán)境保護自衛(wèi)權”。與社會運動不同的在于,自力救濟之動力不是來自于公正、社會正義,而是維護自我權益之需要。目前中國多數(shù)的環(huán)境抗爭事件還沒有發(fā)展到出于公正或社會正義之理念之地步,仍囿于自我權益維護之范圍。
(二)、集體抗議之根源:價值與利益之沖突
發(fā)生于浙江省的環(huán)境污染集體抗議事件并不只是一樁簡單的環(huán)境保護事件,而是一個環(huán)境政治的問題,凸現(xiàn)出價值、利益的結(jié)構(gòu)性之沖突。
最近幾十年,無論西方還是東方,發(fā)達國家還是發(fā)展中國家,環(huán)境問題成為政府、公眾與各類組織高度關注的議題,這表明了人們對環(huán)境價值重要性的認可。但是,圍繞發(fā)展與環(huán)境保護問題上依然有嚴重的分歧與沖突。“價值沖突是環(huán)境政治的核心”。[8] 東陽市與新昌縣兩起農(nóng)民暴力抗議環(huán)境污染之事件正好反映了地方政府、相關企業(yè)與農(nóng)民在價值與利益的沖突。價值沖突表現(xiàn)為政府的GDP至上與民眾的環(huán)境生存權之沖突、企業(yè)利益與民眾的環(huán)境生存權之沖突。
GDP至上是中國不少地方政府的最高價值。對于政績的追求,主要表現(xiàn)為對于經(jīng)濟增長率的追求。經(jīng)濟增長率的提高,則主要依據(jù)大規(guī)模的項目投資,大量的招商引資等。由于政績主要來自于能夠帶來短期效應的大規(guī)模投資與建設,許多長期性的公共問題例如環(huán)境保護與治理、公共衛(wèi)生一直被忽視。盡管人們在口頭上重視環(huán)境保護,但是無論政府、企業(yè)主還是老百姓都認為環(huán)境保護是一種只能在經(jīng)濟發(fā)展到一定水平后才能考慮與進行的。本文的浙江京新藥業(yè)股份有限公司建有國內(nèi)最大氟喹諾酮類藥物生產(chǎn)基地,擁有年產(chǎn)化學合成原料藥1200噸、制劑12億粒/片、輸液500萬瓶的生產(chǎn)能力,主導產(chǎn)品環(huán)丙沙星、左氟沙星全國產(chǎn)銷量第一。對于當?shù)氐腉DP和利稅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上,有關人員不得不承認“新昌制藥廠和新和成的效益的確是好。或許正是這個原因,才導致新昌縣政府很難在經(jīng)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之間做出抉擇。也是成為擺在當?shù)卣媲暗囊坏离y題。”這種以GDP為核心的發(fā)展觀帶來的是政府缺位。我們可以看出,包括生態(tài)破壞和環(huán)境污染在內(nèi)的諸多公共領域問題,主要肇因于政府職能的錯位,而這又來自以GDP為核心的發(fā)展觀。而利潤最大化則是企業(yè)的核心價值。不顧一切地追求利潤最大化往往以犧牲環(huán)境、損害公眾環(huán)境生存權為代價的。東陽的暴力沖突說明這一點:當?shù)卮迕裾J為,因化工企業(yè)的高額利潤、地方政府部門的利益,致使他們的生存權被漠視,話語權被剝奪。
而如果受害者所要求給予的補償不到滿足或多次要求不果的話,那么往往會催生或加劇暴力抗議。美國第一屆“全國有色人種環(huán)境領袖會議”(First National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ummit)在1991年十月草擬了一份《環(huán)境正義基本信條》,在十七個條文中其中包括“環(huán)境正義保障環(huán)境不正義的受害者收到完全的賠償,傷害的修繕以及好的醫(yī)療服務”。[9] 而從東陽、新昌兩事件中可以看出,受害的農(nóng)民多次要求補償未果,即便有了也是不完全的,與他們的要求相差甚遠。
問題的另一個方面還在于利益集團對環(huán)境決策與執(zhí)法的影響甚至掌控。不少地方政府出于本地經(jīng)濟發(fā)展的要求,環(huán)境污染源的地方政府很少會主動要求排污企業(yè)整改乃至關停,本文的兩個事例就是如此。地方政府對于環(huán)境保護政策未有嚴格的執(zhí)行與落實背后一個可能的原因在于“資本挾持環(huán)境治理”:出于發(fā)展地方經(jīng)濟計,各地方政府普遍采取以各種優(yōu)惠政策如稅收、工業(yè)用地的優(yōu)惠政策爭相引進外資或內(nèi)資,這樣一來投資者極有可能會以資本罷工(capital strike)為籌碼來抗拒,致使環(huán)境污染問題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因為企業(yè)外移會引起稅源流失與財政危機。臺灣學者湯京平教授曾經(jīng)研究過利益集體的結(jié)構(gòu)對于臺北市和高雄市環(huán)保官員執(zhí)法的影響:分別有高達79.6%和71.2 %的被訪臺北與高雄市環(huán)保官員表示(非常)同意“政府容易受企業(yè)利益的影響,在決策上不夠重視小市民的生活環(huán)境品質(zhì)”。[10]反映在環(huán)境執(zhí)法上,地方執(zhí)法者就極有可能直接感受到地方對于經(jīng)濟發(fā)展的需求而改變其執(zhí)法態(tài)度。[11] 盡管東陽政府有關官員否認政府與企業(yè)之間存在利益關系,但是還是承認“這些化工企業(yè)都是引進來的企業(yè),市領導重視招商引資,對這些企業(yè)都會表示關注”。面對如此嚴重的環(huán)境污染,東陽市畫水鎮(zhèn)一家公司的環(huán)保主管居然說,“我們也沒有環(huán)境污染問題,而且我們還是東陽市環(huán)保先進單位。在‘4 · 10 '事件中村民打著反對環(huán)境污染的旗號,我們不知道實質(zhì)原因是什么。”可見企業(yè)與政府有關部門的關系了。
本文兩個事件反映了以經(jīng)濟發(fā)展為中心的經(jīng)濟理性主義主導了整個政策思維過程,經(jīng)濟理性淹沒了環(huán)境價值。“山不再青,水不再美,農(nóng)田不可以耕種,莊稼無法良好生長”正是“GDP至上”的經(jīng)濟政策思維下的真實寫照。東陽、新昌等地的農(nóng)民正是這個不正義結(jié)構(gòu)下的受害者。自改革開放到二十一世紀初,中國一直是工業(yè)化帶來的“污染天堂”。寬松的環(huán)境法規(guī),廉價的勞工與土地成本,在經(jīng)濟理性的誘因下,許多高污染性的工業(yè)在中國尤其在浙江等沿海發(fā)展起來。然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們正不斷地在為此付出人命損失與環(huán)境的代價。“年年沒有合格兵員,空氣水源無一幸免”即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三)、公眾參與的缺失與環(huán)境之不正義
《環(huán)境與發(fā)展宣言》、《21 世紀議程》等一系列國際文件均規(guī)定了公眾參與制度。我國環(huán)境立法中對公眾參與制度有一些規(guī)定。例如,我國的《環(huán)境保護法》第六條規(guī)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huán)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huán)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 《國務院關于環(huán)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中規(guī)定:“建立公眾參與機制,發(fā)揮社會團體的作用,鼓勵公眾參與環(huán)境保護工作,檢舉和揭發(fā)各種違反環(huán)境保護法律法規(guī)的行為”。另外,《大氣污染防治法》、《海洋環(huán)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和《環(huán)境噪聲污染防治法》等環(huán)保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也作了相關規(guī)定。但是,“相關法律中的條款過于原則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公眾參與往往局限于環(huán)境損害之后的參與,形式單一。”[12]從參與的過程來看,主要側(cè)重于事后的監(jiān)督,事前的參與不夠。
公眾無權利或機會維護自己的環(huán)境生存權、參與環(huán)境保護與治理正好反映出了環(huán)境正義之缺失。環(huán)境正義之缺失有三種不正義:程序性不正義 (procedure inequity)、地理性不正義(geographical inequity)和社會性不正義 (social inequity)。[13] 從東陽、新昌兩個事件中人們不難看出地方政府與相關的企業(yè)的極端利已主義與不道德的非正義行為。東陽和新昌兩地的農(nóng)民正是這種不正義結(jié)構(gòu)下的受害者,他們的集體性暴力抗議正是對一系列違反環(huán)境正義行為的控訴。
四、走向商議-合作的環(huán)境治理模式:商議性民主與公眾參與環(huán)境保護
因生態(tài)環(huán)境日益遭受到破壞,中國面對著種種舊的、新的挑戰(zhàn)與難題,包括農(nóng)民的集體暴力抗議。究竟應該如何應對這些挑戰(zhàn)與難題?公眾對環(huán)境議題的意見該如何表達出來并被給予充分的考慮?怎樣將公眾參與納入環(huán)境保護之中,改變只有政府與專家參與環(huán)境政策、決策之局面?
(一)、轉(zhuǎn)向商議性民主
聯(lián)合國的“世界環(huán)境與發(fā)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于1987年所出版的《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一書,掀起了全球有關“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口號呼喊以及相關討論、研究與國際公約的簽訂。該書也從制度面提出了包括“一個確保公民有效參與決策的政治體系”在內(nèi)的人類社會應追求的基本主張。聯(lián)合國的《21世紀議程》第23章第2節(jié)明確提出,“要實現(xiàn)可持續(xù)的發(fā)展,基本的先決條件之一是公眾廣泛參與決策。此外,在環(huán)境和發(fā)展這個較為具體的領域,需要新的參與方式,包括個人、群組和組織需要參與環(huán)境影響評價程序以及了解和參與決策,特別是那些可能影響到他們生活和工作的社區(qū)的決策。”而《中國21世紀議程》第二十章的“導言”同樣指出,“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必須依靠公眾及社會團體的支持和參與。公眾、團體和組織的參與方式和參與程度,將決定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實現(xiàn)的進程。考慮到中國憲法和法律已經(jīng)對公眾參與國家事務所作的規(guī)定,并認識到公眾參與在環(huán)境和發(fā)展領域的特殊重要性,有必要為團體及公眾參與可持續(xù)發(fā)展制定全面系 統(tǒng)的目標、政策和行動方案。”
不少學者從社會學、政治學與法學角度論證了公眾參與環(huán)境保護的意義與可行性。問題在于公眾如何參與。公眾應該如何參與?現(xiàn)在的制度能不能滿足我們參與的需要?什么樣的制度設計可以保障我們在決策過程中的參與權與決定權?正是自由主義民主與電子民主等的內(nèi)在局限性,促使人們?nèi)ふ夜娪行У貐⑴c環(huán)境保護與治理過程之中的機制。在尋找與探討過程人們發(fā)現(xiàn)一種稱之為商議性的機制是一種可能的發(fā)展方向,可以為公眾參與環(huán)境保護提供理論之支持與諸種實踐方式。
在1970年代,以民主程序解決環(huán)境危機的主張,遭受許多的批判批評者許多環(huán)保運動者皆對自由民主制度(liberal democracy)感到失望。他們認為自由民主制度所強調(diào)的是對競爭性選舉、個人自由以及私有財產(chǎn)的重視。對于這些面向的重視,所制訂出的環(huán)境政策,是以短期的政治利益為考慮,有利于發(fā)展者的利益和資本的累積,但是卻以犧牲環(huán)境保護為代價因此,人們以為我們只能在兩個方案中做抉擇:任憑現(xiàn)存的經(jīng)濟行為繼續(xù)摧殘生態(tài)環(huán)境;或者我們必須放棄民主的形式,尋求一個具有生態(tài)理念的巨靈(Leviathan)。但是,1980年代以來,這種新霍布斯主義(New-Hobbesian)的主張,已不再受到重視,人們也不再對于尋求一個生態(tài)王(ecological king)報以期待。為了解決代議制度呈現(xiàn)的難題,許多學者強調(diào)可以利用新興電子媒體以及民意調(diào)查的影響力,作為人民表達意見的管道。可是,這種所謂電子民主(teledemocracy)的主張可能忽略環(huán)境議題的復雜性與專業(yè)性,而訂定出對環(huán)境生態(tài)不利的決定,因而迫使許多人對人民的決策能力感到質(zhì)疑,而寧愿將決策權交給了所謂的專家。[14]
事實上,有關商議性的機制是一種可能的發(fā)展方向,人們已經(jīng)從達爾、哈貝馬斯等人的有關理論論述中可以看出這一點。達爾認為,民主的政治過程應該是使所有要受某決策所影響的人能夠具有有效的機會來參與政治過程,并且有平等的權利選擇議題和控制議程;民主程序同時要求一種“開明的了解”(enlightened understanding):須讓公民有充分的信息和良好理性,對有爭議的利益或共同的事務,作出清晰的理解。[15] 哈貝馬斯指出,達爾所談的“開明的了解”這個要件,將民主指向于意志形成的信息和討論性質(zhì)(information and discursive character of will-formation);而充分信息的提供,公民了解事務的機會,以及公民的意志形成,則有賴于公共討論。[16]
(二)、商議性民主的核心觀念與特點
隨著國家的職能越來越復雜而政治之規(guī)模越來越大,而起源于19世紀的自由主義民主的制度及其技術官僚的行政體制似乎越來越不能適合新形勢下所面臨著的一些挑戰(zhàn)。例如,如何讓公民積極參與政治,通過對話取得共識,有效地設計與執(zhí)行公共政策,保證所有的公民都能享受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所帶來的好處。總的來說,傳統(tǒng)的選舉民主在“真正的民主治理”方面做得相當不夠的,在這種民主之中,公民是有權選擇他們的代理者,即政府官員或議員,但是很少能參與對這些代理者所做的選擇進行討論并加以理解。所以,吉登斯說,民主需要深化。現(xiàn)有公民與管理者生活在同樣的信息環(huán)境之下,舊的管理體制在這種社會不再效了;改變一下民主的程序,尤其有助于政治決策更接近選民的日常想法,而網(wǎng)上征求意見、電子投票不會取代原有的決策方式,但是都是很好的補充。[17] 而在哈貝馬斯那里,民主有兩種:制度化民主和商議民主,前者直接表現(xiàn)在議會活動、選舉活動、行政管理活動的制度中,而后者則表現(xiàn)在交往行動中,以一種意見和意志的形成過程發(fā)生著。哈貝馬斯的商議式的民主模式強調(diào)了兩個最為基本的信念。第一,政治決策最好是通過廣泛的商議來作出,而不是通過金錢和權力。第二,在商討過程中參與者應該盡可能平等而且盡可能廣泛。他的商議式民主是對當代民主政治的新詮釋。自由主義民主或選舉民主的缺失正是商議式民主的起點。當今流行于歐美的“商議性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是對自由主義民主或選舉民主的一種修正、一種發(fā)展。
“審議式民主并非天真地回歸直接民主的理想,它仍重視代議制度之下政治人物與公民的分工,但是特別強調(diào)人民必須有共同討論、理性說服的機會,以達成合理的政治判斷;同時要求政治人物必須對其政治決定負責。”[18]凡是涉及到重大的公共決策,在政策實施之前須由公民進行討論和爭辯,通過不同意見的對話,最后達成妥協(xié)和共識。審議式民主提倡理性的討論及相互尊重,即使最后討論的結(jié)果,并未達到共識。根據(jù)商議性民主的理論,一個更具有正當性和更受民眾信任的政府應該滿足兩個基本條件:包容性(inclusiveness)與不受約束的對話(unconstrained dialogue)。[19]
商議式民主具有以下的五個特點。(1) 大眾性。商議式民主旨在恢復公民文化,讓公民能真正參與決策過程。(2) 平等性。商議式民主理論家強調(diào)公民參與討論某一公共決策的權利和機會,強調(diào)參與對話者都擁有商議之能力。根據(jù)憲法,公民享有政治權利,這其中就有參與權,即公民有平等參與重大的公共事務決策的權利。(3) 多元性。民主政治過程實為參與各方的權力與利益達成妥協(xié)的過程。商議民主承認對話的參與者之間存在多元性,他們有不同的利益、信仰和理想,因而就需要通過對話以解決問題或作出決策,這就是商議機制。(4) 決策性。“民主決策”,將大眾引入到?jīng)Q策的過程之中,而這正是商議式民主所強調(diào)的。(5) 身份的不受限制與明確性。
(三)、商議性民主與公眾參與環(huán)境保護的聯(lián)結(jié)
最早且最知名的倡導將商議性民主引入到綠色政治(green politics)的學者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John Dryzek教授。[20] 他認為,比起其他的社會機制包括自由的民主制度來說商議性制度有可能在生態(tài)上更有理性化,在這種制度中人們有能力對與當代各種環(huán)境問題有關聯(lián)的高度復雜性、不確定性和集體行動作出反映。在Dryzek看來,政治機構(gòu)對于負面的反饋與協(xié)調(diào)之能力是生態(tài)理性化的一個必要條件。[21]從理論上看,民主的商議通過積極地加入許多的意見而改善信息的傳播。而商議性的制度安排也更有可能克服協(xié)調(diào)之問題。民主的商議有助于彼此承認和尊重,相互理解和對共善(the common good)的認同。價值多元性不能克服,但是商議性制度安排可以提供一種有效的框架,在這個框架中擴大了的精神能夠被培育。不斷的民主對話有助于對環(huán)境價值多元性的反映,可以提供觀點轉(zhuǎn)變之可能。民主商議可以為公民提供條件,在商議中公民接觸到有關生態(tài)的知識和價值并作出反映,并在他們的判斷和實踐中將這些知識和價值內(nèi)化。根據(jù)Amy Gutman 和 Dennes Thompson 倆人的分析,經(jīng)過商議過程所形成的決策,融入各方參與者的意見,雖未必一定產(chǎn)生正確的決策,但可以在參與者之間產(chǎn)生更多的政治支持、正當性與信任,可以加速未來政策的執(zhí)行,也為以后的合作互動積累長期的信任與社會資本;可以激發(fā)良好的意見表述,公正法律與制度及政治合法性,提升民主治理;因為互相認可,所以不僅是民主的決策程序,更具有豐富的實質(zhì)民主的涵義,可以避免暴力。[22]
對話、商議直接影響了公共行為,增加了公民對公共事務的發(fā)言權和影響力。既然參與了所在社區(qū)的公共事務的決策過程,那么,群眾就會希望他們自己的觀點與要求能夠被直接反映于最終所形成的決策之中。即便不能,但他們的意見與想法畢竟能夠公開地被討論或提出。商議式民主可以地方的治理方式,從而也有可能增強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通過商議與對話有助于重構(gòu)政府與農(nóng)民、企業(yè)與農(nóng)民的信任關系,有助于解決或緩和鄉(xiāng)村社會的各種矛盾。
新昌的暴力抗議環(huán)境污染事件之所以發(fā)生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溝通,造成當?shù)剞r(nóng)民對政府、企業(yè)的極度的不信任:政府同意工廠在2005年7月15日8點開始用7天時間處理該批危險化學品,但是,農(nóng)民誤會廠方復工從四方來圍廠。政府公告發(fā)出之后,村民卻以為是化工廠借口開工。這導致7月15上午,數(shù)千人村民聚集在化工廠門前要求工廠立即停止生產(chǎn),并與保安以及前來維護治安的警察發(fā)生沖突。農(nóng)民之所以誤會實在是他們對當?shù)卣突S的極不信任的必然結(jié)果。東陽的案例也有著同樣的邏輯。
新昌、東陽兩地的農(nóng)民抗議之事件表明,我們應該在公共政策之決議過程中,建立適當?shù)膶徸h機制,使得老百姓在作決定前對議題有深刻的了解同時使得各種不同的聲音皆能在決策過程中顯示出來。“協(xié)商最適合形成和檢驗法律、政治原則和公共政策的問題”。[23]
當然,也有一些學者批評商議性民主。例如,有學者認為,商議性民主之特點(主要指民主的正當性依賴于包容性和不受約束的對話,指向彼此之間的理解)難以說明制度安排的意義。再例如,商議性民主缺乏一種集體選擇的理論或一種決策規(guī)則。[24] 政治需要決策,而商議性民主理論卻很少討論實際的決策規(guī)則,這樣一來,商議性機制中的相互理解與決策效率之間存在著一種張力或沖突。[25]
不過,在中國目前的政治構(gòu)架下恰恰需要商議性安排,而不是決策之次序,現(xiàn)在問題的根本在于公眾沒有參加決策之機會。盡管決策并不能反映所有的觀點,但通過商議,可以使各方的觀點都有機會被考慮。民主的商議之培育可以提供一個導向性的框架,在這個框架下環(huán)境價值與觀點的多元性在政治過程中可以表達出來和給予考慮。它可以提供條件,在這個條件下環(huán)境價值之間的沖突得以諒解,可以尋找復雜環(huán)境問題的解決之道。
(四)、商議式民主與公共政策的新發(fā)展:參與決策過程是關鍵
中國環(huán)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其“環(huán)境保護與公眾參與”一文從五個方面提出了如何推進環(huán)保公眾參與:第一要轉(zhuǎn)變思想觀念;第二要環(huán)境信息公開化;第三是環(huán)境決策民主化;第四是環(huán)境公益訴訟;第五是加強與民間環(huán)保組織的關系。[26]但是,公眾要求保護自己的環(huán)境生存權,參與環(huán)境治理關鍵的是能夠參與決策過程。Goodin 曾經(jīng)在他的Green Political Theory一書中這樣說過,“提倡民主就是提倡程序,倡導環(huán)境保護主義就是倡導實質(zhì)性的結(jié)果:我們能以什么的保證前者的程序?qū)a(chǎn)生后面的結(jié)果?”[27] 而商議性機制改變了公共決策的發(fā)展方向。在西方國家、臺灣,公眾參與環(huán)境決策是近年來環(huán)境行動的主要訴求之一。
商議性民主的假定是,公民可以通過對話(discourse)決定他們追求什么樣的法律和決策,而對話的成員尊重對方,他們都擁有商議之能力。商議民主認為對話的參與者之間存在多元性:不同的利益、不同信仰與不同的理想,因而通過對話以解決問題或作出決策。商議式民主旨在恢復公民文化,提高公共話語在決策中的作用,產(chǎn)生公共的或政治壓力以解決有關問題。商議式民主重在議,在于行動過程本身。由于其本質(zhì)和特征,商議式民主模式就很快影響到公共政策的發(fā)展。公共政策科學向來以專家為導向的,也就是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專家們的事,因為政策的制定需要專門化的知識與能力,而這是一般民眾所不具備的。但是,1980年代以來,這種導向的公共政策科學有了新的變化,其表現(xiàn)是將公民引入到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這就是公共政策的商議式模式。[28]
政治不能狹窄化,只成為專家的計算,而排除公民的參與;政治不只有科學技術單一的標準,而是能容許民間社會多元聲音的對話;政治作為政策制度應該是開放的程序,能夠容納非官方的公共領域之參與。決策的民主就是各方的利益訴求通過公開的表達與和平的協(xié)商而達成共識;民主實現(xiàn)的關鍵是程序公正。
中國各地所進行的“招商引資”之類決策不能只是由懷有政績沖動、GDP至上的地方黨政官員說了算,而應由相應的商議性機構(gòu)認真主持環(huán)評聽證,讓受污染之害的老百姓有民主權利能夠同排污企業(yè)進行博弈,并且能夠得到政府機關與司法機構(gòu)的保護與支持。可是,在現(xiàn)有的程序下,民眾并無多少影響決策的機會。東陽市的例子表明,東陽市畫水鎮(zhèn)的村民無法通過正常的程序,參與當?shù)亻_發(fā)區(qū)有關化工企業(yè)落戶畫水的決策。承租方化工企業(yè)租用園區(qū)土地時,“協(xié)議簽字時,村委沒有與村民代表商議”。當?shù)剞r(nóng)民只能在最后得知政策的結(jié)果。因此,當民眾的意見并未反應在最后的決策結(jié)果時,體制外的暴力抗爭恐怕就在所難免了。
(五)、審議式民主的實踐與公眾參與環(huán)境保護的機制
近幾十年來,商議性民主理念已經(jīng)在西方發(fā)達國家發(fā)展的公眾政策中得到體現(xiàn)與落實。例如,當今美國的全民健康保險政策、福利政策、環(huán)保政策以及小區(qū)安全等公共政策體現(xiàn)了這一點。這些國家例如澳大利亞發(fā)展出不少有關公眾商議之實踐或方式。審議性的機制主要有公民會議(citizen conferences)、商議性民意調(diào)查(deliberative polls)、共識會談(consensus conferences)、聽證會(public hearings)、公民論壇(citizen forums)、調(diào)停(mediation)、創(chuàng)造權與全民公決(citizen initiative and referendum)、公民小組(citizen Panels)和公民顧問團(citizen’s juries)。本文對公民論壇、調(diào)停和全民公決這三種商議性的實踐/機制略作討論。
1、公民論壇
最近一些年來,在西方國家出現(xiàn)了一些創(chuàng)新性的像公民顧問團、公民會議或共識會議、商議性民意調(diào)查等民主實踐。這些屬于公民論壇的新的民主實踐,為公眾商議公共政策議題提供了空間。這些公民論壇通過隨機抽樣或別的方式將公民聚集起來討論公共議題,這些公民通過論壇可以獲得相關的信息或知識,可廣泛地聽取別人的觀點與看法。
當然,這三者也有所不同。例如,參與的人數(shù)不同。通常商議性民意調(diào)查人數(shù)多,而公民顧問團或共識會議參與的人數(shù)則相對要少得多。再比如,選擇的公民方式不同,商議性民意調(diào)查和公民顧問團是按照隨機抽樣選取的,而共識會議則主要根據(jù)社會-人口之標準進行的。此外,結(jié)果有所不同:公民會議或共識會議通過一段時間的商議后要達成一個集體性的決議,而商議性民意調(diào)查所得到的結(jié)果是公民個人觀點之記錄。[29]
公民顧問團 James 和 Blamey 詳細地討論了公民顧問團在澳大利亞公民參與環(huán)境治理如國家公園管理中的角色與作用。[30] 公民顧問團是集合一群隨機選出的公民針對某一特定的議題進行商議,在為期數(shù)日的一段時間里,向參與者提供與議題相關的資訊,并聽取來自證人或基于專業(yè)知識、或基于他們所代表的可能受影響的利益的選擇。在商議的過程中,由受過訓練的主持人來維持公正的進行,參與的成員有機會進行交叉檢視證詞。最后,審查委員會的參與者提出他們的推薦方案,委托單位(政府部門,地方管理當局或其他機關)被要求予以回應,或依據(jù)推薦方案采取行動,或說明不同意的理由。
公民會議或共識會議 “公民會議”或稱“共識會議”是一種創(chuàng)新性的公民參與模式,其目的在于建構(gòu)一個公共討論的場域,讓一般公民能夠了解政策議題,并在知情的條件下,經(jīng)過理性溝通而形成共同的意見。公民會議(citizen conference,或稱共識會議 consensus conference)是在1980年代中期起源于丹麥的公民參與模式。“它在代議民主和利益團體的運作體系,以及菁英/專業(yè)支配的治理模式之外,提供一個讓民眾能夠發(fā)聲的公共討論空間,使得專家知識與常民經(jīng)驗,以及不同的利益觀點和價值立場,能夠進行對話、溝通。”[31] 公民會議目前還只是一種創(chuàng)新性的公民參與模式,但逐漸受到重視,其原因在于它所蘊含的理念突顯了一些重要的民主價值:平等參與的權利;對理性、知情的公共討論及其教育效果的重視;對共善目標的強調(diào)。公民會議,從它另一個廣泛使用的名稱“共識會議”可以得知,非常強調(diào)從爭議中尋求共識。共識的達成,預設參與者有追求共善的傾向,以及偏好轉(zhuǎn)化的可能。透過公共討論的轉(zhuǎn)化過程,參與者調(diào)解彼此的差異和沖突,而尋求共同的價值與利益基礎。[32]
商議性民意調(diào)查 美國學者Fishkin是商議性民意調(diào)查的先驅(qū)者與主要實踐者。他的實驗的步驟如下:第一,在考慮性別、年齡、階級、城鄉(xiāng)、教育、地理位置、等各種變量下,進行隨機抽出樣本,并依樣本對此議題的意見先作初步調(diào)查;第二,將樣本集中幾天的時間。在這段時間中,每個人可以獲得與主題相關的各種問題以及信息;第三,在檢閱數(shù)據(jù)的過程中,參與者可以和專家以及持不同意見者進行面對面的溝通及質(zhì)問;第四、進行一場和專家學者面對面討論及辯論的公聽會,并經(jīng)由電視作現(xiàn)場立即轉(zhuǎn)播;第五,討論之后,立即對樣本作民意調(diào)查,并隨即公布會議前以及會議后,民意調(diào)查改變的結(jié)果。[33]
公民論壇可向決策者提供公民的意見或建議,彌補當代社會代議制民主的缺陷:公民的生活、經(jīng)驗和態(tài)度同以他們的名義下所作出的決策之間差距日趨擴大。此外,通過公民論壇,可以將公共決策的“是非題”轉(zhuǎn)變?yōu)椤斑x擇題”。而以往民眾只能就“同意”與“不同意”之間作抉擇,而無法在許多方案中作出選擇;在中國,更可能的情況是農(nóng)民只能選擇“同意”,或許連選擇“同意”之機會都沒有。不過,現(xiàn)在中國不少地方都在進行民主參與的實驗,積累了大量的好經(jīng)驗。例如,浙江溫嶺市等地出現(xiàn)“民主懇談會”、“民主理財日”、“民主議政日”、“社區(qū)事務民主聽證會”、“民主聽證會”、“民主議事會”和“民主評議村兩委成員”等形式的公民性的論壇。公眾應該有權利與機會、渠道就可能有關建設項目的立項選址的方案、企業(yè)的布局對周邊環(huán)境所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國家或地方政府對環(huán)境可能造成影響的決策進行討論,提出相關的建議。這不僅是公民環(huán)境權的要求,而且可推進公眾參與環(huán)境保護的主動性與責任心。
2、全民公決
公民投票將參與的層次拉高到“決策”本身。全民公決是全體人口直接對憲法的、法律的或政策議題進行投票。就范圍與廣度來說,全民公決原則上無什么界限,大可至國際,小可在一個社區(qū)進行,正如Saward所說,“全民公決的關鍵點在于不管其政治單位(地理上的跨度還是人口規(guī)模)大小它都可運用的”。[34] Budge和 Saward 特別倡導這種方式。Budge的推崇有兩個理由:一是在選舉政治中,因為兩次選舉的間隔期存在造成公眾幾乎不能對政府的政策施加影響;二是選民的偏好與政策沒什么關聯(lián)。[35] 在西方,綠黨就環(huán)境的全民公決取得一些成功,有經(jīng)驗研究表明就環(huán)境議題來說,公眾似乎要比政府立法者更負責任;即便不成功,通過全民公決將環(huán)境議題放到議事日程中可以比自由主義或代議民主方式更能迫使政府關注環(huán)境問題;而全民公決也有公民教育之功能,培育綠色公民性(green citizenship)之理念。不過,在Graham Smith看來,盡管全民公決應該運用到綠色政治與商議性民主之中,但實際上卻很少有討論。
當然,全民公決也存在一些缺陷。因政治、社會、階層等因素造成低參與率是一個問題。精英或某(些)利益集團左右或控制公決卻是另一個問題。就環(huán)境議題而言,參與公投的地區(qū)范圍是個問題。“因為環(huán)境問題具有跨界的特性,各項環(huán)保及生態(tài)保育政策,以行政界線作為決策的界線,并不盡合理”。直接民權與環(huán)境專業(yè)關系是另一個問題。例如有人作這樣的質(zhì)詢:“如果一項通過環(huán)境影響評估的開發(fā)計劃為人民所否決,固應聽從人民的決定;但若一項不能通過環(huán)境影響評估的開發(fā)計劃,欲挾公民投票的力量強行上馬,難道也要犧牲專業(yè)意見,犧牲環(huán)保質(zhì)量?”但是,從新昌、東陽的兩個案例來看,問題不在于直接民權與環(huán)境專業(yè)的關系,也不在環(huán)境的跨界特性,關鍵的是公眾有沒有、有多少公決權利的問題。
3、調(diào)停
調(diào)停是將有關團體聚集起來,解決沖突或問題,以便所涉到的各方都能滿意或者同意尋找進一步解決問題的方法或方式。在倡導者看來,調(diào)停是一個合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集體的考慮將壓過純粹個人的利益。在西方,最初的有關環(huán)境問題的調(diào)停主要集中于偶發(fā)的、地方性、有具體地點的爭論,后擴展到政府對話和規(guī)制性的談判(regulatory negotiation)領域。調(diào)停過程應該做到公正、包容性、開放性和耐心[36],只有這樣方能為環(huán)境保護與治理提供良好的氛圍。在新昌、東陽兩事件中,當?shù)卣皇钦f沒有做過調(diào)停,但是問題在于,一是缺乏公正、包容性、開放性和耐心,尤其公正、耐心不足,這從兩地動用軍警可以清楚地看出;二是當?shù)卣鹊經(jīng)_突發(fā)生后才進行溝通與調(diào)停,如2005年7月4日,黃泥橋村大約50名村民到新昌京新藥廠反映污染問題,并要求廠家為村民進行體檢并賠償“營養(yǎng)費”,但由于廠方領導一再推遲見面時間,村民情緒開始激動,并將接待室的玻璃門砸壞,由此引發(fā)村民與廠家的第一次沖突。當農(nóng)民與企業(yè)發(fā)生暴力沖突時新昌的當?shù)卣懦雒孢M行溝通與調(diào)停,暫時將問題壓下去。東陽地方政府在其沖突事件發(fā)生前,不僅沒有做有效的調(diào)停,相反向村民發(fā)出多次警告。
當然,有一些對于調(diào)停這個機制的批評。例如,有批評者認為,代表性和出席有問題。再例如,將參與各方的利益看作已定的和不可矯正的(incorrigible)。不過,對于中國的環(huán)境治理來說,重要的是公眾是否有參與調(diào)停之機會,調(diào)停者(主要是政府,因為在目前中國的環(huán)境保護與治理模式是政府主導型的)是否能夠做到公正的問題。
五、結(jié)語
發(fā)生于浙江省東陽市與新昌縣兩起農(nóng)民暴力抗議環(huán)境污染之事件不僅表明公共政策制定的缺陷:公眾參與的缺失,而且顯示出中國農(nóng)民暴力抗議環(huán)境污染已經(jīng)成為一個政治問題,一個環(huán)境政治問題。由此向我們提出,需要我們重新思考中國政府主導型的環(huán)境治理模式。正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所指出的,“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須適應全球化時代的新情況,而且權威,包括國家的合法性,必須在一種積極的基礎上得重構(gòu)”[37]。本文正是從商議性民主理論與實踐角度來探究環(huán)境保護、治理與公眾參與的關系,提出環(huán)境治理應該強化民主的協(xié)商(democratic deliberation),倡導“商議合作型環(huán)境治理”模式,從而最終走向生態(tài)民主化之路(toward ecological democratization)。
陳俊宏,“永續(xù)發(fā)展與民主政治:審議式民主理論初探”,(臺灣)《東吳政治學報》,1998年第9期,第85-122頁。
紀駿杰,“我們沒有共同的未來:西方主流‘環(huán)保’關懷的政治經(jīng)濟學”,《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998年第31期,第141-168頁。
李東興、田先紅,“我國公眾參與環(huán)境保護的現(xiàn)狀及其原因探析”,武漢:《湖北社會科學》,2003年第9期,第118-119頁。
茅建興,“浙農(nóng):寧打死 不熏死”, 《香港文匯報》,2005年7月29日。
潘岳:“環(huán)境保護與公眾參與”,北京:《理論前沿》,2004年第13期。
吳國剛,“環(huán)保自力救濟研究”,《科技與法律》,2004年第2期,第119-124頁。
鄭少華著:“環(huán)保自力救濟:臺灣民眾參與環(huán)保運動的途徑——臺灣法制發(fā)展的透視”,《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期。
Checkoway, Barry (1981), “The Politics of Public Hearing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17, 566-82.
Chen, Don-yun, Tong-yi Huang, and Hsiao Naiyi (2003), “The Management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aipei City Government’s Citizen Complaints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26, No.5, 525-547.
Crosby, Ned, Jenet M. Kelly, and Paul Schaefer (1986), “Citizens Panels: A New Approach to Citizen Particip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6, 525-547.
Dryzek, J.S. (2000)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yond: Liberals, Critics, and Contest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shkin, J.S. (1997)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Guess, M. George and Paul G. Farnham. (2000) Cases in Public Policy Analysis, chapter 7,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303-331
Lafferty, William and James Meadowcroft., eds. (1996) Democracy and Environment: Problems and Prospects, chapter 11,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4-212.
Smith, G. and Wales, C. (2000), “Citizens’ Juries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Vol. 48, No.1, 51-65.
Smith, Graham. (2003)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Environment,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Susskind, L. and Ozawa, C. (1985), “Mediating Public Disputes: Obstacles and Possibilitie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41, No.2, 145-59.
注釋:
[1] 以下所描述的兩個事件的資料主要來自于一位記者朋友所作的實地調(diào)查,以及《東方日報》、《東陽日報》、《鳳凰周刊》等報刊及《中國選舉與治理》等網(wǎng)站的資料。
[2] 有關集體暴力抗議事件,我們不時可以從政府的相關人員中聽到“有組織、有預謀”之說。事實上,根據(jù)有關的研究表明,以直接暴力出現(xiàn)的抗議往往與無組織性、“未經(jīng)馴化的群眾”相聯(lián)系的;相反,一旦組織化以后,往往會以策略代替盲動,并以理性化的抗爭形式出現(xiàn)。這一點應該引起我們政府有關領導的注意與反思。
[3] Hiso, Hsin-Huang Macheal (1999)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Taiwan”, in Yok-shiu Lee and Alvin Y.So. Eds. Asia’s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M.E.Sharpe, pp.31-54.
[4]童燕齊,“轉(zhuǎn)型社會中的環(huán)境保護運動: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比較研究”,文載于張茂桂、鄭永年主編的《兩岸社會運動分析》,(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2月版,第406頁。
[5] 蕭新煌:《七0年代反污染自立救濟的結(jié)構(gòu)與過程分析》,臺北:行政院環(huán)保署,1988年,第130頁。
[6] 童燕齊,“轉(zhuǎn)型社會中的環(huán)境保護運動: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比較研究”,文載于張茂桂、鄭永年主編的《兩岸社會運動分析》,(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2月版,第406頁。
[7] 王燦發(fā):《環(huán)境法學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59頁。
[8] Smith, Graham. (2003)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Environment,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p.1.
[9] 轉(zhuǎn)引于紀駿杰的“環(huán)境正義:環(huán)境社會學的規(guī)范關懷”(1996年11月),文章來自于《http://wildmic.npust.edu.tw/sasala/new_page_7.htm》(2005-10-5上網(wǎng))。
[10]湯京平.環(huán)境保護與地方政治:北高兩市環(huán)保官員對于影響執(zhí)法因素的認知調(diào)查[J].臺北:臺灣政治學刊 (No.6,2002/12),第155頁。
[11]湯京平.環(huán)境保護與地方政治:北高兩市環(huán)保官員對于影響執(zhí)法因素的認知調(diào)查[J].臺北:臺灣政治學刊 (No.6,2002/12),第151頁。
[12] 吳國剛,“環(huán)保自力救濟研究”,科技與法律,2004年第2期,第122頁。
[13] 有關西方國家的環(huán)境正義問題可以參閱文同愛的“美國環(huán)境正義概念探析”,《http://www.riel.whu.edu.cn/show.asp?ID=640》(2005-10-5,上網(wǎng))。
[14] 有關內(nèi)容可參閱陳俊宏的“永續(xù)發(fā)展與民主政治:審議式民主理論初探”,文章載于(臺灣)東吳政治學報,1998年,第9期。
[15] Dahl, Robert.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108-110.
[16] Habermas, Jurgen. (1996) Between Fact and Norms: Contribution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316.
[17]吉登斯:《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70-72頁。
[18]陳俊宏,“永續(xù)發(fā)展與民主政治:審議式民主理論初探”,文章載于(臺灣)東吳政治學報,1998年,第9期。
[19] 請參閱Smith, Graham. (2003)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Environment,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pp.56-58.
[20] Smith, Graham. (2003)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Environment,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p.61.
[21] Dryzek, J.S. (1987) Rational Ecology: Environmen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Blackwell, p.54.
[22] Gutman, Amy and Dennes Thompson. (2002)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yond Proces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10, Issue.2, pp.153-174.
[23] 梅維﹒庫克,“協(xié)商民主的五個觀點”,文載于陳家剛選編的《協(xié)商民主》,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4年7月版,第44頁。
[24] Manin, B. (1997) 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89.
[25] Chambers, S. (1995) “Discourse and Democratic Practices”, in White, 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berm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41.
[26] 潘岳,“環(huán)境保護與公眾參與”,《人民日報》,2004年7月15日,第九版。
[27] Goodin, R.E. (1992) Green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168.
[28] 請參見Simon Chambers的“Deliberative Democratic Theory” ,文載于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03年卷,第307-326頁。
[29] Smith, Graham. (2003)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Environment,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p.87.
[30] James, Rosemary F. and Russell K Blamey. (1999)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Rhetoric to Real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ociety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Brisbane, Australia, 7-10 July 1999.
[31] 林國明、陳東升,“公民會議與審議民主:全民保健的公民參與”,臺灣社會學,2003年第六期,第76-77頁。
[32] 有關“公民會議”的意義與做法,請參閱林國明、陳東升的“公民會議與審議民主:全民保健的公民參與”,臺灣社會學,2003年第六期,第71-80頁。
[33] Fishkin, James. (1995) The Voice of People: Public Opinion and Democracy,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177-181.
[34] Saward, M. (1998) Term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83.
[35] Budge, I. (1996) The New Challenge of Direct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15.
[36] Dukes, E.F. (1996) Resolving Public Conflic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176.
[37] 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鄭戈譯,三聯(lián)書店,2000,第76頁。


代藥物與臨床.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