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yè)社會(huì)成本分析
佚名
本文試圖回答的是:為什么國有在推行市場化體制改革和生產(chǎn)率有所提高的情況下,主要效益指標(biāo)卻在惡化,從而出現(xiàn) " 有增長而無 " 的困境。文章認(rèn)為,國有工業(yè)企業(yè)長期以來過高的成本是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根據(jù)問卷調(diào)查的材料,作者對(duì)國有工業(yè)企業(yè)在固定資產(chǎn)投入、人員使用、福利保險(xiǎn)費(fèi)用等方面的社會(huì)成本進(jìn)行了定量的測算,其結(jié)果比以往的估算要高得多。文章從社會(huì)學(xué)的視角指出,圍繞著社會(huì)成本,國有工業(yè)企業(yè)形成了剛性的利益格局和福利功能擴(kuò)大化的趨勢(shì),從而成為改革的巨大障礙。要解決這個(gè)問題,就必須建立國有企業(yè)的 " 擬市場化核算體制 " 和 " 社會(huì)成本的分?jǐn)倷C(jī)制 " 。
在對(duì)國有企業(yè)的歷時(shí)性考察中,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這樣一個(gè)令人困惑的現(xiàn)象:自 1978 年以來,國有企業(yè)實(shí)行了一系列效率優(yōu)先的市場化體制改革,很多表明 , 這些改革措施使國有企業(yè)的 " 全要素生產(chǎn)率 " 得到提高(劉國光主編, 1988 ;董輔等主編, 1995 );但與此同時(shí),國有企業(yè)的總體財(cái)務(wù)經(jīng)營業(yè)績并沒有得到明顯改善,國有工業(yè)企業(yè)的主要效益指標(biāo) ( 如產(chǎn)值利稅率、銷售收入利稅率、資金利稅率 ) 幾乎直線下降,從 1996 年開始,甚至連續(xù)兩年出現(xiàn)全部國有工業(yè)企業(yè)巨額凈虧損的局面 ( 國家統(tǒng)計(jì)局 ,1998) 。國有企業(yè)為什么會(huì)在 " 全要素生產(chǎn)率 " 得到提高的情況下出現(xiàn)虧損?林毅夫等人認(rèn)為,國有企業(yè)的政策性負(fù)擔(dān)成為其預(yù)算軟約束的借口,從而使對(duì)它的經(jīng)營評(píng)價(jià)缺乏所必需的充分信息,這樣也就難以建立公平和充分競爭的市場環(huán)境,而這些是做出任何產(chǎn)權(quán)安排和形成適宜的治理結(jié)構(gòu)的前提條件(林毅夫、蔡、李周, 1997 : 97 );肖耿通過統(tǒng)計(jì)測算指出,由于國有企業(yè)的附加福利或額外收益未被視為財(cái)產(chǎn),其生產(chǎn)力可能被低估,但造成國有企業(yè)低效率的,不是附加福利,而是產(chǎn)權(quán)殘缺造成的資源配置扭曲(肖耿, 1997 : 131-182 );樊綱則提出了工資侵蝕利潤的假說(樊綱, 1995 : 48 )。然而,國有企業(yè)為承擔(dān)社會(huì)責(zé)任所付出的社會(huì)成本究竟在其總成本中占多大的比重?社會(huì)成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沖銷了企業(yè)利潤?社會(huì)成本是否是國有企業(yè)虧損的根本原因?這方面還缺乏詳細(xì)的定量研究,而這正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本文所依據(jù)的資料,是我們 1996 年 8-10 月份對(duì)全國 10 個(gè)大城市(哈爾濱、沈陽、濟(jì)南、上海、武漢、南京、廣州、成都、西安、蘭州)工業(yè)企業(yè)的問卷調(diào)查,調(diào)查根據(jù)行業(yè)、規(guī)模等結(jié)構(gòu)采取主觀抽樣,共獲得有效樣本 508 個(gè);調(diào)查對(duì)象主要是國有企業(yè),占總樣本的 70.5% ;為便于比較各類型企業(yè)的差別,我們使樣本主要集中在工業(yè)制造業(yè),其占總樣本的 96.3% ;問卷調(diào)查項(xiàng)目是企業(yè)的客觀指標(biāo),主要涉及企業(yè)的財(cái)務(wù)和人事方面。
一、社會(huì)成本的界定及其假說
的國有企業(yè)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 " 單位組織 " 。單位組織是一種特殊的組織形態(tài)(李漢林等, 1988 : 273-373 ;路風(fēng), 1989 ;李培林等, 1992 : 178-202 ;李路路、王奮宇, 1992 : 83-103 ),作為單位組織的中國國有企業(yè)不但承擔(dān)經(jīng)濟(jì)功能,也承擔(dān)社會(huì)和功能。國有企業(yè)為實(shí)現(xiàn)其非經(jīng)濟(jì)功能所付出的成本,我們稱之為社會(huì)成本。這是對(duì)于社會(huì)成本概念的一種比較狹窄的定義,與已有經(jīng)濟(jì)文獻(xiàn)中的其他定義有所不同。
早在 1960 年,科斯就寫了著名的《社會(huì)成本問題》一文,他的社會(huì)成本概念的重要意義在于揭示 " 交易成本 " 的存在。在他那里,社會(huì)成本就是私人成本加上交易成本,在完全競爭的情況下,私人成本會(huì)等于社會(huì)成本,但沒有交易成本的世界不是真實(shí)的世界(科斯, 1988/1995:20-25 )。科爾內(nèi)則從整個(gè)國民經(jīng)濟(jì)出發(fā),把社會(huì)成本定義為 " 一切涉及社會(huì)個(gè)別成員和集團(tuán)的負(fù)擔(dān)、損失、痛苦、犧牲或辛苦的現(xiàn)象 " 。這些現(xiàn)象一部分可以用貨幣來度量,但也有一部分涉及心理的感受,是無法用貨幣來度量的。他認(rèn)為對(duì)社會(huì)成本的考察可以從 4 個(gè)方面進(jìn)行:( 1 )生產(chǎn)的內(nèi)部實(shí)物投入,即生產(chǎn)成本;( 2 )外部成本,它并不直接以貨幣的形式反映在企業(yè)或非營利機(jī)構(gòu)的賬目上,如隨著生產(chǎn)能力利用的提高,事故可能增加,工人健康可能惡化,對(duì)環(huán)境的破壞可能加劇等等,為防止這種狀況對(duì)生產(chǎn)的,要有一些 " 預(yù)防性 " 開支,這就是外部成本的內(nèi)部化;( 3 )社會(huì)的分?jǐn)偝杀荆缯畽C(jī)構(gòu)的經(jīng)費(fèi)支出;( 4 )反映大量經(jīng)濟(jì)現(xiàn)象的人們的意向、滿意度和普遍感覺,一種是邊際遞減的社會(huì)成本,如與生產(chǎn)能力利用低水平相關(guān)的失業(yè)以及可能伴隨的犯罪、暴力和自殺,另一種是邊際遞增的社會(huì)成本,如與生產(chǎn)能力高利用度相聯(lián)系的其他領(lǐng)域的 " 瓶頸 " 、 " 短缺 " 以及對(duì)社會(huì)消費(fèi)的負(fù)面影響,前面所說的生產(chǎn)成本、外部成本和社會(huì)分?jǐn)偝杀荆捕际沁呺H遞增的社會(huì)成本。科爾內(nèi)所要說明的是, " 不應(yīng)該總是不惜一切代價(jià)去達(dá)到社會(huì)生產(chǎn)能力的最大利用。如果當(dāng)趨近于生產(chǎn)能力完全利用時(shí),邊際社會(huì)成本已經(jīng)超過邊際社會(huì)效益,達(dá)到這一點(diǎn)就是不值得。 " (科爾內(nèi), 1980/1986 :上卷 273-302 )
社會(huì)成本的告訴我們,社會(huì)成本的準(zhǔn)確測度是很困難的,但這種探索問題的卻是非常有啟發(fā)性的。我們可以設(shè)想,擁有同樣的技術(shù)并生產(chǎn)同樣產(chǎn)品的兩個(gè)不同的企業(yè),其生產(chǎn)成本應(yīng)該是一個(gè)給定的數(shù),而在現(xiàn)實(shí)中這兩個(gè)企業(yè)的成本又可能有很大差異,這就是社會(huì)成本的差異。正是社會(huì)成本的差異決定了競爭力的差別。不同的企業(yè)處于不同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之中,因?yàn)檫@種不同,它們所承擔(dān)的義務(wù)、責(zé)任和負(fù)擔(dān)也不同,付出的社會(huì)成本就有很大差別。盡管社會(huì)成本的可能是比較困難的,但卻是非常有意義的。
在本文中,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們把國有企業(yè)福利供給的成本作為其社會(huì)成本的操作性定義。這種福利供給被區(qū)別為潛在福利和顯性福利。潛在福利指國有企業(yè)用于興辦集體福利的福利費(fèi)用,如圖書館、俱樂部、操場、游泳池、療養(yǎng)院、澡堂、、電影院、草坪、社區(qū)綠化、企業(yè)所屬的各種學(xué)校等。顯性福利指國有企業(yè)主要以貨幣或?qū)嵨锏姆绞街苯又Ц督o職工個(gè)人,用于滿足個(gè)人福利需求的福利費(fèi)用,如過節(jié)費(fèi)、計(jì)劃生育補(bǔ)貼、奶費(fèi)、托兒補(bǔ)貼費(fèi)、冬季取暖補(bǔ)貼、上下班補(bǔ)貼、上下班班車支出、職工探親旅費(fèi)、衛(wèi)生洗理費(fèi)、住房等。
改革以來,國有企業(yè)在市場化轉(zhuǎn)型過程中向相對(duì)獨(dú)立的經(jīng)濟(jì)組織的轉(zhuǎn)化,使其自行配置社會(huì)資源的能力加強(qiáng)了,但其單位組織的性質(zhì)非但沒有改變,反而更加強(qiáng)化;其福利供給的功能非但沒有縮小,反而更加擴(kuò)張。這主要導(dǎo)源于:
第一,在市場化過程中,作為有限理性經(jīng)濟(jì)人的國有企業(yè),會(huì)力圖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其在既定的、被制度化了的利益結(jié)構(gòu)中所應(yīng)體現(xiàn)的收益,主要表現(xiàn)為: (1) 國家的利潤與稅收收益, (2) 企業(yè)本身的收益, (3) 國有企業(yè)經(jīng)營者的收益, (4) 國有企業(yè)職工的收益, (5) 國有企業(yè)所辦集體企業(yè)的收益, (6) 社會(huì)的收益。在這里,如果不計(jì)國家收益與社會(huì)收益的細(xì)微區(qū)別,那么,可以認(rèn)定,國家利益與社會(huì)利益是一致的。這樣,國有企業(yè)的運(yùn)行邏輯就遠(yuǎn)比非國有企業(yè)復(fù)雜得多,因?yàn)橛袝r(shí)它得體現(xiàn)某些公共收益而不只是私人收益〖注:在新經(jīng)濟(jì)史學(xué)研究中做出過特殊貢獻(xiàn)的諾斯( North , DouglassC. )教授,在與托馬斯 (Thoumas,R.P.) 合著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在區(qū)別私人收益率與社會(huì)收益率時(shí),認(rèn)為私人收益率是經(jīng)濟(jì)單位從事一種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所獲得的凈收益;社會(huì)收益率是社會(huì)從這一活動(dòng)獲得的總凈收益(正的或負(fù)的),它等于私人凈收益加這一活動(dòng)使社會(huì)其他每個(gè)人所獲得的凈收益(諾斯、托馬斯, 1973/1989 : 1 )。諾斯和托馬斯是把某一具體經(jīng)濟(jì)實(shí)體所造成的私人收益加上其為其他社會(huì)活動(dòng)單位所造成的收益之和作為社會(huì)總收益來看待的。諾斯和托馬斯的這一概念能夠給我們以有益的啟示:它能使我們考慮到企業(yè)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或非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所產(chǎn)生的外部性問題,也能夠借此考慮到將外部性問題內(nèi)部化之后的成本支出問題。也就是說,倘若將社會(huì)收益的 " 一部分 " 當(dāng)做國有企業(yè)的成本支出,那么,這部分社會(huì)收益的多少,便取決于國有企業(yè)在我們所說的社會(huì)成本方面支出的多少。〗。在市場經(jīng)濟(jì)的邏輯理路之中,對(duì)于企業(yè)內(nèi)部職工來說,私人收益的獲得,可能是眼下最重要的預(yù)期利益獲得,這就與國有企業(yè)的整體運(yùn)行邏輯相矛盾。僅僅靠道德規(guī)范來保證企業(yè)經(jīng)營者與所有者利益的一致,或者企業(yè)職工利益與整個(gè)國家利益的一致,在現(xiàn)實(shí)中是比較困難的。改革所提供的失范機(jī)會(huì),為企業(yè)經(jīng)營者實(shí)現(xiàn)自己的利益制造了難得的運(yùn)作空間。對(duì)于國家來說,企業(yè)利潤率的上升與稅金的如期繳納,可能是最好的選擇;對(duì)于國有企業(yè)自身來說,能夠?qū)⒂邢薜匿N售收入轉(zhuǎn)化為顯性福利或潛在福利支出,就可以使企業(yè)內(nèi)部職工的貨幣收益或非貨幣收益最大化;另外,國有企業(yè)還得顧及其內(nèi)部所辦集體企業(yè)職工的生活問題,否則,來自企業(yè)內(nèi)部的壓力集團(tuán)會(huì)施加無形的影響;盡管國有企業(yè)要步入市場或已經(jīng)頑強(qiáng)地步入市場,但其與社區(qū)之間的那種命運(yùn)共同體結(jié)構(gòu),也使其不得不關(guān)注某些社會(huì)問題(如職工家屬的就業(yè)等)。
所以,在國有企業(yè)所面臨的這一制度化利益結(jié)構(gòu)中,能夠促使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最好選擇,就是將國有企業(yè)利潤的一部分以企業(yè)社會(huì)成本的形式轉(zhuǎn)化為企業(yè)內(nèi)部的福利,這既符合企業(yè)內(nèi)部職工的福利需求,也有利于企業(yè)穩(wěn)定和國有企業(yè)領(lǐng)導(dǎo)層的 " 合理消費(fèi) " 。雖然顯性福利不計(jì)算為財(cái)產(chǎn),但卻屬于企業(yè)產(chǎn)出的一部分,而潛在福利雖然作為國有企業(yè)所屬的資產(chǎn)進(jìn)行統(tǒng)計(jì),但其在使用權(quán)與剩余索取權(quán)上,卻有著不同于其他國有資產(chǎn)的界限。
第二,國有的 " 福利功能內(nèi)卷化 " 趨向,與其面對(duì)的市場結(jié)構(gòu)密切相關(guān)。就市場而言,是否存在某種既定的為國有企業(yè)所需求的福利產(chǎn)品及可替代產(chǎn)品,是國有企業(yè)保持專門化的前提;就企業(yè)而言,即使市場上存在為國有企業(yè)所需的福利產(chǎn)品或服務(wù),但倘若這種產(chǎn)品或服務(wù)的交換價(jià)格高于國有企業(yè)內(nèi)部生產(chǎn)這種產(chǎn)品或服務(wù)的成本,那么,企業(yè)就不會(huì)從市場交換這種功能需求。一般而言,導(dǎo)致交易成本過高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市場的不確定性和供給某種商品的企業(yè)數(shù)量;其二,人們?cè)跊Q策過程中的有限理性和機(jī)會(huì)主義。市場的不確定性是由處于競爭狀態(tài)的、能夠供給某種商品的企業(yè)數(shù)量及其生產(chǎn)能力所決定的。一旦不確定性與有限理性結(jié)合在一起,就會(huì)出現(xiàn)交易成本趨升的。在這種情況下,企業(yè)對(duì)市場供給的某種福利商品,就可能采取內(nèi)部化的方式,即使通過市場購買有助于節(jié)約成本,企業(yè)也可能產(chǎn)生內(nèi)部化的沖動(dòng)。導(dǎo)致企業(yè)將商品需求供給內(nèi)部化的另外一個(gè)原因是缺少市場供給。如果市場上缺失為企業(yè)所需的 " 福利功能 " 供給,而企業(yè)又迫切需要該 " 福利功能 " ,那么,它便只好通過自己生產(chǎn)來滿足這種需求,否則,就只能尋求其他替代品。在這種情況下,職工所消費(fèi)的各種福利,就較供給的服務(wù) " 便宜 " 得多。正因?yàn)檫@樣,表面看起來,每一個(gè)國有企業(yè)為其內(nèi)部職工所支付的貨幣工資數(shù)額比較少,大都低于中外合資合作企業(yè)和一部分私有企業(yè),但其為職工所支付的福利費(fèi)用 -- 潛在福利和顯性福利之和,卻是非常可觀的。改革開放以來,如果說顯性福利的發(fā)放與企業(yè)效益高低有著某種一致性的話,那么,其潛在福利的增加和施惠于內(nèi)部職工的數(shù)量多少,卻與國有企業(yè)的效益并不直接相關(guān)。也就是說,國有企業(yè)的效益并不必然地決定其潛在福利的增加與否。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國有單位的福利保險(xiǎn)費(fèi)用才逐年上升。 1978-1997 年,國有經(jīng)濟(jì)單位的保險(xiǎn)福利費(fèi)用總額從 69.1 億元增加到 2578.8 億元,相當(dāng)于國有經(jīng)濟(jì)單位工資總額的比例從 13.7% 上升到 30.4% (國家統(tǒng)計(jì)局, 1998 : 795 )。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國有企業(yè)收益,會(huì)首先表現(xiàn)為國有企業(yè)內(nèi)部職工的收益。利潤,不管用于納稅還是用于 " 向投資者分配 " ,都會(huì)企業(yè)職工的最終收益。只有擴(kuò)大成本的開支,將成本的一部分轉(zhuǎn)化為企業(yè)內(nèi)部的集體物品〖注:這里以 " 集體物品 " 指稱能夠?yàn)槠髽I(yè)內(nèi)部職工直接消費(fèi)的物品,以 " 公共物品 " 指稱用于國有企業(yè)的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的物品。集體物品與公共物品之間是有著區(qū)別的。像住房等福利設(shè)施就屬于集體物品,雖然其在出售給職工個(gè)人之前,仍然屬于國有企業(yè)所有,但卻不可能被某一具體國有企業(yè)之外的人員所享用。而機(jī)器、廠房等設(shè)施則屬于公共物品,如果不經(jīng)過生產(chǎn)過程的轉(zhuǎn)化就不可能被國有企業(yè)內(nèi)部職工所消費(fèi)。〗,或者將利潤的一部分轉(zhuǎn)化為直接可以被職工所消費(fèi)的顯性福利,企業(yè)的生產(chǎn)活動(dòng)才可能更多地為企業(yè)內(nèi)部職工帶來好處。即使在國有企業(yè)不盈利時(shí),其內(nèi)部潛在福利的開支也存在增長的沖動(dòng)。這就是說,虧損并不必然地抑制福利機(jī)構(gòu)和福利設(shè)施的興建,而這些因素卻直接增加著人工成本的開支總額,并進(jìn)而 " 制造 " 著虧損。
二、國有企業(yè)支付著較高的社會(huì)成本
總體上說,與非國有企業(yè)相比較,國有企業(yè)支付著更高的社會(huì)成本。下面我們從固定資產(chǎn)、人員構(gòu)成和保險(xiǎn)福利費(fèi)用幾個(gè)方面來考察一下國有企業(yè)的社會(huì)成本。
1. 社會(huì)成本在固定資產(chǎn)上的表現(xiàn)
國有企業(yè)社會(huì)成本在潛在福利方面的耗費(fèi)額是十分可觀的。如、學(xué)校、托兒所、食堂等,得首先具備一定的硬件設(shè)備,才能維持起碼的福利施惠。在國有企業(yè)以單位化方式存在的前提下, " 生活 " 設(shè)施 -- 尤其是與生活?yuàn)蕵吩O(shè)施有關(guān)的固定資產(chǎn)的投資,就不可避免。這樣,在國有企業(yè)的固定資產(chǎn)總額中,非生產(chǎn)用固定資產(chǎn)就成為一個(gè)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根據(jù)我們的調(diào)查,到 1995 年為止,國有企業(yè)與國家控股企業(yè)的非生產(chǎn)用固定資產(chǎn),已經(jīng)在固定資產(chǎn)總額之中占居了相當(dāng)大的比重。
從表 1 可以看出,在不同類型的企業(yè)中,國有企業(yè)與國家控股企業(yè),其生產(chǎn)用固定資產(chǎn)所占的份額是最少的,前者占 77.89 %,后者占 71.65 %。而集體企業(yè)、私有企業(yè)與中外合資合作企業(yè)生產(chǎn)用固定資產(chǎn)都在 90 %以上,其中私有企業(yè)所占比重為 94.18 % -- 是這方面比例最高的。相應(yīng)地,國有企業(yè)與國家控股企業(yè)非生產(chǎn)用固定資產(chǎn)的比重就顯得較大,國有企業(yè)為 22.11 %,國家控股企業(yè)為 28.35 %,其中社會(huì)性固定資產(chǎn)在國有企業(yè)與國家控股企業(yè)之中,也占居了相當(dāng)高的比重。前者所占總額的比重為 9.92 %,后者竟達(dá) 13.38 %。可是,私有企業(yè)在這方面的投資為 0 ,集體企業(yè)也僅僅為 2.37 %,中外合資合作企業(yè)為 0.15 %。
〖注:各項(xiàng)數(shù)據(jù)均以 1995 年年末數(shù)計(jì)。在這里, " 辦公用 " 固定資產(chǎn)指企業(yè)總部辦公用的建筑物、運(yùn)輸工具、通訊工具、辦公設(shè)備等。 " 社會(huì)性 " 固定資產(chǎn)指某些由企業(yè)建設(shè)和購置的潛在福利性固定資產(chǎn),包括企業(yè)辦的大中專院校、技工學(xué)校、中小學(xué)、商店、糧店、郵局、派出所等使用的固定資產(chǎn)。資料來源: 508 家企業(yè)調(diào)查。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國有企業(yè)仍然繼續(xù)承擔(dān)著社會(huì)功能,所以,在新增固定資產(chǎn)里,其投資于 " 生產(chǎn)用固定資產(chǎn) " 的數(shù)額也并不高。在 1995 年,調(diào)查樣本家控股企業(yè) " 生產(chǎn)用固定資產(chǎn) " 為 79.02 %,國有企業(yè) " 生產(chǎn)用固定資產(chǎn) " 為 85.85 %。雖然中外合資合作企業(yè)與私有企業(yè)的非生產(chǎn)用固定資產(chǎn)所占居的比重都不小,分別占居了新增固定資產(chǎn)總額的 12.87 %和 18.03 %,但集體企業(yè)、私有企業(yè)和中外合資合作企業(yè)在社會(huì)性固定資產(chǎn)方面,卻都為 0 。
2. 社會(huì)成本在組織機(jī)構(gòu)及其工作人員上的表現(xiàn)
我們知道,潛在福利是以集體物品(即在使用權(quán)上可以被該國有企業(yè)內(nèi)部所有成員在制度內(nèi)享用的物品)的方式累積于企業(yè)之中的。為了使這部分集體物品得到有效的管理,國有企業(yè)就得在內(nèi)部組織機(jī)構(gòu)的設(shè)置上,以專門化的功能單位去維護(hù)和支配這部分資產(chǎn),并隨時(shí)處理與該資產(chǎn)有關(guān)的各種事務(wù)。這樣,在國有企業(yè)內(nèi)部,社會(huì)性組織機(jī)構(gòu)的建立就不可避免,而組織機(jī)構(gòu)在企業(yè)科層制之中,卻要依靠工作人員去填充。這樣,國有企業(yè)不僅在固定資產(chǎn)的設(shè)置上要增加企業(yè)的生產(chǎn)成本,而且在企業(yè)內(nèi)部職工的配置上要擴(kuò)大可變資本的開支。于是,非生產(chǎn)人員中服務(wù)人員的數(shù)量就理所當(dāng)然地增加了。
〖注:各項(xiàng)數(shù)據(jù)均以 1995 年年末數(shù)計(jì)。在這里,各類服務(wù)人員不包括政工、黨務(wù)、團(tuán)務(wù)以及工會(huì)與婦聯(lián)等管理工作人員。 " 社會(huì)性服務(wù)人員 " 指既為本企業(yè)職工服務(wù),也為社會(huì)服務(wù)的工作人員,如在國有企業(yè)興辦的學(xué)校與醫(yī)院中工作的人員。 " 福利機(jī)構(gòu)人員 " 指為本企業(yè)職工福利服務(wù)的工作人員。由于在調(diào)查樣本中,有些企業(yè)在對(duì) " 服務(wù)人員 " 等概念的理解上存在著出入,所以, " 福利機(jī)構(gòu)人員 " 與 " 社會(huì)性服務(wù)人員 " 之和并不正好等于 " 服務(wù)人員 " 數(shù)。
資料來源: 508 家企業(yè)調(diào)查。
如表 2 所示,在全部樣本中,國有企業(yè)與國家控股企業(yè)服務(wù)人員的數(shù)量,分別占職工總數(shù)的 8.02 %和 8.62 %。而在集體企業(yè)中僅占 4.29 %,在中外合資合作企業(yè)中僅占 4.38 %,在私有企業(yè)中僅占 3.34 %。
國有企業(yè)不僅存在著服務(wù)人員比例偏大的情況,而且,這種情況還有隨國有企業(yè)人員規(guī)模的增大而增加的趨勢(shì)。比如,在調(diào)查樣本中,國有企業(yè)人數(shù)為 1000 人以上時(shí),服務(wù)人員占企業(yè)全部從業(yè)人員的比重為 9.03 %。這一比重比全部樣本時(shí)的比重增加了一個(gè)百分點(diǎn)。而社會(huì)性工作人員所占的比重,在全部樣本企業(yè)中占 3.58 %,在 1000 人以上的樣本企業(yè)中增加到 3.61 %。但在集體企業(yè)之中,卻不存在這種增加的趨勢(shì)。當(dāng)把國有企業(yè)樣本選擇在企業(yè)人數(shù)為 2000 人以上時(shí),其服務(wù)人員的人數(shù)占國有企業(yè)全部從業(yè)人員總數(shù)的比重又進(jìn)而增加到 10.05 %,其福利機(jī)構(gòu)工作人員也由 1000 人以上企業(yè)樣本的 5.10 %增加到 5.60 %,而社會(huì)性工作人員也同樣地有著增加的態(tài)勢(shì)。在 5000 人以上的國有企業(yè)之中,其內(nèi)部服務(wù)人員的比重又比在 2000 人以上的企業(yè)有所增加,達(dá)到 10.88 %。這就是說,國有企業(yè)人數(shù)規(guī)模越大,其內(nèi)部服務(wù)人員所占的比重也就越高。
從表 3 可以看出,在不同類型企業(yè)中,國有企業(yè)與集體企業(yè)的富余職工所占全部從業(yè)人員的比重最大,分別為 9 %和 14 %;國有企業(yè)與國家控股企業(yè)的離退休人員占全部從業(yè)人員之比最大,分別為 32 %和 31 %;國有企業(yè)和國家控股企業(yè)的服務(wù)人員和社會(huì)性服務(wù)人員所占比重也最大,分別為 8 %和 3 %。而工程技術(shù)人員和管理人員在全部從業(yè)人員中所占的比重,則在不同類型企業(yè)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這就是說,在人工成本開支所占全部成本的比重上,國有企業(yè)與國家控股企業(yè)會(huì)遠(yuǎn)遠(yuǎn)大于其他類型企業(yè)。
注: "*" 表示 P<0.01 , "**" 表示 P<0.001 。這里用雙尾檢驗(yàn), N=323 ,控制變量是 " 全部從業(yè)人員 " 。
資料來源: 508 家企業(yè)調(diào)查。
表 4 所示的在控制了 " 全部從業(yè)人員 " 之后所做的有關(guān)各變項(xiàng)的偏相關(guān)系數(shù),也顯示出了與表 2 和表 3 相一致的結(jié)果。注意: " 服務(wù)人員占全部從業(yè)人員之比 " 與 " 富余人員占全部從業(yè)人員之比 " 及與 " 管理人員占全部從業(yè)人員之比 " 和 " 離退休人員占全部從業(yè)人員之比 " 等正相關(guān)(偏相關(guān)系數(shù)分別為 0.2085 、 0.1961 、 0.1712 ) -- 這與我們所熟知的國有企業(yè)的狀況基本一致。可是,這里除 " 管理人員占企業(yè)全部從業(yè)人員之比 " 與 " 企業(yè)人均利潤 " 低相關(guān)(偏相關(guān)系數(shù)為 0.1642 )外, " 富余人員占全部從業(yè)人員之比 " 與 " 企業(yè)人均利潤 " 負(fù)相關(guān)(偏相關(guān)系數(shù)為 -0.2458 ),其他各項(xiàng)中,除管理人員占全部從業(yè)人員之比和工程技術(shù)人員占全部從業(yè)人員之比外,均與企業(yè)利潤不相關(guān)。這就是說,在國有企業(yè)之中,服務(wù)人員對(duì)企業(yè)利潤的增加,根本就不起什么積極作用。
3. 社會(huì)成本在福利保險(xiǎn)費(fèi)用上的表現(xiàn)
勞動(dòng)保險(xiǎn)福利費(fèi)用,一直是國有企業(yè)職工非工資性收入的一個(gè)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在 1998 年之前,市場經(jīng)濟(jì)各競爭主體中,如果說集體企業(yè)的勞動(dòng)保險(xiǎn)及其他福利費(fèi)用還有所保障的話,那么,其他非國有企業(yè)的福利保險(xiǎn)費(fèi)用是缺少制度的保障作用的。
在表 5 第( 6 )欄可以發(fā)現(xiàn),惟有國有企業(yè)與國家控股企業(yè)在福利保險(xiǎn)費(fèi)用方面的人均社會(huì)成本才與其人均工資之比較大:國有企業(yè)在這里為 57.66 %,國家控股企業(yè)為 50.33 %。在國有企業(yè)該項(xiàng)成本費(fèi)用比重較大的同時(shí),非國有企業(yè)均顯示出了其與工資之比的低比態(tài)勢(shì) -- 中外合資合作企業(yè)為 20.29 %,集體企業(yè)為 18.74 %,私有企業(yè)為 18.18 %。
資料來源: 508 家企業(yè)調(diào)查。從表 5 還可以清楚地看出,國有企業(yè)與國家控股企業(yè)的勞動(dòng)保險(xiǎn)與社會(huì)保險(xiǎn)費(fèi)用是最多的,前者為人均 1800 多元,后者達(dá)到人均 3000 多元,而集體企業(yè)在這方面占有的支出僅僅為人均 640 多元,私有企業(yè)為人均 330 多元。就是經(jīng)濟(jì)效益一向較為突出的中外合資合作企業(yè),其人均占有的勞動(dòng)保險(xiǎn)與社會(huì)保險(xiǎn)費(fèi)用也只有 770 多元,大大低于國有企業(yè)與國家控股企業(yè)。
在福利費(fèi)支出這一欄中,也是國有企業(yè)與國家控股企業(yè)最高,前者為人均 750 多元,后者為人均 740 多元,而中外合資合作企業(yè)在該項(xiàng)中也低于國有企業(yè),為人均 650 多元。而集體企業(yè)與私有企業(yè),則在該項(xiàng)之中的人均占有份額都不足 500 元。
在人均占有的福利機(jī)構(gòu)支出項(xiàng)中,國有企業(yè)與國家控股企業(yè)同樣地高出了其他非國有企業(yè)。在這里,國有企業(yè)人均分?jǐn)偟母@麢C(jī)構(gòu)支出為 800 多元,國家控股企業(yè)為人均 900 多元。樣本中集體企業(yè)在這里的開支少得可以被忽略。私有企業(yè)為人均 240 多元,中外合資合作企業(yè)為人均 130 多元。由此可以看出,國有企業(yè)與國家控股企業(yè)人均分?jǐn)偟母@麢C(jī)構(gòu)支出費(fèi)用已經(jīng)高于其人均占有的福利費(fèi)了。由于在統(tǒng)計(jì)中,福利費(fèi)欄的統(tǒng)計(jì)屬于顯性福利,福利機(jī)構(gòu)欄的支出代表著潛在福利費(fèi)用,所以,在 1995 年,國有企業(yè)與國家控股企業(yè)的人均潛在福利費(fèi)用支出已經(jīng)超過了其人均顯性福利的支出。即使這里不計(jì)勞動(dòng)保險(xiǎn)與社會(huì)保險(xiǎn)方面國有企業(yè)與非國有企業(yè)存在的差距,而僅僅以福利費(fèi)用來判別國有企業(yè)的成本支出,也可以發(fā)現(xiàn)其要比非國有企業(yè)為高。
通過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國有企業(yè)在進(jìn)行社會(huì)生產(chǎn)的同時(shí),也支付了極其巨大的社會(huì)成本。從固定資產(chǎn)存量方面來說,其非生產(chǎn)性固定資產(chǎn)額較大;從人員編制和內(nèi)部組織機(jī)構(gòu)的興建方面來說,其非生產(chǎn)性人員較多;從社會(huì)福利保險(xiǎn)費(fèi)用支出等方面來說,其在企業(yè)生產(chǎn)總成本當(dāng)中,又占居了相當(dāng)大的比重。
三、成本對(duì)利潤的沖銷
1. 對(duì)虧損國有利潤分配的相關(guān)
是什么使得國有企業(yè)表現(xiàn)為負(fù)利潤呢?換一個(gè)提問方式就是:為什么國有企業(yè)在產(chǎn)量逐年增長的同時(shí),卻步入了虧損之路?
從表 6 可知,在虧損型國有企業(yè)之中, " 本年人均利潤 " 與人均分?jǐn)偟?" 勞動(dòng)保險(xiǎn)與社會(huì)保險(xiǎn)費(fèi)用支出總額 " 、 " 在職職工福利費(fèi)用支出總額 " 和 " 在職職工福利與保險(xiǎn)外收入 " 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相關(guān)關(guān)系。國有企業(yè)的實(shí)際表現(xiàn)也與這里的統(tǒng)計(jì)檢驗(yàn)相一致。因?yàn)椋趪衅髽I(yè)中,人數(shù)眾多、冗員充斥,存在著以工資沖銷利潤的現(xiàn)象。 " 勞動(dòng)保險(xiǎn)與社會(huì)保險(xiǎn)費(fèi)用支出總額 " 也呈逐年上升的趨勢(shì),尤其是在一些老國有企業(yè)中,退休人員與在職職工之比越來越大,對(duì)退休人員退休金和醫(yī)療費(fèi)用及福利的支付,加重了企業(yè)本身的成本開支。再加上自 90 年代以來在職職工工資的迅速增長,工資在國有企業(yè)成本開支中的比重也無形中加大。在職職工福利及保險(xiǎn)外收入,對(duì)成本的增長形成了非常顯著的。在邱澤奇( 1996 : 270 )所做的調(diào)查中,還存在某些國有企業(yè)以固定資產(chǎn)與集體企業(yè)合作以成立新的集體企業(yè)的情況,甚至于也存在以同樣一份固定資產(chǎn)生產(chǎn)國有企業(yè)物品則為國有企業(yè)產(chǎn)值,生產(chǎn)集體企業(yè)物品則為集體企業(yè)產(chǎn)值的情況。這一切都會(huì)增加國有企業(yè)的成本開支,減少其利潤收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國家對(duì)某些國有企業(yè) -- 尤其是對(duì)某些大型國有企業(yè),還采取了 " 貸款 " 發(fā)放工資的措施。這就是說,在本年利潤為負(fù)的情況下,這些企業(yè)內(nèi)部職工的工資和福利費(fèi)用、退休職工的退休金和醫(yī)療費(fèi)用及內(nèi)部福利機(jī)構(gòu)人員的工資等等,都不可能有太大幅度的降低。由此也可以部分解釋樣本有企業(yè)本年利潤與各項(xiàng)人工成本不相關(guān)的現(xiàn)象。
我們本來認(rèn)為,福利與利潤會(huì)密切相關(guān),但與我們的設(shè)想相反, " 本年人均利潤 " 卻與人均分?jǐn)偟?" 福利機(jī)構(gòu)全年支出額 " 和 " 非生產(chǎn)性固定資產(chǎn)凈增加 " 不存在顯著性相關(guān)關(guān)系。這就是說,在國有企業(yè)虧損的前提下,其內(nèi)部顯性福利和潛在福利的增長與否,并不與 " 本年利潤 " 直接掛鉤。這恰好說明,在國有企業(yè)不盈利時(shí),其內(nèi)部潛在福利的開支還可能增長。換言之,即虧損并不必然地抑制福利機(jī)構(gòu)和福利設(shè)施的興建,而這些因素,卻直接增加著人工成本的開支總額,并進(jìn)而 " 制造 " 著虧損。
2. 對(duì)盈利國有企業(yè)利潤分配的分析
那么,如上所述的情況在國有企業(yè)盈利時(shí)又如何呢 ?
作為社會(huì)行動(dòng)者的國有企業(yè),具有使自己收益最大化的要求。在其虧損時(shí),往往會(huì)通過與國家的討價(jià)還價(jià),促使自己內(nèi)部職工的當(dāng)前收益最大化;在其盈利時(shí),則會(huì)在利潤分配過程中,通過某些合法的或不太合法的手段,促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當(dāng)然,這中間一個(gè)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以增加人工成本的方式?jīng)_銷利潤。
在這里,擴(kuò)大內(nèi)部福利設(shè)施 -- 非生產(chǎn)性固定資產(chǎn)的投資,可能是增進(jìn)國有企業(yè)內(nèi)部職工潛在福利的一條重要途徑。
通過表 7 可以明顯地看出,在國有企業(yè)盈利時(shí),各項(xiàng)人工成本與企業(yè)的本年利潤呈顯著的正相關(guān)。這就是說, " 本年人均利潤 " 為正的國有企業(yè)內(nèi)部,人均本年 " 勞動(dòng)保險(xiǎn)和社會(huì)保險(xiǎn)費(fèi)用支出總額 " 大,人均 " 在職職工福利費(fèi)用支出總額 " 、人均 " 全部從業(yè)人員工資總額 " 也在上漲。與此同時(shí),人均 " 在職職工社會(huì)福利及保險(xiǎn)外收入 " 也與 " 人均本年利潤 " 呈正相關(guān)。由此可見,當(dāng)國有企業(yè)盈利時(shí),除企業(yè)內(nèi)部職工的工資收入和福利收入得到增加外,國有企業(yè)退休職工的退休金收入與醫(yī)療費(fèi)用也會(huì)得到改善。
與虧損型國有企業(yè)不同的是,在盈利時(shí),國有企業(yè)的 " 本年人均利潤 " 與人均分?jǐn)偟?" 福利機(jī)構(gòu)全年支出額 " 及 " 非生產(chǎn)性固定資產(chǎn)凈增加 " 卻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其相關(guān)系數(shù)分別達(dá)到 0.378 和 0.396 ,其顯著性也小于 0.001 。這說明,樣本國有企業(yè)在盈利后的利潤分配中,很好地考慮了內(nèi)部福利設(shè)施的建設(shè) --" 非生產(chǎn)性固定資產(chǎn) " 的投資。盈利型國有企業(yè)越大,所生產(chǎn)的 " 本年人均利潤 " 越高,其所投入的 " 非生產(chǎn)性固定資產(chǎn) " 也就越多。具體情況如圖 1 所示。
從上圖可以看出這樣兩個(gè): (1) 在國有企業(yè)中,盡管很多企業(yè) " 人均本年利潤 " 為負(fù)值 -- 處于虧損狀態(tài),但其 " 人均非生產(chǎn)經(jīng)營用固定資產(chǎn)新增加 " 卻仍然為正,而且還表現(xiàn)得較高; (2) 在 " 人均本年利潤 " 為正時(shí),有些企業(yè)的 " 人均非生產(chǎn)經(jīng)營用固定資產(chǎn)新增加 " 表現(xiàn)得比利潤要高。這就是問題的癥結(jié)所在,即其以成本的方式,將利潤轉(zhuǎn)化為企業(yè)內(nèi)部的福利投資了。
如果不以 " 人均利潤 " 為基礎(chǔ),而以單個(gè)國有企業(yè) " 本年利潤 " 與 " 非生產(chǎn)經(jīng)營用固定資產(chǎn)新增加 " 的絕對(duì)值為出發(fā)點(diǎn),那么,如上所述的狀況會(huì)表現(xiàn)得更加明顯。我們以 " 本年利潤 " 為自變量,以 " 非生產(chǎn)性固定資產(chǎn)凈增加 " 為因變量來做預(yù)測,就會(huì)在盈利型國有企業(yè)之中發(fā)現(xiàn),有些樣本的非生產(chǎn)經(jīng)營用固定資產(chǎn)的新增加,遠(yuǎn)遠(yuǎn)超過了其本年利潤的值。雖然在國有企業(yè)盈利時(shí),我們對(duì)其福利設(shè)施的投資無可非議,但從圖 2 中的 " 實(shí)際觀察值 " 曲線上可以看出,當(dāng)某些盈利型國有企業(yè) " 本年利潤 " 在 50000 千元及其以下時(shí),其 " 非生產(chǎn)性固定資產(chǎn)凈增加 " 卻大大超過了 50000 千元。這就是說,在這些樣本國有企業(yè)之中,存在著 " 福利 " 沖銷利潤的現(xiàn)象。
從表 8( 見下頁 ) 可以看出,三次曲線估計(jì)的 R 2 值為 0.257 ,大于直線方程的 0.115 和二次曲線方程的 0.173 。所以,這里我們以三次模型為最佳擬合模型。如果以 X 表示 " 本年利潤 " ,則其方程式為:
Y=5029.55 + 0.4464X +( -3.E-06 ) X2 +( 5.3E-12 ) X3
從這里亦可以推知,有的國有企業(yè)在盈利時(shí),通常會(huì)首先將一部分利潤內(nèi)部化為集體福利,從而使得盈利型企業(yè)的成本增大,減少利潤上繳率。
3. 社會(huì)成本對(duì)虧損的沖銷
如果把國有企業(yè)較之非國有企業(yè)多支付的社會(huì)成本轉(zhuǎn)化為利潤,或以此去沖銷虧損,那么,原來虧損的國有企業(yè),會(huì)不會(huì) " 扭虧為盈 " 呢 ?
從表 9 可以看出,國有企業(yè)如果沒有社會(huì)成本的開支,便可基本上 " 扭虧為盈 " ,因?yàn)檫@些不完全統(tǒng)計(jì)的社會(huì)成本,可以使樣本國有企業(yè)的虧損沖銷到 "0" 以上。也就是說,如果將這些社會(huì)成本轉(zhuǎn)化為利潤,那么,樣本虧損型國有企業(yè)的 " 本年負(fù)利潤 " 都可以轉(zhuǎn)變?yōu)檎麧櫋@纾谥醒胨鶎俚奶潛p型重國有企業(yè)的社會(huì)成本中 ," 新增非生產(chǎn)性固定資產(chǎn) " 相當(dāng)于虧損額的 97.83 %, " 新增社會(huì)性固定資產(chǎn) " 相當(dāng)于虧損額的 4.35 %,僅僅這后兩項(xiàng)合計(jì)就可以將該年的負(fù)利潤沖銷完畢。在省屬虧損型重工業(yè)國有企業(yè)的社會(huì)成本中,僅僅 " 勞動(dòng)保險(xiǎn)和社會(huì)保險(xiǎn)支出總額 " 就完全可以將該年的負(fù)利潤沖銷完畢。仔細(xì)考察表 9 中的各項(xiàng)數(shù)值可以發(fā)現(xiàn),除縣屬虧損型輕工業(yè)國有企業(yè)的社會(huì)成本中 , 該年的 " 新增非生產(chǎn)性固定資產(chǎn) " 對(duì)虧損的沖銷較少,只占 0.35 %外,其他各隸屬級(jí)別企業(yè)在此項(xiàng)的開支,都能夠沖銷 50 %以上的虧損。中央屬虧損型輕工業(yè)國有企業(yè)的社會(huì)成本中, " 新增非生產(chǎn)性固定資產(chǎn) " 竟然可以沖銷 2067.7 %的虧損。所以,僅僅 " 新增非生產(chǎn)性固定資產(chǎn) " 一項(xiàng)開支的節(jié)約,或者說將此項(xiàng)開支轉(zhuǎn)化為利潤,就可以使很多虧損型國有企業(yè)轉(zhuǎn)變?yōu)橛髽I(yè)。這就是說,部分國有企業(yè)社會(huì)成本的膨脹和難以控制的擴(kuò)張沖動(dòng),是造成其經(jīng)營狀況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簡短的結(jié)語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國有企業(yè)的社會(huì)成本比我們預(yù)想的可能還要大得多,這已經(jīng)成為許多國有企業(yè) " 有增長而無 " 的重要原因之一 , 并成為國有企業(yè)轉(zhuǎn)變經(jīng)營機(jī)制和改善經(jīng)營狀況的巨大阻礙。當(dāng)然,國有企業(yè)的社會(huì)成本并非都是無效的成本或多余的成本,其中也有相當(dāng)一部分屬于企業(yè)正常的成本。但是,由于國有企業(yè)社會(huì)成本的擴(kuò)張沖動(dòng)缺乏硬約束,國有企業(yè)會(huì)由此形成人員過密化和福利功能內(nèi)卷化趨勢(shì),從而步入社會(huì)成本的增加大大快于生產(chǎn)的增長的困境。此外,由于缺乏對(duì)國有企業(yè)社會(huì)成本的嚴(yán)格定義和測算,我們實(shí)際上很難弄清在所有國有虧損企業(yè)中,有多少是屬于真實(shí)的虧損,有多少是為了減少上繳利潤或拖欠保險(xiǎn)金的虛假虧損;在真實(shí)虧損的企業(yè)中,又有多少屬于經(jīng)營性虧損,多少屬于政策性虧損;而政策性虧損企業(yè),又有多大比例的虧損屬于經(jīng)營不善所致。所以,必須在國有企業(yè)中建立起 " 擬市場化核算體制 " ,以便厘清每個(gè)國有企業(yè)的社會(huì)成本,嚴(yán)格區(qū)分在社會(huì)成本的承擔(dān)中,哪些是企業(yè)的責(zé)任,哪些是國家和政府的責(zé)任,哪些是職工個(gè)人的責(zé)任,從而建立起國有企業(yè)社會(huì)成本的分?jǐn)倷C(jī)制,為實(shí)現(xiàn)國有企業(yè)的預(yù)算硬約束和優(yōu)勝劣汰掃清利益關(guān)系調(diào)整方面的障礙。
書目:
Coase,R.H.(1937),"NatureofFirm", Economica .Nov.1937 ; --(1960),"TheProblemofSocialCost", TheJournalofLawandEconomics ,3 ; --(1988/1995) ,《廠商、市場與》,陳坤明、李華夏譯,臺(tái)北遠(yuǎn)流出版公司。
董輔、唐宗、杜海燕主編《國有制度》,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樊綱:《論當(dāng)前國有企業(yè)產(chǎn)權(quán)關(guān)系的改革》,載熊映梧、劉常勇主編《公營企業(yè)改革》,黑龍江出版社 1995 年版。
韓福榮、徐艷梅:《合營企業(yè)穩(wěn)定性與壽命周期》,中國出版社 1997 年版。
科爾內(nèi)( Kornai,J. ):《短缺學(xué)》,經(jīng)濟(jì)出版社 1986 年版。
李漢林、方明、王穎、孫炳耀、王琦:《尋求新的協(xié)調(diào) -- 中國城市發(fā)展的學(xué)》,測繪出版社 1988 年版。
李路路、王奮宇:《當(dāng)代中國化進(jìn)程中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及其變革》,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李培林等:《轉(zhuǎn)型中的中國企業(yè)》,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劉國光主編《中國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模式研究》,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 1988 年版。
林毅夫、蔡、李周:《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yè)改革》,上海三聯(lián)書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路風(fēng):《單位:一種特殊的社會(huì)組織形式》,載《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 1989 年第 1 期。
L ü ,XiaoboandElizabethJ.Perry(ed.1997), Danwei:TheChangingChineseWorkplaceinHistoricalandComparativePerspective, NewYork:M.E.Sharpe.
邱澤奇:《集體企業(yè)個(gè)案調(diào)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史丹:《國有企業(yè)虧損的宏觀原因》,載鄭海航主編《國有企業(yè)虧損研究》,經(jīng)濟(jì)管理出版社 1998 年版。
王瑞璞主編《中南海三代領(lǐng)導(dǎo)集體與共和國經(jīng)濟(jì)實(shí)錄》(中卷),中國經(jīng)濟(jì)出版社 1997 年版。
汪海波、董志凱:《新中國經(jīng)濟(jì)史》,經(jīng)濟(jì)管理出版社 1995 年版。
肖耿:《產(chǎn)權(quán)與中國的經(jīng)濟(jì)改革》,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 1997 年版。
熊映梧、劉常勇:《公營企業(yè)改革》,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楊宜勇、辛小柏:《下崗職工基本社會(huì)保障和再就業(yè)的調(diào)查》,載汝信、陸學(xué)藝、單天倫主編《 1999 年社會(huì)形勢(shì)分析與預(yù)測》,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3-254 頁。
鄭海航主編《國有企業(yè)虧損研究》,經(jīng)濟(jì)管理出版社 1998 年版。
張曙光主編《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第 1 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張軍:《 " 雙軌制 " 經(jīng)濟(jì)學(xué) -- 中國的經(jīng)濟(jì)改革( 1978-1992 )》,上海三聯(lián)書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報(bào).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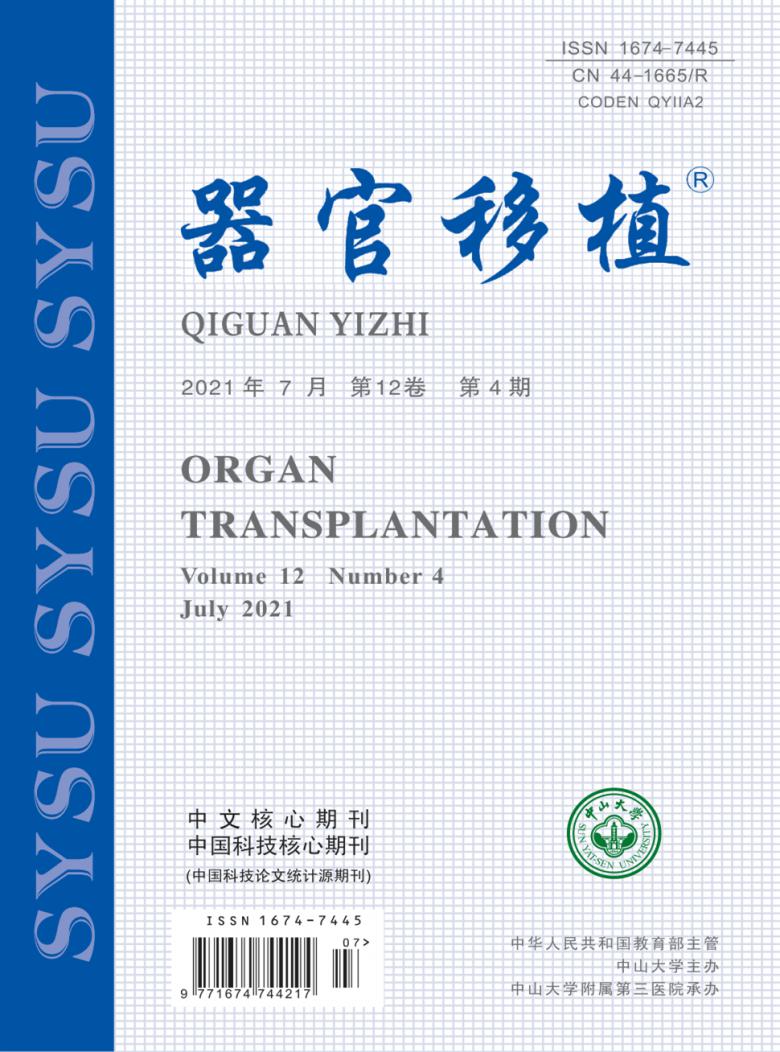
.jpg)
院學(xué)報(bào).jpg)
.jpg)
化.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