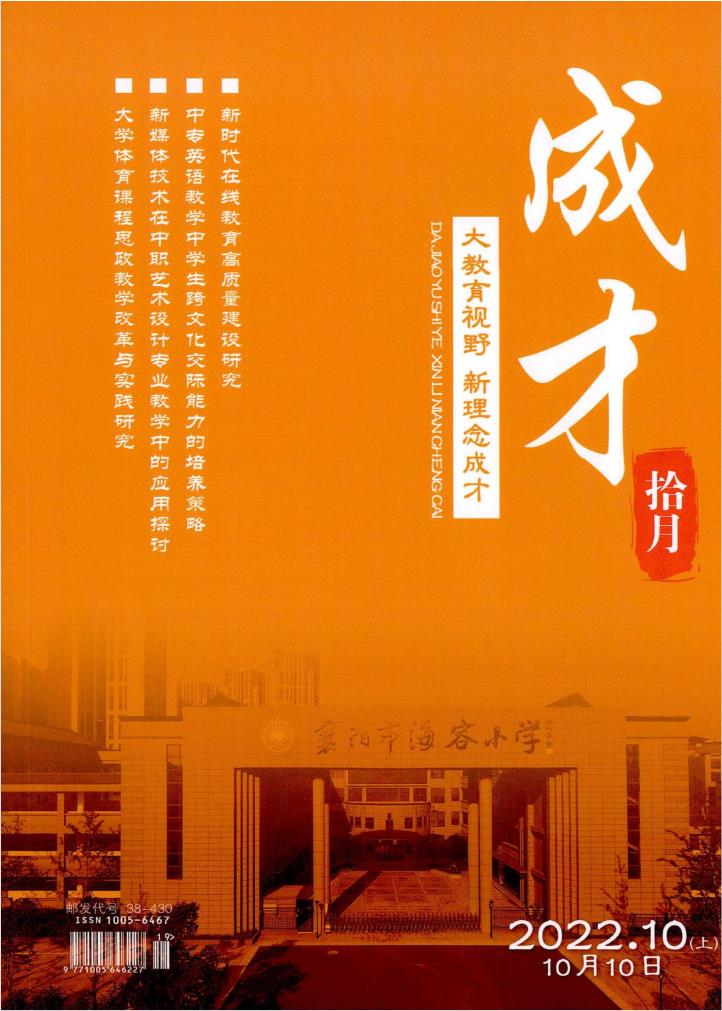關于明人評《三國演義》及其對歷史與虛構的認識
張寶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明代重要文論家對《三國演義》的評論,比較辯證地考察了歷史題材小說中歷史與虛構關系。 關鍵詞:《三國演義》;小說;歷史 “小說感興社會之效果,殆莫過于《三國演義》一書矣。”語出清末民初黃人所撰《小說小話》,說的是羅貫中小說影響之大。且不贅述它對明末農民起義軍、太平天國和清朝君臣的影響;只看清末“西人之居我國者,稍解中文即爭讀《三國演義》;偶與論及中國英雄傳記則津津樂道者,必此書也”。或看今人由此闡發出領導藝術、人才學、謀略學等范疇及在國內上映八十四集《三國演義》電視連續劇而引起的討論熱,足見它的魅力方興未艾。但是歷史演義小說畢竟不是歷史本身,我們必須把握歷史與文學、現實與虛構之間的關系。因為它是一部歷史演義小說,它是以西晉史學家陳壽撰著的《三國志》作底本寫成的通俗文藝讀物。本文分析明代文論家對《三國演義》的評價中所體現的關于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的看法。 一般而言,探析《三國演義》的真實與虛構問題,首先得弄清小說采用的素材即歷史資料,是否可信;小說作者對他所描寫的歷史人物是否做到了“不虛美、不隱惡”,不含有較大的偏見。顯然也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人們才能較為客觀地評論小說家發掘歷史材料、探索歷史背景、描寫歷史事件和藝術地再現歷史人物形象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又有哪些不足,甚至是重大的失誤。而歷來研究者往往更多的是拘泥于細枝末節,單從在歷史上是否實有其事從而作出簡單判斷,研究小說藝術再現歷史人物及歷史發展真實風貌的功能方面則稍微欠缺。當然還是有些文論家卓有見識,能夠理解作者羅貫中是如何運用辯證的方法,適當地采用些虛構的情節來增強作品的藝術性,而又能使這些虛構的情節與歷史上的真人真事不出現太大的矛盾沖突。從而使讀者能夠從思想上進入特定的三國時代氛圍,并“尚友古人”,和小說中自己喜愛的人物產生共鳴。這才是具備洞見識力的文論家超越世俗淺見之處。 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參照陳壽的《三國志》及裴松之的注文,也借鑒了《后漢書》《晉書》中若干紀傳,并旁采《世說新語》《搜神記》《三國志平話》等古籍。同時也取材于《資治通鑒》,而胡三省的注解更有助于讀者理解三國人物與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這就為小說作者按時問順序編寫三國的歷史小說提供了借鑒。民間傳說、歷史文獻、三國故事劇本、正統官修史書的因素夾雜在一起。可見《三國志通俗演義》歷史與虛構相伴而生,也可見時人在歷史觀問題上的混亂之因緣。 明代蔣大器作序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是小說成熟的標志。蔣大器在序里第一次論述了歷史小說的基本特點,肯定了他的社會作用。他明確指出《三國演義》忠實于基本歷史事實,做到了“夫史非獨紀歷代之事”,因而“亦庶幾乎史”;另一方面,它又對歷史材料“留心損益”,對某些人物、情節有所取舍和虛構,表現出與歷史著作不同的特點。他說:歷代之事,愈久愈失其傳。前代嘗以野史作為評話,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厭之。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于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里巷歌謠之義也。……則三國之盛衰治亂,人物之出處臧否,一開卷,千百載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其問亦未免一二過與不及,俯而就之,欲觀者有所進益焉。予謂誦其詩,讀其書,不識其人,可乎?讀書例曰:若只讀到古人處,便思自己忠與不忠,孝處,便思自己孝與不孝,至于善惡可否,皆當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讀過,而不身體力行,又未嘗讀書也。 蔣大器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考證國史,寫作態度非常嚴謹;同時有所加工,完全可以視做史實。他在這里把史與詩放在同等地位。內容信實,文字好讀。書成之后,“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所以雖然有虛構因素,然而就影響而言,應當不遜于傳統的詩教作用。 在語言方面,《三國演義》具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特點,“人人得而知之”,不像歷史著作那樣“理微義奧”。因此,他認為此類歷史小說,既可以幫人們認識歷史,又能幫人們區分忠奸善惡,還可以吸取歷史教訓。由于此書作者有一定的歷史素養,藝術技巧也很高,塑造了一系列風云人物,又生動地描寫了多個政治斗爭和重大戰役,對三國歷史按年代先后作了鳥瞰式的敘寫。這樣此書雖然不大為正統史學家重視,但卻很受群眾歡迎。蔣大器一方面擺脫了正統史學家的偏見,明確指出歷史小說的特點,特別是強調了與正史的區別,指出歷史演義小說可以在必要時加工虛構,為以后張尚德的進一步提出“羽翼信史說”作了準備。同時蔣大器在序中闡述了自己所尊奉的儒家的歷史觀:他推崇孔子修《春秋》“立萬萬世至公至正之大法”,和孟子的言仁義而不言利;至朱熹的《通鑒綱目》“亦由是也;豈徒紀歷史之事而己乎?”這就是說:史書是為“勸懲警懼當世”而作,它不僅是為了紀往事。為此他特別強調此書是貫穿了尊蜀漢,特崇孔明,并尊劉、關、張,貶抑孫權和極端反對曹操的思想。 張尚德駁斥把歷史小說視為多余的觀點,對于明代歷史小說和小說理論的發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他重申蔣大器的一些基本觀點,指出“史氏所志,事詳而文古,義微而旨深”。因此“非通儒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義,因義而興乎感”。他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引里說,史氏所志,事詳而文古,義微而旨深,非通儒宿夙學,展卷問鮮不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語,隱栝成編。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義,因義而興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統必當扶,竊位必當誅,忠孝節義必當師,奸貪諛佞必當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風教廣且大焉,何病其贅耶?客仰而大唬曰:有是哉?子之不我誣也。是可謂羽翼信史而不違者矣。簡帙浩瀚,善本甚艱,請壽諸梓,公之四方,可乎?余不揣谫劣,原作者之意,綴俚語四下韻于卷端,庶幾歌詠而有所得歟。于戲!牛溲馬勃,良醫所珍,孰謂稗官小說不足為世道重輕哉? 歷史演義小說“羽翼信史而不違”,即不違背歷史真實,但又不能與歷史完全等同,否則歷史演義小說也就成了多余。他認為它有不可忽視的社會教育作用,其“稗益風教,廣且大焉”,不能因其是“稗官小說”就認為“不足為世道所輕重”。 自《三國志通俗演義》后,歷史演義小說大量流布,且作者在如何對待歷史事實和藝術虛構關系問題上看法不一。小說理論上,有熊大木和可觀道人為代表的爭論。前者在《新刊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序里對所謂歷史演義小說“不可紊之以正史”的觀點進行了駁斥,申明在尊重歷史基本事實的同時可以“用廣發揮”。后者則在《新列國志敘》里說在“敷衍不無增添,形容不無潤色”基礎上,必得“大要不敢違其實”。其實他們并無根本分歧,只不過是各自的側重不同。當然,這也剛好說明明人在此問題上尚未徹底弄清楚。此后謝肇涮進一步提出“凡為小說雜劇戲文,須是虛實相半,方為游戲三昧之筆,然亦要情景造極為止”。另有袁于令提出小說之幻和史志之真的異質,須知“天下極幻之事乃極真之事,極幻之理乃極真之理”。闡明歷史演義小說在選取歷史素材時必須尊重基本歷史事實,也可潤色刪削,這些文論就比較辯證地考察了歷史與虛構關系。 就《三國演義》的流布和接受情況而言,它很能體現明人對歷史與小說之問辯證關系的認識軌跡。及至諸如《忠義水滸傳》《西游記》等通俗小說創作后,可供參照的文本資源與角度就更加豐富。要真正識別史實部分與小說藝術成分確實不易,故我們要結合三國歷史來閱讀和評論《三國演義》,分清小說中的敘述和描寫哪些與史實相吻合;哪些是移花接木和對歷史的夸大和縮小;哪些完全是虛構,這樣才能較為正確地鑒賞和評品《三國演義》。
注釋: [1]朱一玄:《三國演義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49頁、第650頁. [2]參見蔡景康《明代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版,第95頁. [3]參見張少康《中國歷代文論精品》(第三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頁. [4]謝肇淛:《五雜俎》,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