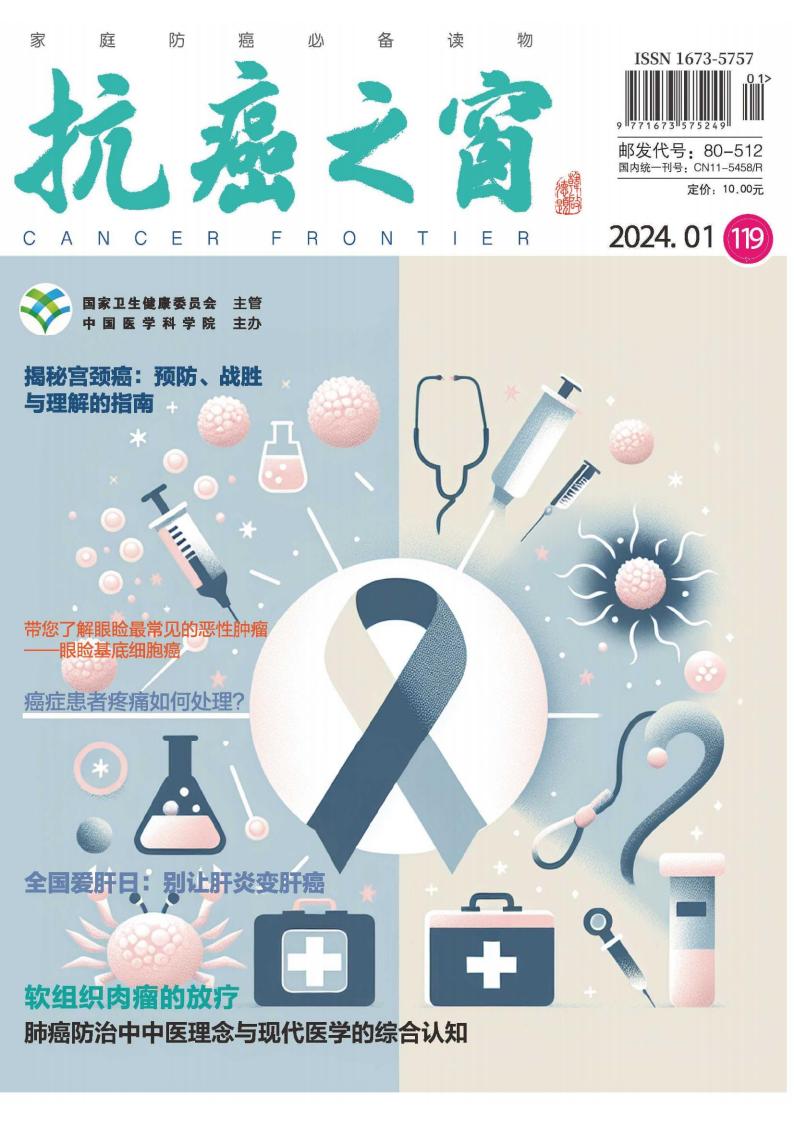虞集《〈西游記〉序》考證
石鐘揚
【內容提要】 元人虞集《西游記序》,就現(xiàn)存文獻而言,最早見諸清初《西游證道書》。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學界始有人對其真?zhèn)芜M行爭議。其實虞集未必偽,只是其所序者既非《長春真人西游記》,也非百回本小說《西游記》。《長春真人西游記》是丘處機西行歷程的“報告書”,與唐僧取經(jīng)故事無涉,而“虞序”則明顯提及唐僧取經(jīng)故事。虞集是元代中葉學者,自然不可能預為明代小說《西游記》作序。虞集所序者當為那深藏在歷史帷幕中的《西游記》平話。《西游記》平話歷來被學者視為元末明初之物,我則考定它為宋末元初之作品。 【關鍵詞】 虞集 《西游記》序 《西游記》平話
虞集《西游記序》,就現(xiàn)存文獻而言,最早見諸清初汪象旭評本《西游證道書》。孫楷第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說:“自象旭此書始冠以虞集序”。《西游證道書》,孫楷第先生于三十年代尚稱:“極不多見”,現(xiàn)存少數(shù)珍本都被束之高閣,凡人是難睹其芳顏的。而國內解放前后所出版的諸種小說史料選本,亦均未收錄此序。今則先將虞序全貌披露,再作考辯。 西游記序
余浮湛史館,鹿鹿丹鉛。一日有衡岳紫瓊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來謁,余于流連浹月。道人將歸,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國初邱長春所纂《西游記》也,乞公一序以傳。”余而讀之,見書中所載,乃唐玄奘取經(jīng)事跡。夫取經(jīng)不始于唐也,自漢迄梁咸有之,而唐之玄奘為尤著。其所跋涉險遠,經(jīng)歷艱難,太宗《圣教》一序,言之已悉,無俟后人贅陳。 而余竊窺真君之旨,所言在玄奘,而意實不在玄奘;所紀在取經(jīng),而志實不在取經(jīng):特此以喻大道耳。猿馬金木,乃吾身自具之陰陽;魑魅妖邪,亦人世應有之魔障。雖其書離奇浩瀚數(shù)十萬言,而大要可以一言蔽之曰:收放心而已。蓋吾人作魔成佛,皆由此心。此心放,則為妄心,妄心一起,則能作魔,如心猿之稱王稱圣而鬧天宮是也。此心收,則為真心,真心一見,則能滅魔,如心猿之降妖縛怪而證佛果是也。然則同一心也,放心則其害如彼,收之則其功如此,其神妙非有加于前,而魔與神則異也。故學者但患放心之難收,不患正果之難就。真君之諄諄覺世,其大旨寧能外此哉? 按真君在太祖時,曾遣侍臣劉仲祿萬里訪迎,以野服承圣問,促膝論道,一時大被寵眷,有《玄風慶會錄》,載之詳矣。歷朝以來,屢加封號。其所著詩詞甚富,無一非見道之言,然亦有如是書之鴻肆而靈幻者,宜紫瓊道人之寶為枕秘也。乃俗儒不察,或等之“齊諧”稗乘之流。井蛙夏蟲,何足深論?夫《大易》皆取象之文,《南華》多寓言之蘊,所由來尚矣。昔之善讀書者,聆周興嗣“性靜心動”之句,而獲長生;誦陸士衡“山暉澤媚”之詞,而悟大道,又何況是書之深切著明者哉? 天歷已巳翰林學士臨川邵庵虞集撰 [1]
一、虞集《西游記序》真?zhèn)慰?/p>
關于“虞序”,實則自清代之吳玉搢(《山陽志遺》)、阮葵生(《茶余客話》),到近世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傅惜華(《內閣文庫訪書記》)都眾口一詞地肯定這篇序言的存在,而無人謂之為偽。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學界對虞序的真?zhèn)尾庞袪幾h。準確的說,關于這個問題,大陸學界在拙作之前尚無人涉及,倒是日本與港臺時有人討論。日本學者太田辰夫認為虞序為真,并據(jù)此推斷元代有一本偽托邱長春所作且富道教色彩的《西游記》(《西游證道書考》,《神戶外大論叢》第21卷5號)。新加坡學者柳存仁認為虞序雖有種種“疑竇”,卻“含有一部分真實的材料”(《全真教和小說西游記》,香港《明報月刊》1985年5━9期)。而臺灣學者鄭明利在其《西游記探原》(臺北文開出版事業(yè)公司1982年出版)中,則力證其偽。其論點轉見容镕《臺灣學者鄭明利對〈西游記〉的探討》(《中外文學研究參考》1985/1)。容文介紹: 鄭明利舉出六條理由證明最早出現(xiàn)于《西游證道書》的所謂元虞集的序(該序聲稱《西游記》作者是丘處機),乃出于汪象旭的偽造:(1)此序不見于今虞集的任何文集中。(2)序中虞集自署“天歷己巳翰林學士臨川邵庵虞集”,然而虞集并未任職翰林學士,作序年應官翰林直學士,此外自稱臨川人,僅見于此序。(3)從序中可以看出虞集對丘處機所知不多,這與虞集對丘處機知之甚深的實際情況正好相反。(4)序中說“一日有衡岳紫瓊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來謁”,然今存虞集未見危敬夫與紫瓊道人,二人顯系臆造。(5)虞序僅見于《西游證道書》,對其出處未作交代,且象汪象旭曾偽造《呂祖全傳》,因此再偽造虞序,自亦可能。(6)虞序不見收于汪本以外的《西游記》及其他載籍。因此鄭明利肯定虞序既屬偽作,丘作之說自可銷聲匿跡。 鄭氏所舉六條理由,乍看似頗充分。若作認真考察,則發(fā)現(xiàn)其殊難成立。恕我分解如次。其一、此序雖“不見于今虞集的任何文集中”,卻不見得不是虞集所作。因為“今虞集的任何文集”,并不等于“虞集的任何文集”,更不等于虞集實寫的全部文章。虞集著述甚豐,歐陽玄《雍虞公文序》有云:“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冊,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稱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人,得所贈言,如獲拱璧。”而其文集即使是集大成的《道園學古錄》(四部叢刊、四部備要本),也遠非全璧。其門人李本對此有“識”云:“在朝稿二十卷,應制錄六卷,歸田稿十八卷,方外稿六卷。蓋先生在朝時為文多不存稿,固已十遺六七,歸田之稿間亦放軼,今特就其所有者而錄之,所謂泰山一豪芒也。” 于今雖不能在僅存的“一豪芒”中尋得《西游記序》,孰謂此序不在那隱沒的“泰山”之中呢? 其二、關于虞序文末之署名問題。虞集祖籍四川,先祖允文在南宋以丞相被封于雍,宋亡虞家僑居江西臨川,虞集晚年亦“病歸臨川”,死后被贈封為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因而虞集“自稱臨川人”,毫不奇怪;其:“平生為文萬篇,稿存者十二三”(《元史》),難說“自稱臨川人僅見與此序”。虞氏“早歲與弟槃同辟書舍為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于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元史》),故有臨川邵庵云云。唯天歷己巳(1329),虞氏為“翰林直學士”,而非“翰林學士”料是轉輾反復或手民誤植所造的失誤。大凡作偽之難在文章之風格,而不在文末之署名。文章之風格是作者個性之流露,作者有其個性,做偽者亦有其個性,兩者殊難融洽。而署名是死板的,有據(jù)可查的,不能設想偽造虞序者連《元史》都不會翻閱。因而以署名之小誤來證作品之偽,總是乏力的。 其三、丘處機(1148—1227)與虞集(1272—1348)間距幾半個世紀,到天歷己巳(1329)作《西游記序》時,已逾百年。丘處機本是個富有神秘色彩的人物,虞集對他自然談不上“知之甚深”。即使虞集對丘處機“知之甚深”,也未必就對《長春真人西游記》“知之甚深”。書與人有聯(lián)系卻畢竟不能等同,更何況《長春真人西游記》又是部富有神秘色彩的書,其載之《道臧》,秘藏于宮、觀,局外人不能輕易見到。清代史學大家錢大昕有《跋長春真人西游記》云: 長春真人《西游記》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風俗,頗足資考證,而世鮮傳本。予始于《道藏》鈔得之。村俗小說有《唐三藏西游演義》,乃明人所作。蕭山毛大可據(jù)《輟耕錄》以為出丘處機之手,真郢書燕說矣。 清代尚且如此,元代更可想而知。虞序指斥“俗儒不察,(將《長春真人西游記》)或等之‘齊諧’稗乘之流”,殊不知正是自己將“‘齊諧’稗乘之流”的古本《西游記》(平話)誤認為《長春真人西游記》,并張冠李戴地為之作序了(關于《西游記》平話容后討論)。 其四、對衡陽紫瓊道人,日本學者太田辰夫在《西游證道書考》中早具有考索,指出他就是元代道士張模。據(jù)《上陽子金丹大要·列仙志》(《道臧 》738)記載,張模屬全真道士體系中人;宋有道(即黃房公)傳李玨(太虛真人),李傳張模(紫瓊真人),張傳趙友欽(緣督真人)。《列仙志》又記趙友欽“己巳之秋寓衡陽,以金丹妙道悉付上陽子”。據(jù)柳存仁先生考證,這“己巳之秋”,正是虞序所署之年份。從趙友欽寓衡陽知,紫瓊道人此時尚健在,虞集此年也有五十八歲,兩人相見不是不可能的。至于危敬夫是否是虞集之友人危素(太樸,1303—1372)之別號或誤植,尚無定考。無定考只當繼續(xù)探考,卻不可因此斷為“顯系臆造”。 其五,關于《呂祖全傳》,孫楷第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數(shù)目》卷三有著錄,云:“讬呂祖?zhèn)鳌>硎最}云‘奉道弟子汪象旭重訂’。象旭字澹漪,原名淇,字右子,里居未詳。此傳口氣為呂仙自述,然實是小說。”這里至少有兩種情況:一是有某氏托呂祖之名撰寫在先,汪象旭為之“重訂”在后;一是象旭托名撰寫之,又不忍失己名,于是再署“重訂”字樣以志。不管是那種情況,汪氏并沒徹底掩飾自己的身份。從“此傳口氣為呂仙自述,然實是小說”云云,則知這部小說以第一人稱(呂仙自述)為之;以第一人稱為之,在作者是“自神其教”——增強作品的真實性,在小說史上卻是個創(chuàng)舉。如果《呂祖全傳》果為汪氏所作,那他之托名呂祖,則是其創(chuàng)舉的必然產(chǎn)物。今天我們陳述此事,只能與孫先生心平氣和地說:“托呂祖撰”,而不可感情用事地以“偽”冠之其首。因今人視托名故事主人公而寫作,為文人慣用“伎倆”,不足為奇。如魯迅托名“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病中日記而作《狂人日記》,茅盾托名“得之與某公共防空洞”誰氏日記而作《腐蝕》,孰謂二公為偽托呢?《呂氏全傳》既不算“偽造”,就不可指控汪氏有作偽之癖,更不能以《呂祖全傳》之例去推斷《西游記序》屬汪氏之“偽造”。自元至清,與《西游記》干系較深且有跡可尋者,大有人在,汪氏既要偽造一序,則大有選擇余地,何必一定要偽托虞集呢? 其六,虞序之全文雖首見諸汪本《西游記》,然他的片段或精神,卻如幽靈般早就跟蹤著吳承恩的《西游記》。金陵世德堂本《西游記》卷首有陳元之序,云: 舊有序,余讀一過,亦不著姓氏作者之名,豈嫌其丘里之言與?其序以為:孫,猻也;以為心之神。馬,馬也;以為意之馳。八戒,其所八戒也;以為肝氣之木。沙,流沙;以為腎氣之水。三藏,藏神、藏聲、藏氣之藏也;以為郛郭之主。魔,魔;以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顛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攝。是故攝心以攝魔,攝魔以還理,還理以歸之太初,即心無可攝。 世德堂本是吳承恩《西游記》現(xiàn)存的最早版本,陳序作于萬歷二十年(1592),是吳氏謝世后十年之物,它之前的“抄本”面目不清,無法證明其有“舊序”。以其言辭稍異而精神酷似推斷,這“舊序”當是那流浪的“虞序”。這以“舊序”面目出現(xiàn)的“虞序”,在世德堂本后不久,又被竄入謝肇淛的筆記著作《五雜俎》之中,謝云: 《西游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為心之神,以豬為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于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 “舊序”、謝說雖追蹤著吳本《西游記》,而實與之精神不合(詳見另文),這就反證“虞序”是同一部與之精神相符的《西游記》共存。 從容文介紹看,鄭氏之證“虞序”之偽的目的在破百回本《西游記》“丘作之說”,用心可謂良苦。應當說,刊于《西游證道書》卷首之“虞序”,對張揚 “丘作之說”影響極大,然“丘作之說”并不首創(chuàng)于 西游證道書 。歷來學者只說《西游證道書》是“清初刊本”,未指確年;竊以為,其與《呂祖全傳》都為汪刊本,若以《呂祖全傳》之刊年——“康熙元年”限之,大概不大離譜。在這之前伍守陽就在《天仙正理·煉已直論五》中說:“丘真人西游雪山而作《西游記》以明心,曰心猿;按其最有神通。禪宗言‘獼猴跳六牕’,狀其輪轉不住,其劣性難馴,惟煉可制”,顯然,這伍某已將寫“心猿”——孫悟空的《西游記》的著作權,廉價送給了那位丘真人。此則文字作于崇禎十二年(1639),較《西游證道書》大概要早二十余年。 凡此種種,足見鄭說不僅不能證明“虞序”為偽造,而且無補于破除“丘作之說”。好在“丘作之說”早在魯迅、胡適的考證鋒芒前“銷聲匿跡”,無待今日勞作。
二、虞集所序者當為《西游記》平話
其實“虞序”所序者,既非《長春真人西游記》,也非吳承恩的《西游記》。《長春真人西游記》是記丘處機西行歷程的“報告書”,與唐僧取經(jīng)故事無涉,而“虞序”則明顯提及唐僧取經(jīng)故事。虞集是元代中葉學者,他自然不可能先知先覺地為明代中葉的吳承恩(1504-1582)的《西游記》作序,況且虞序中宗教唯心主義的說教,與吳承恩旨在“紀人間變異”(《禹鼎志序》)的創(chuàng)作傾向亦無共同處。那么,“虞序”所序者到底是部什么樣的書呢? 眾所周知,在宋刊《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與吳承恩《西游記》之間,除《西游記雜劇》之類戲曲外,至少還有一部作為吳承恩《西游記》祖本的小說,即朝鮮《樸通事諺解》所收片段與《永樂大典》第13139卷所收《魏征夢斬涇河龍》一節(jié)的古本《西游記》。 應當指出,《永樂大典》與《樸通事諺解》所收古本《西游記》片段,在語言形態(tài)上差異相當大。《永樂大典》的修撰開始于明成祖(朱棣)永樂元年(1403),定稿于永樂五年(1407),其“用韻以統(tǒng)字,用字以系事”的編輯方法,“上自古初,迄于當世,旁搜博采,匯聚群書,著為奧典”。 [2]所謂“匯聚群書”,即對所收典籍基本上是整段、整篇,乃至整部地抄入。因而有理由說,《永樂大典》所收“夢斬涇河龍”,基本保存了古本《西游記》文字的本來面貌。從現(xiàn)存片段看,古本《西游記》文白夾雜,遠勝《三國志平話》,而近似《三國志通俗演義》。前段寫涇河龍故意“錯了時辰,少下些雨”以刁難神相表守成,結果弄巧成拙遭到天譴的情節(jié),這里從略;僅錄魏征夢斬涇河龍一節(jié): 玉帝差魏征斬龍。天色已晚,唐皇宮中睡思半酣,神游出殿,步月閑行。只見西南上有一片黑云落地,降下一個老龍,當前跪拜。唐王驚怖曰:“為何?”龍曰:“只因夜來錯降甘雨,違了天條,臣該死也。我王是真龍,臣是假龍,真龍必可救假龍。”唐王曰:“吾怎救你?”龍曰:“臣罪正該丞相魏征來日午時斷罪。”唐王曰:“事若干魏征,須教你無事。”龍拜謝去了。天子覺來,卻是一夢。次日,設朝,宣尉遲敬德總管上殿曰:“夜來朕得一夢,夢見涇河龍來告寡人道:‘因錯行了雨,違了天條,該丞相魏征斷罪。’朕許救之。朕欲今日于后宮宣丞相與朕下棋一日,須直到晚乃出,此龍必可免災。”敬德曰:“所言是矣。”乃宣魏征至。帝曰:“召卿無事,朕欲與卿下棋一日。”唐王故遲延下著,將近午,忽然魏相閉目籠睛,寂然不動。至未時,卻醒。帝曰:“卿為何?”魏征曰:“臣暗風疾發(fā),陛下恕臣不敬之罪。”又對帝下棋。未至三著,聽得長安市上百姓喧鬧異常。帝問:“何為?”近臣所奏:“千步廊南,十字街頭,云端吊下一只龍來,因此百姓喧鬧。”帝問魏征曰:“怎生來?”魏征曰:“陛下不問,臣不敢言。涇河龍違天獲罪,奉玉帝圣旨令臣斬之。臣若不從,臣罪與龍無異矣。臣適來合眼一霎,斬了此龍。”正喚作魏征斬了涇河龍。唐皇曰:“本欲救之,豈期有此!”遂罷棋。” [3] 而《樸通事諺解》作為朝鮮人學習漢語的教科書 [4],其間所敘《西游記》故事,是以對話加注釋的方式出現(xiàn)的,對話敘述情節(jié),注釋說明背景。對話與注釋所引皆非古本《西游記》原文,相對而言,對話中的語言可能更接近古本《西游記》原文風格。其中敘述得較完整的唯“車遲國斗圣”的故事。先敘道人伯眼大仙,被車遲國王拜為國師,并煽惑國王毀佛崇道。唐僧到達時,伯眼大仙們正在做羅天大醮,被孫行者奪吃了祭星茶果還打了兩鐵棒。于是伯眼要唐僧與他當著國王的面斗圣,一決輸贏,拜強者為師。于是有下面“斗圣”場面: 伯眼道:“起頭坐靜,第二柜中猜物,第三滾油洗澡,第四割頭再接。“說罷,打一聲鐘響,各上禪床坐定,分毫不動,但動的便算輸。大仙徒弟名鹿皮,拔下一根頭發(fā),變作狗蚤,唐僧耳門后咬,要動禪。孫行者是個胡孫,見那狗蚤,便拿下來嗑了。他卻拔下一根毛衣,變做假行者,靠師傅立著,他走到金水河里,和將一塊青泥來,大仙鼻凹里放了,變做青母蝎,脊背上咬一口,大仙叫一聲,跳下床來。王道:“唐僧得勝了。”又叫兩個宮娥,抬過一個紅漆柜子來,前面放下,兩個猜里面有甚么。皇后暗使一個宮娥,說與先生柜中有一顆桃。孫行者變做個焦苗蟲兒,飛入柜中,把桃肉都吃了,只留下桃核,出來說與師傅。王說:“今番著唐僧先猜。”三藏說:“是一個桃核。”皇后大笑:“猜不著了!”大仙說:“是一顆桃。”著將軍開柜看,卻是桃核,先生又輸了。鹿皮對大仙說:“咱如今燒起油鍋,人去洗澡。”鹿皮先脫下衣服,入鍋里。王喝采的其間,孫行者念一聲“唵”字,山神土地鬼神都來了。行者教千里眼、順風耳等兩個鬼,油鍋兩邊看著,先生待要出來,拿著肩膀日侯在里面。鹿皮熱當不的,腳踏鍋邊待要出來,被鬼們當住出不來,就油鍋里死了。王見多時不出時:“莫不死了么?”教將軍看。將軍使金鉤子,搭出個亂骨頭的先生。孫行者說:“我如今入去洗澡。”脫下衣裳,打一個跟頭,跳入油中,才待洗澡,卻早不見了。王說:“將軍你搭去,行者敢死了也!”將軍用鉤子搭去。行者變做五寸來大的胡孫,左邊搭右邊躲,右邊搭左邊去,百般搭不著。將軍奏道:“行者油煎的肉都沒了。”唐僧見了啼哭。行者聽了跳出來,叫:“大王有肥棗么?與我洗頭。”眾人喝采:“佛家贏了也!”孫行者把他的頭,先割下來。血瀝瀝的腔子立地,頭落在地上,行者用手把頭提起,接在脖項上依舊了。伯眼大仙也割下頭來,待要接,行者念金頭揭地、銀頭揭地、波羅僧揭地之后變做大黑狗,把先生的頭拖將去,先生變做老虎趕,行者直拖的王面前日侯了,不見了狗,也不見了虎,只落下一個虎頭。國王道:“元來是一個虎精,不是師傅。怎生拿出他本像?”說罷,越敬佛門,賜唐僧金錢三百貫,金缽盂一個,賜行者金錢三百貫打發(fā)了。這孫行者正是了的。那伯眼大仙那里想胡孫手里死了。古人道:“殺人一萬,自損三千。” [5] 不難看出,這段文字,近似《三國志平話》,而遠遜于《三國志通俗演義》,亦遠遜于上文所引《永樂大典》本《西游記》。但其敘述故事詳略程度,又與“夢斬涇河龍”相當。不過,即使如此,將其二者置于一處,同作為古本《西游記》來考察,實嫌勉強,其間可能有許多環(huán)節(jié)被省略。然而,在尚無文獻去填充從《樸通事諺解》本《西游記》到《永樂大典》本《西游記》的中間環(huán)節(jié)時,也只能勉強將它們扭結在一起,視之為古本《西游記》的基本形態(tài)。 這本古本《西游記》長期隱匿在歷史的帷幕之中。即使是上述兩個不怎合轍的片斷,也是晚近才被重新發(fā)現(xiàn)的。《永樂大典》中的“夢斬涇河龍”的被重新發(fā)現(xiàn),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鄭振鐸發(fā)表于1933年的《西游記的演化》說: 原來,在北平圖書館所收藏的許多傳抄本永樂大典中,有一本第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九卷的,是送字韻的一部分,在許多“夢”的條文中,有一條是 魏征夢斬涇河龍。 引書標題作“西游記”,文字全是白話,其為小說無疑。誰能猜想到,殘存的永樂大典一冊之中,竟會有西游記小說的殘文存在呢?在吳承恩之前,果有一部古本的西游記小說!魯迅先生的論點是很強固的被證實了。這一條,雖不過一千二百余字,卻是如何的重要,如何的足令中國小說研究者雀躍不已! [6]
注釋: [1] 虞集《西游記序》,原載清世德堂刊本《西游真?zhèn)鳌肪硎祝挥忠娭煲恍染帯段饔斡涃Y料匯編》第64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版。按,朱一玄等編《西游記資料匯編》中州書畫社1983年7月版未收虞序;朱一玄編《明清小說資料匯編》齊魯書社1990年2月版始收虞序。劉蔭柏《西游記研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版也收了虞序。 [2] 明成祖朱棣《永樂大典序》,轉見張忱石《永樂大典史話》第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3月版。 [3] 《夢斬涇河龍》,《永樂大典》卷1319送字韻夢字類,(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 [4] [5] 《樸通事諺解》,《奎章閣叢書》第八種,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昭和十八年(1943)影印本;又朝鮮亞細亞文化社編《老乞大·樸通事諺解》1973年版朝漢文對照本。(朝鮮)李聃《樸通事諺解序》:“蓋漢語之行于國中者,有《老乞大》,有《樸通事》,所謂《輯覽》,即匯二冊要語而注釋者。自得是本,窒者通、疑者解,不啻若醒之呼寐,燭之遇幽。”可見其于朝鮮傳授漢語之功。 [6] [8] 鄭振鐸《西游記的演化》,《文學》一卷四號。又見劉蔭伯編《西游記研究資料》第62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版。 [7] [9] [14]趙景深《談〈西游記平話〉殘文》,《文匯報》1961年7月8日第3版。 [10] 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第4冊第93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2月版;蘇興《西游記及明清小說研究》第10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11] 參見劉蔭柏《〈西游記〉與元明清寶卷》,《文獻》1987年第4期。 [12] [13]胡適跋《銷釋真空寶卷》,《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5卷第3號(民國20年5—6月)。 [15] 郁博文《瓷枕與〈西游記〉》,《光明日報》1973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