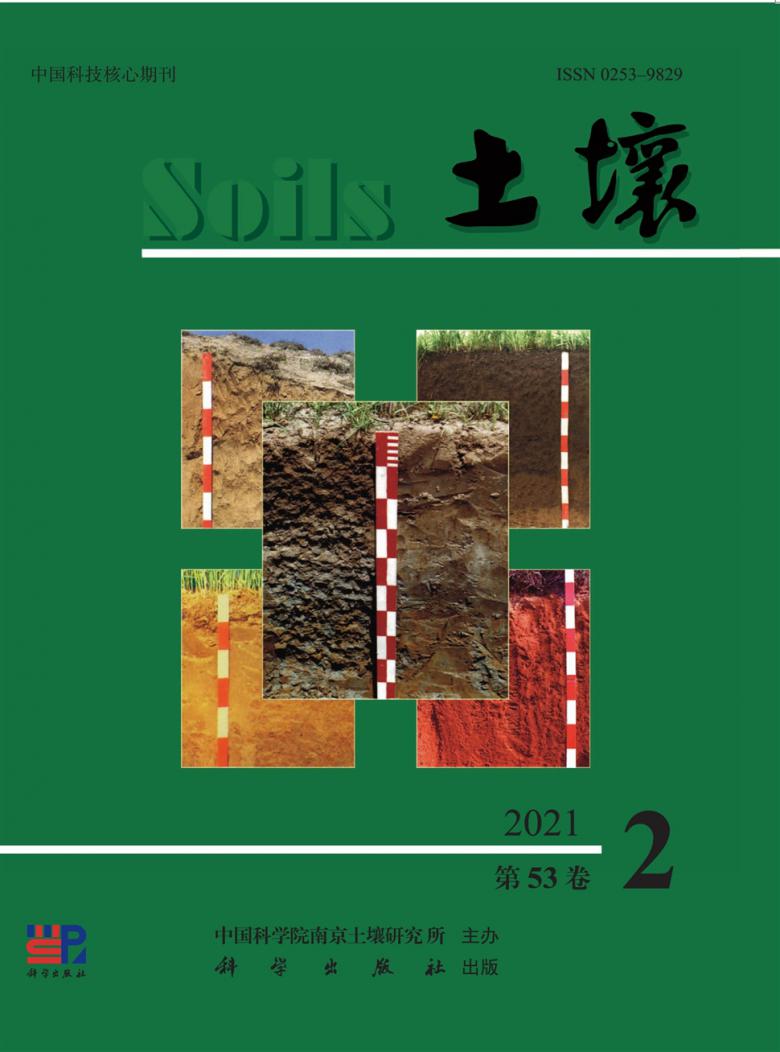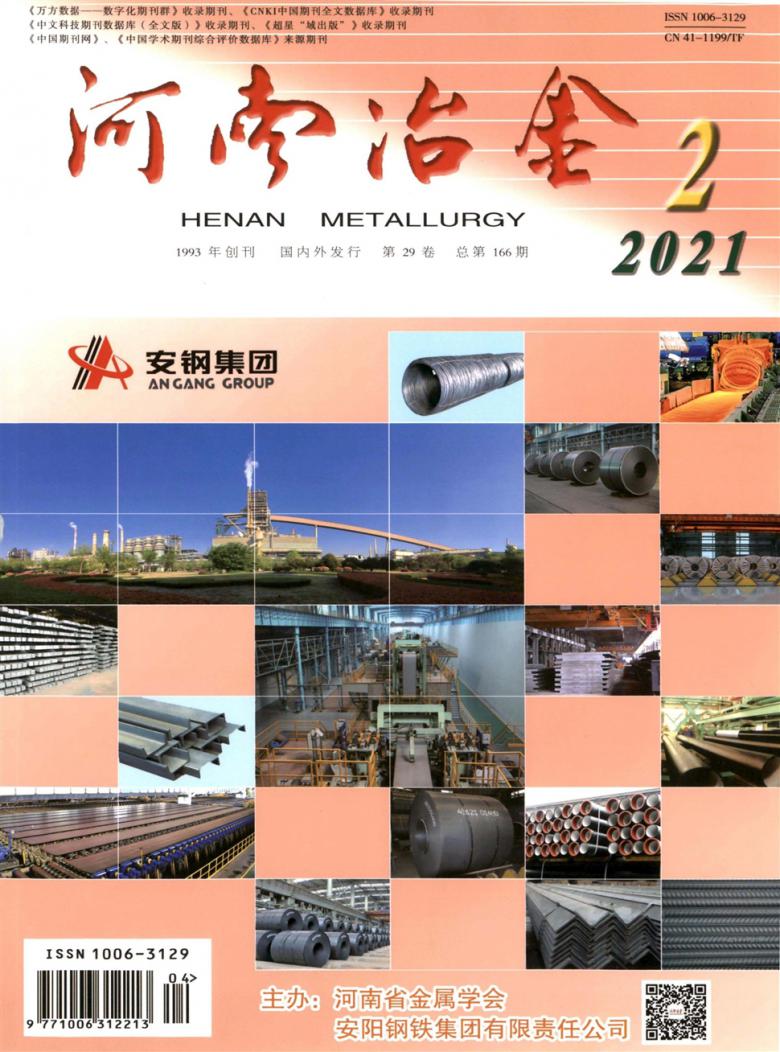地理語言學和衡山南岳350個村子高密度的方言地理研究
彭澤潤
1.地理語言學和歷史語言學
地理語言學和歷史語言學是分別首先從空間和時間兩個角度對語言進行研究的科學。正如時間和空間總是聯系在一起,歷史語言學和地理語言學也總是聯系在一起。相對來說,歷史語言學發展得比較充份。
如果說歷史語言學是一種時間語言學,那么地理語言學就是一種空間語言學。地理語言學糾正了歷史語言學過份重視歷史材料的偏向,彌補了歷史歷史材料缺乏的局限,加強了對活語言或者口語的重視和利用。應該說“共時語言學”,就是研究語言空間的,但是,一般局限在特定時間的特定空間抽象出來的單一系統,或者幾個這樣的現代單一系統的比較。所以我們不僅要看到“歷史語言學”和“共時語言學”的對立統一關系,而且要看到“歷史語言學”和“地理語言學”的對立統一關系。
日本學者巖田禮《漢語方言“祖父”“外祖父”稱謂的地理分布》在《中國語文》1995年第3期發表,文章的副標題就是《方言地理學在歷史語言學研究中上的作用》。
給語言或者方言的歷史關系分類,實際上也是在對它們進行一定程度的空間關系的分類,因為一定共同的空間分布往往有一定共同的時間歷史關系。但是它們又往往出現不少例外。例如印度在亞洲,卻跟歐洲許多語言有密切關系。衡山其實在湘語包圍中,古代全濁聲母的變化卻既不像湘語也不像有與湖南有歷史移民關系的贛語,卻像覆蓋在湖南南部“土話”方言上面構成雙方言格局的西南官話。
如果沒有主次關系地從時間和空間關系得出一個綜合類型,那會帶來許多交叉重疊的麻煩,實際上沒有嚴格區分開來。例如,“是否保存濁音”就是一個不一定可靠的標準,因為一方面,濁音分為音位性和音素性兩種,一方面,濁音是一個不穩定音素。
“是否濁音”,對于許多方言不是音位性特征;相反,“是否送氣”是漢語方言共同的音位性特征。所以,雖然從衡山的后山話來看,這兩個特征都有音位性,可以用來跟前山話區分,但是放在湖南甚至更大范圍內考察,就只有“是否送氣”這個普遍特征的發展差異才具有比較價值。
如果根據一定特征,把方言分成不同區域,然后對不同方言進行內部比較,就會畫地為牢,忽視相同行政管理空間的不同方言的相互關系。只有首先從地理語言學角度,不管方言類型,用地圖表現相同語言單位的事實,才能發現更多的實質關系。
從6.3和6.4的論述,結合長沙話演變的歷史記錄(鮑厚星,2002),說明無論前后鼻音的混淆還是前后舌尖元音的混淆,都說明湖南不少方言這些語音系統特征在100前以前還跟北京話沒有什么不同,但是在語言消磨過程中,它們在逐漸走向簡化,偏僻或者人口穩定地區比發達或者人口不穩定地區變化慢。
所以,無論從遠離長沙市區的湘潭、衡山,還是從接近市區的長沙市郊區的空間變化事實,都可以幫助我們深入認識漢語方言的歷史變化。這是彌補漢語缺乏系統細致的歷史記錄的重要途徑。當然,“方言地圖只能推測各種形式的新舊關系,也就是說相對年代。要確定一個詞產生的絕對年代,我們還需要把方言地圖和文獻資料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巖田禮,1995)
2.地理語言學的歷史和類型
“地理語言學”是《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1982)第4個部分的標題。但是目前多數人習慣叫做“語言地理學”或者“方言地理學”(袁家驊等,1983,p.12)。因為它作為語言學領域的術語,應該是運用地理科學方法和成果研究語言的科學,屬于語言學,所以,我們建議仿照“歷史語言學”、“共時語言學”、“結構主義語言學”等術語,叫做“地理語言學”。否則,把“語言地理學”放在現代語言學分支類型的術語中,顯得不協調,好像它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在《人文地理學》(王恩泉等,2000)中就把“語言地理”當做跟“政治地理”、“旅游地理”、“宗教地理”等并列的。
地理語言學是19世紀80年代在歐洲興起的。1876-1881年德國語言學家最早運用這種方法繪制了有“同語線(同言線)”的6幅德國方言地圖。以后,法國、意大利等國家都有了相關成果。例如法國在1902到1909年出版了《法國語言地圖集》。
1934年上海申報館出版的《中華民國新地圖》有一幅“語言區域圖”,是中國第一幅語言地圖,由當時的中央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提供。當時的中央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一個重要成果是1948年出版的《湖北方言調查報告》,里面有66幅方言地圖。類似調查成果后來帶到臺灣由楊時逢研究整體出版了云南(1969年)、湖南(1974年)和四川(1984年)3個省的漢語方言調查報告。當時的中央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學者白滌洲1933年開始調查,他去世以后由俞世長整理在1954年由中國科學院出版的《關中方言調查報告》,有23幅地圖,涉及陜西關中42個縣級地點的材料。
20世紀50年代,為了配合普通話推廣進行了全國性的方言普查,不少調查研究成果繪制了方言地圖。例如江蘇和上海的有43幅,福建的有51幅。
中國學者丁聲樹、李榮等1959年開始調查,1960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昌黎方言志》,有地圖12幅,涉及193個村級地點的方言特點。葉祥岑1978年開始調查,1981年在日本出版的《蘇州方言地圖集》,有地圖51幅,涉及263個村級地點的材料。這些是到現在為止對一個縣級行政區域進行調查地點最多的地理語言學成果。
但是對材料從理論角度進行比較和分析不夠。
20世紀末期出版的方言成果地圖豐富的首先是有里程碑意義的1987-1989年出版的《中國語言地圖集》。它用地圖的方式,根據重要特征進行概括以后對中國不同語言和漢語的不同方言進行了大致的空間劃分,就是分區。
另外詹伯慧、張日升等研究廣東珠江三角洲和廣東西部,侯精一、溫端等研究山西,鮑明煒等研究江蘇等方言成果使用不少地圖。例如1998年鮑明煒主編的《江蘇省志方言志》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著作刊登了54幅描寫一個省的各個縣的方言特征地圖。
除了大集體協作研究以外,不少學者個人或者小集體也使用地圖研究方言。例如,劉村漢在《方言》1985年第4期發表《廣西蒙山語言圖說》,用了6幅地圖。錢曾怡帶領合作者多次使用這種研究方法發表成果(錢曾怡,2002年)。1991年錢曾怡、曹志耘和羅福滕在《方言》第3期合作發表論文,為了體現一個縣內部的語音差異,對山東省平度縣進行了59個地點的地理研究,畫成6幅方言特征地圖。
2002年曹志耘《南部吳語語音研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本著作除了使用大量表格表現方言特征的空間差異,也使用了一些方言特征地圖。
外國學者對中國地理語言學做出了重要貢獻。比利時學者賀登崧(W.Grootaers)(1911-1999)利用在中國傳教的機會采用地理語言學方法研究漢語方言和民俗文化。他1943-1945年在《華裔學志》發表《中國語言學及民俗學之地理的研究》。他的漢語地理語言學成果集中在巖田禮等編譯的《論中國方言地理學》(中國の方言地理學のために),(東京:好文出版,1994)。石汝杰先生發表《漢語方言地理學的優良教科書——評介賀登崧<論中國方言地理學>》(石汝杰,1997)介紹,并且已經把它翻譯成漢語叫做《漢語方言地理學》(賀登崧2003)出版。
日本學者對漢語地理研究也有貢獻。例如,巖田禮《中國江蘇安徽上海省一市境內親屬稱謂詞的地理分布》(《開篇》單刊,東京:好文出版,1989)《漢語方言“祖父”“外祖父”稱謂的地理分布》(《中國語文》1995年第3期)。橋本萬太郎《語言地理類型學》(余志鴻翻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中國學者王輔世是賀登崧的學生,在1949-1950年撰寫了碩士論文《宣化方言地圖》(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研究所出版,1994年),但是他后來主要研究少數民族語言。
一般的漢語方言研究跟地理語言學有密切關系。但是方言地圖有兩種,也體現出地理語言學的兩種方法:第一,根據一定特征對方言材料地點進行分類,例如《蘇州方言地圖集》;第二,根據重要特征對一定連續空間進行區域分割,例如《中國語言地圖集》。
總之,地理語言學有分區和分類的不同又有聯系的研究方法。對一個地點的語言或者方言內部系統做準確的描寫和分析是地理語言學的基礎。但是漢語方言研究從分類的地理語言學角度對一定特征進行高密度的地理空間研究的成果比較缺乏。像巖田禮一樣不僅用地圖分類,而且進行理論分析的成果更加少。要高密度研究漢語方言地理不能首先貪圖全國范圍,因為范圍越大工作數量,無法細致。所以要從小范圍打基礎,“小片方言的方言地圖或者地圖集應當多多出版”(陳章太等,2001)。
3.湖南的語言地理
湖南在中國的中南部。湖南的地理特征除了北部有洞庭湖平原地帶,其余主要是丘陵地帶。北部邊界有長江,跟湖北和四川交界;東部邊界有羅宵山脈,跟江西交界;南部邊界有南嶺山脈,跟廣東和廣西交界;西部有雪峰山脈跟貴州(高原地帶)、重慶和四川交界。
湖南秦朝以前的民族成份是“蠻”、“越”。秦朝以后的主要民族成員是河南等北方地區移民的漢族。
秦朝到宋朝有3次因為戰亂形成的南北移民浪潮:第一次在東漢末年,北方漢族從北方跨越長江到南方,準確地說是東南方,進行大規模移民,開始形成南方漢語。第二次在唐朝末年,北方漢族向南方移民,加速南方漢語方言的分化和成熟。第三次,在宋朝末年。從此,除了少數山區,中國東南各地的主要民族成份都是漢族。(李如龍,2001,p.20)
湖南在經歷以上北方到南方的漢語移民以后,后來又經歷了從東方到西方的漢族移民。
元朝末期到明朝初期,因為戰爭導致的“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大移民,湖南的主要民族成份是來自東方的江西以及江蘇、浙江的漢族。(李永明,2001,p.10)
湖南的現代漢語方言就是在這樣先后經歷兩個大方向的漢族移民以后形成的。南北方向的移民,特別是距離現在最近的南北移民和北方官員和士兵的流動,不僅形成了洞庭湖平原地帶的比較典型的西南官話,而且在湖南南部南嶺山脈地帶,由于不同湖南“土話”體系密集,不方便溝通,所以形成作為區域共同語的具有不同程度湘語特色的各種西南官話,從而使湖南南部出現雙方言格局。湖南西部個別偏僻區域也保留這種“土話”,例如沅陵邊界的“鄉話”。
東西方向的移民不僅普遍使湖南方言跟贛語(或者客家話)的關系更加密切,而且湖南東部尤其是東北部的羅宵山脈區域形成狹長的贛語(或者客家話)地帶,在湖南西南偏向中間的雪峰山脈區域的隆回和洞口形成贛語方言島,贛語特色非常明顯的新化也在這個區域。
當然這兩個方向的移民產生的作用,有的是綜合的。但是,不管什么作用,有一個共同特點:交通方便和交往頻繁的地區變化最快,也最不容易被新層次的方言特點完全覆蓋。
例如,洞庭湖平原地域交通比山區方便,加上歷史上為了開發洞庭湖平原的農業進行的局部移民,就被西南官話完全覆蓋了。相反,湖南南部和西部即使由于作為漢語“土話”和少數民語語言使用者的共同語的交際需要,引進了西南官話,但是不僅仍然在不同偏僻農村保存了“土話”,而且它們的西南官話具有明顯的“土話”痕跡。
長沙、衡陽、株洲、湘潭等湖南的大城市,明顯比它們周圍的農村發展速度快,而且長沙市又比湘潭市快。方言歷史資料證明長沙市區方言現在的塞擦音和擦音沒有舌尖前和舌尖后的區分,但是100年以前有這種區分,而且這種區分在周圍的農村和周圍的城市湘潭、寧鄉仍然保存。同時,這些大城市作為湖南歷代交往活動的中心,它們具有共同的湘語特征,沒有一個被贛語或者官話或者其他方言完全或者大部份同化。
衡山作為中國五大名山,當然是歷代旅游勝地,即使古代全濁聲母的演變跟周圍方言格格不入,類似西南官話,但是由于它的位置在湖南中心地帶,所以,它在許多方面保留了周圍典型湘語的特點。
如果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向中原漢族區域侵略或者移民,導致中原漢族向南方移民,同時導致南方少數民族向偏僻地區移民;那么,可以認為當漢語向湖南范圍中的中心區域滲透的時候,原來分布在這些區域的少數民族語言被擠到了偏僻山區。所以,湖南的少數民族語言集中分布在西部和南部的山區。不僅有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洲,還有懷化市管轄的麻陽、芷江、靖州、通道4個少數民族自治縣,邵陽市管轄的城步1個少數民族自治縣,永州市管轄的江華1個少數民族自治縣。
湖南省在20世紀末期已經出版了幾十個地點的系統的方言研究專著,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詹伯慧,2000),但是方言地理研究還相當薄弱。2001年出版的《湖南省志方言志》也缺乏地圖。
4.從衡山和南岳方言看地理語言學的語言理論價值
地理語言學使人們認識語言變化規律的眼界寬廣了,給我們提供了活生生的自然語言變化事實。但是要防止走任何片面的極端。下面結合我對湖南省的衡山縣和衡陽市南岳區的350個村子進行高密度地毯式調查研究的結果,提出要正確處理以下在語言理論上的關系。
(1)縣城做方言代表地點的優勢和局限
一般對一個省進行方言地理研究的時候,把縣城作為代表地點。這樣可以在相對有限的對象中盡快獲得結果。但是正如方言分區和省行政劃分不一定一致,一個省內部的方言分區也不一定跟縣行政劃分一致。衡山縣的方言情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衡山南岳漢語方言大致可以根據南岳衡山這座大山作為自然界線,分為前山話和后山話兩種系統類型非常不同的方言。
我們從地理上對它們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調查,畫成方言地圖,從語音上討論了它們的分布、分界、過渡、相互接觸,以及它們跟周圍方言的關系,它們在湘語中的地位等。
現代湘語是湖南的第一大漢語方言,古代是全濁的現代塞、塞擦聲母,無論濁音和清音是否對立,無論出現在平聲還是仄聲中,一般都不送氣,也就是不跟發音部位相同的次清聲母混合。現代官話是湖南第二大方言,古代是全濁的現代塞、塞擦聲母一般是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在這兩大方言中,只有湘語中的新化等方言,官話中的芷江、會同等方言例外:它們一般都送氣,具有明顯的贛語特征。
從古代全濁聲母今天讀塞、塞擦聲母,而且不論平聲和仄聲都不送氣的情況來看,后山話跟周圍的衡陽、湘潭、長沙等方言一致,具有湘語的一般特點。由于同時伴隨濁音,在從清入合流到陽平的結果中構成清濁對立,跟臨近屬于湘語清濁對立類型的雙峰方言一致。
然而,在現代前山話中,古代是全濁的現代塞、塞擦聲母,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跟湖南官話的演變規律一致,成為湘語區域中的一種特殊情況。
從聲調類型和入聲歸屬以及入聲調值來看,前山話比較接近長沙、湘潭方言;后山話比較接近雙峰方言。從陰平、陰去聲調的調值特征來看,前山話仍然比較接近長沙、湘潭方言;后山話卻比較接近衡陽方言。
從古代[知章見]組聲母現在多讀塞音的特征來看,前山話和后山話有共同特點,而且跟雙峰、寧鄉等方言一致。從后山話塞擦聲母分舌尖前和舌尖后而前山話不分的特征來看,后山話跟雙峰、湘潭方言一致,前山話跟長沙話、衡陽話一致。
從古代咸、山攝開三、四等韻母現在多讀鼻化“i”的特征來看,前山話和后山話有共同特點,而且跟雙峰方言一致。
從“跑”這個詞的情況來看,前山話叫“打飛腳”,跟雙峰、長沙等方言一致;后山話叫“蓬”(陽平聲調,跟“蹦”不同)、“打蓬咕子”,跟周圍方言都不一樣,也不像新化、邵陽等方言叫“走”。但是,前山話又用“蓬”表示牛“跑”,體現與后山話的深層關系。
從上面的主要特征的比較可見,由于方言是語言使用者在時間和空間變動的雙重作用下形成的,方言分區和分類是非常復雜的。我們可以根據不同需要選擇不同標準,根據不同標準可以得出不同的分區和分類結果。語音特征的系統性最強,永遠是給方言分區和分類的重要標準。
從地理上考察,前山話和后山話之間以及它們各自的內部有逐漸變化也有突然變化,有相對穩定的大區域,也有多變化的區域。在兩種方言交界的時候,既形成了聲調系統邊界清楚的突然過渡區域,又形成了這個區域兩邊在其他個別因素上邊界模糊的逐漸過渡的區域。
南岳山東南部和西北部為什么分別使用兩種方言?南岳衡山作為天然屏障制約了它南邊的前山話和北邊的后山話密切聯系,雖然行政上的整體性可以部份抵消一些制約程度。前山話在南岳山的南邊,延續到湘江中游的兩邊包括衡東縣的絕大部分地區。南岳衡山作為著名的山,作為重要的宗教活動場所,加上明朝到清朝衡山南岳社會安定,很少發生戰爭,就不斷吸引了江西等地方的人到這里定居。湘江是歷史上最好的交通渠道。在這種情況下,湘江兩邊的前山話成為在古代全濁聲母現代特征上與周圍的湘語很不一樣的方言島嶼,就可以得到一定的解釋:可能是在交通方便和人口流動的作用下,通過移民形成的。然而,后山話區域被四周與湘潭、雙峰、衡陽交界的高山隔離,是湘江的支流涓水流經的上游區域,交通比較閉塞,因而更多保留了跟周圍湘語一致的特點。當然湘江也成為前山話細微區別的界線,衡山區域內的涓水下游也成為后山話和過渡區域的夾山腔之間的界線。
衡山作為中國五大名山之一,當然是歷代旅游勝地,即使古代全濁聲母的演變跟周圍方言格格不入,類似西南官話,但是由于它的位置在湖南中心地帶,所以它在許多方面保留了周圍典型湘語的特點。
(2)語言分區和分類的辯證關系
我們在繼續研究分區的同時,加強分類地理研究。
方言分區只是在地理空間上劃分一個大致范圍,往往受到一定的行政劃分的局限。一個區域內部的特殊性很容易“被不適當夸大”。一個區域的方言不能籠統地說跟哪個區域的方言有特別關系,必須“跟周邊的方言逐一進行比較”才能說明區域內部不同局部跟不同方言的明顯關系。(張振興,2000)這種地理空間的比較,就打破了宏觀分區的局限。我們的調查表明,不僅衡山縣內部前山話和后山話會相互影響,而且周邊的衡陽、雙峰、湘潭等縣的方言會在邊界交通方便的一定范圍互相影響。所以方言和方言之間似乎像鏈條一樣連接,有界限又沒有界限,在重疊中分離,在穩定中變化。
從對歷史語言學的貢獻來看,“一般地說,方言地圖展示的區域越大,地圖能夠挖掘的歷史越深。”“微觀的地圖只能闡明在短暫時間內發生的語言變化”。(巖田禮,1995年)
“調查的方言越多,方言點越密,繪制的方言地圖就越準確,方言地圖的標示,反映的方言及其特征的情況就越可靠,越有價值。”(陳章太等,2001)
我們既需要大范圍的宏觀地理語言學研究,也需要小范圍的地毯式的微觀地理語言學研究,這樣才能提高宏觀考察的可靠性,避免遺漏重要細節,尤其是偏僻地區的細節。語言特征空間細節的揭示,不僅能夠全面體現變化的過程,而且能夠給方言分區提供更加具體的條件。根據共同特征的多少,可以多層次地進行方言分區。
在中國由于特征分類的地理語言學發展相對慢,所以一方面應該加強縣級范圍的高密度的特征分類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另一方面應該加強整體性的特征分類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在進行大范圍地理語言學研究的時候,不能忽視城市以外的重要細節,只停留在各個城市地點之間的比較和分類。代表性地點的系統研究是這種地毯式的空間比較研究的基礎。如果沒有前期關于衡山的前山話和后山話的研究成果,我們要在短期內進行地毯式地理研究,可能難以確定方向,會出現大海撈針的局面。應該說漢語方言研究經過20世紀的努力,基本上具備了進行大規模地理語言學研究的基礎。
地理語言學中的分區和分類是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種研究方法。對一個地點的語言或者方言內部系統做準確的描寫和分析是地理語言學的基礎。但是漢語方言研究從分類的地理語言學角度對一定特征進行高密度的地理空間研究的成果比較缺乏。像巖田禮一樣不僅用地圖分類,而且進行理論分析的成果更加少。要高密度研究漢語方言地理不能首先貪圖全國范圍,因為范圍越大工作越無法細致。所以要從小范圍打基礎,“小片方言的方言地圖或者地圖集應當多多出版”(陳章太等,2001)。
(3)語言界線的相對性和絕對性的辯證關系
《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1982)用兩個相似的小標題強調:“方言沒有自然的界線”,“語言沒有自然的界線”。這當然是正確的,因為語言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現象。但是,這并不影響我們對方言和語言存在相對界線的認識。索緒爾(1982,p.285)自己也說:“然而從一種語言突然過渡到另一種語言是常見的”,“例如斯拉夫語和日耳曼語的界線,我們就可以看到有一種沒有任何過渡的突然的飛躍。”同樣,我們在前山話和后山話的界線上,既可以看到有“夾山腔”過渡區域的北部界線,也可以看到沒有過渡區域的南部界線。
(4)語言共性和個性的辯證關系
我們不能過份強調不同語言或者方言的個性。
用地理語言學的方法畫出來的地圖,可能都不一樣,似乎讓人不能看到方言的界限。有人甚至認為只有一個特征的分區,沒有整個體系的分區。其實,有的同語線或者同語線的有的部份只是代表個別現象,不能作為劃分方言的依據。(袁家驊等,1983,p.12)例如,在衡山縣東北邊界的嶺坡和福田鋪兩個鄉交界的區域“酒”和“九”同音(參看地圖10),似乎屬于后山話,但是這種個別語音現象不影響它在整體上屬于前山話,因此這一段同語線在宏觀上應該忽視。
(5)語言發展的突然性和逐漸性的辯證關系
我們不能過份強調語言或者方言變化的逐漸性。
對比不同同語線可能發現這些線條不是非常集中的。雖然這樣可以糾正歷史語言學中迷信語言突然分裂的傾向,但是可能導致有人認為變化只有逐漸性,沒有界線的片面觀點。其實正如社會變化是逐漸的,但是遇到戰爭和大改革,社會就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突然變化,語言也是這樣。在地理空間上,可能會由于自然地理和社會行政管轄范圍的不同,出現突然的變化。例如,作為山名稱的衡山成為前山話和后山話的突然空間變化的分界線。但是在衡山縣東北部衡山山脈走勢平緩的區域,就出現了一個逐漸過渡的區域。然而這個過渡區域的兩邊也有比較明確的界線。
(6)語言的任意性和理據性的辨證關系
我們不能過分強調語言的理據性。
一般認為無論語言變化中存在多少程度的理據性,但是語言的形式和內容的關系在本質上是任意的。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有人為了強調理據性,就說任意性是錯誤的,這樣就會牽強附會找規律。也有人為了強調任意性,就可能導致對語言規律的忽視。例如,我們可以發現在后山話向前山話過渡的區域,不少語素的聲調常常違背自己系統的規律,采用對方聲調類型對應的調值。但是我們又發現在比較穩定的“夾山腔”過渡區域,有一個聲調比較整齊地接受了另外一方的陰平調值。可以這樣來解釋:變化可能是從沒有秩序地進行個別現象的吸收開始的。這種當初的“錯誤”可能會經過系統類推和優化,使一種錯誤像滾雪球一樣壯大,有規律性地成為新的正確標準。衡山的“夾山腔”的聲調系統(參看地圖1),可能就是在后山話的基礎上,由于前山話的影響開始出現少數讀陰平的語素的調值從[55]降低到[33],然后逐漸變成集體現象。
(7)語言變化的規律性和例外性的辯證關系
我們不能過份強調語言變化像數學公式一樣整齊有規律。
語言變化確實受到人的生理條件以及自然和社會條件的種種制約,并且形成一定的規律。但是,不能排除一些偶然或者無法發現的原因導致面目全非的變化。
例如,一般“娘”無論從古代音韻地位還是現代方言事實來看,幾乎都是鼻音聲母,[i]開頭的韻母。只有廣州話和前山話等例外,是拼合開口呼韻母。音質跟前山話幾乎完全一樣的耒陽話、常寧話和后山話也是拼合齊齒呼韻母,但是前山話確實拼合的是開口韻母,雖然研究衡山話多年的毛秉生曾經肯定(毛秉生,1983,1985),后來又否定,認為還是拼合齊齒呼(毛秉生,1988,1995)。前山話和后山話的“娘”的聲母雖然都是舌面前鼻音,但是前山話不能拼合齊齒呼韻母,后山話只能拼寫[i]開頭的齊齒呼韻母(參看地圖85)。當然它們無論是否實際拼合齊齒呼韻母,都不會發生齊齒呼和開口呼的對立,因為凡是在北京話中[n]拼合開口呼和合口呼韻母的單位,聲母幾乎一律變成[l]。那么后山話讀[ni]音質的“泥你日義”等語素前山話的[i]怎么辦?前山話的[i]這時鼻化,同時聲母從舌面前變化成舌尖,讀[n]。經過系統的特殊調整,就保證了衡山前山話舌面前塞音和鼻音不拼合齊齒呼和撮口呼,只能拼合開口呼和合口呼的格局。
(8)語言變化的條件性和磨損性的關系
我們不能過份強調語言演變的條件性。
一般我們認為語言變化有外部的社會條件,也有內部的系統矛盾的調節。這是對的。但是,如果過份強調它,就難以解釋衡山南岳方言中“知道”(參看地圖66)的后面一個音節的變化為什么這么豐富。當然仔細觀察,多數是在[ti]的音質基礎上變化,[t]可以變成邊音[l],[i]可以鼻化,聲調也有不同變化。這個語素跟“知”的古代音韻地位比較一致,可能是“知”的各種語素變體。從語法上看,這個“知”的功能同普通話做補語標記的結構助詞“得”,例如“要[ti]”、“做[ti]好”等。這樣解釋可以照顧一批現象。應該說這個常見的口語的詞會保持穩定,但是由于是多音節的詞,而且它在音節的后面,人們很容易淡化它的發音,從而產生模糊的音響效果,導致在流傳過程中容易產生磨損出現偏差。由于方言缺乏書面規范的可能,更加容易導致這種內部歷代流傳的誤差。因此,語言變化中,在缺乏規范約束力量的情況下,錯誤或者模糊流傳是語言變化的一個重要途徑。
(9)語音形式和作為語言實體的詞匯和語法的關系
不僅單純的語音考察要建立在詞匯的基礎上,而且有特征的詞匯和語法現象的空間分布,是方言分類和分區的重要條件。例如,文讀和白讀跟詞匯的選擇密切相關。如果從漢字出發很容易被文讀誤導,不能發現方言底層的本質特征。即使是詞,還要看是固有的還是借用的。例如“跑”是一個詞,如果只是拿這個詞去記錄衡山方言的發音,就有點像用普通話說“的士”。這樣既會混淆前山話和后山話的區別,又不能體現方言詞匯的實質。其實,表示普通話“跑”這個意思的詞語,前山話是一個固定詞組“打飛腳”,后山話是“蓬”或者“打蓬牯子”(參看地圖73)。表示“門檻”的詞前山話叫做“門探”,后山話叫做“地方”。“地方”成為后山話的一個重要特征詞,而且它的分布非常集中和穩定,跟語音上的參差變異完全不一樣。(參看地圖90)
詞匯還可以挖掘不少文化現象。例如前山話說“芹菜”,后山話為什么說“富菜”?(參看地圖43)用“富菜”代替“芹菜”在湘潭話等方言中也有。這是語言形式和內容的矛盾產生的文化效應。后山話和湘潭話等一樣,“芹”和“窮”同音。使用芹菜一般用來炒肉,以前只有過節日和做喜事才有肉吃。所以,在生活不富裕,迷信思想比較重的舊時代,為了回避“窮菜”產生不吉利的聽覺誤解,只好回避這個聲音。
(10)語言個體變化和系統制約的關系
無論語言形式還是語言內容的變化,都要接受系統的整體需要的制約。
“不能把方言和語言看成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民族共同語也不是各種方言的總和”。(錢曾怡,2002,p.1)這就是說,無論普通話還是各種方言,系統本質是一樣的,都是漢語的一種系統的體現。
從語音形式來看,無論我們前面討論的輔音發音部位和方法的變化,還是元音舌位的高低前后的變化,都是在系統制約下,像雪山崩塌一樣發生的連鎖反應。而且這種連鎖反應,在一定情況下會出現難以跨越的距離。例如,雙唇和唇齒部位可以相互轉化,形成“嘴唇”大陸,舌尖和各個舌面部位可以相互轉化,形成“舌頭”大陸,但是這兩個大陸之間除了擦音,相對難以相互轉換。
在衡山前山話里,用“爹爹”指“父親”,用“公公”指“爺爺”,在長沙話里“爹爹”指“爺爺”,“爺爺(/爺)”指“爸爸”,雖然它們的詞指稱的客觀對象單獨看來不僅相互之間有矛盾,而且跟北京話的“爺爺”和“爹(爸爸)”部分或者全部相反,但是并不妨礙長沙話對客觀對象的區分。
長沙話也可以用“公公”和“爹爹”分別表示“爺爺”和“奶奶”。那么長沙話兩個“爹爹”是否有矛盾沖突呢?從漢字看來當然沖突,但是從口語看來沒有沖突,因為聲音不同。表示“爺爺”的是“[tia33tia33](爹爹)”,表示“爸爸”的是“[tie33tie33](爹爹)”。這就是語言的系統性。
同樣,前山話表示“跑”的“蓬”由于專門用于牛等一般動物,所以表示人“跑”就用“打飛腳”表示。從語法結構來看,“打飛腳”跟北京話的“跑”還是不一樣。例如,北京話說“抓到的賊跑了”,衡山話不能用“打飛腳”直接替換“跑”,只能說“逮到的賊走估噠”。這說明“走”在古代表示“跑”的意思的殘留痕跡。但是由于其實“走”跟現代北京話的用法基本一致,所以不能感覺“逮到的賊走估噠”中的“走”有明顯的“跑”的意思。為什么?在這里只需要表示“逃脫”的意思,用“跑”還是“走”的方式逃脫沒有對立性,可以任意選擇一個語義變體。
語法規則也一樣。一個動詞涉及兩個受事對象的時候,表示人(R)和表示物體(W)的受事位置關系在漢語各個方言中,會出現3種格局的選擇:AB,BA,AB/BA.(邢福義,2000)。如果集中格局并存,往往有一種強使格式。例如,普通話“打(D)不(B)贏(Y)他(T)”在衡山的方言中有3中格式:DTBY,DBYT,DBTY.其中第一種最常見,第三種前山話比后山話更加少見。(毛秉生,1996)
(11)同音詞的系統性質和語言自我化解障礙的能力
我們經常容易不分時間和空間系統差異,錯誤地夸大漢語同音詞的數量和語言使用的消極性。其實,任何語言及其方言都有一定的同音詞,但是絕對不會多到影響信息的系統表達。由于語言變化的條件不同以及系統協調的角度不同,可能出現不同概念范疇的同音詞。例如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發現后山話區域有的地方出現“中飯(午飯)”和“蒸飯”同音,有的地方出現“生”和“三”同音。其實,“蒸飯”作為名詞一般會說“缽子飯”,與“中飯”對立的可能性小。“生”和“三”詞性不同,可以通過句子結構地位的明顯不同自然分化。可以說,特定系統中的同音詞只有在詞性不同的條件下才有機會停留下來。有人會說北京話的“是”和“事”同音,其實北京話會用“事兒”或者“事情”避免跟“是”同音。由于漢字可以區分同音語素,給人們偷懶的機會,就經常把“事兒”或者“事情”省略成“事”。這樣帶來的消極作用是不僅加大了普通話口語和書面語詞匯系統的距離,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模糊了北京話系統的真實面貌。因此,我們在方言或者語言詞匯地理空間研究中必須重視語音系統的具體事實,不能被漢字掩蓋的語音假象迷惑。
語言有一種自我化解語言障礙的能力。頻率是重要砝碼。如果兩個概念在相同語境中經常使用,然而表達它們的語言形式,無論是詞還是詞組,必然造成交際困難,語言系統必然會在人的安排下做出自我調節,實現自我化解障礙的目標。即使是漢字造成的人為障礙,也會這樣。例如由于過多依賴漢字,忽視口語,導致“期中”和“期終”不能區分。口語自然會調節成“期中”和“期末”來區分。經常使用的概念必須用詞而且是音節盡量少的詞,經常使用的詞組必然會壓縮成詞。漢語的“哥哥”和“弟弟”用詞表達,英語對應的是用詞組表達,英語的詞“brother”,可以概括漢語“哥哥”和“弟弟”兩個概念,因為漢語必須表達大小等級的觀念文化,英語不很重要。
在表示普通話“掃墓”的意義的時候,前山話用“掛墳”對應概括后山話“拜墳”和“輪墳”兩個詞。(參看地圖70)說明兩個地方的人對概念的細節認識不一樣,區分它們的詞就會進行調整,化解表達障礙。
(12)特征詞在語言分類分區中的作用
給一種語言或者方言找特征詞是最危險的,往往費力不討好。因為說特征,就是說這里有,其他地方沒有。說這里有容易,說其他地方沒有太難。但是,只要我們在一定范圍內,在一定基礎上討論,仍然應該大膽比較和討論,哪怕最后被別人否定,也是有開拓意義的。
如果在衡山這個范圍內來討論。毫無疑問,下面這些詞就是區分后山話和前山話的特征詞:表示“門檻”的“地方——門檻”(參看地圖90),表示“臉”的“臉——面”(參看地圖36),表示“翅膀”的“翼架——側架”(參看地圖40),表示“芹菜”的“富菜——芹菜”(參看地圖42),參看地圖36),表示“傾倒”的“傾(水)——垮(水)”(參看地圖64),表示“辣”的“辣——麻”(參看地圖78)。
(13)語言過渡區域和語言混合的關系
什么空間會出現過渡區域?在交通方便,使用不同語言或者方言的人發生頻繁交往就會出現。過渡區域又是根據離開核心方言的距離遠近呈現階梯形式的級別。即使在典型的邊界位置,也會有兩種成分在混合中保留程度的不同。在衡山的“夾山腔”中,很明顯是后山話成分占主要地位,也就是強勢方言前山話引起后山話變化。在階梯邊緣靠近前山話區域也會出現前山話受到后山話的影響,但是這個影響比較弱。
在“夾山腔”中,經常出現一個概念用前山話和后山話兩種表達形式的現象。這當然與他們經常接觸兩種方言有關系。因此,語言的混合可能有兩種。
(1)穩定類型:A+B=Ab,aB
(2)不穩定類型:A+B=A(/a)b(/B),a(/A)B(/b)
夾山腔屬于不穩定類型。如果這個區域的人群由于行政或者自然條件,使他們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群體,就可能促使他們在不同的詞語中做出選擇,有的可能選擇了來自前山話的,有的可能選擇了來自后山話的。這樣就形成了穩定的混合方言。
5.結束
如果說歷史語言學是一種時間語言學,那么地理語言學就是一種空間語言學。
有時候“方言區劃與古代行政區劃的聯系不很密切,倒是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更為密切。”(謝伯端2000)地理語言學不僅給解釋語言發展提供了重要途徑,而且糾正了歷史語言學過份重視歷史材料的偏向,彌補了歷史材料缺乏的局限,加強了對活語言或者口語的重視和利用。地理語言學使人們認識語言變化規律的眼界寬廣了,給我們提供了活生生的自然語言變化事實。
[1]鮑厚星,顏森.湖南方言的分區[J].北京:方言,1986,(4).
[2]鮑厚星等.長沙方言研究[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3]鮑厚星.《湘音檢字》與長沙方言[J].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學報,2002,(4).
[4]鮑明煒等.江蘇省志方言志[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5]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漢語方言詞匯[M].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
[6]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漢語方音字匯[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7]曹志耘.南部吳語語音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8]陳暉.漣源方言研究[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9]陳章太,詹伯慧,伍巍.漢語方言地圖的繪制[J].北京:方言,2001,(3).
[10]儲澤祥.邵陽方言研究[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1]崔振華.益陽方言研究[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2]河北省昌黎縣縣志編纂委員會,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昌黎方言志[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
[13]賀凱林.溆浦方言研究[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14]賀登崧[比利時].漢語方言地理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15]衡山縣志編委會.衡山縣志[M].長沙:岳麓書社,1994.
[16]湖南省公安廳.湖南漢語方音字匯[M].長沙:岳麓書社,1993.
[17]江灝.長沙方言去聲字的文白異調[J].北京:中國語文,1981,(2).
[18]李如龍.漢語方言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9]李維琦.祁陽方言研究[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0]李永明.衡陽方言[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1]李永明等.湖南省志方言志[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2]羅昕如.新化方言研究[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3]毛秉生.衡山方音簡析[J].湘潭:湘潭大學學報.1983,(增刊)
[24]毛秉生.衡山方音舌面前塞音聲母考[J].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學報,1985,(增刊).
[25]毛秉生.方言[A].衡東縣志[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2.
[26]毛秉生.方言[A].衡山縣志[M].長沙:岳麓書社,1996.
[27]毛秉生.湖南衡山方言音系[J].北京:方言,1995,(2).
[28]彭逢澍.湘方言考釋[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29]彭建國,彭澤潤.湖南湘潭茶恩寺方言音系[A].彭澤潤,王開揚主編.語言文學文化[C].長沙:中南大學出版社,2003.
[30]彭澤潤.方言[A].零陵縣志[M].中國社會出版社,1992.
[31]彭澤潤.衡山方言研究[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32]彭澤潤.衡山方言舌面前塞音的組合能力和演變趨勢[A].湖湘文化論集[C].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33]彭澤潤.湖南宜章大地嶺土話的語音特點[J].北京:方言,2002,(3).
[34]彭澤潤.湖南宜章大地嶺土話(的幾個現象)研究[J].長沙:湖南社會科學,2003,(1).
[35]錢曾怡.漢語方言研究的方法與實踐[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36]橋本萬太郎[日本].余志鴻(翻譯).語言地理類型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37]石汝杰.漢語方言地理學的優良教科書——評介賀登崧《論中國方言地理學》[J].北京:國外語言學,1997,(1).
[38]索緒爾[瑞士].高名凱(翻譯).普通語言學教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39]唐作藩.音韻學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40]汪化云.自主的輕聲和非自主的輕聲[J].太原:語文研究,2003,(1).
[41]王本瑛.湘南土話的比較研究[D].臺北:國立清華大學,1997.
[42]王恩泉等.人文地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3]王福堂.漢語方言的語音演變和層次[M].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
[44]王曦.衡山縣馬跡話調查報告[A].粱宋平等.湖南省第二屆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45]吳啟主.常寧方言研究[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46]葉祥岑.蘇州方言地圖集[M].東京(日本):龍溪書舍,1981.
[47]謝伯端.再論湘西漢語方言語音特征及分區[A].盛興華等.語言論叢[C].長沙:岳麓書社,2000.
[48]邢福義.小句中樞說的方言實證[J].北京:方言,2000,(4).
[49]徐通鏘.歷史語言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50]巖田禮.漢語方言“祖父”“外祖父”稱謂的地理分布[J].北京:中國語文,1995,(3).
[51]袁家驊等.漢語方言概要(第2版)[M].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52]曾毓美.湘潭話音檔[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53]曾毓美.湘潭方言語法研究[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1.
[54]詹伯慧.20年來漢語方言研究述評[J].北京:方言,2000,(4).
[55]張振興.閩語及其周邊方言[J].北京:方言,2000,(2).
[56]趙元任.語言問題[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57]鄭慶君.常德方言研究[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58]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中國語言地圖集[M].香港:朗文遠東出版有限公司,1987-1989.
[59]鐘奇.湘語的音韻特征[A].詹伯慧等.暨南大學漢語方言學博士研究生學術論文集[C].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