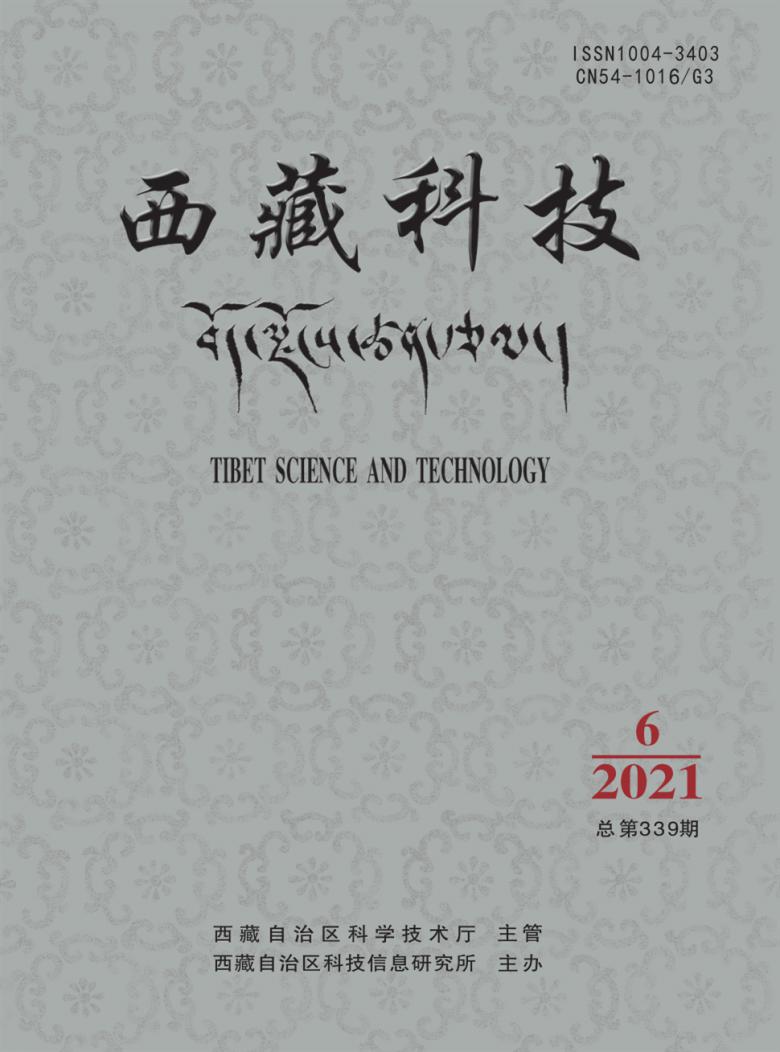殖民語境中魯迅與馬華文學
鄒賢堯
【摘 要 題】臺港澳與海外華人文學
【正 文】 按新加坡文學史家方修的界定,馬華新文學就是接受中國五四文化運動影響,在馬來亞(包括新加坡、婆羅洲)地區出現的,以馬來亞地區為主體,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華文白話文學;淵源于中國新文學,同屬于語文系統,但在其發展中,又漸漸獨立于中國文學之外,自成一個系統。這個界定從發生學的角度,傳遞給我們一個信息:中國五四新文學對馬華文學產生了一種“形成性影響”。資料表明,也可以直接說是事實表明,在中國新文學經典對馬華新文學的影響當中,又以魯迅為最:馬來亞作家韓山元(章翰)的觀點具有代表性:“魯迅是對馬華文藝影響最大、最深、最廣的中國現代文學家……”(注:韓山元:《魯迅與馬華新文學》,新加坡風華出版社,1977年版,第1頁。);在馬來亞廣泛流傳著一個小冊子《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全是歌頌魯迅如何偉大的;魯迅的作品作為經典被新馬作家最大程度地摹仿、移植,單是《阿Q正傳》就有上十個摹寫本、改寫本; 魯迅的雜文在新馬被極度推崇,成為一種主導性寫作潮流;新馬作家、學者方修、趙戎、高潮、方北方等論述文學問題處處以魯迅為依據;魯迅逝世后新馬文化界對他的悼念,是新馬追悼一位作家最隆重、最莊嚴、空前絕后的一次……問題是,為什么對馬華文學產生巨大影響或說馬華文學最多接受的,是魯迅而不是別人,不是郭沫若、茅盾、巴金,不是在新馬呆過的老舍、郁達夫……?文學影響經過的路線是:放送者,媒介者,接受者。從“放送者”考察,魯迅是新文學的奠基人,也是中國新文學中聲名最大的,直接淵源于中國新文學的馬華文學自是對這新文學的“奠基人”和聲名卓著者有特別的關注;魯迅作品本身的藝術感召力又自有其向馬華文壇的巨大輻射力。從“媒介者”考察,一如新加坡學者王潤華所述,魯迅“以左翼文人的領袖形象被移居新馬的文化人用來宣揚與推展左派文學思潮。除了左派文人、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愛國華僑都盡了最大努力去塑造魯迅的英雄形象。”(注:王潤華:《華文后殖民文學——中國、東南亞個案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頁。)接著的問題是,也就是從“接受者”考察,為什么新馬左派文人對魯迅的更多“非文學性”的宣傳會激起那么大的響應?王潤華論述道:“共產黨在新馬殖民社會里,為了塑造一個代表左翼人士的崇拜偶像,他們采用中國的模式,要拿出一個文學家來作為膜拜的對象,這樣這個英雄才能被英國殖民主義政府接受。魯迅是一個很理想的偶像和旗幟。”這段話啟示我把問題放到殖民語境中去考察。面對殖民主義者,面對強權,馬華文學自覺承擔起啟蒙與救亡的雙重使命,而魯迅恰恰被左派文人塑造成這樣一個以文學來進行啟蒙與救亡的民族英雄,從而進入新馬文化人的“期待視野”。
一、殖民語境中對前驅作家的獨特選擇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半殖民地”是指在國際關系中,一個或一些國家在與其他國家交往中主權所處的半獨立的地位。部分的國家主權受制于他國。“在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財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屬關系的羅網包圍著。”(注:《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8頁。)帝國主義列強向中國多次舉行侵略戰爭,打敗中國后,強迫訂立不平等條約,中國就“在形式上獨立”,而政治經濟等都嚴重“受制于”列強。生活在這種半殖民地處境中的青年魯迅,高揚“我以我血薦軒轅”,其志不在文學,而在科學救國,轉而以醫學強國民之體,最后才落實到以文學變國民之心。也就是說,魯迅自己對文學的選擇,不是或主要不是基于對文學的興趣,也不是或主要不是基于生性中的文學稟賦,而是或主要是在于當時的他認定文藝更能改變人的精神,從而“立人”,從而進行民族自救。 魯迅具體的創作是外國作品推動的,一如他自己所說,寫小說“所仰仗的全是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而魯迅對外國作品的選擇,不大以藝術性的高低來取舍,而注重挑選那些反映被壓迫民族和弱小國家人民苦難命運的作品來閱讀和介紹,他曾說:“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干諸小國作家的東西特別多。”(注:《南腔北調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又在《雜憶》里說:“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復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應。 那時我記得的人, 還有波蘭復仇的詩人 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愛國詩人Pet fisandor;飛獵濱的文人而為西班牙政府所殺的厘沙路。”進入從文之初的魯迅視野的、對魯迅的創作構成“形成性影響”的外國前驅作家,并非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等等,而是俄國的契訶夫、果戈理,挪威的易卜生,匈牙利的裴多菲,乃至算不上經典的波蘭的顯克微支,菲律賓的黎薩爾等。這些國家、這些國家的作家、這些作家的作品,對被壓迫被奴役的苦難的反映,對民族命運的憂思,對爭取獨立富強的心聲的抒發等等,正好滿足了半殖民地魯迅的情感訴求。 同樣的情況出現在新馬作家對魯迅的接受上。1819年1月25日, 英國軍官萊佛士在新加坡河口登陸后,新馬便淪為英國殖民地。馬來亞在1958年獨立,新加坡拖延到1965年才擺脫殖民統治。馬華新文學正是在這種殖民語境中生成。面對殖民統治,馬華文學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精神上的父親”,來以文學作武器抵抗強權,這個文學上的又是精神意志上的“父親”被塑造出來,這就是魯迅。 許多論者都已指出,馬華文學對魯迅的接受,有一個“形象轉變”的過程。20年代的新馬文壇響應大陸的“革命文學”,批判魯迅“落伍”。1930年,《星洲日報》副刊發表一位署名“陵”的作者寫的《文藝的方向》,說道:“我覺得十余年來,中國的文壇上,還只見幾個很熟悉的人,把持著首席。魯迅、郁達夫一類的老作家,還沒有失去了青年們信仰的重心。這簡直是十年來中國的文藝,絕對沒有能向前一步的鐵證。”(注:陵:《文藝的方向》,《星洲日報·野葩》(副刊)1930年3月19日;又見方修編《馬華新文學大系》1冊。) 然后轉折出現了,1929年前后,創造社、太陽社停止對魯迅的攻擊,1930年“左聯”成立,魯迅成為領導人,于是他在新馬的形象來了個大轉變:不再是落后的甚至“反動的”,也不只是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的重要作家,而是一個左派的、反資產階級的、屬于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的作家。這個“形象轉變過程”即體現了馬華文壇對魯迅的選擇更多地不是出于藝術的訴求,而是出于“革命”的訴求。拒絕與接受,批判與大肆宣傳,都存在著對魯迅的嚴重“誤讀”,都有過多的政治闡釋。事實上,可以這樣說,對魯迅的批判,是嫌這個文學與意志上的“父親”不夠有“革命”的力量;對魯迅的推崇,是魯迅在中國成了左翼領導人,是因為這個“父親”成了強有力的“革命”的父親。 移居新馬的左派作家張天白(丘康)稱魯迅是“偉大的民族英雄”與“中國文壇文學之父”;新加坡作家方修稱頌魯迅為“青年導師”、“新中國的圣人”,甚至引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話論證魯迅就是“具有最高道德品質的人”;馬來亞作家韓山元,著《魯迅與馬華新文藝》,宣稱:“魯迅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在新馬社會運動的各條戰線,魯迅的影響也是巨大和深遠的……魯迅的著作,充滿了反帝反殖反封建精神……對于進行反殖反封建的馬來亞人民是極大的鼓舞和啟發,是馬來亞人民爭取民主與自由的銳利思想武器。”……魯迅就是這樣被塑造成戰士、巨人、導師、反殖反封的民族英雄進入新馬。“魯迅作為一個經典作家,被人從中國移植過來,是要學他反殖民、反舊文化,徹底革命”,“要利用魯迅來實現本地的政治目標:推翻英殖民地。”這就是殖民語境中馬華文學對前驅作家的獨特選擇,突出思想政治功能而并不突出藝術功能,重政治的革命的身份和形象(民族英雄、戰士)超過對文學身份和形象的看重。
二、殖民語境中的特定主題
可以說,殖民語境中的兩個主題詞是“啟蒙”與“救亡”,兩者并不構成對立。比如在魯迅那里,就統一于他的“立人”思想。怎樣“立人”?靠啟蒙;“立人”后怎樣?救亡,以立國。即是魯迅所謂“救國之道,首在立人”。又統一于他的“遵命”而“吶喊”的文學觀,吶喊是為喚醒沉睡的國民,承擔啟蒙的功能;吶喊以慰藉戰斗的勇士,承擔救亡的功能。 這種文藝觀被殖民地新馬文壇移植過來。在魯迅還沒有被新馬“正式接受”之前,他的作品已傳入南洋,他的文藝觀已在那里得到認同與響應。1926年4月, 一家華文周刊《星光》雜志上,發表了南奎的文章《本刊今后的態度》,寫道:“我們深愿盡我們力之所能地掃除黑暗,創造光明。我們還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決不是登高一呼,萬山響應的英雄,只不過在這赤道上的星光下,不甘寂寞,不愿寂寞,忍不住的吶喊幾聲‘光明!光明!’倘若這微弱的呼聲,不幸而驚醒了沉睡人們的好夢,我們只要求他們不要唾罵,不要驅逐我們,沉睡者自沉睡,吶喊者自吶喊……”(注:南奎:《本刊今后的態度》,《星光》1926年4月。)大到觀念,小到造句、用詞,都明顯有魯迅《吶喊·自序》的影子。這樣的文藝觀對文學的主題表達以一定的規約,“驚醒沉睡的人們”,是為“啟蒙”,所謂“沉睡者自沉睡”不過是憤激之詞;“掃除黑暗,創造光明……忍不住吶喊”,在殖民語境里即是“救亡”。從而,文學的主題主要就不是抽象的愛與死、情與仇,甚至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具體的“慘淡的人生”和“改變”這人生;不是休閑甚至不是“雅致”,而是“吶喊”與“戰斗”。 殖民地新馬作家由于有著和魯迅相同的情感和精神的訴求,在閱讀和借鑒魯迅作品時,首先就在主題和內容上獲得共鳴,很快“認同”了魯迅對國民劣根性的解剖,對被奴役的處境的揭示,以及其所承擔的啟蒙、“立人”與“救國”。然后他們對之加以“消化變形”,力求以富于自己新馬特色的文學形式“表現”出來。各種南洋版的《阿Q正傳》、吐虹的《“美是大”阿Q別傳》、丁翼的《阿Q外傳》、 林萬菁的《阿Q正傳》、李龍的再世阿Q……在對魯迅的《阿Q 正傳》加以“消化”后,又“變形”為殖民者統治下南洋國民的“精神勝利”的獨特“行狀”:一是拜金,“美是大”阿Q、再世阿Q等都千方百計地撈錢;二是逐色,丁翼筆下的阿Q“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天是躺在布床上一面摸女人的大腿,一面吞其黑米”;三是忘祖,都反對學華語,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四是崇洋,如“美是大”阿Q以“惡馬劣根”(American)自居。魯迅的《阿Q正傳》已透露出殖民主義者與本地封建主合謀,構成對人民的掠奪——投靠洋人的假洋鬼子與趙太爺勾結,共同剝削雇農阿Q。馬華文學的“阿Q”將這一點充分放大,暴露出殖民主義統治下, 新馬社會拜金主義盛行,殖民文化打壓華文、摧殘華族文化,崇尚洋文化,從而導致拜金、忘祖、崇洋等南洋特質的“國民性”。正是經由類似的移植、變形、放大,馬華文學呼應和延續著魯迅的主題,在殖民語境中頑強書寫著啟蒙與救亡。
三、殖民語境中的藝術偏好
殖民地新馬文學在接受中國新文學時,表現出特定的文學思潮傾向,即特別青睞現實主義的思潮及作家。從1919年10月前后馬華新文學運動興起開始,文學工作者的興趣就主要集中在現實主義方面,幾乎全部模仿學習五四新文學中現實主義流派的作品,以魯迅的作品、文學研究會作家的作品為主要對象。方修在《馬華文學的主流——現實主義的發展》中說:“馬華文學創作的主要傾向,一開始就是現實主義的,盡管幾十年來新馬文學運動有時高漲,有時低沉,但現實主義精神卻始終貫穿著戰前新馬的文學史,體現在所有重要的作品里,成了文學創作的主流,從未間斷過。”然后他又進一步認為,只有魯迅的作品是舊現實主義中最高一級的徹底的批判的現實主義,只有魯迅的作品達到這個高度。另一位作家,馬來西亞的方北方,即使在20世紀80年代論述馬華文學時,也處處以魯迅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為最高的典范與模式。這些事實這些論斷說明,馬華文學在對中國新文學的諸種思潮進行篩選后,主要選擇的是現實主義,又主要是魯迅的現實主義。 一種文學思潮只有在相對適宜的精神氣氛中才能得到相對充分的移植和發展。殖民主義殘酷統治下的新馬,沒有適宜浪漫主義文學生長的精神氣氛,因此一是遲至1925年7月15日(而現實主義早在1919 年即傳入)創刊的《新國民日報》文藝副刊《南風》上,才由一位來自中國的喜愛浪漫主義的移民作者“拓哥”第一次介紹五四新文學中以郭沫若為代表的浪漫主義;二是浪漫主義文學在新馬雖也形成一定的氣候,但其勢頭還是遠不如現實主義的創作。現代主義從哲學、文化的高度對生活進行把握,它有意地將生活變形,與生活拉開距離,它在殖民地新馬也沒有適宜的土壤,致力于救亡圖存的新馬文化人無暇去對人生進行過多的抽象思辨,他們需要貼近現實的“地面”。于是,自覺承擔反帝反殖、啟蒙救亡的馬華文學,與注重客觀寫實的現實主義思潮相遇,與中國新文學現實主義的經典魯迅相遇。 殖民地新馬文學在接受中國新文學經典時,還表現出特定的體裁偏好,尤其體現在對魯迅雜文的特別關注與推崇:“雜文,這種魯迅所一手創造的文藝匕首,已被我們的一般作者所普遍掌握……即一般較有現實內容,較有思想骨力而又生動活潑的政論散文,也是多少采取了魯迅雜文底批判精神和評判方式的。在《馬華新文學大系》的《理論批評二集》中,有許多短小精悍的理論批評文章基本上都可以說是魯迅式底的雜文……在《馬華新文學大系》的《散文集》中,則更有不少雜文的基本內容是和魯迅雜文一脈相承的……”與雜文被推崇,成為一種主導性的寫作潮流相對,寫抒情感傷的散文被認為是一種墮落,寫閑適幽默的小品文遭到大罵。古月寫雜文《關于徐志摩的死》,批判新月派的感傷文風;丘康作《關于批判幽默作風的說明》,將林語堂的文藝觀斥為“墮落”。富于現實感富于戰斗性的雜文受到禮遇,感傷類閑適類的散文受到冷遇,這可以用魯迅自己的話來解釋個中緣由:“在風沙撲面,狼虎成群的時候,誰還有這許多閑功夫來賞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呢?”(注:《魯迅全集》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441、443頁。)在特定的殖民語境中對雜文的戰斗性的強調,對閑適類小品的批判是必要的、合理的。前者更具有對現實的清醒度,更真切地觸摸了存在之痛。 四、殖民語境中的文學民族性訴求
一個復雜的情況是,魯迅是激進地反傳統的,在文學資源和創作方面,他甚至主張“少看——或竟不看中國書,而多看外國書”(17) 他的作品的歐化現象也確實很重,從結構到意象到造句。三四十年代“民族形式之爭”時,魯迅所代表的五四傳統是以民族傳統的對立面出現而被一部分人竭力捍衛的。但另一方面,魯迅的作品又極具民族性地方性,他筆下的人物——孔乙己、祥林嫂、七斤、華老栓乃至揭示出了精神勝利法這一“普遍”人性的阿Q,都打上鮮明的厚重的本土的烙印。阿Q,絕對是那個“未莊”的阿Q。魯迅作品洋溢著濃郁的江南風情,包含著深厚的越文化底蘊。即就藝術形式而言,魯迅的講究白描,在行動、對話在動態的描寫中刻畫人物性格、心理,包括《阿Q正傳》對傳統說書體的反諷式的模擬,都分明有“民族形式”的要素。以致我們在說“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時,常常以魯迅為例。 魯迅是一個極其豐富的存在,他在接受外國文學資源時其實同時又在抗拒,他對外國文學經典既吸收、借鑒,又誤讀、偏離,以彰顯自己的獨特性,而與西方經典抗衡;他以徹底“反傳統”的面目出現,但半殖民地魯迅又分明有著本能的民族文化自衛心理。他反的是傳統的積弊,是禮教的“吃人”。在“反”的同時明明又有“樹”,“破”時明明又有“立”。他樹大禹、墨子等是“中國的脊梁”,在著名的《拿來主義》里極深入極理性地主張對傳統文化要“拿來”,批判中分明有繼承。 馬華文壇是將魯迅主要作為“反帝反殖的民族英雄”引進的,正如前面所述,他們樹立魯迅的偶像,是為實現其政治目的:推翻英殖民統治。馬華人力圖以民族主義為基礎來抵抗殖民文化。反映到他們的文學創作里,就是有著明確的民族性訴求,自覺追求作品的地方特色,著力營構一種“民族寓言”。 在半殖民地魯迅的作品里,“未莊”是辛亥革命后中國的一個縮影,《藥》里上演了華、夏兩家也即是華夏民族的深重悲劇,七斤的辮子風波是近代中國農民命運的濃縮……深受魯迅影響的殖民地馬華文學,找到了它營構“民族寓言”的獨特載體:橡膠樹。橡膠樹把華人移民及其他民族在馬來半島的生活遭遇呈現出來,把西方資本主義者與大英帝國通過海外移民、海盜式搶劫、奴隸販賣的罪行揭示出來,把殖民地官員與商人進行壓迫和資本輸出的殘忍勾當暴露出來。浪花的小說《生活的鎖鏈》是建構“民族寓言”的代表性文本。在下著雨的、寒風刺骨的橡膠園,一個化學工程師兼督工的紅毛人趁一位膠工的女兒來借錢為母親治病時,將她奸污。陰森黑暗的膠園,呈現的是當時東南亞勞工的艱苦環境;少女任洋人發泄性欲,是華人勞工任人宰割的象征,是殖民主義者強奸土著的歷史的縮影。作品內容本身即已顯示出強烈的反帝反殖傾向。作品鮮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寓言”的營構,又以其自覺的文學民族性訴求來反抗殖民主義的強勢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