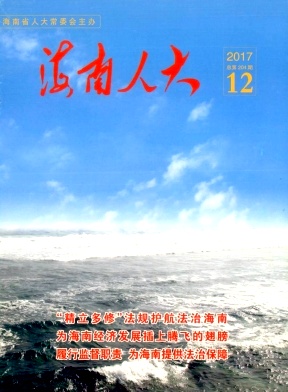臺灣散文概述
蔡江珍
一 臺灣文學界多年來以它的各項文學獎,不僅使文學在媚俗的文化情境中仍堅持一種抗拒姿態,而且直接推動文學新生代的成長。雖然,近年來,幾大報的主要獎項在極力鼓勵藝術創新的同時,越來越多獲獎作品讓人“完全看不懂也讀不下去”,臺灣學者、清華大學教授呂正惠認為這些作品不是“浮而不實的‘使命文學’,就是只在文字上花功夫的‘后現代文學’。這些當代作家都只在‘耍’什么,而不是在‘思考’什么,在‘寫’什么……”〔1〕但,文學獎仍是每個年度中文學的盛會,更是新生代作家一展才華之良機。 《中國時報》的時報文學獎1996年散文甄選首獎為張啟疆的《失聰者》,寫一個失聰的,促使作為父親的“我”在悲傷中不斷反思,從個體出發走向人性的關懷,“透過這樣的反思,作者才不致一味陷溺于情緒,而能以理性打開克服生命之孤絕的曙光。”〔2〕“失聰者”在作者的反思下不僅指涉一個實在的個體,“而是隱喻了更多心靈絕緣的人們”。該文融匯感性描寫與知性思考,語言細致、流暢而凝重。散文評審獎為王威智的《遺址通知》,這是一篇少年成長故事,以兒童的嬉戲引發來自于死亡印象的對生命底秘的參悟;文中不論是扮演死人入棺的游戲還是對“爺爺”腐敗尸身和生前難堪的生活描寫,都刻意用諷世且無情的筆調,而作者的巧思和用心隱藏其中。 1996年聯合報文學獎第一名得主為柯嘉智,作品《答問》,該文以獨白的方式寫成長的過程和人生的迷惘,“所有青春期的癥狀、孤獨、恐懼、寂寞,甚至對同性戀的向往,生理變化帶動心靈的掙扎,都寫得很深入。”〔3〕第二名為陳建志的《萬寶堂之火》,雖然文中的描寫平淡無奇,甚至有過分平鋪之嫌,但作者試圖在一種喻象的描繪中藉一場火災表現出臺灣的文化與歷史“被外來勢力焊接”的狀況,顯其獨特的入視角。第三名為鄭立明的《畫個一》和張啟疆的《安寧病房》同獲;前文從“一”展開聯想,構思新穎,從夸父逐日開始,寫出地平線在人類精神生活中的寓意,“水平線浮在現實與夢想之間。”因為它通往遠方,因為它最初和最終限制人類的視線,而具有了神秘的力量;隨著歷史文明的發展(比如飛機的發明),人類脫離了“那條線”,也就迷失了自己,今天人類在困惑中再回來找人的道路、人的定位……該文從抽象的概念出發寫出了豐富的內蘊,雖然展開聯想的轉換有時顯得突兀,但思想上有一定深度,在藝術表現上亦有較獨到的魅力。后文則緊扣“生死之間”展開意象,筆調沉穩,自成一格,顯示了較強的文字駕馭力,是一篇在評選中得分較低但評委一致認為“不得獎有點可惜”之作。 1997年的時報與聯合報文學獎散文類首獎得主均為馬來西亞藉的鐘怡雯,分別為《垂釣睡眠》和《給時間的戰帖》;前文以綿密的文字寫失眠,雖是俗常小事,卻因作者巧妙的比喻和幽默的描述而見新意,比如說睡眠是蹺家迷路的壞小孩,作者要想盡辦法哄誘垂釣……該文在層遞的情境描寫中,不只寫出暗夜的動靜,同時傳達了失眠者的浮躁暴怒,充滿語趣。后文寫一位老人用勤練書法來對杭時間以挽留他的時代,既有出新之處也顯其刻意,但文中對書法內蘊的文化及人生韻味的領悟,頗為深刻。 該年時報散文獎的評審獎為簡捷的《一天中的印象》,從自然景物(光和色彩)的轉換來表現一天時間的流動,并藉此來寫自然光景的變化和內心的想望,顯得自然流暢,文字很簡練恬淡,但也較少堪以回味的深層意涵。而聯合報的散文第二名為鄭景中的《變身》、第三名為邱惠珠的《國民用藥手冊》。《變身》是以與自己對話的方式,在追憶童年中寫成長的寂寞,這是在卡通片中成長的一代,在“美少女戰士”的“變身”中沉迷的一代,作者說這樣長大的“我們也有我們的童年”。評委簡媜認為作者“正圖跳脫繁重的現實枷鎖,回到純真和友誼都還沒有變質的年代……”〔4〕楊牧則“真切地看到作者那種類似鄉愁的失落的童年”。〔5〕應該說這是一篇文字的裝飾性較突出,而藝術感染力未必甚佳之作。《國民用藥手冊》體現了作者對中國民間用藥的了解,將文字與各種藥方結合,以中國人屯藥、用藥的“焦慮”中表現對老、對生死的焦慮,隱隱關涉著更深層的國民性問題。 此外,尚有梁實秋文學獎、《明道文藝》學生文學獎、鹽分地帶文學獎等獎項中的散文獎得主也多為新生代作者,其中鐘怡雯、唐捐、張啟疆、王威智、吳鈞堯等人,或一人囊括幾種獎項的散文獎,或在多種文類上獲過獎,他們的寫作雖然不是起步于文學獎,但文學獎為他們的成長打開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而以散文寫作的宏觀成就贈獎的吳魯芹散文獎第13屆(1996)和第14屆(1997)分別頒給了藝術品格與思想深度都更加沉穩的中年作家黃碧端和蔣勛。 黃碧端是“以委婉密實的文風及清晰論理的反思魅力”獲獎的,得獎散文集為《期待一個城市》等,雖然她筆下所談的問題也是“島上文化人士所熟悉的、所抱怨的、所引以為憾的、所贊譽的、所引以為榮的,”〔6〕但她的獨到之處在于不論揭發社會病象、還是警策人生,總用一種期待的筆調,冷眼看世界時保留了一份溫情,正如臺灣作家周志文所言:“黃碧端無疑也有她的冷眼和熱情,冷眼使她遇事不會過激,而熱情使她對一個也許十分傖俗、十分無望的城市也充滿期待。”因此,“她的文字表面看來相當平和,可以說是溫文儒雅,但后頭的力道卻是沉雄的。”〔7〕 蔣勛的創作涉及文學、戲劇、美學、繪畫諸領域,以其創作生命的豐沛,被譽為“博學”的創作者。在他的創作中,“繪畫對蔣勛而言是一種挽留,是對于即將消失事物的無可奈何。文學創作卻是要把事情說清楚,但是越分析說明就越要陷入生命更巨大的空虛和荒蕪中。”〔8〕當他以散文集《島嶼獨白》獲得1997年吳魯芹散文獎時,他自況“這是寫給孤獨者的書”,是他在島嶼上的四處游走而獲得的“探索窺伺命運本身”的形式,是以日記、信件等似小說似散文的方式發出的心底的“獨白”。他說“我在島嶼上觀看著日出日落,潮來潮去,花開花落,觀看著星辰的移轉,觀看著生命的來去和變遷。”〔9〕在他看來,島嶼變得匆忙、急躁,迫切于答案的心,使島嶼的居民非常不快樂……而我們終其一生不過只是在玩著“瞎子摸象”的游戲……蔣勛的島嶼不只是立足之地,更是文學的島嶼、內心的島嶼。他的另一篇散文《不可思議種種》〔10〕再次讓讀者聆聽“島嶼獨白”的續言:對愛的倫理的求解、從父親病痛中讀解的肉身與人間愛的真切感、從一個雜手的不可思議之舉到人類那一張張充滿仇恨的臉、充滿貪欲的臉……作者要傳達的是人生種種“真實中仍然非常虛幻”的無可確定性。蔣勛的散文文體模糊、內蘊豐富,不僅拓展了散文的涵容量,也是對散文體式的大膽創新。 二 散文是臺灣文學名家薈萃的最大一塊綠地,不僅眾多本色散文家勤奮耕作,更得到各門類高手紛紛伸出之“左手”的援持,因此這兩年的臺灣散文在文學低谷中依然保持了較為堅實的步履。 龍應臺這兩年的筆觸,更加綿密婉轉,其層層深入的思理與利如揮劍的批判,銳氣不減當年,而文字的感染力與思想的圓熟更勝一籌。如《干杯吧,托馬斯曼》〔11〕放筆縱談流寓異國他鄉考“向日葵的心態”;雖然遷徙他鄉不見得就是放逐,但“失去語言,因而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實體,”就猶如“貧血的向日葵”……全文情思回環綿遠,語言十分圓融。又如《蘇州的識者》〔12〕則寫自己“到虎丘其實不為看風景古跡,而為了看一個文化,一個美感充沛的文化。”但卻看到“花了兩千年時間沉思琢磨而成的歷史風貌,只需要兩年的時間就可以徹底消除。”在深刻的文化思考與人文批判中也流露了一些無奈與沉痛。此外,《頑童捕蟬》〔13〕以較為素樸輕盈的文字細述孩童捕蟬,感嘆時光、生命又如何能把握丈量;《魂牽》〔14〕寫的是背尸歸鄉的感人故事,流注著濃厚的葉落歸根的深情。龍應臺這兩年散文創作的生命力十分旺盛,有大量作品見諸報刊,并出版了散文集《干杯吧,托馬斯曼》,筆端觸及文化批判、社會關懷、人生尋思,并極力印證臺灣文化與世紀交接的發展,內蘊沉潛。 余光中多年來在個人寫作之外還多做了一項“被動的文章”,那就是為人作序,于是他將所寫序言選了三十多篇,于1996年以《井然有序》為書名結集出版。他的序文并采微觀與宏觀,兼有情趣與理趣,講究氣勢與韻味,不僅被當作書評來讀,而且他序中對作家作品的評賞在臺灣文壇常起到定位作用。而他為《井然有序》寫的自序《為人作序》〔15〕更是一篇兼具辭采與文理的知性散文,文中縱談古今序文的衍變、為人作序的種種滋味,更以“證婚人”喻“寫序人”,自有余氏獅子搏兔式的深刻與幽默。他的又一篇散文《日不落家》〔16〕再次體現余氏的幽默文風。他說自己一家人分居五國,吻合現代人“地球村的感覺”,而妻子(四個女兒的母親)“曳著電線,握著聽筒,跟九千里外的女兒短話長說;正如以前妻子懷孕時用臍帶向體內腹語,不過現在“是用電纜向海外傳音”,都是母子情深的方式,因此,余光中體會到“所謂恩情,是愛加上辛苦再乘以時間,所以是有增無減,且因累積而變得深厚。”余氏散文之精警與獨具魅力的想象由此可見一斑。 楊牧定居北美十多年后回到了臺灣,他將這十年來特定時空下心神交集的體會與領悟之作于1996年結集出版,即散文集《亭午之鷹》,其筆端多涉大自然與人文世界的交感,平淡從容中更保持了對鄙陋與俗媚的抗拒姿態。如在《借來的空間里》,他說“這是一個缺少希望的時代”;在《來自雙溪》中,他自問“我會不會將半生服膺、追求、捍衛的有限真理混淆、錯亂了?”因此,他將自己“物化為一只鷹,那一只來過,然后再也沒有蹤跡的‘亭午之鷹’,因為他曾一瞥地佇足于廣漠的自然中。”〔17〕楊牧受著這浪漫情緒的驅策,不斷創作出沉湎于追尋浪漫同時凝聚著無限愁思的散文。他發表于1997年9月8日《聯合報》上的《昔我往矣》,是他回臺灣花蓮定居后喚起的童年的記憶和血脈中的鄉情的表白,他說那是一份特殊的感覺,“一直保存在感官的記憶深處,縱使到那時為止我還不知道如何具體描寫那氣味,但我能判別它,指認那氣味……”對此,他說自己可以用比喻和象征作為捕捉它并且敘述它的方式,這比喻和象征使楊牧的散文常有一種磅礴的豐美與詩性的意境。同期他亦出版了另一本散文集《下一次假如你去舊金山》。 小說家李黎這兩年中出版了兩本散文集:《晴天筆記》和《世界的回聲》。《晴天筆記》是一本親子之書,也是一本真實而美麗的心靈之書,分“感懷四簡”和“晴天筆記”兩部分。第一部分記寫喪失愛子時生命巨慟的創傷與絕望,第二部分是一個閱盡無常世事的母親對重獲新生命的希望、喜悅與反思。《世界的回聲》收作者近年的20多篇散文,分世情、人情、心情三輯,寫人、寫事、寫景、寫物,“是一個觸覺敏銳的女子關照這個世間的形形色色時,為我們收錄的聲音——經過她辨聲錄制,加入她的質地的聲音。”〔18〕 被認為文字不斷出新的簡媜,近年的散文寫作更注重體式的創新,1996年底出版的《女兒紅》是1991至1996年創作的結集,文體介乎散文與小說之間,重在探勘女性的內在世界。如《貼身暗影》,寫一位長年照看臥病在床的父親的女子“深不可測的孤獨”、在隔膜的人世中獨自掙扎的徬徨種種難以盡述的內心世界;而《肉身啟示錄》〔19〕是對現代女性在“那套女體規格化標準”下“女人的身體與心靈永遠是愚民者的殖民地”的感嘆;對女性覺醒之艱難,簡媜下筆既熱諷又深具同性的同情,當女性像流行病似地忙于減肥、塑胸時,簡媜告誠同胞“肉身是靈魂用來探險的船”,不論胖瘦,都是一尊獨一無二的肉身藝術,何不“把它當作大師最滿意的雕塑品”?簡媜這兩年的散文益發洗卻女性散文習見的柔美甜媚,而更增多了熟稔人世滄桑后的瘦硬之氣。 近五年未出書的席慕容于1996年7月出版了散文集《黃羊·玫瑰·飛魚》,這是她1990年以來的作品合集,記述了她這些年的奔波與浮沉,尤其是對原鄉——蒙古草原的深切關注。此外,席慕容從1996年1月至12月為《幼獅文藝》寫了一年的“高原札記”,1996年3月起為《皇冠》雜志寫了一年的“大雁之歌”,它們是作者對夢魂牽縈多年的原鄉——蒙古草原的觀照,雖然只是“一點點地來描繪出一些簡單的輪廓”,但對作者而言,不論是知識上的“資料”還是實地得來的經驗,都已“進入我全部的感覺系統,成為我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 舒國治也是一位將詩歌的觸角延伸至散文領域的散文家,這兩年他更頻繁地行走于臺灣大地,企圖深入而切實地探尋到他生存的這塊土地更內在的真實,他的《人生臺北》〔21〕及1996年10月在《中國時報》連載的《臺灣重游》便是這切實觀察后的體認。兩文的文字均簡潔明朗。他的另一篇作品《永遠的碧潭》〔22〕則是逸出都市觀察的清新之作,以那曾拍打過“我”和太多北部少年的渾沌胸膛的碧潭,寄寓蓬勃的生命源泉,那是“清涼,卻從不荒苦”的生命印證,是原鄉給予的滋養。如今碧潭的時代過去了,留在作者心中的是揮之不去的悵惘。 此外,張秀亞、楊青矗、隱地、陳芳明等作家更加人情練達、醇樸雅正的文字堪為這兩年臺灣散文的又一道風景。如張秀亞的《不凋的葵花》〔23〕抒寫梵高畫筆下的葵花,蘊藏著深邃的人生感念;“這金輪,這黃褐色的葵花,在生之道途上輾轉已久,好像凝聚著悲哀與歡笑,憂傷與安慰,煎熬與狂喜,在喜劇與悲劇中輪流作主角。”而揚青矗的《死皇帝與活乞丐》〔24〕言傳一種素樸而誠摯的人生秘諦,他說“活著就是人生的意義”,其價值僅是個人的認知自己而已。他的《欖仁樹》〔25〕寫欖仁樹葉從過去的習以為常到如今的身價陡增,記敘個人的一些經歷,流露些微的感觸,是一篇非常平易樸實的作品。 陳芳明的《秋天的簽名式》〔26〕則是一篇灌注著深沉的生命感念的抒情文字,一位離鄉久遠的中年男性生命浮游中在梭羅的墓前“獲得了生命的詮釋”,當他以自身的精神探觸到已經散發在花魂與樹魂之中的梭羅的生命時,他更加深刻地領悟到“人的精神枷鎖與權力束傅,往往來自內心的物欲……人在一無所有的時候,抵抗的意志必然比任何時候還來得堅強。”而隱地的《身體一艘船》〔27〕感嘆的是人生如航船載沉載浮,但自己的身體是一艘會思想的船,在航行60年的今天,不禁隨著煙塵往事,想著人在大地上的存活,想著人生的悲喜劇,想著世紀末種種光怪陸離的現象……人生的滄桑感躍然紙上,文末更有自勵勵人的勸勉,表達了對人生的執著。 杏林子的《年方九十》〔28〕寫李可染、蘇雪林、顏水龍諸位文藝界泰斗對生命不盡的歡喜和期盼,一句“年方九十”包蘊了怎樣從容、坦蕩的人生情懷,杏林子用她特有的溫馨的筆調寫出了前輩對生命的無限珍愛。而向陽的《微雨》〔29〕也是對生命的探問之作,但它用的是一種美麗而哀愁的意象:微雨,它象征著一個詩人尋找詩路的迷離人生,也吻合細細瑣瑣的中年心境;當詩人終于肯認了那記載著個人生命并與個人生命同存的聲音便是詩的聲音時,他可以在煙雨中開始生命的再出發了。高大鵬的《未完成的浪漫》〔30〕卻是為一個未完成的生命發出的“深沉的人性的嘆惋”;作者說一曲“未完成交響曲”正象征了音樂家舒伯特悲劇的一生,而刻在他墓碑上的墓志銘:“死亡在此埋葬了無比美好的天賦及美好無窮的希望!”更“道盡了世人對他未完成的生命及未完成的使命之無窮盡的惋惜與追念!”高大鵬以詩情濃郁的文筆抒寫了對生命的吟詠,他這兩年的散文更多地注入這種如詩如繪的人生感懷,情思飽滿深沉,文字柔美綿密。1996年,他獲得了以出版散文集著稱于臺灣文壇的九歌出版社的九歌年度散文獎。
〔1〕鄭喻如《現代小說與讀者漸行漸遠》, 《聯合文學》1997年第8期。 〔2〕顏崑陽《活在一意孤行的感官世界》,1996年10月2日《中國時報》。 〔3〕《前衛與鄉土的沉思——散文類決審會議紀實(中)》,1996年9月23日《聯合報》。 〔4〕〔5〕楊蔚齡《散文,生命的印記》,1997年9月26日《聯合報》。 〔6〕〔7〕周志文《冷眼與熱情——評黃碧端〈期待一個城市〉》,《聯合文學》1996年第10期。 〔8〕〔9〕魏可風《在孤獨里獨白——蔣勛訪問錄》,《聯合文學》1997年第1期。 〔10〕《聯合文學》1997年第1期。 〔11〕1996年1月1日至2日《中國時報》。 〔12〕1996年12月21日《中國時報》。 〔13〕1996年9月12日《中國時報》。 〔14〕1996年1月20日《中國時報》。 〔15〕1996年10月9日至10日《聯合報》。 〔16〕1997年6月1日《聯合報》。 〔17〕王鴻卿《緬懷國度里的楊牧》,《幼獅文藝》1997年第5期。 〔18〕黃碧端《感性的回聲——評李黎〈世界的回聲〉》,《聯合文學》1996年第9期。 〔19〕1996年3月28日《中國時報》。 〔20〕席幕蓉《高原札記“資料”與“經驗”》,《幼獅文藝》1996年第5期。 〔21〕1996年8月1日至4日《中國時報》。 〔22〕1996年11月21日《中國時報》。 〔23〕1997年10月5 日《聯合報》。 〔24〕1997年2月10日《聯合報》。 〔25〕1996年9月16日《中國時報》。 〔26〕1997年1月2日《中國時報》。 〔27〕1997年1月13日《中國時報》。 〔28〕1996年6月26日《聯合報》。 〔29〕《聯合文學》1996年5月號。 〔30〕1997年3月24日《中國時報》。 〔31〕〔32〕沈冬青《觀察、解說與創造:閱讀劉克襄》,《幼獅文藝》1997年第6期。 〔33〕《幼獅文藝》1997年第6期。 〔34〕《聯合文學》1996年第9期。 〔35〕《幼獅文藝》1996年1月號。 〔36〕《幼獅文藝》1996年5月號。 〔37〕《幼獅文藝》1997年第4期。 〔38〕1996年5月27日《聯合報》。 〔39〕1997年4月23日《聯合報》。 〔40〕1996年12月26日《聯合報》。 〔41〕1996年12月7日《中國時報》。 〔42〕1997年10月6日《聯合報》。 〔43〕1997年9月8日《聯合報》。 〔44〕1996年8月14日《聯合報》。 〔45〕陳義芝《新極短篇·序全民寫作》,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