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從“天葬”所感悟到的中國畫藝術(shù)心態(tài)
高民利
西藏這片神奇的土地,對(duì)于我來說,它是我心中永遠(yuǎn)的圣地,它給予了我多少生命的啟迪和感悟,給予了我豐富的靈感和美的享受,那里的一草一木是那么的圣潔和神秘,那里的溝溝壑壑是那么的博大和深邃,我慶幸自己作為一名畫家,能夠更加深刻地體會(huì)到這里給予我的一切啟示和震撼。
第一次去西藏的時(shí)候,我就被她那種遼闊和深遠(yuǎn)的地域風(fēng)情所深深吸引,這是和大都市完全不一樣的生活,我?guī)缀跬俗约菏且幻嫾遥且粋€(gè)異鄉(xiāng)人懷著虔誠的心靈終于尋找到自己夢(mèng)想中的第二故鄉(xiāng)。我是來朝圣的,在大昭寺,看萬盞酥油燈長明,記錄著朝圣者永不止息的足跡,也記錄了歲月的永恒。在巴松措,看著綠色的湖水純凈如玉,心中的煩惱不由蕩滌一清。在藏南,我試圖和藏民打成一片,為的是把我的心變得更加純凈。來到天葬臺(tái),我有幸參加了西藏人的天葬。在這里,我分明感悟到生死輪回過程中,萬物與宇宙一體、共融共化的感覺,感到生命是神的恩賜,沒有神祗的恩賜,生命不會(huì)往生。沒有奉獻(xiàn)精神,生命更不會(huì)永生。因?yàn)榉鹜愚D(zhuǎn)生,以肉身飼鷹。
我看到天葬師把死體背到空曠的高臺(tái)上,遠(yuǎn)處是死者的親朋好友,他們?cè)隍\的看著天葬師在高臺(tái)上模糊的身影,在為一個(gè)亡靈超度,他們虔誠的祈禱,那種感覺真是肅穆、莊嚴(yán),竟然感覺不到一點(diǎn)恐怖和惡心。我想,這也許就是生命的輪回。死亡并不是生命的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種形式的存在。
我翻閱資料,看到在中國古書中就有關(guān)于天葬的記載。例如,“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出自《周易?系辭傳》),“蓋上也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于壑。他日過之,狐貍食之,蠅蚊嘬之。”(出自《孟子?滕文公上》)。
在現(xiàn)代社會(huì)的一些地區(qū)的人群中天葬儀式依然存在。例如在西藏,天葬師把尸體背朝著天,折斷四肢,在尸體中央和兩肩用力撕開皮膚露出肌肉,然后退開,蒼鷹鋪天蓋地而下競(jìng)爭(zhēng)啄食。天葬臺(tái)上剩下骷髏時(shí)天葬師用石頭將骷髏敲成骨醬揉成一團(tuán),禿鷲再次鋪天蓋地而下,食盡散去,周圍的人開始長跪頂禮。又如生活在非洲東部地區(qū)的馬塞族人,他們死后將死者的全身用水洗干凈之后,細(xì)細(xì)地涂上一層奶油,放在屋內(nèi)中央位置,親屬們默跪在遺體四周做一天的祈禱,隨后村中長老引路,眾人抬著遺體來到荒郊野外,將遺體放在那里,任野獸吞食,飛鳥叼啄,借此表示馬賽人死也不同土地結(jié)緣。
關(guān)于天葬,藏傳佛教認(rèn)為,點(diǎn)燃桑煙是鋪上五彩路,恭請(qǐng)空行母到天葬臺(tái),尸體作為供品,敬獻(xiàn)諸神,祈禱贖去逝者在世時(shí)的罪孽,請(qǐng)諸神把其靈魂帶到天界。天葬臺(tái)上桑煙引來的鷹鷲,除吃人尸體外,不傷害任何動(dòng)物,藏人稱之為“神鳥”。據(jù)說,如此葬法是效仿佛祖釋迦牟尼“舍身飼虎”的行為,所以西藏至今仍流行天葬。
對(duì)于天葬,我們漢人恐怕無法接受,漢人講究的是入土為安,其實(shí)無論是天葬還是入土為安,對(duì)于生命來說都是一種形式,漢人講究的是投胎轉(zhuǎn)世,藏人講究的是生死輪回,在西藏人眼里,天葬是圣潔、高貴的。他們是一種生死的輪回,是從感知界通向往生界的一種途徑。在天葬的過程中,聽著法號(hào)長長的余音在空谷中回蕩,我對(duì)于生命的感知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特殊體驗(yàn)。仿佛這種聲音把我們和未來連接起來。
這樣那幅《天葬》也應(yīng)運(yùn)而生了,我只希望我自己能用手中的畫筆把這種感受深切地記錄下來。讓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莊嚴(yán)。
帶著這種感覺,我發(fā)現(xiàn),西藏的神奇與博大,并不在于他的寬廣、厚重、離天很近,而在于她內(nèi)里蘊(yùn)含的虔誠之心和自然淳樸的態(tài)度。在西藏,自然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正正常常,沒有一點(diǎn)矯揉造作。即使人的生老病死,也是自然的,它是一種輪回,一種通過輪回而使靈魂涅槃的圣地。在這種地方,感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用心去體味那里的一切,用心去在寺廟千年的香火中,感受那獨(dú)特的充滿人文的美感。
西藏帶給我的感受,也讓我在創(chuàng)作中,充滿了藝術(shù)的靈感,我明白,這種靈感不是閉門造車,而是通過對(duì)心靈的體悟和對(duì)西藏風(fēng)情的理解,來打通一個(gè)境界與一個(gè)境界的聯(lián)通。就像天葬,人本是自然中人,那最終是要回歸自然的。人的生態(tài),就如佛祖以肉身飼鷹,讓自己的軀體有所價(jià)值。人的價(jià)值,在生前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家庭、一個(gè)社會(huì),在死后,也應(yīng)該回歸自然,回報(bào)自然。這也許是天葬給予我的最大啟示。
在創(chuàng)作中,我發(fā)現(xiàn)感覺最重要,沒有感受,就沒有激情。沒有感受便沒有好的創(chuàng)作。所以作為一個(gè)藝術(shù)家,既要有感受,也要有生活。我喜歡以潑墨大寫意表現(xiàn)藏民的形象,表現(xiàn)他們豐富多彩的生活形象。
事實(shí)上,我想從藝術(shù)的本質(zhì)——?jiǎng)?chuàng)造這一體認(rèn)的角度,進(jìn)行我的認(rèn)知,從而在認(rèn)知層面,以獨(dú)特的感覺,在西藏人物畫的創(chuàng)作上,進(jìn)行新的構(gòu)成。畢竟,要寫意出富有時(shí)代精神的畫面,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要表現(xiàn)一個(gè)對(duì)于我來說還很陌生的民族之魂更是不容易,我只能更加用心地深入這片土地,用心體會(huì)。
我選擇西藏風(fēng)情并在反復(fù)皴擦渲染的同時(shí)依舊堅(jiān)持以“線”造型,強(qiáng)調(diào)人物的線性節(jié)奏與韻律。同時(shí),線條的質(zhì)量和筆墨的皴染也非常重要。在同一畫面中,既要注重線條的質(zhì)量,又要設(shè)計(jì)筆墨的成分。務(wù)必使線條流暢自然而又毫不浮滑,凝練概括而又不乏筆墨的豐富變化,再加之淡淡的背景渲染,將藏族人物天性颯爽卻又略帶羞澀之氣的精神情狀非常委婉地表現(xiàn)了出來。使整個(gè)畫面給人以強(qiáng)烈的浪漫主義抒情韻味。
其次,就表現(xiàn)技法來看,因?yàn)樘厥獾牡乩憝h(huán)境因素,西藏的民族服飾明顯帶有比較“厚重”質(zhì)感,但藝術(shù)家要表現(xiàn)這種“厚重”,就非得借助于光影,通過畫體積塊面才能實(shí)現(xiàn)。有些畫家的西藏人物畫的的確很厚實(shí),明暗關(guān)系也很突出,但那與中國畫之間到底有沒有血緣關(guān)系?在我看來,畫家表現(xiàn)西藏人物,就造型上來講,應(yīng)該關(guān)注的是其身上依然存在的線性之美,而不是他“厚重”的質(zhì)感及“濃艷”的色彩。再者,這種厚重感同樣可以通過“厚重”的筆力來傳達(dá)。但在我的畫中,我非常注重寫的語言,在寫的恣肆隨意中,調(diào)動(dòng)我的感受,以筆墨的行筆線路,來在畫面的構(gòu)成上,尋找新的突破。我想用筆鏗鏘有力,沉著穩(wěn)健,或是大筆橫掃,勢(shì)如破竹,最能體現(xiàn)我的個(gè)性。所以我的情感表達(dá),是快意的,是堅(jiān)韌不屈的。我知道在我的感覺中,對(duì)佛那種無休止的虔誠精神,雖然于我們的個(gè)人生活于事無補(bǔ),但是對(duì)于藏民族與惡劣自然的條件抗?fàn)幍男木常沂欠浅5恼鸷场?/p>
在多年的西藏生活中,我覺得藝術(shù)創(chuàng)作,既要甘于寂寞,又要胸懷開闊,在西藏廣漠闐寂的生活中,遠(yuǎn)離塵囂,埋頭鉆研,不斷的汲取營養(yǎng),慢慢體會(huì)創(chuàng)作靈感與激情。因此,我在不斷的追求個(gè)性中,不急于定格,而是清醒的認(rèn)識(shí)到一個(gè)成功的畫家,其作品必須體現(xiàn)個(gè)性,更要有自己的風(fēng)格。但是這個(gè)風(fēng)格是在艱苦的摸索和實(shí)踐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是一個(gè)水到渠成的過程。近幾年來,我經(jīng)過反復(fù)嘗試,找到了一種以筆墨為主調(diào),在皴擦過程中,以強(qiáng)烈的感情色彩,在西藏人物的形象上進(jìn)行深刻寫意,因此,我以氣運(yùn)筆,在中國畫的創(chuàng)作中,使中國畫更具神韻和氣魄。這是我在西藏人物畫創(chuàng)作領(lǐng)域的一點(diǎn)點(diǎn)心得和體會(huì),我相信通過不斷的藝術(shù)探索,我的人物畫創(chuàng)作將會(huì)再攀新的高峰。
面對(duì)他們不屈不撓地與惡劣的自然條件作斗爭(zhēng)的英雄一般的堅(jiān)韌精神——也正是這種不屈不撓的堅(jiān)韌精神煥發(fā)出了這種苦澀的美感——現(xiàn)實(shí)的苦澀與滄桑令人們充滿同情與憐憫,而生命的堅(jiān)毅與神奇更令我們欽佩不已!
因此,在我的藝術(shù)理念中:“情感大于任何形式,沒有情感的形式像失去生命的貝殼”,我堅(jiān)信獨(dú)特的情感會(huì)產(chǎn)生獨(dú)特的藝術(shù)形式,拒絕慣性思維與無聊的筆墨游戲。同時(shí),關(guān)懷苦澀的生命、贊美圣潔的靈魂、謳歌這一偉大的民族又是我藝術(shù)作品永遠(yuǎn)的精神追求。我相信,真實(shí)地再現(xiàn)藏人的生活場(chǎng)景不如凝練地表現(xiàn)他們的精神狀態(tài)更有價(jià)值。這也是我從天葬臺(tái)上得到的體悟。

督檢測(cè)與造價(jià).jpg)
院學(xué)報(bào).jpg)
代塑料加工應(yīng)用.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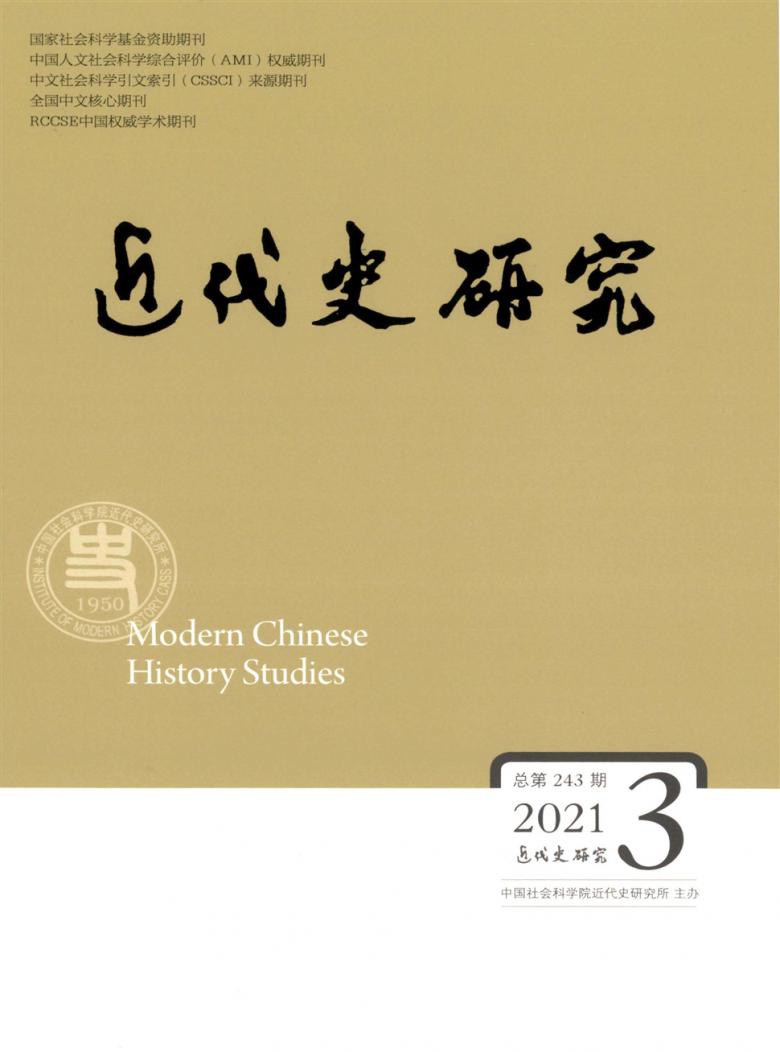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