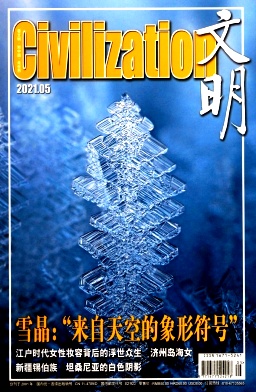《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小狗卡列寧的隱喻及其藝術作用
張科文
摘要:從看文章的形式描述,再聯系到具體的文章內容,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小狗卡列寧,首先隱喻的是特麗莎的命運,同時也是他們夫婦共同命運的象征。用卡列寧這一形象來隱喻人物命運,起到了表現人物性格、增強場景氛圍、暗示小說主題的藝術作用。 關鍵詞:卡列寧;隱喻;特麗莎;他們夫婦;命運;藝術作用 在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長篇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有一條叫卡列寧的小狗。對于它的來歷,小說中是這樣寫的: 為了能夠減輕特麗莎的痛苦,托馬斯娶了她,并且還送給她一只小狗(終于他們退掉了她那間經常空著的房子)。 小狗是一位同事的一條圣.伯納德種狗生的,公狗則是鄰居的一條德國種牧羊犬。沒人要這些雜種狗崽,而同事又不忍殺掉它們。 托馬斯知道如果不要這些小狗的話,它們只有死掉。他覺得自己就像總統站在四個死囚面前,而只有權利赦免其中一個。最后,他選擇了一條母狗。狗的體形如德國牧羊公犬,頭則像它的圣.伯納德母親。他帶它回家,交給了特麗莎,那只狗當即在特麗莎的胸前撒了一泡尿。 他們隨后設法給它取個名字。托馬斯要讓狗的名字能夠表現主人是特麗莎。他想到她來布拉格時帶了一本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就建議狗的名字叫“托爾斯泰”。 “不能叫它托爾斯泰,”特麗莎說,“它是女孩,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么樣?” “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馬斯說,“女人不可能有它那樣滑稽的面孔,它倒是象卡列寧,對,他是安娜的丈夫,就是我想象的樣子。” “叫卡列寧會不會影響她的性機能吧?” “完全可能,”托馬斯說,“一條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叫得次數多了,有可能發展至同性戀趨向。” 真是奇怪,托馬斯的話果然言中。雖然母狗大多數鐘情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而顯然卡列寧是個例外,決定與特麗莎相處好。為此托馬斯非常感謝卡列寧,總是敲敲小狗的頭:“卡列寧,干得好!當初我要你就為了這個。我沒能將她安頓好。你可一定得幫我。”(《第一章.第11節》,著重號是本文作者加的,下同。) 孔德拉在書中說:“作品中的人物不像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來的,他們誕生于一個情境,一個句子,一個隱喻(《五.15》)。”根據這個思想,這個叫“卡列寧”的狗,顯然也是有隱喻的。 托馬斯建議給狗起名“托爾斯泰”。托爾斯泰是俄國人,把狗用俄國人的名字命名,首先隱喻了托馬斯對俄國人1968年侵占捷克的憎惡;更重要的是:托爾斯泰是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把這狗稱“托爾斯泰”,即隱喻著這個小狗也通一點人性,或者說這狗的命運就隱喻了人的命運。 哪這狗的命運又隱喻著書中誰的命運呢? 狗的主人是特麗莎,當然它首先隱喻的是特麗莎的命運。 自托馬斯把卡列寧送給特麗莎后,它“當即在特麗莎的胸前撒了一泡尿”,可以說,一見主人就和主人“貼了心”了。從此,它日夜都陪伴著特麗莎,不遠萬里,跟著他們夫婦倆從布拉格去了蘇黎世,又悄然地跟著特麗莎一人回到了布拉格;托馬斯追特麗莎回到布拉格后,由于時局混亂,他丟掉了外科大夫的工作,成了一名窗戶擦洗工,但他卻仍暈暈乎乎地過著日子,和過去一樣,不斷地去搞他的所謂“性友誼”,這就使抱著“她的身體不能成為托馬斯唯一的身體,那么她一生中最大的戰役已經失敗(《四.6》)”的特麗莎,也仍和以前一樣,不停地做噩夢,整天生活在驚恐當中。卡列寧就忠實地跟著她去上街買東西、到野外去散心、到她上班的酒吧去……,伴她度過了多少個痛苦難耐的日日夜夜啊。特麗莎買東西時,也總忘不了給卡列寧嘴里叼個面包圈,她和它就這樣常常形影不離,以至到鄉下去后,卡列寧還緊跟著特麗莎整天去放牛。一直到特麗莎親自選好墓地,最終把它葬了。它是特麗莎喜就喜,特麗莎悲則悲,可以說,見了卡列寧的悲喜,就可知道它的主人特麗莎內心的悲喜,生活中它是她的影子。 再從“卡列寧”這個名字本身看,在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中卡列寧是安娜的丈夫,安娜在外面風流,卡列寧“戴了綠帽子”,還為顧及面子而左右為難,這就是托馬斯把有“滑稽的面孔”的狗叫“卡列寧”的原因;但托馬斯在嘲笑別人的時候,不料,“真是奇怪,托馬斯的話果然言中”,他自己不斷地追尋別的女人,卻讓妻子特麗莎做噩夢,卡列寧這條狗“滑稽的面孔”,不就正像它的主人的尷尬處境嘛。 這都表明,在卡列寧的遭遇中隱喻了特麗莎的命運。 但卡列寧又是托馬斯送給特麗莎的,是替托馬斯去為特麗莎解悶的;它的起名也有一個從“女(安娜.卡列尼娜)”到“男(卡列寧)”的過程,它是他們夫婦倆走到一起的見證,應該說,它的命運,實際上也隱喻著他們共同的命運。這樣理解,就正好對應了它“雜種狗崽”——女頭男身、又女又男的身材特點;對它為什么“母狗有公狗的名字”也有了最合理的解釋。 卡列寧因為與特麗莎相處得好。“為此托馬斯非常感謝卡列寧,總是敲敲小狗的頭:‘卡列寧,干得好!當初我要你就為了這個。我沒能將她安頓好。你可一定得幫我。’”特麗莎帶著卡列寧悲傷地一個人從蘇黎世回到了布拉格,正暈眩欲倒。“第五天,托馬斯突然回來了,他們還來不及互相做出必要的表示,卡列寧就向他猛撲過去(《二.28》)。” 卡列寧不僅深情地依戀著它的主人特麗莎,看,它對它的男主人托馬斯也是多么喜愛,也因此使托馬斯對它很是滿意。 卡列寧無兒無女,恓惶依順地陪伴著在凄苦多變中生活的他們夫婦二人,最后它得癌癥凄凄慘慘死了,不久他們夫婦也就離開了人間。在卡列寧生活的最后日子里,它曾掙扎著狺狺叫、搖尾巴向他倆“微笑”,用三條腿陪他倆散步。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它這樣做只是為了我們,”特麗莎說,“它并不想散步,只是為了讓我們快樂。”她的話中透出一種悲哀,她還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快樂的。他們不是沒有悲哀而快樂,恰好是因為悲哀而快樂。他們拉緊了手,眼睛中都閃動著共同的景象:一條跛腳的狗代表了他們生命中的十年(《七.3》)。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卡列寧的微笑”是悲哀的笑,他們夫婦的快樂是悲哀的快樂,卡列寧的命運隱喻著他們夫婦的命運。 把卡列寧作為特麗莎及他們夫婦命運的隱喻,在藝術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首先,借卡列寧的形象特點,表現了人物性格。 書中說“人類真正的道德測試,最一般的測試,包括了對那些受人支配的東西的態度,如動物。”照作者的這種觀點,我們讀文中多次出現的這個情景:“特麗莎總在我腦海中出現。我看見她坐在樹樁上,撫摸著卡列寧的頭,反復思考著人類的潰裂(《七.2》)。”就可以看出:特麗莎是一個善良、充滿仁愛心的人,如同卡列寧喜歡“一個象樣的活動場地(《五.21》)”一樣,她也愛好“一幅田園生活的圖景(《七.1》)”,對人世生活充滿了非常天真的浪漫情調;如同卡列寧的嗅覺特別靈敏一樣,特麗莎的鼻子也很敏感,“她像一條狗將他(托馬斯)全身嗅遍才辯明怪味(頭發中的)是什么:一種女人下體的氣味(《四.1》)。”這種隱喻,實際上揭示了特麗莎很重要的一種性格特征:敏感。——她能“體驗到奇異的快樂和同樣奇異的悲涼(《七.7》)。”而這敏感性,正是影響她幸福感,造成她一生命運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用卡列寧這一可愛的形象,創造出了鮮明生動的場景氛圍,使文章有了濃郁的抒情氣氛,給讀者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如:當特麗莎滿懷著希望和托馬斯去了蘇黎世,她本想著托馬斯到了蘇黎世后就避開了他在布拉格的那些情人和國內政局的騷擾,但到蘇黎世后,忽然發現托馬斯又被別的女人勾引去了。她一下子感到自己心煩意亂,渾身疲軟,不能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心頭的思緒不斷亂翻:在一個陌生的國家里生活,就像在空中踩鋼絲一樣,時時都有被掉下去的危險,在這危險中生活,事事也就只有靠托馬斯了。如果她被拋棄了怎么辦?她一輩子都要生活在怕失去他的恐懼中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