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薩爾》與民間藝術(shù)關(guān)系研究述評
扎西東珠
摘 要:英雄史詩《格薩爾》在其長期、廣泛的流傳過程中,被民間說唱藝人恰如其分地吸收、借鑒并運(yùn)用了各相關(guān)民族民間藝術(shù)中的音樂、舞蹈、民歌、曲藝、美術(shù)(繪、繡、雕、塑等)、戲劇等體裁的藝術(shù)形式,形成了熔多重藝術(shù)形式之精華于一爐的綜合性藝術(shù)特點(diǎn)。各民族研究者們對于史詩與民間藝術(shù)關(guān)系的研究,拓展了“格學(xué)”研究領(lǐng)域,它也是我國“格學(xué)”研究已走向博深的標(biāo)志之一。
英雄史詩《格薩(斯)爾》以其特有的藝術(shù)風(fēng)貌和精神氣質(zhì),扎根于藏族以及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普米族、白族等相關(guān)民族豐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以它旺盛的生命力不斷開花、結(jié)果。不論在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方面,還是展示相關(guān)民族藝術(shù)審美思想方面,都以其獨(dú)特的藝術(shù)形式成為我國民族藝術(shù)之苑中無可替代的一朵奇葩。 對《格薩爾》的藝術(shù)研究,20世紀(jì)50、60年代雖有涉及,但不深入。真正全面認(rèn)識、客觀把握《格薩爾》藝術(shù)成就的方方面面,是起始于20世紀(jì) E80年代之后。我國的研究者們或單項或綜合地從《格薩爾》的語言藝術(shù)、演唱藝術(shù)、造像(繪畫、雕塑等)藝術(shù)、與傳統(tǒng)藝術(shù)借鑒、繼承、發(fā)展的關(guān)系等方面,展開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尤其在音樂藝術(shù)的研究方面,成績尤為突出。 民間藝術(shù)和同屬精神文化的民間文學(xué)一樣,是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組成部分。就其自身的特征來說,民間藝術(shù)是以造型和表演為手段來塑造形象,表達(dá)和寄托人們的思想感情的。 民間藝術(shù),其包容的面十分廣泛,有音樂、舞蹈、曲藝、美術(shù)(繪、繡、雕、塑等)、戲劇等等。這些民間藝術(shù),在恪守傳統(tǒng)又不斷創(chuàng)造、發(fā)展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專事說唱《格薩(斯)爾》的藝人的說唱表演中,被渾然一體、恰如其分地運(yùn)用,形成了熔多重藝術(shù)形式于一爐的綜合性藝術(shù)特點(diǎn)。 對于《格薩爾》上述藝術(shù)特點(diǎn)的形成之因與過程,郭晉淵在其《〈格薩爾〉史詩的藏戲文化》一文中作了客觀的闡述:從主觀上講,仲巴藝人在早期史詩孕生期,絕不是作為一種從事表演藝術(shù)的專門人才去進(jìn)行有意的表演。他們的主旨僅是為了宣敘作為祖先——英雄崇拜的信仰,才去進(jìn)行莊嚴(yán)的、歷史性的傳承。而為了將所要宣敘的主旨(語言、思維與信仰合一的史詩)傳達(dá)得更具體,表達(dá)得更形象、生動、傳神,他們便主動地因循了圖騰傳統(tǒng)以及由此而生發(fā)的沖動的行為、表象、模糊的藝術(shù)形式等,進(jìn)而固定成以傳播為目的的表演形式。其后由于這種形式的實(shí)效性、有益性優(yōu)點(diǎn)對他們來說顯得十分重要,從而進(jìn)一步繹化成刻意規(guī)定的傳統(tǒng),這種傳統(tǒng)中既包含與史詩內(nèi)容十分貼切的特點(diǎn),又包含對藏戲藝術(shù)的需求性接受,從而形成了史詩說唱中的多元化藝術(shù)特點(diǎn),并一直保留了下來。 對《格薩(斯)爾》與傳統(tǒng)藝術(shù)之關(guān)系種種的研究分述如下: 1、音樂。音樂,是隨著原始人的勞動節(jié)奏,隨著圖騰意識的勃起而回流出的天籟之音。在初期,它是與歌、舞、沖動的感情揮逸等關(guān)注一體的。在藏族——《格薩爾》中,除用文字記錄了簡單的樂譜注音文字外,留下的大量材料就是被稱作“俄達(dá)”的曲牌——曲調(diào)名稱。 郭晉淵認(rèn)為,從這部分文化材料中,大致可以描摹出雛形藏戲或史詩在音樂發(fā)展方面的基本特點(diǎn),那就是:(1)古拙的仿聲特征;(2)擬形傳情到戲劇化繹化特征;(3)由模糊的戲劇形態(tài)向雛形藏戲發(fā)展即音樂戲劇化的定型特征。 邊多在《論〈格薩爾〉說唱音樂的歷史演變及其藝術(shù)特色》一文中指出:“在《格薩爾》中這種祭天祀神的內(nèi)容,是來源于藏族早期的民間說唱曲‘古爾魯’。而早期‘古爾魯’的來源是苯教……隨著社會的發(fā)展,這種習(xí)俗漸漸地延伸成為將士去前方迎戰(zhàn)之前、男女舉行婚禮之前、過年過節(jié)時都要進(jìn)行的祭天祀神活動。藏族古代的‘古爾魯’,正是反映這方面的實(shí)際生活。西藏民族民間的這一傳統(tǒng),在《格薩爾》中得到了充分的運(yùn)用。”他還舉例指出,《格薩爾》說唱音樂在西藏地區(qū),因?yàn)楦鞯氐臍夂颉⒌乩怼v史、方言和生活習(xí)俗等各方面情況的不同,而有兩種不同風(fēng)格色彩的地區(qū)音樂:一種是具有康區(qū)色彩的“與康區(qū)民間果卓音樂的風(fēng)格色彩特別相似的”音樂。 另一種是藏北牧區(qū)色彩。“這種說唱音樂不僅具有相當(dāng)濃郁的藏北牧區(qū)民間音樂所特有的那種風(fēng)格色彩外,而且還具有藏族牧民所特有的寬廣的心胸和動人心弦而幽默的生活氣息等。” 邊多認(rèn)為,《格薩爾》說唱曲所特有的三個樂句組成一樂段的結(jié)構(gòu)形式,也是來自西藏古老的民間說唱“古爾魯”。這種形式是與三句一段的唱詞結(jié)構(gòu)相一致的。另外,在《格薩爾》說唱音樂結(jié)構(gòu)形式中,還有兩種基本的曲式結(jié)構(gòu)形式,一是上下兩句組成一個樂段的曲式結(jié)構(gòu)形式;一是共有四個樂句組成一個樂段的曲式結(jié)構(gòu)形式。這兩種曲式結(jié)構(gòu)形式都與西藏其他民間歌曲的結(jié)構(gòu)有著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同時它又與古代民間‘古爾魯’也有著千絲萬縷的特殊關(guān)系。真正具有本土特征的,那便是《格薩爾》音樂。他指出:“在藝術(shù)形式上,《格薩爾》是繼承和發(fā)展了藏族古老的說唱藝術(shù)‘古爾魯’,而在吐蕃赤松德贊時期,‘古爾魯’又分為民間和宗教兩種之后,《格薩爾》就是西藏民族民間‘古爾魯方面’的一個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馬成富2002年7月提交第五屆國際 《格薩(斯)爾》學(xué)術(shù)研討會的論文《〈格薩爾〉唱腔音樂探秘》中,對《格薩爾》唱腔音樂源于“古爾魯”的觀點(diǎn)持反對意見。他認(rèn)為“產(chǎn)生于游牧民族部落時代的《格薩爾》唱腔不可能形成一種統(tǒng)一模式……不可能形成如‘古爾魯’那樣固定的說唱形式,更何況‘古爾魯’只是指聲腔……如果它是一種說唱形式,它就應(yīng)有一套固定的表演程式、一種固定的唱腔,那么今天的格薩爾史詩就不可能有成千上萬的唱腔曲調(diào)了”。 在蒙古族——蒙古族是說唱藝術(shù)很發(fā)達(dá)的一個民族。蒙族《格斯?fàn)枴返恼f唱以男性藝人的單口表演為主,在表演中十分強(qiáng)調(diào)表情性和藝術(shù)渲染,用馬頭琴和四胡伴奏,進(jìn)行自拉自唱。扎西達(dá)杰在《蒙族〈格斯?fàn)枴狄魳费芯俊芬晃闹兄赋觯骸皬囊魳番F(xiàn)象看,流傳在內(nèi)蒙、新疆、蒙古、俄羅斯布里亞特等地區(qū)的《格斯?fàn)枴罚淖謨?nèi)容外,語言、曲調(diào)、演唱形式等方面很少受到藏族的影響,音樂上實(shí)屬自己的創(chuàng)造。”蒙族《格斯?fàn)枴芬魳吩诎l(fā)展過程中,不但吸收本民族其他民歌的養(yǎng)分,而且形成了一種大膽的行動,那就是根據(jù)情節(jié)、情緒的需要,將一些說書調(diào)、好來寶、贊歌等本民族其他說唱藝種的樂曲整首搬來,為我所用,并且結(jié)合得和諧、自然。如在史詩中婚禮、慶賀的場面常用到好來寶曲調(diào),贊物頌人時常用贊歌的曲調(diào)。 在土族——土族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許多男子都愛唱和善唱酒曲。他們中許多人雖不會說《格薩爾納木塔爾》,但在《格薩爾》藝人說唱時可進(jìn)行伴唱。“《格薩爾納木塔爾》的曲調(diào)是受了土族‘酒曲’的影響……”“在演唱曲調(diào)方面,主要以藏族民間曲調(diào)為主,其中也有土族本民族的音樂曲調(diào),這主要表現(xiàn)在土族婚俗方面。就現(xiàn)已掌握的資料來看,就有十七、八種曲調(diào)。在演唱過程中,不同情節(jié)用不同的曲調(diào),形式變化多樣,曲調(diào)悠揚(yáng)婉轉(zhuǎn)。再加他有獨(dú)特的音質(zhì)和聲調(diào),唱起來悠揚(yáng)動聽,繪聲繪色,有表情有動作。” 扎西達(dá)杰提交《格薩(斯)爾》學(xué)術(shù)研討會的論文《從〈格薩爾〉音樂看土族文化的多族交融性》一文指出,土族《格》音樂由多民族曲調(diào)構(gòu)成,其中包括土族曲調(diào)、藏族曲調(diào)、“花兒”曲調(diào),甚至有蒙古族曲調(diào)的痕跡。其音樂表面上繁雜,但雜而不亂,似乎有一種天然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和順成的規(guī)律將各種要素結(jié)合得協(xié)調(diào)、完美,進(jìn)而構(gòu)成它的多樣、多彩和表現(xiàn)上的豐富性。 在白族——據(jù)章虹宇考證,以云南鶴慶縣為核心,“輻射”于滇西地區(qū)白、彝、藏、納西和漢族群眾中的較有特色的,被人們普遍崇拜的 “本主”——“老藏王”,即為格薩爾王。而當(dāng)?shù)亍岸滟狻保ㄎ滓牐┚褪峭ㄟ^唱 “神歌”(其內(nèi)容多為格薩爾神話故事)來表達(dá)人們對“老藏王”的崇拜、祭祀之情的。流傳在當(dāng)?shù)氐母袼_爾降生、捉鬼、降魔、姜國打仗、征戰(zhàn)、鹽城打仗的故事,也都是用“春歌”的“打歌”形式演唱出來的。無疑,“神歌”、“春歌”的音樂形式是當(dāng)?shù)匕鬃迕耖g的傳統(tǒng)藝術(shù),是演唱《格薩爾》的主要藝術(shù)手段。 在普米族——把《老藏王傳奇》作為史詩演唱,邊唱邊舞。據(jù)說過去普米人出征前必演唱此歌,把史詩作為民族的戰(zhàn)歌,作用于戰(zhàn)前動員和鼓舞本民族的人,勇敢地走上戰(zhàn)場,投入新的戰(zhàn)斗。 2、曲藝。各地流傳的《格薩(斯)爾》,無論是說唱兼?zhèn)洌€是只說不唱,都屬于曲藝范疇。即以帶有表演動作的說、唱來敘述故事、塑造人物、表達(dá)思想感情、反映社會生活。 藏族傳統(tǒng)的曲藝形式豐富多彩,有民間故事、六弦琴彈唱、拉瑪麻尼、折嘎、白嘎爾等。而藝人在說唱《格薩爾》時,就是吸收并綜合了這多種曲藝形式的表現(xiàn)方式與手段,以一人多角色的說唱表演充分展示史詩的故事內(nèi)容,表達(dá)說唱者的思想感情。可以說,說唱這種曲藝形式是《格薩爾》這種文化現(xiàn)象的載體。扎西達(dá)杰在《玉樹藏族〈格薩爾王傳〉說唱音樂研究》一文中說:“玉樹藏族《格薩爾》說唱調(diào)不但各種調(diào)式俱全,而且與歌舞音樂相比,由于不受舞蹈的限制,節(jié)奏、節(jié)拍及曲調(diào)更為多變、復(fù)雜。但與以自由見長的山歌比較,又相對顯得方正,有規(guī)律性。”這也就是說,《格薩爾》說唱是一種藏族特有的曲藝品種。他還進(jìn)一步指出:“由于是同一地區(qū)的同屬民間演唱類藝術(shù),玉樹藏族《格薩爾》說唱調(diào)與玉樹歌舞(弦子、鍋莊等)、山歌、對歌、故事調(diào)、念經(jīng)調(diào)、酒歌等音樂,無不有相互聯(lián)系、相互滲透之處。有好些曲調(diào)在旋律、音調(diào)、節(jié)奏、節(jié)拍、風(fēng)格、情緒等方面,非常接近和比較類似。” 對《格薩爾》說唱這個藏族特有的曲藝品種的表演形式,黃銀善在其《〈格薩爾〉中的說唱音樂》一文中有所歸納:表現(xiàn)形式——(1)只說不唱的說書形式;(2)連說帶唱的說唱形式;(3)載歌載舞的歌舞形式;(4)自拉(牛角琴)自唱的“布旺”形式;(5)藏戲演出的戲劇形式等。其中,以說唱形式的表演風(fēng)格尤為突出。表演程式——有的先行焚香請神儀式而祈禱誦經(jīng);有的要掛英雄畫像而指畫說唱;有的托帽說唱;有的手捻佛珠邊說邊唱……總之,形式多樣,不一而足。音樂手段——表演時,每個人物出場先得歌唱;各個人物也要求唱各自的專用曲調(diào),像格薩爾、珠牡這樣的主要人物就各有其十幾種較為固定的音樂曲調(diào)樣式;同一個人物在不同環(huán)境中還要求采用不同的曲調(diào)或同一曲調(diào)的變體即興演唱。結(jié)構(gòu)方式——有的以事件為中心,而有的又圍繞人物為中心進(jìn)行演唱。“以上表明,民間說唱的表演形式既具有嚴(yán)密的規(guī)范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即興性和隨意性。” 蒙古族《格斯?fàn)枴返恼f唱則更多地吸收、借鑒了傳統(tǒng)曲藝的表現(xiàn)方式和手段。正如扎西達(dá)杰所說:我們知道蒙古族是說唱藝術(shù)很發(fā)達(dá)的一個民族,分別擁有說書、說史詩、說好來寶、說故事、贊歌、祝福歌、二人轉(zhuǎn)等多品種的說唱藝術(shù)。《格斯?fàn)枴氛f唱就是可譽(yù)為蒙族說唱藝術(shù)之魁首的“說史詩”類中的一種。蒙族《格斯?fàn)枴窂奈捏w上講,說唱體、散文體、故事體、傳說體俱全。蒙族《格斯?fàn)枴匪嚾四苷f、會唱、善奏,兼多種說唱藝術(shù)于一身。多為以師徒傳承而就的“聞知”藝人,說唱諸多《格薩爾》分章本。 3、歌舞。藏族民間傳統(tǒng)的歌舞與《格薩爾》的說唱有著極為密切的關(guān)系。“從民間說唱藝術(shù)領(lǐng)域看,《格薩爾王傳》又廣泛地綜合和吸收了藏族民間音樂中豐富多樣的藝術(shù)形式。它把樸實(shí)無華的折尕爾(說唱)、古樸悠揚(yáng)的勒(酒歌)、高亢婉轉(zhuǎn)的納伊(山歌)、活潑詼諧的則肉(表演唱)、節(jié)奏明快的單(舞蹈)等融為一體,集各種民間歌舞音樂藝術(shù)形式于一爐。”從一定的意義上講,《格薩爾》的說唱形式就源于民間歌舞。就文體來說,《格薩爾》采用散韻結(jié)合的形式,以唱詞為主,但散文敘述也占很大比重,在整部史詩中有著重要作用。而“《格薩爾》的唱詞部分多配用魯體民歌和自由體民歌的格律。”魯體民歌通常一首有數(shù)段,以三段的為最多,也有少數(shù)只有一段的,每段少至二、三句,多至十?dāng)?shù)句,其中采用三至五句的較為普遍。但《格薩爾》中不受這種規(guī)律的限制,往往不分段,根據(jù)內(nèi)容需要,有時一口氣唱下去,猶如江河奔流,一瀉千里,多達(dá)數(shù)百行。這種內(nèi)容,這種氣勢,只有用魯體民歌的格律才能充分表達(dá)。魯體民歌的格律每句有七個音節(jié)和八個音節(jié)的兩種,間或有九個音節(jié)的。在敦煌出土的吐蕃時期藏文文獻(xiàn)中,就有“魯”這種歌體。可見其源遠(yuǎn)流長。許英國也說,“藏族英雄史詩的韻文部分是傳承民歌形式而發(fā)展起來的,具有婉轉(zhuǎn)、流利、活潑、音樂性強(qiáng)的特點(diǎn)。” 關(guān)于《格薩爾》說唱曲調(diào)與民歌的關(guān)系,扎西達(dá)杰在《玉樹藏族〈格薩爾王傳〉說唱音樂研究》一文中說:《格薩爾》說唱曲調(diào),在玉樹地區(qū)間的交流也比歌舞藝術(shù)來的廣泛。如果說在牧區(qū)曲調(diào)中吸收山歌(魯)因素的情況較為多見的話,那么農(nóng)區(qū)曲調(diào)中與歌舞音樂相聯(lián)系的情況相對多見。各地相同的部分,屬農(nóng)區(qū)曲調(diào)傳入牧區(qū)者為多見。特別是玉樹藏族《格薩爾》說唱曲調(diào)廣泛吸取了山歌的種種音樂手法。如:自由處理的節(jié)拍、變化繁復(fù)的節(jié)奏、頻繁運(yùn)用的裝飾音,一曲反復(fù)演唱過程中進(jìn)行即興發(fā)揮、自由變化等。 在說唱《格薩爾》的幾種類型藝人中的“博仲”藝人的演唱,他們講究要說、唱、跳三技集于一身,情緒融貫,形象地表演。即所謂:“唱要音全調(diào)齊分大小,跳要姿美準(zhǔn)確有程式,說要流暢完整分詳簡。”其中的“跳”,含有舞蹈和表演兩種意義。官卻杰在觀察了藝人才讓旺堆在說唱時的動作表演之后認(rèn)為:“他反復(fù)的動作基本不變,而且表現(xiàn)強(qiáng)勁的‘鍋哇’(武士舞)、粗獷的‘卓’(鍋莊舞)、抒情的‘伊’(弦子舞)和技巧性較高的‘熱巴’舞,比較諧調(diào)、優(yōu)美。特別是在運(yùn)用體現(xiàn)內(nèi)容的道具上,與動作較為統(tǒng)一,變化很自如,銜接也緊,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了藝人在演唱時吸收和借鑒“鍋哇”舞、弦子舞、鍋莊舞、熱巴舞的動作和程式“為我所用”之外,還有干脆利用藏傳佛教寺院特有的法舞的形式進(jìn)行演唱的。如,在青海貴德昨那寺的《格薩爾》“羌”舞的演唱——“……格薩爾王在繪有雪山雄獅、戰(zhàn)神等(圖案的)十幾桿旗幟的引導(dǎo)下昂然出場,只見他全副盔甲,佩劍持刀,威風(fēng)凜凜;總管王察根和漢地富商俄吾對酒當(dāng)歌,歌頌格薩爾的千秋功績;美麗的王妃珠牡和梅薩翩翩起舞,十三員大將舞刀弄槍,好一陣威風(fēng)。……既有說唱又有舞蹈,樂隊、道具、服裝也很齊全。” 還有獨(dú)立流傳于說唱藝人表演之外的專門舞蹈,如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德格等地,西藏的昌都地區(qū),“有‘格薩爾林卓’的一種鍋莊,內(nèi)容都是歌頌格薩爾事跡的。” 在西藏工布江達(dá)地區(qū)流傳的民間舞蹈“卓舞”、“箭舞”中,“有歌唱格薩爾和珠牡的內(nèi)容,用問答形式,邊唱邊跳,生動活潑,至今流傳不衰,深受群眾喜愛。” 牧區(qū)的圓圈舞(亦稱“果諧”)里,歌唱格薩爾的內(nèi)容就更多。還有歌頌和平與勞動的“珠牡牧羊舞”、“珠牡紡織舞”等等。 蒙族專門用蒙古長調(diào)、牧歌、情歌、短調(diào)等樂曲演唱《格斯?fàn)枴贰?/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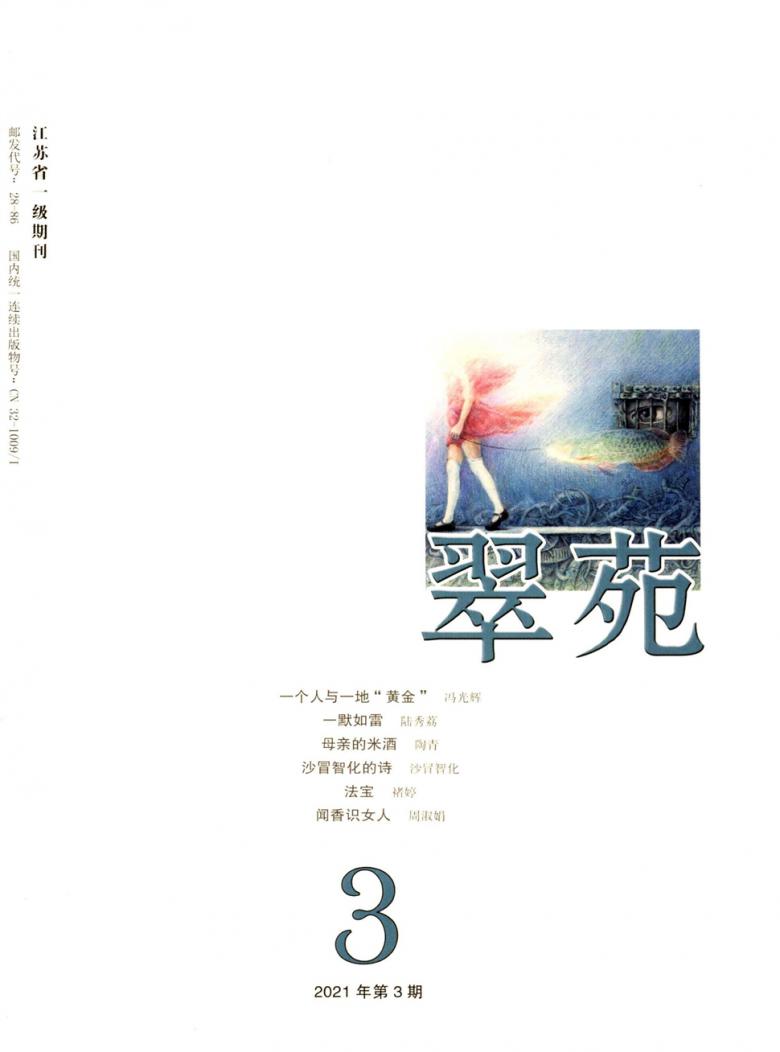
與對抗.jpg)


.jpg)
與技術(shù).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