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寶雞民俗文化產(chǎn)業(yè)傳承與發(fā)展分析
李強(qiáng)
論文關(guān)鍵詞:鳳翔木版年畫與彩繪泥塑 傳承 發(fā)展
論文摘要: 隨著國家的轉(zhuǎn)型和社會經(jīng)濟(jì)、文化的發(fā)展,傳統(tǒng)民俗文化正面臨著嚴(yán)峻的挑戰(zhàn),同時也面臨著發(fā)展的機(jī)遇。本文通過對鳳翔木板年畫和彩繪泥塑手工生產(chǎn)的研究,為寶雞地區(qū)的民俗文化產(chǎn)業(yè)傳承和發(fā)展提供參考價值,探索民俗文化融入現(xiàn)代生活得到持續(xù)的發(fā)展的途徑。
鳳翔木版年畫與彩繪泥塑是陜西具有代表性民俗文化特征的民間美術(shù)品,它們通過民俗文化活動與百姓的生活和精神需要緊密相連。木版年畫與彩繪泥塑的生產(chǎn)歷史可以追溯到五六百年。近些年彩繪泥塑與木版年畫成為國家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項目,曾經(jīng)存在于下層民眾中的民間藝術(shù)得到政府的支持與資助。民間藝術(shù)長期生存于中國廣大的鄉(xiāng)村這片文化土壤,成為百姓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直至今日。
一、鳳翔木版年畫與彩繪泥塑的傳承
(一)鳳翔木版年畫的傳承
年畫的生產(chǎn)與民俗需求緊密相關(guān),貼門畫的習(xí)俗歷史悠久,專家考證木版年畫的定性與蓬勃發(fā)展在宋代,古代文獻(xiàn)典籍中也多有記載,《夢粱錄》與《武林舊事》中就記述有北宋時民間流行鐘馗、財馬、門神、桃符的民間年畫。明代年畫再次興盛,從現(xiàn)存的明代年畫實(shí)物資料看,無論題材內(nèi)容、刻繪技法還是藝術(shù)風(fēng)格都十分多樣,樣式也趨于定式,許多題材與后世相差無幾,天津楊柳青、蘇州桃花塢、陜西鳳翔的木版年畫均是從明代開始興起的。
鳳翔木版年畫的主要產(chǎn)地在鳳翔城東南——南肖里村,村中邰姓的“祖案”記述,明朝正德年間南肖里村已有邰姓藝人從事木版年畫的生產(chǎn),在清代的康乾時期,生產(chǎn)已具規(guī)模,除了個體的生產(chǎn)外,還出現(xiàn)了集體合作的生產(chǎn)作坊。工藝以印刷與手繪結(jié)合(線稿印刷手繪施彩)。到了嘉慶、道光年間藝人學(xué)習(xí)外地先進(jìn)的年畫印刷技術(shù)改進(jìn)生產(chǎn),線稿與施彩工序全部套版印刷。年俗的大量需求使生產(chǎn)規(guī)模逐漸增大,產(chǎn)地除南肖里村外還擴(kuò)展到北肖里村與陳村,三個村從事年畫生產(chǎn)的有三十多戶,規(guī)模化的作坊五六家,銷售逐步擴(kuò)展到西北地區(qū)。較大規(guī)模的作坊,當(dāng)?shù)厝朔Q為“畫局”。繁榮時期畫局有十多家,其中世興畫局、忠興畫局、復(fù)盛畫局名聲較大。畫局將字號刻在印版之上,類似于廠標(biāo),通過銷售宣傳以擴(kuò)大知名度。生產(chǎn)規(guī)模的擴(kuò)大,促使畫局在年畫的生產(chǎn)分工上更加細(xì)致,有經(jīng)濟(jì)實(shí)力的畫局專門聘請當(dāng)?shù)刂嚾水嫿硜碓O(shè)計畫稿,刻板、印刷等環(huán)節(jié)各有專人負(fù)責(zé),規(guī)模化的生產(chǎn)自然帶來成本的降低,專業(yè)化的分工同時帶來質(zhì)量的提高,這都增強(qiáng)了市場的競爭力,良好的聲譽(yù)使鳳翔木版年畫成為西北地區(qū)頗有影響的民間藝術(shù)品。清末民初年間,木版年畫的生產(chǎn)達(dá)到繁盛,這一時期鳳翔木版年畫的年產(chǎn)量合計在四百多萬張,而世興畫局年畫的生產(chǎn)量占到了全縣總產(chǎn)量的一半,年畫品種多樣,有了名牌產(chǎn)品“金三裁”年畫。產(chǎn)品銷往陜、甘、寧、青及河南等地,真正創(chuàng)出品牌的知名度。
年畫是春節(jié)很普遍的一種民俗消費(fèi)品,在豐年幾乎家家張貼。從年畫的種類看門神等“六神畫”的生產(chǎn)量就占到一半以上,這也是為了適應(yīng)民俗市場的需求。木版年畫因?yàn)槊袼咨畹钠毡樾枰笈可a(chǎn),形成規(guī)模,趨于半專業(yè)化,與很多還處于業(yè)余、自娛階段的其他民間美術(shù)生產(chǎn)比較,它在生產(chǎn)的規(guī)模和文化影響方面都較大。
(二)鳳翔彩繪泥塑的傳承
鳳翔彩繪泥塑的生產(chǎn)以六營村胡姓家族為主,制作技藝作為傳統(tǒng)的家族手藝代代相傳,關(guān)于鳳翔泥塑的產(chǎn)生有這樣的傳說。元末明初時期朱元璋軍隊屯扎于鳳翔此地,時間長了軍士轉(zhuǎn)為地方居民,軍中有一些來自江西具有陶瓷制作手藝的人利用當(dāng)?shù)仞ば院軓?qiáng)的觀音土(俗稱板板土)和泥捏塑,制模做偶、施加彩繪,然后到各大廟會出售。當(dāng)?shù)乩相l(xiāng)購泥塑置于家中,因風(fēng)俗而用于祈子、護(hù)生、辟邪、鎮(zhèn)宅、納福。“六營”村名似乎可以從這一面佐證。
泥塑生產(chǎn)仍延續(xù)了手工生產(chǎn)方式,其民俗文化內(nèi)涵以一種集體民俗意識被繼承。彩繪泥塑是普通百姓創(chuàng)造的藝術(shù)品,同時他們也是欣賞者和消費(fèi)者,彩繪泥塑出現(xiàn)在許多民俗禮儀之中,與當(dāng)?shù)氐拿袼谆顒泳o密相連。彩繪泥塑因?yàn)檫@種民俗活動的需求擁有了消費(fèi)市場。在六營村就留傳有這樣的諺語:“寧舍二畝田,不舍靈山、周公會。”民俗生活的需要是彩繪泥塑生產(chǎn)發(fā)展的必要條件。一直以來彩繪泥塑的生產(chǎn)與民俗生活都緊密相關(guān)。靈山求子的泥娃娃,孩子滿月親友送來的保佑平安成長的坐虎,老人壽誕賀壽的泥虎,以及春節(jié)屋內(nèi)懸掛的驅(qū)瘟辟邪的掛虎,背后都有它豐厚的民俗文化內(nèi)涵。
泥塑虎懸掛于家中鎮(zhèn)宅、驅(qū)邪,作為保護(hù)神加以膜拜,產(chǎn)生于民間藝術(shù)與原始藝術(shù)共有的原發(fā)性與復(fù)功用性特征,源于遠(yuǎn)古的虎圖騰崇拜。在中華民族中影響深廣的“虎、龍、鳳、蛙”等形象都具有圖騰的性質(zhì)。歷史學(xué)家考證虎是生活在西北地區(qū)以狩獵為主的古羌戎族圖騰,經(jīng)過漫長的歷史演化發(fā)展,崇虎的文化意識已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觀念。“泥耍活”是對彩繪泥塑的俗稱,但當(dāng)我們觀察后會發(fā)現(xiàn)“鳳翔彩繪泥塑中的掛虎、坐虎無論從材料還是型制上看,都不適合孩子來把玩翻弄,而更適合于恭敬
嚴(yán)肅地懸掛或高置案廚之上,就人來說是表現(xiàn)出一種供奉的態(tài)度,就物而言則處于一種君臨居室環(huán)境的地位。就形象而言,它又是在獰惡兇猛的大輪廓骨架中以細(xì)小填充的紋樣和色彩給予柔化、生活化”。[1]在鳳翔及鄰近地區(qū)一帶農(nóng)村,孩子們過滿月或生日時,外婆或娘舅把這種泥活作為禮品送到孩子家中,它的意義與其說是給孩子玩耍,不如說是為了給新生的小生命驅(qū)惡辟邪,充當(dāng)鎮(zhèn)宅守魂的神靈瑞獸。彩繪泥塑作為原始文化的嫡傳,顯現(xiàn)出生命繁榮的審美理想。
二、鳳翔木版年畫與彩繪泥塑的發(fā)展
二十世紀(jì)七十年代末隨著改革開放,各地的民間民俗文化活動開始復(fù)蘇,而融入民俗的各種民間藝術(shù)也漸漸恢復(fù),在八十年代中期鳳翔木版年畫與彩繪泥塑特別受到美術(shù)界專家的關(guān)注并給予很高的評價,聲名鵲起。但由于經(jīng)濟(jì)的市場化轉(zhuǎn)型,手工生產(chǎn)的民間美術(shù)品逐漸被大機(jī)器生產(chǎn)的競爭擠出市場。另外,民間美術(shù)“土”的特色,也使逐漸追求時尚喜好的人們漸漸將它們淡忘。鳳翔木板年畫與彩繪泥塑也經(jīng)歷了沉浮起落,在當(dāng)下生存下來并繼續(xù)發(fā)展。
(一)鳳翔木版年畫的發(fā)展
改革開放使曾經(jīng)的傳統(tǒng)文化禁錮得到解放,春節(jié)貼門神的風(fēng)俗習(xí)慣逐步恢復(fù),八十年代初期南肖里村有多個家庭生產(chǎn)年畫,在此基礎(chǔ)上藝人們成立了鳳怡年畫研究會,為年畫的恢復(fù)與繼續(xù)發(fā)展發(fā)揮了作用。但隨著機(jī)器印刷的年畫商品在市場的出現(xiàn),具有印刷成本低廉、色彩耐久等優(yōu)勢的機(jī)器印刷品強(qiáng)烈地沖擊了木版年畫原有的市場地位,手工生產(chǎn)的木版年畫市場很快被擠壓,以民間藝人一己之力,無法挽救和阻擋木版年畫在市場競爭中的頹勢和逐漸在大眾消費(fèi)市場消失的趨勢。行業(yè)也不得不遵循“適者生存”的原則尋求新的出路。 年畫藝人邰立平的經(jīng)驗(yàn)對今天非物質(zhì)文化保護(hù)是有益的參考,他是年畫老字號世興畫局的傳人,在面對困局時,他仍堅持個體手工生產(chǎn),優(yōu)化工藝,提升質(zhì)量,將木版年畫的品種開發(fā)與傳統(tǒng)種類挖掘整理結(jié)合起來。經(jīng)過二十余年的努力,他整理印制了《鳳翔木版年畫選》三卷,保護(hù)了傳統(tǒng)年畫。他將木版年畫展覽搬到各大美術(shù)院校,在全國各地、海外交流推廣,贏得了聲譽(yù)。經(jīng)過多年的努力,邰立平已是鳳翔木板年畫行業(yè)的佼佼者,成為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鳳翔木版年畫主要傳承人。雖然木版年畫失去了大眾的春節(jié)年畫市場,但木版年畫藝術(shù)層次的提升使其價格升了數(shù)十倍。本只從事年畫手工生產(chǎn)作為藝人的邰立平卻承擔(dān)了多種角色,他不僅從事年畫生產(chǎn),而且進(jìn)行組織管理、整理、研究對外交流的多種工作,他將搶救保護(hù)傳統(tǒng)遺產(chǎn)工作視為己任,具有一種獻(xiàn)身精神,他的技藝水平和多方面能力在其他藝人身上很難復(fù)制。這樣高質(zhì)量的個體手工生產(chǎn)使得目前生產(chǎn)方式更加顯得精英化,也成為民間藝術(shù)在現(xiàn)代社會生存的一種模式。
(二)鳳翔彩繪泥塑的發(fā)展
鳳翔彩繪泥塑生產(chǎn)在上世紀(jì)八十年代的恢復(fù)得到文化部門的支持,彩繪泥塑作品進(jìn)京并在美術(shù)館展出,美術(shù)界的專家學(xué)者對其藝術(shù)價值也給予很高評價。藝人們還跟隨文化藝術(shù)交流團(tuán)到國外獻(xiàn)藝辦展,這些都促進(jìn)了彩繪泥塑的生產(chǎn),產(chǎn)品還由工藝美術(shù)公司代銷,以老藝人胡深為代表六營村多家農(nóng)戶從事這種副業(yè)生產(chǎn)。但隨著民俗熱的逐漸降溫,泥塑生產(chǎn)并未持續(xù)興盛。
新世紀(jì)之初,人們在享受現(xiàn)代化帶來的物質(zhì)便利的同時,也注重起精神消費(fèi),開始思考和重新認(rèn)識包括民俗文化在內(nèi)的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這時彩繪泥塑得到了一個大的機(jī)遇,2002年、2003年泥塑馬、泥塑羊登上了中國郵政發(fā)行的生肖郵票,使鳳翔彩繪泥塑一夜之間家喻戶曉,當(dāng)?shù)卣矊⒚耖g藝術(shù)作為一張地方文化名片在政策上加以扶持。伴隨著生產(chǎn)訂單的源源涌入,六營村家家戶戶開始彩繪泥塑的生產(chǎn),生產(chǎn)的一擁而上,在短時期也出現(xiàn)了市場的惡性競爭,幾年的市場沉浮之后彩繪泥塑的生產(chǎn)有了多樣形式,近年隨著國家新農(nóng)村建設(shè)和一村一品戰(zhàn)略的實(shí)施,彩繪泥塑成為了一種標(biāo)志性的品牌產(chǎn)業(yè),現(xiàn)在泥塑生產(chǎn)的形式趨于多樣化,有以老藝人胡深為代表的家庭式生產(chǎn),也有青年藝人胡新民創(chuàng)建的大規(guī)模的民間美術(shù)生產(chǎn)的文化企業(yè)。因?yàn)橹扰c文化需求而帶來了大量訂單生產(chǎn),使彩繪泥塑以一種良性的競爭方式發(fā)展。
市場的需要影響了彩繪泥塑的生產(chǎn)。年俗產(chǎn)品成為彩繪泥塑產(chǎn)品的主流,即以生肖泥塑為主,就如老藝人胡深談道:“什么年(生肖)生產(chǎn)什么,什么需要生產(chǎn)什么。”市場的需求決定了泥塑生產(chǎn)品種,但也使彩繪泥塑的圖案造型傳統(tǒng)發(fā)生了微妙變化。傳統(tǒng)的泥塑掛虎最具鳳翔彩繪泥塑的代表性,原本具有豐富內(nèi)涵的民俗文化圖案漸漸向簡化、視覺裝飾化發(fā)展,現(xiàn)在的泥塑產(chǎn)品更加美化,易于大眾接受,但似乎少了鄉(xiāng)土民俗的味道。孩子百天送泥虎,護(hù)佑健康成長的保護(hù)神的民俗性質(zhì)已經(jīng)逐漸地褪去,而更加大眾娛樂化,使其成為既帶有民間藝術(shù)特征又具有現(xiàn)代視覺裝飾性的民間工藝品。
從非物質(zhì)文化的角度看木版年畫與彩繪泥塑,我們關(guān)注了它們在當(dāng)下的生產(chǎn)情況與藝人的出路,“非物質(zhì)文化形態(tài)的鮮活性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生存的具體體現(xiàn)。保護(hù)中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不是只是保存物質(zhì)化的‘遺產(chǎn)’或收藏遺產(chǎn)化的‘文物’,其根本要旨是使傳統(tǒng)文化形態(tài)能夠‘生活’在當(dāng)代,成為當(dāng)代社會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實(shí)際構(gòu)成”。[2]民間藝術(shù)反映民俗文化,是民俗文化的有形載體,民間美術(shù)融入百姓的民俗生活,民俗與民族精神關(guān)聯(lián)。在新時期多元化的文化環(huán)境使得民間藝術(shù)的身份更加微妙,鳳翔木版年畫與彩繪泥塑以其各自不同的生產(chǎn)方式為民俗文化產(chǎn)業(yè)的傳承發(fā)展提供了例證。我們清楚地認(rèn)識到民間藝術(shù)不是“文物”,它是文化,而且與我們的生活相關(guān)聯(lián),只有自然地融于我們的生活中,才能良好地發(fā)展。
[1]王寧宇.中國西部民間美術(shù)論[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179.
[2]彭迪.建言民間美術(shù)的活態(tài)保護(hù)[J].美術(shù)觀察,2007,(11).
[3]陳勤建.中國民俗學(xué)[M].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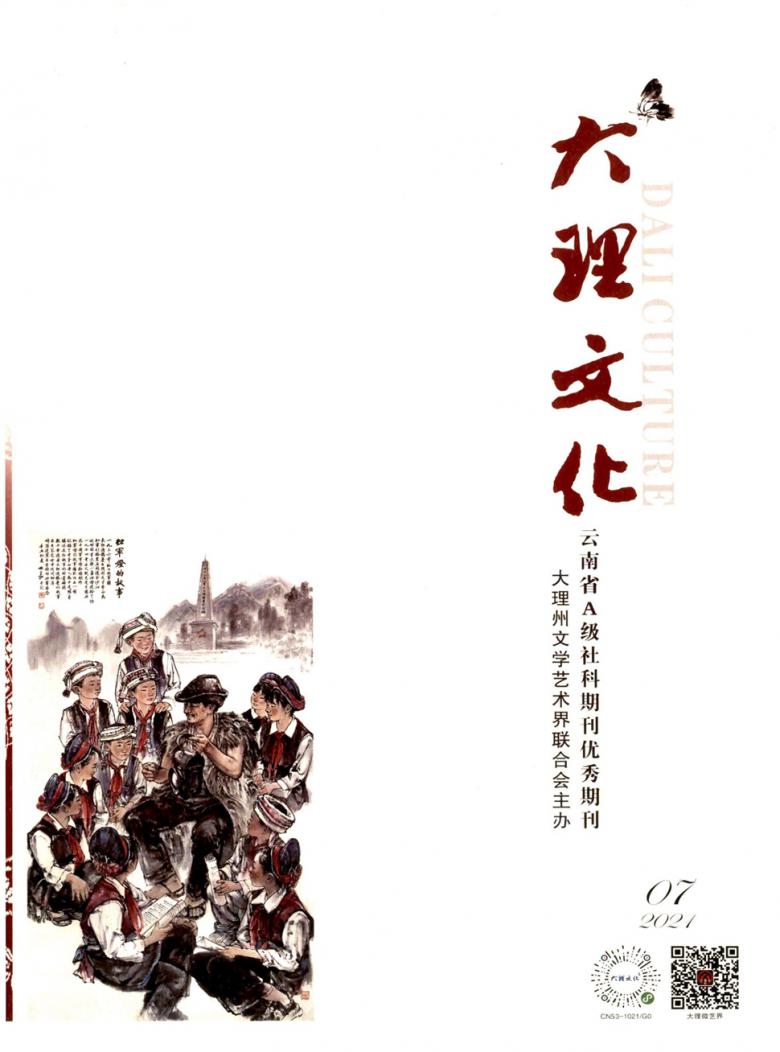
院學(xué)報.jpg)
技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