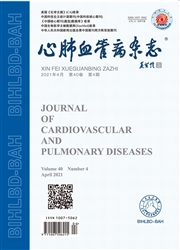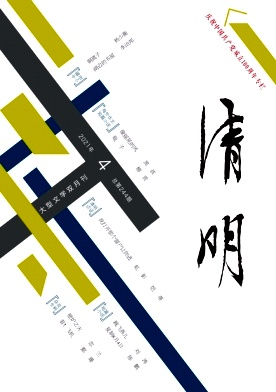災后農村恢復重建過程中的傳統文化保護思考(1)
未知
摘 要: 汶川5·12特大地震使四川、甘肅災區城鄉居民蒙受了巨大的損失。而地震引發的地質災害將形成長期的影響。在這場劫難中,大量完整保持著傳統狀態的羌族、藏族村寨聚落被損毀,它們承載的傳統文化也面臨危機。本文介紹了地震、地質災害對農村地區的影響,結合災后農村恢復重建工作,集中探討了保護傳統文化的迫切性和面臨的問題,并提出了保護災區聚落的初步規劃思考。
關鍵詞: 災后重建; 聚落; 傳統文化; 新農村規劃
1序:災害造成農村巨大損失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8.0級大地震,世界震驚。四川省汶川、北川、青川等10個縣、市災情最為嚴重,嚴重受災村莊多達3700多個,大部分村莊90%以上的房屋倒塌,鄉村自然和文化遺產遭到破壞,生產生活設施損毀嚴重。
1.1農村設施損失巨大
地震造成農村建筑物與基礎設施大量損毀,例如四川彭州龍門山鎮寶山村,14座小水電被毀,5座度假賓館倒塌,56位村民死亡失蹤,608戶房屋倒塌;四川茂縣鳳儀鎮坪頭村農民房屋全部倒塌;四川北川縣東溪溝村農民房屋全部倒塌,新規劃的農家樂旅游和觀光農業化為泡影此次地震還波及甘肅省隴南、天水、平涼、白銀、武威、定西、慶陽、甘南、臨夏等9個市州,其中甘肅省距離震源相對較近的隴南市災情最為嚴重
1.2傳統文化損失巨大
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物質文化損失,物質文化中尤其以建筑文化的損失最為突出,特別是具有羌族特色的建筑——碉樓和羌寨損毀慘重。四川省汶川縣古羌王遺都蘿卜寨,具有4500年歷史的羌族村寨文化遺產民居全部倒塌;汶川的威州地區、雁門鄉、龍溪鄉、克林鄉、綿篪鎮五個鄉鎮,傳統的羌族民居里沒有一棟完好的建筑四川理縣桃坪鄉桃坪羌寨,3座著名的古碉樓出現裂縫,樓尖部分垮塌,2000年歷史的羌族村寨民居全部倒塌地震波及甘肅省隴南市的5個藏族鄉震情非常嚴重,兩萬余名藏族人受災非物質文化損失也非常慘重,北川縣文管所保管的館藏文物已全部被毀
1.3次生災害損失仍在持續
地震的瞬間威力令人瞠目;而另一種容易被人忽視的威脅——次生地質災害將長期侵蝕災區農民的家園和生存環境。北川、汶川、理縣、茂縣等地的高半山地區地質災害首當其沖,這里同時又是大量寶貴的羌族聚落的聚集區。鱗次櫛比的羌房碉樓也許經歷地震屹立不倒,但隨著雨季的到來,難逃被泥石流、山體垮塌淹沒的噩運。即使村落本身地質環境尚安全,其生產要素——土地、溝通外界的生命線等等也有遭地質災害破壞的危險。當代技術可以加固山體、堅韌的羌人也許可以在懸崖上開辟出土地、勇敢的工程人員可以反反復復搶通道路,但在長期存在的地質災害面前,為了幾百人云中棲居而付出的巨大成本就將難以接受。這是愚公也拗不過的事實,在自然兇猛而漫長的毀滅力面前,“人定勝天”這句話完全沒有意義。
2災后重建任務勢在必行
我們無法回避災難,但是我們可以選擇如何面對災難。眾所周知,災后重建工作勢在必行、刻不容緩;當然,災后重建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國務院抗震救災總指揮部在部署下一階段的工作中強調,要通過政府投入、對口支援、社會募集等方式籌集災后重建資金,加快災區恢復重建。
2.1物質環境建設勢在必行
在災后重建的工作中,農村物質環境的重建是必須首先考慮的,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民居建筑與基礎設施的恢復重建。保障災區民眾在最快的時間內安定生活與恢復生產,是需要并重的物質環境建設目標。在針對農村居民安定生活的民居建筑恢復重建過程中,活動板房的建設對于他們來說既不適用也不經濟,在原有村落或者原有民居建筑的基礎上,進行修繕、加固、維護、改造可能是比較現實的途徑。當然,對于那些被徹底摧毀的村寨,可能還要涉及到村寨新址的選擇與新型村寨的規劃設計,同時涉及到民居建筑的設計與建設。在針對恢復生產的基礎設施建設中,道路交通與電力供應等是需要從區域的角度進行統籌安排的,而農業機械與生產工具等設施則需要因地制宜,逐村逐戶分別對待。
2.2精神家園建設勢在必行
在物質環境建設的同時,受災區域精神家園的建設必須同步進行。一方面,災區民眾在精神上遭受了巨大的創傷,需要社會各界的關懷與撫慰。另一方面,災區農村多為少數民族地區,包括羌族與藏族,他們的宗教信仰與生活習俗是需要關注的,諸如村寨宗教活動場所與裝備的恢復重建、民居建筑中佛龕與祭祀設施的恢復重建等。這樣,不僅可以讓災區村民重歸原來的生活傳統,同時讓他們可以重建生活的信念,進一步重振民族文化。
3傳統文化保護非常迫切
在災后重建的過程中,無論是物質環境的建設,還是精神家園的建設,都必須注重傳統文化的保護。物質文化的保護也許是非常顯見的和具有共識的,而非物質文化的保護可能不容易落實,所以更需要加以關注。
3.1物質文化保護非常迫切
羌族傳統村落與農宅具有完整性和體系性,包括在村落演變過程中形成的聚落形態體系與建筑體系。村落從組織肌理、空間結構到建筑的布局形體、裝飾細節往往具有完美的和諧感,并與所處環境有機共生。這種體系是村民長期文化認同的載體,是寶貴的物質文化遺產,在很多情況下也是最適應環境最安全的人居形態。此外,羌族建筑特色鮮明,特別是羌族碉樓與石砌民居,充分體現了羌族人民的智慧,是值得保護的物質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在災后重建的過程中,村寨的保護可能面臨兩種挑戰:一是無意識的影響——即指各種社會力量為了幫助災區農民盡快安居,而建設脫離原來村落與原有傳統的村寨及民宅,或者在原來村寨中置入大量異質性內容,導致建設性破壞。二是價值觀的擾動——即村民自己在外來文化與外來資金的影響下,不滿足于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并且盲目引進外來的建筑類型進行建設,導致村落體系的破壞。上述兩個方面,都是造成物質文化方面的“次生災害”。通過長期深入研究,試圖把握地方聚落的結構和部分文化內容,并在新的建設中予以繼承,是有可能實現的。但如何在體現災后重建迫切性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減少對傳統體系的擾動是值得思考、而且非常迫切的任務。
3.2非物質文化保護非常迫切
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民協主席馮驥才先生在《緊急保護羌族文化遺產座談會》上講到:中華文化的多樣性主要表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上,我們的少數民族文化大都是非物質文化遺產,而大部分又不在城市里。物質性的東西受到損毀可以進行修復,甚至可以重建,但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旦消失了,比如傳承人沒有了,文化的根脈就斷絕了,就永遠沒有辦法銜接 羌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包括羌族宗教文化、禮俗文化、服飾文化、傳統節日、民間藝術、生活方式等等。同時,由于羌族沒有文字,羌族語言、文化均靠年長者口授身傳來傳承。會羌語的長者、通曉羌族歷史文化的“端公”等對羌文化的記述和傳承至關重要,所以,羌族文化的保護,首先是人的保護。
3.3傳統文化保護面臨的問題
3.3.1村落建設缺少技術力量
大量農村地區傳統民居建造手藝高超,但建設現代建筑方面技術力量薄弱。成本不低、結構不合理的新農宅比比皆是,在這次災害中損毀慘重。但統一的技術標準在農村地區并不適用。各地、各村、甚至各戶農宅的地理環境、經濟條件、風俗習慣都有很大區別。一刀切的工程技術要求部分農民無法承受。如何以低成本植入專業技術力量協助農宅建設,是個艱巨的課題。也許通過調研制定因地制宜、成本不同的技術導則,以及明確政府監督負責的制度,比編制技術標準更有意義。即使制定技術標準,也必須盡量體現地域、成本的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