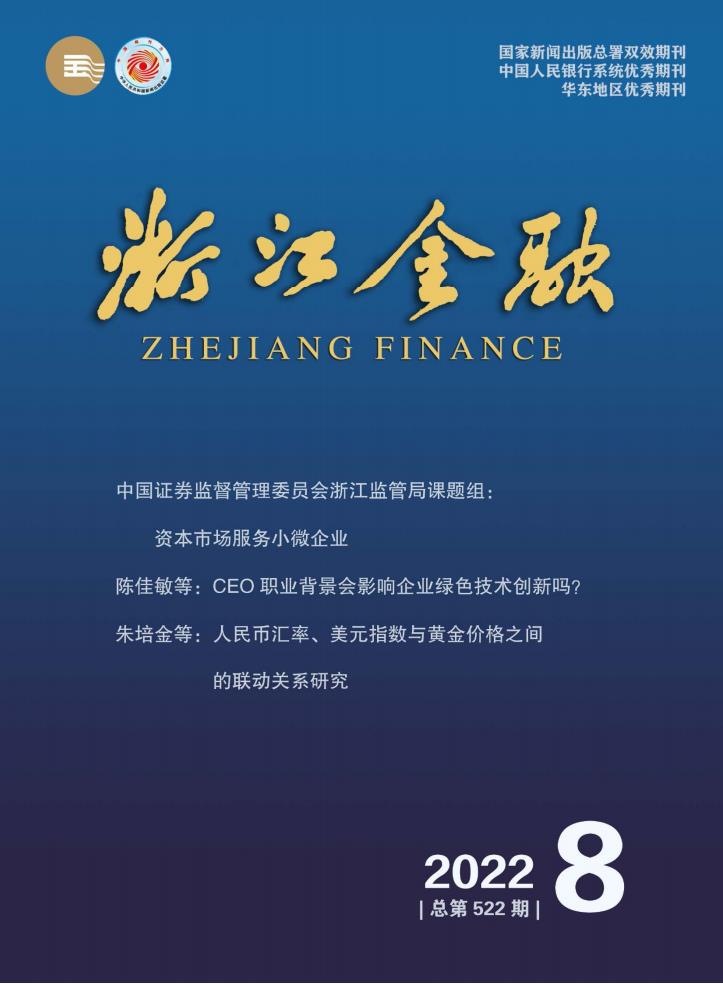論倫理學與詮釋學的內在關系
龔群
一、 就人類的學術史而言,“倫理學”這一學科是自從亞里士多德對人類科學進行學科化的研究后才有的。然而,倫理學這一人文學科在不同的著作家那里,是完全不同的。究其原因,倫理學是一門人文社會科學,在不同時代的著作家那里,它所反映的是那個時代的實踐理性精神以及那個時代對于倫理學的學術要求。如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倫理學是德性倫理學,主要集中論述的是人的德性問題。在康德那里,則是道德哲學,他從人的普遍道德理性上論證人的道德何以可能的問題,在黑格爾那里,則成了法哲學。黑格爾把個體的道德意識看成屬于道德的范疇,而把家庭、市場以及國家都看成是倫理實體。德國的近代現代哲學家布倫坦諾、舍勒和哈特曼等則把倫理學看成是價值倫理學,認為倫理學的中心論題是價值。如布倫坦諾認為,一如真理認知在于確定真理的“存在”與“非存在”一樣,價值判斷首先是對象的“善”與“惡”的直觀把握。知識本身是一種價值。舍勒則認為,肯定價值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肯定的價值。元倫理學則把對于倫理道德的概念分析以及道德判斷句的邏輯分析看成是倫理哲學的基本任務。不過,元倫理學的出發點是事實與價值的區分,這種事實與價值的二元論認為倫理領域是一個與事實無涉的價值領域。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有多少倫理思想家,就有多少種倫理學。 在眾多學者那里倫理學有著如此不同的面貌和實質,那么,有沒有一個思想家們大致認同的學術畛域?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還得回到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說:“倫理德性則是由風俗習慣熏陶出來的,因此把習慣(Ethos)一詞的拼寫方法略加改變,就成了‘倫理’(Ethike)這個名稱。”(1) “倫理”這詞的字面意思與品格相關,而它來自于習慣與風俗,品格的德性來自于習慣。后來,羅馬人使用的拉丁文,沿用了古希臘的“Ethike”這一名詞,在拉丁文中寫成“Ethikos”。“倫理”這一概念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人所養成的習慣(成為德性),二是社會風俗習慣。海德格爾曾指出,倫理這一概念在古希臘語言中,具有人的居所的含義。社會的風俗習慣是人類存在的精神維度。在原始人那里,是風俗的統治。正是風俗決定人的特性,人的品格。一個地區、一個部落的風俗,決定了這個地區、這個部落的人的精神特質,決定了人們評價人、衡量人的社會標準和尺度。同時,風俗本身也內化到人的內心,成為人的品格,這就是亞里士多德所稱之為的倫理德性。現代英語、法語、德語中的“Moral”一詞的詞源是拉丁文中的“Moralis”。這個詞是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在翻譯希臘的“Ethike”時創造的一個詞。因此,在詞源學的意義上,“倫理”和“道德”在意義上是同一的東西。“Ethike”和“Moralis”這兩個詞是指一種比我們今天所言的人類的倫理道德現象更為本原的人類存在現象。它既是社會共同體的共同的存在因素(風俗),同時也指個體(品格、習慣)作為人而存在的因素。因此,“Moral”這個詞本來并不具有中國古代漢語的“道德”這詞的意思,也不具有現代英語中等西方語言中的“道德”這詞的意義。“Moralis”這個詞其意思是與“More”(意為“品格”、“作風”、“習慣”、“風俗”)相關的東西。而我們今天使用倫理與道德這樣兩個概念,都應當看到在它們所具有的人類本性這樣深層次的意蘊。因此,無論是亞里士多德的德性論,還是康德的絕對命令,還是黑格爾的倫理實體,都是人類的這種深層次的倫理本性的某個方面的體現。 其次,倫理學領域是以善與惡為基本范疇的對象領域。亞里士多德在其著名的《尼可馬科倫理學》的響亮的開篇詞中所說的:“一切技術、一切規劃以及一切實踐和選擇,都以某種善為目標”,(2)深遠地影響著倫理學的理論特性。這里所謂的“一切”,指的是人類的一切活動,為什么人類的一切活動都具有一個這樣的特性?這是因為,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人類從其本性上是一種志趨優良、志趨更美善的生存的社會動物。人類與其他非智力動物的區別就在于,她從本性上看有一個至善的目標,她就是趨向這個至善的存在。而其余一切善目都是因這個終極性善而存在。“在實踐中,確實有某種以其自身而被期求的目的,而其他一切目的都要為著它。”(3)在這個意義上,倫理學不僅是關于人類的存在的精神品格或精神性現實因素的現實描述,而且是關于人類的應當的學說。前者又可稱為實然性,后者又可稱為應然性。在有的倫理學家那里,側重的是前者,如亞里士多德;有的側重的是后者,如康德。然而,不論是何種倫理學,都離不開善與惡這對范疇。因為人類的善的追求,本身是在與惡的斗爭中展開的。人類要通過自己的努力提升自己,也就潛在地包括了對自身不完善的確認。這種不完善性實質上是一種惡。中世紀基督教以上帝與魔鬼的對立形象地說明了人類處境的這種二元性。如果說,善的追求來自于人性,邪惡的因素同樣來自于人性。怎樣使人除惡向善成了倫理學研究的一個基本領域。這是因為,在規范倫理學看來,倫理學的職志與使命在于使人趨向于善,提升人的道德境界。 值得指出的是,倫理學不是把人在本性上志趨優良看成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命題。人為何具有道德本性的問題,歷來是倫理學探討的形上本體問題。從古希臘的“倫理”的原始意義看,倫理學所回答的是人是什么的問題,即涉及到人的存在本體的問題。倫理學所要研究的就是孟子所言的人與動物相區別的那一點“幾希”。人之所以區別于其他動物,就在于人有道德。也就是說人是有人性的。孟子以“四心”說力圖回答這個問題。認為人在道德上的向善性是人的先天本性。而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存在著自然的人性與教化養成的人性的差別。自然的人性有著內在的向著道德的人性轉化的需要。是社會生活本身提供了這樣一種轉化的途徑。 人的道德性并非是人在本原性意義上就有的,狼孩的故事生動的說明了這點。如果自然人在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最初幾年中失去最初的社會化機會,這個自然的個體將永遠不可能獲得人性,他將永遠不可能變成社會人。在這個意義上,人成為人是人對自我的塑造。人對自我的塑造表明人有著將自然的本性改變為社會的、道德的本性的內在潛能。人性本身就是這樣的一個成長的過程。因此,也可以說,只有人可以在確定自己的本性方面起著根本性的作用。即使生理、心理、精神和歷史方面的狀況極大的制約著個人,但不同的個人有著自身的不同可塑能力。如果從人與其他動物相比的角度看,則是沒有任何生物能像人那樣創造自己的世界。彼德·伯格說:“(與動物)相比,人在出生時的本能結構既非專門化地且非直接地適應于一個種類的特殊環境。在上述意義上,不存在人的世界。人的世界是通過自己的建造而逐漸形成的。這是一個開放的世界,即,這是一個必須通過活動來塑造的世界。”(4)當然,人塑造自己成為人因而具有多方面的特性,但由于人的活動在本性上有著一種趨向善的特性,在這個意義上,人類所有與此相關的活動都可稱為道德活動。在這個意義上,人通過自己的行為活動所創造的世界也就是一個具有道德意義的世界。實際上,道德價值對于一個人作為人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如果一個人沒有財富、美貌、地位,人們可能不會認為他有什么不幸,但如果他成為一個騙子、殺人犯或盜賊,這與不幸又有了質的差別,人們會認為這是一個人作為人的失敗。這種失敗表現在人是什么和作為人他必須做什么的層次上。 人的行為活動的趨向善或背于善的特性,就是人類活動的價值特性。人通過教化、通過自己的價值活動,能夠對自己的本性作出決定,能夠化性起偽,決定自己是什么人或成為什么樣的人,從而建構一個道德價值意義的世界,使自己獲得作為詮釋者的詮釋視域。因此,沒有作為道德世界的活動的人,也就沒有作為詮釋者的詮釋活動的人。加達默爾指出:“人之為人的顯著特征就在于,他脫離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東西,而人之所以能夠脫離直接性和本能性的東西,就在于他的本質具有精神性的理性的方面。‘根據這一方面,人按其本性就不是他應當是的東西’——因此,人就需要教化。黑格爾稱之為教化的形式本質的東西,是以教化的普遍性為基礎的。從某種提升到普遍性的概念出發,黑格爾就能夠統一地把握他的時代對于教化所作的理解。向普遍性的提升……是在總體上維護人類理性的本質規定。人類教化的一般本質就是使自身成為一個普遍的精神存在。”(5)加達默爾認為,如節制、審慎等行為活動都體現了我們追求普遍性的這種實踐教化的本質。是教化使我們脫離我們的自然性,從而使我們成為一個精神性的存在者,并因此而形成我們的視域。加達默爾從教化的本體奠基性上將倫理學與詮釋學內在關聯起來。 同時,道德活動本身也內在具有詮釋性的活動。“人的活動趨向善或背于善”,這本身是一個價值判斷,不同的行為主體對于道德價值的選擇,先在性的前提就是價值判斷。而要進行價值判斷,其先行條件就是人必須進行價值理解,理解與領會是人的生存論的結構因素。價值理解通過對既存的價值體系或價值系統的詮釋,達到一種生存意義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人對價值的創造和自我創造,是以詮釋理解為前提的。 哲學詮釋學所言的詮釋理解,對于作為理解者或解釋者所面對的任何對象,都可以把它看作是文本,加達默爾曾指出,歷史活動就是這樣一個大文本。對于社會道德價值,也是這樣一個文本,需要詮釋者的詮釋理解。不同的詮釋者對于道德價值,出于自己的體驗和經驗,必然會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有多少道德價值的詮釋者,也就有多少種解釋。然而,對于道德價值的詮釋多樣性,并不意味著人類在道德領域里必然陷入相對主義。麥金太爾認為我們處在一個相對主義的道德文化環境,但并不意味著他就持有相對主義的觀點。在麥金太爾看來,任何道德規范、關于善與惡的價值觀念,都可以從它所派生的社會制度背景中尋找到源頭。道德觀念總是與社會一起變化,而不是隨著社會變化而變化。因為(道德)價值是社會存在本身的構成因。 倫理價值的這種確定性根源于一定的制度背景的相對穩定性。但我們也要看到,制度背景并不是僵死地存在于人的活動之外。它為人的活動提供背景,同時也存活于人的活動之中。人的活動總是有所理解的活動。在這個意義上,理解也具有建構社會存在的功能。同時,這樣一種共存于人的活動中的人類制度,也為善的的解釋提供了一種客觀依據。人類的善并非是一種虛無化的價值。并非虛無化,因為可以找到某種非個人的標準,這種標準,可理解為詮釋者所共識的東西。即使在一個多元主義的時代,還是可以找到共識的。如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中所提出的交*共識(overlap)的論點。羅爾斯認為,雖然人們不可能在任何問題上達成共識,但我們仍可以在共同關切的政治領域等公共領域中達成共識。不過這種共識不是普遍全整式的,它只能是交*共識。這種共識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任何一個社會成員都生活在一定的社會制度結構之中,我們每個人“對這一基本制度結構能因生而入其中,因死而出其外(這大概是我們可以適當假定的)。在我們看來,我們已經物化,仿佛不是從任何地方來到這社會世界中的某一位置上的,按照我們的幸運或惡運來看,也仿佛無所謂利弊好壞。我之所以說[我們仿佛]‘不來自任何地方’,是因為我們沒有任何先驗的公共認同或非公共認同:我們并不是從某個地方來到這個社會世界上的。”(6)任何一個人生存于這個世界上,他所生活的社會的社會制度,是他所行動與思考的社會背景。這是一切政治共識觀念的前提。但這并不意味只有一種合理性的善的觀念。在現代立憲政體下,各種相互沖突的無通約性或無公度性的學說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在立法中所提出的所有涉及或接近于憲法根本或基本正義問題的問題,也都應該盡可能地通過公民們以同樣方式認可的那些原則和理想來加以解決。惟有可能理性地期許全體公民認可的政治正義觀念,才能作為公共理性和公共證明的基礎。”(7)交*共識的理念與政治正義的理念相輔相成,它是各種合乎理性的完備性學說達成的。在這種共識中,各種合乎理性的學說都從各自的觀點出發共同認可這一政治觀念。而社會的統一就建立在對這種政治觀念的共識的基礎上。或者說,體現不同價值的學說都可以從自身的價值領域出發,達到對共同的正義原則的不同理解。這種不同的理解在涉及正義的根本問題上可以達到共識。 羅爾斯這里所說的是關于正義原則的共識理念,但他所講的共識之所以達成的原理,對于所有人類共同經營的領域都是適合的。詮釋者出于自身的需要或出于自我的體驗與經驗,出于自我的教養,得出自己的詮釋觀點,對于不同的詮釋者而言,這些論點可能是不同的,但對于人類價值文化的建構都有所貢獻,并且并不意味著不同的價值文化視域沒有產生共識的可能。這種共識產生于共同的社會背景,產生于作為共同體的成員對共同善的追求,或者說,是生活世界中的具體的價值確定性使得人們有了共識的可能。 這里意味著兩種根本性的問題,一是詮釋學的任務向“有意義的對話”的擴展(8),二是善的價值的問題。首先我們討論第一個問題。加達默爾說:“凡是在沒有出現直接理解的地方,也就是說,必須考慮到有誤解可能性的地方,就會產生詮釋學的要求。”(9)現實生活中的多元性價值觀念的存在,人們對于事物產生誤解或理解分歧的可能性隨時隨處可見,在這個意義上,就有詮釋學的要求。這種詮釋學的任務在于對陌生性的克服,在于不同理解或誤解與歧意理解之間產生對話是否有可能。因此,在加達默爾看來,理解首先是指相互理解。“人們大多是直接地相互理解的,也就是說,他們相互了解直到取得相互一致為止。了解也總是對某物的了解。相互理解就是對某物的相互理解。語言已經表明,談論的東西和涉及的東西并不只是一個本身任意的相互理解不必依賴于它的談論對象,而是相互理解本身的途徑和目的。”(10)也就是說,人們的相互理解總是指向某種東西,這既是理解的途徑,也是理解的目的。加達默爾指出,人們的相互理解需要人們的話語交往,理解本身是在語言交往中形成,因此,意義理解與理解時的語境是直接相關的,同時,加達默爾還提到人們的語言對話的藝術,如提問的藝術、回答的藝術以及反對和拒絕的藝術等對理解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加達默爾認為,這些都是輔助性的,詮釋學的任務所需要的達成意見一致或形成共識,總是回到一種傳統,或者說,詮釋學對不能理解或理解發生歧義的地方,總是要回到一種一致意見,而意見一致是通過趨同的傳統達到的。因為在加達默爾看來,某種像支持意見一致的東西已在一切誤解以前存在。(11)說到底,也就是回到前理解,回到前理解所內蘊著的習俗和傳統,換言之,理解的前提已經從邏輯上蘊含了共識的可能。(12) 加達默爾對于“共識”提出了另一種理解,即他從文化傳統而不是從制度背景意義上強調共識的可能。實際上,強調傳統并不是否定制度背景的意義,而是在一種更為深遠的意義上再次強調了制度背景的作用。這是因為,任何傳統因素要起作用,都不可避免地存活于現存的制度背景中,或者說,作為制度背景的文化因素而起作用。不過,加達默爾的這一“回到傳統意義上的共識或相互一致理解”的論點遭到了哈貝馬斯的批判。哈貝馬斯認為,傳統本身也是可以質疑。在他看來,無論哪一種意見一致在原則上都是可以批評的。傳統語境本身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一種武斷性,而且也受種種壓制力量的支配。這種壓制力量使得主體間的同意變形和扭曲,并一貫地歪曲日常交往。哈貝馬斯從社會交往的意義上提出,要真正達到意見一致或理解上的共識,就需要預期地建構那種沒有強制的交往,在這種理想交往中建構休戚與共的共存結構。只有在這種理想的話語語境中,才可達成真正的共識或相互理解。換言之,非強制的普遍同意成為可能的生活方式,才有真正的相互理解。因此,哈貝馬斯把他對共識或一致性理解的希望建構在一種社會烏托邦之上,即理想的話語語境上。毋庸置疑,不受強制的自由的交往語境是交互主體達成交往性共識或一致理解的一個交往前提,但哈貝馬斯在這里只強調了交往條件的重要性,沒有認識到,即使是有了這種合理交往的社會前提,人們達成共識或相互一致性理解的實質性內涵是什么?這種內涵如果有,它為什么所蘊含?在我看來,這就是羅爾斯所強調的最基本的社會結構所體現的社會價值與共同善。理想的對話前提僅僅是排除了對于真理的遮蔽條件,并非意味著真理本身。無論我們的詮釋學對話在怎樣理想的前提下進行,所要達到的真正共識就是對于共同善的理解。怎樣的善才是社會共同的善?就一個正義合理的社會制度而言,這種共同善存在于最基本的社會結構之中。在現代社會中,這些善的最基礎性條件是為最基本的自由平等的理念所闡明的。自由與平等既是最基本的正義理念的核心內含,同時又是現代民主制的最高理念。自洛克以來直至羅爾斯的自由主義傳統一再指出了這一點。 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或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時期中,為社會基本結構所體現的共同善與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或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可能并不相同。如亞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共同善就是共同體的成員在一種德性生活中對于共同利益的追求與分享。自由主義所理解的共同善(基本善)則建基于個人權利的基礎上。但我認為,人類歷史上的共同善,盡管有不同的形態,但都可看作是對人類至善的分有,是人類對至善的認知的不同階段性成果。人類不可能窮盡對至善的追求,但任何至善都一定涉及到人類的共同利益。而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共同利益都可看作是至善的體現。倫理學的任務就在于闡明這個歷史過程中的善以及作為終極性目標的至善。對這種善的認知,對于詮釋者而言起著先在性的作用。對什么是共同善或至善的認知實際上起著詮釋者的視域的作用。它存在于詮釋者的視域中,構成某種詮釋的出發點。但善的知識正如加達默爾所指出的,它并不是一種先學而知的東西,我們是在對善的追求中才知道什么是善的,在對善的追求的成功與失敗中認識到什么是真正的善,在交朋友的實踐中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同時,善的知識本身也具有流動性的特點,它并非凝固在思維中的某個點上。但是,我們總是在某種善的知識背景下進行理解與詮釋的。 當然這樣講并沒有否定概念講明的作用。清晰的概念既是倫理思考也是詮釋理解的前提。蘇格拉底作為一個街頭哲學家,畢生所做的工作就是教導雅典的青年,將他們從混亂的道德認知中解脫出來。但對任何一個生活中的人講授道德學,與講授數學物理等自然科學根本不同在于,他并非空無道德知識,他原本就過著一種道德生活。倫理的實踐性與哲學詮釋學的實踐性是內在相關的。我們是在詮釋理解的實踐中才能有對某種文本的理解。如果我們沒有任何有關本文的知識,我們自己沒有相應的視域,我們不可能理解相應的文本。在這個意義上,人生的體驗與經驗對于倫理實踐和詮釋實踐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性作用就碰在一起了。實際上,這兩者就是一個東西。我們在倫理道德的實踐中獲得我們的道德教化,形成我們的善的觀念、價值觀念,同時也獲得我們的詮釋視野。 社會世界以及人化的自然界是人作為倫理實踐者和詮釋理解者的雙重身份所創造的。人類的行為活動所及的任何事物,都留下了人類作為道德實踐者的價值印記。當然,就社會世界與人化的自然界的價值蘊含來說,如果說人化的自然界僅有人類的價值印記,那么,社會事物都可看著是人類的價值的凝結。社會事實內蘊著人對價值的理解與追求。因此,社會事物又可說是價值事物。對于社會價值的不同理解,必然產生不同的價值內含物。人類的精神外化而產生的一切道德行為、一切行為活動,以及一切活動的產物,都凝結著人類對至善的追求,對美的追求(亞里士多德就是這樣理解的)。人類每對道德價值或對美的概念的重新定義,重新詮釋,都可能改變或推進人類對價值的創造。價值世界是一個每日都有新鮮事物的世界,這根源于人類對于美善的無止境的重新詮釋與追求。“止于至善”實際上說的是無限追求。因為人類永遠不可能完善地達到這一終極目標。
注釋: (1)亞里士多德:《尼可馬科倫理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頁。 (2)同上書,第1頁。 (3)同上書,第2頁。 (4)Peter Berger,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C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9.p.5. (5)加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頁。 (6)[美] 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頁。 (7)[美] 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第145頁。 (8)加達默爾:《真理與方法》,第232頁。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得不提及當代丹麥學者P.肯普的觀點,即他認為,詮釋學與倫理學是內在沖突的。我們看到,加達默爾的詮釋學與倫理學的聯結體現在兩個維度,一是從人文主義的主要概念如教化等體現倫理因素,二是話語對話。當然我們還談到價值理解。但肯普認為,詮釋學是存在的哲學,它的主要對象就是人從屬于“效果歷史”。而人的存在,本質上是語言學的,人對自我的認知或自我理解是通過敘述形成的,人通過敘談論過去或某種實在,通過敘述表現人的歷史性處境,敘述提供了生活的圖解。肯普指出,這樣,他人起什么作用呢?他人或是講述者,或是聽取者。但這些作用幾乎沒有為倫理學和對他人的關心開拓地盤。他說:“在當前的解釋迷的爭論中,倫理學并沒有起重要的作用,因為,在語言中或通過語言,對存在的關注拒絕或輕視對他人的關注。”(P.肯普:“解釋學與倫理學的沖突”,北京,《哲學譯叢》,1987年第2期,第45頁)我們也確實看到,加達默爾的詮釋學是從個體主體出發的,而不是以他者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的。即使是從個體的詮釋理解擴展到對話性相互理解,仍然不是從他者視野出發。從他者視野出發的倫理學與從主體存在出發的倫理學確實是兩個理論向度,而且前者更具有倫理學的意味。因為倫理不僅意味著對自己的善,更意味著一種道義關懷。我完全贊同肯普對加達默爾的詮釋學的批評。但不過,我們不能僅因詮釋學缺少這一理論向度而否認詮釋學與倫理學有內在關聯的一面。 (9)加達默爾:《真理與方法》,第232頁。 (10)同上書,第233頁。 (11)參見哈貝馬斯:《解釋學要求普遍適用》,北京《哲學譯叢》,1986年第3期,第31頁;同時參見加達默爾:《解釋學問題的普遍性》,載《哲學解釋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7頁。 (12)后來加達默爾在回答德里達提出的三個問題時,加達默爾再次強調了在達到共識或意見一致中對話的作用。他認為,即使是那些使人們聯系在一起并使人們成為對話伙伴的那些因素,也并不一定意味著他們能夠在理解或相互之間完全一致。就是在兩人之間,這也要求一種永無終止的對話。這同樣適用于靈魂與其自身的內部對話。他說:“當然我們會不斷受到種種限制;我們各說各的,互不相干,甚至處于與我們自己的矛盾誤解之中。但在我看來,如果我們沒有共同行進長長一段時程(甚至在我們自己也不承認的情況下),便完全無法做到這一點。整個人類的團結,全部社會的穩定,都以此為前提。”(“加達默爾與德里達的一次對話”,《哲學譯叢》,1991年第3期,第78頁)在這里,加達默爾只字沒有提及對話的語境。實際上,任何對話都是在具體語境下的對話,即使是內心的對話,也有心境因素在起作用。 (13)加達默爾:《科學時代的理性》,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1頁。 (14)同上書,第44頁。 (15)同上書,第67頁。 (16)同上書,第68頁。 (17)同上書,第42頁。 (18)同上書,第85頁。 (19)同上書,第43頁。 (20)同上書,第1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