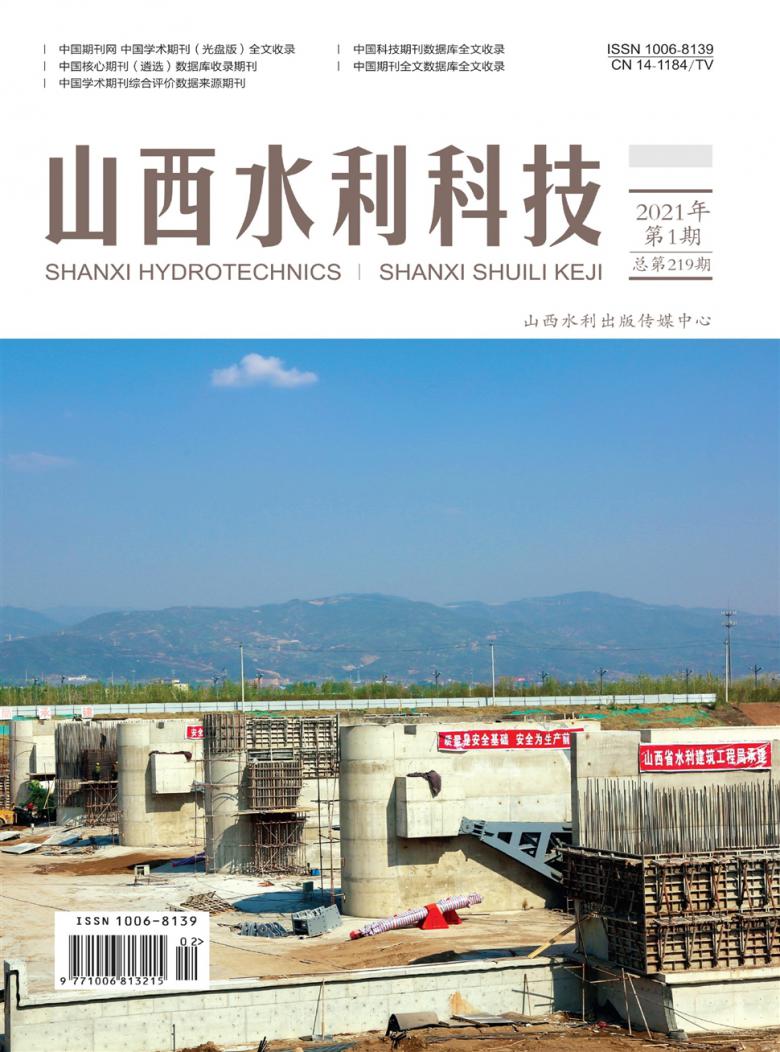神學倫理學的當代意義——"奧斯維辛"和"文化大革命"所引出
楊慧林
在二十世紀人類的記憶中,"奧斯維辛"(Auschwitz)和"文化大革命"也許是最深刻地凝結了一切苦難的經驗。從而后人無論就何種意義進行追溯和表達,這兩個已經符號化的事件都會相互在精神的進路上,使人的存在、創造、理性、信念和價值遭到根本的質詢。對于當代人而言,無法面對這一質詢的任何思考,都不再具有人文學的性質。
"文化大革命"與"奧斯維辛"之間固然存在著種種不同,但是它們至少在兩個維度上使東、西方不同的生存經驗得以溝通:其一是集體無意識的幻想、狂熱及其合力的無可遏制;其二是人類既有價值、秩序和規范的脆弱。正是因此,當代中國人所面臨的文化問題才與西方人日益相似。這兩個事件之間的可溝通的部分,成為東、西方在同一起點上進行思想對話的基礎。
對"奧斯維辛"的反思,實際上已經融入西方人文學研究的各個方面。從朋霍非爾(Dietrich Bonhoeffer)、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弗羅姆(Erick Fromm)、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保羅·利科(Paul Ricoeur)、阿蘭德(Hannah Arendt),一直到90年代以來的哈斯(Peter Haas)和費辛(Darrell J. Fasching)等人的新作,(1)"奧斯維辛"問題或隱或顯,但都從不同的角度將追問引向人文學的一些基本關注。這種關注對以往的"真理制度"(discursive form)所表示的懷疑,似乎使人類的全部精神活動都不得不帶有重新進行倫理選擇的性質。因而純粹的倫理學話題,或許會更多地離開應用的層面,而轉入它們的內在依據。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確實早已被"徹底否定"。80年代以來便不斷有文學作品,回憶錄及理論探討試圖對之進行批判和總結;近些年更是借助一個海外女作者的群體,通過自傳式的"小說"使中國人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個體經驗引起西方的強烈反響。(2)但是迄今為止,這些見諸文字的表達基本上只是否定曾經有過的"真理的結論",甚至只是建構一種"世人皆醉我獨醒"的那西索斯神話(narcissistic myth),(3)卻很少涉及到導致那些"真理結論"的"真理制度"本身。在原有的"真理制度"之內、持守原有的邏輯方式和話語系統,任何對"真理結論"的"徹底否定"實際上都很難奏效。因為,這種批判的起點已經注定使它失去批判的張力。更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世俗倫理的標準及其慣性,都潛在著相當強大的消解力量,乃至隨時都可能將人們已經意識到的問題重新納入一個圈套,使之自我消解、化為烏有。這種世俗倫理的標準和慣性有如布魯赫(Ernst Bloch)所描述的"代碼"(Code),一旦接受這樣的代碼,也就接受了其中限定的意義;因為"言說的一方所采用的代碼,本身就規定了對方的話語的形式。"(4)基于這樣的考慮,我認為當今東、西方思想界就此進行對話的前提,首先應當是建立和分享一種共同的"問題意識",即:"奧斯維辛"與"文化大革命"所延伸出的根本問題究竟是什么?它們留給后人的思想空間究竟在哪里?我們的一切問詢和談論在何種意義上才是有效的?
一、西方學者關于"奧斯維辛"問題的一種歸納
在西方學者對"奧斯維辛"問題的諸多研究中,比利時魯汶大學保利菲(Didier Pollefeyt)博士的一篇文章特別值得一讀。(5)他的討論是從維辛多(Simon Wiesenthal)《向日葵》一書的一個耐人尋味的情節開始。(6) 《向日葵》的作者描述了自己在納粹集中營的特殊經歷。有一天,他被帶去見一個垂死的納粹士兵,那個士兵講述了自己參與屠殺一群猶太人的故事,然后對他說:"我知道我所講的是駭人聽聞的。在長長的夜晚,我不得不躺在這里等待死亡的降臨,我愈來愈渴望把這些事講給一個猶太人聽。并且求他寬恕。不過,我不知道還有沒有猶太人活著。"在一陣可怕的沉默之后,作者什么也沒有說,離開了那個房間。
保利菲博士認為:受到迫害的猶太人能不能、或者應不應該寬恕一個垂死的納粹,這關涉到兩種倫理選擇的尖銳對立。其一是懲罰犯罪者的沖動和責任,其二是容人改過自新的憐憫和良知。前者出于正義,后者出于仁愛。當它們互相面對時似乎都很難成為實際的倫理選擇,但是就其自身而言它們確實各自具有充分的理由。
維辛多的故事,將我們帶回歐洲中世紀就已經存在的上帝的四個女兒之爭的事件上。(7)同時它也使我們不得不想到:真理、正義與憐憫、和平的爭論可以在《農夫皮爾斯的夢》中輕易地化解,可以被《威尼斯商人》賦予喜劇的形式,(8)為什么會在"奧斯維辛"之后特別突出地成為一種相對性的倫理悖論呢?
在猶太思想家那因拿斯(Emmanuel Levinas)看來,毫無限制的憐憫忽略了人的自由和責任,因而也藐視了人的尊嚴,所以他提出:"如果將寬恕極端化,就是建立一個非人道的世界。"(9)還有一些基督教神學家也由于納粹的罪惡而特別強調"正義"的世俗倫理原則,譬如詹姆摩亞(James F. Moore)曾經寫到:"既然我們看到寬恕會在巨大的暴行面前粉身碎骨,基督徒便面臨一個問題--在日常的情境之中,我們能不加分辨地談論寬恕嗎?……至少,奧斯維辛使(寬恕)這一基督教神學的核心觀念蒙上了陰影。"(10)
但是問題在于:如果說人類及其倫理原則不能抗拒、也無法避免"巨大的暴行",那么所謂"正義"便能彌補"寬恕"的脆弱嗎?"上帝的四個女兒"一旦進入世俗的語境、一旦成為現世的倫理原則,她們之間還存在多大的分歧呢?
這種質疑,或許應當是保利菲博士文章的焦點;盡管他是從兩方面提出自己的問題:第一,"能夠因為巨大的罪惡將宗教化簡為倫理嗎?"第二,"寬恕在今天仍然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嗎?"然而,對這兩方面問題的追問,似會導致不同的結論。
保利菲博士認為:"在奧斯維辛之后,關于罪惡的不同倫理見解意味著對寬恕的可能性及其限度的不同看法。"因此,他將"罪惡觀"分為三種基本模式。
第一種模式被稱為"惡魔化"(Diabolicisation),即:把犯罪者視為非人的惡魔,從而可以對罪惡盡情地表示憤慨和譴責。"惡魔化"使犯罪者成為"非人","復仇"便也獲得了合法的理由。"復仇"所帶來的,常常又是新的罪惡,因此如作者所說:"在反抗法西斯主義的時候,反抗者本人恰恰也可以變成法西斯主義者。"
另一方面,"惡魔化"實際上是將"善"的理想與人類社會必然地聯系在一起。譬如作者引述到1962年在耶路撒冷判納粹劊子手艾殊曼斯(Eichmanns)一案,公訴人就是將此案看做"兩個世界的沖突":光明的人類世界和相反的黑暗世界。人類固然可以這樣描述自己的理想,但是"這種幻覺也產生了一個文明的神話,即:奧斯維辛并非現代文明的邏輯結果,而只是墮入了野 的……悲劇式的沉淪……"(11)
更重要的是,"惡魔化"所體現的善惡二元觀,為人提供了心理上的極大安慰。只有將犯罪者視與我們迥然不同的"非人",我們自己的身份才不會受到威協。所以這樣的善惡二元論,是把善惡的區分轉換為"我們"與"他人"的區分,把罪惡置于"我們之外"。作者指出:除去"納粹",還有許多概念都潛在著相似的內容,譬如"外來戶"、"外籍勞工"、"同性戀者"、"精神病人"、"猶太人"、"吉普賽人"、"失業者"、"非信徒"、"異己分子"等等。通過"向外"指稱罪惡和譴責罪惡,通過使"我們"抽離于"他人",人們隨時可以為自己的價值選擇找到合法性的依據。
作者由此得出結論是:"惡魔化"是"復仇"的邏輯基礎,它甚至為人類的相互仇視提供著合理的道德形式。只要對罪惡采取"惡魔化"的態度,"寬恕"就無從談起。因此西方學者針對"奧斯維辛"的反思,從70-80年代開始出現了"反惡魔化"(dediabolicisation)的第二種態度。(12)這也正是"罪惡觀"的第二種模式。
保利菲博士將第二種模式稱為"普泛化"(Banalisation)。它與"惡魔化"剛好相反,即:不再是強化"我們"與犯罪者的界限,卻更加關注"每一個人"和"人類整體"的"罪性"及其潛能。譬如猶太哲學家阿蘭德(Hannah Arendt)就提出:在持續了十幾年的納粹大屠殺之中,實際上有成千上萬的人參與其間,卻很少人產生道德上的負疚感,這是"惡魔化"的善惡二元論所不能解釋的。因而即使確實存在一些惡魔式的納粹分子,其人類也不足以構成真正的危險,更可怕的倒是參與、容忍或者回避暴行的眾多的普通人。這樣現代社會的"罪惡"與人們以往的認知有所不同;(13)最主要的問題已經不是為什么會有人作惡,而是為什么大眾不以其為惡。
"普泛化"將追問引向"我們"的倫理生活和"我們"的文明秩序,使"奧斯維辛"不再是一個"道德的例外",而只能是西方社會的邏輯結果,這當然要比"惡魔化"深刻得多。但是,"普泛化"也確實有可能為犯罪者提供托辭,乃至罪惡似乎都是被一系列社會、歷史、政治或者心理的因素所決定,犯罪者不僅不是自我選擇了"惡的行為",反而同樣是"惡的環境"之受害者。
如果上述托辭成為"普泛化"理論的落點,那么它非但沒有實現"反惡魔化"的初衷,而且恰好以另一種方式滿足著人們對道德慰藉的虛幻的心理需求。二者的區別,不過是歸咎于"他人"還是歸咎于"社會","向外"指稱罪惡的基本思路并未改變。就這一意義而言,保利菲博士針對上述兩種模式所批評的"過高"或者"過低"估計"個人的自由選擇",似乎不是問題的關鍵。而他所論及的第三種模式,則是從"向外"的脫罪、延伸到"向內"建立罪惡的倫理依據。
保利菲博士的第三種模式被稱作"護罪"(Apology of Evil)。根據"普泛化"的罪惡觀,有人認為"奧斯維辛"的暴行只是由于專制的國家制度將人蛻變為毫無思想的機器,只是由于大眾的無知及其對權威的盲目服從。而事實上,人們對罪惡的參與常常并不那么被動。因此"護罪"理論所揭示的,正是從"非罪"的動機導致"犯罪"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說,是為"犯罪"作出"非罪"的解釋。
的確,人類歷史上的許多罪行也許并不完全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是為了更高的道德原則或者政治原則、為了民族的前途或者某種虔誠的信仰。在一場真正的災難之中,實施暴行和遭受暴行的雙方常常是同樣在譴責"不道德"。就連希特勒也認為德國的衰敗是道德墮落的結果,要挽救德國就必須"重振道德"。保利菲博士在文章中還引述了希特勒本人的判斷:"只有日耳曼民族使道德律令成為行動的指南"。(14)
"護罪"理論以及"奧斯維辛"所代表的暴行似乎可以說明:任何一個群體都有能力對善與惡做出全新的闡釋,這些闡釋的誘人之處,足以使整個群體坦然地投身于罪惡;他們并不需要拋棄道德,只需要用自己的方式去界定道德。所以在保利菲博士看來:"納粹的屠殺持續了多年,(在德國)卻沒有任何政界、法律界、醫學界或者宗教界的領袖提出有意義的反對。……人們發現:納粹主義的倫理原則……與西戶的倫理歷史存在著某種承接,……因而德國人接受納粹的屠殺十二年以上,卻仍然認為自己是有道德的人,……仍然認為這是實現納粹的更高目標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既然如此,那么諸如"負疚"、"寬恕"等問題根本不存在:于是"罪"也得到了最徹底的消解。
上述三種模式的核心問題,或許可以納入這樣的概括:"惡魔化"是歸咎于他人,以成全自身的清白;"普泛化"是歸咎于社會,以擺脫個人的責任;"護罪"則干脆使"罪"成為"非罪"。三者共同的實質,都在于通過論說而使道德主體不必為罪惡承擔責任。因此與其說這是"罪惡觀"的三種模式,不如說是"脫罪"和自我慰藉的三種途徑。
保利菲博士關于三種模式的許多描述都相當精采,但是由于對上述核心問題的理解略有不同,他直接轉向了犯罪者的心理因素以及"寬恕"的意義。按照他的分析,"社會角色的不分裂"(fragmentation of different social roles)和"自我欺騙"(Selfdeception)既是人們得以在罪行中生存的方式,又是人類罪惡不斷延續的原因。要解決這一問題,唯一的辦法便是絕對的"寬恕"。因為任何"不寬恕"都只能使犯罪者更加懼怕被群體和自我所拋棄,從而愈發自我封閉,并且為自己的行為尋找更多的理由。這似乎就是作者所說的"對寬恕概念的后奧斯維辛闡釋。"
然而,絕對的"寬恕"真的可以通過解除犯罪者的恐懼而結束罪惡嗎?"寬恕"就是"奧斯維辛"的苦難所能換來的真正教訓嗎?這一點,或許可以從中國人的經驗中得到進一步的討論。
二、"文革"經驗與上述模式的對應
毫無疑問,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20世紀后半葉最具影響力的事件之一。中國社會和經濟格局的真正變化,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獨立思索,都是繼此而始。除去激烈的政治角逐和權力之爭,"文化大革命"也像"奧斯維辛"一樣,伴隨著殘酷的迫害、暴行甚至殺戮。但是它所留給后人的問題,卻并不僅僅在這里。譬如:
第一,"文革"初期的暴行往往是假手于"紅衛兵"或"造反派",許多人認為其中的殘酷是由于"破四舊"的運動摧毀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基本的道德規范。然而除去綿延了數千年的傳統道德,1949年以后的各種"思想教育運動"也并非僅僅教人"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特別是對于青少年,"尊重師長"、"助人為樂"等等正面價值實際上仍然是主要的教育內容。那么這一切何以在1966年8月的一夜之間全然失效,代之以血腥、野蠻,甚至對自己親人的毅然決然的仇恨呢?(15)毛澤東青年時代的一聲"造反有理"何以能激起那樣強烈的回應?而傳統道德以及此前的"共產主義教育"何以那樣地不堪?
第二,"文革"前各級領導人,被"大字報"揭露得體無完膚;其中除去"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項政治性批判之外,更多的內容都是指向其個人的品德(譬如生活腐化、道德敗壞、賣友求榮等)。而新產生的領導人又閃電般地更換,一旦下臺,新的道德申斥必定隨之而起(16)這種循環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上至"四人幫"被"打倒"、毛澤東"走下神壇",下至基督組織的種種矛盾,"道德批判"始終是相當普遍的方式。值得思索的是:在最不道德的暴行之中,一方面是道德約束的全然失效,另一方面卻是如此之多的"道德批判",此種"道德"究竟為何物?同時,如果按照"道德批判"所揭露的"事實"及其邏輯推論下去,那么傳統道德所依托的"理想人格"有可能存在嗎?
第三,對"文革"的一項重要否定,在于指出它是個別領袖人物"錯誤發動"的結果。但是"文革"之前早有一系列殘酷的政治運動(僅管后來也被--否定),只不過涉及的對象有所不同,打擊的范圍沒有那么"史無前例"而已。
如果說"文革"是毛澤東個人的"錯誤發動",那么此前歷次政治運動的參與者和受益者是否毫無責任呢?如果"文革"的對象和范圍有所收斂,像以往的政治運動一樣,是否就不會被視為一場災難呢?
第四,作為"社會良心"的代表,中國知識分子在"文革"之后"痛定思痛",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一些措辭激烈者大談"中國知識分子被強奸了四十年"的時候是否還記得:"文革"當中大批飽學的知識分子惟恐效忠而不為人知,改造而不夠徹底,"風口浪尖"而"經不起考驗",敢于"痛"中言"痛"的又有幾人?"文革"中的集體虛偽愈演愈烈,難道推波助瀾者聲稱自己"被強奸"就可以辭其咎?
第五,"文革"常常被描述為一出"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鬧劇,在這出鬧劇中每個人似乎都只是在表演的玩偶、都被別人牽動著引線。就連毛澤東本人,如果說是他給出了"第一推動力",那么他很快就發現自己也不能收控自如,甚至多少會被一個已經無法停止的巨輪所左右;只是他身處巨輪的軸心,被左右的程度略小而已。(17)他所接受的瘋狂崇拜就是一例,否則以他的學養和經驗,怎么會不知道一個凡人"道成肉身"的代價?這里的問題在于:當毛澤東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玩偶的時候,牽動那引線的究竟是誰?
對"文化革命"進行如上的反思,結論只能有一個,即:"文革"與"奧斯維辛"一樣, 典型地體現著一種集體無意義的歷史合力,同時也典型地暴露著理想價值在現世中的片面和限度。"罪惡"之所以得以實施、"惡魔"之所以得到成全,恰恰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從不同的角度參與其間;就終極的意義而言,在這種持久、巨大的罪惡之中,幾乎不可能存在什么純潔的"受害者"。而參與罪惡又能以多種途徑逃避自我譴責,則是因為自相矛盾的現世價值理念完全可以為任何一種選擇提供合法的解說。
集體無意義的作用和"自我保護"的心理暗示,還使人們實際上很難面對這一過于痛苦的事實,而寧愿借助譴責罪惡將真正的痛苦轉化。轉化的方式,則是"人之于味,有同嗜焉"。因此對于"后文化大革命"的心態的分析,正可以借助保利菲博士的三種模式。需要特別強調的,只是這三種模式的共同結果并不在于是否應該寬恕, 或者寬恕的理由何在, 卻在于是否還有人需要寬恕。
"惡魔化"的集中例證,也許可以說是從70年代末的"傷痕文學"到目前海外女作者的大批自傳式作品,以及二十多年來各種形式的回憶錄。許多這一類作品在控訴"惡魔"的同時,都會將某信主人公、某位遭到迫害的領導人、作者本人或者親人描述為清醒、理性的反抗者,描述為理想人格的化身;他們既可以潔身自好、不與流,又往往得到"惡魔"之外的"絕大多數人"的同情甚至支持。這樣的敘述自然可能含有某種程度的真實因素,然而就總體而言,任何有過親身經歷的中國人都知道這不是"文革"中的普遍事實。否則,群眾性的、似乎也很真誠的瘋狂又如何解釋?關于"受害者"之言行的一些史料是否必須改為?
在這一類回憶中發生作用的,更多的是一種文學的幻想。如果僅僅是作為文學的劇作當然無可厚非,而由此秀露的心態,恐怕無法排除兩種成分:其一是在"理想"導致的"罪惡"之中得新修復破碎的理想:其二是希冀在罪惡之后獲得虛擬的自我安慰。
"普泛化在中國的對應形式,是所謂"替歷史受過"說。這在理論界的一部分知識分子當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替歷史受過"當然意味著言說者不應當受過,從而特定社會歷史環境的決定作用使個人的選擇和責任幾近于零。這種"逃避自由"的邏輯結果,必定是在批判以往罪惡的同時仍然無法作出超現實環境的選擇,因此實際上永遠找不到一種可以追究的罪惡。
這種"決定論"的最大問題,也許在于徹底斷絕了反思人類理性及其歷史過程的可能性,使完全相反的"真理結論"可能不斷地導源于同一種"真理制度"。其中比較極端的例子,或可說是1989年"春之交"的許多"不同政見":僅管其立論似乎相當激進,但是其表達方式、語言系統與它們所要批判的東西如出一轍。這正是由于"文革"經驗未能得到恰切總結而留下的真正悲哀。
"后文化大革命"的"護罪"理論,與兩個基本的事實相關。
首先是在多年以后,人們逐漸感到"文革"很難被"轍底"否定。除去它從反面刺激出的經濟改革和獨立思想之外,60年代末期歐洲和美國發生的激進運動,以及薩特(Jean-Paul Sartre)、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新一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理論家,似乎都與之存在著一定的呼應;同時,"文革"式的藝述活動也從游離于政治的角度得到了人們的重新回味和評價。
其次是近些年的腐敗之風以經濟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使許多人開始懷念毛澤東時代的若干好處。在這樣的氛圍中,有人以學術的方式鼓吹"鞍鋼憲法",有人以新的神話讓毛澤東重新走上"神壇,民間以毛澤東書像"辟邪"之事更是屢見不鮮。
由此生發的"護罪"理論或者情緒,也許未必不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在反思"文革"經驗的意義上看,其結果同"惡魔化"和"普泛化"的觀念沒有多少區別,即:在一場巨大的災難過后,留下來的只是"今是而咋非"或者"咋是而今非"的論說,卻無法追究災難的原因和責任。如果進而再去論說"寬恕",那么可"寬恕"的對象何在呢?從增一個僅供論說的話題而已。
中國"文革"后的事實證明,僅管對"文革"進行了"轍底否定",但是除去非常有節制的措施之外,(18)并沒有誰一定要反對寬恕,而主張報復。即使在"文革"結束之初,也有一些典型、有趣,并且富于中國特色的通用說法,譬如"把帳算在四人幫頭上"或者"化悲痛為力量"等等。這一方面或許反映了"相逢一笑泯恩仇"民族氣度,另一方面似乎也使西方人所關注的"寬恕"無從談起。因為,既然除去已經"蓋棺定論"者沒有人應該為罪惡承擔責任,誰還需要寬恕呢?
至少就中國的經驗而論,"寬恕"的先在性并沒有因"文革"的災難而遭到動搖。但是"向外"指斥罪惡的邏輯和種種"脫罪"的論說,卻同樣沒有被"先在的寬恕"(Priori forgiveness)所改變,反而會使"寬恕"完全落空。因此"寬恕"不可能成為"文革"后重建論理秩序的基點。
三、問題:"寬恕"還是"追究"
自古以來,中國文化的傳統中并不缺少"寬恕",而"寬恕"的根據大都在于世間"善""惡"的相對性。如《太上感應記篇》已有"論心不論足"與"論足不論心"之辨;蒲松齡也說:"有意為善,雖善不賞;無心作惡,雖惡不罰。"總之,"惡"的行為紿終具有從"心"(觀念或動機)與"足"(行為或結果)兩方面進行論說、從而獲得"脫罪"的可能。但是這從來沒有制止新的罪惡,"文革"只是一例。
西方末必沒有類似的問題。譬如:按照一些基督教神學家的思路,可以從"愛"和"律法"的兩種意義上分別闡釋"金律"。(19)愛的誡命將金律帶向寬容,金律原則既能防止愛的邏輯導致無序、又能使愛在社會生活中落實。這樣,律法的辨證便成為愛的中介,而愛又激勵著律法。(20)然而即使這消除了"愛"與"律法"在神學理論上的緊張,在社會的實際運作之中,有時它可能依然會成為無效的循環論證。
基督教之"愛"與"寬恕"的邏輯,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尤其需要進一步的闡釋。其前提應當是一種外在于人的、永恒的"他者"(The Other),卻不僅僅是現實的人倫關系、善惡之間的理性選擇,或者相對化的社會制衡。中國文化傳統中始終潛在著一種動力,即世俗與神圣的合一、理性與信仰的合一、王權與與神圣的合一、行為規范與精神權的合一。因而儒學才可以被視為"儒教",一些現代的政治學說或信仰也很容易被宗教化(譬如"方化大革命"中的崇拜)。而在倫理問題上,也許恰恰需要這幾組因素的分離。否則,道德與否的最終判定必然受到現實利益的制約。
基督教傳統似乎應當對終極的倫理更為關注。但是從"奧斯維辛"所引申出的有產爭議和"寬恕"之說,可以看出在西方社會的宗教世俗化和倫理應用化的趨向當中,基督教的神學倫理觀也同樣需要重申與及"再闡釋"。離開"他者"的前提,絕對的"愛"和"寬恕"不僅無法被理性所確認,不僅無法解決內在的悖論,而且必然像任何一種世俗的道德規范一樣,無法從自身產生實際的約束力。
近代以來的倫理道德學說,實際上大都不同程度地執著于"契約"、利益的平衡和可操作性。(21)從"奧斯維辛"推演出的"寬恕",并非沒有保持平衡的"策略"上的考慮。而利益的平衡永遠都是相對的,道德主體以此為據的時候,恐怕不得不使"道德"本身承受雙重的風險,即:任何"不道德"都可以成為"道德"的權宜之計,任何"道德"都會變成一種缺少實際內容的、空洞的出發點。
因此"奧斯維辛"和"文化大革命"的經驗不需要以"寬恕"來化解,卻需要進一步的追究。所謂"追究"絕不意味著"不寬恕",它指向的并非任何個別人的"罪人",而是人本身,它質疑的并非某一種道德論說,而是"道德"本身。只有通過這樣的追究,神學倫理學的真正意義才可以凸顯。
神學倫理學家華斯他頓(Johan Verstraeten)曾提出一種基本的界定,即:"《圣經》的意義是元倫理(metaethical)或者超倫理的(transethical).。"(22)鮑他沙(Hand Ursvon Balthasar)則是從"信仰的倫理"建立自己的"神學美學"。(23)這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當屬一種棄"禮"而求"道"的化理觀,即如老子《道德經》三十八章所說:"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作為行為規范的"禮"缺失了道、德、仁、義的支撐,所以被老子視為"忠信之薄,而乳之首",卻并不能維系道德。
針對"奧斯維辛"和"文化大革命"的反省,必然要涉及到文化的歧義、道德價值的歧義和人性本身的歧義。而神學倫理學的視角也許可以這樣延伸我們的思考:在苦難中遭到動搖的倫理準則,必須回溯到一個穩定的支點;由此開始的不僅是現世道德秩序的重建,更是一種終極價值的依據。這一點,應當是全部人文學探索的進深之路。
注釋:
(1) 前者著有《奧斯維辛之后的道德納粹倫理的根本挑戰》Morality after Auschwitz: The Radical challenge of the Nazi Ethic,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92); 后者著有《奧斯維辛之后的敘事神學:從翼化到論理》Narrative Theology after Auschwitz:From Alienation to Ethics,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92).
(2) 這些發作者幾乎都末曾用母語從事過寫作,但是她們以自身經歷為基礎的作品幾乎都成為西方的惕銷書, 有的還被 譯作多種文字,甚至被譯回中文。較著名的如Zhang Hong 的Wild Swans, Min An-Qi的Red Arolle和Katherine ,另外還有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Red China Blues, Red Flower of China, A Leaf in Bitter Wind 等等。
(3) 即希臘神話中自戀的Narcissus,最后終因愛上自己的影子而惟悴致死,死后化作水仙花。這種敘述"文革"經驗的方式在上述"小說"和一些回憶錄中尤為明顯,乃至人們讀過這后常常會受到一種誤導,即:除去毛澤東本人以及林彪、"四人幫"等極個別的"壞人", 似乎沒有任何其他人應當承擔"文革"的責任。這樣,一場全民族的悲劇被過于輕飄飄地化解為只有少數人在表演的鬧劇。
(4) 文章課題為《奧斯維辛之后的倫理、寬恕和不可寬恕》"Ethics, Forgiveness and the Unforgivable after Auschwitz", by Dr. Didier Polleteyt, K.U. Leuven: Faculty of Theology, 1998.
(5) 布魯赫在《政治語言》一書的第9頁寫到:"…when you have allowed someone to speak in the code, you have practically accepted his proposal, "since" the code adopted by the speaker contains within itself a set pattern of speech for the other party."
(6) 英文版 The Sunflower,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97.
(7) 上帝的四個女兒即中世紀一些文學作品所描述的真理(Truth)、正義(Righteous-ness)憐憫(Mercy)、和平(Peace)。她們的爭論通常自然地分為兩組,正是保利菲博士在其文章中所及的問題。
(8) 《晨夫皮爾斯的蘿》The Version of William Concerning Piers the Plowman, 據認為是WilliamLangland(?-1388) 所作:《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 即 William Shakespeare of Venice即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的作品。前者描寫到基督受難后來到地獄,上帝的四全女兒在地獄門中爭論基督能否解救地獄中的靈魂,但很快就以基督的騰種告終。后者關于Shylock的控辯也涉及"正義"與"仁愛"的分歧,但最后終究是以喜劇的方式得以解決。
(9) Essays van Emmanuel Levinas, 46頁,Baam: Ten Have, 1984,引自保利菲博士上述文章。他的原話是:"Making forgiveness almighty is creating an inhuman world."
(10) Christian Theology after the Shoah, by James f. Moore, 140頁,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3, 引自保利菲博士。他的原話是:"The question became for Christians, can we even in everyday situation now that we see how forgiveness can crumble in the face of enormous atrocity.…At least, the shadow of Auschwitz looms over this central Christian theological category."
(11) 不另注出處的引文為保利菲博士上述語文章的觀點。
(12) 根據上述文章的介紹,第一部以納粹暴行為背景,有系統批判"惡化"的著作,是太女哲學空阿蘭德(Hannah Arendt)的《艾克曼在耶路撒冷:關于罪惡之普泛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4.該書出版后,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13) 在西方傳統中,"罪"通常被理解為妒、恨、驕、淫、貪、惰、怒等等道德缺陷。但是Hannah Arendt 在其書156-157頁指出:現代的極權國家已經改變了"罪"的特微。
(14) 此話的原文為:"…only the German race has made the moral law its leading principle of action." 原引自Hugh Redwald Trevor-Roper編《希特勒1941-11944年的秘密談話》第6頁 Hitlers Secret Conversations 1941-1944,N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World Lierature, 1961).
(15) 1996年8月曾有"紅八月"之稱,在北京率先發生了一系列"紅色恐怖"事件,譬如"抄家"、"批門"、"破四"(即所謂打破思想、舊風尚、舊道德、舊文化)等,"文革"的暴行自此而始。有的原領導人在兩年之內就被"批門"200多次。許多"紅 兵"剛剛"抄"完別人家,自己的父母也被"抄家"。另外揭發、批門、仇恨自己父母的青年學生也大有人在,特別是出身于"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家庭者。故而"暴行"并非"破四舊"的結果。
(16) 譬如最初的"中共中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簡稱"中央文革"),曾有原光明日報總編輯穆欣為成員,幾個月以后穆欣被"打倒",給人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什么政治問題,卻是被"大字報"猛攻的"道德污點。無論證據是否確鑒,此種攻擊一向最具殺傷力,"文革"語言中的"揭老底",此之謂也。
(17) 所以"文革"開始不久,毛澤東就在給江青的信中抱怨有人"欲要打鬼,借助鍾馗";后來以在與美國率者愛德伽·斯諾的談話中,對"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之稱以及到處豎立自已的塑像表示不滿。
(18) 譬如擔任第一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主任的陳云,曾經提出不能重用"文革"中的幾種壞人。但時間愈久,這一標準恐怕就愈難把握理
(19) Jahan Verstraeten《作為倫理意義之元倫理結構的圣經"世界"》" The Bible of the World as Meta-Ethical Framework of Meaning for Ethics",見《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圣經:闡釋學、價值與社會》,144頁Holy criptures in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Lslam: Hermeneutics,Values and Society, edited by Hendrick M.Vroom &Jerald D. Gort).
(20) 所以常有西方學者從不同的角度討論"不平衡也是一種平衡""A symmetry is a symmetry."
(21) 出處同注18,140頁。
(22) 請參閱Louis Roberts,巴爾塔隆的神學美學》一書The Theological Aesthetics of Hans Ursvon Balthasar,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7. 作者在該書第10頁寫到:"倫理學與美學的合一,是巴爾塔隆的代表性觀點。事實上,奠定巴爾隆美學基礎的信仰的倫理學,已經成為宗教哲學論爭的中心話題。如果可以說這是"信仰的美學",那么應當將巴爾塔隆視為這一論爭的核心。
(23) 請參閱Louis Roberts《巴爾塔薩的神學美》一書Theological Aesthetics of Hans Ursvon Balthasar,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7。作者在該書第10頁寫到:"倫理學與美學的合一,是巴爾塔薩的代表性觀點。事實上,奠定巴爾薩美學基礎的信仰倫理學,已經成為宗教哲學論爭的中心話題。如果可以說這是"信仰的美學",那么應當將巴塔 視為這一論爭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