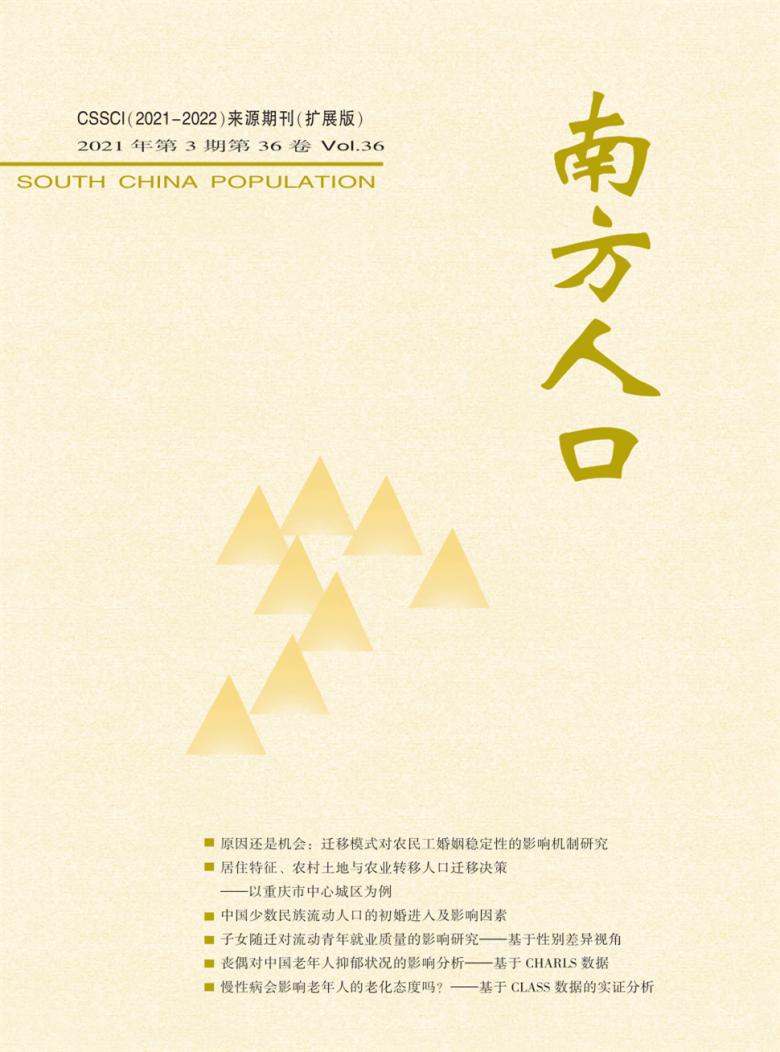論日本歷史上的三次法律移植
佚名
[內容提要] 本文旨在分析日本歷史上的三次大規模的法律移植,揭示其原因、過程、方式,探究法律移植給日本社會帶來的巨大變遷。法律移植作為近年以來法學研究的重大熱點問題,文中將闡釋本人對其的思考與見解。在我國當今的司法改革中,許多法學領域的進步和完善都必須涉及到法律移植。如何更好地利用法律移植來完善中國的法律制度——這是當今司法改革中值得法學家們深思的問題,也是本文的時代意義之所在。
[關鍵字]法律移植 日本
法律移植(legal transplant)是西方比較法學中經常使用的一個詞,其含義一般是:特定國家(或地區)的某種法律規則或制度移植到其他國家(或地區)。相當于中國國內所講的對其他國家或地區法律的借鑒或吸收等。但有時,移植的含義似乎又比借鑒等詞有稍多的意義。但也沒有太大的差別[1]。在西方比較法學作品中所使用的與“移植”相當的詞還有“借鑒”(drawingon, borrowing)、“吸收”(assimilation)、“模仿”(imitation)和“轉移”(transfer)、“傳播”(spread)、“引進”(introducing)等,但較普遍的還是“移植”。因為移植一詞最能生動、深刻、全面地揭示出某種法律被運用于另一法律體系并與之有機相融的現象。法律移植的形式多種多樣,可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類。從移植的內容來看,可分為全部移植與部分移植。前者是指將他國法律原封不動地全部輸入本國;后者是指有選擇地吸收他國法律中的某些因素。從移植的內容是一國的法律還是多國的法律來看,移植可分為一元移植與多元移植。一元移植是指移植者在移植時僅考慮和僅移植一國的法律;多元移植是指移植者在考察和比較多國的法律后,分別從這些國家的法律中吸取有用的因素。多元移植又可稱為綜合移植。從移植發生在法制運行的哪一個環節來看,法律移植可分為立法環節的移植與司法環節的移植。前者是指立法者在立法時移植他國的立法經驗、制定法、習慣法與判例法。法律移植通常是指立法環節的移植。后者則是指法官在司法實踐中直接適用他國制定法、習慣法與判例法[2]。法律之所以具有可移植性,主要是因為:
第一,法律移植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需要。一方面,經濟基礎的需要決定相應法律制度的產生,經濟基礎的變化決定相應法律制度的變化與其方向。另一方面,法律制度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法律制度通過對社會生活的控制和調節,保護和促進相應的經濟基礎鞏固和發展,排除其對立物。而在法學意義上,法律制度之間的差異,不只是方法和技術上的差異,也有法的時代精神和價值理念的差異。正是根據時代精神和價值理念的差異,各種法律制度中間有先進與落后、完善和不完善的區分。對于其法律制度仍處于落后和不完善狀態的國家來說,要加速法制進程,必須移植相對發達的國家的法律,尤其是對于后者法律制度中反映經濟共同規律和時代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則,要大膽吸收。若是把自己封閉起來,對先進國家長期積累的法制文明置之不理,繼續一點一滴地積累經驗,或者故意另起爐灶,那只能拉大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延緩本國法制發展的進程,以至喪失法制發展的機會。
第二,法律的技術性,即許多國家在解決某一社會問題時,總是要采取某些類似的法律措施。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法律各有其特殊性,但同時也存在著某些共同的、普遍適用的法律規則、原則和精神。這些共同的法律要素能夠為國際社會所認同,并且會體現在世界各國的法律制度中。這是因為人們雖然生活于不同的國家或地區,但具有人之為人的諸多共同屬性與特質,又面臨著生存與發展方面的諸多共同問題。這樣,不同國家或民族所創造的法律文明之間必然具有共同性或相通性,可以相互吸取和移植。同一時期不同國家的發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它們或者處于不同的社會形態,或者處于同一社會形態的不同發展階段。在這種情況下,后發展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就會遇到發達國家曾經遇到過的問題,而后者已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并形成一些行之有效、高度技術化的法律制度。這就為后進的國家提供了經驗。正如埃爾曼教授所說的:“當改革是由于物質的或觀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對新的形勢不能提供有效對策或僅能提供不充分的手段的時候,這種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成功或部分成功。”
第三,法律的相對自主性,即法律相對獨立于社會的其他領域(如宗教、倫理和政治因素等)。法律的自主性是現代社會中分工日益發達,社會關系日益復雜的一種表現。社會分工是法律產生的基本條件之一,而法律一旦脫離社會的物質生產而獨立起來,就會順著自身的運動方向運行。在人類歷史發展演變過程中,社會分工領域逐漸擴大,分工水平逐漸提高,社會關系日益復雜,社會結構各部分的功能也越來越專門化。依照杜爾克姆的說法,功能專門化一直是經濟、政治社會高度發展的前提和結果[3]。規模日益擴大的功能分化,必將伴隨著實現這些功能的社會要素之間的更大獨立性。法律在其成長過程中也日趨擺脫宗教、倫理和政治因素的束縛,獲得真正的獨立,日益鮮明地呈現出自主性。法律的相對自主性,使法律移植成為可能。
以上幾個方面表明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各國都不同程度地采用法律移植的手段完善本國的法律制度。其中,日本的法律移植,其時間之久,規模之大,范圍之廣,影響之深遠,是無與倫比的。日本法制發展的歷程,自始至終都貫穿著“拿來主義”。當代日本的法學,通過繼承日本的封建遺產(主要以中華法系為基礎),采用大陸法系之基本原則和框架(明治維新以后),吸收英美法系的許多學說、理論(主要是二戰后),從而兼容并蓄,日漸發達。其發展過程耐人尋味,值得探究。
一、 日本歷史上的三次法律大移植
1.“大化改新”對中國法的移植與日本社會的封建化
在“大化改新”之前,日本已相繼經歷了繩文時代、彌生時代、古墳時代等數個歷史階段。公元二世紀末,繼從中國和朝鮮半島傳入鑄造青銅的技術后,鐵器又傳入日本,隨著生產力不斷發展,日本開始出現部族國家。三世紀時,本州中部興起了一個比較強大的奴隸制國家“大和”,它不斷擴張,到五世紀統一了日本。然而,相比起大陸上的中國和朝鮮半島各國,當時的日本還是個相當落后的國家,政權和土地分散在豪族的控制下,依靠“部民”勞作實行奴隸制生產,勞動效率低下。當時日本的法律尚處在簡單的習慣法與蒙昧的“神明裁判”的統治下。據(唐)魏徵等《隋書·列傳四十六·東夷·倭國》(卷81)載:“其俗殺人強盜及奸皆死,盜者計賦酬物,無財者沒身為奴,自馀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弓以鋸其頸,或置小石于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屈者即手爛。或置蛇甕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螯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隨著航海技術的發展,日本與大陸上的中國、朝鮮半島諸國來往日益頻繁,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藝、科技文化、宗教思想等源源不斷地傳入日本,這無疑使整個日本社會對燦爛的中華文明萌生無限的羨慕之情與強烈的學習欲望。在頻繁遣使、不斷學習與借鑒的過程中,日本法律制度逐步被納入了中華法系之中。公元604年,“廄戶皇子(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年)取儒、佛二教之旨,斟酌隋朝之法制,定《憲章》17條,此為成文法之濫觴。當時中國文化之發暢已顯著,故日本上流之士競研究大陸之學,而圖國家制度之改良,既知儒、佛二教,復紹受隋唐之法制,自是歷事漸改舊時之不成文法,而編定公私諸法。”[4]而大規模地對中國法律的移植則是在“大化改新” [5]之后。 “大化改新”使日本的中央集權政治得以確立,日本的封建法制體系也得以建立。“大化改新”后,日本展開了一系列以中國法律為模式的法典編纂活動。
這些借鑒和吸收的成果主要體現諸多的律令典章中,據史料可查的“大化改新”后二百余年間頒布的日本法典有十余部。其中,以《大寶律令》和《養老律令》最具代表性,體現其借鑒唐律的立法特色。
《大寶律令》頒布于公元701年,共有《律》六卷,《令》十一卷,模仿唐律,以刑法為主,諸法合體。雖然至今難以斷定《大寶律令》的借鑒對象,但其移植唐初律令,吸取中華法律之精萃,是顯而易見的。而《養老律令》則是在《大寶律令》的基礎上于公元718年制定的,《養老律》包括《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12篇,500條,數目與《永徽律》均一致。在法律思想與法規的內容上,兩者間亦有大量相同或近似的規定。如在刑法的適用上,同樣有“一準乎禮”(完全依照儒家禮教)的立法思想,規定了嚴懲企圖危害朝廷與踐踏禮教的惡性犯罪(《唐律》規定的十惡與《大寶律》中的“八虐”基本相同,惟后者將“不睦”省并入“不道”,又因日本近親結婚甚多,而奸父祖妾又可并于“不孝”之中,故刪去“內亂”)和對特權階級的袒護(《唐律》中的“八議”,日本略去“議勤”、“議賓”)。《大寶律》照搬《唐律》的五刑二十等刑名(惟有流刑不明記里數,僅分近、中、遠流三等,或為日本國土狹小之故)。日本法律還吸收了中國法中重視親屬等級秩序、強調宗法血緣和同居相容隱等長期以來貫徹的家族制宗法觀念。在刑罰分則方面,日本法律的規定比唐律略輕,如《大寶律》規定:“(凡)闌入宮門,徒一年(《唐律》‘徒一年半’)”;“凡造御膳,誤犯食禁者,典膳徒三年”;“凡御造舟船,誤不牢固者,工匠徒三年(《唐律》以上均處絞)”;“毆打兄姊者,徒一年半(《唐律》處徒二年半)”等不一而足。尤其是在平安時代(公元九至十二世紀)中有三百四十年死刑刑措的記錄,據分析,與當時的日本社會普遍盛行佛教是分不開的。
在民法方面《大寶律》、《養老律》與《唐律》相似之處也甚多,但不及刑法。尤其是在繼承制度上,《大寶令》、《養老令》完全打破了《唐律》“諸子均分”的原則,《大寶令》中規定,動產的一半及其它財產的全部,由嫡子來繼承,剩余的財產才由庶子來均分,這是極端嫡庶異分主義的表現。《養老令》則改為:嫡母、繼母、嫡子各二分,庶子一分,女、妾各半分[6]。這種分歧的緣由,將在下文闡釋法律移植與本土化問題時予以詳述。“大化改新”后,從中國借鑒的法律制度奠定了日本社會嚴格的封建體制,延續千余年,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的明治維新時期。
2.明治維新對大陸法系法律制度的移植與日本社會的近代化
1192年,日本進入了幕府政治時期。1603年,德川氏取得了世襲的“征夷大將軍”的稱號,在江戶(今東京)設置了幕府。德川幕府統治時期(也稱江戶時代,公元1603—1868年)是日本歷史上繼鐮倉幕府(公元1192—1333年)和室町幕府(公元1336—1573年)以后又一個由將軍代替天皇實行全權統治的時期,幕府竭力維持日本的封建體制。在政治上,幕府將武士階層作為統治支柱,奉行架空天皇、削弱大名(地方諸侯),獨攬國家權力的政策;經濟上,“日本有純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組織和發達的小農經濟”[7],手工業和商業發展受到重稅和苛政的雙重限制;法律制度上,混亂和殘暴是江戶時代日本法制的主題,“自武家政治實行以來,刑法遂趨于殘酷,所謂‘《德川百個條》’ 者殆已登峰造極。即以生命刑而論。即有所謂‘鋸挽’(鋸兩肩,磔尸),‘磔刑’(以長槍貫穿兩脅及喉),‘獄門’(即梟首),‘火罪’(即焚殺),‘斬罪’,‘解死人’(割首棄尸)六種,蓋不啻人間之地獄也。彼時法律既不公布,而在今日所視為輕微犯罪者,恒皆被處死刑。”[8]在對外關系上,幕府堅持“鎖國”路線嚴防國外勢力乃至西方世界的思想意識、文化科技傳入日本,惟恐其構成對幕府封建專制的威脅[9]。在這樣的環境下,日本社會的進步可謂阻力重重。
但從十八世紀末起,日本社會逐漸發生了變化。一方面,社會生產力有了顯著提高,商品經濟日益頻繁,統一的國內市場逐漸形成。在規模不斷擴大的城市中,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但新興資產階級卻在各方面深受幕府的壓制;另一方面,隨著商品經濟滲入農村,出現了把土地租給佃農然后收取地租的新興地主。然而在封建領主集中了農業生產全部剩余的情況下,靠在領主與農民之間榨取的新興地主不可能得到充分發展。由此,新興資產階級與新興地主(其主要來源是思想較開明的下層武士)同封建幕府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加之十九世紀中葉美、英、法、俄等西方列強用武力打開了日本國門,在使日本人有亡國之憂的同時,深受西方文明之刺激,眾多有識之士意識到學習西方給本國帶來的希望。在主張效仿西方的維新派和頑固不化的幕府之間,一場激烈的沖突不可避免地爆發了。公元1868年(明治元年),幕府被推翻了。由此,圍繞著仿效西方制度,學習西方文明,振興日本民族的明治維新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了。
從明治維新初期新政府采取的廢藩置縣、“四民平等”、地稅改革、殖產興業等措施來看,目的都在于掃除阻礙日本社會發展的封建制度障礙。然而,只有在法律這一上層建筑領域建立一整套保障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法律體系,為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提供適合的土壤,才真正有望實現民族的富強。這樣的法律在日本的歷史上是不曾具備的,因此只有向西方國家(特別是擁有完備的資本主義法律體系和成熟的立法技術的法、德等大陸法系國家)吸取經驗,借鑒成果。另外,在明治維新前期日本與西方國家商討廢除治外法權等早期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過程中,列強以日本法律制度落后、法律體系不完備為由予以拒絕。這內外兩方面因素的結合,促使明治政府不得不對國內的法律體系進行徹底改革,依據西方近代法律理念來編繤制定法律,建立資本主義法律體系。
明治維新開始后,在政治上確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為法律的西化提供了強大的政治基礎。思想文化上,明治政府成立后,推行了文明開化政策,開始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文明。資產階級憲政思想、自由民主思想與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一齊涌進日本。西方著名法典也被廣泛地翻譯(1873年箕作麟祥翻譯出法國六法全書,率先系統引入西方法律制度)。與此同時,政府還興辦法律學校(以東京開成學校——東京大學法學部的前身和司法省法學校開風氣之先)、創辦法學刊物、聘請西方法律人才。這樣,就為日本近代資本主義“六法”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眾多部門法中,與社會生活最密切相關的法律,是民法與刑法。在明治維新初期的法律編纂活動中,首先著手進行的是刑律(即《新律綱領》,主要是參照我國的《大清刑律》進行修訂),但是近代化法典的編纂首先著手的卻是民法。明治政府建立伊始,就開始著手編纂民法典。最初主持這項工作的是被譽為“日本商鞅”的江藤新平,他的指導思想是“誤譯亦不妨,惟需速譯”,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所謂民法編纂實際上是將法國民法典在不做任何改動的情況下,翻譯過來即可。在兩任司法卿江藤新平、大木喬任等人的推動主持下,先后編而成的民法草案有太政官制度局的《御國民法》(明治四年)、司法寮的《皇國民法暫行規則》(明治五年)、司法省的《民法暫行法則》(明治六年)、《左院民法草案》(明治六、七年)、司法省的《明治十一年民法草案》(明治十一年)等。由于這些草案皆處于嘗試階段,很不完善,自然都未予施行。明治十三年,政府組織了民法編纂局,以法國學者G.E Boissonade(保阿索那特)教授為中心正式開始民法典編纂。明治二十三年(公元1890年),以《法國民法典》為藍本的民法典編纂完成,于同年予以公布。該部法典成為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近代意義上的民法典(是為“舊民法典”,也叫“保阿索那特民法典”)。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則——所有權的絕對性、契約自由、過失責任在“舊民法典”中得到明確的貫徹,財產及財產交易在各方面都受到充分的保護。[10] “舊民法典”的編別體例采取的自然是《法國民法典》的體例格式,但在其基礎上亦做了大膽的改良——不拘泥于《法國民法典》第二編(“財產及對于所有權的各種變更”)和第三編(“取得財產的各種辦法”)的結構,對其構成作了一些調整,并新增了債權擔保編、證據編兩編。這樣就構成了“舊民法典”的五編:第一編人事編;第二編財產編(又分為兩部——物權和債權及其義務);第三編財產取得編;第四編債權擔保編(又分為兩部——對人擔保和物上擔保);第五編證據編——證據和時效[11]。
“舊民法典”的公布,似一石激起千層浪,不僅在法學界,也在社會各界引起廣泛的爭議,圍繞著“舊民法典”的頒布實施,一場激烈的爭論展開了。這場大論爭最終以反對“舊民法典”的“延期派”戰勝擁護“舊民法典”的“斷行派”而告終,“舊民法典”的實施終宣告流產。探究“舊民法典”本身,我們不難發現其先天不足與后天缺陷:
其一,編別體例不甚合理。雖經保阿索那特改良,但仍遺留了許多《法國民法典》的固有缺陷。例如,“舊民法典”第一編中關于人格能力的規定與親族關系的規定就被混淆在一起;將有關物權的法規和有關債權的法規這性質不同的兩者一同規定在財產編中;把與身份關系密切相關的繼承法規放到財產取得編中等等。
其二,“舊民法典”中內容龐雜細密,有很多地方出現了前后重復或矛盾,而缺少一般性、原則性的規定,給實際應用帶來極大不便。更有甚者,“舊民法典”中夾雜有許多屬于公法性質的行政法規,如關于公共征收征用、不動產的登記及國民分限等公法方面的規定,超出了其私法實體法應有的范疇。
其三,“舊民法典”由于保阿索那特在起草過程中使用法語,在商討擬定后再轉譯為日語,使得法條行文晦澀難懂,甚至很多條文的意義模棱兩可,不甚明了。
最后,也是最最致命的缺陷在于:“舊民法典”極大脫離了日本當時的社會現實,背離了當初大木喬任司法卿所確定的“尊重固有傳統習慣”的指導思想。在“舊民法典”中存在相當多的同日本的風俗民情、傳統習慣不相適應的規定,尤其是在家族法方面這種傾向更為明顯。關于這方面,加拿大法學家、國際比較法學會主席克雷波(P.A.Crepeau)認為:“在某些領域,特別是在人、婚姻、家庭等法律領域,法律規則是基于根本不同的道德宗教價值觀念的。在財產法或勞動關系法領域的某些社會價值也是如此。在這兩個領域,‘法律移植’即將具有某種社會價值的法律引入不存在這種價值的其他法律管轄區中,必然是相當困難的。”[12] 為適應調和日本自古以來的以家為中心的家族主義和歐洲以婚姻為中心的個人主義的沖突,“舊民法典”的起草者做了不少努力,但在家族法部分即人事編及財產取得編中,更多的依然是直接從《法國民法典》的身份法照搬來的規定,與日本固有的家族傳統制度相去甚遠。對此,在明治二十四年八月發行的《法學新報》上,東京大學法學部教授穗積八束發表論文《民法出則忠孝亡》。同時他在《國家學會雜志》發表了《耶酥教以前歐洲家的制度》。這兩篇文章雖然不長,然而卻抓住了“舊民法典”的致命之處,尤其是前者以其富有煽動性的標題立即吸引了世人的關注。他指出:“我國乃祖先教化之國、家族制度之鄉。權利與法皆生于家……氏族、國家不過為家制之推移……然民法之法文精神,先排斥國教,繼而破滅家制……他們違背萬世一系主權與天地共長久之根本、祖先之教法和家制之精神。”[13] 其實,探究民法典論爭的內在本質,不僅要考察雙方爭論的主要內容,還必須將其放到當時特定的環境和時代背景之下來考察。經過明治政府的一系列努力,至民法典論爭之時,資本主義體系在日本已初步建立,但是日本社會及明治政府,仍然保持有大量的封建殘余,其最集中的表現就是天皇君主專制政權的保留。而東亞社會君主專制政權的社會基礎,乃是傳統的宗法倫理和家族制度。傳統家族倫理制度不保的話,君主專制政權便不能穩固。因此可以說,民法典論爭反映了當時日本特定的社會發展階段所出現的所謂進步的自由主義、民權主義思想與保守的國家主義、君主主義思想這兩種政治思想在法律領域里的沖突和較量。那么,在兩者力量懸殊的情況下,“舊民法典”施行的流產就不足為怪了。
民法典論爭結束后,伊藤博文內閣于1892年8月設置了“法典調查委員會”,由“延期派”穗積成重和“斷行派”富井政章、梅謙次郎負責對“舊民法典”進行徹底的修改,幾經周折,草案于明治三十一年四月提交國會通過,這就是所謂的“明治民法典”。“明治民法典”以當時最新的《德國民法典》第2章為范本,采取了《德國民法典》的體例,設立高度抽象化、一般化的總則編,以下分物權、債權、親屬同繼承四編(前三編為財產法,后兩編為家族法),在體例上無疑大大優于“舊民法典”。另外與“舊民法典”相比,“明治民法典”用語更為簡明扼要,通俗易懂。而在內容上,無論是財產法還是家族法都有自己的特色。在財產法部分,資本主義民法的三大原則和內容依舊得到充分的貫徹,例如有關權利能力平等的原則,第1條之三規定:私權的享有,始自出生;有關所有權,第206條規定:所有人于法令限制的范圍內,有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所有物的權利;有關契約自由,第91條規定:法律行為的當事人,表示了與法令中無關公共秩序的規定相異的意思時,則從其意思;有關侵權行為709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權利者,負因此而產生損害的賠償責任(這表明采取了過失責任原則)。[14] 而在家族法部分,則體現了與內容前一部分大相徑庭的特點,保留了大量的封建習慣。在民法典論爭中,“延期派”所堅持的維護固有家族法傳統制度的主張在“明治民法典”中得以采納,因此在家族法領域保留了大量習慣法,具有濃厚封建色彩的大家族制度基本上保留了下來,對以戶主權為核心的家制度與“家督繼承”做了具體而詳細的規定。這樣一來就構成了“明治民法典”的最大缺陷:財產法部分的“近代性”和家族法部分的“封建性”之矛盾。表面上,似乎這兩部分建立在不同的基礎和原則上,互不相關,并無影響。但實際上,經濟關系與身份關系是密切相關的,身份上的支配關系同經濟上的平等關系是互不相容的。“明治民法典”的“新”與“舊”這一內在矛盾,對日本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也就是這一點決定了二戰結束后家族法部分與財產法部分不同的歷史命運。前者被從根本上加以大規模修改,按照西方國家現代家庭精神,徹底廢除了家制度和“家督繼承”;相反,民法典財產部分經過一定程度的修改補充后,一直沿用至今。
《明治民法典》于公元1898年正式實施。此外,明治政府參照德國憲法,于1889年頒布移植的成果——《大日本帝國憲法》。1890年公布由德國人羅斯勒(K.H.F.Roseler)起草的商法典(“舊商法”),九年后公布實施了仿效《德國商法典》制訂的《明治商法》。1880年日本頒行了保阿索那特主持編纂的參照《法國刑法典》制定的刑法典(“舊刑法”),1908年又開始實施借鑒德國刑法的新刑法典。1890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同樣有德國法的濃厚痕跡。在步入二十世紀之時,日本已將大陸法系國家的“六法”體系成功地移植到了本國。縱觀明治時代移植法律之過程,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穩步的法律移植。明治時代的法律移植,并非從一個法律部門著手,而是自始就注重穩步建立一整套完整的近代法律體系。從上文列舉的數據可見,在二十年光景的時間內,日本完整地將大陸法系(特別是德國)的核心法律制度——“六法”體系移植到了本國。
第二,兩重的法律移植。從上文我們可知,當時日本無論是民法典、商法典還是刑法典的編纂,都在跨入二十世紀的前后由原先的借鑒法國法轉向借鑒德國法。圍繞著移植對象的轉變,當時社會上的爭議是極其激烈的,從“民法典論爭”中可見,支持派與反對派各抒己見、據理力爭。而在三次論戰中,最終都是支持的一方獲得勝利。其道理何在?第三點將予以揭示。
第三,與本國社會相適應的法律移植。在法典編纂之初,明治政府就以其是否符合國情為移植法律的標準,因此不惜工本,派遣高層次、大規模的考察團到歐陸各國考察國情,選擇與日本社會相適應的借鑒對象。從最初以學習法國法為主轉向后期以學習德國法為主,也正是基于對這一點的慎重考慮。但是,從維新伊始,明治政府在發展資本主義來富國強兵的同時,以振興民族之名,不僅保留大量封建傳統,而且將國家權力無限擴張,定君權,限民權。因而,在適應這樣的社會的法律制度(不論是公法還是私法)中,存在著強烈的封建性與強權性也是必然的。
第四,博采眾長、兼收并蓄的法律移植。明治時代的法律移植的對象最終主要都是德國的法律制度。但在法典編纂時也兼顧其他國家(包括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律制度,取其精華。例如,《明治民法典》參考了歐洲十八國的民法,《明治商法》在移植德國法的同時也吸收了法國和英國商法的一些內容,同時保留了本國傳統的商業習慣。正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這一點對于日本近代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功不可沒的。 3.二戰后的法律移植與日本社會的民主化。
明治維新使日本走上了富國強兵之路,但同時也使其走上了對內壓制民權,對外侵略他國的軍國主義道路。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日本社會在政治上完全處在法西斯勢力控制下,經濟上實行家族式的大企業、大財團的壟斷經營,國民經濟被完全納入戰爭軌道,整個社會君主主義和軍國主義思潮可謂登峰造極。法律淪為了暴政的工具和幫兇。政府制訂了一系列維護反動統治的政令:行政法方面的《國家總動員法》(1938年)、《國民征用令》(1939年)將整個日本社會拖入戰爭的恐怖中;刑事法方面的《思想犯保護觀察法》(1937年)、《戰時刑事特別法》、《國際保安法》、《戰時管制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法》(1942年)實質上剝奪了人民的一切公民權利,使近代奠定的刑法基本原則名存實亡。法西斯勢力還不擇手段地扼殺進步的法學思想和理論,迫害進步的法學界人士,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35年發生的“天皇機關說” [15]事件。日本法制出現了全面的大幅度倒退。
1945年8月,處于戰爭窮途末路中的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隨著同盟國軍隊的進駐,大規模的整肅運動在日本展開:法西斯勢力被加以肅清,壟斷財團也在戰后大幅度地被削弱,實行了農地改革,經濟開始向自由資本主義方向發展,軍國主義和君主主義思潮受到有效遏制。與此同時,在駐日盟軍的授意下,不但法西斯的戰時政令悉數被廢止,日本的法律體系也被向著民主化的方向加以改良。在這次法律民主化改革中,首當其沖的是憲法。1946年,由駐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主持制訂的《日本國憲法》公布了。這部新憲法與之前的憲法相比的主要表現在:(1)譴責戰爭,強調和平;(2)著重保護公民的民主權利,禁止特別立法予以限制;(3)削弱皇權,建立君主立憲的內閣制,確立了權力分立與制衡機制的資產階級憲政體制。緊接著新憲法的出臺,在刑法、行政法、經濟法、訴訟法等公法領域和民法、商法等私法領域均進行了相對應的修訂和改革[16],以到達內容與精神同憲法規定相一致。在這次法律改革中出現了日本歷史上的第三次大規模的法律移植,其特點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其一,外力支配下的法律移植。這與明治維新時期的主動、積極、開放地向外國法借鑒形成鮮明對比。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歷史清晰地表明:日本的封建傳統勢力是如此頑固,單靠其國內力量實現民主化是十分困難的,對日本社會的改造需要外力協助。同樣,法律制度的民主化,也離不開外部力量的積極指導。美國作為駐日盟國之首,在日本法律民主化過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眾所周知,美國憲法是近代史上第一部成文的資產階級民主憲法,以其三權分立的分權制度、廣泛的民主權利和嚴格的司法審察制度享有盛譽。美國的其他法律制度由于幾乎不曾受到封建法制的影響和傳統觀念的束縛,相比歐洲國家而言更能有效保障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為了使日本法律制度盡快融入民主化的時代潮流中,駐日當局有意識地將美國法律制度引進日本。在改革后的諸部門法中,都能或多或少地發現英美法系的影子。除了上文提到的1946年憲法,較典型的有1947年公布實行的《禁止私人壟斷及確保公正交易法》(反壟斷法),該法包括了美國兩部反壟斷法——《謝爾曼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的主要條款,在日本,甚至有人把美國的反托拉斯法稱為日本禁止壟斷法的母法[17]。在實行之初,該法的目的是結束明治以來日本經濟領域家族式大財團壟斷行業經營的局面,鼓勵和保障中小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發展自由經濟。而到了日后則對減輕和避免外國勢力對本國經濟的不利影響,保護本國工商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動和促進了日本經濟的崛起,故而被譽為“經濟憲法”。
其二,對英美法系法律制度的有限移植。二戰后的日本法律民主化改革中,移植的對象基本上都是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集中從美國法中吸收借鑒。與大化改新、明治維新時的法律移植不同的是,引進英美法系法律制度,并非意味著對原有大陸法系法律的全盤否定,而是在原有的基礎上的引進改良,并糅和以本國的法律傳統。以民法為例,1898年《明治民法典》其體系結構、概念術語,深受《德國民法典》草案的影響。由于這個歷史原因,日本的民法學也深深地打上了德國民法學的烙印。二戰后,雖然英美法學開始侵入日本,但由于日本民法典的結構體系未變,因而戰后日本民法學的發展,還是在繼受德國民法學的既成基礎上進行的,且向更加理性(繼去其糟粕,取其進精華)的方向發展了[18]。其他部門法亦莫不如此。除此以外,日本國民的法律價值觀也并未完全改變,許多傳統觀念,如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矛盾注重“以和為貴”的儒家理念仍深入人心,直至今日日本國民重調解,輕訴訟的社會風尚依然是日本法制的一大特色(1953年至1959年的鐵路交通人身傷害事故中,通過民事訴訟方式解決的不到1%)。總而言之,二戰后日本向英美法系的借鑒并未改變日本作為大陸法系國家的特點,而只是摻入了英美法系的部分特色。
其三,對美國法的繼受,具有內容上的選擇性,即側重于有關和平、民主的內容,而具體的操作技術則沒有改變。此處以日本的刑事訴訟法為例:在二戰前(尤其是1922年刑事訴訟法修訂后),日本受大陸法系國家訴訟制度的影響,在刑事訴訟中主要奉行職權主義,即認為追究犯罪是國家的職權,刑事訴訟中的主體是法院和檢察廳等國家機關,被告人只是處在消極的、被動的受追究之地位。這種刑事訴訟法原則,是西方“糾問式訴訟”思想的變種,其最大缺陷就是容易產生冤假錯案,侵犯被告人的基本人權。二戰后,1948年頒布了新的《刑事訴訟法》。其立法改革雖不甚徹底,但在克服上述弊端方面向前進了一步。新刑事訴訟法采用了“起訴狀一本主義”原則,即檢察官在提起公訴時,只向法院提交一份起訴狀,而不移送案卷和訴訟材料;廢除了預審制度;采用“令狀主義原則”,即偵察機關的強制措施必須根據法官發出的令狀,使戰前警察隨意抓人的現象不復存在;限制了被告人自供和傳聞證據的證據能力;對上訴審從原來的復審制改為事后審查;在審理和證據方面徹底貫徹“公審中心主義原則”和“當事人主義原則”;承認被告人有被保釋的權利。這部現行刑事訴訟法基本采取了美國刑事訴訟法的模式,但卻沒有采用陪審制度(與日本輕視司法的民風不無關聯),而且保留了許多大陸法系刑事訴訟法的特點,所以日本刑事訴訟法兼有兩大法系的特點,被稱作“混成法”。其中抗辯制度的采用對于訴訟制度的民主化意義最為重大,推動了日本司法程序領域的發展與進步。
二、對日本歷史上三次大規模法律移植的進一步探究
1.探究日本歷史上法律移植的原因
首先,討論日本法律移植在經濟上的原因。法律移植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需要。在本文的開頭已經闡述過,在歷史上,當一種先進的生產關系成為社會主流之時,就必然需要相應的法律制度保障和鞏固其發展。日本歷史上的三次大規模的法律移植,恰好都發生在其社會經濟發生重大轉型之時。六世紀初,日本社會以“部”為生產單位依靠部民間的簡單協作進行生產的奴隸制經濟向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封建小農經濟的轉變,促使“大化改新”后的日本朝廷尋求與之相適應的土地與稅制立法,但日本國內固然缺乏這類立法的經驗;而同時的中國唐朝,以《唐律疏議》的頒布標志著中華法系的建成和中國封建立法走向了成熟。到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的興起與統一的國內市場的形成需要自由的經濟體制和嚴格的私有財產所有權制度。但江戶時代的政令(如“棄捐令 ”——廢除武士債務的法令)卻往往站在其對立面,在當時的世界,唯有資本主義發達的歐陸國家制訂了保護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先進和成熟的民法典和商法典。二戰以后,日本經濟面臨向自由化轉型時,美國法向其提供了最佳的經驗。對與本國新興的生產關系具有共性的先進國家的法律體系的借鑒和移植往往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用較少的成本對國內新興生產關系提供完備的法律保障,促進社會發展進步。
其次,討論日本法律移植在思想上的原因。在十九世紀中期,位處東亞的日本與中國都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且都被西方列強用武力打開了國門,使西方文明得以侵入,為何惟有日本能較快且積極地向西方借鑒法律制度呢?一方面,日本資本主義生產自始受到的束縛相對較小,在明治維新后更是發展迅速,因而法制上的需要更為迫切;另一方面,得歸結于日本人較為開放,善于繼受的民族性格(日本人稱之為“國民性”)。早在“大化改新”之前,當先進的中華文明傳入日本、日本人見聞中國之盛況時,他們便為之心醉,爭相效仿,無論是建筑服飾、工藝器具,直至語言文字,都極深地打下了中華文明的烙印。從此以后,大和民族善于繼受的國民性就形成了。除此之外,直到近代,日本人始終不曾有過中國那種作為冊封體制的核心而自認為天朝大國俯視萬邦的心態。日本在“戰國時期”(公元1467—1573年)后遠離了冊封體制,不需要用“安撫”之類的觀點、方法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系,便利了其與外部世界的聯系與交往[19]。同時由于武家政治的緣故,日本也未仿造中國實行嚴格刻板的科舉制度,知識分子受儒家正統觀念的束縛也較少,相反在江戶時代后期,隨著以“蘭學”為名的西方思想文化傳入日本,社會上學習西來知識的“蘭學家”越來越多,極大促進了西方文明在日本的影響——這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不存在的。特別是在開埠后,面對先進發達的西方和傳統落后的東方之間的巨大反差,日本社會“脫亞入歐”的呼吁日漸增多,包括法律在內的各項制度的西化就顯得水到渠成了。
最后,討論法律移植與外力影響的關系。事物的發展,內因雖起決定性作用,而外因亦可起到促進或延緩的作用。在日本近代和現代的法律移植中,外力的促進作用是顯著的。1886年明治政府在與列強的“改約會議”上保證在10年內改造全部法律制度以換取列強廢除治外法權等不平等條約,這促使日本在短期內推出民法典、商法典、民刑事訴訟法等移植大陸法系法律制度的成果。二戰結束后,日本法律的民主化改革更是美國一手策劃指導的結果,在短期內即讓日本的法制面貌大為改觀。
2.日本法律移植的方針——廣泛地借鑒與吸收
無論是古代、近代還是現代的日本法律移植,無一例外地貫徹了廣泛借鑒與吸收的移植方針。這體現在兩個層面上:一方面是法律移植時空上的廣泛性。善于“拿來”的國民性讓日本人在移植法律過程中善于借鑒各種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法律制度。奈良朝廷在法律移植中遍擷唐代武德、貞觀、永徽乃至開元時期的律令格式;明治政府的法律移植也不僅遍訪大陸法系國家不同時期建立的法律制度,還開始涉足英美法系;盡管二戰后的法律移植以借鑒美國法為主,五十年代起仍有大批學者赴聯邦德國留學、考察,回國后成為日本法學界的中間力量。另一方面是法律移植范圍上的廣泛性。縱覽三次大規模的法律移植,無不是在整個法律體系上大刀闊斧地開展的。就前一種廣泛性而言,只有博覽各國法律制度,才能更多地發現每一鐘法律制度的特點和長處,從而帶有選擇性地加以吸收,增加法律移植所帶來的價值。就后一種廣泛性而言,在整個法律體系進行借鑒改良,無疑在法律移植后避免部門法之間在法律內容和精神上出現重復和矛盾,保持整個法律體系的和諧一致。
3. 日本法律移植的過程——謹慎地本土化
前文已論及法律適應社會的重要意義。如果機械地將外國法律生吞活剝,那么其勢必由于與本國國情的脫節難以很好地適應社會,其在國民中的認可度和權威性勢必得受到影響,法律實效也可能將比預期大為降低,甚至產生種種負面作用。因而,將外來的法律制度本土化——對其加以改造后使之符合國情,適應社會的需要——顯得十分必要。法律本土化是為了使法律效果達到最大化,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日后法律制度與社會上通行的觀念習慣產生的矛盾。例如日本的班田令與唐代的均田令就有許多不同之處。日本對均田令的引進分為好幾鐘情況:均田令中與日本國情完全適合的條文,被班田令全部照搬使用;不太適合日本國情的條文,則是吸收其中的基本原則,進行適當的增減,以適應本國的需要;而那些完全悖于日本國情的條文,則不予吸收。此外,還有許多根據日本國情獨創的條文,例如“班田年限”、宅院地不得施舍寺院等規定[20]。明治維新和二戰后對外來法律所進行的“本土化”實踐,上文已較詳盡地列舉,此處不再贅述。從根本意義上說,廣泛地借鑒吸收與謹慎地本土化目的是一致的,二者相輔相成,使移植后的法律制度達到效果最大化,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4.法律移植對日本社會進步的重大意義
前文已闡述過,先進的法律制度能通過對生產關系的保障和社會制度的維護客觀上促進生產力發展。日本歷史上三次大規模的法律移植植入了適應新國情的法律體系。法律領域的煥然一新也帶來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大化改新”后的法律移植使日本法制走出了蒙昧的習慣法和神判法階段,推動了封建經濟的發展和封建政權的鞏固,使日本成為繼中國和朝鮮之后的東亞文明國家。明治時代的法律移植掃除了大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障礙物,促進了日本社會的近代化,使之擺脫了淪為半殖民地的厄運,并逐漸成為東亞的經濟和軍事強國。二戰后的法律移植則確立了日本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自由的經濟制度,使日本社會在短時間內得到振興,成為現代世界的經濟強國。這三次大規模的法律移植,都因為時機準確,方針正確,措施得當,從而推動了日本社會的進步。
三、對中國司法改革中涉及的法律移植的深入思考
在當代中國,隨著對司法體制和具體法律制度的改革與完善的深入,法律移植已越來越多地被付諸實踐,且越發成為法學界密切關注的問題。當代中國法律移植的必要性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和根本特征決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當今世界市場機制是綜合世界經濟的最主要機制。盡管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市場經濟會有不同的特點,但它運行的基本規律,如價值規律、供求規律、優勝劣汰規律是相同的,資源配置的效率原則也是相同的。這就決定了當今中國在建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和制定市場經濟法律過程中應當吸收和采納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立法經驗,節省時間成本,避免不必要的挫折和彎路。市場經濟本質上是外向型和開放型經濟,其客觀的發展規律必然沖破一切地域的限制,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對接,把國內市場變成國際市場的一部分,從而達到生產、貿易、投資和技術的國際化與一體化。這就要求在制定相關法律時必須與國際法和國際慣例相銜接,即法律的國際化。另一方面,法律移植是對外開放的必由之路。在當代,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離不開世界,特別是像我國這樣的經濟和文化都尚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更有時代的意義。開放必須是全方位的,即對世界上所有地區開放,對所有類型的國家開放;不僅在經濟和科技上要開放,而且文化上和政治上也要對外開放。當今世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不僅使經濟國際化,而且其他的社會生活領域,諸如資源開發、環境保護、人權保護、懲罰犯罪、維和行動、婚姻關系、財產繼承等跨國性亦日益增強。法律在處理涉外糾紛和跨國問題的過程中,必然逐步與國際社會通行的法律和慣例接軌,那么將國際通行的法律和慣例吸收到國內部門法中,無疑是順應時代潮流之舉。法律移植這一問題對于當代中國社會之重要意義,于此可見一斑。
但是法律移植并非易事,它往往涉及到一系列的問題,其實施并非總是收效顯著,歷史上也不乏適得其反,被迫終止之例,19世紀歐洲大陸移植英國的陪審制便是其中之一。對于當代中國的法律移植問題,必須把握住幾個關鍵點:(1)我國目前借鑒和移植國外(或特定地區)的法律是我國選擇接受的,決不是外力強加的,其目的是為了有利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2)我國在借鑒和移植國外(或特定地區)的法律時,應認真地研究移植來源國家或地區以及本國的各種社會或自然條件。(3)作為當代中國的法學家,應研究國外法學中有關法律移植的經驗和理論,特別是研究我國歷史上與當代在移植法律方面的經驗和理論[21]。另外,法的移植要有適當的超前性。在各國的法律移植實踐中,獲得成功的占到了壓倒性的多數。經驗表明,只要把握好時機,做到方針正確,措施得當,法律移植必然有其無可替代的價值。
如今,中國民法典的制訂與實施已被提上日程表,成為法學界乃至社會各界所關注與探討的一大熱門話題,于此之中必然也涉及到法律移植的問題。縱覽當今世界,不僅一些主要的大陸法系國家早已頒布了系統完備的民法典,即便是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比如市場經濟起步較晚的越南等國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也頒行了民法典。而相比西方國家,我國的民法制度建設可謂望塵莫及。隨著經濟體制轉型與對外經貿的頻繁,當今中國國內的民事關系已日漸復雜,出現了民事法律跟不上時代發展的問題。《民法通則》的制訂盡管也解釋了一些基本規則問題,但由于內容過于簡略(僅僅156條,而國外的民法典通常都是數千條),使實際操作往往無法可依,時常同一個案子不同的法官會有不同的裁判(這里排除法官素質上的問題)。另外,我國現在的民事法律淵源多而雜,應用中時常碰到內容相互矛盾的問題,給司法實踐帶來了另一重麻煩。通過制訂一部體系完備的民法典,能有效地解決當今司法實踐中無法可依和法律間矛盾的困境,提供統一的判定依據和標準,也有助于減少司法腐敗、裁判不公的問題。當今中國社會迫切需要與時代發展相適應的民法典,在編纂中,法律移植乃是吸收和采納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立法經驗,節省時間成本,避免不必要的挫折和彎路的最佳手段,因而借鑒西方立法成果勢在必行。其中應當看到我國近代雖然受大陸法系民法制度的影響,但在改革開放以后,英美法系,特別是美國法律文化對我國影響也不小。這一點在合同法、侵權行為法、擔保法中更顯而易見。所以無論是大陸法系、英美法系還是其它法系,我們都要兼容并蓄,廣泛地加以借鑒,在立法體系上可以在堅持大陸法的系傳統的同時吸收英美法的經驗。在法律移植的過程中,務必做到使外來的法律制度恰到好處地實現本土化,從而順應當今國內經濟的轉型和其它國情,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社會的更大進步。在文章的結尾,我想說,日本歷史上三次大規模的法律移植給我國當前的立法實踐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值得我們為之深思并加以借鑒的。[i]
[1] 沈宗靈:《論法律移植與比較法學》,北大法律信息網。
[2] 參見彭科:《法律移植與本土化問題資料綜述》,北大法律信息網。其實,除了殖民地或保護國極少有國家在制度上明確規定法院可以直接適用(即移植)他國法律,直接適用他國法律被視為是對本國主權的侵犯。英國最高法院的判例過去通行與英聯邦各國,但如今在英聯邦國家中英國法院做出的判例也愈來愈少地被允許適用。
3 孫笑俠:《論市場經濟社會法的民族化和國際化》,載《杭州大學學報》1993年第4期。
[4] [日]富井政章:《開國五十年史》(漢文本),轉引自楊鴻烈:《中國法律對東亞諸國之影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頁。
[5] “大化改新”,是公元645年大和朝廷發生的一次宮廷政變,改革派推翻豪族蘇我氏的統治,擁立孝德天皇即位,建年號為“大化”,此后進行了一系列仿效唐代制度的政治、經濟、法律上的改革。主要內容包括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的政治機構,模仿中國建立官制,實行“公地公民”制度(即國家直接管理和支配土地和農民),實施仿效中國土地制度的“班田收受法”和租庸調制。
[6] 參見李昌道、徐靜琳主編《外國法律制度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頁。
[7]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1972年版,第223頁。
[8] 楊鴻烈:《中國法律對東亞諸國之影響》,第257頁
[9] 幕府于公元1639年下“鎖國令”,逐出外商和傳教士,但允許與中國和荷蘭在長崎港與之保持少量貿易,使以“蘭學”為名的西方思想如絲如縷地傳入日本。
[10] [日]福島正夫:“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和私法(四)”,載[日]《法律時報》第二十五卷四號,轉引自丁明勝:《日本明治時期的民法典論爭》,載《法律史論集》,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553頁。
[11] 參見丁明勝:《日本明治時期的民法典論爭》,第553頁。
[12] 轉引自沈宗靈主編:《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頁。
[13] 王家驊:《儒家思想和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頁。
[14] 以上所引用的法條皆摘自《日本民法典》,曹為、王書江譯,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
[15] “天皇機關說”是日本法學家、貴族院議員美濃部達吉(1873-1948年)創造的與“天皇主權說”相對立的理論,其認為統治權應屬于作為法人的國家,天皇作為國家最高機關,行使統治權,該學說有限制皇權,將之限定在憲法約束的范圍內,并加強議會的地位和權力的目的。1935年2月,菊池武夫在貴族院的發言中攻擊“天皇機關說”違反國體,誣稱美濃部達吉犯有“不敬罪”。同年4月,政府查禁了美濃部的《憲法撮要》等三部主要著作,“天皇機關說”被全面禁止傳播,美濃部也被迫辭去議員職位。
[16] 如1947年公布施行的《伴隨日本國憲法實行的民法應急措施法》、《刑法部分改正法律案綱要》、《禁止私人壟斷及確保公正交易法》、《法院法》,1948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等等。
[17] 參見李昌道、徐靜琳主編《外國法律制度導論》,第334頁。
[18] 參見何勤華《20世紀日本法學》,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396頁。
[19] 關于這一點,可參見[日]依田熹家:《日本近代的歷史問題》,雷慧英等譯,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24頁。
[20]參見李昌道、徐靜琳主編《外國法律制度導論》,第307頁。
[21] 參見沈宗靈主編:《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106頁。
[
1. 楊鴻烈 《中國法律對東亞諸國之影響》,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P173—257。
2. 李昌道、徐靜琳主編 《外國法律制度導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P305—361。
3. 何勤華 《20世紀日本法學》,上海:商務印書館2003年,P388—398。
4. 丁明勝 《日本明治時期的民法典論爭》,載《法律史論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P552—554。
5. [日]依田熹家:《日本近代的歷史問題》,雷慧英等譯,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P121-124。
6. 沈宗靈主編 《法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P10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