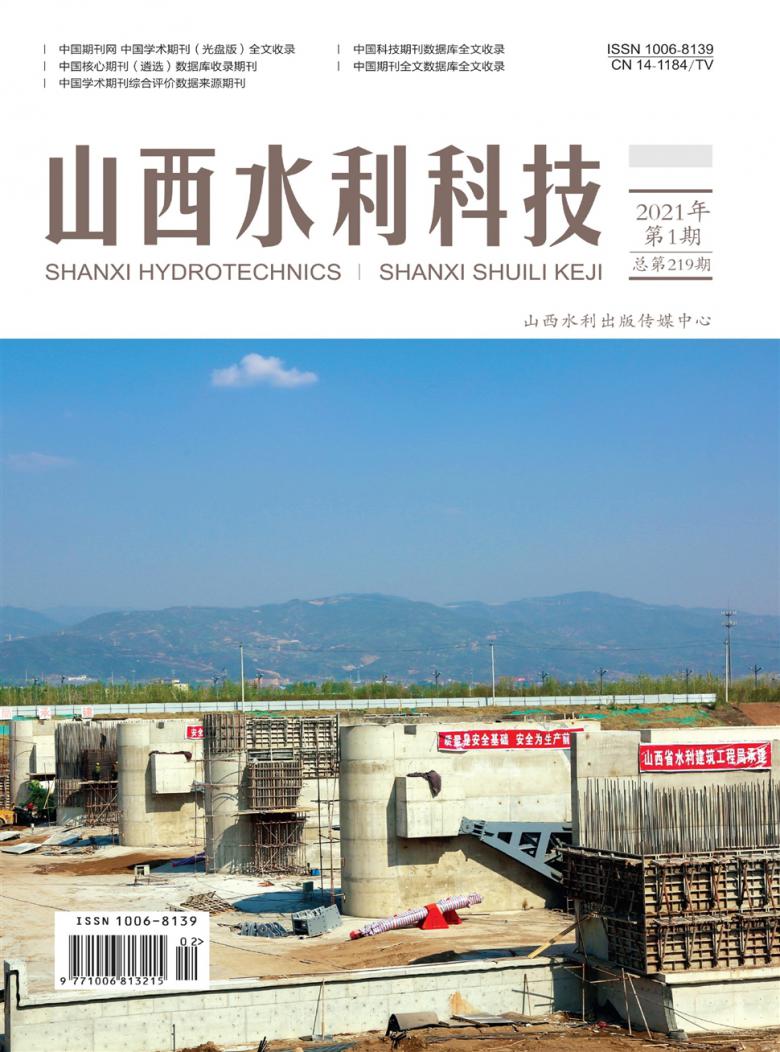文學革新的內在悖異——戊戌維新啟蒙策略選擇
姜異新
【內容提要】 在近代中國東西方文明第一次大規模的沖撞中,戊戌維新啟蒙運動面臨的是政治文化的雙重危機。在“救國”總目標統攝下,啟蒙策略呈現出“使用傳統反傳統,使用反傳統實現傳統”的悖論駁雜色彩。其內在悖異性已構成中國第一代啟蒙的文化支點和文學現代化起步的立足點。
戊戌維新時期的啟蒙運動,是在西方文明入侵后變幻莫測的混亂秩序中拉開序幕的。政治危機與文化危機交織互動,傳統世界觀與價值規范逐漸失去舊有的文化功能,并由此引發出許許多多無法疏導和化解的激情。盡管當時啟蒙的基本訴求非常明顯,但傳統思維在“救國”總目標的統攝下,呈現出錯綜復雜的面貌。反傳統言論絲毫不影響近代啟蒙者對傳統資源作深入而廣泛的應用,這使得啟蒙在中國并不首先表現為思維方式的革命,而是如何使用傳統以應付千年未有之變局。啟蒙策略因此顯露出“使用傳統反傳統,使用反傳統實現傳統”的悖論駁雜色彩。康德曾將啟蒙描述為人類運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屬于任何權威。勇敢地去認識,堅信自己的理解成為啟蒙的真諦。然而,“使用傳統反傳統,使用反傳統實現傳統”的啟蒙策略正是理性缺乏的集中表現,其內在悖異性已然構成中國第一代啟蒙的文化支點和文學現代化起步的立足點。這其中,運作最成功的就是對文學的“使用”。盡管晚清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革新作為啟蒙工具的有效性已成定論,然而傳統文學資源和文學精神是如何被啟蒙所用,其內部復雜性又是如何呈現的,還有待于深入剖析,本文便是一種嘗試。
一
啟蒙作為思想運動,最基本的工具是語言,語言的變化往往滲透出思想的變化。第一代啟蒙大師首先選擇在語言變革上作文章,開展“白話文運動”。早在1887年,從事外交活動的黃遵憲就曾將中國語言與外國語言進行比較,提出文字與語言合一的主張。在1895年正式出版的《日本國志》里,他強調“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要求“變一文體為適用于今、通行于俗者”,“欲令天下之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1898年,裘廷梁在《蘇報》上發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指責中國兩千年來的文言窒息了民族的發展,第一個打出“崇白話而廢文言”的大旗。1899年,陳榮袞發表《論報章宜改用淺說》,要求報刊行文詞匯盡量與日常生活相聯系。上述倡導“言文一致”的主張旨在推行“民主”,讓更多的平民受教育,因與形勢非常契合,很快就得到了響應,大量白話報刊和作品開始紛紛涌現。
然而,盡管社會上掀起了一股白話文熱潮,啟蒙者對在文學層次上引入白話應用,卻還有一個漸次的認識過程。梁啟超曾于1896年反思過“中國文學,能達于上不能逮于下”的原因,指出:“抑今之文字,沿自數千年以前,未嘗一變;而今之語言,則自數千年以來,不啻萬百千變,而不可數計。以多變者與不變者相遇,此文、言相離之所由也。” ① 這時,他看到了言文分離問題的存在,卻還沒有完全意識到文學語言變革的必要性。1897年,在到湖南時務學堂任職時,訂立《湖南時務學堂學約》,其中第六條規定:“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學者以覺天下為己或務瑰奇奧詭,無之不可;覺世之文,則辭達而已矣,當以條理細備,詞筆銳達為上,不必求工也。”這里透露出只有“言文一致”的白話才能做到“辭達”,起到“覺世”作用的信息,言外之意,運用白話能作應用文學,卻不可能用來“傳世”,或者說白話根本達不到正統詩文所追求的“傳世”境界。“言”只是再現表象或內在觀念,而“文”則意味著另外一種東西。作為對這一理論的呼應,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大量“覺世之文”,創立了“新文體”。但由于還未完全意識到語言變革的重要性,備受歡迎的“新文體”也還是始終沒有擺脫文言高雅、白話低俗的觀念。“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亡命日本,精心研究西學,才發現“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 ② 也就是說,當暗中把主張俗語革命的歐洲文學史作一映襯時,梁啟超才開始將視線投向文學自身,發現語言變革不光“保國保種”,更是文學發展的必然規律。這里的“文學”也開始接近明治時期在日本得到普及的literature一詞的譯語,而不再泛指“文章博學”。
作為一種語言系統向另一種語言系統的挑戰,晚清白話文運動彰顯的是傳統與現代思想的新舊消長。當變動不居的現實與用來描繪現實的固定符號之間產生一種深刻的分裂和張力,啟蒙現代意識與舊有的語言體系即因無法融合而逐漸發生迸裂,人們不得不拋開自身文化傳統中占統治地位的符號去另辟蹊徑。然而,白話文運動作為戊戌維新啟蒙的一部分,也是啟蒙的結果,其最主要的動機還是啟迪民智,傳播先進思想文化,而不是文學近代轉型的主動訴求。早在1868年,黃遵憲就曾呼吁過只有打破禁忌,自鑄新辭,“我手寫我口”,不受古人拘牽,方能創作出好的文學作品。他身體力行,輯錄研究山歌,并將之與《詩經》并列,成為近代重 視白話審美的第一人。然而,這種吸取民間語言美的做法并未受到近代啟蒙者的重視,打動無數士大夫的也只是其“言文一致,方能保國保種”的功利論斷。這正說明對白話的開發利用,曾在時局的推動下,一度膨脹為救國憤世的社會共同意識,成為傳統“經世致用”思潮的集中反映,可視為“使用反傳統實現傳統”的策略驗證。在傳統觀念中,白話是不配表達精英思想的,采用白話來宣傳國家民族觀念,啟迪民眾,無疑是士大夫階層俯就大眾水平的反傳統行為,然而,透過反傳統外殼呈現出的卻又是利用新的語言利器來闡釋普及傳統思維方式的內理,其目的仍是正統的“治國平天下”意識。這樣,近代啟蒙者就無法看清日常政治語言與文學審美語言的區別,根本無視語言的藝術特征,直接拿白話來為啟蒙所用,使其理所當然地成為思想啟蒙的工具和實質內容的一部分,造成白話文運動從一開始就只從政治啟蒙立論,忽視作為語言生命性之審美啟蒙的先天缺陷。實際上,晚清文壇主導潮流的依然是文言、白話并存不廢的現象,用白話翻譯與創作都談不上成功,即使是倡導白話的理論文章也是用淺近一些的文言寫成的,并非真正的白話文。同時,白話的淺白又反過來限制了近現代思想的傳播和現代意識的表達。這不僅僅是傳統遺留或過渡舊痕的問題,而是“使用”策略的內在悖異使然。要想使新的語言系統與新現代思想和審美觀并行不悖地融合到一處,自覺達成完全契合,必須等到再一輪思想文化啟蒙高潮席卷而來,才徹底完成。
二
晚清白話文運動作為啟蒙的先導,終于在深入開展中使近代啟蒙者看清了自身不易察覺的文學中心感,這種曾經的文學優越感在與西方文化的比較中,更加顯現出不合時宜的自大。于是,從相信“文學”能夠“治國平天下”的士大夫演變而來,以拯世濟民為己任,一度在國家政治危機中視詩文為雕蟲小技的第一代啟蒙者,在從政治舞臺上碰壁后,迅速回頭轉而迫切要求文學的全面革新,并順理成章地將其推到歷史的前臺,相繼掀起詩界、文界、小說界(包括戲曲)三界革命的高潮。甲午戰敗后,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曾薈萃北京,在對“新學”的狂熱崇拜中,開始創作大量“扯新名詞以自表異”的“新詩” ③ 。而在此前,曾以外交官身份游歷西方的黃遵憲也已嘗試寫作“新派詩”。其時,他的《人境廬詩草》稿本正迅速流傳,遠比“新詩”更能贏得讀者。黃的詩不僅寫景抒情,筆觸細膩;刻畫人物,個性突出;描摹他國風光也是新異瑰瑋,對新思想、新名詞運用自如,絲毫不顯得生硬造作。尤其是《今別離》四首,充分證明舊詩是完全可以表達現代事物的。不過,梁啟超當時并不賞識黃遵憲的詩風,直到自己成為戊戌維新的劫余人物,流亡異邦,也有了置身于他者文化的經歷后,才慨嘆當年“緣法淺薄”,重新將黃遵憲的“新派詩”搬出來,推為“詩界革命”的最佳范本。這使人不能不承認西方文化對中國詩歌近代轉型影響的深且巨。1898年,梁啟超擔任主筆的《清議報》在日本橫濱創辦,其中特辟詩欄,不斷刊登既有新名詞又有流俗語入詩的“新體詩”。從此,“自由”、“共和”、“民主”等等日譯新詞大量入詩,“新詩”和“新派詩”開始向著政治啟蒙的方向合流。1899年12月25日,漂泊在東京至夏威夷海途中的梁啟超,因受日譯英語“革命”(Revolution)一詞的啟發,終于在《夏威夷游記》里,正式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他戲謔舊詩人為“鸚鵡名士”,發出“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的呼吁,認為欲“成其為詩”,必須做到:“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這時的他推許黃遵憲為詩王,盡管對其詩“新語句”尚少還頗有遺憾。在分析了近代詩人運用歐洲意境語句“多物質上瑣碎粗疏者”之后,梁啟超倡言“吾雖不能詩,惟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在他看來,西方的政治態度,進化論思想,自然科學知識,愛國精神以及崇高的人格等等,都理所當然地成為新思想、新意境。利用詩歌推動社會思潮的啟蒙意圖充分顯現。自1902年起,《新民叢報》辟出“詩界潮音集”專欄,其中刊載了蔣智由的《盧騷》,代表著“詩界革命”進入鼎盛階段。同時,梁啟超繼續在《飲冰室詩話》中大力鼓吹“新體詩”的創作理論,不過,一個微妙的變化引人矚目,那就是革命綱領被重新概括為“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新語句”一項已悄然抹去。黃遵憲再次被抬高為“近世 詩人能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由此前對其詩“革命”意義的肯定轉移到后來偏重文學成就的褒揚,凸顯出此時梁啟超對詩歌“舊風格”的無比重視。
從堆積新名詞到追尋新思想,再到留戀古風格,這一“詩界革命”前后各有側重的詩歌創作過程,清晰地折射出“使用”悖論的內在精神線索。當新名詞絡繹于筆端,不曾提防的是美的境界正漸行漸遠,這促使梁啟超逐漸淡漠了對新名詞的追逐,流露出對古風格的珍愛。他之不決意打破舊形式,努力去創造新風格,無可避免地意味著,古體詩進入藝術鑒賞博物館的日子也同時來臨了。因為新的現實世界已經無法遷就古老的審美趣味。想用新語造新境,又想不露痕跡,點化自然,這種良苦用心源于“使用反傳統實現傳統”的內心藩籬,說明詩歌創作動機還在為傳統思維方式所驅使。不肯為了外部的反傳統啟蒙而拋棄對中國古詩意境的偏愛,更顯示出外來文化沖撞下近代詩歌轉型的內在被動。當梁啟超主張以“日本譯西書之語句”入詩,以俗語入詩,提倡詩歌的通俗化,音樂性和史詩式的宏偉規模時,可視之為對舊詩傳統用語的新突破。而黃遵憲“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的創作口號,更以其淺顯和自由觀念向著數千年的因襲挑戰,這些似乎都在宣揚一個完全可以按照自身意愿寫詩時代的到來。然而,匆促、慌亂、因應失據的近代啟蒙語境使得使用新語句與制造新意境之間時時捉襟見肘,更與努力保留“舊風格”常相背馳,不得已陷入補偏救弊的革新尷尬。如果說梁啟超等人創作專以堆積新名詞取勝的“新學之詩”是使用傳統反傳統,對詩歌傳統形式的突破還未有自覺意識的話,那么,“詩界革命”中“革命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 ④ 的反傳統姿態,終于在努力實現傳統審美趣味面前,將古詩革新的步伐逼到了無法前進的死胡同。這就暗示著“用新意境入舊風格”才是古體詩新生的唯一途徑,舊詩是根本不應當被徹底取消或替代的,說明隨著近代啟蒙者在政治上趨于保守,借用“詩界革命”表現新思想新精神的積極性便大大削弱,詩歌自身的文學價值問題也才因此而浮現出來。然而,傳統思維羈絆正如革命決絕態度一樣鮮明無比,充分證明了中國近代詩歌發展中思想層面可能性與純文學形式可能性之間的難以協調。
三
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近代文學各種文類轉型的步調并不是一致的,與“詩界革命”難舍舊格律、古風格相輝映的是近代散文文體的大解放。我們看到,梁啟超始創的“新文體”,無論語言體例,結構修辭,還是表情藝術,甚至標點符號等等,都在發生著亙古未有的變化。此前,盡管近代散文也在潛變,但主要還是八股文控制社會,桐城派籠罩文壇。隨著近代啟蒙運動催生出新的公共領域,政論散文在報刊中執輿論界之牛耳,成為宣傳維新思想最合用的工具。“新文體”應運而生,并因多發表于《時務報》、《新民叢報》,而又被稱作“報章體”、“時務文體”和“新民體”。1899年12月29日,在提出“詩界革命”口號三天后的《夏威夷游記》里,梁啟超又提出“文界革命”,稱贊日本新聞主筆德富蘇峰的《將來之日本》等著作“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為文界別開一生面者”,斷言“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點于是也。”并始終在自己主持的報刊上不懈地進行文體改革實踐。
中國古代向來政論文發達,散文被用作輸導、傳播啟蒙思想的得力工具似乎天經地義,也是傳統載道文學的應有之義。只不過,古代散文面臨的是遲滯的現實和單一的思想,而在變法維新運動中產生的近代散文,卻運載著復雜多變的社會內容和嶄新的反傳統精神。從戊戌時期的鼓吹變法,批判守舊,到流亡日本期間偏重“新民”之說,介紹西方文化,近代散文傳達出的可謂是振聾發聵,“以筆端攪動社會”的破壞之論。而梁啟超將輸入“歐西文思”視作革命起點,足以說明西學東漸是促使“新文體”產生的直接文化因素。“新文體”在創作中融入了若干日本文體的硬性成分,自模仿后進一步醇化,逐漸打破了傳統義法,沖決著傳統古文“文”與“道”、“義”與“法”的桎梏。多種文化的交叉影響造成了“新文體”獨特的表征,這就是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總結的:“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隨著近代散文容量不可遏止地迅猛擴大,被內容決定的形式迫切要求變 幻多姿。比詩歌轉型更具有革命意義的是,“新文體”最大限度地掙破了古舊的形式,對傳統古文體式,外國詞匯語法,民間俚語俗語,一概兼收并蓄,使之在與古代散文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同時,又能盡情揮灑、酣暢流瀉下西方文化的自由思想,可謂使用傳統文類“激民氣之暗潮”,實現“播文明思想于國民”的反傳統目的。當讀者從“新文體”中讀到莊子風格的聯想比喻,《左傳》筆法的委曲詳盡,《史記》語匯的生動流暢時,心中激起的已不再是傳統溫柔敦厚的審美情感而是渴望在自由解放的道路上迅跑的激情。因而,和“新體詩”比較起來,“新文體”既有感情與理智,現實與歷史的和諧統一,更有著思想和文體的雙重自由。
“新文體”之突破傳統規范,被老輩痛恨不已,詆之為反傳統的野狐禪,然而,它開了一代新風,推動著中國散文的現代化進程,在當時和以后,都產生了巨大影響。梁啟超的政論散文如《瓜分危言》、《亡羊錄》、《少年中國說》、《呵旁觀者文》、《過渡時代論》等等,行文汪洋恣肆,跌宕起伏;句式駢散雜糅,舒卷自如;氣勢縱橫馳騁,深沉激越,極具說服力和煽動性。他的傳記體散文,如《譚嗣同傳》、《羅蘭夫人傳》等,融敘事、抒情、議論為一體,表現人物栩栩傳神。這種令人耳目一新的言說方式,對當時渴望新思想、新知識的讀書人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其淺近的文辭不但打破了士大夫壟斷讀者受眾的局面,更使文化水平不高的平民百姓樂于接受,廣受啟迪。黃遵憲曾贊揚新文體:“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 ⑤ 嚴復贊之曰“一紙風行,海內視聽為之一聳。” ⑥ 梁啟超自己也說,新文體“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⑦ 。然而,正是這“魔力”,又使人不禁心生疑竇。比之僵死的古體散文,“新文體”確實有著飽滿充沛的感情,一往無前的銳氣,和鋪張揚厲的作派,不過,它的以煽情見長,華麗鋪張,往往使說理成分深深匿藏于激情迸發的外殼,洗盡鉛華之后不免失之空泛。讀者會一時被情感的波濤裹挾而去,無法進行冷靜的理性反思,這就在鼓蕩民氣,啟發蒙昧之時,偏于造勢,無形中再度助長了不利于啟蒙的傳統思維習慣,而新的精神權威和偶像很可能就蘊含在這種非理性的狂熱中。“新文體”引發的所謂“若受電然”,“舉國趨之,如引狂泉”的盛況除了表明國人對西學的盲目崇拜和空洞的愛國情緒外,西方真正的理性精神并沒有被我們所吸收。作為反傳統實績出現的“新文體”,無形中暗合和普及的還是傳統文化心理。
四
如果說,在詩歌散文的變革中,中國傳統精英文學的內質并沒有因啟蒙而發生根本變化,從而還看不出多少矛盾沖突的話,“小說界革命”則最明顯地體現出近代文學轉型迎合啟蒙策略的悖論特點。1897年,天津《國聞報》發表了嚴復、夏曾佑的《本館附印說部緣起》的長篇專論。他們首次把進化與人性理論引入小說研究,認為小說所以經久不衰,就是因為反映了“崇拜英雄”、“系情男女”這些人類之“公性情”,即普通人性。因為“聞歐美、東瀛,其開化之初,往往得小說之助”,所以打算“不憚辛勤,廣為采輯,附紙分送”。康有為早先編撰,1897年由大同譯書局刊印的《日本書目志》,專設“小說門”,在該書“識語”中,康有為對“通于俚俗,故天下讀小說者最多”的事實十分重視,從而萌發以小說進行啟蒙教育的想法:“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喻,當以小說喻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
然而,第一代啟蒙大師在借小說啟蒙的過程中迅速忘卻了其之所以暢銷是因為反映了普遍人性這一最初發現小說價值的出發點。他們無暇顧及作為純粹文學樣式的小說該如何發展,直接要求其對現實的社會政治改革有所補益,透露出“使用”本意。這一思想在“百日維新”失敗,維新派由帝王之師變成亡命者,由在朝的“智囊團”淪為流亡的清議派后空前突出。彼時,啟蒙者在啟蒙策略上很快由依賴皇帝變法轉為“新民決定論”。對于如何造就“新民”,梁啟超在1902年于日本創辦的《新小說》創刊號上用那篇影響深遠的歷史性文獻——《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明確道出了小說應有的啟蒙角色: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 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需要注意的是,梁啟超在這里并不是有意抬高小說地位,而是找到了啟蒙與彼時大眾文化樣態的聯結點,無意中打開了重建文學格局的突破口。要知道,戊戌變法之前,晚清文壇曾一度出現過“文學無用論”思潮,梁啟超即認為誰要想以詩詞鳴于世,誰就是“浮浪之子”,誰耽于吟詠,誰就是“玩物喪志”,詞章危害之大,“竟與聲色之累無異” ⑧ 。這里所講的“文學”甚至還不包括小說,也就是說,連弄文學都已是玩物喪志,那么,“壯夫不為”的“小技”更不在話下。而在流亡日本后,梁啟超卻一下子把小說家抬到可以“握一國之主權而操縱之”的地位,宣稱小說對于廣大群眾,“如空氣然,如菽粟然,為一社會中不可避,不可屏之物”,小說的社會作用受到空前重視。這前前后后看似貶低詩文抬高小說的言論,既充分體現了各種文體樣式在啟蒙家眼中曾經的位置,又可清晰辨出啟蒙天平向大眾的再度傾斜。自此,小說不但順理成章地與詩文同列于“文學”這一神圣的名稱之下,并且遠離“小道”稱謂,真正成為可以“借闡圣教”,“雜述史事”,“激發國恥”,“旁及彝情”的大學問” ⑨ 。實際上,正是小說的娛樂性使其藝術活力遠遠大于詩文,成為其獨立性的重要標識。從啟蒙應直接訴諸廣大國民而不是上層統治階級這一角度出發,小說可在寓教于樂中使啟蒙思想更迅速地植入人心。梁啟超深諳此點,為了配合啟蒙思想宣傳,他無情解構了傳統文論對小說的既成定位,第一個喊出了小說乃“文學之最上乘”的響亮口號。他總結出多種舊小說敘述模式,并將之與國民文化心理聯系起來,認為其“魚爛”于才子佳人,綠林俠義,官場公案,妖巫狐鬼等等誨淫誨盜的敘述思想之中,直接把小說推上了“國民之魂”的“大道”之位。當古小說中蘊藏著的舊意識形態無法再催生出新的變革社會的思想,梁啟超強烈的批判精神便為“新小說”的孕育開辟了航道,而最先引起他注意的是與當時社會改革關系更為直接的政治小說。他在《清議報》上翻譯連載了日本政治小說《經國美談》、《佳人奇遇》,在國內轟動一時。《譯印政治小說序》中,梁啟超對小說開歐洲文明風氣之功無比神往:“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于小說”,“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最高焉”。他不無樂觀地規劃和憧憬著“新小說”中的新人物、新理想和新的時代精神,并創作了《新中國未來記》等政治小說,以借書中之人物,抒發一己之政見,期望借助小說的“熏、浸、刺、提”不可思議之力漸漬深入于國民腦質。西方小說譯本的大量出現開始幫助中國小說逐漸改變傳統意識和程序化格式。而“政治小說”引進中國,最終“導致了傳統小說觀念的崩潰,建立全新的小說觀念因而具有了無限的可能性。”這也正是“小說界革命”真正的革命意義 ⑩ 。
盡管如此,啟蒙者外在的決絕姿態并不代表內在思想觀念的斷乳。梁啟超之所以重視小說,也有其傳統根由。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他還重申了其師康有為的觀點:一則“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學之人少,而粗識之人多。‘六經’雖美,不通其義,不識其字,則如明珠夜投,按劍而怒矣”,因而才需要用小說加以“教之”、“諭之”、“治之”;二則小說“終不可禁”,因此不如“從而導之”。顯然,康梁眼中真正“美”的文學還是“六經”,小說不過是適合“愚人”的下等文學。為了迎合大眾,近代啟蒙者不得不拓展文學載道內容的內涵與外延,借用小說的通俗性宣傳精英思想。自此,啟蒙之志滲透至小說,使其具備了載道資格,“道”便被化約為近代國家民族思想。因而,“新小說”觀念中的傳統因素不是減少了而是加重了,其理論精神依然是重視文學社會作用的傳統實用理性的反映。要求小說承擔起改良社會政治重任的反傳統姿態,傳達出的仍是傳統文學關乎世道人心之核心理念。這就不可避免地在“小說乃國民之魂”與小說的第一特征在于“俚語”這兩種觀念之間劃出了鴻溝。隨著小說地位由邊緣向文學中心移動,想像中的讀者對象也不自覺地從普通大眾逐漸傾斜回愛國精英。當看到很多翻譯作品的譯文完全是用典頻繁的文言,而不是適宜于啟發蒙昧的讀物時,就更充分地證明此點。回顧小說的發展史,《漢書·藝文志》曾確立了小說乃“史”的附屬品這一共通觀念,隨著白話章回小說的興盛,又出現了 小說可供一時娛樂之用的看法。其實,這正是小說作為一個文體從“史”中獨立,獲得自身發展的契機。而“小說界革命”使啟蒙性成為小說娛樂性的免罪符,無形中再度確認了其從屬性。可以說,近代啟蒙者不顧忌小說在傳統文類中的卑下地位,不探討其內部發展規律,一上來就從政治上肯定其對改造國民和社會的重要性,充分顯示出早期啟蒙文學思想所達到的政治高度,以及“使用”策略的所有矛盾復雜性,這也正是近代小說發展中傳統觀念與現實需求、外來影響諸種因素互相糾纏、沖突的特質。“新小說”的開山之作《新中國未來記》對此即有著非常典型的體現。
在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歷程中,《新中國未來記》具有先導意義,很多藝術逐新嘗試使其成為別開生面之作。例如,效法西歐、日本小說,直接狀寫社會變革潮流,把小說現實主義創作推上一個新階段;結構采用倒敘法,為近代小說打破平鋪直敘的僵局樹立了楷模;敘事引入演說體,在不同政見人物的往復詰難,批駁辯論中刻畫人物形象,等等。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文本在新意簇擁的外表包裹下,仍有著傳統滯后的主體意識。可以說,支配作者寫作技巧的價值觀念、思維方法與傳統相比并沒有多少新突破。就拿作品采用“幻夢倒影之法”來說,開場還是先抖出了一個傳統敘事模式中的“大團圓”結局,只不過這個“大團圓”已自個人命運膨脹至國家、民族乃至世界。為了這個傳統“善”的文學觀念支配下的“大團圓”,作者在藝術構思上煞費苦心,對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和前景,做了種種預設。很顯然,受進化論思想影響,創作主體自覺吸納了未來決定論,然而,這種在當時頗先進的直線向前,不可重復的歷史時間意識,卻在倒敘手法的引導下,悄然轉化為古老輪回循環論的變相。“中國在小說中被設計成一個世界超級強國,使人不禁懷疑這不過只是當時歐洲列強模式的翻版。從比較歷史的角度看來,1962年的新中國的這個‘未來’,將只不過實現了1902年歐洲‘曾發生過’的事情。”11 為了讓骨子里仍遵循“士志于道”傳統的新知者實現啟蒙偉業的“大團圓”,作者不惜把維新和革命思想轉換形式硬塞入到敘事中,結果不可避免地流于解釋,成為羈絆,文本因而呈現出理性與非理性相互吊詭、彼此削弱的情狀,使讀者不期然讀到一個用藝術創造忌諱的模式化理性講述出的與啟蒙精神相背離的非理性故事。
與此同理,晚清無論是政治小說還是譴責小說,大都或是用“舊小說之體裁”載運“新意境”,或是用新的藝術手段承擔傳統載道之義,古典小說的內蘊都或深或淺地存在著。也許是對舊制度的暴露攻擊、詛咒批判構成了與古代回目形式完全矛盾的新內容,也許是完全嶄新的藝術動姿搖曳出傳統觀念之剪影,所不同的僅限于所載之道是今道而非古道而已。同樣,戲曲改良亦可作如是觀。當時的所謂“說部”、“稗史”,既指小說,也指戲曲和彈詞。戲曲有著和小說同樣的遭遇,被認為是文苑之“附庸”,因而“小說界革命”本身也就包括戲曲。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小說叢話》中經常論及戲曲改良問題,并于1902年11月,在《新小說》的《本報之內容》上,明確宣告“欲繼索士比亞、福錄特爾之風,為中國劇壇起革命軍”,宣稱戲曲為文學中之“大國”、韻文中之“巨擘”,打破了鄙視戲曲的偏見。他還在《新民叢報》上先后發表了《劫余灰傳奇》和《新羅馬傳奇》,標志著傳奇雜劇已從供少數人玩賞的貴族藝術,轉變為面向現實和民眾,旨在“振國民精神”的啟蒙教育工具。《新羅馬》還成為我國戲劇史上第一部以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史為題材的傳奇劇本,起著扭轉風氣的關鍵作用。它的詞藻不為音律所拘,開辟了傳奇雜劇創作的新途徑。與“新小說”同步,戲曲改良打破了僵化的傳統體制,使劇本可以較為自由地抒寫,打開了改良傳奇的新格局,同時又在過分追逐改變人心風俗,振奮國民精神上難脫載道舊徽記,再次證明了傳統思維模式始終在控制著中西交融的近代文學語境。
綜上所述,表面上看來新舊雜糅的近代詩文、小說(戲曲),內里映襯出的實際是激烈的文化沖突景象。近代啟蒙主體的身心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有焦慮,有掙扎,有迎合,但更多的還是過分自信地拾起傳統文學樣式激烈地去回應。近代文學的轉型也就不可能主動地在思想藝術雙方面進行充分的孕育和準備。眾所周知,貫穿晚清文學三界革命的一個重要事件是流亡。當遠離了個體曾經賴以生存的文化模式后,流亡中的啟蒙者更加明確地要求選擇東西方文明各自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經過沖突而達于調和,以期造出一種新文化。梁啟超就曾稱20世紀是中西文明結婚的時代。可是,他又斷言“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 也。”12 將西方文化比作女子,嫁于我東方文化,這種頗具東方色彩的比喻本身就帶有很強的文化自大意識。表明彼時啟蒙者的目力所及還只是西方文明現成的思想成果和具體文學創作,潛意識中運轉的思維方式并未逸出傳統框架,骨子里仍然堅信中國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優越性,中國文學經過“革命”洗禮必將再現輝煌。所以說,近代文學在中西對抗過程中嬗變的復雜性并不像“掙脫傳統又回歸傳統”描述的那樣清晰可辨,而將其說成是革命不徹底的表現,更是將問題作簡單化處理。實際上,在近代,當主導性的文化模式開始失范,新的文化精神并沒有如期而至。在使用傳統文類反抗傳統思想,和使用反傳統精神實現傳統規范方面,晚清文學改良無處不顯露出急于求成中的慌亂和尷尬,可以說,從一開始就在發展的可能性中孕育著阻礙發展的可能性。所有矛盾的焦點均集中在傳統思維方式和邏輯結構根本就沒在啟蒙運動中轉換,從而導致各方面的革新總在有意無意之間與傳統舊夢重溫。這一切只有等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到來才能夠大踏步解決。
注釋
①梁啟超:《沈氏音書序》,載《時務報》第4冊(1896年)。
②梁啟超:《小說叢話》,載《新小說》第7號(1903年)。
③④梁啟超:《飲冰室詩話》,載《新民叢報》第29號(1903年)。
⑤黃遵憲:《致飲冰室主人書》。
⑥嚴復:《與熊純如書札節鈔》。
⑦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⑧劉納:《嬗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
⑨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幼學》,載《時務報》第18冊(1897年)。
⑩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頁。
11王德威:《想像中國的方法》,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12頁。
12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