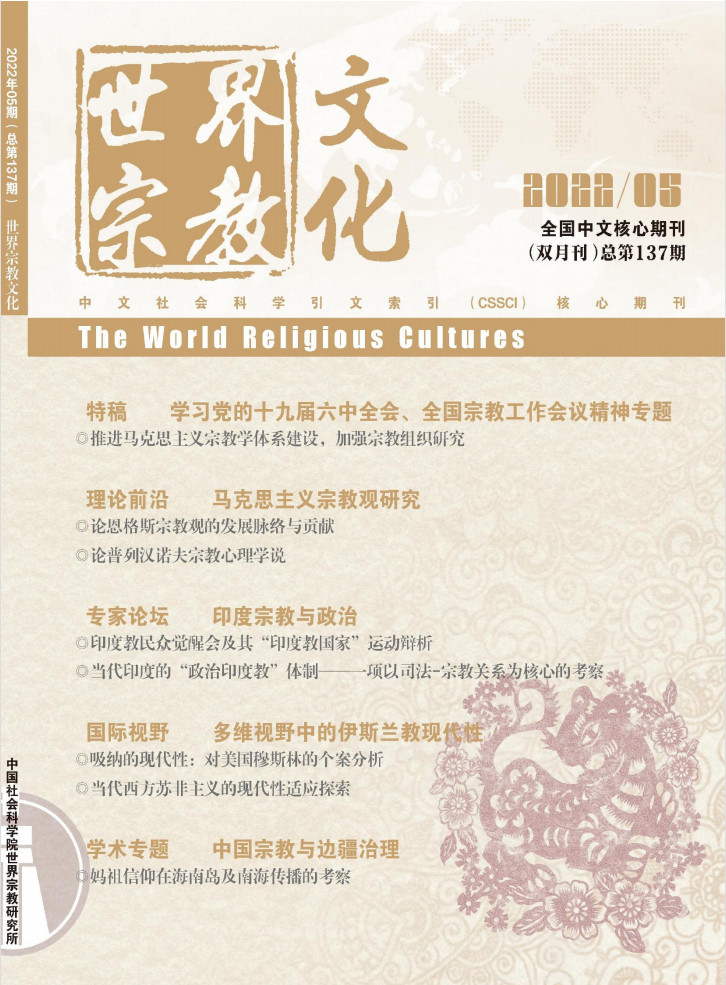“毛澤東時代美術”筆談
王璜生/李公明/尹吉
【摘 要 題】美術史
【正 文】
記憶的圖像和思考的圖像 “毛澤東時代美術文獻展”的策劃和組織,初衷是希望通過對這一時期的美術圖像的重組和呈現,探求這些圖像本身所隱含或背后所具有的社會學、文化學意義,當然,這種重組和呈現本身就是研究、整理以及重新審視歷史的重要環節和過程。圖像具有文化記憶的意義,記憶載負著文化而產生思考和審視的內涵,當歷史中的文化圖像以新的角度和方式,在新的時間空間中被重新呈現出來,它們將體現出新的思考點,引發人們對圖像進行重新解讀,以更深地挖掘圖像的歷史內涵,延伸其與當下文化之間的意義鏈。 但是,在整個展覽的呈現和接受過程中,我們發現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人們似乎更多地以現實而通俗的眼光來看待這樣的歷史文化圖像,在這些圖像中,更多看到的是與個人經驗相關的情感記憶,帶有較普遍的懷舊或追懷的情緒,以及認同和滿足的心態。畢竟,那個特定時代的美術圖像,更多保留和體現著那個時代對“美”的一種普遍的、意識形態化的呈現和理解,保留著經過改造的思想和情感對社會、現實以及“美”的真誠的表達。那個時代的美術,曾經以它作為一個時代理想的、有著恒遠意義的“美”的代表,深深地扎根于人心,并曾經成為一代成長中的人們心中對美好前景的憧憬和想象。“美”以其強大的圖像化的力量占領了人們的視覺以至思想,這種力量,可以說是社會性的、鋪天蓋地的,它不僅緊緊抓住人們的視覺,更深深地成為人們的記憶。因此,當我們有了一定的歷史距離之后,重新來面對這樣的圖像時,記憶成為了這些作品最突出也最容易生效的特征和亮點。因此,“毛澤東時代美術”的圖像,似乎更主要地成為了記憶的圖像,與個人的情感經驗、個人的成長經歷、普遍的追懷心理相關的記憶圖像。 記憶,當然是圖像一種無法回避的功能和特點。然而,我們面對的也許不僅僅是個人普遍而現實的情感和經驗,作為一個特殊時代的圖像,所凝聚的記憶的內涵也不應僅僅限于“美”的圖像化的視覺意義,當圖像作為文化和歷史而存在,而被追溯其意義,圖像的重新解讀、重新組合和呈現,它的思考的意義更可能被體現出來。 作為文化圖像的“毛澤東時代美術”,具有完整而獨具一格的形態和樣式,具有獨立的史學價值和美學價值,形成了獨特的視覺文化形象。這其中,包含著意識形態史和觀念史等方面的豐富內涵。從意識形態史的角度上講,這一時代的美術,從1942年甚至更早的時期開始,美術圖像的建立和應用,建構了包括文藝思想和理想、文藝體制和教育結構、美術的功能和目的、藝術家的身份認同和創作圖式、意義指向等。這方面,美術圖像與國家政治、政權、政黨、制度、國際陣營與文化較量等,有著無法脫離而且是服從、服務的關系。從社會觀念史和藝術觀念史等方面看,革命化、現代化、民族化、大眾化,還有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現代主義、波普藝術思潮、民間意識、女性意識、形式與內容關系等,構成了中國社會在這一特定時代的文化觀念的發展歷程,以及在世界進程中,中國所表現出來的獨特性和影響力。其實,無論從何種角度看,“毛澤東時代美術”在中國美術史、文化史上,都形成了強烈、獨特、無可替代的影響,這一時期的美術圖像,更是具有深入研究、反思的意義和必要性。因此,在時間過去了二十多個年頭,我們現在又處在一個從文化接受、思維維度、社會環境、經濟關系等都有大不一樣空間的時代,我們有了相應的歷史距離以及對意義、價值等的不同認知和定義,對于那一時代的美術圖像,我們應該而且可以去尋求思考的新起點,去獲得思考的新意義。 但是,我們所處的又是一個疏于思考和不斷弱化判斷力的“讀圖時代”,公眾樂于接受清晰無誤、情感單純的圖像,簡單明了于圖像本身的內涵和意義,并且用平面化的圖形來傳達平面化的思想。圖像不僅能夠輕而易舉地占領和統治人們的視覺,使視覺在愉悅中安詳而疲倦,幾乎喪失了面對圖像去安靜深入思考的能力,并且,圖像還不斷地引導和干擾著我們的思考,我們好像活在一個被別人或被時代、歷史規定好的視覺世界里,同時,我們也以我們的方式去規定別人的視覺。這樣,圖像的記憶,情感、經驗、經歷的記憶成為了某些圖像,如“毛澤東時代美術”的圖像的最主要的功能和特征,也輕而易舉地使人們滿足于欣賞和情感記憶。 也許,記憶更多的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礎上,而思考則來自于思想和精神的支撐。一個時代,或一個時代對另一個時代的研究和反思,更需要這種支撐。
概念的使用與研究的價值 有學者提出對“毛澤東時代美術”概念的質疑,我認為的確應該對我們所運用的概念進行討論。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到底是在什么語境中運用這個概念?在我們這次“毛澤東時代美術文獻展”和研討會的策劃理念中,主要是在現代美術史研究的學科框架中設定和使用“毛澤東時代美術”這一概念,也就是說,我們是在美術史學的語境中使用它的。 “毛澤東時代”作為一個歷史學的概念在黨史研究和現代史研究中早已被運用,問題在于,“毛澤東時代美術”作為一個美術史學的概念是否成立呢?如果說從美術批評的角度來看,“毛澤東時代的美術”這個概念是可以成立的話,我們就來看看在美術批評概念與美術史學概念之間究竟可能存在著什么樣的聯系。 大量的美術批評概念的確不能成為美術史學概念,但是也有一些源出于美術批評的概念卻成為了美術史學的概念。如“哥特藝術”就是從被用來定義一種藝術風格發展為可以用來概括一個歷史時期的概念(注:參見邁克爾·卡米爾《哥特藝術》,第9頁,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4年版。)。當然,從美術批評概念轉換為歷史學中的“時代”的概念必須滿足一些必要的條件,如一定的時段性,在該時段中對該領域影響的全面性、普遍性等等。因此,我們也恰恰是在認為美術在這一歷史時期的確深受時代政治的影響的基礎上提出和使用這個概念的。如果在這個領域中的相關課題的研究結果表明這個概念的歷史學性質并不成立,那么我們當然就不應該使用它。以目前的研究語境來看,提出和使用這個概念可能具有突出時代特征的意義,而最終能否成為一個獨立的歷史時期概念,還要通過不斷研究來檢驗。 第二個問題是,“毛澤東時代美術”對于今天具有何種價值?這是一個更為復雜的問題。當然,這不會是指毛澤東時代的藝術品在今天的經濟價值——那種價值是沒有人會懷疑的。實質上它首先指的是指導“毛澤東時代美術”的生產、傳播、建構的社會成員的審美意識和精神世界的那種價值觀念在今天——在一個已經遠離了那個時代話語的大眾商業文化語境中的存在以及是否可以發揮有效作用的問題,其次還指“毛澤東時代美術”作為文化遺產在今天的歷史判斷中的價值問題。雖然“毛澤東時代美術”在今天對于不同的社會階層所具有的意味是很不相同的,但“毛澤東時代美術”對于我們來講仍然具有重要的價值。這種價值是:第一,作為引導藝術生產的一種價值觀念,它在今天可以成為藝術多元格局中的一種重要的積極因素;第二,作為文化遺產,它的歷史價值更是不容置疑;第三,對于“毛澤東時代美術”所訴諸的對象而言,它仍然具有喚起社會群體的主體意識的意義。
藝術史解讀的復雜性 1 對“毛澤東時代”的界定不僅要注意到時間的意義,還要注意到空間的意義。延安時期毛澤東思想在解放區內占主導地位,但在整個中國并不如此,即使1949年10月以后,毛澤東思想也有一個逐漸占支配地位的過程。我們可以籠統地把1949年10月1日以后的中國稱作“毛澤東時代”,但這只是政治意義上的,還不能說是文化上的“毛澤東時代”。從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到此前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全國范圍發揮作用并深入人心,有一個歷史過程,這可以用馬克思的經典理論來解釋,即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1949年以后從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轉化有一個歷史過程,城市中的對私有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村中的人民公社化的運動,在時間和空間都有一個過程,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對全民的思想教育也同樣是一個歷史過程。在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說:“人民革命的勝利和人民政權的建立,給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學藝術開辟了發展的道路。”(注:毛澤東:《毛澤東論文藝》(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毛澤東時代”這個概念凸顯的是毛澤東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核心領導作用,但在最初它們并不完全同步,只是到了一定的歷史階段才開始同步。1949年7月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文藝思想就被確定為新中國文藝發展的指針,從而為新中國文藝樹立了明確的方向,但從確定到深入人心進而變成自覺行為需要時間。這個問題很重要,忽略這個歷史過程會影響我們對那個時代文化現象的解釋效果。 2 應當注意到,毛澤東文藝思想從1942年到1976年對于美術實踐的作用同樣有一個歷史過程。 1942年前后的延安地區在文化上有特殊性。一般而又普遍的左翼思想被毛澤東思想所取代是一個重要過程,從左翼的文藝思想向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轉化需要研究。 1949年到1957年是新中國的初創期,在文化和思想上則表現為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與非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激烈沖突。在國內的大部分地區,軍事上的敵人已被戰勝,但是文化上和思想上的敵人遠未肅清。1949年7月2日至9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這是文學藝術工作者全國規模的第一次盛會。毛澤東在賀電中說:“如果沒有人民革命的勝利,如果沒有人民政權的建立,進步的文學藝術工作者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大團結,就不可能在全國范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獲得自己的發展。”實際上,這是一次全國“進步的文學藝術工作者”的會議,當然不包括“落后的文學藝術工作者”,更不可能包括“異己的或反動的文學藝術工作者”。“我國是處在經濟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況中。在革命勝利以后,我們的任務主要地就是發展生產和發展文化教育。我們相信,經過你們這次大會,全中國一切愛國的文藝工作者,必能進一步團結起來,進一步聯系人民群眾,廣泛地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文藝工作,使人民的文藝運動大大地發展起來,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經濟建設工作”(注:毛澤東:《毛澤東論文藝》(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1957年是各種思想和文化全面較量的高峰時期,而文藝界的“右派”曾經大部分是“進步的文學藝術工作者”。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中,確定了這一場斗爭的性質:“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1958年到1966年,“進步的文學藝術工作者”的社會作用被“革命的文學藝術工作者”或“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工作者”的社會作用所取代,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才真正在全國范圍內起支配作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才由延安的文藝經典變成新中國的文藝經典。“文化大革命”主要批判的是建國十七年的“資產階級思想和路線”。到了1966年以后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居全面支配地位,對其后的歷史發展當然也要作具體分析。 3 對“毛澤東時代美術”有多種理解,與藝術史的功能視角關系密切。 按鄒躍進的理解,“毛澤東時代美術”就成了在毛澤東思想影響下的美術,這種美術可以從1942年算起。由邊緣到中心,由延安到北京,由地方到整個新中國,也可以將這種美術史看成“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所建構的中國美術史”。這種美術史不考慮1949年之前國統區的美術,也不考慮1949年以后非主流的美術或所謂“地下”美術。這種功能視角可以凸顯毛澤東文藝思想與美術之間明確的關系。而另一個問題是,從延安時期到新中國時期的美術,特別是革命美術,它們不僅與毛澤東思想有關系,也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有關系,特別是在中蘇決裂之前,與當時蘇聯實行的文藝政策有更為密切的關系。俄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框架影響深遠,普列漢諾夫的理論為人們所熟知,大量留蘇的藝術家在延續前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傳統,這樣的景觀也呈現出思想內部的復雜性。此外,同樣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組成部分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也部分地打開了與西方和中國古代文化傳統的聯系。毛澤東的頭腦里有“嫦娥”,有“吳剛”,有《紅樓夢》,有“三李”。因此,觀念建構藝術的復雜性就需要有更深入的個案研究,不斷地打開問題序列。 另一種理解是,“毛澤東時代美術”是毛澤東政治時代的所有美術。1949年成為起點。這種美術既包括體現毛澤東思想的主流美術,即表現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美術,也包括那些非毛澤東思想的非主流美術,甚至包括曾被認為是“毒草”和“黑畫”的那部分美術。這種視角可以凸顯毛澤東政治時代美術的復雜性、毛澤東思想與非毛澤東思想的緊張關系、毛澤東思想的播布過程、毛澤東思想與不同類型的藝術家的互動關系。毛澤東時代美術史,既有一個“紅畫”史,又有一個“黑畫”史;既有一個“香花”史,又有一個“毒草”史。對堅持毛澤東思想的人們來說,毛澤東時代美術史是“香花”戰勝“毒草”的美術史,是“紅畫”戰勝“黑畫”的美術史。多種歷史并置、預設了多種功能視角。換句話說,毛澤東政治時代的美術,并不都是政治美術,也存在非政治美術。用政治視角只能解讀政治美術,但不能有效地解讀非政治美術。藝術史要建立解讀的復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