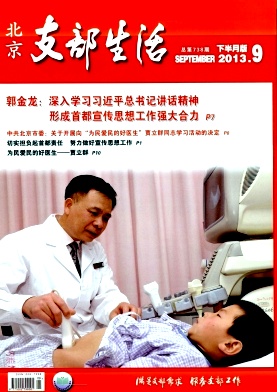唐代文館與文學研究的檢討和突破
吳夏平
關鍵詞:唐代文館;文館與文學;研究歷史;研究空間
近年來,唐代文館逐漸為研究者所關注,涌現出不少與此相關的論著,比如李德輝先生《唐代文館制度及其與政治和文學之關系》,吳夏平《唐代中央文館制度與文學研究》等,極大地推進了相關領域的研究。毋庸置疑,以往的研究在制度淵源流變考鏡、文獻整理、文館與文學關系的討論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總體來看,轉變研究視角和思維方式,尋求新的切入點,宏觀通照性地發掘文館與文學更深層的關聯,是當前此研究領域亟需解決的問題。本文在梳理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力圖探索解決問題的相關途徑。
“文館”到底指什么,關涉到研究對象的確立,各家研究都有所不同的表述。正史所記,無一統攝性確定概念,而僅出現于專有名詞之中,如弘文館、崇文館之類。兩《唐書》有“三館”一詞,如《舊唐書》卷八十八韋嗣立上武則天書云“三館生徒,即令追集”及《新唐書》卷十四“三館學官座武官后”,但此“三館”當指國子學、太學、四門學三館,與文館概念相去甚遠。
較早關注文館的學者是日本池田溫先生,他認為唐代學館之盛,中古所未見,而學士榮譽,尤著于青史。唐朝官制,政府圖書之署有秘書省,國史編纂之府則有史館,而教授學生之學校亦有國子監,及州、縣學。其外更有館院之設,可謂備矣。唐朝館院,名稱屢改,興廢不常,其名目大致有文學館、弘文館、崇文館、崇玄館、廣文館、集賢院、翰林院。[1]190-192照池田溫氏的說法,文館的范圍是很大的,舉凡掌管學藝、庋藏圖籍、教授生徒、政治輔弼之機構,概應納入文館范圍。
李德輝先生認為文館似不應包括秘書省、史館、國子監。上揭氏著指出:“兩漢以降各王朝政權都以‘尊儒重學'為名,在掌理圖書的秘書省之外設置了各種名目的‘館',主掌圖籍的校理編撰與生徒教授等事,以其多從事著撰文史等務,且館中所聚都是文人,故統稱文館。它雖然屬非常設性文化機構,但其在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發揮作用之大,卻是一般秘書省、史館、國子監等文化機構所無法比擬的。”[2]1這樣就將文館與常設性機構區分開來。
筆者認為,文館概念所指,是與論題的選擇密切相關的。研究者所關注的對象和所要解決的問題不同,對文館的界定大可不必相同。拙著《唐代中央文館制度與文學研究》,從制度與文學的關聯性入手,在制度考辨的基礎上,解決與此相關的文學問題。因此,從宏觀通照的角度出發,將“中央文館”界定為:(1)是指唐代中央文館,與地方文化機構有別;(2)是指與文化建設和文學發展的聯系較為密切的館所。因而選定包括國子監、史館、秘書省和崇文館、弘文館、集賢院、崇玄館、廣文館等文化館所作為研究的對象。[3]4-5正是緣于所解決的不同問題,其所關注對象也不一樣。羅時進先生《唐詩演進論》比較重視文館與詩歌關系的討論,因此該書的第一章《唐初文館與初唐詩風》說:“在初唐詩壇上有四代文館學士相繼主持局面,而四代人恰恰形成四個學士集團,這就是開國初太宗朝文館學士集團、高宗朝文館學士集團、武后朝的珠英學時集團和中宗朝的景龍學士集團。”[4]4-5另外,李福長《唐代學士與文人政治》[5]著重探討的是學士與政治的關系,因此選取的對象依次為秦府文學館學士、弘文館學士、北門學士、集賢學士、翰林學士。聶永華《初唐宮廷詩風流變考論》[6],也是從實際研究需要出發,對文館有不同的擇取。
(一)文館制度梳理和考辨
以文館作為切入點來討論,以往的研究更側重于歷史學和政治學,因此,制度考辨和文館史梳理成為研究的熱點。關于國子監研究,在一般論文之外,大都散見于各種教育史專書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臺灣高明士《唐代學制之淵源及其演變》[7]和任育才《唐代官學教育的改革》[8]、《唐代官學體系的形成》[9],諸文在制度考論方面極為細致翔實。對唐代史館的研究,本身就是史學界一個熱門,討論的文章和著作都很多。不過,相較而言,臺灣張榮芳《唐代的史館與史官》[10]一書尤有特色,張氏較為全面地梳理了相關制度。關于唐代秘書省的研究,主要有趙永東《談談唐代的秘書省》[11],陸慶夫《唐代秘書述略》[12]和曹之《唐代秘書省群僚考略》[13]。李萬健《唐代目錄學的發展及成就》[14],從目錄學發展的角度分析了秘書省在古代目錄學發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弘文、崇文二館的制度性考辨,亦主要散見于諸教育史著作中。論文方面,李錦繡《試論唐代的弘文、崇文館生》[15]和牛致功《唐代的學士》[16]二文,較為詳細深入。研究集賢院最珍貴的資料是唐代韋述的《集賢記注》,但原本已佚,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宋代王應麟《玉海》中所引的數十條。上世紀二十年代,朱倓鉤稽排比,撰成《〈集賢記注〉輯釋》[17],是研究集賢殿書院的基本材料。日本學者池田溫《盛唐之集賢院》[1]從沿革、省舍、儲藏、修纂、故實、職掌、祿廩、官聯八個方面進行考察。隨后,鄭偉章、趙永東、劉健明、李湜等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對集賢院制度進行考察。
關于崇玄館的研究相對薄弱,一般置于對唐代道舉和道教的考察之中。討論廣文館的文章也不多,廖健琦《唐代廣文館考論》[18]從設立時間、設立原因和中唐之后的存否等方面立論,較有新意。關于廣文館的性質,臺灣高明士先生認為“其目的在招收國子監學生之攻讀進士科者,有如今日在學校內附設之補習教育。”[7]206但這種說法并不完全合乎事實。招收國子監學生攻讀進士科者固然不錯,但所謂的補習教育因廣文館自身為一獨立教育單位而不能成立,廣文館業進士者的資格亦非補習生。
(二)文館與詩歌
文館與文學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詩歌方面,包括律體律調分析、唱和詩集整理、詩學著作考辨和詩學理論溯源等。
1、關于律體律調的探討較早研究唐詩律體律調的是郭紹虞先生,收錄于《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19]中的《永明聲病說》、《從永明體到律體》、《再論永明聲病說》、《聲律說考辨》等文章主要從五言詩音步的角度,說明“古”、“律”之間的聲律問題。1986年,趙昌平發表《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風格溯源》[20],考定初唐九次重要“七律”應制唱和組詩,結論是七律并不像有些人所說的是五律每句加二字而來的,七律的淵源當是蛻化于駢賦化的歌行。香港鄺健行《初唐五言律體律調完成過程之觀察及其相關問題之討論》[21],從單句句調不合、失對聯數、失黏首數、不合律首數等方面,考察初唐作家虞世南、李百藥等22人519首接近五律詩歌的聲律狀況。鄺文認為律調受到重視和探討,主要是作者順應文體本身的發展、從事探索的結果,跟君主的好文無關。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葛曉音先生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分別討論宮廷文人在初盛唐詩歌藝術發展中的作用、七言歌行的發展以及絕句的發展等問題。葛氏雖不是直接探討初盛唐詩歌律體律調,但卻有借鑒和啟發意義。正是在乃師的鼓勵和啟發之下,杜曉勤在此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從永明體到沈宋體——五言律體形成過程之考察》[22]指出:五言律體的形成雖然幾經波折,但每一次發展都離不開宮廷詩人。如果沒有他們對詩歌聲律美的不懈追求,沒有他們對原有詩歌聲律模式的突破與創新,五言新體詩的律化進程無疑會更漫長。可是,杜氏所認為的律體律調最終定型于沈宋即“沈宋體”的看法,雖與眾多文學史同調,卻不為陳鐵民先生所接受,陳先生經過分析考證,認為律體的定型是初唐一批珠英學士、修文館學士,其功不能全歸于沈宋二人。[23]
2、唱和詩集的整理初唐唱和詩集的整理主要集中在《翰林學士集》、《珠英學士集》、《景龍文館記》。
(1)《翰林學士集》翰林學士之名,始于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其時改翰林供奉為翰林學士。因此,對于《翰林學士集》的結集和標題,眾多學者提出揣測,但以陳尚君和日本森立之的說法為上,森立之疑為許敬宗所撰,陳尚君進一步指出可能為許敬宗別集殘卷,理由為集中收許詩最多,每題皆有其作品,且目錄亦以其詩列目。[24]3賈晉華先生在《翰林學士集》的基礎上,廣引文獻,將太宗朝宮廷詩人群的唱和篇章及文學活動逐一考證,起于武德九年九月,終于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共考得太宗君臣唱和詩214首又2斷句,文賦13首,預唱詩人45人。[25]12-33
(2)《珠英集》《珠英集》又稱《珠英學士集》,五卷,唐崔融集武后時修《三教珠英》學士李嶠、張說等詩而成,宋以后散佚。現存敦煌寫本二卷,分藏英國和法國,編號為斯2717、伯3771。《珠英學士集》的整理經歷了漫長的過程,董康、向達、王重民、項楚、吳其昱等學者都作出過重要貢獻,最終由徐俊先生全面完成。徐俊先生將英、法所藏寫本拼接對看,得出法藏伯卷當為英藏斯卷《珠英集》第五卷的部分內容,這樣就將二處分藏的殘篇連接起來。徐先生對《珠英集》考證的重要成果主要有兩點:第一,校正歷來關于學士人數的記載,明確為47人;第二,全面整理校勘現存詩歌,共得55首。[26]548-587
(3)《景龍文館記》據《新唐書·李適傳》、《唐詩紀詩》卷九李適條、《唐會要》卷六十四“宏文館”條、《直齋書錄解題》卷七、《玉海》卷五十七等文獻記載,中宗景龍二年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以象四時八節十二時,其后被選者不一。他們圍繞中宗宴飲優游、頻頻唱和。身為學士之一的武平一將此其間的活動記錄下來,并錄有唱和作品及諸學士傳,名為《景龍文館記》。較早注意到《文館記》的是日本學者,如高木正一《景龍の宮廷詩壇と七言律詩の形成》,西村富美子《唐初期の應制詩人》、安東俊六《景龍宮廷文學の創作基盤》都力圖還原宮廷文學活動及其相關背景。[25]44我國學者的研究主要有陶敏《〈景龍文館記〉考》[27],賈晉華《〈景龍文館記〉輯校》[25]和《〈景龍文館記〉與中宗朝學士群》[25]。陶文側重于成書始末及版本流傳等文獻學方面,賈文則全面輯校了《文館記》,并對其間活動進行編年。
3、相關詩學著作考辨和詩學理論溯源初唐三大詩學著作,即上官儀《筆札華梁》、元兢《詩髓腦》、崔融《新定詩體》。此三者始見錄于中唐求學之日僧空海所著《文鏡秘府論》,后輾轉傳抄,面目全非,經王夢鷗先生大力考證,基本上還其原貌。王先生認為宋代《吟窗雜錄》所錄《魏文帝詩格》即傳抄《筆札華梁》所成,而以現存于《吟窗雜錄》卷六李嶠《評詩格》所載十體九對之文字與《文鏡秘府論》所引崔氏之語相對照,李嶠《評詩格》與崔融《新定詩體》實為同一書,《評詩格》乃后人所偽托李名也。此后所論,陳陳相因,大抵不出王先生所述范圍。
王氏不僅考論有關初唐新體詩成立的兩種殘書,更論及初唐詩學產生之淵源,并分析其成因。認為初唐詩學,多為適應宮廷之藝文生活而發達,殆與齊梁時代相類似。其詩體既沿襲江左余風,而詩學之所發明者,亦即為齊梁詩體之分析。從分析而創立若干規格,轉成唐代試士之圭臬。按其作業,自始即偏向于“綴文”之道,而與吟詠“情志”者無直接關系。[28]
詩歌之外,研究文館與文學之關聯性較多的,主要集中在探討唐初所修前代“八史”與初唐文學思想的關系。這在文學批評史、思想史等著述中都有論及,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論述尤為詳備。曾守正《唐初史官文學思想及其形成》[29],從唐初史官文學思想的主要內容、成因、評騭三方面來考量初唐史官的文學思想。李勝《初唐史家文論特色檢討》[30]認為:以令狐德棻、魏征為代表的初唐史家的文學見解,表面看來,像是折衷調和,論其實質,則表現了對文學發展規律的全面認識,較早、也較正確地為光輝燦爛的唐代文學指出了發展方向。
其它文體方面,如從文館的角度來觀照小說、散文的演變之類的論著不多。拙著《唐代中央文館制度與文學》力圖有所突破,對文館與唐傳奇、實錄、墓碑文、行狀等文體之關聯,都進行了積極的探索。拙文《從行狀和墓碑文看唐代駢文的演進》[31],從文館的角度提出構建分體駢文史的斷想。
從文館研究的歷史來看,研究者比較重視這樣幾個問題:(1)歷史學視野,關注文館制度本身的淵源和流變,著重于制度的梳理和考辨。(2)政治學視野,著力剖析文館文士與政治之間的關系。(3)文館與文學的關系,可歸結為:文館學士與作家群體;文館創作與文壇風尚;文學盛衰與文學嬗變;文館唱和和詩體發育等方面。[2]399-402
上述成果無疑為未來的研究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但其中的缺失和不足也不容忽視。由于側重點不一,他們往往致力于某一中央文化機構的研究,“點”多“面”少,缺少較為全面系統的研究。又囿于論題性質,歷史學、政治學研究較多,因而在“與文學”之關系的討論方面,有待進一步深入。
重新思考已有成果,筆者認為文館與文學研究空間的拓展,主要還有賴于思維方式的轉變和研究視野的開拓。應用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和理論,選取文士社會角色作為切入點,進一步探究文館與文學之關系,是比較有價值和意義的:其一,回歸文學本位研究。傳統研究在歷史學、政治學等方面揭示文館的價值,但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來觀照,我們必須同時看到,其成果一方面可作文學研究之參照,另一方面其落腳點并非文學。吸收前人成果,推進并深化文館與文學之關系的研究,改變過去的研究格局和研究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學術史意義。其二,運用已有文館研究成果,借鑒社會學理論,進行多學科交叉研究,力圖在歷史文化學和文學社會學層面有所突破,還原文館文人與唐代文學演進的歷史原貌。因此,系統化現有成果的同時,也是對前沿學術方法運用的檢測,具有理論探索意義。其三,從近年來國內外研究現狀來看,文人生存狀態和心理狀態日益成為研究熱點。學者熱衷于從空間分布、科第出身、文化背景等角度來剖析文士的精神風貌,對于文士社會角色與生活方式、心理狀態之聯系則關注不夠。因此,從文士社會角色變遷來考察文館文人的精神風尚及其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其成果具有一定的開創意義。
依據社會學相關理論,社會角色有規定性角色和開放性角色之分。就文館而言,前者主要有學官、史官、圖籍校勘官、著作郎官、學士五大類,后者主要包括經學家、思想家、文學家等角色。這兩種角色有時難免交叉和互換。未來的研究應打破成例,努力解決與此兩種社會角色相關的文學問題,從角色之意識、評價、社會流動、心態等層面分別探討與文學生成、發展、衍變之間的內在聯系,剖析文士角色與詩歌、散文、小說等各種文體演變的相互關系。加強動態研究,揭示文士角色與文學團體、文學風氣、文藝思潮、文學傳播等各種文學現象和文學流派之間的潛在規律。筆者以為可以圍繞以下幾方面展開。
其一,文士任職中的角色本位意識與文學樣式。所謂本位,在這里是指各文館職事活動的規定性,比如學官之教育、史官之修史、圖籍官員之校勘、著作郎官之著述等等。不同社會角色的文學創作,往往在題材、內容,甚至風格上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差別。比如秘書省校書官本位意識與詠物詩創作,文士任職與散文寫作,史官“泛諫諍意識”與中唐傳奇勃興等。
其二,文士社會角色評價與文學。社會評價系指社會在文士選任、遷轉和地位諸方面對文士職務作出價值判斷和預測。從任職資格歸納文士選任中的文學因素,從職務變遷總結與遷轉相關的文學質素,通過計量分析,在整體上把握選任和遷轉的規律,并由此還原文士生活生存狀態與文學群體性活動之間的關系。比如由于任職形成文學創作小集團,集體創作觀念對文壇風尚之影響,各文館社會地位高低變化與士子價值認同和價值取向等等。
其三,文士社會角色流動性與文學活動。文士社會角色流動是指文士京都任職與地方任職之間的區域流動。京都長安和洛陽是中央文館所在地,也是當時的文化強勢區,文士離開京都到其它地方任職,勢必帶動文化的交流和傳播。比如由韓愈遷謫嶺南、白居易貶江州、劉禹錫之夔州等角色流動,推動弱勢區文化教育的發展,促進強弱勢區域之間文學思想的交流和傳播等等。
其四,學士文學角色批判與詩歌復古進程。將學士單獨列出來討論,是因為過去的研究將其局限于初唐詩歌聲律問題。文學發展是諸種合力的結果,若將詩歌分成主流創作和非主流創作,從非線性發展來重新審視唐詩進程,則會發現唐詩演進軌跡受主流與非主流文化之沖突的影響很大。一般而言,學士處于創作主流地位,同時又是京城文化、宮廷文化的代表,而非主流作家則是地方文化、民間文化的代言人。從這個角度來看,詩歌復古實質上是文化沖突在文學上的一種表現,詩歌復古進程也是文化沖突與順應的過程。
不過,多學科交叉研究要求研究者同時具備多門學科知識,在知識結構方面應有所提升和完善。同時,還應注意點面結合、虛實相間的問題。筆者以為可以采取現代科技手段,創建與研究相關的數據庫,加強一般與個別有機相融的動態系統分析。
綜上所述,歷時性地來看,唐代文館與文學研究在制度淵源流變的梳理和考辨、文館與詩歌的分析探討方面成果較為豐碩,而在文館與小說散文等方面的討論相對薄弱。總體而言,個案分析較強,整體論述較弱。雖然出現了《唐代文館制度及其與政治和文學之關系》和《唐代中央文館制度與文學研究》等專著,但從文學本位的角度來看,略嫌關注不夠。因此,將歷史學、政治學、文學等與社會學結合起來,從文館文士社會角色切入,解決相關文學問題,當是深具發掘潛力的未來研究空間。
[1]池田溫.盛唐之集賢院[A].唐研究論文集[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2]李德輝.唐代文館制度及其與政治和文學之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吳夏平.唐代中央文館制度與文學研究[M].濟南:齊魯書社,2007.
[4]羅時進.唐詩演進論[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5]李福長.唐代學士與文人政治[M].濟南:齊魯書社,2005.
[6]聶永華.初唐宮廷詩風流變考論[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7]高明士.唐代學制之淵源及其演變[J].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報,1977(4).
[8]任育才.唐代官學教育的改革[J].臺灣興大歷史學報,1998(8).
[9]任育才.唐代官學體系的形成[J].臺灣文史學報,1997(27).
[10]張榮芳.唐代的史館與史官[M].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4.
[11]趙永東.談談唐代的秘書省[J].文獻,1987(1).
[12]陸慶夫.唐代秘書述略[J].秘書之友,1985(1).
[13]曹之.唐代秘書省群僚考略[J].圖書與情報,2003(5).
[14]李萬健.唐代目錄學的發展及成就[J].文獻,1995(1).
[15]李錦繡.試論唐代的弘文、崇文館生[J].文獻,1997(2).
[16]牛致功.唐代的學士[J].社會科學戰線,1987(1).
[17]朱倓.〈集賢記注〉輯釋[J].國立中山大學文學史研究所月刊,1934(1).
[18]廖健琦.唐代廣文館考論[J].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2004(6).
[19]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0]趙昌平.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風格溯源[J].中華文史論叢,1986(4).
[21]鄺健行.初唐五言律體律調完成過程之觀察及其相關問題之討論[J].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90(21).
[22]杜曉勤,從永明體到沈宋體——五言律體形成過程之考察[J].唐研究,1996(2).
[23]陳鐵民.論律詩定型于初唐諸學士[J].文學遺產,2000(1).
[24]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25]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26]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M].北京:中華書局,2000.
[27].陶敏.〈景龍文館記〉考[J].文史,1999(48).
[28]王夢鷗.初唐詩學著述考[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29]曾守正.唐初史官文學思想及其形成[A].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八號)[C],臺北: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研究所,1994.
[30]李勝.初唐史家文論特色檢討[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3).
[31]吳夏平.從行狀和墓碑文看唐代駢文的演進[J].文學遺產,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