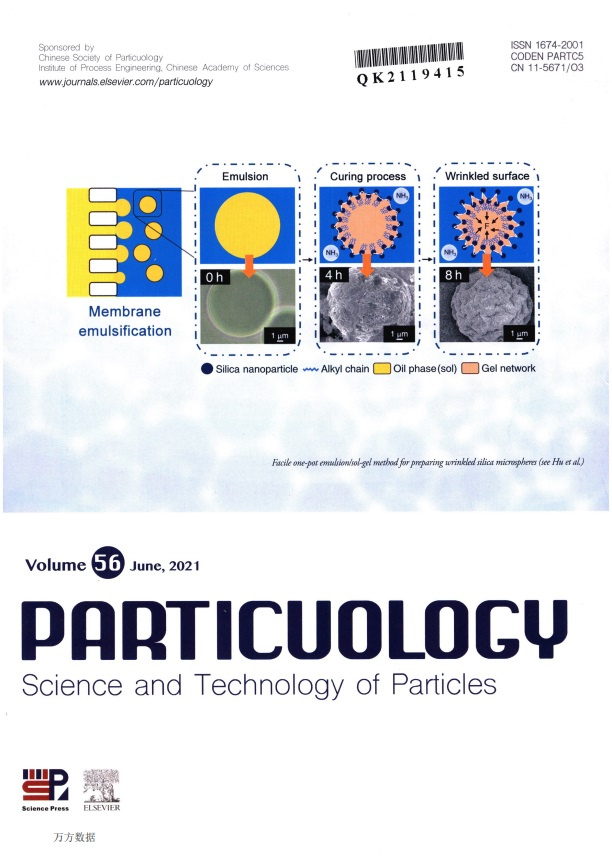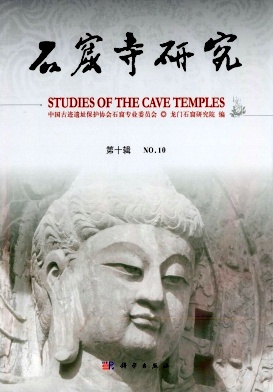“選精”、“集粹”與“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對傳統經濟史研究方法的檢討(上)
佚名
【提要】"宋代革命說"是國際史壇上最流行的成說之一,本文徹底否定了這種觀點。文章指出,中國是個傳統的農業,如果真有"宋代經濟革命",首先應表現為"宋代江南農業革命",但從經濟成長方式看,宋代江南雖有若干重要進步,但并沒有出現可以稱為"革命"的重大變化。因此,"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只不過是一個"虛像"而已。產生這種錯誤的根源是論,主要表現為"選精法"和"集粹法",這兩種方法的主要錯誤都在于將某一或某些例證所反映的具體的和特殊的現象加以普遍化,從而使之喪失了真實性。因此,對以往的方法進行,是今日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當務之急。
【關 鍵 詞】宋代、江南、農業革命、選精法、集粹法
近年來國內外史壇上的一個重要動向,是對以往各種具有共識性的成說以及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進行檢討。通過這個檢討,摒棄不合理者,改進不完善者,同時提出新見,引入新法,從而推動史學研究的(注:參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第2章,中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本文的目的,就是通過對宋代江南農業有關的討論,對中國經濟史壇上最重要而且也是最流行的成說之一--"宋代經濟革命"說--以及導致此說的方法進行檢討,看看這些方法是如何和為何導出重大的錯誤結論來的;在此基礎之上,探討如何改進我們的研究方法,促進我國的經濟史研究在新世紀中取得更大的進展。
一、"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宋代經濟革命"的中心
在史家眼中,宋代是中國上最具魅力的。41年前,宮崎市定將其關于中國歷史發展的總體觀點總結如下:"中國文明在開始時期比西亞落后得多,但是以后這種局面逐漸被扭轉。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亞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歐洲文明向前發展了。到了文藝復興,歐洲就走在中國前面了。但起初二者之間的差距還很小,直到18世紀還是處于一種雁行狀態。但是革命一發生,歐洲便把中國遠遠拋在后面了。"(注:宮崎市定:《宋代における石炭と鐵》,刊于《東方學》第13輯(1957年)。)由這段話可見,這位日本漢學大家認為宋代不僅在中國歷史上,而且在世界歷史上,都占有一種特殊的地位。16年后,英國漢學家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了中國"中古時期的經濟革命"( medieval economic revolution)和"帝制晚期的沒有技術變化的經濟發展"(The late imper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out technological change)的,認為中國在唐宋(特別是宋)時期出現"經濟革命",而自14世紀以后則出現重大轉折,陷入"量的增加,質的停滯"(Quantitative growth,qualitative standstill)(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年版。)。又過了13年,中國宋史學家漆俠提出了我國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兩個馬鞍形"模式,即在秦漢時期達到第一個高峰,魏晉以下低落,隋唐有所恢復和回升,到宋代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發展,從而達到了一個更高的高峰","把宋代中國推進到當時世界經濟文化發展的最前列";元代急遽下降,明代中葉恢復到宋代水平,以后雖有所發展,但在一定程度上顯現了遲緩和停滯(或者說,在金、元時期出現"逆轉",以后則"逐漸地緩慢、停滯下來")(注:漆俠:《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及其在中國古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刊于《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以及同氏《宋代經濟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0-31頁。)。而到最近,在當代世界經濟研究中享有盛譽的經濟學家安古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以迄今為止歐美學界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用經濟學的方法對中國歷史上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做了估算。根據其的結果,無論是作縱向的還是橫向的比較,宋代在世界經濟史上都具有一種非同尋常的地位:在960-1280年間,盡管中國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卻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但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著此水平,到1952年更下降到537美元。與此相對照,歐洲在960-1280年間人口增加了70%,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從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而1700年達到870美元,超過中國;1820年達1129美元,已將中國遠遠拋在后面;1952年更高達4374美元,為中國的8倍(注: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gr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8年版,第25、40頁。)。由此可見,在過去的40多年中,中外許多學者從各自的研究中和從不同的方面,都得出了"中國經濟在宋代出現飛躍,達到了頂峰,爾后發展減緩,最后限于停滯"的結論。這個結論已成為現今學壇上關于中國歷史發展模式的主流觀點,而此觀點的主要基石之一,就是宋代中國經濟出現了巨大進步,即"宋代經濟革命"。
"宋代經濟革命",按照伊懋可的總結,包括農業革命、水運革命、貨幣與信貸革命、市場結構與都市化的革命和技術革命(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PartⅡ。)。而依照斯波義信的歸納,則主要包括農業革命、革命、商業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變化(注:斯波義信:《北宋の社會經濟》(收于松丸道雄、池田溫、斯波義信、神田信夫和濱下武志合編《世界歷史大系--中國史》第3卷,山川出版社1997年版),第4-8小節。)。他們所說到的各種"革命",從種類來說都大致相同。因此如果真有"宋代經濟革命"的話,主要內容應當大致也就是這些。宋代中國在這些經濟領域中出現了重要的變化,這是沒有爭議的。但問題是,這些變化合起來,是否就可以稱為"經濟革命"?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就要對"經濟革命"作一界定。
從宏觀的層面來說,"經濟革命"指的是一個社會經濟成長方式的重大變化(注:參閱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Presidential Address:Questions about 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刊于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51卷第4期(1992年)。)。一般而言,經濟成長方式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只有"量的擴大"(quantitative increase)而無"質的改進"(qualitative improvement),另一種則既有"量的擴大"、又有"質的改進"。在西方學界,有人也將前者稱為"增長"(growth),而將后者稱為"發展"(development)。所謂經濟革命,通常指的是經濟成長方式由只有"量的擴大"而無"質的改進"的"增長",向既有"量的擴大"、又有"質的改進"的"發展"的轉變(注:關于"量的擴大"、"質的改進"、"增長"、"發展"這些說法及其與技術進步、勞動生產率提高之間的關系,見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306-316頁;黃宗智(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年版,第11-13頁。)。因此如果真有"宋代經濟革命"的話,那么一定是宋代經濟成長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由"增長"轉變為"發展"。
在一個農業社會中,經濟以農業為主體,其他經濟部門不僅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很小,而且還往往依賴于農業或與農業密切相關,所以整個經濟成長方式的變化主要取決于農業的變化。在此意義上而言,只有出現了農業革命,經濟成長方式才可能出現重大改變,因此經濟革命也可以說主要就是農業革命。如果沒有農業革命,雖然可能也會有一個商業革命(或水運革命、貨幣與信貸革命、市場結構與都市化的革命,等等),但那只是局部的變革,整個經濟成長方式并不會因此而發生重大改變,所以并不能真正稱為經濟革命。宋代的商業、手工業、運輸業乃至業等都有相當大的發展,但農業仍然在經濟中占有主導性的地位。伊懋可和斯波義信在對宋代各經濟領域的"革命"的歸納中都將"農業革命"置于首位,這是很正確的。其次,在宋代各主要經濟區中,無論從經濟發展水平或是在全國經濟中所占有的分量來說,本文所說的"江南"居于首位(注:"江南"本是一個界限不甚明確而且不斷變化的地理概念,我在過去的文章中已對其作了界定(見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刊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在本文中,為了討論的方便,將所論的"江南"地區限定于地中的江南平原(或太湖平源),范圍大體包括宋代浙西路轄下的蘇州(平江府)、常州、秀州(嘉興府)、湖州與江陰軍。),這已是史壇共識,毋庸贅言。伊氏和斯波氏也都明確地指出:他們所歸納的各經濟領域的"革命",并非出現在宋代中國的每一個地方,而是主要發生于中國東南地區,特別是江南。雖然其他地區(特別是福建、江西、浙東、四川等地)在宋代經濟發展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宋代經濟革命"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仍然是江南。如果沒有福建、江西、江東、浙東、四川諸地區中任何一個,都不會從根本上動搖"宋代經濟革命"之說;相反,如果沒有江南,"宋代經濟革命"之說定然要破產。
由于農業和江南二者是"宋代經濟革命"說賴以建構的主要基石,所以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如果確有一個"宋代經濟革命"的話,那么這個"革命"應當以在宋代江南農業中表現最為明顯,因而對宋代江南農業的探討也就成為研究"宋代經濟革命"的核心。如果這個探討的結論是宋代江南農業沒有出現一個"革命",那么"宋代經濟革命"之說也就難以成立了。二、"宋代江南農業革命":一個"虛像"
如前所述,所謂革命,通常是指經濟成長方式由只有"量的擴大"而無"質的改進"的"增長",向既有"量的擴大"、又有"質的改進"的""的轉變。而這兩種成長方式的主要差別,又在于技術有無重大進步以及勞動生產率是否大幅提高。因此經濟革命也就以技術的重大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為主要特征。在本文中,我們也將以此作為判別是否有"宋代江南農業革命"的兩個主要標準。其中,在勞動生產率方面,我們將采用糧食畝產量增加作為判斷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主要指標。這樣做的原因并不難理解:在農民人均耕地與生產技術未有很大變化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是通過畝產量的增加來達到的。而我們知道,與唐代相比,宋代江南人口雖有大幅度增長,但耕地增加也很快,因此人均耕地面積即使不比唐代更高的話,也不會少于唐代(注:例如,按照中唐時期的官方數字,元和時期浙西路戶均耕地為18.5畝,而南宋時期江南農戶的戶均耕地則在40畝左右。當然唐代的數字明顯偏低(因為這只是政府征稅田地的數字),但無論如何,南宋江南農民戶均耕地面積不少于唐代,應當是可以肯定的(唐代與南宋的情況分別參見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農業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頁;《宋末至明初江南農民經營方式的變化--十三、十四世紀江南農業變化探討之三》,刊于《農史》1998年第2期)。此外梁庚堯也指出:即使是以江南最重要的州府--蘇州為代表,自北宋中期至南宋末期,人口增加與耕地增加的趨勢,正相呼應(見梁庚堯《宋元蘇州的農業發展》,收于許倬云、毛漢光、劉翠溶主編《第二屆中國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漢學資料及服務中心1983年印行)。)。倘若宋代江南畝產量有大幅度的提高,當然也就表明勞動生產率有明顯提高。
持"宋代江南農業革命"說的學者,大都十分重視技術進步。晚近大澤正昭將以往學界公認的宋代江南農業的進步,為以下四個方面:(1)水利田(圩田、圍田等)的大規模開發;(2)占城稻的廣泛種植以及一年二作制的普及;(3)生產出大量的稅糧和人口增加;(4)出現了以《陳旉農書》(以及樓璹《耕織圖詩》)為代表的高水平的農業技術(注:大澤正昭:《唐宋變革期農業社會史研究》,汲古書院1996年版,第236-249頁。)。這個總結,與伊懋可和斯波義信所總結出來的情況大體相同(注:參閱Mark Elvin,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118頁;斯波義信:《北宋の社會經濟》,第175頁。伊氏所提供的關于宋代農業進步的證據,主要集中在南方(特別是長江下游);而斯波氏則認為有關進步主要發生于長江中下游、浙江、福建等東南沿海地區,中心是長江三角洲和福建。也就是說,以江南為中心。),可以說代表了以往學界在此方面的主要看法。由此可見,以往所說的"宋代農業革命",從技術進步方面來看,主要包括耕作技術的改進、新作物品種(特別是占城稻)的引進、一年二作制的普及、水利技術的提高以及農具改良與肥料廣泛使用。由于這些技術進步主要集中在江南,所以引起了"宋代江南農業革命"。
在畝產量的研究方面,學壇上的普遍看法是宋代江南糧食畝產量比過去有明顯提高,并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就比較"保守"的估計而言,余也非估計唐代江南畝產1.5石,宋代畝產2石(均為米,下同)(注:余也非:《中國歷代糧食平均畝產量考略》,刊于《重慶師范學院學報》1980年第3期。);吳慧的估計是唐代1石,宋代2石(注: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量研究》,農業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160頁。)。斯波義信較早的估計是北宋初1石,南宋后期2石;較后的估計則是北宋1.5-2石,南宋2-3石(注:斯波氏前一估計見《宋代の消費、生產水準試探》,刊于《中國史學》第1號(1991年),并可參閱同氏《宋代江南經濟史の研究》,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8年版,第90-91、137-141頁;后一估計見同氏《北宋の社會經濟》與《南宋と金國の社會と經濟》(后者也收于松丸道雄等合編《中國史》卷三),第175、353頁。斯波氏估計南宋江南平均畝產量為2石,但他也發覺這個估計與常熟、紹興(該地官圩田畝產量也僅為0.74石)的畝產量相差太多,所以他又說這大概是因為量制變化的結果。)。閔宗殿的估計屬于比較"中間"者:兩宋均為2.5石(注:閔宗殿:《宋明清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刊于《中國農史》1984年第3期。)。"激進"的估計則更高,如顧吉辰估計北宋蘇州一帶水稻畝產4石,"接近于今天的水平",江南其他地區則在2石上下(注:顧吉辰:《宋代糧食畝產量小考》,刊于《農業考古》1983年第2期。)。而漆俠在其1983年發表的論文中,認為江浙地區的畝產量,宋仁宗時為二三石,南宋初年為三四石,南宋晚期為五六石;在1986年發表的論文中,估計兩浙路太湖地區的水稻畝產量,北宋時為3石,南宋時為五六石或六七石;而在1987年出版的專著中,則認為江浙地區畝產量,南宋初期為三四石,南宋中后期為五六石,而在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兩浙地區達六七石:如與前代和后代相比,則宋代江南畝產量為唐代的2-3倍,與明清相差無幾,"雖然不能說它已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但至少可以說是接近這個水平了"(注:漆俠:《宋代農業生產的發展及其不平衡性》,刊于《中州學刊》1983年第1期(轉引自閔宗殿《宋明清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以及漆氏《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及其在中國古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宋代經濟史》第2、26、138、178頁。)。事實上,漆氏最末的一句話顯然是太過保留了,因為他關于宋代江南畝產量的估數,已超過或達到今天在運用的蘇州、上海等江南高產地區豐收年份的水稻最高畝產量(注:據1998年11月1日《文匯報》報道,上海"七五"、"八五"期間的平均畝產量分別411.8公斤和547.7公斤。1998年達50公斤,創最高紀錄。又,1980年以前蘇州地區的單季晚稻畝產量的最高紀錄,是1966年的878斤。宋代畝產米1石,約合今日畝產稻谷180斤(見閔氏《宋明清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如果畝產6石與7石,那么相當于今日畝產1080斤和1260斤,分別為1966年蘇州畝產量的1.23倍和1.44倍。因此依照漆氏的估數,南宋后期江南水稻畝產量比1980年以前蘇州單季晚稻的最高畝產量高出23%-44%,相當于(甚至超過)上海有史以來的最高畝產量。)。即使按照比漆氏估數低的顧氏估數,北宋蘇州的畝產量也不僅大大超過明清江南的平均畝產量(注:閔宗殿估計江南太湖地區畝產量,明代為2.2-2.3石,清代為2石(見閔氏《宋明清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而我從供求關系出發對明清江南糧食產量所作的宏觀的結果,是明末江南水稻畝產量約為1.7石,清代中期升至2.3石(見李伯重《"天"、"地"、"人"的變化與明清江南的水稻生產》,刊于《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4期)。即使扣除了度量衡與畝積變化的因素,顧氏對宋代的估數也大大高于明清的畝產量。),而且超過了1955年和1975年蘇州的平均畝產量(注:蘇州地區的單季晚稻畝產量,1955年為485斤,1975年為689斤(見閔氏《宋明清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因此,如果宋代畝產米4石,就相當于今日畝產谷720斤,比1955年和1975年的平均畝產量高出48%和4%。)。
由上述估數來計算宋代江南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結果也高得令人驚詫。例如,南宋江南農戶戶均種田面積若以漆氏所言的30-50畝計(注:漆俠在分析南宋蘇州與華亭學田租佃情況時指出:一個農戶,一般可種田30-50畝。見漆氏《宋代經濟史》,第218-219頁。在該書第74頁,漆氏又說宋代兩浙路大部分農民的耕地數在19.5-25畝以下,而在第331、1204頁中所引用的一些個案例子,則又表明江南一些農戶種田之數多達60、80畝。因為其前說(30-50畝)所根據史料比較具體而且明確,姑采之。我本人的估計則是每戶種田約40畝,而其他學者如柳田節子、草野靖、梁庚堯等的估計或提供的各地戶均耕地數,也在30-50畝之間。見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農民經營方式的變化--十三、十四世紀江南農業變化探討之三》。),畝產量以五六石與六七石之中數6石計,那么一個農戶一年可生產180-300石米。其時江南人均糧食消費量,大約是每人每日1升米,一個5口之家一年食米共18石(注:參閱斯波義信《宋代の消費?生產水準試探》。)。換言之,一個農戶所生產的糧食,就可以養活10-16.7個同樣規模的家庭(包括該農戶在內)。換言之,只要有大約6%-10%的家庭從事農業,就足以養活整個社會。這樣的比例,相當于1994-1995年新西蘭農業就業人數在社會總就業人數中所占的比例(9.6%),高于我國省(10.5%)、韓國(12.5%)和俄羅斯(14.9%),更遠遠超過我國大陸(52.7%)(注:有關統計數采自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第60頁。)。由此可以推論宋代太湖平原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已達到20世紀末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才達到的水平。此外,按照這些估數計算出來的畝產量和勞動生產率增長幅度,也非常可觀。例如根據漆氏的估數計算,在兩宋時期中,江南畝產量增加了116%或120%,南宋時期內增加了86%,而在唐宋時期則增加了1-2倍。正是由于宋代畝產量的大幅提高,所以漆氏認為南宋太湖平原的農民的勞動生產率比唐代提高了兩三倍(注:漆俠:《宋代經濟史》,第175頁;及同氏《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及其在中國古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與此相對照,在英國農業資本主義化的18世紀(前半期是以"圈地運動"為標志的資本主義大農業的形成時期,后半期則已發生農業革命),雖然有一系列重大的組織變革和技術進步,但在此一百年中,該國(英格蘭和威爾士)糧食畝產量僅增加了10%略多,而農業勞動生產率大約只提高了25%(注:Philips Dean &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4年版,第69、75頁。),提高幅度都小于上述漆氏所說的江南畝產量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幅度。
技術的重大進步和由畝產量劇增所導致的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二者所組成的總體圖像,當然是指江南農業在宋代有了突飛猛進,自非"農業革命"莫屬。然而,這個為學界廣泛接受的總體圖像,近來卻受到越來越猛烈的批評。用大澤正昭的話來說,所謂"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并非事實,而只是一個"虛像"。
大澤正昭在關于宋代江南農業生產力的專項研究中,對過去學界所說的宋代江南農業技術進步的四個主要方面逐個進行了深入分析,指出:(1)宋代江南圍田(或圩田)的大量興建,只是濕地開發的初始階段,所開土地在"干田化"之前,生產能力頗低,而且產量頗不穩定。而江南的"干田化"運動要到了明代才開始;(2)占城稻的種植在宋代江南并未得到普及;(3)糧食總產量的增加,也可以采取粗放的農業經營方式達到;(4)以《陳旉農書》(以及樓璹《耕織圖詩》)為代表的高水平的農業技術,并不是當時普遍運用于本文中所說的江南地區的農業技術;即使到了南宋,江南農業中所使用的技術,從總體水平而言,也并未超過唐代后期陸龜蒙所描述的那種技術水平(注:大澤正昭:《陳旉農書の研究》,農山漁村文化協會1993年版,第40-44頁;同氏《唐宋變革期農業社會史研究》,第239-249頁。關于"干田化"的,見濱島敦俊《土地開發與客商活動--明代中期江南地主之投資活動》,收于《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第2輯,中央研究院1989年印行。)。足立啟二、北田英人、游修齡的研究也從不同的方面證實情況確實如此(注:見足立啟二《宋代兩浙における水稻作の生產力水準》,刊于熊本大學《文學部論叢》17號(1985年);北田英人:《宋元明清中國江南三角洲農業の進化と手に關する發展研究》(1986-1987年度研究費補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報告書);游修齡:《占城稻質疑》,刊于《農業考古》1983年第1期。)。此外,我本人對唐代至清代中期農業的長期發展趨勢的研究也表明:在這一千多年中,江南農業技術的變化,是漸進性的,而且是朝著同一方向的。在此基礎之上的農業發展,當然也不會出現戲劇性的突變(即"革命")和爾后長期性的停滯,因此無論是從事實上還是邏輯上來說,"宋代江南農業革命"之說都是難以成立的(注: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人口與耕地的變化--十三、十四世紀江南農業變化探討之一》,刊于《中國農史》1997年第3期;《宋末至明初江南農業技術的變化--十三、十四世紀江南農業變化探討之二》,刊于《中國農史》1998年第1期;《宋末至明初江南農民經營方式的變化--十三、十四世紀江南農業變化探討之三》,刊于《中國農史》1998年第2期;《宋末至明初江南農業變化的特點和歷史地位--十三、十四世紀江南農業變化探討之四》,刊于《中國農史》1998年第4期。)。
近來對宋代江南畝產量的研究,也證明了宋代江南糧食畝產量決不像一般所認為的那么高。例如斯波義信對南宋《常熟縣學田籍碑記》中114例學田地租數字進行分析的結果表明,嘉熙以前該縣一般畝產量大約在0.65石上下(畝產量以地租量之倍計,下同)(注: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の研究》,第143-144頁。)。方健對該碑文中的數字進行復核,指出實屬該縣的學田地租數字應為153例,所涉及的學田共1784.94畝,平均畝產量為0.88石;而據袁甫《言氏子孫記》中的田租數字計算,同時期該縣上等學田(450畝)的平均畝產量也僅為1.68石(注:方健:《兩宋蘇州經濟考略》(中國經濟史學會1998年年會論文)。)。我本人用嘉熙時該縣50都的義役田51310畝的地租數字計算,平均畝產量僅為1石(注: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農民經營方式的變化》。又,稍前端平時該縣義役田地共50522畝,歲收租米22998石,畝產也當為1石(見《重修琴川志》卷六《義役省札》。);其中產量較高者(438畝),也只是在1.36-1.5石之間(注:例如按照同樣的計算,該縣歸政鄉的義役田438畝的平均畝產量為1.36石(見《重修琴川志》卷一二所收張攀《歸政鄉義役記》),而當時官買田地800余畝,可得租米600余石,則畝產量應為0.75石(見《重修琴川志》卷六《義役省札》)。)。此外,該縣有職田32262畝,田租總數364153石。據此推算,平均畝產量更只有2.24斗(注:職田及田租數字見《重修琴川志》卷六《敘賦》。職田交租,也是對分制(見漆俠《宋代經濟史》,第301頁)。)。學田、職田、義役田在當地應屬中等田地(注:漆俠指出:"中等水平的田地在兩浙學田中占優勢"。參見漆氏《宋代經濟史》,第363頁。職田、義役田也應如是。),因此南宋該縣的一般畝產量在1石以下,應可確定。南宋人程公許說:"姑蘇產甲兩浙枝邑,常熟復甲姑蘇。"(注:程公許:《常熟重開支川記》,收于《重修琴川志》卷一二《役》。)可見常熟農業在整個蘇州乃至兩浙路都名列前茅。若常熟一般畝產量僅為1石以下,那么蘇州的一般畝產量決不可能到達2石或2石以上(注:據方健從不同中所收集的南宋平江府(蘇州)一府三縣的學田地租的數字,平江府(300余畝)畝均田租為6.7斗,昆山縣(69.5畝)為13斗,常熟縣(450畝)為8.4斗(此處常熟數字出自《吳都文粹續集》卷七袁甫《教育言氏子孫記》,系上等田地田租),嘉定縣(1362畝)為2.8斗(見方健《兩宋蘇州經濟考略》)。從方氏文中所附買田價來看,所涉及的昆山、常熟學田是上等田地,而平江府學田數字因其相對于該府學田總量來說太小,因而在統計學上的意義不大。余下的嘉定縣,如畝產量以田租之倍計,則僅為0.56石,與《常熟縣學田籍碑記》中所表現出來的常熟學田一般畝產量(0.65石)相近。又,漆俠《宋代經濟史》第362頁學田地租表中吳縣和無錫學田的畝均收租量大大高于前述常熟和嘉定的收租量,但前兩縣學田數量(259.66-384.66畝)也遠少于后兩縣(1785畝和1362畝),因此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前兩縣情況的普遍性應當較后兩縣為小。況且無錫60%的學田每畝地租在7.7斗以下(即畝產量在1.4石以下),而收租量達1石(即畝產達2石)以上的學田,其數量也只占學田總量的9.52%。吳縣是蘇州(平江府)附郭縣,也是江南畝產量最高的縣份,其情況與一般縣份應當有較大差別。不過即使在吳縣,如據學田數量較大的開禧元年情況而言,收租量在1石(即畝產2石)以上的學田也僅占學田總數的3.5%。由此而言,在蘇州全州范圍內,畝產2石以上并非常見的情況。)。事實上,淳熙10年根括到的平江府官田124203畝,歲收官租21233石(注:《宋會要》食貨六一之三七(并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六《紹興至淳熙東南鬻官產始末》),淳熙十年十月十七日浙西提舉王尚之言。);平均畝收租0.17石。據此推算,平江府官田的畝產量僅為0.34石。嘉定縣學田1362畝的畝產量也只有0.56石(注:《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二一《嘉定縣學田租田記》(轉引自方鍵《兩宋蘇州經濟考略》)。)。這里的平江府官田、嘉定縣學田、常熟學田與職田畝產量都來自較大面積的國有田地的收租數字,應當比較能夠表現當地的一般情況。這些田地上的畝產量都遠低于1石,但是從足立啟二、大澤正昭、北田英人等人所指出的宋代江南"低田地帶"由于生態環境不良而致使農田產量不穩定和使用"易田"農法的情況來看,這樣的低產量也并非不可能(注:見足立啟二、大澤正昭、北田英人等人的著作。這里我們可以舉一例以說明之。假如某地農作實行"再易"之法,實際種植的田地畝產為1石,但按田地總數平攤則為1/3石。種植和休閑每年變化不一,若都按實際種植情況征收田租,就頗為麻煩。為簡便起見,收租仍然按照田地總數而不論各塊田地當年究竟是否種植。因此之故,平均每畝收租量及平均畝產量就會顯得很低。)。據我的研究,南宋江南平均畝產量,應僅1石左右(注: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農民經營方式的變化》。)。因此,以往對宋代江南畝產量的估計,肯定是大大高于實際情況。
既然"宋代江南農業技術有重大進步和畝產量有大幅提高"之說均不符事實,那么說"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只是一個"虛像",也就不是故作驚人之語了。當然,江南農業在宋代確實出現了一些重要變化。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空間的變化,即農業生產重心從與江南平原毗鄰的寧鎮丘陵和浙西山地的"高田地帶"向江南平原的"低田地帶"的轉移。這個轉移并不意味著"低田地帶"的農業技術與畝產量在宋代發生了劇變。相反,這個地帶農業的更大發展,是在農業重心的轉移已完成之后的明清時代(注: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農業變化的特點和歷史地位》;《"革命"乎?"虛像"乎?--宋代江南農業的空間變化》,刊于《九州》第2輯。)。因此,這種空間變化才是宋代江南農業變化的"實像"。
那么,"宋代江南農業革命"這種"虛像"是如何產生的呢?當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其中最主要的,我認為是研究方法方面的問題。我把持此說的學者所使用的方法作了一個分析,發現這些方法大體可歸為兩種。在本文中,姑且將第一種方法稱為"選精法",而將第二種方法稱為"集粹法"。下面就對這兩種方法進行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