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中央與地方財(cái)政關(guān)系述略
李治安
秦漢以降,中央與地方的財(cái)賦分配關(guān)系,隨著國(guó)家集權(quán)統(tǒng)一或分裂割據(jù)的發(fā)展大勢(shì),經(jīng)歷了或聚財(cái)于中央,或藏富于地方的曲折變化過程。元王朝的政治體制是蒙古草原游牧君主制與漢地傳統(tǒng)的封建中央集權(quán)制度的融合體,又兼行省、宣慰司、路、府、州、縣等地方行政建置多達(dá)五、六級(jí),有元一代中央與地方的財(cái)政關(guān)系,呈現(xiàn)出與以往封建王朝不盡相同的新情況。關(guān)于這個(gè)問題,中外學(xué)者迄今尚無認(rèn)真的研究。筆者擬從路府州縣的賦稅征收和支用,行省在中央與地方財(cái)賦分配中的作用等方面,作如下較系統(tǒng)的探討。
(一)路府州縣的賦稅征收和支用權(quán)限
在元代路府總領(lǐng)逐級(jí)科斂的征稅體制下,稅糧、科差及部分課程等,大都以路府州縣為單位,規(guī)定數(shù)額,強(qiáng)制完成。元廷不僅規(guī)定路府州縣“非奉朝省明文,不得騷擾科斂百姓,” 各地因水旱等自然災(zāi)害蠲免錢糧,通常也是以皇帝詔書等形式頒布的。 田賦增加等,多取決于朝廷的政令。 在行省所轄區(qū)域內(nèi),行省也有權(quán)調(diào)整路府州縣的賦稅數(shù)額。行省對(duì)所屬路府州縣的賦稅額,或許多半限于高低上下,此增彼減的調(diào)整權(quán)。 若是蠲免稅額,估計(jì)行省應(yīng)咨請(qǐng)中書省批準(zhǔn),才能合理合法地付諸實(shí)施。至于路總管府一級(jí)的官府,是沒有權(quán)力減免所轄民戶稅額的。越權(quán)行事,朝廷就會(huì)“罪其專檀”。
所謂逐級(jí)科斂,就是在路總管府總領(lǐng)的前提下,實(shí)行中統(tǒng)初規(guī)定的“府科于州,州科于縣,縣科于民。” 各級(jí)地方官府均由“管民正官董其事”。 自中統(tǒng)初,路府州等向下屬官署及民戶“催督差發(fā)”,還要同時(shí)頒發(fā)信牌、文字作為憑據(jù)。官府事先準(zhǔn)備帶有編號(hào)的信牌,遇有“科催差發(fā)’時(shí),“隨即附簿粘連文字,上明標(biāo)日時(shí),定立信牌回日”。下屬官署接到信牌及文字后,按照規(guī)定的期限,“本人賚擎前來赴總管府當(dāng)廳繳納。” 路府州縣管民官通常以科斂賦稅為政務(wù)之首。“民戶安,差發(fā)辦,乃為稱職。”科稅“漏落”不實(shí),要治罪。尤其是“刷出漏籍等戶”,“并不申報(bào)上司,私下取斂差發(fā)”的官吏,更要受到監(jiān)察官的糾劾處罰。 征稅之前,有些地方還“先取管民官甘結(jié)文字”。屆時(shí)不能兌現(xiàn),依甘結(jié)文字問罪受罰。 因“國(guó)家兩稅銖龠不可減,”“每歲將終”,有些路總管府“往往械系縣長(zhǎng)貳,俾之督稅不少貸。民窮無可償,官至質(zhì)朝所授書糴粟補(bǔ)完弗憚也。” 下級(jí)地方官身受械系,甚至典當(dāng)官誥補(bǔ)完稅額,足見其上逼下困,左右為難之窘態(tài)。縣和錄事司向民戶征稅,一般要頒發(fā)“花名印押由帖,仍于村坊各置粉壁,使民通知。”“差科皆用印押公文,其口傳言語科斂者,不得應(yīng)付”。 縣衙科斂文字“下鄉(xiāng)如火速”,百姓虧糧欠稅,要挨“官棒”。有時(shí)不得不鬻賣子女,以償官稅。
需要指出的是,路府總領(lǐng),逐級(jí)科斂的方式,主要適用于稅糧、科差及課程中的酒醋課、商稅等。課程中的鹽課、茶課兩項(xiàng)大宗榷賣,除世祖至元二年后的短暫時(shí)間外,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朝廷是委付直屬于中書省或行中書省的大都河間、山東東路、河?xùn)|陜西、江淮、兩浙、福建等都轉(zhuǎn)運(yùn)鹽使司等,代表中央直接負(fù)責(zé)征收或榷賣。據(jù)說,各都轉(zhuǎn)運(yùn)鹽使司在所掌鹽課及茶課的區(qū)域內(nèi),“總管府、州若縣承命不敢少后。” 相當(dāng)多的“州縣奉鹽司甚謹(jǐn),頤指氣使,輒奔走之。” 有些實(shí)行鹽引制的地區(qū),歲終都轉(zhuǎn)運(yùn)鹽使司將賣不出的食鹽強(qiáng)行攤派給附近城鄉(xiāng),“督責(zé)州縣,臨逼百姓,追征食鹽課鈔。” 有的都轉(zhuǎn)運(yùn)鹽使司下屬的提舉司“所司辦鹽裁三分之一,其二分則驅(qū)迫州縣。” 在實(shí)行“計(jì)口受鹽”的地區(qū),鹽課“皆勒有司征辦,無分高下,一概給散。”各路州的鹽課引額是由都轉(zhuǎn)運(yùn)鹽使司決定的,路及直隸州幾乎完全仰其成命辦理。 辦完后,又如數(shù)上繳,不得虧欠。由于都轉(zhuǎn)運(yùn)鹽使司等所辦鹽課、茶課是國(guó)家財(cái)政收入的大宗,直接歸中央及行省掌握,由于元代財(cái)政高度中央集權(quán),路府州縣完全服從于中央而幾無獨(dú)立性,在鹽課等辦集過程中,路府州縣唯都轉(zhuǎn)運(yùn)鹽使司等馬首是瞻,就不足為奇了。
唐宋時(shí)期,地方官府的財(cái)賦支用權(quán)限,大體采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模式。中唐以后,實(shí)行兩稅“上供、送使、留州”的三分制,不僅規(guī)定了中央與地方在財(cái)賦占有方面的得益定額劃分,而且,“兩稅之法,悉委郡國(guó)。” 地方官府享有較大的制稅權(quán)或配稅權(quán),還可以較機(jī)動(dòng)地支配“送使、留州”的數(shù)額,“任于額內(nèi)方園給用。” 兩宋完全改變中唐以后的體制,對(duì)地方官府采取“制其錢谷”的政策,各州賦稅收入除日常給用外,凡錢帛之類一概“輦送京師”, 致使朝廷“財(cái)力雄富”,“外州無留財(cái)”,“外權(quán)始削,而利歸公上”。各地財(cái)賦支用,完全聽命于朝廷三司使等。
元朝在路府州縣財(cái)賦支用權(quán)限方面,沿用了與趙宋王朝類似的政策,一直對(duì)路府州縣經(jīng)費(fèi)支出和公帑錢谷出納等進(jìn)行嚴(yán)格的管制。通常,路府州縣官署日常辦公經(jīng)費(fèi),數(shù)額固定,多來自本地賦稅中的一小部分留成。因諸王部民留駐等,個(gè)別路及直隸州賦稅收入有限而開銷較大,其經(jīng)費(fèi)或由朝廷給賜頒發(fā)。 其它多數(shù)路府州縣不能享受此類待遇,日常辦公經(jīng)費(fèi)嚴(yán)重不足。如世祖至元年間,臨潼縣衙“經(jīng)用官給緡錢三可支一。” 在負(fù)責(zé)征集稅糧、科差及一部分課程過程中,路府州縣管民官是可以暫時(shí)掌握相當(dāng)可觀的一部分財(cái)賦的。路總管府所屬,也有倉庫官的設(shè)置。 估計(jì)路府州縣所征財(cái)賦多半是先匯集、儲(chǔ)存于路及直隸州所轄倉繳,然后再解運(yùn)行省或朝廷。但是,正如虞集《平江路重建虹橋記》所言:“今日之制,自一錢以上,郡縣毋得擅用府庫。” 路府州縣官吏對(duì)所經(jīng)辦的財(cái)賦,對(duì)暫時(shí)存放在路府倉額中的錢谷,是沒有獨(dú)立支用權(quán)的。“經(jīng)費(fèi)不貲,帑藏有數(shù)”, 地方官不敢擅自動(dòng)用屬于國(guó)家的府庫帑藏,為滿足本衙門費(fèi)用之需,只得暗中向百姓征斂。世祖至元中期,成都路非法科斂收貯的“羨余米”就多達(dá)五千石。 臨撞縣國(guó)家規(guī)定的經(jīng)費(fèi)僅足三分之一,“余悉賦之民”。為防備上司和監(jiān)察官的糾劾,官府私自征斂,往往不頒發(fā)符信公文。這樣一來,胥吏“旁緣為奸,脅持巧取”,又給境內(nèi)庶民百姓造成很大的騷擾。
路府州縣經(jīng)費(fèi)缺乏,財(cái)賦支用權(quán)甚小,使各地水利交通及官衙公廨等興修的費(fèi)用籌措,成為十分棘手的事情。元制,“役不可擅舉”,若有工役造作,必須事先稟報(bào)請(qǐng)示行省,乃至朝廷,獲得批準(zhǔn),并撥給經(jīng)費(fèi)。 行省在路府州縣官吏動(dòng)用公帑時(shí)的批準(zhǔn)權(quán),甚為重要。路府州縣官吏必須遵照其命令行事。 某些情況下,行省只批準(zhǔn)造作項(xiàng)目,“官不給錢”,不撥付經(jīng)費(fèi)錢款。地方官府“視公帑一錢莫敢動(dòng)。” 即使是奉上司撤文興辦工役造作之際,因申請(qǐng)官費(fèi)“煩文書,遲歲月”,一些路州官不得不自籌款項(xiàng),命富民出錢粟,貧民出力役。 有的則依賴官營(yíng)高利貸“規(guī)運(yùn)子錢”解決。 類似這樣的工役造作雖然“官無毫米之費(fèi)”, 但對(duì)州縣民力耗用頗多,籌措舉辦并非易事。姚隧曾說,在工役造作方面,廟學(xué)容易,官府艱難。廟學(xué)興修,有朝廷詔令嚴(yán)飭,有學(xué)田貢莊資助,還可以“責(zé)使”儒戶出錢“佐力”。官府則不然。“府無公須,山虞澤衡,皆有例禁,財(cái)無所于取也,民不敢擅征而役也。” 姚氏的說法,大體反映了當(dāng)時(shí)路府州縣財(cái)賦支用權(quán)微小,受制于人,囊中羞澀的狀況。另外,官府經(jīng)費(fèi)匿乏和官吏不得擅自動(dòng)用錢糧,也給各地的災(zāi)荒賑濟(jì)帶來了麻煩。災(zāi)民“嗷嗷仰給”,官府卻“卒無以應(yīng)之”,“遂至鬻子賣妻,輕則為道路之流民,重則為原野之餓莩”。
元朝廷對(duì)路府州縣財(cái)賦收支的管制,還表現(xiàn)在嚴(yán)格實(shí)行歲終上計(jì)和鉤考理算。
上計(jì),戰(zhàn)國(guó)官僚制建立之初就已有之。元代財(cái)賦高度集中于中央,路府州縣支配權(quán)甚小。歲終上計(jì),遂被賦予一些新的內(nèi)容和含義。路府州縣的上計(jì),分為中書省直轄區(qū)腹里和各行省兩種情況:世祖中統(tǒng)元年(1260年)十二月初一,中書省曾“集諸路計(jì)吏類校一歲簿賬”,當(dāng)是較早的腹里路總管府首領(lǐng)官等赴中書省的財(cái)賦上計(jì)。 而后,各路及直隸州“計(jì)吏歲一詣省會(huì)之”,成為定制。行省所屬路及直隸州的上計(jì),與腹里內(nèi)容大致相同,只是按規(guī)定增加了“各處正官”每季度“照勘”和赴行省上計(jì)時(shí)行省官吏“稽考”虛實(shí)等細(xì)節(jié)。由于行省接受所屬路及直隸州的上計(jì),大體是代中書省行事,所以,上計(jì)稽考完畢,行省又需要“總其概,咨都省、臺(tái)憲官閱實(shí)之”。 歲終上計(jì)之外,路及直隸州官吏有責(zé)任隨時(shí)將本衙門的財(cái)賦收入情況申報(bào)行省。發(fā)現(xiàn)累年“未申除錢糧,虛作實(shí)在,為數(shù)巨萬”,也申報(bào)行省“銷破”。 上計(jì)和稽考財(cái)賦時(shí),行省官員有權(quán)適當(dāng)懲罰路州官吏。
理算和鉤考,形異而義近,都是清查檢核財(cái)賦的意思。蒙元較早的清查檢核財(cái)賦,當(dāng)是憲宗七年(1257年)的阿蘭答兒鉤考。元朝建立以后,經(jīng)常不定期地派遣官員分赴各地,對(duì)路府州縣掌管的財(cái)賦進(jìn)行理算鉤考。世祖中統(tǒng)初,中書省欲“置局磨勘”“東平路民賦帳冊(cè)”,“會(huì)計(jì)前任官侵用財(cái)賦”。后因中書省吏員王惲等“力言其不可”,才寢而不行。 至元年間,鉤考理算日漸增加。“真定、保定兩路錢谷逋負(fù),屢歲不決”,翰林直學(xué)士唐仁祖曾受派遣“往閱其牘”。檢覆結(jié)果,“皆中統(tǒng)舊案,亟還奏罷之”。 在各路總管府與轉(zhuǎn)運(yùn)司并立之際,各路轉(zhuǎn)運(yùn)司,也是朝廷理算、鉤考的對(duì)象。“至元八年,罷諸路轉(zhuǎn)運(yùn)司,立局考核逋欠。”戶部令史劉正“掌其事”。發(fā)現(xiàn)“大都運(yùn)司負(fù)課銀五百四十七錠”。按照逋欠必須追征包償?shù)你^考舊例,立即“逮系倪運(yùn)使等人征之”。后來,劉正“視本路歲入簿籍,實(shí)無所負(fù),辭久不決。”又“遍閱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關(guān)領(lǐng)課銀文契七紙,適合其數(shù),驗(yàn)其字畫,皆司庫辛德柔所書”。最終拘捕辛德柔歸案,“悉得課銀”,洗清了倪運(yùn)使等四人的冤枉。 不難看出,鉤考中既要追究主管官吏逋欠等責(zé)任,又需稽察貪贓奸偽等弊病。而派遣和設(shè)置專門官吏(“立局”),檢覆簿籍帳冊(cè),追征逋欠,必要時(shí)逮系當(dāng)事官吏,強(qiáng)制其執(zhí)行賠償?shù)龋耸抢硭沣^考的基本程序和內(nèi)容。
元代路府州縣官府經(jīng)費(fèi)由朝廷規(guī)定,數(shù)額甚少,公帑錢谷不得擅自動(dòng)用,財(cái)賦出納不得留有羨余, 還實(shí)行嚴(yán)格的歲終上計(jì)和不定期的鉤考理算等,所有這些均將路府州縣的財(cái)賦支用置于朝廷的嚴(yán)格管制之下。路府州縣官府在財(cái)賦占有和使用方面的權(quán)力,與它們承擔(dān)的征收賦稅的繁重義務(wù)相比,實(shí)在是少得可憐。似乎可以說,元代路府州縣的財(cái)政職能已很不完整,它們的財(cái)賦占有和使用數(shù)量很少,而且使用之際又常常秉命于朝廷或行省,無甚自主性。在這方面,元代沿著兩宋“外權(quán)始削,而利歸公上” 的路子,走得相當(dāng)遠(yuǎn)了。
(二)行省對(duì)轄區(qū)財(cái)賦收支的綜領(lǐng)督辦
大約在世祖末成宗初,各行省督辦的錢糧賦稅已有了數(shù)額方面的規(guī)定。行省官督辦錢糧數(shù)額,即所謂“合辦額”,是以年分 為單位計(jì)算的。“合辦額”直接向朝廷負(fù)責(zé),或增余,或足額,或虧欠,由朝廷逐年檢核 。有些場(chǎng)合還履行“自執(zhí)政以下,皆取認(rèn)狀”之類的“署字”承應(yīng)程序 。各行省所督辦的錢糧數(shù)額并不相等,而是高下懸殊,差距很大。以稅糧為例,江浙行省最多,達(dá)4494783石。甘肅、遼陽二行省最少,僅六、七萬石 ,相差六十余倍。就其在全國(guó)稅糧總數(shù)中的比例而言,江浙一省可占到37%左右。按照各行省承擔(dān)的賦稅定額,朝廷予以嚴(yán)格檢查和督責(zé),并實(shí)行獎(jiǎng)勵(lì)增羨和處分虧空等政策。《元史》卷18《成宗本紀(jì)一》元貞元年閏四月庚申條運(yùn):“河南行省虧兩淮歲辦鹽十萬引,鈔五千錠,遣札剌而帶往鞫實(shí),命隨其罪之輕重治之。陜西行省增羨鹽鈔一萬三千五百余錠,山東都轉(zhuǎn)運(yùn)使司別思葛等增羨鹽鈔四千余錠,各賜衣以旌其能。”河南行省下屬兩淮都轉(zhuǎn)運(yùn)鹽使司所掌鹽課居天下之首,世祖末歲額達(dá)到六十五萬引左右。額重難完,成宗初竟虧欠六分之一以上,折合中統(tǒng)鈔五千錠。朝廷遣官鞫問,處罰十分嚴(yán)厲。對(duì)監(jiān)守自盜者,要罰以苦役或罷官。辦事遲緩的,也要取招問罪。另一方面,對(duì)陜西行省等辦課增羨的,則要給行省官“做記驗(yàn)”,并賜以錦衣。運(yùn)司有功官吏還要添與散官,晉升官階 。行省在督辦賦稅過程中,有時(shí)掌握的“歲課羨余鈔”多達(dá)四十七萬緡。甚至可以不上繳朝廷,卻貢獻(xiàn)給食邑在本省境內(nèi)的皇太子帶等,以取悅于權(quán)貴 。
行省有權(quán)參與議定路府州縣所掌的賦稅數(shù)額、征收方式等事宜。如至元二十八年江南各行省“任錢谷者”及“行省轉(zhuǎn)運(yùn)司官”曾應(yīng)召赴朝廷“集議治賦法”等 。湖廣行省建立之初,行省長(zhǎng)官阿里海牙規(guī)定:“稅法畝取三升,盡除宋他名征。后征海南,度不足用,始權(quán)宜抽戶調(diào)三之一佐軍。”據(jù)說,湖廣行省賦稅較江浙為輕,就是阿里海牙當(dāng)初確定稅率的結(jié)果 。后來,湖南宣慰司張國(guó)紀(jì)建言,欲按唐宋舊例征民間夏稅,湖廣行省平章哈剌哈孫又“奏止其議”。另,西南建都一帶的賦稅,也是至元二十三年六月由“云南、陜西二行省籍定”的。
“國(guó)計(jì)莫重于鹽筴“ 。在行省對(duì)諸色課程綜領(lǐng)的過程中,多以鹽課為重點(diǎn)。行省對(duì)轄區(qū)鹽課的管理,具體表現(xiàn)在:某種程度地節(jié)制都轉(zhuǎn)鹽使司,整頓鹽法,掌管榷賣數(shù)額等三方面。元世祖以降,腹里地區(qū)的都轉(zhuǎn)運(yùn)鹽使司直屬中書省,行省轄區(qū)的都轉(zhuǎn)運(yùn)鹽使司等則分別隸屬于行省。行省對(duì)轄區(qū)都轉(zhuǎn)運(yùn)鹽使司某種程度的節(jié)制,包括了綜領(lǐng)鹽務(wù)過程中的一些統(tǒng)屬關(guān)系:第一,較重要的事情,都轉(zhuǎn)運(yùn)鹽使司需要隨時(shí)稟報(bào)行省,“照勘議擬”。獲得批準(zhǔn)后,才付諸實(shí)施 。第二,都轉(zhuǎn)運(yùn)鹽使司上奏朝廷,一般需要先申行省,由行省“明白定擬”,然后咨呈中書省參詳。中書省作出指示后,也須回咨本省,再轉(zhuǎn)發(fā)都轉(zhuǎn)運(yùn)鹽使司等執(zhí)行 。第三,在實(shí)施中書省鹽務(wù)方面的命令時(shí),朝廷多半要責(zé)成行省派官吏赴現(xiàn)場(chǎng)坐鎮(zhèn)督察,如順帝至元六年(1340年),中書省批準(zhǔn)撥鈔一萬錠,供兩淮運(yùn)司“起蓋倉房”,即由都省“移咨河南行省”,命其“委官與運(yùn)司偕往,相視空地,果無違礙,而后行之 。第四,行省可“承制”遷除鹽場(chǎng)等下級(jí)官吏,事后再申朝廷批準(zhǔn) 。
行省可以介入整頓轄區(qū)鹽法等事宜。這類整頓或與朝廷所遣官一同進(jìn)行 ,或由行省根據(jù)轄區(qū)情況,上奏論列利弊,提出建議,如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月,江西行省左丞高興奏言:當(dāng)時(shí)隸屬于江西行省的“福建鹽課,既設(shè)運(yùn)司,又設(shè)四鹽使司,今若設(shè)提舉司專領(lǐng)鹽課,其酒說悉歸有司為便”。世祖聽從其建議,精簡(jiǎn)了福建榷鹽官署及職事 。他如至元三十年(1293年)河南行省平章伯顏?zhàn)嘌韵鳒p兩淮都轉(zhuǎn)運(yùn)鹽使司下屬鹽司建置,改襄陽民戶買食兩淮鹽 ,英宗朝,“湖廣鹽法廢壞已久”行省參政海南攜聶以道“榷牢盆,盡除老奸宿蠹,
拔塞本源,無遺余者等 ,均屬行省轄區(qū)鹽法的事例。
行省官還直接負(fù)責(zé)匯總審核都轉(zhuǎn)運(yùn)鹽使司的歲辦鹽額。多數(shù)時(shí)間內(nèi),兩淮、兩浙鹽課“直隸行省,宣慰司官勿預(yù)” 。行省既管轉(zhuǎn)運(yùn)司的鹽引出售數(shù)額,又監(jiān)督所轄諸鹽場(chǎng)的煎鹽引額。如世祖末,博羅歡任河南行省平章,足額辦集兩淮鹽課 ;河南行省僉事昔里哈剌“治鹽法于淮東,厘革宿弊,增課二十余萬” ;武宗朝,河南行省參政某赴兩淮都轉(zhuǎn)運(yùn)鹽使司會(huì)計(jì)鹽課收入,且欲以增羨二十五萬引作為日后的“歲入常額”,后因都轉(zhuǎn)運(yùn)使敬儼的極力反對(duì),才未能遂愿 ;仁宗朝陜西行省參政史壎以“陜西歲辦鹽課良苦,奏減五萬緡” ;泰定進(jìn)士楊維禎擔(dān)任錢清鹽場(chǎng)司令,灶戶因賦重困苦不堪,楊“屢白其江浙行中書,弗聽”。“乃頓首涕泣于庭,復(fù)不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 ;以上阻止增羨入常額和力請(qǐng)減鹽引數(shù)事,有些雖然是應(yīng)都轉(zhuǎn)運(yùn)使和鹽場(chǎng)官請(qǐng)求辦理,但行省官對(duì)都轉(zhuǎn)運(yùn)鹽使司的歲額增羨,乃至鹽場(chǎng)煎鹽數(shù)所擁有的某種決定權(quán),又是顯而易見的。行省得以內(nèi)掌握和過問都轉(zhuǎn)運(yùn)鹽使司每年輸往京師的鹽課收入數(shù)額。當(dāng)朝廷在年輸京師定額之外臨時(shí)調(diào)撥行省所屬鹽運(yùn)司十萬鈔左右的鹽課,用作他省賑濟(jì)等事時(shí),行省左丞等官可以用‘周歲所入,已輸京師“等理由,回答中書省,也可以折合來年輸京師鹽課數(shù),遵都省命令,“如數(shù)與之” 。這類事告訴人們,行省在輸入京師之外,尚留部分鹽課余額。對(duì)后者,行省官員的確具有某種程度的支配權(quán)。
元代地方酒課,通常由路府州縣具體掌管。但行省官對(duì)轄區(qū)的酒課征收方式,有權(quán)過問和更動(dòng) 。還常常派官會(huì)計(jì)審核路州的酒課數(shù)額 。
金銀等課,是行省負(fù)責(zé)的另一項(xiàng)重要的課程。行省對(duì)境內(nèi)各銀場(chǎng)提舉司等進(jìn)行檢復(fù)監(jiān)督,還派官“體勘”銀場(chǎng)經(jīng)營(yíng)和收支盈虧 。有關(guān)銀場(chǎng)役使民夫煉銀免其稅糧數(shù)額等事宜,行省可通過奏報(bào)朝廷,予以放寬優(yōu)待 。行省提調(diào)銀課的官員,每歲均有固定的數(shù)額,必須完成。一些行省官欲減少課額,或須上奏皇帝,獲得恩準(zhǔn),才可“從實(shí)辦之” 。偶爾也有個(gè)別行省官妄言增辦銀課,以邀恩寵。課不及額之際,則“賦民鈔市銀輸官” 。江西行省所屬的蒙山銀課最為有名。據(jù)說,蒙山銀課“歲辦銀五百定之額,始于至元二十一年。后漸次升至七百定”。管理方式也比較特殊:“惟行省相臣一人,瑞州守一人兼領(lǐng)其事,雖憲府不與也 。泰定朝,江西行省平章?lián)Q住“始減蒙山銀課三百定”,“*富民蒙山提舉之爵,征贓五十余萬緡” 。
行省官還介入商稅征收。如遼陽行省左丞亦輦真“薄關(guān)市之征,以通商旅” ;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高克恭去“稅司或植椼楊于門,以伺匿稅者”之弊 ;英宗朝杭州“商稅比歲不登”江浙行省掾史孔濤奉命“趨辦,旬日而集,時(shí)宰以為能” 。商稅也是課程的組成部分。行省官督促或改進(jìn)其征集方法,表明他們對(duì)包括商稅在內(nèi)的課程征集的高度重視。元代多數(shù)時(shí)間內(nèi),海外貿(mào)易由江南若干行省兼領(lǐng)。如世祖朝江淮行省左丞沙不丁、參政烏馬兒奉旨“領(lǐng)泉府、市舶兩司”,掌管泉州等處的海外貿(mào)易;江西行省參政(遙授)胡頤孫“行泉府司事”,掌管廣州等處的海外貿(mào)易 。行省提調(diào)官多半推行“官本船”制,“發(fā)舟十綱,給牒以往,歸則征稅如制”;抽分之際,常親臨監(jiān)督,或“閱商舶南海上” 。
行省掌管轄區(qū)財(cái)政支出,首先表現(xiàn)于對(duì)路府州縣財(cái)政支出的監(jiān)督。元制,
路府州縣如有工役造作,必須先稟報(bào)請(qǐng)示行省,乃至朝廷,獲得批準(zhǔn),并撥給經(jīng)費(fèi)。如順帝初婺州路興建通濟(jì)橋時(shí),就是由新任中書省參政徐某“白于宰相執(zhí)政”,“符下”,“江浙行省既給以前所沒入之錢二萬余緡” 。行省對(duì)路府州縣動(dòng)用公帑的品種權(quán),甚為重要。路府州縣官吏必須遵照其命令行事 。某些情況下,行省只批準(zhǔn)造作項(xiàng)目,“官不給錢”,不撥付經(jīng)費(fèi)錢款 。行省所屬路及散府、州的上計(jì),與腹里內(nèi)容大體相同,只是按規(guī)定增加了“各處正官”每季度“照勘”和赴行省上計(jì),大體是代中書省行事,所以,上計(jì)稽考完畢,行省又需要“總其,咨都省、臺(tái)憲官閱實(shí)之” 。歲終上計(jì)之外,路及直隸州官吏有責(zé)任隨時(shí)將本衙門的材賦收入申報(bào)行省。發(fā)現(xiàn)累年“未申除錢糧,虛作實(shí)在,為數(shù)巨萬”,也申報(bào)行省“銷破” 。上計(jì)和稽考財(cái)賦時(shí),行省官員有權(quán)適當(dāng)懲罰路州官吏 。
關(guān)于行省的財(cái)賦支用權(quán)限,程鉅夫《論行省》云:“今天下疏遠(yuǎn)去處,亦列置行省……今江南平定以十五余年,尚自因循不改……凡去行省者,皆以宰相自負(fù)……錢糧羨溢,則百端侵隱,如同己物。” 從程氏所言看,行省官員的財(cái)賦支用是相當(dāng)大的。程氏《論行省》一文寫于江南平定十五年以后,即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左右。至元十七年(1280年)江淮行省阿里伯等“擅支糧四十七萬石,”朝廷“屢移文取索”稅糧,竟“不以實(shí)上”;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湖廣行省左丞相阿里海牙因鉤考錢糧被逼身亡 ……都印證了程氏之說是真實(shí)可信的。不過,它反映的大體只是至元二十八年以前的情況。其后,就大不相同了。瞻思《有元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榮祿公神道碑》云:“舊諸行省之用及千定,必咨都省” 。瞻思所述,系大德三年左右事。表明迄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行省只具有機(jī)動(dòng)支用中統(tǒng)鈔一千錠以下的權(quán)力,超過一千錠,就必須咨請(qǐng)中書省批準(zhǔn)。事實(shí)也大體如此。一些數(shù)額較小的經(jīng)費(fèi)開支,如修建路醫(yī)學(xué)教授廳等,行省可以直接批準(zhǔn)支用“官帑” 。但對(duì)一些數(shù)額較大的開支,元中后期的行省往往需要稟報(bào)朝廷了。例如仁宗朝陜西“大饑”,行省參政史尋壎在奏報(bào)未獲準(zhǔn)的情況下,“發(fā)另廩以賑民”,事先曾作過“設(shè)不從,以私家之產(chǎn)償之耳”的承諾 ;文宗至順元年()江浙行省重修拱北樓,“縻鈔以錠計(jì),一千七百九十有七,米以石計(jì)二百九十”,即由“省具聞中書……不逾時(shí),報(bào)可” 。違反此類規(guī)則,擅自動(dòng)用官府材賦,會(huì)受到責(zé)罰。仁宗時(shí)嶺北行省官員忻都擅自支用“官錢犒軍”,即被“免官”。后來,鑒于他用于‘犒賞“軍隊(duì),而非據(jù)為己有,英宗即位才特意降詔恢復(fù)其官職 。
耐人尋味的是,若若干年后由于嚴(yán)格實(shí)施上述稟報(bào)制度,各行省處理政務(wù)
多一味稟命于朝廷,顯得消極而不敢負(fù)責(zé)了。針對(duì)這種狀況,大德九年()中書省又下達(dá)公文,譴責(zé)各行省應(yīng)決不決,“泛濫咨稟”的做法。然而,對(duì)“重事并創(chuàng)支錢糧”,仍重申“必合咨稟”的舊制 。換句話說,朝廷雖強(qiáng)調(diào)各行省積極承擔(dān)責(zé)任,替行省分辦庶務(wù),但仍不允許行省官不經(jīng)請(qǐng)示而動(dòng)用較多數(shù)量的錢谷。即便是各行省歷年按國(guó)家制度“應(yīng)付各投下歲賜緞匹、軍器物料等”,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內(nèi)也是“每歲咨稟都省,送部照擬回咨”方能發(fā)放。直至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五月,才改為各行省“照勘年額相同,別無增減,就便依例應(yīng)付,年終通行照算” 。
(三)藏富諸省與上供留用
黃溍說:“昔之有國(guó)家者,藏富之所,散于列州。而今也,藏富之所,聚于諸省” 。魏晉隋唐兩宋,州是地方高級(jí)行政官署,又是相對(duì)獨(dú)立的地方財(cái)政單位。地方財(cái)賦首先聚集于各州,而后再做上供朝廷和地方留用之類的分配。唐后期實(shí)行的兩稅“上供、送使、留州”的三分法,也是以州之財(cái)賦單位所征集的財(cái)稅為基數(shù)進(jìn)行分割的 。元代則不然。州之上,又有路及宣慰司,還有轄區(qū)廣、品級(jí)高、權(quán)利大的行中書省。路總管府及直隸州(府)“言可以專達(dá),事可以專決” ,并能在征收賦稅方面發(fā)揮重要作用。但除腹里中書省直轄區(qū)外,路及直隸州(府)又是直接聽命于行省的。尤其是在財(cái)賦方面,路及直隸州(府)需要把所征集的財(cái)賦先送往行省,并由行省儲(chǔ)藏或轉(zhuǎn)運(yùn)上供朝廷。在此過程中,行省代表朝廷集中各路州的財(cái)賦于行省治所,是元代中央與地方財(cái)賦分配的關(guān)鍵。特別是元前期行省多以中書省派出機(jī)構(gòu)出現(xiàn)的情況下,財(cái)賦聚集于行省,也就等于朝廷的囊中物了。在這個(gè)意義上,“藏富之所,聚于諸省”,已是基本將各地財(cái)賦集中于朝廷了。各行省直屬的倉庫,“所統(tǒng)郡邑歲入上供及經(jīng)費(fèi)之出納,無所不掌”。特別是江浙等江南三省,“歲所入泉幣-金玉、織文、它良貨賄待用之物,以鉅萬計(jì)。所儲(chǔ)為甚厚,所系為甚大” 。由于多數(shù)財(cái)賦集中各行省,所轄區(qū)域內(nèi)各路州倉廒多半空虛,“有名無實(shí)”,有些州甚至“糧不宿倉”。得以保留下來的一些路州倉庫,也受到行省所派官吏的清查檢核 。需要指出的是,藏富之所,聚于諸省“,行省替朝廷征集賦稅,早在元行省雛形的燕京等處三斷事官時(shí)期業(yè)已開始。拉施德《史集》說:“合汗()把全部漢地授予了撒希卜馬合木?牙剌瓦赤管理;把從畏兀兒斯坦領(lǐng)地別失八里和哈剌火者,[從]忽炭、合失合兒、阿力麻里、海押立、撒麻耳干和不花剌[一直]到質(zhì)渾河岸[的地區(qū)],授予牙剌瓦赤的兒子馬思忽惕?伯;而從呼羅珊到魯木和迪牙別克兒的[地區(qū)],則授予了異密闊兒吉思。凡從所有這些地區(qū)征收的全部賦稅,他們每年都送到國(guó)庫來” 。
換言之,燕京等處斷事官不僅在組織結(jié)構(gòu)、與朝廷的關(guān)系等方面,為元行省制提供了基本模式,而且率先充當(dāng)了替朝廷征集、轉(zhuǎn)運(yùn)賦稅的重要工具。后者對(duì)元行省在中央與地方財(cái)賦分
配的角色,頗有影響。
隨著行省在成宗初由朝廷中書省派出機(jī)構(gòu)轉(zhuǎn)化為地方最高軍政機(jī)關(guān),各地財(cái)賦集中于行省后,自然出現(xiàn)了解運(yùn)京師、上供朝廷和各省留用的問題。《元史》卷二二《武宗紀(jì)一》大德十一年九月己丑條云:“晉王也孫鐵木兒以詔賜鈔萬錠,止給八千為言,中書省臣言:‘帑藏空竭,常賦歲鈔四百萬錠,各省備用之外,入京師者二百八十萬錠……臣等慮財(cái)用不給,敢以上聞。’帝曰:‘……可給晉王鈔千錠,余移陜西省給之’”。這段奏言及武宗諭旨,是迄今所見反映行省征集財(cái)賦上供與留用關(guān)系的重要資料。其中“常賦歲鈔四百萬錠”,與成宗初中書省右丞相完澤所言“歲入之?dāng)?shù),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 比較,似不包括金、銀及稅糧石數(shù)收入。而中統(tǒng)鈔四十萬錠的差額 ,估計(jì)是成宗一朝所增加的。即便四百萬錠只限于武宗初全國(guó)歲鈔收入,它與“各省備用之外,入京師者二百八十萬錠”句,前后相綴,也能說明如下幾點(diǎn):
第一, 全國(guó)歲鈔收入四百萬錠中,二百八十萬錠統(tǒng)統(tǒng)解運(yùn)、上供京師。上供京師的歲
鈔數(shù)占全國(guó)歲鈔收入的70%。各省留用僅占30%。
第二, 上供京師二百八十萬錠以外,明確講是由“各省備用”,而未提路府州縣。或者
可以說,由于“藏富之所,聚于諸省‘和行省演化為地方最高行政建置,元中后期中央與地方的財(cái)賦分配已是在朝廷與行省之間進(jìn)行(腹里地區(qū)除外)。地方留用財(cái)賦的支配權(quán),主要由行省掌握。
第三, 唐后期兩稅三分制下各州上供數(shù)額只是留州、送使之后的自然余數(shù),通常明顯低于全國(guó)兩稅收入總額的一半 。元代由歲鈔所反映的中央與地方財(cái)賦分割比例,竟高達(dá)七比三。顯然,元朝廷所占比重高于唐代,某種程度上又是兩宋盡收州縣財(cái)賦于中央政策的繼續(xù)。據(jù)說,明代中央與地方鹽稅等分割比例是八分起運(yùn),二分存留,而且也是在中央與各省之間分割的 。如此看來,迄武宗朝已實(shí)行的歲鈔上供與留用的比例,又開了元明兩代中央與地方省級(jí)政權(quán)財(cái)賦分割的先河。
第四, 由于行省起初是朝廷中書省的派出結(jié)構(gòu),朝廷行省之間財(cái)賦七三分成政策之下,
行省仍然主要充當(dāng)朝廷簡(jiǎn)直財(cái)權(quán)的工具。行省除了上供中央和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懸殊比例和嚴(yán)格控制路府州縣的財(cái)賦支用,還有義務(wù)遵照朝廷的命令額外提供錢谷,以彌補(bǔ)中央財(cái)政支出的不足。武宗海山命令陜西行省在上供之外,代朝廷向晉王支付一千錠賜鈔,即屬此例。
至于糧食上供,更表現(xiàn)了中央利用行省對(duì)江南稻谷主要極力產(chǎn)地的搜刮。世祖朝創(chuàng)立江南之糧海運(yùn)入京師制度以后,海運(yùn)糧食由每歲四萬余石,逐漸增至三百余萬石。這些糧食多取之于平江、嘉興、松江為中心的江浙行省。然而,元后期江浙行省稅糧年收入最高是四百四十九萬四千八百八十三石 。顯而易見,江浙行省稅糧收入的一大半,都要被解運(yùn)京師。元人陳旅說:江浙行省“土賦居天下十六、七” ,殆非虛語。這種異乎尋常的搜刮,使江浙行省可供民間食用的糧食數(shù)額大為減少。成宗大德年間,號(hào)稱天下糧倉的江浙一帶,連年發(fā)生嚴(yán)重饑荒,甚至出現(xiàn)了“野無青草樹無膚,人腹為棺葬萬夫”的悲慘景象 。這或許是元廷對(duì)江浙行省肆無忌憚的糧食搜刮所間接產(chǎn)生的惡果之一吧!
各行省的上供與留用雖然在整體上實(shí)行七三分成政策,但因政治、經(jīng)濟(jì)、軍事等因素,具體執(zhí)行上述政策時(shí),各省很不平衡,差異相當(dāng)大。元制,“一歲入糧一千三百五十萬八千八百八十四石,而江浙四分強(qiáng),河南二分強(qiáng),江西一分強(qiáng),腹里一分強(qiáng),湖廣、陜西、遼陽一分強(qiáng),通十分也” 。一般說來,在每年上供朝廷二百八十萬錠中統(tǒng)鈔等財(cái)賦總額內(nèi),經(jīng)濟(jì)富庶的江浙、江西等江南行省為最多。與其形成鮮明對(duì)照的是,嶺北、遼陽、甘肅、云南等行省,不僅稅糧、課程歲辦額較少,而且?guī)X北等行省的經(jīng)費(fèi)也主要由朝廷撥賜。這類經(jīng)費(fèi)撥賜,少者萬余錠,多者幾十萬錠,幾乎達(dá)到全國(guó)歲鈔的四分之一。此外還有鹽引、雜彩、糧食、金寶等賜與 。撥賜數(shù)額多半遠(yuǎn)遠(yuǎn)超過該省年度稅課收入。元廷之所以拿出如此大數(shù)額的錢谷撥賜上述幾個(gè)行省,是有緣由的。有元一代,嶺北是蒙古肇興之地,又系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和蒙古大千戶所在。自世祖朝,元廷方面長(zhǎng)期屯列大軍于和林、稱海等地,防御叛王騷擾。“朝廷歲出金繒布幣后餱糧以實(shí)之,轉(zhuǎn)輸之事,月日相繼,猶以為未足。又捐數(shù)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又可勝計(jì)。由是遂為殷富。”嶺北行省獲取巨額撥賜,主要是用于供給駐屯軍隊(duì),賞賜諸王及各千戶部民 。“甘肅省僻在邊陲,城中蓄金谷,以給儲(chǔ)王軍馬”,“仰哺省者十?dāng)?shù)萬人” 。云南行省和河南行省也是蒙古軍都萬戶和萬戶密集駐屯之處 。元代嶺北、甘肅、云南、等少數(shù)行省向朝廷上供很少,卻能從朝廷得到數(shù)量可觀的經(jīng)費(fèi)撥賜,完全是為著蒙古貴族入主中原后防御西北叛王和鎮(zhèn)遏被征服地區(qū)的政治和軍事需要而服務(wù)的。在某種意義上,嶺北、甘肅二行省的設(shè)置宗旨,也于其它漢地行省有所差別。供給軍需,賞賜和安撫諸王部民,始終是著兩個(gè)行省的主要使命和職司。
江南三行省擔(dān)負(fù)大部分上供財(cái)賦,與嶺北、甘肅等行省很少上供、反倒獲取朝廷的巨額經(jīng)費(fèi)撥賜,造成了元代行省上供與留用,乃至中央與地方財(cái)賦分配體制內(nèi)極不平衡的狀況。由于這種不平衡,全國(guó)范圍內(nèi)中央與行省間上供與留用的比例雖然大體是七比三,但70%的上供數(shù)額絕大多數(shù)由江南三省承擔(dān)。具體到這三個(gè)行省向朝廷上供的數(shù)額,肯定會(huì)高出70%很多。這就使元代中央與地方的財(cái)賦分割中,南方北方待遇高下懸殊,北方受優(yōu)遇,南方受榨取,最終大大加重了江南三省民眾的賦役負(fù)擔(dān)。元末“窮極江南,富夸塞北”的怨謠 ,某種意義上也是對(duì)上述財(cái)賦分配不平等的憤*和抗議。值得注意的是,元廷對(duì)江南三省的過度榨取,造成了嚴(yán)重的災(zāi)難。至大元年()江浙行省紹州、臺(tái)州、慶元等六路大饑,“死者相枕籍,父賣其子,夫鬻其妻,哭聲震野,有不忍聞” 。但當(dāng)年十一月朝廷又以“近畿艱食”為由,強(qiáng)令江浙行省“歲運(yùn)海道糧二百三十萬有奇”,較前一年的一百二十四萬石增加一百多萬石。元廷不用江浙儲(chǔ)糧就近賑濟(jì)瀕死之饑民,反而大幅度增加江浙北運(yùn)京師的漕糧數(shù),真可謂不顧江浙災(zāi)民之死活!在這個(gè)意義上,至大二年主持江浙行省春運(yùn)五十八萬石至京師的烏馬兒平章,顯然是元朝廷的大功臣。然而,對(duì)江浙一百三十三萬流離失所的災(zāi)民來說,他又是千古罪人!正如虞集所言:“海運(yùn)之實(shí)京師,國(guó)家萬世之長(zhǎng)策也。然而,東南之民力竭焉,頻歲浙西水旱,廩不充數(shù),江淮上流三省數(shù)十郡州縣之吏、斗升之民,終歲勤動(dòng),越江歷湖,以助其不足,而爭(zhēng)斗無機(jī)勿戢,又有深可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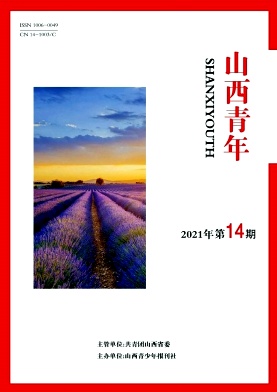
計(jì)量.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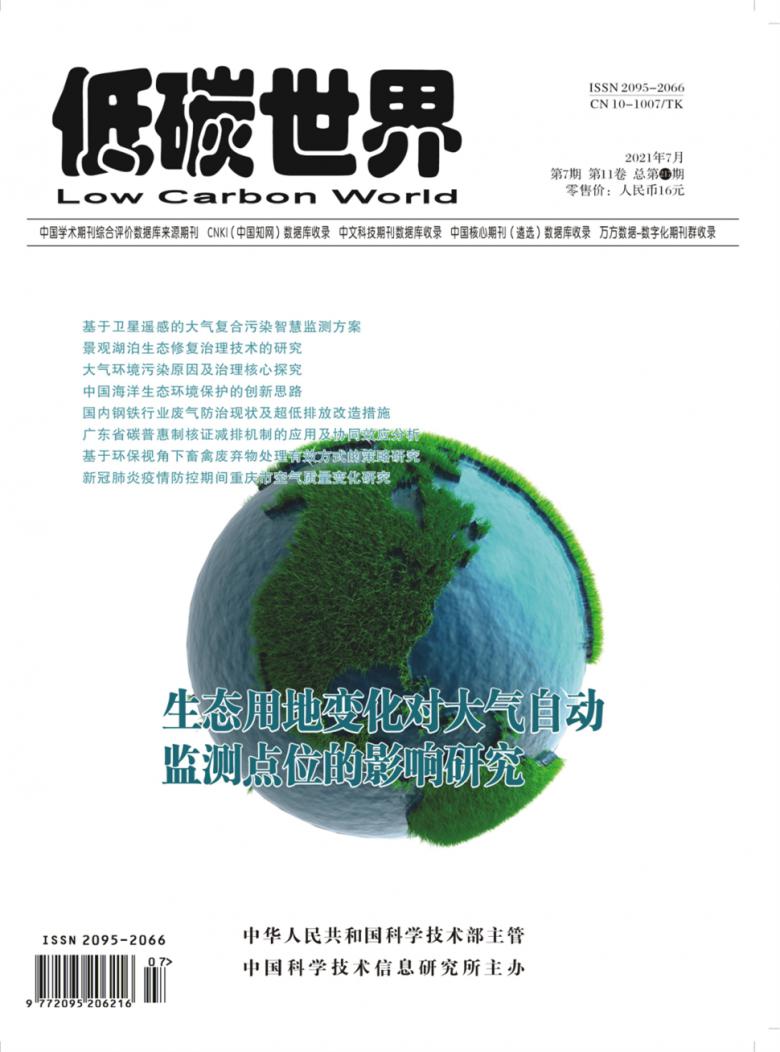
際護(hù)理學(xué).jpg)

新技術(shù)新產(chǎn)品.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