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當代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國家戰(zhàn)略
呂永剛 華桂宏
[論文關(guān)鍵詞]改革開放;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經(jīng)濟轉(zhuǎn)軌;戰(zhàn)略升級
[論文摘要]30年前開啟的改革開放是推進當代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國家戰(zhàn)略。改革開放的戰(zhàn)略起點是突破中國發(fā)展面臨的發(fā)展困境,改革開放的戰(zhàn)略目標是以實現(xiàn)國家利益為歸宿的發(fā)展目標的動態(tài)演進,戰(zhàn)略途徑是漸進式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間接路線”,戰(zhàn)略手段是多力并舉提升發(fā)展效應。改革開放戰(zhàn)略的經(jīng)驗在于:戰(zhàn)略目標的制定上,堅持階段性與長遠性相統(tǒng)一;戰(zhàn)略路徑的選擇上,堅持重點性與系統(tǒng)性相統(tǒng)一;戰(zhàn)略手段的選擇上,堅持自主性與特色性相統(tǒng)一。在新階段,中國改革開放應順應形勢發(fā)展要求實現(xiàn)戰(zhàn)略升級。
三十年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zhuǎn)到以發(fā)展生產(chǎn)力為中心,從封閉轉(zhuǎn)到開放,從固守成規(guī)轉(zhuǎn)到各方面的改革”的歷史性轉(zhuǎn)折。改革開放沖破了束縛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體制障礙,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形成了對外開放的全新格局,不僅造就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同時催生了獨具風格的“中國模式”,彰顯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生命力。改革開放為當代中國的發(fā)展進步提供了強大動力,是決定中國命運的戰(zhàn)略抉擇,質(zhì)言之,改革開放本身就是推動當代中國發(fā)展進步的國家戰(zhàn)略。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發(fā)展中大國來說,“戰(zhàn)略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戰(zhàn)略的失敗是最大的失敗。”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從國家戰(zhàn)略視角審視改革開放在推進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中的戰(zhàn)略地位,對于科學總結(jié)改革開放的歷史經(jīng)驗,在發(fā)展新階段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yè)繼續(xù)推向前進,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本文將基于戰(zhàn)略學分析進路,對改革開放的戰(zhàn)略起點、戰(zhàn)略構(gòu)成、戰(zhàn)略經(jīng)驗等問題展開分析。 一、改革開放的戰(zhàn)略起點:突破中國面臨的“發(fā)展困境” 戰(zhàn)略的精髓在于選擇,能否選擇適當?shù)膰覒?zhàn)略,對于一國發(fā)展進步至關(guān)重要。國家戰(zhàn)略得當,一國就可能掌握發(fā)展主動,順勢而起;相反,國家戰(zhàn)略失當,一國就可能出現(xiàn)發(fā)展被動,陷入困境。改革開放前夕,經(jīng)歷“文革”浩劫的中國經(jīng)濟面臨嚴峻形勢: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體制、發(fā)展戰(zhàn)略和發(fā)展模式弊端叢生,難以為繼,迫切需要進行根本性轉(zhuǎn)變,以適應國內(nèi)發(fā)展和國際競爭的要求,這構(gòu)成了改革開放的戰(zhàn)略起點。當時,中國面臨的“發(fā)展困境”集中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體制困境”:傳統(tǒng)計劃經(jīng)濟體制期待變革 新中國成立后,參照“蘇聯(lián)模式”建立了計劃經(jīng)濟(實質(zhì)是統(tǒng)制經(jīng)濟、命令經(jīng)濟)體制,這一體制具有所有制結(jié)構(gòu)單一、經(jīng)濟決策權(quán)高度集中、資源行政式計劃配置、經(jīng)濟組織結(jié)構(gòu)封閉化等特點。在建國后的一段時期內(nèi),依托國家(執(zhí)政黨)所具有的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加之蘇聯(lián)援助成為早期工業(yè)化的關(guān)鍵性外部條件,我國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工業(yè)體系和科技體系,奠定了國民經(jīng)濟的發(fā)展基礎(chǔ),顯示了計劃經(jīng)濟體制的特殊優(yōu)勢。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計劃經(jīng)濟體制的內(nèi)在弊端逐漸暴露,其體制優(yōu)勢迅速消耗,中國的國民經(jīng)濟遂陷入低度發(fā)展狀態(tài)。雖然早在效仿“蘇聯(lián)模式”構(gòu)建計劃經(jīng)濟體制之時,毛澤東就覺察到該體制存有弊端,提出要“以蘇為鑒”,并先后進行過旨在調(diào)動地方政府和企業(yè)積極性的行政性分權(quán)、旨在調(diào)動職工積極性的“鞍鋼憲法”等嘗試,但并未從根本上糾正計劃經(jīng)濟體制的弊端。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我們過去照搬蘇聯(lián)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fā)現(xiàn)了,但沒有解決好”。傳統(tǒng)計劃經(jīng)濟體制所暴露出來的體制弊端從反面構(gòu)成了“市場化改革”的體制性背景。 (二)“后發(fā)困境”:“后發(fā)劣勢”的現(xiàn)實性與“后發(fā)優(yōu)勢”的潛在性 歷史經(jīng)驗表明,發(fā)展中國家既可能利用后發(fā)優(yōu)勢而收獲“后起之益”,也可能陷入后發(fā)劣勢而遭遇“后起之弊”。經(jīng)濟史學家格申克龍認為,落后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潛在優(yōu)勢,它在一定條件下能化壓力為動力,化動力為現(xiàn)實競爭力,推動經(jīng)濟的迅速發(fā)展,并稱之為“落后者的優(yōu)勢”。對于后發(fā)國而言,后發(fā)優(yōu)勢客觀存在,但其實現(xiàn)卻需要理想的條件:后發(fā)國與先發(fā)國之間的發(fā)展差距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別,而不存在本質(zhì)上的差別;并且,兩者發(fā)展時面臨的內(nèi)部條件與外部環(huán)境應基本相同,只有這樣,后發(fā)國的模仿才可能成功,后發(fā)優(yōu)勢才能體現(xiàn)出來。新中國成立之初,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十分落后,與發(fā)達國家發(fā)展差距過大,不利于后發(fā)優(yōu)勢的發(fā)揮。例如,1973~1975年,我國大規(guī)模從美國、日本和西方引進技術(shù),由于過于強調(diào)“先進性”和“規(guī)模大、速度高、效益大”,與我國當時的技術(shù)吸納能力有較大差距,還與我國建國以后從蘇聯(lián)和東歐引進技術(shù)的基礎(chǔ)上建立的工業(yè)體系和技術(shù)能力不能有效地匹配和協(xié)調(diào),降低了技術(shù)引進效果,并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如果說后發(fā)優(yōu)勢的發(fā)揮只是一種潛在的優(yōu)勢,其優(yōu)勢的發(fā)揮需要一定的主觀條件,那么,后發(fā)劣勢對于后發(fā)國家來說卻是一種現(xiàn)實存在。納克斯的“貧困惡性循環(huán)論”、利本斯坦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論”均揭示出落后國家(地區(qū))擺脫發(fā)展困境的難度。新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起點很低,缺乏推進經(jīng)濟起飛的必備條件,產(chǎn)生了顯著的“遲發(fā)展效應”。由于我國有著悠久的中央集權(quán)傳統(tǒng),缺乏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需要的內(nèi)在產(chǎn)權(quán)、法治、信譽和文化信仰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基礎(chǔ),在經(jīng)濟發(fā)展中后發(fā)劣勢變成現(xiàn)實存在,尤其在計劃經(jīng)濟的體制優(yōu)勢衰減之后,后發(fā)劣勢愈發(fā)顯著,成為必須突破的發(fā)展障礙。 (三)“趕超困境”:封閉條件下趕超戰(zhàn)略難以為繼 與“體制困境”和“后發(fā)困境”相伴而生的是“趕超困境”。中國歷史上的大國傳統(tǒng)、近代以來的落伍經(jīng)歷、現(xiàn)實中國際競爭和體制競爭的嚴峻壓力以及國家振興的發(fā)展目標,決定了新中國具有強烈的“趕超沖動”。加之當時“以蘇為鑒”,我國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后就確立了趕超戰(zhàn)略。這一戰(zhàn)略的特點是:從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角度看,是一種把重工業(yè)作為突出固定重點的“傾斜發(fā)展戰(zhàn)略”;從經(jīng)濟增長方式的角度看,是一種以增加生產(chǎn)要素為主途徑的粗放發(fā)展戰(zhàn)略;從經(jīng)濟運行機制的角度看,是一種以廣泛發(fā)動群眾為主要動力的經(jīng)濟發(fā)展戰(zhàn)略。趕超戰(zhàn)略的實施,在短短十年之內(nèi),就迎來了20世紀50年代中國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第一個高峰期,現(xiàn)代化實現(xiàn)程度提高了11個百分點。趕超戰(zhàn)略有力地促進了我國工業(yè)化發(fā)展水平的提升,推動建立起強大的國家戰(zhàn)略防御體系,但我國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種戰(zhàn)略執(zhí)行不是市場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各級政府主導下形成的。即以片面追求GDP的增速為目標,不顧一切,采取爭項目、爭投資、爭資源等措施所形成的。在當時相對封閉的條件下,我國缺乏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以填補國內(nèi)發(fā)展缺口的條件,為實施趕超戰(zhàn)略,確立并執(zhí)行了低消費、高積累的政策,這種政策的表現(xiàn)往往是不顧條件,大干快干,導致經(jīng)濟運行大起大落,起伏跌宕。總之,趕超戰(zhàn)略是以資本密集、低就業(yè)能力、資源高消耗、環(huán)境重污染、自我封閉、自我循環(huán)的重工業(yè)為導向的發(fā)展模式,這不符合中國人均資源稀缺、資本短缺、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基本國情,是不可持續(xù)的發(fā)展模式。 二、改革開放的戰(zhàn)略內(nèi)涵:推進當代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戰(zhàn)略體系 如前所述,改革開放是在既有發(fā)展戰(zhàn)略不能適應發(fā)展要求,必須加以改變的情況下展開的,當時,既沒有成熟的理論可資參考,也沒有現(xiàn)成的經(jīng)驗可以照搬,體現(xiàn)出強烈的“試錯性”和探索性。因此,改革開放戰(zhàn)略一開始并不是以完整的體系的形式出現(xiàn)的,而是經(jīng)過了長期的探索才逐漸呈現(xiàn)出較為清晰完整的發(fā)展脈絡。現(xiàn)代戰(zhàn)略的核心范式是“目標(ends)一途徑(ways)-手段(means)”。有鑒于此,改革開放作為推進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國家戰(zhàn)略,其戰(zhàn)略內(nèi)涵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概括:戰(zhàn)略目標,這構(gòu)成制定戰(zhàn)略的方向和統(tǒng)領(lǐng);戰(zhàn)略途徑,這構(gòu)成戰(zhàn)略實施的具體“抓手”;戰(zhàn)略手段,這構(gòu)成與戰(zhàn)略途徑相配套的實施工具。 (一)戰(zhàn)略目標:以實現(xiàn)國家利益為歸宿的發(fā)展目標的動態(tài)演進 國家戰(zhàn)略目標是國家所要達到的戰(zhàn)略預期任務,是一定時期國家利益的集中體現(xiàn),是戰(zhàn)略決策中的關(guān)鍵性因素。戰(zhàn)略目標規(guī)定了一個時期的戰(zhàn)略任務。任務的提出既基于主體的利益訴求,也受發(fā)展的階段性限制。改革開放戰(zhàn)略最初是為了適應時代進步潮流提出的。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這表明,作出改革開放這一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歷史性決策和關(guān)鍵抉擇,既要擺脫我們黨和國家當時所處的嚴重困境,擺脫高度集中的計劃經(jīng)濟的長期束縛,擺脫閉關(guān)自守的封閉狀態(tài),實現(xiàn)從困境中重新奮起,又要順應和平發(fā)展的時代潮流,趕上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參與國際經(jīng)濟合作和競爭。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fā)展,在系統(tǒng)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基礎(chǔ)上,我國的發(fā)展目標日漸清晰:從提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的目標,到新世紀新階段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目標,再到提出對內(nèi)構(gòu)建和諧社會、對外構(gòu)建和諧世界的目標,標志著我們黨對發(fā)展階段性的準確把握和對發(fā)展目標的科學定位。從發(fā)展層次上,改革開放的戰(zhàn)略目標的確立可劃分為:第一個層次,改革開放戰(zhàn)略的根本目標具有整體性,其目標在于使全體人們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做到發(fā)展為了人民、發(fā)展依靠人民、發(fā)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實現(xiàn)中國的國家現(xiàn)代化,實現(xiàn)中國人民的富強文明民主和諧,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第二個層次,改革開放戰(zhàn)略的具體目標具有漸進性,例如,我國經(jīng)濟體制改革目標幾經(jīng)調(diào)整,最終的確立直到黨的十四大才得以解決;第三個層次,改革開放戰(zhàn)略的階段性目標具有差別性,例如,開放之初,我們主要希望實施經(jīng)濟開放,獲取我國現(xiàn)代化建設所需要的資金、技術(shù)和管理經(jīng)驗,但在加入WTO之后,改革戰(zhàn)略具有了全面融入國際社會的內(nèi)涵,而在當前進入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新時期,我們需要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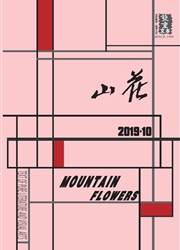

學.jpg)
會計.jpg)
.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