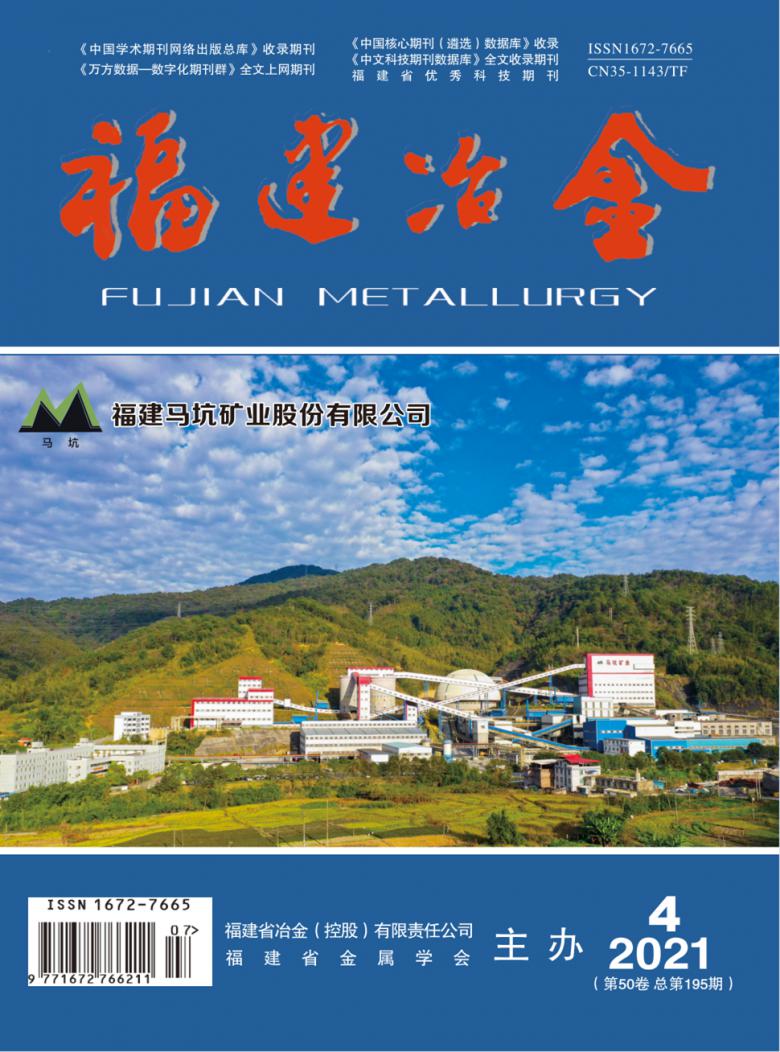試談認識中國歷史的范式
佚名
在當代中國的學術背景上,認識中國歷史的理論前提之一是對于認識范疇和范式的考察。從韓德強先生《重新認識中國歷史》文中可以看出,他對此有著較為清晰的意識。但是,我比較奇怪的是韓先生對一些范疇的使用與一般的用法略顯不同。比如,他說:“在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新王朝建立之初,基本上都有一次土地改革,或者平分,或者承包,使每個家庭都擁有一份土地。這時,有市場經濟,但缺乏大規模的失地農民,也許可以叫做小資產階級社會,甚至可以叫社會主義社會。大體上,經過30、50年后,由于水旱災害、生老病死等各種變故,貧窮的農民只好出賣土地,或流入城市打工,或流入大農場,成為大地主的雇工,社會分化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社會性質就應該是資本主義社會。”[1]很明顯,韓先生這里使用的“小資產階級社會”、“社會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意義和當代漢語中這些詞匯的一般意義不同。在我國學術界一般的使用中,這幾個概念都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學說等近現代社會歷史或經濟學說緊密聯系,都和人類歷史在時間中演進到晚近階段相關。比如,“資產階級”在馬克思的著作中(也是國內學術界的一般理解中)有著清晰的含義,指的是近代以來占有生產資料、剝削工人剩余勞動的階級。而韓先生理解的資產階級指的是中國歷史上任何朝代的“大地主、大商人和大官僚”[2]。就一般意義而言,這兩種理解顯然有著極大的差異,前者顯然不可能包括“大地主”和“大官僚”;即使是“大商人”,也不一定就是是資產階級,象韓先生所舉的范蠡、弦高、呂不韋等怎么也不可能被馬克思和國內外學界視為資產階級。作為成長在這種話語環境的青年學者,韓先生當然清楚這些范疇的這種用法,但他卻在改變內涵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理解來使用這些范疇。從寬和的角度來理解,這種使用也并非完全不可以。但是,我擔心這種使用有時會造成一些概念混淆,不利于思想的清晰表達。實際上,他完全可以用新造或類似的范疇來表達這里想表達的意思。
不過,韓先生這里較為特殊的概念用法從他自己的角度來說有其理論緣由。這一緣由在于他對馬克思的歷史認識范式的一些誤解。或說,這里的概念混淆源僅僅是一種結果,其原因在于其歷史認知范式中的問題。這個問題也就是他僅僅從生產關系的維度而明確放棄生產力的維度上來理解階級和階級關系。對此,他表達得相當清晰明白。比如,在談到資本主義時他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有兩種理解。一種定義是從生產技術的角度定義的。手工磨產生封建主為首的社會,機器磨產生以資本家為首的社會。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完全是工業革命的產物,在此之前,只有地主、領主、奴隸主,沒有資本家。”“原來,馬克思還有另一種定義,即從社會的基本生產關系來定義資本主義的。大體來說,如果一個社會的基本生產關系是奴隸主與奴隸的關系,則該社會是奴隸社會;是領主與農奴制的關系,則是封建社會;如果是資本家與自由雇工的關系,則是資本主義社會。”[3]他認為,根據前一種定義,無法理解馬克思將工業革命前的尼德蘭革命、英國克倫威爾革命等理解成資產階級革命,因為他認為馬克思以為資本主義是由生產力發展到工業革命階段才導致的。所以只有根據后一定義(僅僅考慮生產關系維度)才能將這幾次革命理解為資產階級革命。
我們說,韓先生在此對馬克思歷史觀的理解是不符合理論事實的。因為根據今天我們能看到的文獻,馬克思并沒有認為資本主義是由工業革命導致的。韓先生上文所引 “手工磨”(原文當為“手推磨”)“機器磨”(原文當為“蒸汽磨”)的話只是馬克思用來說明不同的生產力導致不同的生產關的例證。所以這句話的上文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4]這并不證明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由生產力發展到工業革命階段才產生的。實際上,我們略微翻一下馬克思留下的文獻,就可以發現他實際上認為資本主義遠遠早于工業革命產生。比如,他談到分工時說:“工場手工業分工的一個產物,就是物質生產過程的智力作為他人的財產和統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對立。這個分離過程在簡單協作中開始,在工場手工業中得到發展,在大工業中完成。在簡單協作中,資本家在單個工人面前代表社會勞動的統一和意志,工場手工業使工人畸形發展,變成局部工人,大工業則把科學作為一種獨立的生產能力與勞動分離開來,并迫使科學為資本服務。”[5]也就是說,馬克思認為在工業革命前資本主義經歷兩個發展階段:簡單協作階段和工場手工業階段。這兩個階段也就是世界經濟史上經常談到的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的手工工場階段。對于手工工場階段,馬克思本人曾談到:“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在工場手工業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態。這種協作,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具有特征的形式,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占居統治地位。這個時期大約從16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最后30年。”[6]在這個階段,從馬克思的表述可以清楚看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存在且向前演進的,只不過是到了工業革命時期才成熟。因此,韓先生用工業革命階段的生產力水平來定義資本主義的產生并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實際上,如一些世界經濟史著作所描述的,從十四、十五世紀開始,歐洲生產力得到較快的提高,尤其是農業生產力的進步(如輪作、二圃制、三圃制的實行、重型鐵犁的廣泛使用等)相當明顯,這促使封建莊園經濟發生變化,商品市場逐漸發展,并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在一些地區(如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米蘭等)出現。這種生產力的提高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相互促進,直到十八世紀才導致工業革命的產生。因此,以工業革命來解釋資本主義的產生既不符合馬克思的認識,也不符合一般世界經濟史的史實。
實際上,在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解中,他從沒將資本主義理解為可以分別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來定義。在他的理論中,他一直將資本主義理解為包括一定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社會有機整體,他一直將資本關系理解力為一定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比如,他說:“資本關系的形成從一開始就表示,資本關系只有在社會的經濟發展即社會生產關系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的歷史階段上才能出現。它從一開始就表現為歷史上一定的經濟關系,表現為屬于經濟發展即社會生產的一定的歷史時期的關系。”[7]其他生產關系和社會形態也是如此。因此,一定水準的生產力決定一定的生產關系,而這種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也具有反作用。如果一定的生產力水平沒有達到,是不可能產生與它相聯系的生產關系以及建立在這一關系之上或這一關系體現出的階級關系,也就不可能出現和這種生產力及生產關系相聯系的社會形態。而這種理解在馬恩的論述中也有大量支持的證據,比如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的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說:“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8]。又如馬克思說:“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的發展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范疇。”[9]
當然,有人可以不同意甚至激烈批評這種理解,也可以指出它的各種不足和弱點。但對于這種理解的客觀存在及建立在它之上的概念使用我們無疑是應該明白的。從韓先生的表述可以看出,他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認知范式的理解有所了解,但他將這種范式“拆散”后使用,放棄生產力的維度而僅僅利用生產關系的維度,從而使馬克思的社會形態學說“破碎不堪”,這種破碎的歷史認知范式的利用當然會導致認知結果中的邏輯問題和事實偏差,而且他也沒有對于這種“拆散”進行充分論證。具體說來,如果按照韓先生的理解:“中國古代社會各王朝前期,農民從國家分得土地,既可理解為農民直接受雇于國家;亦可理解為農民都擁有私有土地,是自我雇用,只需要向國家交稅,不受地主、領主或奴隸主剝削。”[10]他認為這種時代“倒是接近新中國土地改革后的社會”,并把這樣的時代叫作“小資產階級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我們說,首先這段話來存在著實事方面的問題,中國古代只有北朝、隋唐等幾個頒布過均田制的國家實行過土地的大規模分配,其他王朝的土地分配雖然也有過,但都不足以在社會經濟制度中占據主導地位,漢宋元明清都是如此。這樣一來,似乎只有北朝和隋唐初年是“社會主義社會”或“小資產階級社會”,到了后來這兩種社會又不見了或說自然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了。這樣,這兩種社會也就沒有多少價值了。因為如果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可以自然而然地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至少在馬克思的意義上,這種社會主義的歷史意義不大。而且,如果社會主義社會象中國北朝或隋唐社會那樣,建立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上,廣大人民過著當時水準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受著當時的政治統治和壓迫,并最終會導致農民大起義的推翻,這樣的”社會主義”在今天看來恐怕也沒有多少現實意義和未來意義,恐怕也不會成為人們追求的理想了。
韓先生還說:“在王朝初期,重農抑商政策的確將放慢資本主義社會的到來的步伐,但是,由于市場經濟的兩極分化傾向極其強烈,資本主義社會還是要頑強地到來。從各王朝中期起,以大地主、大商人和大官僚為主體的資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導經濟力量,這種力量最終將擺脫政府的調節,將政府權力市場化、資本化,使社會崩潰。”[11]又說:“恰恰是市場經濟的兩極分化機制,導致了資產階級財富的積累和無產階級人數的壯大。與此同時,權力體系也日益失去制約,權力集中到少數謀求短期私利的權臣、宦官或外戚手中。資本的積累與權力的積聚相互推波助瀾,社會財富完全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中,社會必然崩潰。”[12]這里韓先生提出了考察中國歷史周期性興亡問題的又一種解釋,即市場經濟導致社會的兩極分化,并使權力資本化,最后導致社會崩潰。不過,這種解釋的經驗理由和邏輯理由似并不充足,或者說,仍有進一步補充和說明的必要。其中,最為關鍵的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市場經濟是否這樣發達,足可以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并導致社會崩潰。在我見到的一些材料中,學者們對于中國傳統社會市場經濟功能的估計沒有韓先生這樣“樂觀”,比如方行先生經過各個方面對中國封建社會價值規律作用的探討后得出的結論是:“總之,價值規律對封建社會農民商品生產的促進和調節作用,無疑是不能忽視的。但是,在封建社會的社會生產中,封建租賦和農民自給性產品的生產比重很大,而商品生產的比重很小,價值規律調節社會生產的范圍是很小的,同時,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自然條件以及小農經濟本身,對價值規律調節生產,促進生產技術改進和農民兩極分化的作用,具有種種限制,使它在這些方面對農民商品生產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效果,都受到影響,因此,對它在農民生產中的作用也不宜估計過高。”[13]因此,考慮到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結構的現實情況,過分肯定傳統市場經濟的兩極分化功能是不甚恰當的。那么,到底導致中國傳統社會周期性興亡的原因何在呢?這確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我在此只能給出自己的一點感覺。首先,我們似不應過分強調周期性特征,因為這只我們在回觀歷史時形成的一種大致印象,細致考察起來并不甚準確,或說并不具有歷史發展的嚴格必然性。其次,表現出大致周期性的中國王朝興亡是在由秦王朝確定的國家框架內由兩種因素導致的。其一是民族紛爭導致的顛覆,其二下上相爭導致的顛覆。前者可以由各民族文明之間發展的不平衡來解釋,后者的原因相當復雜,我覺得大致可以由秦暉先生提出的大共同體本位的社會結構導致的壓迫和剝奪來進行某種解釋。[14]總之,我認為韓先生以市場經濟造成的兩極分化導致中國傳統社會崩潰的解釋是不太成功的,至少他還需要更為細密的研究和論證才能使之具備一定的解釋力量。
總結上文所論,我認為韓先生重新認識中國歷史的范式有一定缺陷:既存在一些知識性偏差,又造成了范疇的變異和易于混淆,同時也沒能較好地解釋中國歷史上的重大現象。因此,從總體上來說是成立不了的。
最后,我想談幾句對韓先生整篇文章的三點看法。第一,這篇文章可能不是韓先生深思熟慮、嚴密論證的結果,似乎有些想到哪里寫到哪里、“信馬由韁”的味道。因此,整篇文章的內容和結構都略顯零亂。第二,這篇文章某些地方的論判有些武斷。比如,他將馬克思定位為“資本主義的首席經濟師,甚至是當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首席經濟師”[15],對于這樣一種令人驚異的判斷,他的理由僅僅是因為馬克思肯定過資本和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坦率地說,恐怕沒有幾個人能接受韓先生這種有些機械論色彩且以偏概全的論斷。第三,這篇文章表現出一種較強的努力突破既有成見的勇氣,但可惜的是,知識預備和理論預備似都略顯不足,因此,得出的某些些結論實際上是無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