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以家庭暴力罪為基點(diǎn)透析刑事和解制度
王麗
論文摘要 家庭是社會(huì)組織結(jié)構(gòu)的細(xì)胞,是以婚姻、血緣及共同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為紐帶所組成的共同生活、共同居住的親屬團(tuán)體。家庭內(nèi)部關(guān)系的安寧關(guān)系著社會(huì)的和諧與穩(wěn)定。由于受我國兩千多年封建思想的影響“三綱五常”、“男尊女卑”的這些倫理道德觀念已深入人心,從而使得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婚姻家庭觀念不免打上歷史的印記,同時(shí)也給家庭暴力的形成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家庭暴力無疑是阻礙家庭內(nèi)部關(guān)系穩(wěn)定與和諧的絆腳石,它極大的危害著家庭成員的身心健康、家庭的和睦及社會(huì)的穩(wěn)定。這個(gè)問題已成為全球性關(guān)注的社會(huì)焦點(diǎn)問題。因此,本文從犯罪學(xué)角度論述了家庭暴力的概念和犯罪構(gòu)成,在分析其現(xiàn)狀及成因的基礎(chǔ)上透析我國家庭暴力的解決機(jī)制。因我國立法上的空白,還未將家庭暴力罪以明確的法律條文入罪,且在其量刑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重罪歸罪,輕罪免罰的情況,使得受害人的利益無法得到確實(shí)的保護(hù),出現(xiàn)了權(quán)益保護(hù)缺失的真空狀態(tài)。本文落腳點(diǎn)在于對(duì)家庭暴力罪的訴訟形式進(jìn)行研究,摸索出一個(gè)更好的解決此問題的法律機(jī)制。
論文關(guān)鍵詞 家庭暴力 訴訟模式 刑事和解
一、家庭暴力現(xiàn)狀
我國現(xiàn)行法律中未對(duì)家庭暴力行為做出明確界定,只是根據(jù)犯罪的構(gòu)成要件,歸罪于虐待罪、故意傷害罪、強(qiáng)制猥褻婦女兒童罪等,實(shí)為立法之缺陷。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guān)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釋中采取概括式的方法對(duì)家庭暴力作出規(guī)定,“行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qiáng)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給其家庭成員的身體、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傷害后果的行為。持續(xù)性經(jīng)常性的家庭暴力,構(gòu)成虐待罪。”該司法解釋是目前中國對(duì)家庭暴力行為作為犯罪入刑的唯一的也是最權(quán)威的法律界定。筆者認(rèn)為家庭暴力可以定義為,發(fā)生在具有血緣、婚姻、收養(yǎng)、撫養(yǎng)、贍養(yǎng)、監(jiān)護(hù)等法律關(guān)系中對(duì)家庭成員的身體、人格、尊嚴(yán)、經(jīng)濟(jì)、性方面的合法權(quán)益以各種暴力方式對(duì)其在肉體上或精神上造成巨大痛苦或傷害的行為。 在我國,根據(jù)法律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家庭暴力行為造成受害人重傷以上后果,以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入罪處罰,最高刑種可判死刑;而對(duì)于只造成輕微傷的,至多也就是批評(píng)教育;由此觀之,由于情節(jié)的輕重及主觀惡性不同,處罰的結(jié)果大相徑庭,差距甚大。一種由于后果的嚴(yán)重性,司法機(jī)關(guān)可通過公權(quán)力介入,對(duì)行為人提起公訴,保護(hù)受害人的合法權(quán)益;另一種由于犯罪情節(jié)較輕,影響面較小,亦可通過教化達(dá)到目的。但若受害人長期的,經(jīng)常的受到行為人的暴力行為(即刑法領(lǐng)域中的“親告罪”),他們?nèi)绾伪Wo(hù)自己的合法權(quán)益?因?yàn)榇祟惏讣僮栽V案件,法院遵照“不告不理”的原則,受害人自己不提起訴訟,司法機(jī)關(guān)是不會(huì)主動(dòng)介入的。即使受害人提起訴訟,由于家庭關(guān)系的隱蔽性,取證十分困難,更不要說勝訴了。并且在一些偏遠(yuǎn)地區(qū),受經(jīng)濟(jì)條件的制約,許多受害人往往放棄追訴權(quán),不去尋求法律的幫助。筆者試圖通過這一視角,尋找到解決這一糾紛的有效機(jī)制。
二、我國目前解決家庭暴力犯罪機(jī)制
(一)司法前置 目前,中國的警察機(jī)構(gòu)對(duì)解決家庭暴力雖起到一定作用,但仍然存在諸多問題。由于警察介入的是一些情節(jié)輕微不需要進(jìn)行刑法處罰的案例,它在程序、步驟以及具體的方法上沒有一個(gè)明確的規(guī)定,往往草草了事,加之批評(píng)教育即可,沒有達(dá)到合理有效的保護(hù)受害人的目的,一定程度上還可能造成更大的損害。另外,警察出警的消極被動(dòng)觀念,認(rèn)為家庭暴力屬家庭內(nèi)部糾紛,是可以通過成員間自己就可解決的。但是,警察卻忽略了婦女、兒童和老年人在家庭中處于弱勢(shì)地位,是不可能通過自身調(diào)解可以解決的。 (二)訴訟模式 對(duì)于家庭暴力所造成的后果不同,可以選擇和解模式,也可以選擇訴訟模式,但若自訴人提起訴訟又存在諸多困難:(1)取證難。因?yàn)榧彝ケ┝κ前l(fā)生在家庭內(nèi)部之間的,本身具有隱蔽性,證人證言難以獲取;(2)舉證責(zé)任不合理。受害人一般處于家庭弱勢(shì)地位,更不要說舉證責(zé)任了;(3)證據(jù)易毀損丟失。因?yàn)榧彝ケ┝Χ嗍峭话l(fā)性,對(duì)行為實(shí)施的過程、結(jié)果難以保存相應(yīng)的證據(jù);(4)證據(jù)不充分。因受害人法律意識(shí)欠缺,不能及時(shí)在鑒定機(jī)關(guān)作出驗(yàn)傷證明,在醫(yī)院發(fā)開的診斷書中也未注明是由家庭暴力所致,法官常以證據(jù)不足為由,駁回訴訟請(qǐng)求;(5)判決賠償數(shù)額的不可罰性。家庭暴力所引發(fā)的輕微刑事犯罪,即使判決書認(rèn)定有罪并要求作出相應(yīng)賠償,也是空頭支票,因?yàn)槲覈?guī)定婚后夫妻財(cái)產(chǎn)共有制,就無所謂賠與不賠的問題;(6)對(duì)于沒有造成嚴(yán)重后果和進(jìn)行口威脅或者冷暴力犯罪排除在外。 基于以上觀點(diǎn)分析,在不排除訴訟模式的前提下,我們要探索一條更適合解決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律機(jī)制。
三、中國司法實(shí)踐中的刑事和解模式
鑒于家庭暴力犯罪的特殊之處,衡量各種解決糾紛方式的優(yōu)劣,在保證合理有效的維護(hù)受害人合法權(quán)益的前提下,規(guī)避訴訟中存在的諸多困難,在現(xiàn)行的基本刑事制度的基礎(chǔ)上應(yīng)該根據(jù)我國的政治、經(jīng)濟(jì)發(fā)展?fàn)顩r,創(chuàng)設(shè)出適合我國國情的刑事和解制度,讓它在最大范圍內(nèi)發(fā)揮更大的作用。 (一)刑事和解概述 由于國內(nèi)學(xué)者對(duì)刑事和解制度研究情緒的高漲,存在諸多意見,未形成統(tǒng)一觀點(diǎn)。比較通行的觀點(diǎn)認(rèn)為刑事和解一般是在犯罪發(fā)生后,由中間人(調(diào)解人)對(duì)被害人和行為人作出“斡旋”,使得雙方可以直接商談,解決糾紛或者沖突的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就是為了最大程度內(nèi)修復(fù)雙方所破壞的家庭關(guān)系,彌補(bǔ)被害人所受到的傷害,并且使行為人改過自新,重新回歸社會(huì)。
(二)刑事和解的理論基礎(chǔ) 在我國,和解其實(shí)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tǒng)的積淀,有些學(xué)者將其概括為“和合”文化。和合文化的精髓可概括為兩個(gè)方面,第一是人與自然的保持“和合”的關(guān)系,人要順應(yīng)自然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與自然融為一體,所謂“天人合一”;第二是人與人之間要保持“和合”的關(guān)系,注重社會(huì)關(guān)系的和諧與穩(wěn)定,避免糾紛。而孔子則把“無訟”視為古代審判活動(dòng)所追求的最高標(biāo)準(zhǔn),積極促成爭(zhēng)議雙方和解,是讓雙方相互退讓最終達(dá)成一致。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和合文化其實(shí)蘊(yùn)含著寬恕、博愛的理念,十分推崇和緩、寬容的解決方式。刑事和解制度恰恰吸收了這一思想內(nèi)涵,在和合文化理念的基礎(chǔ)上生根發(fā)芽。
(三)刑事和解的政策導(dǎo)向 自《刑法修正案八》出臺(tái)以后,使我們更加明確了“寬嚴(yán)相濟(jì)”的政策導(dǎo)向。對(duì)于一些暴力性,組織性的重罪,我們堅(jiān)決實(shí)行刑罰處罰,在量刑上堅(jiān)持從重原則;而對(duì)于一些輕微刑事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或是偶犯且危害程度不大的,國家更多的傾向于輕刑。另外,細(xì)看刑事訴訟法不難發(fā)現(xiàn)有諸多法條透析著這一思想,例如:“對(duì)于犯罪情節(jié)輕微,依照刑法規(guī)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免于刑事處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做出不起訴決定”即“酌定不起訴”。雖然我國目前還沒有一套完整的刑事和解制度,但在司法實(shí)踐中刑事和解制度卻彌補(bǔ)了訴訟體制的不足,使之更為公平,更為迅捷。對(duì)司法機(jī)關(guān)來講,也減輕了工作的重?fù)?dān),節(jié)約了司法資源,提高了訴訟效率;對(duì)當(dāng)事人來講,更加公平合理,操作性強(qiáng)更強(qiáng)。
四、家庭暴力犯罪的刑事和解模式
(一)主觀條件 第一,犯罪人自認(rèn)是刑事和解的先決條件。自認(rèn)意味著犯罪嫌疑人承認(rèn)家庭暴力行為是自己所為,認(rèn)識(shí)到加害行為對(duì)被害人的實(shí)際危害。刑事和解是為被害人提供疏通被阻滯情感的渠道,如果沒有加害人有罪答辯的先決條件,就無法達(dá)到預(yù)期的設(shè)計(jì)效果。第二,雙方當(dāng)事人同意是刑事和解的核心條件。在一起家庭暴力案件中,夫妻雙方的感情破裂,無論被告人怎么樣認(rèn)罪道歉,被害人始終不同意任何賠償,只想讓被告人受刑處罰。此時(shí),和解程序無法啟動(dòng)。所以,被害人的同意極其重要,必須保證被害人的同意是被害人真實(shí)的意思表示,從而保證被害人表達(dá)真實(shí)的和解意愿,免于被強(qiáng)迫或者誘騙。同樣地加害人的同意也很重要,對(duì)于加害人來說,如果違背其自由意志,使其非自愿地參加到和解中來,則不利于保障犯罪人的基本人權(quán),不能使其真正地悔罪認(rèn)錯(cuò)。達(dá)不到矯正的目的。 (二)客觀條件 刑事和解制度的客觀條件主要是指案件的事實(shí)及證據(jù)。由于家庭暴力行為往往發(fā)生在家庭內(nèi)部具有隱蔽性,如果沒有出現(xiàn)重傷亡的情況,相關(guān)司法機(jī)關(guān)是很難主動(dòng)介入的。所為在具體實(shí)際操作中,大致以基本查明案件事實(shí)為最低限度要求。即家庭暴力行為已經(jīng)發(fā)生,加害人就是犯罪行為人。至于證據(jù)方面,由于其自身缺陷,使得取證工作具有很大難度,所以不能以是否取證,證據(jù)是否充分,作為能否啟動(dòng)和解制度的關(guān)鍵。 (三)中間調(diào)解人 作為刑事訴訟的一項(xiàng)制度,和解制度本身也有著一套從立案到執(zhí)行的司法程序,但讓誰來擔(dān)當(dāng)“中間人”這一角色呢?根據(jù)對(duì)家庭暴力犯罪的分析,司法機(jī)關(guān)很難積極介入,加上“家丑不可外揚(yáng)”的思想在大眾心中根深蒂固,不愿擺到“公堂”上說,但為了解決此類糾紛,同時(shí)保證雙方的利益得到有效維護(hù),我們可以選擇人民調(diào)解模式,在保證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又能使雙卻方當(dāng)事人“不失臉面”達(dá)到解決糾紛的目的。 人民調(diào)解模式是指在人民委員會(huì)的主持下,以國家的法律、法律、規(guī)章、政策、輿論道德為依據(jù),對(duì)輕微的家庭暴力案件的當(dāng)事人進(jìn)行說服教育,規(guī)勸疏導(dǎo),促使糾紛互諒互讓,平等協(xié)商,自愿達(dá)成一致后,制作協(xié)議書,經(jīng)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huì)審查簽字之后生效的一種新型的人民自治活動(dòng)。我國《婚姻法》第43條、45條明確規(guī)定“實(shí)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家庭成員,受害人有權(quán)提出請(qǐng)求,居民委員會(huì)、村民委員會(huì)以及所在單位應(yīng)當(dāng)予以勸阻、調(diào)解”,“對(duì)重婚的,對(duì)實(shí)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構(gòu)成犯罪的,依法追求刑事責(zé)任。受害人可以按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guān)規(guī)定,向人民法院自訴;公安機(jī)關(guān)應(yīng)當(dāng)依法偵查,人民檢察院應(yīng)當(dāng)依法提起公訴”。由此可見,在我國現(xiàn)行刑法中,人民調(diào)解制度和訴訟制度已經(jīng)有了有效銜接,表面看來,針對(duì)此類案件的刑事私法化有可能存在弊端,但真正探析案件的實(shí)質(zhì),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種方式的優(yōu)越性。在此,必須說明人民調(diào)解只是和解過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刑事和解還應(yīng)包括對(duì)案件事實(shí)的審查,監(jiān)督等最終處理。 我們應(yīng)當(dāng)看到,目前在我國建立刑事和解的人民調(diào)解模式,雖然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礙,但在司法實(shí)踐中許多問題需要解決。例如:人民調(diào)解制度的定位,人民調(diào)解的職能范圍,專職調(diào)解員的資格認(rèn)證,調(diào)解協(xié)議效力的界定,人民調(diào)解制度與訴訟制度的有機(jī)銜接等一系列問題需要進(jìn)一步細(xì)化。
.jpg)
工作研究.jpg)

州文化研究論叢.jpg)
略研究.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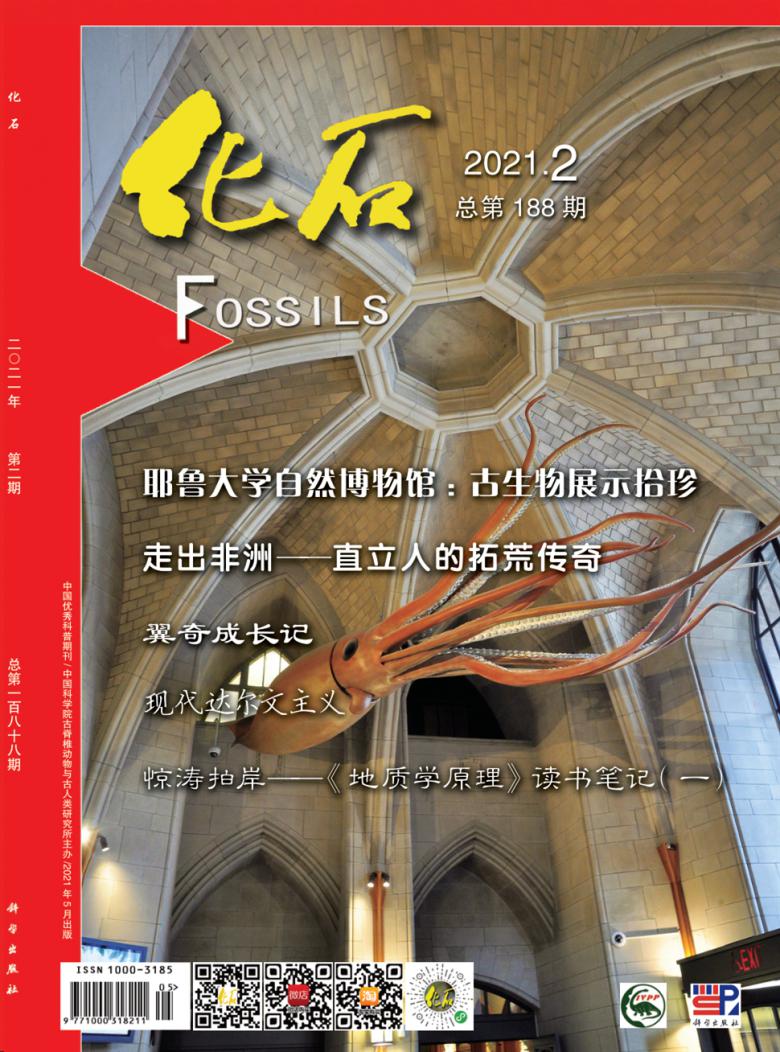
于我們.jpeg)